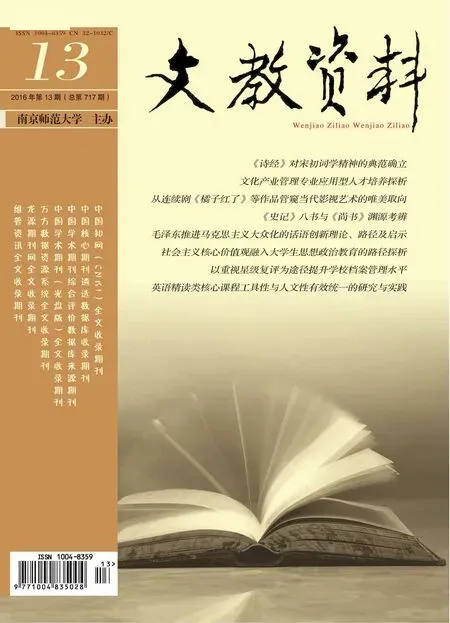《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的家庭暴力与女性成长
唐瑞娟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安徽 巢湖 238000)
《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的家庭暴力与女性成长
唐瑞娟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0;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安徽 巢湖238000)
摘要:安吉拉·卡特是二十世纪英国以独特叙事魅力著称的女性主义作家,毕生为“解构父权制神话”而写作。她通过形式风格多样的作品探索女性生存、命运和发展,试图改变被父权制扭曲压制的女性形象。《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是卡特选编的围绕女性叙事的民间童话故事集,渗透了其睿智鲜明的女性观。本文仅通过其中几则关于家庭暴力的故事,分析卡特通过披露家庭暴力源起的真相传达的反抗男性霸权压迫的思想。
关键词:民间童话故事家庭暴力女性成长女性主义
安吉拉·卡特是当代英国个人风格、思想最强烈独特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充分调动所有感官,用整个身心细致深刻地感受,思考她要表达的一切,突破表象和陈规,将对外部世界的印象和内心世界的体验深思自然地糅合起来,极尽所能地利用陌生化的创作手法,构建意象繁复、观念敏锐的个人语言王国。卡特生于女性主义蓬勃发展的二十世纪中后期,一个女性迅速觉醒成长的时代,其创作持续深刻关注女性生存困境、命运悲欢和两性互动。卡特十分钟情童话体裁,她深知童话作为人类最初的文化启蒙,如何深刻长久地影响着两性对彼此、对世界的认知和行为。她广泛搜集、选编、译介,并改编了一系列童话,力图从源头上重新塑造女性成长轨迹,探索如何消解男权社会给女性设下的思维陷阱。“与人为虚构的人类经验一样,传统女性经验的普遍性、确定性与统一性,亦是传统男性社会在两性权力关系中设置的大胆骗局”[1]。如何揭穿解构这骗局重构价值体系是卡特一生的追求。
《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是卡特弥留之际选编的民间童话故事集,由1990年出版的 《悍妇精怪故事集》(The Virago Book of Fairy Tales)和1992年出版的《悍妇精怪故事集第二卷》(The Second Virago Book of Fairy Tales)合成。“Virago”在英文中指的是英勇、可效仿的女性,汉语中“彪悍”一词或许可以略表卡特的深意。她呈现没有被父权制扭曲驯化的女性形象,机智、勇敢、坚韧,主动积极地开创和掌控命运,无论善恶,都不是屈服顺从,没有个人意志的牵线木偶。“倘若女人具有男人般的意志,有太多的胆量和智能,男人便会惊恐不已,诅咒她们是妖女、悍妇”[2]。总之,不合男权标准的女性便是“悍妇”了。
“这些故事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围绕某个女主人公,不管她是聪明、勇敢、善良,还是愚昧、残酷、阴险,也不管她有多么不幸,她都是故事的中心,和真人一样鲜活”[3]7。与之前卡特对一些经典童话大刀阔斧的改写不同的是,这本故事集是没有经过改写和删节的,因为“想保留各种不同声音带来的效果”[3]14。但正如故事集的引言中提到的:“人们搜集故事不仅牵涉阶级、性别,还牵涉采集者的性格”[3]13。卡特承认“采集者或者翻译人的性格必然会侵入故事中”[3]14。她将女性从幕后带到了前台,精选了围绕女性的叙事,探索了女性的生存经验、情感和婚姻,渗透了自己的女性观。
故事集中的女性形象多样,主题亦广阔多元。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浪潮中,家庭暴力问题日渐成为女性关注和斗争的焦点之一。据调查,“英国被害妇女中近乎半数是遭其配偶或情人杀害的”[4]。这样触目惊心的事实,这样的时代背景,卡特必然对家庭虐待和暴力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本文仅通过其中几则关于家庭暴力的故事,分析卡特通过赤裸裸地披露家庭暴力源起的真相传达的反抗男性霸权压迫的思想。这几则故事中的女性从毫无反抗意识地被动挨打,到得到他人的救援,从逃离被欺凌的命运坚持自我拯救,再到彻底消灭把女性的生命当草芥的恶徒,带给女性读者的是开悟和教化。
1.幸运逃脱暴力的女性
《打老婆的理由》用诙谐巧妙的方式讽刺了某些暴力行为完全是男性为了达到主宰女人的目的而导致的。故事中,两个朋友见面交流,其中一个挑唆另一个打老婆,哪怕她是“良家闺女”[3]469,没有任何过错,“她每件事都做得合我心意”[3]469。当第二个人找不到理由时,第一个人教给他一条理由:“你去买一大堆鱼回来,拿去给她说:把鱼做好,因为我们请了客人吃晚饭,然后你就出门。过一会儿等你回到家,不管她烧了什么,你都说你要的是另一种烧法。”[3]469第二个人采纳了他的建议。贤惠周到的妻子因为丈夫没有明确交代就准备了各种做法。“快开饭的时候,年幼的儿子在桌子旁边的地上拉了一泡屎”[3]470,而她来不及打扫,便把盘子盖了上去遮丑应急。当丈夫刻意刁难地提出种种要求,妻子一一满足时,最终困惑无奈的丈夫再也说不出要什么,冒出“我要一坨屎”[3]471的昏话,“妻子立刻掀开地上的盘子,说:‘在这儿呢!’”[3]471似乎永远也不能满足丈夫无理要求的难题被有如神助的妻子一一化解了。故事在令人哄笑的高潮处结束,在轻快的喜剧氛围中讥讽了男人无理取闹制造理由打老婆、压迫女性的阴谋。那么现实中的妻子们呢?能这般无灾无祸地躲开某些通过故意找茬否定、贬低女性价值以树立男性权威的伎俩吗?故事用一坨屎的隐喻揭露了有时虚弱不堪、漏洞百出的所谓男性权威,以及很多女人无缘无故被家暴的理由是如何荒诞和阴暗。不合男人心意便要挨打,即便如意也要将一篮子鸡蛋挑剔成一篮子骨头,于是故事中的男人给东不要给西不要,终于只好得到一篮子骨头——“一坨屎”了。
2.得到拯救的女性
《七次发酵》讲述了一个老妇人拯救了两个被家暴的妻子的故事。老妇人碰到的第一个毒打妻子的男人苏丹是因为妻子不能生育。怎样毒打呢?“男人拿来了这么大一捆棍子,然后打了起来——哪儿最疼来着?他打着妻子的肋骨,把棍子都打断了”[3]475。“最后把一整捆棍子都打折了”[3]475。老妇人出谋划策让妻子假装怀孕,最终不动声色地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法从外面抱了一个孩子充当苏丹的妻子生的孩子,帮她摆脱了被例行毒打的悲惨命运。不能生育便要挨打甚至有生命危险,女性本质上只被视做生孩子的工具,古往今来在现实中因为各种生育问题受欺受责的女性素来连最基本的人身权利也得不到保障,更遑论其他种种权益。生育这一项本是女性天赋独有的权利却成为灾祸的源头之一。老妇人似乎计谋圆满,但解决方式实属无奈。
老妇人遇到的第二个妻子同样没有任何说得上的罪过,她将丈夫带回家的一串黑葡萄装在灰白色的大平盘里,只说了一句:“黑色加在白色上多漂亮呀!”[3]479便被丈夫怀疑“养了个黑奴做情人”[3]479。即使抗议只是指葡萄,仍不被信任并遭毒打。老妇人让妻子再一次用灰白色大平盘装葡萄,并在其丈夫面前做了同样的评论。丈夫终于意识到妻子的背叛不忠仅是自己的猜疑,于是停止了无端的虐待。同样一个观点从他人和从自己妻子口中说出带来的反响竟如此迥异。而现实生活中,男性常常会本能地轻视自己的妻子,认为女性是缺乏理性智慧的次等客体,对妻子和他人表达的相同言论采取不同态度。
“在男性文本中,‘老妇’常常是一个被否定的对象,她的经验、精明、智慧与少女的天真、无知、温顺形成鲜明的对比”[2]。她们要么被完全驯化用男性价值体系衡量对待女性,成为男权的帮凶帮着男人压迫女性;要么成为公正的智者,作为年轻女性的引路人帮着她们摆脱被无理伤害的厄运。故事里救妻子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妇人足智多谋,见多了男性欺侮女性的手段和伎俩,秉着女性团结互助才可以改善和救赎命运的态度扮演着济世的角色。
3.主动逃离暴力的女性
《两个找到自由的女人》中,面对心胸狭窄,一心要控制妻子一切,不符合其一点心意便要虐打妻子的丈夫,与前两则故事中百般迎合丈夫无理要求或被动得到拯救的女性不同的是,两个女人主动选择逃离,她们筋疲力尽,走投无路,逃进一只死去的巨鲸的肚子里,无论丈夫怎么呼唤她们也不肯出来,哪怕鲸鱼的尸体恶臭熏天,“但是臭气总比挨打强”[3]285。她们从此一直安居在鲸鱼的尸体里,“有足够的东西吃——不管有多腐烂——也有暖和的地方睡觉。据说她们在新家里过得非常幸福”[3]285。这样夸张的结局反衬了妻子在毫无尊严的婚姻中身心的痛苦,更突出了女性反抗被控制、被欺凌命运的决心,即使经济不能独立、温饱不济,也要得到基本的人权和自由。死去的鲸鱼尸体隐喻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狭小贫瘠的生存空间,展露了经济的不平等给女性带来的困顿。这两位妻子的丈夫想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这并没有办法保障幸福,那种将妻子当做私有财产或者说没有灵魂的物品任意处置、随意侵犯的男性霸权思想只会导致女性群起突围,彻底摆脱约束和枷锁。君主也要有子民才可以行使统治权,于是她们出走了,在无法改变、调和两性关系的情况下选择了彻底的放弃。
4.向施暴者复仇的女性
《狐先生》里的男主人公杀害女性的罪行是一切家庭暴力升级到顶峰的必然结果,这篇故事类似1979年卡特改写出版的黑暗系童话《染血之室》。狐先生不断以热情富有的虚假表象引诱一个又一个天真无辜的姑娘成为他的囊中物,又以残忍的手法置她们于死地。那些遇难的妻子们象征着蒙昧、毫无危机意识的传统女性。当然卡特式的女主人公不会嗅不到血室内的凶险,她善于观察、思考不同寻常的蛛丝马迹,质疑狐先生没有邀请她或兄弟前去拜访。她毫不理会未婚夫的警告,去了她未曾被邀请涉足的城堡——他的家。她的洞察力令她看到了罪证,亦看到了凶险的残害过程。玛丽小姐毫无惧色地当面揭穿了狐先生,并联合亲友除掉了他。狐先生为何要杀害漂亮姑娘们呢?虽然故事没有明示,但可以推想,她们是他不断寻找下一个姑娘满足其财色需求的绊脚石,他完全无视女性的生命权,现存的社会体制道德准则通常不能容忍其对待女性集邮癖式的贪婪私欲,他便杀害她们以绝麻烦和后患。卡特毫不留情地展示着社会真相,拒绝让童话戴着温情脉脉的面纱,即使它主要是给孩子们的读物,因为她知道,现实有时比故事更复杂、更隐蔽、更残酷,生活在温室中的儿童被瞒得太多会终究难以承受现实的冲击。
5.觉醒之路被阻断的女性
《丈夫如何让妻子戒掉故事瘾》中的丈夫厌恶妻子爱听民间故事的癖好,正如一切希望妻子头脑简单、驯顺、易摆布的丈夫们,他们作为男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当然千方百计地阻止女性思想的启蒙和开化,“他不住地打妻子,弄得女人憎恨故事,再也不听了”[3]287。一切独立自主的革新都是从受压制的对象“悍妇”们发出不讨喜的声音开始的,被以各种暴力形式排斥在知识文化边缘的女人们失去了接触思想和表达理念的机会,丧失了思考能力和抗争的觉悟,便只有无边的沉默和被持久压迫的命运了。
6.结语
“男性会寻找许多借口殴打配偶,以保证其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对配偶的暴力行为是迫使妇女对男子处于从属地位的重要社会机制之一”[5]。读者从这些故事中看不到有哪一条虐待残害女性的理由是名正言顺的,只看到荒谬和无理残酷。然而给女性的启示却十分鲜明,只有实现经济、精神、思想和行动上的独立自主,才有希望摆脱暴力生活。
卡特一生不乏革新意义突出的大胆作品,在最后的生命旅程中将主要精力放在民间童话上,颇有些返璞归真,想必她意识到通常底层的女性受到的压迫和规训最严重,比起宏大、抽象、遥远的女性叙事女权理论,民间童话这样短小精悍的通俗文学体裁更容易被底层广大普通女性接近。这些关于家庭暴力的故事蕴含的朴素民间智慧传达了卡特的忧思,没有男性观念的颠覆,没有女性的觉醒与抗争,女人们的无妄之灾不会结束。没有深切的自省和成长,女人们的命运难以改善。
参考文献:
[1]黄炜芝.安吉拉卡特的重构童话文本研究[D].广东:暨南大学比较文学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4.
[2]罗婷.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3](英)安吉拉·卡特.郑冉然,译.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黄列.家庭暴力:从国际到国内的应对[J].环球法律评论,2002:104-114.
[5]郑玉敏,李波.针对女性家庭暴力的女权主义解读[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3(3):3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