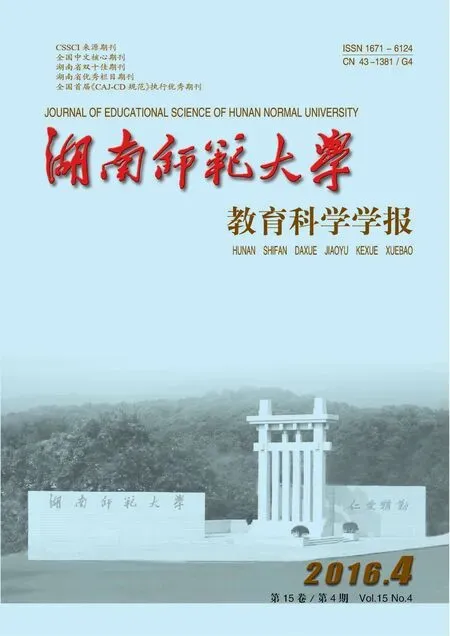普罗塔戈拉论公民教育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普罗塔戈拉论公民教育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普罗塔戈拉是古希腊雅典时期最为著名的教育家,他第二次到雅典施教时,遇到苏格拉底用雅典民主的公民德性难题向他发难。普罗塔戈拉就教育问题即时发表了一段论说,对苏格拉底的发难给出了漂亮的回答。他巧妙地驳倒了雅典民主的自以为是,并论证说,即便是民主城邦的公民,其政治德性也来自惩戒性教育。普罗塔戈拉用惩罚来界定政治教育的本质,暗含的意思是,公民的政治德性其实来自城邦的立法。公民在德性上的资质参差不齐,如果要让公民们在德性上向“好”品德看齐,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立法”。通过解读普罗塔戈拉的这段论说,两千多年前的普罗塔戈拉对教育的看法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
柏拉图;普罗塔戈拉;公民教育;政治德性;民主政制
普罗塔戈拉不仅是古希腊雅典时期最为著名的教育家(不是之一),史称收费办私学的第一人,也是西方文史上的要人,智术师派的代表。然而,他的教育观并没有直接的文献流传下来①。所幸的是,柏拉图的对话作品《普罗塔戈拉》记叙了普罗塔戈拉第二次到雅典施教时的一段经历,其中有他关于教育的长篇论说(323a5-328d2)②。尽管这段论说经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双重转述,不能算普罗塔戈拉的原作,却有可能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其教育思想的精粹,因为,这段论说是普罗塔戈拉对苏格拉底质询他的教育理念所作的回答。
认识两千多年前的普罗塔戈拉对教育的看法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吗?通过细读普罗塔戈拉的这段论说,我们将会看到,普罗塔戈拉的教育观具有让人意想不到的现实意义。
一、普罗塔戈拉在雅典施教面临的政治困境
《普罗塔戈拉》中的普罗塔戈拉关于教育的长篇论说有一个具体的语境,我们必须首先清楚了解这个语境,才可能理解普罗塔戈拉所谈的对教育问题的看法。
普罗塔戈拉来到雅典的第二天,有个名叫希珀克拉底的雅典青年一大早敲开苏格拉底的门,请求带他去见普罗塔戈拉,引荐他做普罗塔戈拉的学生。希珀克拉底并没有把苏格拉底视为老师,而是仅仅希望苏格拉底将自己引荐给外国来的老师。他与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还没有能力分辨什么样的人才是够格的老师。
苏格拉底把希珀克拉斯领到普罗塔戈拉下榻的雅典富豪卡利阿斯的院子时,那里已经有一大堆人:除普罗塔戈拉和跟他来的十来号学生外,还有另外两位外国来的老师(雅典人称他们为“智术师”)和他们的学生们。于是,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戈拉即将展开的是一场面对众多年轻人的公开对话——既有外国来的年轻人,也有雅典城邦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不能因此断定,柏拉图记叙这场对话的基本意图是教育年轻人,让他们学会辨识老师。毋宁说,柏拉图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教育老师。毕竟,要求年轻人学会辨识老师,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也不符合人性的要求。反之,对老师的品德提出总哪怕是有些过高的要求,也并不过分。
普罗塔戈拉先让苏格拉底当着所有在场的人的面说,为什么带希珀克拉底来找他。苏格拉底简扼地说,这位年轻人希望做普罗塔戈拉的学生,因此想先了解一下,自己成为学生后结果会怎样。苏格拉底要求普罗塔戈拉具体回答,他作为老师能在哪方面让年轻人“变好”。普罗塔戈拉回答说:他要传授的不是“什么算术以及天文、几何、音乐”之类的技艺,而是“持家方面的善谋,亦即自己如何最好地齐家,以及治邦者方面的善谋,亦即如何在治邦者方面最有能耐地行事和说话”(318d5-319a2)。显然,普罗塔戈拉并没有把自己看作如今大学中那类教各种专业课的教师,而是近似于我们教政治课的教师。谁都知道,这类课程不是要传授具体的专业学科知识,而是要“造就好城邦民”。
不过,这里的所谓“城邦民”的含义颇为含混,既可以指普通公民,也可以指政治家。比如说,在君主政体或贤良政体中,“城邦民”的含义是“臣民”,所谓“政治家”只会是某一个人或少数人——按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他们应该是德性优异的人。如果说一个人具有诸如“正义”“虔敬”之类的德性就可以算好“臣民”的话,那么,一个人具有诸如“正义”“智慧”“节制”“勇敢”之类的德性才可以算好“君主”或政治家。换言之,政治共同体对治邦者的德性要求远远高于对公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是在民主政体中,“城邦民”的含义就直接等同于“政治家”,因为,按照民主的原则,每个“城邦民”都有参政的政治权利。
倘若如此,普罗塔戈拉当众宣称自己是培育好政治家的教师,他心目中的培育对象究竟是少数天素优异的人呢还是都有参政的政治权利的每个“城邦民”呢?我们看到,普罗塔戈拉的表述很含混:他既说自己传授的“技艺”涉及“如何最好地齐家”——如何当好家长,这显然指的是教育少数天素优异的人;但他又说自己传授的“技艺”涉及“如何在治邦者方面最有能耐地行事和说话”——这听起来像是说他要教育的是有政治权利的每个“城邦民”。
为什么普罗塔戈拉要回答得如此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我们可以这样来推测:普罗塔戈拉赞同的是君主政体或贤良政体原则,即政治共同体当由少数天素优异的人来实行统治——但是,眼下他在实行民主制的雅典,如果他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就会被视为民主政体的敌人遭到迫害或被逐。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马上改口说,自己要教的是“如何在治邦者方面最有能耐地行事和说话”。这里的“治邦者”指的是民主政制中的城邦民,由于他们有参政的政治权利,他们个个都需要“有能耐地行事和说话”的能力。
我们的推测马上得到证实:苏格拉底敏锐地听出了普罗塔戈拉在自我介绍时的含糊其辞后,随即表达了两点困惑,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追究普罗塔戈拉的含糊其辞。第一点,苏格拉底说,在实行民主政制的雅典,城邦民并不需要普罗塔戈拉这样的讲政治课的教授。因为,民主政制让每个公民都自以为是政治家,或者说自以为有政治德性——比如说政治“智慧”。苏格拉底举例说,民主的雅典通过召开公民大会来决定公共事务,如果讨论的是造船或建房,雅典人仅允许懂木匠手艺的人发言。谁都知道,造船或建房需要懂精工技艺,要掌握任何精工技艺则需要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如果要成为巧匠,除了学习和训练还需要天分,毕竟,并非每个学习木匠手艺的人都会成为好木匠(巧匠)。但是,苏格拉底接着说,当讨论城邦事务时,雅典人允许所有人发言——如今叫做“有话大家说”。这表明,雅典城邦的民主政制预设,治理城邦需要的不是技艺,而是“智慧”之类的政治德性。既然雅典城邦允许所有公民在政治问题上发言,无异于预设所有公民都有治理城邦所需要的“智慧”之类的政治德性(319b5-e1)。
苏格拉底的第一点困惑可以这样来归纳:民主政制的公民无需谁来实行政治德性教育。苏格拉底的第二点困惑则表述得非常简洁明确,无需归纳:“即便我们最智慧、最优秀的城邦民,也没法把自己具有的德性传授给其他人”(319e1-320b5)。苏格拉底仅举伯利克勒斯这位民主政制的领袖人物为例,说他虽然“本人是个智慧人”,却不教自己的儿子成为有智慧的人,也没把儿子们托付给其他有智慧的人去教育,他似乎懂得,“智慧”之类的政治德性没法教,这是一个人的天性带来的东西,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虽然苏格拉底表达的两个困惑是在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追究普罗塔戈拉的含糊其辞,但他毕竟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普罗塔戈拉实际上不赞同民主政制的预设。事实上,苏格拉底当众表达的两点困惑同样含糊其辞:第一个困惑通过对比雅典人在对待公共事务时的不同态度实际上质疑了雅典民主政制的预设,但他的表述听起来仅仅是个困惑而已。不仅如此,苏格拉底表达的两个困惑自相矛盾:既然伯利克勒斯也没法把自己的政治“智慧”传授给自己的儿子,雅典公民自以为有政治“智慧”从而无需谁来教他们具有政治“智慧”就是荒谬的。这无异于说,民主的“参政”原则是荒谬的,除非人们认为,雅典公民人人天生就有“智慧”之类的政治德性——但这显然违背常识。
我们同样可以推测,苏格拉底表达的前一个困惑其实是假的——雅典公民无需谁来实行政治德性教育,仅仅是民主政制的一种预设而已,并不真实。毕竟,雅典公民人人天生有“智慧”之类的政治德性的观点明显太过违背常识。换言之,苏格拉底很可能与普罗塔戈拉一样赞同的是君主政体或贤良政体,但身为雅典公民,他不能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异见”。苏格拉底表达的第二个困惑才真正是对普罗塔戈拉的自我介绍提出的质疑:既然“智慧”之类的政治德性是少数甚至极少数人天生的,而非由某个“智慧人”传授的,普罗塔戈拉宣称自己是教政治“智慧”的教师就并不可信。
倘若如此,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在表达困惑时非常地道地替普罗塔戈拉隐藏了其不敢明言的政制观。但是,这两个困惑又的确当众给普罗塔戈拉出了两道考题。必须注意,苏格拉底表达的困惑并非仅仅是说给普罗塔戈拉听的,也是说给在场的其他所有人——尤其是一同来的希珀克拉底和三位智术师的众多学生们听的。反过来说,普罗塔戈拉的解惑同样并非仅仅说给苏格拉底听,也得说给在场的其他所有人听。由此可以说,苏格拉底的两个困惑要考的是普罗塔戈拉作为老师的言辞能力。普罗塔戈拉当然懂得,在所有人间事务中,治理城邦最难,无论处理内乱还是应对外敌的挑衅,需要何等的智慧、正义、节制和勇敢德性!在民主的雅典,普罗塔戈拉不敢明说,雅典公民个个自以为有政治“智慧”是荒谬的,否则会犯政治不正确的错误。另一方面,在眼下的场合,普罗塔戈拉又不敢明说,“智慧”之类的政治德性来自极少数人天生具有的资质,这种资质需要培育,因此需要他这样的“智慧人”来施教——否则,那些跟随他的学生乃至在场的所有年轻人该如何解释自己追慕老师的行为呢。毕竟,在场的所有年轻人未必个个有优异的自然资质。
普罗塔戈拉的困境更在于:眼下的场合还有另外两位智术师在场——无论对于身在民主雅典的处境还是面对众多年轻人的处境,普罗塔戈拉事实上都可以用似是而非的言辞来掩护自己和糊弄年轻人。但是,如果他不说出自己的真实见解,他就会在苏格拉底和另外两位智术师面前丢份。
只有充分理解了普罗塔戈拉面临的困境,我们才能看到普罗塔戈拉作为老师在修辞方面的卓越。我们必须记住两点:首先,普罗塔戈拉关于教育的长篇论说涉及的是政治德性的教育问题——他当然认为“智慧”之类的政治德性是可教的,否则他来雅典就是荒唐之举。第二,在眼下的场合,他不能把为何“智慧”之类的政治德性可教的道理直白地讲出来。这样一来,如果他要讲清楚政治德性可教的道理,就不得不用高妙的言辞来表达。
苏格拉底希望普罗塔戈拉给自己解惑,普罗塔戈拉爽快地答应了。随后我们看到,普罗塔戈拉讲完之后,苏格拉底对他的说法表示基本赞同,仅仅说“有个小小的地方没想通”(328e4)。换言之,就普罗塔戈拉表达的教育观本身而言,苏格拉底并无异议——这意味着,普罗塔戈拉的修辞能力的确堪称卓越。
接下来,我们来看普罗塔戈拉怎样解答苏格拉底提出的两个困惑。
二、普罗塔戈拉对雅典民主意识形态的解释
普罗塔戈拉首先问大家,他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解答苏格拉底的困惑,在场的人让他随意。于是,普罗塔戈拉即兴编了一个神话故事,化用普罗米修斯给世人盗火的传说,寓意地论证人世生活为何需要政治技艺的道理。以编故事的方式讲道理,有如给小学生或年轻人讲课,要引人入胜、通俗易懂——普罗塔戈拉做得很好,显示出他作为诗人和教师的才能。尽管如此,这个即兴的故事仅仅传达了两个观点:第一,人世生活所需要的政治“智慧”只能来自人世中的个别聪明人的发明,普罗米修斯能给世人盗火,却没法从宙斯那里为人世偷来政治智慧——普罗塔戈拉暗示,他自己才是有能力发明“智慧”的聪明人。第二,普罗塔戈拉把政治“智慧”理解为一种特别的“技艺”。
这样一来,普罗塔戈拉虽然成功地向在场的年轻人证明,他们需要普罗塔戈拉这样的“智慧人”做老师,但他并没有解答苏格拉底表达的困惑。换言之,也许由于他急于向在场的年轻人显示自己的教师才能,他在即兴编故事时没有把解答苏格拉底表达的困惑考虑进去。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匆匆结束神话故事,说宙斯让所有世人都分有“正义和羞耻”,并“立下一条法律:把凡没能力分有羞耻和正义的人当做城邦的祸害杀掉”(322d4-5)。
这个匆忙添上的故事尾巴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既然宙斯让所有世人都分有了“正义和羞耻”德性,随后的立法就是多此一举,因为每个人都有“羞耻和正义”德性。如果宙斯的立法是当真的,那么,宙斯让所有世人都分有“正义和羞耻”的德性就不能为真。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与普罗塔戈拉在自我介绍时的自相矛盾一样,隐含着两种政制原则的差异。如果宙斯让所有世人都分有“正义和羞耻”为真,民主政制的原则就可以成立——至少,每个城邦民有权利凭靠自己的“羞耻和正义”德性参政。如果宙斯宣布的立法为真,民主政制的原则就不能成立,因为,有的城邦民“没能力分有羞耻和正义”。于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每个城邦民天生都有“正义和羞耻”德性,如果这是不可能的话,政治秩序的建立就得靠严厉的立法,而非民主的“有话大家说”。换言之,普罗塔戈拉用自相矛盾的修辞既肯定又否定了民主政治原则。
普罗塔戈拉结束故事后宣称,他的这个故事结尾已经解答了苏格拉底的第一个困惑,即为何雅典城邦允许所有人在政治问题上参言——因为,所有人都分有“正义和节制”这两种德性,“不然就不会有城邦”(323a1-4)。其实,普罗塔戈拉自己心里清楚,他的这个故事结尾并没有解答苏格拉底的第一个困惑。普罗塔戈拉的心知肚明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他用“正义和节制”替换了故事结尾时说的“正义和羞耻”;第二,他马上转而直接对苏格拉底说:
不过,为了你不至于以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被蒙骗——也就是,所有人实实在在都认为,所有男子都分有正义或其他涉及治邦者的德性——你不妨考虑一下如下论证(323a5-7)。
普罗塔戈拉特别提到“为了你[苏格拉底]”,无异于直接向苏格拉底暗示,他接下来的话才是解答困惑——这也无异于向苏格拉底和在场的另外两位老师辈的智术师暗示,前面讲的故事是用来教育年轻人的。因此,他说自己接下来说的是“论证”,而非讲“故事”。换言之,他接下来要讲的道理是对少数聪明人讲的。但是,由于有众多各色年轻人在场,他们未必适合听接下来要讲的道理,普罗塔戈拉仍然必须用曲里拐弯的修辞来向苏格拉底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
这样一来,普罗塔戈拉对苏格拉底的解惑就披上了另一种修辞外衣,这为我们把握普罗塔戈拉关于教育的观点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比如,普罗塔戈拉其实知道苏格拉底表达的第一个困惑是假的,雅典公民个个有“治邦者”的政治德性明显太违背常识。因此,当普罗塔戈拉说“为了你[苏格拉底]不至于以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被蒙骗”,未必指的是苏格拉底“被蒙骗”,而是指民主的雅典公民自以为有政治德性其实是自己“蒙骗”自己。于是,我们看到,普罗塔戈拉首先向苏格拉底“论证”的是:雅典公民的这种自己“蒙骗”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
毕竟,就其他德性而言,如你所说,要是有人说自己是个好吹箫手,或在某些其他技艺方面好,而实际上他并不是,人们就会讥笑[323b]他或严厉谴责他,乡亲们也会出面训斥他疯癫。但涉及正义或其他涉及治邦者的德性时,倘若他们明知他不义,而这人自己在众人面前说出自己的真实,那么,说真话在别处会被认为是节制,在这儿就会被认为是疯癫。
普罗塔戈拉以“吹箫手”为例替换了苏格拉底表达困惑时举的工匠例子,以此突显他要说的“节制”德性——乐师必须节制自己守住规定的乐律。但奇妙的是,普罗塔戈拉说,民主的雅典公民的“节制”德性体现在没有“正义”德性的公民都谎称自己有这样的德性。这段说法以曲里拐弯的修辞表明,事实上,不可能每个雅典城邦的公民都具有“正义”的德性(这是常识)。
普罗塔戈拉说,在民主的雅典,一个众所周知的不义之人如果当众承认自己是不义之人,会被当做脑筋有毛病(疯子)。这岂不是说,公民的“节制”德性等于在政治德性方面说假话吗?这样子讲对雅典民主政制岂不刻毒!难道普罗塔戈拉想要明目张胆地攻击雅典民主政制?其实不然。所谓“节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性的,一类是政治性的。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身体的健康在比如饮酒或吃肉方面节制,并非等于他有“节制”的政治德性——作为政治德性的“节制”必然关涉政治共同体。普罗塔戈拉在这里把雅典人在政治德性上说假话说成“节制”,指的是政治上的“节制”。雅典眼下实行的是民主政制,这种政制宣称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政治权利,用今天的话来说,只要年满18岁就成。换言之,民主政制的公民“参政”原则基于每个人的政治权利,而非基于每个人的政治德性。要论证每个人都有政治权利不难——这是自然权利,要论证每个人都有“正义”德性就难了——人的自然[天性]没法证明每个人都有“正义”德性。由于有“正义”德性才有资格参政议政,民主政制必须打造每个人都有“正义”德性的假定。
而且,据说,所有人无论自己正义抑或不义,都必须宣称自己正义,或者说,谁不让自己显得正义就是[脑筋]疯癫。仿佛这是必然的:[323c]我们中间没谁在这[正义]方面没份儿,否则就不算世人中的一员。
普罗塔戈拉在这里用了“据说”——这意味着,在政治德性方面不说实话是雅典城邦的一种约定。在民主政体中,如果一个人没有“正义”德性却老老实实地说没有,就违背了民主政制的约定,从而可以说缺乏民主政制所要求的“节制”德性。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普罗塔戈拉在讲神话时说,宙斯分配给所有人的政治德性是“正义”和“羞耻”(322c6),但随后马上就改为“节制”和“正义”。既然出于民主城邦所要求的“节制”说假话是“正义”的体现,说假话就无需感到羞耻。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种“约定”是一种城邦意识形态。雅典民主政制的意识形态是:人人都天生有“正义”德性。如果不是如此,民主政制的正当性何以成立呢?所有人在政治事务上都有发言权,何以不是“疯”的规定,反倒是明智的规定?因此,民主的意识形态要求所有人在“正义”德性方面有不说实话的“节制”。如果“正义”德性的实现往往需要靠“节制”德性,不讲实话的“节制”也就体现了“正义”。从逻辑上讲,普罗塔戈拉的说法可以让人推论出这样的结论:民主政制的“正义”就是“不正义”——因为,“节制”在这里具体指公民必须在“正义”德性上说假话,而说假话就是“不正义”③。普罗塔戈拉虽然用“据说”和“仿佛这是必然的”一类修辞让自己与雅典民主意识形态保持了距离,但却准确地揭示了民主意识形态的性质。现在,我们当能更好地理解他在一开始对苏格拉底说,“为了你不至于以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被蒙骗”——所谓“蒙骗”指的是民主意识形态具有让公民自我“蒙骗”的性质。
“意识形态”是20世纪政治学中的热门议题之一,这来自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著名剖析。就哲学道理而言,“意识形态”与黑格尔的著名说法有关: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意味着,何谓政治德性并没有自然的规定性,其规定性仅来自人为的约定即城邦政制的规定。不过,要说最早指出城邦需要某种“意识形态”的必要性,还得算普罗塔戈拉这位西方政治学鼻祖。在《泰阿泰德》中,苏格拉底曾模仿过普罗塔戈拉的观点:
不论何种东西,只要在城邦的观念中是正确和美好的,城邦就以之为是;而聪明人使好东西在城邦的观念中不止看上去好,而且真的好,以替代城邦原有的一些坏东西。同理,假如他有能力用这种方法教导那些受教育的人,智术师也堪称聪明人,在那些受教育者看来,他值一大笔钱。这样,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聪明,没有人判断错误,你必须得承认这是个尺度,不论你情愿与否,因为凭着这些论述,我的理论得救了(《泰阿泰德》167c4-d4,贾冬阳译文,下同)④。
这意味着,在公民的政治德性问题上,只有真正的哲人才会较真,智术师并不较真,而是认为关于美好还是丑恶、正义还是不义、虔敬还是不虔敬,没有自然正确的衡量尺度,城邦怎样规定就是怎样。对智术师来说,在这些事情上,没有哪个立法者更高明,也没有哪个城邦更高明(《泰阿泰德》172a1-6)。
在正义和不义、虔敬和亵慢的事情上,人们倾向于认定,这些事情没有一个是原本就自然存在的。众人在一个意见上达成公议,这个意见就变为真实,从公议达成那一刻开始,只要此公议成立就一直真实(《泰阿泰德》172b3-7)。
虽然普罗塔戈拉没有用到过“意识形态”这个术词,他对如今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性质说得实在透彻:“意识形态”是一种城邦意见,其性质有三个要点:首先,城邦众人的意见;第二,通过法律形式确立下来的意见;第三,具有政治法权的意见。
不论一个城邦为本邦立什么法,只要这个城邦就此达成[一致]意见,这些法令在其存续期间对订立它们的城邦就是正义的。然而,事关好的东西,没有谁仍然会充满男子气,敢为这个主张而决斗:无论一个城邦相信什么东西好并将之订为法律,这些法律在其存续期间都会对该城邦有好处——除非这个人要给“好”另行命名……(《泰阿泰德》177d1-5)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普罗塔戈拉为什么说,在雅典城邦,“所有人无论自己正义抑或不义,都必须宣称自己正义……我们中间没谁在这[正义]方面没份儿,否则就不算世人中的一员”。通过解释雅典的民主意识形态,普罗塔戈拉成功地修补了他在先前的神话结尾时的含混说法:宙斯让所有人都分有正义和羞耻,意思不是所有人天生有政治德性,而是所有人都必须有城邦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德性。
三、公民的政治德性与惩罚性教育
说明雅典公民的“节制”德性是一种民主意识形态的体现,不等于解答了苏格拉底提出的第一个困惑:为什么城邦需要普罗塔戈拉这样的德性教师。毋宁说,指出民主的雅典公民没有“正义”德性也得谎称自己有这种德性,其实是在为如下证明作铺垫:即便民主的雅典城邦也需要德性教师——因为,雅典公民的“节制”德性恰恰证明,他们绝非个个天生有“正义”“虔敬”之类的政治德性。因此,普罗塔戈拉接下来对苏格拉底说:
[c5]我想要向你进一步揭示的一点是,人们并不认为,这[德性]是天生的或自己冒出来的,而是教会的,靠努力培养出来的。毕竟,人们认为,世人都会有许多[323d]天生的或偶然得来的丑,别人有这样的丑,没谁会生气,或训诫或教导或惩罚这些人,使得他们不带着这些丑生活。相反,人们会怜悯他们。比如,有人长得丑,或个儿矮,或弱不禁风,谁会如此没理智到要去对他们做这类事情呢?毕竟,[d5]据我看来,人们知道,这些东西——美及其反面——对世人来说都是天生的和偶然的。不过,人们认为,对世人来说,好品质出自努力或训练或施教,[323e]谁要是没有,却有与此相反的坏品质,针对这些人,人们的生气、惩罚、训斥就来了。其中的一种[坏品质]就是不义和不虔敬,[324a]总而言之,就是那种与治邦者的德性整个儿相反的东西。
可以看到,普罗塔戈拉明确说,“正义”“虔敬”之类的政治德性不是公民身上“天生的或自己冒出来的,而是教会的”——通过教育才养成的德性。值得注意的是他用来证明这一点时所做的类比:有人生来就丑或个儿矮或弱不禁风,这是天生的偶然,没谁会为此谴责他,否则就太没道理——城邦也没可能要求他变得漂亮、个儿高、体魄强健,因为这些天资没有可能学成。但是,如果有人天生就“不义和不虔敬”,城邦就不能容忍。这一类比看似在强调,自然资质是先天的自然所成,因而是偶然的,政治德性是后天的教育所成,因而是城邦的必然规定所成——实际上,普罗塔戈拉强调的是,公民在政治德性方面的天生资质并不好:正如有人天生“长得丑,或个儿矮,或弱不禁风”。无论美女还是美男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甚至极少数,同样的道理,有人天生就“不义和不虔敬”——天生具有“正义和虔敬”之类政治德性的公民同样是少数,民主政制不会使这种人变得更多。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普罗塔戈拉用同一个语词来指称自然的“丑”(kaka)和政治品质的“坏”(kaka),对自然的“美”(kala)和政治的“好”品质(agatha)则用了两个不同的语词。这种区分无异于说,公民在政治品质方面的“坏”是自然而然的“坏”,就像有人生来就丑或个儿矮或弱不禁风。然而,公民在政治品质方面的“好”就不是天生的“美”了。天生的“美”有自然基质,作为政治德性的“好”品质则没有类似的自然基质,而是出于城邦的约定,需要靠教育培植出来。
一个真正的“美人”在任何城邦都会被视为“美人”,一个“好”公民是否真的有“好”的政治品质,则要依城邦而定——不同的政制会对公民或臣民提出不同的要求。所谓“好”指的是意识形态性的品质,即城邦所要求的品质⑤。普罗塔戈拉由此进一步证明了政治德性的意识形态性质,但他现在要向苏格拉底强调的是,他当然懂得:正如常人的自然资质天生良莠不齐,民主城邦公民的德性资质同样天生良莠不齐。前面对雅典城邦的“节制”德性的解释,恰恰揭示的是公民的政治德性有自然天性上的差异。城邦不需要也没可能把常人天生良莠不齐的自然资质整齐,但城邦必须把公民天生良莠不齐的德性资质整齐,否则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政治秩序。因此,城邦有理由对天生的“不义和不虔敬”之人生气、训斥,甚至施予惩罚。毕竟,生得丑或长得矮的人对政治共同体并无害处。相反,有的人天生“不义和不虔敬”明显会危害政治共同体的生活。
在这里,谁都的确会对所有这号人生气和训斥,显然是因为,这种(治邦者的)德性可以靠努力和学习来获得。毕竟,要是你愿意动脑子想想,苏格拉底,究竟会在哪一点上惩罚那些行为不义的人[a5],那么,这本身就会教你[懂得]:世人的确认为,德性是一种可以搞出来的东西。
普罗塔戈拉说到这里时叫了一下苏格拉底的名字,似乎在暗示苏格拉底:我普罗塔戈拉当然懂得你表达的困惑其实是假的,你不过在给我出难题而已——瞧,我现在可以很好地解答你的困惑,同时又不会得罪雅典人的民主意识形态。普罗塔戈拉现在明确告诉苏格拉底:由于公民在德性上的资质参差不齐,城邦公民需要受到教育——从而,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需要他这样的政治德性教师。普罗塔戈拉由此得以摆脱如下危险:他要教的是让雅典公民在“正义”德性方面学会说谎。
然而,普罗塔戈拉在证明民主城邦也需要施行公民教育的同时,还强调这种教育必须是强制性的——甚至强调这种教育在性质上应该是惩罚性的。普罗塔戈拉的这番说法听起来像是在呼应他讲神话结尾时让宙斯“立下”的那条法律:“把凡没能力分有羞耻和正义的人当做城邦的祸害杀掉。”普罗塔戈拉要苏格拉底“动脑子想想”,其实更多的是让在场的年轻人“动脑子想想”下面说的道理:为何惩罚是一种教育。
有脑筋的人没谁惩罚行为不义的人,仅仅因为和由于这人行为不义——谁也[324b]不会像头野兽那样毫无理性地报复。带有理性地施行惩罚,不会报复一桩已经犯下的不义行动。毕竟,已经做成的事情不会[因惩罚而]不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惩罚为的是将来的事情,以便无论行不义的人自己[b5]还是看到行不义受到惩罚的他人都不会再行不义。有这样一种想法的人当然就会想到,德性是教育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惩罚是为了劝阻。因此,所有采取报复——[324c]不管以个人方式还是以民众方式报复——的人都持有这种意见。
普罗塔戈拉区分了两种“惩罚”:一种是“毫无理性地报复”,要求行不义之人偿还“正义”;一种是理性的惩罚,即仅仅把惩罚视为一种教育程式。这种区分也是动物性与人性的区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所谓“理性”在这里显得是懂得计算,一桩已经犯下的不义不会因惩罚而不再是已经犯下的不义,即便是“报复”也不能抵偿已经犯下的不义——处决一个任意杀人犯,实际上没法偿还被害人的命。这段说法听起来与前面说没法对“有人长得丑,或个儿矮,或弱不禁风”生气或训斥或惩罚相似:你对“行为不义”本身没法生气或训斥或惩罚,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用。但是,人类的政治共同体为什么离不了惩罚呢?因为惩罚的实际作用是政治教育:处决城邦的罪犯是要让世人看到,城邦要求公民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德性。
普罗塔戈拉由此证明,公民的“德性是教育出来的东西”。然而,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在论证公民的政治德性需要教育时,普罗塔戈拉举的例子仅仅是惩罚。我们可以理解,教育可能甚至必须包含惩罚,但把惩罚当成教育本身就难以理解。毕竟,我们不能说我们在接受教育等于是在接受惩罚。不仅如此,城邦也往往用嘉奖来对公民实行政治德性教育:树立德性上的模范人物。可以说,施行教育离不了奖惩两个方面,普罗塔戈拉仅仅用惩罚来证明政治德性可教,听起来有些荒唐——否则,如果某个公民因想要成为正义的好人而渴望受到教育就无异于渴望惩罚。我们甚至可以说,普罗塔戈拉把教育的性质说成是惩罚,与他想要论证的德性教育相矛盾。因为,如果把惩罚直接等同于教育,便无异于说,人们在受教育时付出的努力和训导对于培育人的政治德性其实没有任何作用。
用说明何谓理性的惩罚来证明公民的政治德性是教育出来的,明显有严重偏颇。我们都能看出这一点,难道普罗塔戈拉看不出来?如果我们不能设想普罗塔戈拉的智商比我们还低,就只能设想普罗塔戈拉是在佯谬修辞传达某种观点。倘若如此,他要传达的是什么观点呢?普罗塔戈拉明确说:惩罚针对的是“不义或不虔敬”的人——如果这种人的如此品性是自然而然生出来的,又怎么可能靠惩戒来让他们修改自己的天性呢?换言之,通过这个有严重偏颇的论证,普罗塔戈拉要向苏格拉底暗中传递这样的意思:他在前面讲神话时让宙斯送给所有人“正义和羞耻”德性,是为了应付民主城邦的政治正确——他其实心里清楚,民主政治假定公民天生都有“正义和羞耻”德性不仅荒唐,而且幼稚到极点。因为,民主意识形态甚至幼稚到不懂这样的自然事实:有的人天生“不义和不虔敬”。公民在德性上的资质参差不齐,如果要让公民们在德性上向“好”品德看齐,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立法”。普罗塔戈拉把惩罚说成教育本身,暗含的意思是:公民的政治德性其实来自城邦的立法。这样一来,惩罚即德性教育所表达的含义就与前面关于城邦意识形态的说法达成了一致——意识形态有如一种立法。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教育,那么,立法的本质就是公民教育。
普罗塔戈拉把自己讲的这番道理推而广之,以此结束自己的论证:
所有其他[地方的]人都不会报复和惩罚他们认为行不义的人,不仅仅你的雅典城邦民们如此。按照这一道理,雅典人也属于认为德性是可搞出来和[c5]可教的那类人。因此,你的城邦民们看似会采纳铁匠和鞋匠对城邦事务提出的建言,因为他们认为德性可教、可搞得出来——这些证明对于你,苏格拉底,至少在我看来[324d]已经够充分。
普罗塔戈拉在结束这一论证时的口吻不无得意,因为他让苏格拉底看到,自己的双重修辞功夫如何厉害:既在意识形态上肯定了雅典民主,又通过把教育等同于惩罚否定了雅典民主政制原则的正当性。普罗塔戈拉特别对苏格拉底说到“你的雅典城邦民们”……言下之意,苏格拉底给他出的难题没有难倒自己,他巧妙地驳倒了雅典民主的自以为是。即便是民主城邦的公民,其政治德性也来自惩戒性法律。如果不首先培养出“好”的立法者,就不可能有“好”的公民。说到底,民主城邦的政治德性也来自惩戒性法律,公民的自然资质要么生来就丑或个儿矮或弱不禁风,自然资质漂亮、个儿高、体魄强健的公民少之又少,因此,没可能指望民主的公民会给自己订立惩戒自己的法律——于是,公民自己给自己立法的民主政制原则堪称荒谬。
注释:
①关于普罗塔戈拉的史料文献,参见特雷德·德蒙.普罗塔戈拉考[M]//刘小枫,陈少明.柏拉图的真伪(“经典与解释”第16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②刘小枫.柏拉图四书[M].北京:三联书店,2015:73-83.以下随文注方括号中的编码。施特劳斯指出,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如此长度的发言十分罕见。参见施特劳斯的《普罗塔戈拉》讲疏(未刊讲课稿,见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网站”)。《普罗塔戈拉》的研究文献,参见刘小枫.谁来教育老师:《普罗塔戈拉》发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③比较康德的《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参见康德.康德全集(第8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33-439。
④比较Joe Sachs,Plato’s Theaetetus,St.John’s College,Annapolis,2004;关于《泰阿泰德》中的苏格拉底模仿普罗塔戈拉,参见克莱因.柏拉图的三部曲:《泰阿泰德》、《智者》与《政治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27-142。
⑤比如,当今的罗尔斯对“正义”的理解就是如此,即按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国家的约定(英美现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平等主义原则”)来理解“正义”——如布鲁姆所说,罗尔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都是平等主义者”。布鲁姆.正义:罗尔斯与政治哲学传统[M]//刘小枫.巨人与侏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310-336。
Protagoras on Civil Education
LIU Xiaof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When Protagoras,the most famous educator during the Athenian time of ancient Greece,arrives in Athens to teach for the second time,he confronts Socrates,who challenges him with the problem of civic virtue of Athenian democracy,to which Protagoras replied wonderfully with a long impromptu speech about education.He tacitly refutes the self-righteousness of Athenian democracy,demonstrating that even in a democratic city,if its citizens are to acquirepolitical virtues,punitive education is necessary.That Protagoras defines the essence of political education by punishment implies that the legislation of a city is the very source of its citizens’political virtues.However,as citizens vary in their virtues,if they are required to look to“good”virtues,the only practical way is by“legislation”.Through a reading of this argument of Protagoras,this essay shows that what was held by Protagoras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ago towards education still has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day.
Plato;Protagoras;civil education;political virtues;democracy
G417
A
1671-6124(2016)04-0005-08
2016-05-30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