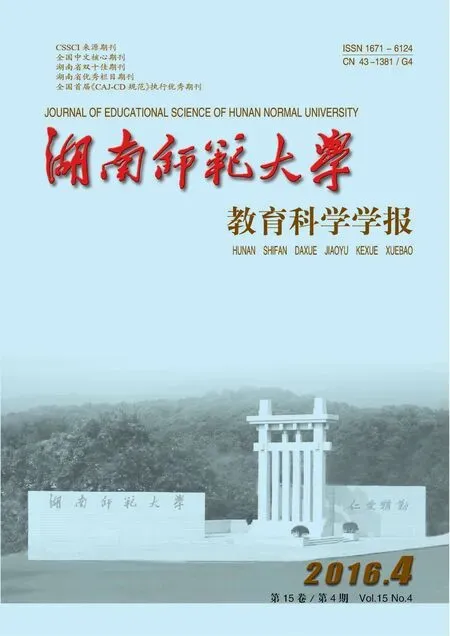作为教育方式的历史书写
——卢梭论历史与教育
张建伟,李成静,陈华仔
(1.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2.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3.安庆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作为教育方式的历史书写
——卢梭论历史与教育
张建伟1,李成静2,陈华仔3
(1.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2.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3.安庆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卢梭的历史观带有强烈的教育启蒙目的。针对启蒙哲学在教育大众方面的失败,卢梭重新梳理了历史与“真实”及大众教育之间的本质关系,并改变了传统历史评判的标准,从而把历史书写上升到一种哲学的方式。卢梭通过对自我人生的历史书写,践行了其历史评判的新观点,并改变了历史书写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位置。
启蒙哲学;卢梭;历史人生;真实;教育
一、启蒙哲学与教育的迷途
卢梭生活在西方启蒙的黄金时代,启蒙哲学一反传统哲学对人类真理的理想性追求,主张通过对人类现实事务的考察,从“这个世界”中寻找社会和人类存在的普遍真理:真理来源于我们的生活世界,来源于所有人身上都具有的性情,因而,通过教育每个人都能理解并掌握它。在卢梭看来,启蒙哲学通过降低自身的哲学品性来达成大众教育的目的,是对知识名号的僭越[1],它导致哲学本身与社会的双重异化:“哲学已然堕落为一种时尚,或者说消除偏见的战斗本身已向一种偏见蜕变,这种荒谬局面使他大为震惊。”[2]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深刻分析了启蒙哲学与大众意见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文明腐败:一方面,启蒙哲学成为大众意见的产物,遗忘了对普遍真理的追求,学者基于大众的意见而非德行研究科学,必然使现代科学从罪恶中诞生;另一方面,启蒙哲学非但没能实现教育的任务,反而助长和养成了邪恶而虚伪的社会风尚,使人心愈发腐败,“如果哲学堕落为偏见,就会存在永远毁灭智识自由的可能性”[2]。
哲学书写是传统社会最严肃、最重要的教育方式,然而通过考察,他对启蒙哲学再次承担教化大众的重任充满了失望和怀疑①:启蒙哲学的堕落使哲学本身的存在成为了问题,哲学的灵魂已被遗忘;文明社会的腐败状况也导致大众无法祛除对哲学的偏见,哲学教育的存在空间变得非常狭小,甚至是不可能。因而,通过哲学书写来教化大众的路径,在卢梭时代似乎难以实现,他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教育方式以改变日益腐败的社会与人心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书写进入了卢梭的视野。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主义观念发端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所开创的启蒙哲学传统,在这种新的哲学传统中,历史研究和写作成为了哲学家们启蒙大众、解构古典自然权利普遍性和建立新的政治哲学大厦的最有力武器。“历史主义的读书法将进步视为当然:新的比旧的好,后来的比先到的新,简言之,将好坏、高下等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等同于时间的先后,即历史。”[3]虽然历史的真理性饱受质疑,但历史书写中生动、丰满的人物和事件是人们最容易接受、最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因而,卢梭试图通过改变历史评判的标准,把历史书写与哲学真理性的要求结合起来,利用历史的“面具”,以期达到逐步改善社会道德和提升大众德性的目的。这种改变使得卢梭对历史认识独具特色:一方面,通过分析历史与“真实”的关系,他批判了当时历史书写教育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他也通过对历史书写内涵的重新解释,否定了古典哲学对历史书写本身“教育作用”的简单忽视。并且,通过对自己一生的历史性创作,卢梭践行了其关于历史研究与写作的新标准,从而实现“历史人生”与历史教育的有机融合。可以说,卢梭通过提升历史书写的思想性来实现它的教育性,这对于历史书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从“事实真实”到“哲学真实”:历史书写教育意义的展开
“历史真实”是历史书写对自身真理性问题的思考:历史书写如何看待、描述“真实”,或者在何种意义上与“真实”相关,是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标准,也是历史书写体现自身教育性的重要标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般的历史书写,包括传记、自传以及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强调特殊事件,都强调某人做了或经历了什么,而不是强调这个人可能或理应做什么[4]。亚里士多德把历史作品的这种特征称为追求“事实真实”(factual truth)。对“事实真实”的强调使得历史书写的教育意义大打折扣,因为,一方面,生活于现在的历史作家和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即便是记录自己生活的自传作者,在回忆曾经的生活经历时,都难免会带有后来的理解和偏见,产生很大的误差③。因而,史学家不可能客观地展示他们所记述的事情的繁复状态,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各种历史事件之间内在的因果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书写一方面不可能完全再现“事实真实”,要想毫无偏见地回复历史事件只是自欺欺人;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历史书写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随意更改和利用,他们用一些臆造的虚拟原则,把一些本无关联的历史事件随意联系起来,以达成自己的目的。那些看似因果相关的事件,其实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历史碎片。
与之相应的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哲人对历史书写真理性的普遍怀疑。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诗比历史更有哲理,更为严肃。因为诗叙述普遍,而历史叙述个别。”④他认为,一部以叙述特殊性为旨归的历史作品,不可能表达某种普遍的真理。故,历史性著作,包括传记都缺乏严肃性,“从哲学的根本出发点来看,把焦点聚集于任何特殊存在之上,特别是集中于一个人自己的特殊存在之上,都算不上顶严肃的事业”[5]。对特殊性的强调和对普遍性的缺乏关注,使得以“事实真实”为宗旨的历史书写被排除在“严肃的事业”之外,与以获取普遍真理为目的的教育事业大相径庭。真理性的缺乏使得历史书写在古典时代受到轻视,并始终无法进入教育的视野⑤。
卢梭似乎完全理解并赞同亚里士多德关于传统历史书写的评判,即叙述个别事实绝非哲学。他宣称:“在历史所记述的那些事情,并不是怎样经过就怎样准确地描写的,他们在历史学家的头脑中变了样子,他们按照他们的兴趣,塑成了一定的形式,他们染上了他们偏见的色彩……无知和偏袒把整个事情化了一次装。”[6]在卢梭看来,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历史学家过分关注事实的精确程度,缺乏对人类事务的普遍关系的了解,这使得历史著作中所描述的事情成为个人无知和偏袒的产物。卢梭认为,那些糟糕的历史学家无法真正做到“事实真实”,因为历史书写要做到完全客观是根本不可能的;又由于不能理解事务因果之间的自然关系,缺乏把“个别事实”转化为普遍关系和普遍因果的能力,使得历史书写完全成为历史学家个人的偏见,变得毫无意义。正因为如此,卢梭把糟糕的历史学家与糟糕的小说家相比:“小说家一味描写他自己的想象,而历史学家则是盲从别人的想象”,“小说家或好或歹总还抱有一个道德的目的,而历史学家才不管那一套咧”[6]。
卢梭对历史书写的批评很明显追寻着亚里士多德的脚步,然而,与亚氏普遍的批判和鄙视历史书写本身不同,卢梭通过改变评判历史的标准,肯定了好的历史学家有可能写出好的历史著作,或者说历史研究和写作本身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只需要我们改变以往书写历史的方式。在卢梭看来,这种改变就是放弃对事实精确程度的过分关注,逐渐向诗和哲学靠拢,追求一种“哲学真实”。“哲学真实”主张把客观、普遍的真理寓于对个人事实的描述之中,从而使得仅仅为“对于某人而言的真实”显示出普遍的意义,使得本来只适合于作者本人的真理变成适合于所有人的普遍道德标准。在《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卢梭着重分析了“普遍的、抽象的真实”与“特殊的、个人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卢梭声称“普遍的、抽象的真实是一切财富中最可宝贵的”[7],而“事实真实”显得无足轻重,“一桩不起眼的事实,从哪方面看都无关紧要”[7],它要么毫无用途,要么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显然,在历史书写中,“哲学的真实”具有首要的意义,只有把“普遍的、抽象的真实”贯穿于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那些零碎的、无关紧要的“事实真实”才有可能显示出其教育作用和价值。
可见,卢梭通过对“事实真实”和“哲学真实”内涵的深入分析,肯定和继承了传统思想中对历史书写真理性缺乏的批判,但与简单放弃历史书写的教育意义不同,卢梭进一步探讨了历史书写真理性缺乏的原因,并提出了对其进行改造的可能方案:历史作家哲学修养的不足是导致真理性缺乏的根本原因,从“事实真实”向“哲学真实”的转向是历史书写教育意义展开的基础。
三、历史书写教育意义展开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通过论述历史与“真实”的关系,卢梭改变了人们评判历史的传统标准,但为何要做出如此改变呢?即:改变这一标准的目的何在?很显然,卢梭认为“哲学真实”比“事实真实”在某种意义上对历史研究和写作更为重要,就像哲学、诗歌比历史更重要。我们通过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写作传统的分析,哲学始终处于教育最顶端的位置,这是因为它能最好地发现和保存普遍的真理,因而,能最严肃、最好地达到教育的目的。正因为如此,诗歌虽然也关涉普遍真理,但由于在纯粹性上与哲学有差别,所以当城邦需要纯粹的教育时,诗歌也有被逐出城邦的危险[8]。这样,为了教育的目的,历史就必须向“哲学真实”靠拢,必须研究普遍真理和人心。
“事实真实”不能单独构成历史书写的意义,而必须通过带有哲学眼光和目的的“包装”,才能使之显现出连贯、完整的意义,卢梭把这种历史的创作过程称为“虚构”。按照他的“惟有说话者的意图才决定言论的效果,才可以确定其狡黠或善意的程度”[7]的标准,卢梭严肃区分了“谎言”和“虚构”。他说:“为了自身利益撒谎是欺诈;为了别人的利益撒谎是作弊;以损人为目的撒谎叫做恶意中伤,这是谎言中最坏的一种。而对自己和别人既无损又无益的撒谎不能算撒谎:这不是谎言,而是虚构。”[7]
在卢梭看来,虚构的目的是为了“用感性的、赏心悦目的形式把有益的真理包装起来”[7],他把这种带有道德目的的虚构称为“道德故事或寓言”。换言之,历史只有以“道德故事或寓言”的形式书写,才有可能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因而才具有存在的价值。他说:“我希望是在这种虚构中,至少用道德真理来替代事实真相,也就是要很好地表现人心的自然情感,始终从中得出某些有用的教益,总之,要使之上升为道德故事或寓言。”[7]
卢梭通过诉诸道德用途的普遍标准,改变了传统历史书写中的“事实”标准,即:用“哲学真实”代替了“事实真实”。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论及一位“好的”史书家希罗多德,他认为作为史书家的希罗多德所记录的远非史实,他还有更为重要的写作目的,并且阐述了如下的观点:“古代的历史学家所描述的事实即使是错误,然而他们有很多见解可以供我们采用。我们都不善于认真地利用历史;大家所注意的是那些引经据典的批评:好像要从一件事实中得出有益的教训,就一定要那件事情是真的。明理的人应当把历史看作为一系列的寓言,它的寓意是非常适合于人的心理的。”[6]
显然,“得出有益的教训”是希罗多德历史书写的更重要的目的,为了这一教育目的,历史书写就必须从“事实真实”上升到“哲学真实”,因为,只有蕴含普遍真理的事物才能成为教育可欲求的对象。
然而,即便是经过“哲学虚构”的历史书写,在传统的意义上而言,仍然属于诗的范畴,而不是哲学范畴[9]。为着教育的纯粹性,卢梭为何不向前再走一步,用严格的哲学教育来直接教育大众呢?卢梭显然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他充分地认识到,哲学的书写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哲学通过提供“‘先是一个维度,然后又是另一个维度’,让我们自己对事物的真理做出判断;诗则‘立即展现整体’,为我们做好评判”[5]。很显然,哲学教育只是展示真理的维度,真正的判断交由教育对象,因而,哲学真正的对象只能是少数天赋极好或理智真正成熟之人;而诗则一下子端出了事物的“外表”,事先为我们做好了善恶的判断。因而,对于卢梭所言的“人都是模仿者”的普通大众而言,诗比哲学更有用,也更有效⑥。另一方面,卢梭也认识到,历史比哲学教育更适合大众还有一个明显优势,那便是,以道德故事、寓言为表象的历史书写,由于经过了虚构,从而把有用的“真理”用可以感知、使人愉悦的形式包装了起来,它更容易引起缺乏理性判断能力的大众,特别是理智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人的阅读兴趣,因而,比之生涩、教条的哲学著作更能有效地教育大众和青少年。
另外,卢梭通过把历史包装成道德故事或寓言,融合“事实真实”和“哲学真实”优点,从而赋予历史书写以教育的可能性。但这样的虚构如果不加以审慎的区分,历史书写的教育意义将会产生巨大的疑问:一是这两者能否实现真正的融合?如果只是把历史事实按照自己的兴趣而不是“自然原则”任意虚构,那么这样的历史书写不会有任何的教益,还会把人们引向歧途。因而,历史书写需要真正的“好的史学家”,他们能真正把握自然的真理,并合理地运用到历史中。二是对虚构本身将产生怎样的结果?过于个性化和愉悦性的虚构可能使历史的真理性打折扣,也可能使人们专注于愉悦而忘记真理,特别是对理智未成熟的青年和孩子影响更大。在《爱弥儿》中,卢梭以拉·封丹的寓言《乌鸦和狐狸》为例,质疑了寓言这一类著作(当然包括他心目中的历史)对年幼孩子的教育作用,他说看了这个故事后,“他们(孩子们)一方面嘲笑乌鸦,而另一方面却非常喜欢狐狸”[6]。年幼的孩子由于不了解寓言背后的成人动机,往往不由自主地忽略了成人的美德,而容易受到邪恶的感染,教育收到了相反的效果⑦。正因如此,卢梭虽然承认历史是理智成熟的爱弥儿走向社会、了解人心的首选,但仍然坚决反对他在理智未成熟时接触任何历史著作。他宁愿爱弥儿推迟进入社会,而不愿他在理智完全成熟前迈出这危险的一步。可见,作为寓言的历史和作为教育的真理之间,存在着不稳定的互补关系,而不是完全的同一。卢梭虽然认为历史是教育大众的好方式,但仍需要审慎地研究和对待。
卢梭对历史评判标准的改变,带有自身的特殊目的,然而,正是卢梭的改变,并率先以身示范,使得历史研究和写作具有了未来发展的意义和可能。同时,对“哲学真实”的追求赋予了史学家虚构的权利和自由,从而对未来的史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只有真正了解人类事物普遍因果关系,真正把握人类心灵一般真理的好的史学家,才能够对“事实真实”进行恰如其分的虚构和包装,否则,任何的随意和任性都将导致“谎言”。
四、卢梭的“历史人生”与历史教育
卢梭为我们展示了他对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新的评判标准,并且开始着手按照新标准写一部“人类的历史”和“自我的历史”。对于他的主要著作中的历史特征,卢梭一点都不忌讳: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卢梭把人类当做一个整体,描述了人类发展的自然状态及其走向社会歧途的过程。他试图使这本书成为人类的“历史”,第一次告诉人类自己真正的“历史”,他向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宣布:“这便是你的历史,我相信在你的同类人的谎言之书中读不到,而只能在从不撒谎的自然里得到”[10]。《爱弥儿》则描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个体的健康成长史,这个人所受的教育以对自然的恰当认识为基础,他把《爱弥儿》称为:“我的同类的历史”[6]。《忏悔录》展示了一个受到不良教育的人在社会中的不健康发展,及其如何可能达成健康之途的历史,卢梭因而把这本书看成是“我的灵魂史”。可见,卢梭试图通过他的历史书写解决关于人类发展的所有哲学问题。
卢梭对历史书写的痴迷,并不表示他对传统思想的历史偏见毫不在意,而是自信经过自己的改造,他的历史书写能融合“事实真实”与“哲学真实”的优势,从而把道德模仿与哲学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达成教化大众的目的。在《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第四卷,卢梭承认自己在著作中太容易用寓言代替事实真理了,承认自己没有严格遵循“事实真实”的标准,但他否认玷污了自己的理论,以谎言来达到掩饰恶习和窃取美名的目的[7]。同样,他虽然承认自己的历史写作中存在着“推论”或“为回忆增加细节”的行为,但他仍然认为自己在作品中“倾注的诚实、真实、坦率,达到了不比任何人逊色的地步,甚至走得更远”[7]。通过前面对卢梭关于历史书写与“真实”关系的论述,我们很容易理解他这些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观点。
卢梭对历史评判标准的改变,与他教化大众的殷切期待密切相关:卢梭一方面把自己看成“好的史学家”之列,通过历史研究和写作告知人们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真理和人心的普遍原则,通过大众的教育来改变文明社会的腐败状况;另一方面,卢梭也试图通过自身的历史研究和写作,为未来的史学家树立榜样。可见,卢梭的历史书写肩负着双重教育意义,既为了教化大众的需要,也为了培养少数未来的“好的史书家”。
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卢梭的“历史人生”以对历史评判标准的改变为基础,以对自己一生的历史性研究和写作为归宿。鉴于历史的传统观点,卢梭充分地意识到这种用历史书写自我的方式,有可能带来的对其自身形象及声誉的不利影响,这可以从他不断对“真实”做出审慎区别中看出来。换言之,只有我们充分地理解了卢梭的历史观,我们才能客观地看待他在著作中所展现出来的“卢梭式真实”的意义和价值,这为我们理解卢梭的思想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下面这首谜底为“肖像”的谜语对卢梭的“历史人生”和历史教育做出了最形象的描述:“艺术之子,自然之子;无人因我长寿,有人因我而死。我多么真实,又多么虚假。岁月的刻痕,使我变得无比年轻。”[5]
五、作为教育方式的历史书写
启蒙哲学以人类的“自我保存”欲望建构起真理和知识的大厦,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哲学,甚至任何形式的知识都成了满足自我欲望的工具。卢梭认为历史因其真实与虚假之间的古怪结合,正被启蒙哲学家们随意地利用和修改,或用来满足自我的虚荣和名声,或为了讨好大众的需要,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自我的利益。卢梭对历史书写的哲学改造不仅是对历史本身的不信任,更是对启蒙哲学的不信任。
从自我而不是从真理出发来对待历史,也正是我们这个“言必称史”的时代的普遍现象:历史被任意地拿来“借古喻今”,稍有点知识的人都可以在电视上面对大众“戏说历史”,历史已经成为某些人获取虚名,满足大众好奇心的一种颇受欢迎的廉价工具。如此历史研究的风行,却正是历史的悲哀。与上述对历史书写的态度相适应,当前历史教育的“娱乐化”、功利化盛行,历史要么成为个人的“恩怨情仇史”,个人的恩怨情仇大于天,与整个社会和政治的真理无关;要么就是尔虞我诈的“权术史”,只有残酷的阴谋诡计,而缺少对人性的真善美的关切。
生活于几百年前的卢梭似乎就意识到了历史书写有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状况,他试图通过对“事实真实”和“哲学真实”关系的哲学探索,显明历史书写要达成一种教育的意义,就必须从仅仅关注个体和事实中超脱出来,提升到公共性与真理性的高度:公共性使得历史书写从关注个体生存转向社会和政治,转向我们生活的共同体,转向对政治共同体生活的一般原则的思考,从而使得每个人都能从自我的狭隘中走出来,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公共意识和公共德性,从而达成公民教育的目的;真理性则使得历史书写成为研究人类心灵普遍规律、人类整全知识的活动,它将引导人们探索人类的共通性,从而引导我们真正理解和走向他人,达成哲学教育的目的。卢梭关于历史书写及其教育意义的观点仍然是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解毒剂。
注释:
①对于哲学与社会的双重异化,卢梭有充分的认识,他所遇到的问题与苏格拉底遇到的政治哲学问题本质上具有相似性。
②卢梭试图改变当时腐败社会和人心的强烈愿望毋庸置疑,他始终坚信自己找到了一条道德重建的真理之途。
③对于这一点,本文在论述卢梭对自己的自传性质著作与真实的关系时会有回应。
④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同时,在柏拉图的观点中,诗歌对道德普遍性的追求似乎仍然不及哲学写作,这在著名的“诗与哲学之争”中体现了出来。这可见西方古典思想对普遍性的特殊偏好。
⑤现代历史主义试图赋予历史研究和写作兼具“事实”和“普遍性”双重属性的努力,似乎回应了古典传统对历史的批判,但这种努力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难以实现的。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
⑥在这一点上,卢梭持有传统哲人的审慎态度。对于哲学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区别,卢梭有清醒的认识,相关研究可参考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论卢梭的意图》。
⑦这种效果的产生卢梭把它归结为人的“自爱”天性。
[1]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9.
[2]列奥·施特劳斯.论卢梭的意图[M]//刘小枫.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82,83.
[3]黄继勇.列奥·施特劳斯的古典阅读之道[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1):15-18.
[4]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3-36.
[5]凯利.卢梭的榜样人生——作为政治哲学的《忏悔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4,21,11.
[6]卢梭.爱弥儿:论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331,332,199,133,416.
[7]卢梭.孤独漫步者的遐想[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38,40,41,45,48,47.
[8]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403-407.
[9]卢梭.卢梭论戏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9.
[10]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03.
As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Education Way——On Rousseau’s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Education
ZHANG Jianwei1,LI Chengjing2,CHEN Huazai3
(1.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4,China;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205,China)3.College of Education,Anqing Normal University,Anqing,Anhui 246011,China)
Rousseau’s conception of history has a strong purposes for enlightenment.Considering the failure on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in mass education,Rousseau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evaluation criteria on history by re-combing the natural relationship among history,“real”and education,thereby,raised historical writing to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Through 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 self-life,Rousseau practiced a new view of his historical judgment,and changed the sequence of history writing in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Rousseau;historical life;real;education
G40
A
1671-6124(2016)04-0029-05
2016-04-29
张建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