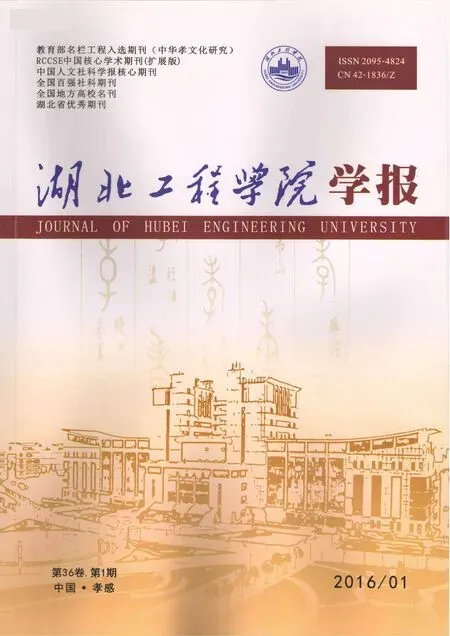《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的诗性解读
刘建朝
(三明学院 学报编辑部,福建 三明 365004)
《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的诗性解读
刘建朝
(三明学院 学报编辑部,福建 三明 365004)
摘要:郭居敬编撰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对二十四孝故事人物进行筛选、排序,再配上诗歌。郭居敬在诗体上选择四句的五言诗,平直亲切,长短适中,便于上口和记忆;在题材上选择更富有情感性、想象性、节奏感的孝行故事,以利于营造诗性的情境;在语言文字上进行适当的雕琢,使诗歌通俗而不庸俗,具有文本的艺术审美价值。郭居敬的诗性创造,使二十四孝人物更加完善,且弥补了诗歌这种体裁的缺失,丰富了二十四孝的传播方式。
关键词:郭居敬;《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孝;诗性
作为儿童启蒙读物的《二十四孝》,集图、诗、文于一体,在明清直至民国时期广为流行,影响十分深远。在20世纪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二十四孝》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再度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如考证“二十四孝”成书年代,探析“二十四孝”的人伦道德价值,阐发“二十四孝”体现的儒家孝道思想,探讨“二十四孝”对当代孝文化教育的启示,分析“二十四孝”的叙事魅力等。然而,研究者从《二十四孝》的图画或故事展开论述的较多,对于其中的诗作却不够重视。
《二十四孝》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据传诗歌部分为元代郭居敬所创作。笔者曾阅览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的《新刊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但其所载的孝行故事却有二十五则(其中的“伯俞”故事有注“或本无黄山谷有伯俞”),且都有题诗留存,即诗歌数明显超过了二十四篇,这与所载的“郭居敬……尝摭尧舜而下二十四人孝行之概, 序而诗之”[1]127不符。那么,郭居敬创作了多少孝诗,有无他人参与创作《二十四孝》的孝诗,成了难解之谜。
赵超在谈及二十四孝故事的起源时说:“通过大量文物, 可知二十四孝义故事这一系统在北宋时已经广泛地于民间流行开来。其起源则更可以上推到唐代或更早时期。”[2]近年,从多处的宋代墓中出土了二十四孝雕刻图像,但这些二十四孝人物有所差异,与后代的《二十四孝》人物更不一致。可以说,“二十四孝”的说法早已有之,但“二十四孝”的人物系列处于不断变化中。将《新刊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与清代画家王素的《二十四孝图册》、清代画家任伯年的《二十四孝图》、近代画家李霞的《二十四孝图》相比较[3],后三种所列的孝行故事是相同的,而《新刊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多了“张孝、张礼”“田真”“伯俞”的故事,缺少了“仲由百里负米”“江革行佣供母”的故事。由此可推测,郭氏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被后代稍作了改动,但“二十四孝”人物系列已基本固定下来。[4]进而可知,即使《二十四孝》的诗作非郭居敬一人独创,绝大部分也是出自他一人之手。那么,郭居敬编撰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为何会被后代广泛认可,其创作的诗歌起着怎样的作用?本文试图以《新刊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下文或简称为《二十四孝》)的诗歌为对象展开诗性的解读。
一、《二十四孝》的诗性创造
《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5]1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是由孝产生的,因此人的品行中最重要的是孝行。“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5]19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把“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且重视人们的孝行教育。如秦汉之际就出现了《孝经》,西汉刘汉编撰了《孝子传》。随着绘画、雕刻技艺的发展,还出现了有关孝行的绘画创作。如南宋时期的画家赵子固有“二十四孝书画合璧”一卷,还有各种石刻孝子图像,用更直观的方式宣传孝的思想。中国是“诗的国度”,很早就有以诗歌寄托孝思的例子。如唐代白居易作的《警孝诗》以燕作喻,警劝世间不孝者;宋代虞汝明作的《训孝诗》,表达父母养育之恩重如山,须及时尽心行孝的思想;宋代林同著《孝诗》,以五言诗颂扬从先秦至唐代有孝行孝德的人物。
为了宣扬孝行,人们运用了文字、绘画、雕塑等多种艺术方式,其中的“二十四孝”就有多种艺术表达方式。如果说刘向《孝子传》等整理的故事属于首创,那么“二十四孝”故事就属于汇编,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教变文《二十四孝押座文》将故事改编为说唱文体,属于再度创作。至于“二十四孝书画合璧”“宋代二十四孝砖雕”,便是用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表达方式来表现和传播“二十四孝”。我们发现,在这些艺术方式中却没有诗歌的身影。元代的郭居敬开了用诗歌来表现和传播“二十四孝”之先河,不过,郭居敬并没有以现成的“二十四孝”人物故事直接改编为诗歌,也不是给现成的“二十四孝图”作配图诗。他是在已有的“二十四孝”基础上做了认真甄选,剔除不适宜的孝行故事,增补了一些值得宣传的行孝人物,再进行排序,最后再给每个孝行故事创作一首诗,所谓“序而诗之”。可以说,郭居敬所撰的《全相二十四孝诗选》,以诗人的创造力,弥补了孝题材诗歌这种体裁的缺失,且从诗体选择、诗境营造及诗化语言等方面进行加工、融合,达到了诗性创造的目的。
二、《二十四孝》的诗体选择
郭居敬,少博学,好吟咏,今有《百香诗》一卷存于世,为琴、棋、书、画、笔、墨、纸、砚、鱼、燕、茶、酒等题材的咏物诗,共101首。《百香诗》是七言绝句,而他的《二十四孝》全是五言诗。这种诗体选择的差异,体现了郭居敬诗歌创作的诗体意识。
就四言与五言而论,刘勰《文心雕龙》云:“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6]146在刘勰看来,四言体雅致润泽,而五言体清新流丽,因而在众诗中五言句式成为主流格调。钟嵘《诗品序》也有相似观点:“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7]钟嵘认为五言诗较四言诗更有“滋味”,是叙事抒情描物的最佳诗体,因而被广泛采用。事实上,最早的“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6]429;而王力认为,西汉的民谣是五言诗的真正起源,到东汉才有文人创作的五言;赵成林认为,五言句在东汉逐渐兴盛, 是魏晋以后最为经典的诗歌句式。[8]
就五言与七言而论,刘熙载认为:“五言质,七言文;五言亲,七言尊。”[9]335与七言的文雅、雍容华贵之感相比,五言诗具有质朴、亲切、诚挚的特质。蔡良骥从诗的句式长短来分析:“一般说来, 长的诗句由于词语之间连系比较紧密, 语气连贯,少有停顿, 其节奏便显得舒缓、平和、柔美,而短的诗句因音节较少, 语气急促, 上下句有较明显的间歇, 节奏也就明快、强烈、有力。”[10]也就是说,当要表达缜密、婉曲、连绵等情感时,可以用七言句式;而要表达直朴、安适、平缓等情思时,宜选用五言句式。
郭居敬编撰《二十四孝》,目的是宣扬孝行事迹,向儿童灌输和普及孝的思想观念。而五言诗作为最流行的诗体,既没有四言的“文繁而意少”之弊,也没有七言的典雅尊贵之隔膜,它平直亲切,长短适中,便于上口和记忆。以郭居敬的不同诗体为例。如《百香诗》之《贫女》:“寂历蓬门春日长,奉姑辛苦事蚕桑。自甘镜里冰霜影,不带人间脂粉香。”语句舒缓平和,虽写贫家女子,但透露出文人诗作的文绉气。而《二十四孝》的“黄香”诗:“冬月温衾暖,炎天扇枕凉。儿童知子职,千古一黄香。”诗句清新,节奏明快,更便于记诵。可以说,诗体的句式并不单纯地只是形式,它可以隐含着一定意味,而内容主旨只有与恰当的诗体相融合,才能真正实现表情达意的效果。正如刘熙载所说:“几见田家诗而多作七言者乎?几见骨肉间而多作七言者乎?”[9]335宋代林同的《孝诗》也是五言体,郭居敬与林同都是福建人,《孝诗》又刊行于晚宋时期,郭居敬有可能参考林同的《孝诗》。[11]28-29不管是参考借鉴,还是自身的领悟所得,郭居敬写二十四孝诗弃“七言”而选“五言”,正是考虑诗歌写作目的、诗体意味等方面的结果。
三、《二十四孝》的诗境营造
每种文体都有自己的写作特征或规范,如小说可以虚构而不必照搬现实,散文通常要有真情实感而不考虑时效性,而诗歌可以有别材别趣,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不涉理路,无理而妙。诗歌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以体现文本的诗性。“诗性意味着某种与历史性、思辨性、科学性、逻辑性相对立的特征。情感性、想象性、节奏感,这三者的结合大体就可以造就一首‘合格’的诗。”[12]114二十四孝的一些题材来自于故事传说,不都具有历史真实性,但与郭居敬二十四孝诗的诗性要求相吻合。如“大舜”诗:“对对耕春象,纷纷耘草禽。嗣尧登宝位,孝感动天心。”首先,按常理而言,野生的大象和飞鸟绝不会耕种;再则,参照正史《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并无鸟兽帮助耕耘播种的记载。然而,《二十四孝》的注文说:“舜耕于历山,有象为之耕,鸟为之耘。其孝感如此。”也就是说,舜极有孝心,而感动了鸟兽,这突显了舜孝行之崇高,孝道影响力之广大,从诗歌情感上而言并不突兀。郭诗不讲舜如何行孝,只讲行孝之效果,孝行也变得可感了,而这不必纠缠于行孝故事本身的真假。
诗性的想象性、情感性,可以不拘泥于现实或史实。又如“董永”诗:“葬父贷方兄,天姬陌上迎。织绢偿债主,孝感尽知名。”此诗描写的故事,人们几乎耳熟能详,即董永卖身葬父,孝心感动了仙女下凡,织女嫁给董永,以织绢还债赎身。“董永”诗与“大舜”诗一样,暗含着孝行的强大感召力,两者不一样的地方是,“董永”诗叙述了孝行故事的前因后果:因是葬父,过程是仙女相逢,结果是偿还债务。传说中的故事在改编为诗歌后,仍营造了一个超越现实、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意境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诗歌文体的诗性。诗性还意味着一个超出具体可感的物理世界,而进入一个超凡脱俗的超验世界。[12]114因为“诗性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审美功能的信息,它在方式上不是指称性的,而是自我指称性的,所以它是指向自我的一种信息”[13]。郭居敬在根据“董永”故事创作诗歌时,语言构成了自己的焦点,具有自我指涉的特点,从而营造诗歌自足的超验世界。
鲁迅曾谈及阅读《二十四孝》的感受:“哭竹生笋”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14]“哭竹生笋”即“孟宗”故事:“泪滴朔风寒,萧萧竹数竿。须臾春笋出,天意报平安。”“卧冰求鲤”即“王祥”故事:“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至今河上水,一片卧冰模。”虽然鲁迅所谈是二十四孝故事本身,不是针对二十四孝诗,但故事与诗都是审美的艺术,显然鲁迅没进入诗意的艺术空间,而是简单地附会于现实,将诗性化的孝行视为现实的真实记录。这种充满功利性的阅读方式比照于现实,不仅无法获得艺术的美感,而且无法感受诗性语言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如“哭竹生笋”一诗,孟宗寒风中对竹泣泪,有笋竟然破土而出,孟宗取回家煮给母亲吃,母亲的疾病竟不治而愈。诗中表现了孝子的悲苦、无奈、欣喜等情感,而诗中的诗性想象,激发读者体验这些情感,“并于不知不觉之中将诗性生存外化为现实的生活方式”[15],化为自己的处世方式,从而得到孝行孝义的熏陶。
虽然诗性的功能能够创造另一个审美世界,但诗歌创造并非可以无限度地“为所欲为”。郭居敬在甄选二十四孝行故事时,还运用了诗性正义的原则。“诗性正义是作家主体性精神和正义感的伦理表征,是文学对于社会正义的伦理诉求和政治关切,也是文学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道德基础。对于作家来说,诗性正义是作家个人的首要美德,是作家正义精神的审美诉求,是构成作家主体性的道德品质;而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来说,诗性正义则是文学叙事的审美理想和伦理法则。文学的诗性正义要求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必须拥有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16]5如在宋代金代版本的二十四孝中,有刘明达卖子孝母和曹娥投江尽孝的故事,但郭居敬把这两则故事删除了,而留下了郭巨为母埋儿的故事。就“刘明达”与“郭巨”两则故事来说,卖子还能保存小孩的性命,而埋儿却是杀死了小孩,埋儿比卖子更残忍百倍。但这只是表面的解读,再深入些可发现,卖子的结果是失去了儿子,埋儿的结果是得到一坛黄金,且儿与母俱得以存活。郭居敬在“郭巨”诗云:“贫乏思供给,埋儿愿母存。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从诗歌艺术上看,郭居敬选择了更有诗意张力、浪漫色彩的郭巨题材,而放弃了实录但情节平稳的刘明达题材;从诗性正义上看,郭居敬体现了自身的正义感和善观念,在想象性描写中补救了现实生活中社会正义的缺失。
文学的诗性正义是自我指涉的想象性正义,它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正义并不具有同构对应的逻辑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正义越是匮乏,文学中的诗性正义就发挥得越强烈。[16]6郭巨埋儿在常理之下必是悲剧,而诗歌中“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的反转,使之具有强烈的诗性正义效果。同样,不具诗性正义的曹娥投江故事,郭居敬没有选取,也未作诗颂扬。郭居敬的诗性正义感,得之于《孝经》的精神内涵。《孝经》有云:“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5]11没有尽孝道的,常常会招致祸患,而真正行孝的,其孝行会感动天地神明,不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故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5]34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郭居敬选择的二十四孝行需要能体现善报,为此可以不避夸张甚至神化的故事情节。如“丁兰”诗,“刻木为父母,形容在日新”,木头因孝而有生命迹象;“曾参”诗,“母指才方啮,儿心痛不禁”,母子可以远距离相互感应;“杨香”诗,“深山逢白额,努力搏腥风”,小孩能与猛虎相搏斗。“大凡孝子精诚所至, 总有天意来成全他的孝心。道德一旦罩上神灵的光圈, 人们就要闻之肃然, 心向往之了。”[11]32郭居敬对二十四孝故事的诗性转化,使二十四孝具有完整的诗意氛围,而诗人的诗性正义使诗歌留给了读者美好而充分的想象。可以说,郭居敬的题材选择和诗境营造为二十四孝诗的阅读效果奠定了文本基础。
四、《二十四孝》的诗化语言
上面,我们主要从诗体选择、诗境营造方面论述《二十四孝》的诗性创造。诗人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通过诗化语言的排列组合,才能形成具体可感的诗句,才能使诗性材料真正转化为诗化的情境。郭居敬对《二十四孝》诗歌的语言运用也颇具诗心,在他的诗作中,他常常以诗人身份出现。如《百香诗》的《月》:“天上嫦娥试晚妆,团团一镜照清光。蟾宫果有长生药,乞与诗人一粒香。”在这里,他以诗人的身份向嫦娥求取仙丹。《诗》:“呕出心肝只恁狂,清风明月满奚囊。他年会遇君王颜,题在金屏家家香。”诗行中暗含了诗人创作经典文本和留取诗名的心理。郭居敬的二十四孝诗主要面向儿童,要通俗易懂,为此,郭居敬对诗化语言进行精心组织,力求通俗而不庸俗,具有诗的美感。如“庾黔娄”诗:“到县未旬日,椿庭遘疾深。愿将身代死,北望启忧心。”庾黔娄的孝行主要表现有二:一是亲尝父粪,二是愿以身代死。其他的二十四孝版本,常突出庾黔娄的尝粪事件,甚至将其孝行故事概括为“尝粪忧心”,但郭居敬在诗中宁愿舍弃了尝粪事件,不让“粪”之类的这样恶心的字眼在诗中出现。再如“杨香”诗:“深山逢白额,努力搏腥风。父子俱无恙,脱身馋口中。”全诗未出现“虎”,而以“白额”代之,清代学者王琦曾注“白额”:“盖虎之老者,力雄势猛,人所难御。”又以“搏腥风”暗示相搏之激烈,注重诗歌的含蓄表达,而避免过于直白。又如“孟宗”诗,笔者所见《新刊全相二十四孝诗选》的第三四句为:“须臾春笋出,天意报平安。”有些版本把“春笋”改为“冬笋”。其实,孟宗在寒冬对竹而哭,忽有笋冒出。郭居敬笔下的“春笋”,原是到春天才破土而出的,却在冬天冒了出来,这样就赋予了竹笋一种灵性,诗作更有张力,且强化了孟宗孝行的效果。
为了更好地了解郭居敬对诗化语言的妙用,可将郭居敬和林同二人的孝诗作一比较。如同样是写“舜”,林同诗:“孩提知所爱,妻子具而衰。大孝终身慕,予于舜见之。”[17]1林同写舜孩提时知孝,长大后妻子却受牵连,主题略显不集中;再者诗人从背后跳了出来,“予于舜见之”即言“我从舜身上看到了大孝”,主观的说教破坏了诗的氛围。而郭居敬只写孝行的效果,以“对对耕春象,纷纷耘草禽”开篇,采用便于朗诵的双声叠韵“对对”“纷纷”,具有诗句的美感。再如同样写郭巨,林同诗云:“为养宁埋子,那知地有金。如何有天赐,且复怕官侵。”[17]22用了较多的虚词,如“为”“那”“如何”“且”等,后三句都落在了“黄金”上,诗意过度延伸。而郭居敬诗:“贫乏思供给,埋儿愿母存。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用字简练,将埋儿前因后果紧凑地点出,最后一句“光彩照寒门”,“光彩”与“寒门”对比,以孝行得善报结尾,有力而留回味。又如写“黄香”,林同诗前两句为“冬月常温席,炎天每扇床”[17]24,用了“常”“每”虚词,而郭居敬前两句为“冬月温衾暖,炎天扇枕凉”,用字紧凑,且“温”与“扇”、“衾”与“枕”、“暖”与“凉”对仗,读来朗朗上口,更有诗作的美感。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郭居敬作诗主题更集中,遣词造句的意识更明显,尽可能地以诗性语言自觉呈现诗境。当然,此处对比并没有贬低林同的意思,林同也有精彩的诗篇,他创作大量的孝诗,首创之功更不容置疑。
郭居敬还根据题材特征及隐含的读者层次,斟酌使用诗化语言。如“汉文帝”诗:“仁孝临天下,巍巍冠百王。汉廷事贤母,汤药必亲尝。”汉文帝是历代帝王中唯一入选的人物,因此郭诗先对汉文帝的孝行进行高度赞扬,因其有仁孝,凭此就可超过所有的帝王,“巍巍冠百王”,随后再点出“汤药必亲尝”的孝行。“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5]4文帝事母三年,“不交睫,不解衣”,但郭居敬只言其亲尝汤药一点,不及其余。普通读者读之,必定会对文帝心生钦佩,而后代帝王读之,“仁孝”二字开题,加上文帝具体孝行,也会有所反思。再如“黄山谷”诗:“贵显闻天下,平生孝事亲。汲泉涓溺器,婢妾岂无人?”诗开篇就点明黄山谷的显贵身份,而这样的社会上层人物却能终身尽孝,有何孝行呢?黄山谷每天为母亲洗尿壶。这里就产生强大的反差,富有诗歌的张力。另外,“溺器”是夜壶或尿壶的文明称法,郭居敬似乎担心用“溺器”不够文雅,以“汲泉”搭配之,即用清澈的泉水来洗涤,达到了适度的美化。最后一句“婢妾岂无人”,以反问结语,达官贵人读之,必有当头棒喝之感,引人醒悟自身的孝行。又如“吴猛”诗:“夏夜无帷帐,蚊多不敢挥。恣渠膏血饱,免使入亲闱。”郭居敬先陈其事,无帷帐却不驱赶蚊子,不仅让蚊子咬还让它们吸饱,诗人最后点出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不使蚊子再咬父母”。此诗与“汉文帝”诗和“黄山谷”诗不同,无一字言孝,但孝行自显。此诗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故事中常人难以理解的“魏晋风流”。故事中的吴猛为晋朝人,当时为小孩,而少年儿童读此诗,虽不解孝之义理,但从吴猛的行为中能亲切地感受到同龄人的纯朴、天真、稚气,发挥了诗化语言的艺术感染力。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5]12宣扬孝行,践行孝道,不仅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也是家庭和个人的需求。郭居敬不仅“博学,好吟咏”,而且“性笃孝,事亲左右承顺,得其欢心”[1]127,他以对孝的切身体会,发挥自身文学所长,筛选孝行故事,又为孝行作诗颂扬。郭居敬的“二十四孝”诗,通俗易懂而又有审美价值,具有寓教于乐的效果。《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既呈现诗歌文本的独立性,又与“二十四孝”图文形成“互文性”,让读者沉浸于生动感人的孝行故事中的同时,又能从诗性文本中感受行孝楷模的精神力量。因此,郭居敬的诗性创造,丰富了二十四孝的传播方式,扩大了二十四孝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程毅中.关于“二十四孝”的两点补充[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4).
[2]赵超.“二十四孝”在何时形成(上)[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1):51.
[3]王素,任伯年,李霞.二十四孝图绘本三种[M].周殿富,注.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1-3.
[4]赵文坦.关于郭居敬“二十四孝”的几个问题[J].齐鲁文化研究,2008(7):48.
[5]胡平生.孝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6]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7]钟嵘.诗品序[M]//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一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07
[8]赵成林.五七言诗体赋论略[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 62(3):279.
[9]刘熙载.艺概注稿[M].袁津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蔡良骥.论诗的体型[J].文艺理论研究,1994(3):45.
[11]叶涛.二十四孝初探[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
[12]张卫东.“诗性”概念的谱系[J].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 ,3(4).
[13]赵晓彬.西方文论关键词 诗性功能[J].外国文学,2014(1):108.
[14]鲁迅.二十四孝图[J].莽原,1926(10):417.
[15]谭容培,颜翔林.想象:诗性之思和诗意生存[J].文学评论,2009(1):192.
[16]向荣.诗性正义:当代文学的主题和价值[J].小说评论,2012(2).
[17]林同.孝诗[M]//王云五.孝诗及其他二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责任编辑:祝春娥)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16)01-0019-05
作者简介:刘建朝(1984-),男,福建三明人,三明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文艺学硕士。
收稿日期:2015-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