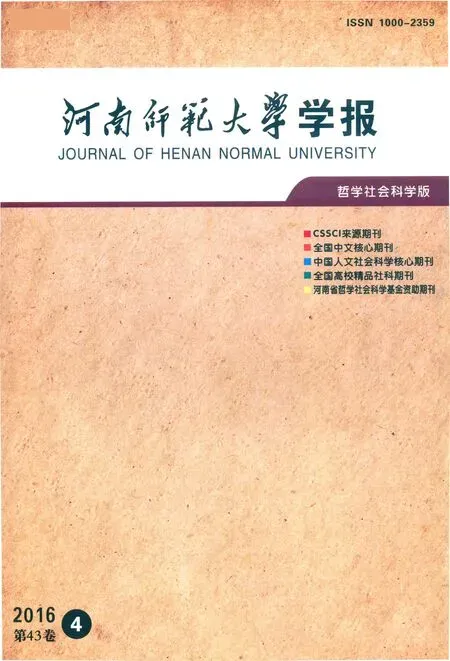李石岑的柏格森思想研究述评
李伏清,马 瑞
(湘潭大学 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 ,湖南 湘潭 411105)
李石岑的柏格森思想研究述评
李伏清,马 瑞
(湘潭大学 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 ,湖南 湘潭 411105)
民国时期,柏格森热掀起,知识分子在引介阐释取舍柏格森思想的过程中,体现了各自的人文关怀和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石岑曾大量介绍西方各派哲学包括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并在《民铎》杂志上刊出“柏格森专号”,对柏格森思想的引介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以其敏锐的卓识提出了别于同时代人的一些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李石岑 ; 柏格森 ; 生命哲学
民国时期,尼采热和柏格森热的掀起,反映了一些在人生意义探求中感到迷惘痛苦的青年学者们,对某种“精神危机”的觉悟及由此引起的焦虑中产生的共鸣。柏格森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过程,始终和时代语境紧密相连。知识分子在引介阐释柏格森思想的过程中,从来都不是机械的、教条的,他们对柏格森主义的取舍阐发,体现了各自的人文关怀和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作为时代弄潮儿的李石岑同样如此。
李石岑(1892-1934),原名邦藩,湖南醴陵枧头洲人。1913-1919年间,留学日本,在东京发起组织“学术研究会”,曾编辑出版《民锋》杂志。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并在上海继续主编《民铎》,曾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和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并曾任上海多所大学哲学、心理学教授,文名大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大量介绍西方各派哲学,如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德国倭伊铿的精神生活论、尼采的超人哲学、英国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等。在《民铎》杂志上刊出的“尼采专号”“柏格森专号”“进化论专号”等,颇具影响。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对李石岑思想的研究寥若晨星,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以求教于方家。
一
李石岑对柏格森思想的关注并非无源之水,与民国时期的柏格森热紧密关联。
1913年钱智修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现今两大哲学家学说概略》一文,介绍了德国哲学家倭伊铿和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揭开了柏格森主义东渐的序幕。柏格森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在上世纪20年代达到了顶峰。1920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应邀在北大作了题为《现代的三个哲学家》的演讲,对柏格森哲学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引介,扩大了柏格森在中国的影响。在此后的整个20年代,柏格森的主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如《创化论》(张东荪译,商务印书馆,1919年)、《形而上学导言》(杨正宇译,商务印书馆,1921年)、《物质与记忆》(张东荪译,商务印书馆,1922年)、《心力》(胡国钰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时间与自由意志》(潘梓年译,商务印书馆,1927年)。而李石岑与柏格森热直接关联。
首先是张东荪。因感伤于民国初年政治乱局,1917年逐渐告别政坛的张东荪,将相当多的精力倾注到《时事新报》的编辑工作中。不久,19世纪末20世纪流行于欧洲的生命哲学引起了他的关注。从1918年1月起,张东荪翻译了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中译本取名为《创化论》,在《时事新报》上连载达3个月,次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1920年3月已发行第三版,半年中连印三次,1922年10月发行第四版。张东荪翻译的《创化论》的出版,使柏格森的著作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成为时人了解柏格森的重要途径。张东荪翻译的《创化论》是从柏格森的代表作L′évolution créatice的英译本L’evolution creatrice转译而来的。英译本出版于1911年,由阿瑟·米歇尔(Arthur Mitchell)博士翻译。当时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对柏格森非常推崇,两人在学术上可谓同道和知音。阿瑟·米歇尔博士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詹姆斯的举荐和支持下进行了,詹姆斯还帮助米歇尔推敲译文,增加了译本的可靠性。因此,张东荪在《创化论》的扉页上注明“法国柏格森原著,美国密启尔英译,张东荪重译”的字样。随后,张东荪又翻译柏格森的另一重要代表作《物质与记忆》,并于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而李石岑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在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民铎》杂志主编的同时,还相继担任了《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笔、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的主编,自然对当时轰动一时又是在《时事新报》所刊载,又为商务印书馆多次连印出版的《创化论》及其后的《物质与记忆》有所了解。1920年10月底,李石岑陪同杜威、罗素、章太炎、蔡元培、张东荪和吴稚晖等人到湖南讲学。张东荪曾在《东方杂志》发表过两篇论文讨论言性的问题,并提出理智救国的主张。李石岑和杜亚泉也围绕着同一问题,在《一般》上起过一番辩论,三人曾一度为了“我们的生活应该受理智支配,还是应该受感情支配”的话题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论战。可见,李石岑对张东荪的思想应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在翻译过程中,张东荪多有参鉴日人的译法来加以修正。如在《创化论》篇名上,张东荪参考了日本人金子桂井二的译本,日译为“创造的进化”,并最终择定为“创化论”。而曾留学日本的李石岑,在日本接触到西方思想如尼采超人说、柏格森生命哲学并深受浸染。我们在李石岑引介柏格森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多处采用“创造的进化”一说。另外,在柏格森思想的核心词方面,张东荪在检讨了当时译界的三个流派,即东译派、严复派、译音派基础上,最终斟定为“绵延”。而李石岑对柏格森的评介中也采用“绵延”一说。可见李石岑对张东荪思想有一定的接触甚至认可。
其次是朱谦之。朱谦之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曾一度信奉虚无主义,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宣传社会革命和教育改革。而在1922年前后,对生命的反思促使他抛弃了一度信奉的虚无主义,重返中国传统文化的起点,通过重新阐发孔子之学,提出了颇有创见的唯情论哲学体系而名噪一时。其理论以“情”作为宇宙本体,以“复情”作为人生观。总体上,朱谦之早期的虚无主义思想和后期的唯情哲学中,都受过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正如艾思奇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说:“又如朱谦之先生的唯情哲学之受柏格森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虽然朱先生曾说柏格森的直觉哲学重记忆,唯情哲学重理想,前者累于过去,后者能烛照将来,似乎有一步的前进,但根本的方法,则宁可说朱先生是柏格森的摭拾者。”[1]而我们从《李石岑讲演集》之《我的生活态度之自白代序》一文中可以得知,李石岑和朱谦之关系不错。文中论及梁漱溟的人生态度时指出:“我友朱谦之先生,也多少和这种态度相似,所以从前为怀疑一切而著《虚无哲学》,现在却转向信仰,而发表他的《周易哲学》了。”[2]5该文成于1924年元旦,而反映朱谦之虚无主义思想的《革命哲学》一书出版于1921年,1922年朱谦之出版《无元哲学》暗示思想的转向。代表朱谦之思想转向的著作《周易哲学》虽然出版于1923年,但是他的实际写作时间,起始于1920年底。1920年至1923年间,朱谦之的思想实现了由“虚无”到“唯情’的蜕变,这种转变又恰好为友人李石岑所识。因此,摭拾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朱谦之的思想,自然也会潜移默化影响到有着强烈历史时代感和责任感、同为思想家的李石岑。
再次就是1923年前后的科玄论战。
论战中,柏格森作为“玄学派”的思想资源,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梁漱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通过对柏格森生命哲学的阐释,反思以“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被公认为玄学派的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在建构各自新儒学体系回应科学派的诘难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如张君劢留学之时受教于德国哲学家倭伊铿,并对柏格森的学说非常倾慕,他在人生观论战中的言论借鉴了柏格森对物质科学的批评和有关“生命冲动”“自由意志”“直觉”方法的论述,主张将柏格森、倭伊铿思想引为同道,作为他建构“新宋学”的外援。对此,吴稚晖多有批驳,他在与《李石岑讲演集》之《吴稚晖序》中也有与李石岑评论张君劢的人生观。而李石岑对倭伊铿风靡全球的“精神生活”论深为服膺,除在《哲学概论》《西洋哲学史》和《人生哲学》(上)等文中多有提及外,还著有《倭伊铿精神生活论》,认为倭伊铿、柏格森和詹姆士同为生命派、行为派和具体派之哲学。可见,李石岑对柏格森思想的服膺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张君劢有关系。而梁漱溟就更不用说。柏格森思想对梁漱溟的影响已成公论,我们能从其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时刻感受到这种思想的震撼力。而李石岑曾在《我的生活态度之自白代序》一文指出,“我友梁漱溟先生亦复和先生同样地留心学问”[2]1,并在阐述其三种生活态度理论时,将梁漱溟归入第一种“为生活而学问”并加以评析。同时,李石岑还著有《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中国公学讲演》一文,从梁著的内容、作者的态度和作者的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批评。可见,李石岑对梁漱溟的理论自然也是耳熟能详的,自然也不会放过对柏格森思想的赏析。
而科学派的代表之一吴稚晖,曾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指出,柏格森具有以精神意志反抗上帝的一面,而柏格森的哲学本和人生观无关,介绍到了中国,才被玄学利用,成了人生观的学说。他用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观察到柏格森生命哲学与时代氛围的微妙关系,看到了柏格森思想是经过阐释和发挥才与上世纪20年代当时思想界的议题成功对接。在同文中,吴稚晖提出,人生观论战期间,胡适、朱谦之、梁漱溟和梁启超四位先生,是当时中国思潮的代表。四人中胡适对柏格森多有讥评,后三者却都是深受柏格森思想的影响。而在《李石岑讲演集》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石岑和吴稚晖多有书信往来。而从《我的生活态度之自白代序》一文更能清晰地得出两点:一,李石岑和吴稚晖早在民国九年(1920年)一同到湖南讲演时得以认识;二,李石岑曾读了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论及人生观》一文并表示佩服吴之卓识和“那种童稚未凿的天真和精进不懈的努力”[2]1。
正是基于人生观论战的影响,李石岑发表了不少与人生观相关的讲演,如《人生哲学大要》《人格之真诠》《怀疑与信仰》《教育与人生》《佛学与人生》《哲学与人生》《科学与人生》等,都收录于《李石岑讲演集》一书中。这些文章,字里行间所受柏格森的影响也多有流露。
另外, 李石岑在担任《民铎》杂志主编时,于1921年12月,发行了“柏格森专号”,曾敦请梁漱溟等人撰文。该专号共收入17篇文章介绍和研究柏格森的思想。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将柏格森的代表作翻译到中国,代表了中国当时研究柏格森思想的最高水平,相关研究涉及柏格森思想的时代背景以及柏格森生命哲学中的核心概念,柏格森思想以生命哲学的形象受到各界的关注,茅盾和蔡元培还曾专门写文章介绍这期杂志*佩玮(茅盾):《介绍民铎的柏格森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1月11日。另见《茅盾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13-314页。蔡元培:《五十年中国之哲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3-284页。。
当然,李石岑对柏格森思想的赞赏和认可,除了以上思想界的外围影响外,也离不开柏格森思想本身的魅力。柏格森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具有很大的亲和性,有利于强化知识精英包括张东荪、朱谦之、梁漱溟、张君劢、李石岑等人对生命哲学的把握和阐释,由此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建构人生观时的重要思想资源。柏格森思想在正确的时间的传入,恰好迎合了知识精英于“五四”启蒙运动后探讨人生观的迫切的实际的思想需要。
二
李石岑对柏格森思想的引介和评析主要集中在《挽(晚)近哲学之新倾向》《柏格森哲学之解释与批判》《柏格森哲学与实用主义之异点》(在杭州第一师范)和《现代哲学杂评》等文,收录于《李石岑哲学论著》和《李石岑讲演集》中。另在《现代哲学小引》第二章《法意哲学》之六《柏格森——直觉主义》及《西洋哲学史》中也有引介。而在《人生哲学》(上)等著作中,李石岑在阐释其“表现生命”的人生观过程中,时常流溢出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元素[3]。
李石岑对柏格森思想的引介和评述,主要集中于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和《时间与自由意志》两书。
李石岑认为,要了解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的中心意义,首先要把握绵延(Durée,Duration)。在李石岑看来,柏格森的绵延即吾人意识之真理。李石岑譬喻言之,如闻邻家之犬声,忽联想客至,忽怀旧友,忽念故乡,意识界刻刻变化增进,无刹那静止;而说明意识变化增进的好例譬如流水,濯足急抽出又复入之,则其水已非前水,又以滔滔不竭之故,随流随广,涓涓之水,汇成江河。说明意识活动的好譬则如时间之刹那刹那间流转迁变,不可捉摸。李石岑还认为,柏格森哲学上之“时”与日常生活之时有别,并非应实际要求之描写空间的可区分可量计之“时”,而是“息息变化,息息增长,无数可数,无量可量,既艰于说明,复难于理解”,但我们可以通过“内观自证,由直觉而得”。认为“由直觉而得之时,是谓时之真义,是谓绵延;然则绵延者,一溶和渗透之内质的变化之连续也”[4]7。
其次,李石岑介绍了柏格森的“记忆”论。柏格森欲以绵延概万有之真相,而以“记忆”说明之。认为“记忆者,活动而无消耗之绵延也”。记忆是我们意识的根柢,没有记忆则过去与现在相切离,更不能抟为一体与未来生交涉,如此宇宙或几乎息。李石岑介绍了记忆之天职和功用,认为记忆之天职在于合过去现在以侵入未来,而谋不断的发育,而“凡过去之所以生长,所以保存”正依赖于记忆之功。但记忆不是一种能力,而是担负过去,紧迫现在刹那之后而追随我们的一种冲动力和倾向。“凡吾人之意识所以息息变化增长者,皆此全过去之力,亦即全记忆之力也”[4]7。 李石岑指出,在柏格森看来,我们意识界刻刻变化,刻刻创造,“故凡一瞬间所表现之新状态,皆为前此所未经见,故不可预测;不可预测,故非循环;非循环,故自由;自由,故创造”[4]8。李石岑认为“创造”一词在柏格森哲学中有极重要的意义,认为创造并非局限于有机物,即便是无机物也负有创造之责。李石岑称颂柏格森对于有机物和无机物之解释“为其哲学新生之曙光,是不得不珍重叙述者”[4]8。
其三,李石岑强调了柏格森的有机物和无机物之说。柏格森认为,有机物与无机物之区别在于“个性”,“个性发现之原因,为绵延性,而有机物则最富有绵延性者也。无机物以存在完其职,有机物则存在之外,且生且长且成熟,生长成熟,绵延性之表现也”[4]8。但有机物之绵延性也不过全生命之潮流之绵延性之一时的假现而已。因此,全生命之潮流之流动进化是宇宙的真相,各有机物所以形成进化之幻影。而无机物也自有其历史,即自有其保存与消失之事实,而这种保存消失是生长创造的消极的方面,而有机物表示创造的积极的方面,两者都为绵延,“皆向创造之涂以趋,故宇宙为创造也”[4]9。
其四,李石岑介绍了柏格森对直觉与知觉的区分。正如前言,有机物的创造进化不过是进化之幻影绵延之假说,绵延的真相要靠直觉来获得。李石岑基于柏格森的理论,对直觉和知觉进行了比较。“直觉者,与知觉对立者也”。两者在对象上不同:对于物质界的解释由知觉而得,对于意识界之解释,则非直觉不为功。在层次上,“知觉为普通知觉之精,属第一种之认识;直觉为纯粹知觉之精,属第二种之认识”。在学科分属方面,“知觉者,科学之事也;直觉者,哲学之事也”。在方法路径和表现方面,“知觉以分离物质为能,故重分析个别,为外部的,功利的,分量的,同时的;直觉以统一意识为本,故重内观自证,为内部的,本然的,性质的,继续的”[4]9。因此,在柏格森看来,要明意识之真相,舍直觉之外别无他法,而一切的语言文字都不过是精神符号的说明而已。在李石岑看来,柏格森的真理观既非如唯心论所谓主观的产物,也不是如实在论所谓客观的存在,是主客亲和一多相即之宇宙生命之呼吸而已。此惟直觉非知觉无由成,可见直觉之不可须臾离。
一般看来,柏格森的直觉方法极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唯心论,而李石岑则准确理解了柏格森所说的“共感”,即直觉方法是一种主客交融的认识方法,并非单纯的唯心论。
其五,李石岑还明确了柏格森对纯粹知觉和纯粹记忆的区别和比较,由此阐释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李石岑指出,柏格森认为纯粹知觉即物质而离精神,纯粹记忆即精神而离物质,前者生于现在,后者生于过去。二者共存于普通知觉之中。认为“普通知觉之中,既含纯粹知觉,复含纯粹记忆,即物质精神两方同具也”。“以普通知觉为界,上行为意识界(精神界),下行为物质界;意识界,向上自由之世界也;物质界,宿命下向之世界也”[4]10。李石岑把绵延理解为一种运动,认为这同样是柏格森所说的“实在”。物质和意识,不过是运动的状态和幅度不同罢了。在李石岑看来,只有明确了意识界和物质界这点,才能与之言生命之进化。认为意识与物质,并非根本不相容,而是可以谋两者之调和。“意识者,积极的也,主也;物质者,消极的也,从也。若一旦意识征服物质,融通而利用之,则物质反有相助之功能。且纯粹意识,视万有一切平等,不生差别,则物质亦有自身之效用;思想假文字而益显,则意识假物质而愈明,则直觉又未尝不有待于知觉也”[4]10。正如柏格森所认为的,“吾人非真生命之潮流,吾人实负有物质者,而此物质固生命之潮流之实质之硬化者也”[4]10-11。也即生命之绵延具有紧张弛缓两个方面,紧张之则为精神,弛缓之则为物质,可见精神和物质实自共同之一根源而来。物质与意识,不过运动之比较的状词而已,而促此运动之力,则在于“生之冲动”。柏格森正是本于“生之冲动”来阐释其“创造的进化”论。我们也可以从这一论述中看出,在李石岑那里,柏格森的思想并非时人更非后人所理解的单纯唯心论,并不排斥物质,相反,认为意识与物质并非根本不相容,而是可以相调和的。
因此,李石岑多次提到,柏格森对于理知,对于科学并不反对,唯一反对的是以理知作为认识宇宙的唯一能事(途径或方法)。这一观点于科玄论战中,回应科学派的诘问不能不谓为有力的回击,也是一种卓见。
三
李石岑对柏格森直觉主义思想的引介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李石岑有别于时人对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一味关注,而认为柏格森形而上学的主要原理,都蕴含于《时间与自由意志》之中,认为该书是理解和介入柏格森思想的窗口。《时间与自由意志》的重要性早在中译本问世之前就已经受到了李石岑的重视。他指出:“柏氏以三大著作著称,即《时间与自由意志》《物质与记忆》《创造的进化》三者是已。论者谓《创造的进化》为柏氏哲学上之代表作,实则柏氏哲学之神髓全贯注于《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然则批评柏氏之哲学,不能不最初于《时间与自由意志》所表著之思想批评之。今请阐明此著为其他各著所从演绎之点。”[4]38
他借用《创化论》英译者Mitchell的话,指出柏格森形而上学的主要原理,都蕴含于《时间与自由意志》之中,此后的《物质与记忆》《创化论》中未见有大的改动或扩充。在生命哲学的体系中,最令李石岑感兴趣的是柏格森有关直觉的论述。
李石岑指出,柏格森哲学的主要点在于“时间”“意识”和“本能”,并就此三说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李石岑认为,时间为《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讨论的主题,意识为《物质与记忆》一书讨论的主题,本能为《创造进化论》一书讨论的主题。认为三者都是阐明“直觉哲学”主要的著作,但其主要原理悉含蕴于第一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中。“由时间发挥绵延之性质,由意识阐扬心物之关系,由本能规定直觉的方法,皆于首著发其端,于后二著集其成,正可见柏格森哲学早已组成一种系统。他如《释笑》《形而上学序论》《精神万能论》或则阐明直觉之性质,或则细述意识本态,皆所以培植精神的一元哲学之根基。闻柏格森刻正从事美学与伦理学之著述,则所以启示生命进化之途者,且未有艾也”[4]54-55。
其次,李石岑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进行了比较。如在《柏格森哲学与实用主义之异点》一文中,于“默实在根本的肯定”“宇宙之实在之无限的流动进化”“欲认识绝对的真理,须超越实用主义的生活”和“脱却‘一切不变的固定的见解’之知性”等四个方面,将柏格森哲学与实用主义的不同之处进行了比较,认为基于第一点的细微不同而导致后面三点差异。在李石岑看来,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以总全的经验为其立脚点,以人类的努力为其归宿点,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如出一辙。认为在反主知方面而言,“柏格森亦一实用主义者也”。当然,李石岑的这一说法,借鉴于席勒对柏格森的评价,席勒认为柏格森在法国为实用主义之骁将,而就直觉方面而言,詹姆士亦一直觉主义者。李石岑认为柏格森和詹姆士二氏之学,一以“行为”开其局,一以“生命”总其成,皆撷取近代人本主义、主情意主义之菁华,扫除前此绝对主义、主知主义之迷妄。他给二氏之学以很高的评价,“人生之真意义,人生之真价值,至是乃发挥透辟,举无余蕴矣!”[4]13认为对国人思想之启蒙具有很大的意义,“煌煌二哲,皆产生于民主国之中,其所受自由思想之赐,因以蔚成独创之天才者,不足以增吾人觉悟之量耶?”[4]13
再次,李石岑强调了柏格森创造进化论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区别。在当时的文献中,鲜有人分析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创造进化论之间差异,似乎从侧面验证了至少在民国初年知识界对进化论的理解本身包含了唯意志论的成分。而李石岑敏锐地觉察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李石岑有别于当时将柏格森的进化论理解为线性进化论的观点,认为,柏格森的“创造的进化”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迥异。他指出,达尔文全以因果关系之机械律立论,难以语得进化之真诠;而柏格森极力排斥关于进化的机械观的与目的论的说明,而认为“进化仅由直觉之神秘生命与创造活动乃得而行之”,即“生之冲动”[4]48。李石岑认为两者有两个大的不同:首先,在方向上,达尔文说明进化,由现在推寻原始以律未来,而柏格森则以进化为由原始而现在而未来而永续无穷的巨流,而其所谓原始为“生之冲动”。其次,在对“适应”的理解上,达尔文认为生命之存续以适应外界为第一要义,而柏格森则认为不应夸大外界的影响,适应不过用来说明进化之道路之曲折与高低而已,决非说明运动的方向与运动自身,生命进化的动力在于生命冲动。在柏格森看来,生之冲动才是充塞宇宙的精神实在,于生命之创造具有强大雄厚的特殊的功能。有鉴于此,李石岑继而对罗素对柏格森之进化论所进行的极猛烈的攻击一一进行了诘难[4]49-52。
而李石岑对柏格森哲学的引介取舍也有一显著特点。李石岑将柏格森的思想定义为直觉主义,对柏格森的关注,并不停留于绵延、创化这些描述宇宙论的概念上,去考虑宇宙论和终极意义的问题,相反,他将绵延和创化引向对全体的感悟,着重阐释柏格森哲学感悟本体的方法,认为无论是绵延还是生命冲动,都离不开直觉的体悟。由此,直觉作为方法在李石岑眼中反倒成了柏格森思想的内核,这也是为何李石岑一再将生命哲学定义为直觉哲学的原因。这对时人将柏格森的思想引导至与国内思想界的时代主题人生观的讨论接轨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一意义与方东美在1919年发表《柏格森“生之哲学’》[5],将柏格森哲学定位为“生之哲学”,落脚点在人生,而引导国人对柏格森思想的定性由进化论向生命哲学的转向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体上,李石岑对柏格森的思想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李石岑曾如此评价道:“柏格森诚具有独创之天才者也。古来不恃论理学之诱导,而仅凭洞识(Insight)以建立一种有统系之哲学,皆为不可及之天才。康德而外,吾仅见柏格森焉。”[4]55-56在《自序——思想方法上之一告白》中有类似表达。他在对杜威和罗素思想进行比较评析后指出:“我比较赞成且加上佩服的,便是法国柏格森的哲学。柏格森的哲学,可谓取杜罗两人的长处,去掉他们的短处。”[2]41李石岑对柏格森思想的这种引介和评析于我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对柏格森思想的定性的转变有很重要的意义。
[1]艾思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M]//艾思奇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8.
[2]李石岑讲演集[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李伏清,欧阳欣欣.论李石岑“表现生命”的人生观[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3):18-22.
[4]李石岑哲学论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5]方珣(方东美).柏格森“生之哲学[J].少年中国,1919,1(7).
[责任编辑 张家鹿]
On Shih-tsen Lee’s Thought of Bergson’s ideological
LI Fu-qing
(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民国), there raised a hot wave of research on Bergson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the Bergson thought, the intellectuals have their own ideological to trade-off, which embodies the humanistic care and the response to the time problem. In the “May 4th”new culture movement, Shih-cen Lee once introduced a large number sects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cluding Bergson's life philosophy, and published “Bergson special issue” on the magazine of people’s? big bell (《民铎》). Shih-cen Lee has great contribution to introducing Bergson ideological. He has some unique insights which different from contemporaries into Bergson’s?thought, and so has a certain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Shih-cen Lee; Bergson; Philosophy of life
2015-06-15
湖南湘学研究所基地委托项目(11JD69)
李伏清(1981- ),女,湖南湘乡人,哲学博士,湘潭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湘潭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湘学研究和近现代思想研究。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4.002
B26
A
1000-2359(2016)04-00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