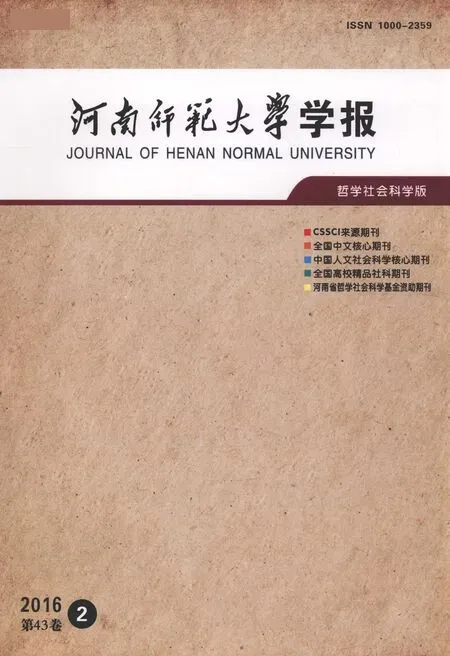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价值虚无主义课题
刘 雄 伟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价值虚无主义课题
刘 雄 伟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传统形而上学本来试图通过对“最高价值”的承诺来支撑个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但它却不自觉地走向了对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蔑视。马克思意识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内在悖论,因而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最高价值”的虚无本质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价值虚无主义困境,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现实历史的存在论澄明,以“人的解放”的旨趣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道路。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内蕴着丰富的克服价值虚无主义的理论资源,但这一点至今没有被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识到。
形而上学;价值虚无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长期以来,人们在没有澄清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的历史哲学的内在超越的前提下,把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地理解为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这就不可避免地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的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强烈观照,而将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公式和万能钥匙。考量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性的价值虚无主义的克服,无疑有利于破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释放出历史唯物主义本有的“人本情怀”。这无论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还是对于当代人的精神家园的重构来说,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最高价值”的幻象与马克思对价值虚无主义根源的指认
价值虚无主义根源于传统形而上学对抽象的“最高价值”的悬设,这是马克思对价值虚无主义的基本判定。传统形而上学本来试图通过对世界的终极追问来确立人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本和生命的逻辑支撑点,但它却不自觉地蒸馏了现实的人的全部价值,把现实的人的价值完全对象化给了彼岸的世界,进而以彼岸世界的“抽象价值”来宰制人们此岸的现实生活,促使现实的人完全沦为他所创造的虚幻价值的奴仆。柏拉图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奠基者,在他那里,现实的世界被看作是虚幻无常的,超现实的理念世界则被看作是真实可靠的。在柏拉图看来,个人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只有同超现实的理念世界勾连在一起时,才是完美的,才能摆脱尘世的苦闷和生命的短暂性,获得人生的意义和尊严;相反,如果离开理念世界所悬设的“最高价值”的支撑,个体的生命将会陷入一种无意义的窘境之中,其生活也就不值得一过。基督教是柏拉图哲学的具象化,因而它最能够体现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运作机制。在基督教中,人们彻底掏空了自己的全部价值,把自己的一切价值都对象化给彼岸的上帝,以为上帝才是自己个人价值的源泉,因而对上帝顶礼膜拜,而始终意识不到,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近代以来,伴随着人的觉醒和世界的发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上帝只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它不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源泉,相反,它只是人类现实苦难的表征。然而,一旦现代人意识到宗教的虚无本质,人们的世俗生活就会变得黯淡失色和毫无意义可言了,甚至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价值虚无主义深渊之中。19、20世纪之交的尼采彻底挑明了现代性的价值虚无主义困境,他甚至把现代性的价值虚无主义看作是“危险中的危险”。
价值虚无主义根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在运作机制,它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必然宿命,或者可以说,传统形而上学实质上就是一种漠视现实的价值虚无主义。在马克思看来,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就已经同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以往的一切形而上学进行了公开而鲜明的斗争。但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如拉·梅特里、爱尔维修、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等,由于仅仅把现实的人理解为感性的人、自私自利的人,所以并没有在对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批判中真正确立起人的价值和尊严,反而加速了价值虚无主义的进程和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这就是为什么18世纪的唯物主义会遭到人们的谴责和误解,恩格斯说:“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的一切龌龊行为。”[1]也正因为如此,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导致了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的强有力的反弹和复辟。马克思说:“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2]159-160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之所以“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是因为当时流行的的黑格尔哲学一方面认识到了传统形而上学所悬设的“最高价值”的彼岸性质,但另一方面,它又没有完全走向对个人的主观任意的盲目崇拜,而是以“实体即主体”的思路改造了以往独断论的形而上学。
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现实的历史进程本身,作为上帝意志的显现和理性的自我展开,就是合目的的过程,是人类逐渐自我实现和走向自由的历程,而现实的人的生命正是由于根植于人类文明史的厚重土壤,所以才会有自由和尊严可言。黑格尔辩证地实现了个体理性同普遍理性的和解,拒斥了自笛卡尔以来人们对单子式的个人的抽象自由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确实重建了已经失落了的“最高价值”和人类伦理共同体。黑格尔具体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就是地上的神,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个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尊严,人不仅意识到了人之为人的神圣本性,而且还彻底实现了人的这种神圣本性。伴随着人类全部的价值理想的实现,历史由此而走向终结。
尽管黑格尔创造性地将辩证的原则灌注到了僵化而教条的传统形而上学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和解了传统形而上学所割裂了的此岸的人的价值和彼岸的最高价值,确证了人类现实历史进程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但不得不承认,黑格尔并没有在根本上突破以往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视域,他同样抽离了人类感性的现实历史本身,掩盖了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自私自利和无产者的苦难,误把资产阶级所宣传的价值看作是人的实现了的价值。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哲学不仅没有真正解决在宗教世界观破产之后的现代人的价值虚无主义命运,反而以美化资产阶级社会的方式彻底掩盖了现代人的价值虚无主义困境。黑格尔哲学是资产阶级自我辩护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为什么它会受到现代哲学群起而攻之的原因所在。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颠倒了历史的主客体,把“历史”本身理解为合目的的绝对主体,而把真正创造历史的现实个人抽象为历史的客体,这样一来,现实的个人的主体能动性和价值就被彻底抹杀了,取而代之的不过是历史自身的僵化的合目的运动。“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于现实的人来说,也就是变成了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2]108。归根到底,同以往的形而上学一样,黑格尔哲学在本质上是教条的和独断论的,作为一种凌驾于人们现实历史之上的“独立的哲学”,它从来都没有认真反思过自己所盲目悬设的“绝对理念”,更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悬设的“绝对理念”的虚幻本质,而一味地以“绝对理念”的名义来压抑个人的价值和尊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只是世俗化的神学历史观,是神学目的论的现代版本,它在实质上依然是虚无主义的。因此,只有彻底颠倒已经被黑格尔所颠倒了的历史主客体关系,揭露黑格尔历史观的神正论实质,才能真正确证现实的人的价值,走出价值虚无主义的困境。
基于这种洞见,历史唯物主义以历史性原则彻底终结了以超历史的先验标准出发的传统形而上学,它不再从“任意的和想象的前提出发”,拒绝任何的神圣形象和最高价值,力求在现实的历史中来寻求规范人们生活的标准和尺度,并反过来以人们的现实生活本身来考量这些规范人们生活的标准和尺度的合法性。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也没有做”,“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2]105,因而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理念。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同时也就意味着在人的目的之外并不存在抽象的历史目的,或者说,现实的人的目的,就是历史应当与之相适应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较之历史唯心主义实现了最为深刻的理论变革,它彻底消解了历史自身的主体能动性,破解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封闭体系,张扬了现实的人的自由和尊严。
然而,为了使历史唯物主义获得所谓的科学的名义,为了谈论历史的必然性,那些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不自觉地抹去历史中的现实的人的主体能动性,总是大谈特谈所谓的历史目的,而从来都不关注现实的人的目的和价值。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深刻的哲学变革就化为泡影了,历史唯物主义被抽象化为传统的历史哲学。很显然,教条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正视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因而也就不可能真实地应对现代性的价值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代越来越被人们所疏远的根本症结之所在。可以说,破解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发掘历史唯物主义中潜在的应对现代性的价值虚无主义的理论资源,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理论任务。
二、现实历史的澄明与人类价值诉求的历史性原则
黑格尔撇开人的现实活动而考量历史的必然性,抹去了历史中的人的主体能动性和价值,致使历史自身成为在人之外的、有着独立目的的能动主体,而现实的人的价值和尊严则被完全抹杀。尽管同黑格尔一样,马克思的历史观也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但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主体不再是抽象的绝对主体,而是内蕴于历史中的、具有实践本性的有限主体,也就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在这里,现实的人已经不再被动地从属于历史,历史的抽象目的完全被还原为人的目的,而作为“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历史只不过是现实的人的外在存在形式而已。历史唯物主义彻底彰显了历史中的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从而也就为真正确证人的价值和尊严、克服价值虚无主义提供了可能。
人们一般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看作是系统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文本,并主要从该著作出发来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确实,在该著作中,马克思着重表达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本质不同,并在具体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的基础上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全新的运思路向。马克思着重强调,不管是黑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所悬设的“最高理想”的抽象性的指责,还是青年黑格尔派对老黑格尔的反思,都是在传统形而上学的地基上进行的,都把人的现实价值蒸馏为抽象的彼岸的价值;而与这种历史唯心主义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则强调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而且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现实历史的地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66-67。
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受到黑格尔的深刻影响,经历了从一位黑格尔主义者逐渐转向同黑格尔进行对抗的道路。《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马克思同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的一个节点,它强烈地透露出马克思对那些“哲学家们”离开现实的历史而抽象地思考历史规律的反感。也正是在针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意义上,马克思才针锋相对地提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82。但这里需要重申的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是针对思辨的历史哲学亦即历史唯心主义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颠倒;一旦脱离同思辨历史哲学争辩的语境,马克思就已经不再教条地强调抑或放大所谓的“决定关系”了,更没有抛开“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而抽象地谈论过所谓的历史规律和历史目的。在考察现实历史时,马克思始终坚守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然而,教科书哲学中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却恰恰是脱离了马克思对思辨历史哲学批判的语境,而无限度地放大了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西方学者所一再批评的“经济决定论”。教科书哲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导致了极为严重的理论后果,这就是,它在根本上窒息了马克思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强烈关注,把观照人的现实价值的历史唯物主义抽象化为同黑格尔三段论式的历史哲学同质的普遍公式和万能钥匙。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表达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纲领及其全新的运思路向的话,那么,《资本论》则是马克思对“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论澄明。正如有学者指出,《资本论》“在人类思想史上史无前例地揭示了‘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揭示了‘现实的历史’即‘存在’的秘密”[4]。作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资本论》一方面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澄清了人的历史形态的依次演进,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另一方面,《资本论》又基于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形态,确证了与这种历史性形态相适应的人的价值诉求。具体言之,在传统社会中,现实的人是依赖于社会和他人的,因而与此相适应,旧形而上学家的历史任务就是通过确立总体性的伦理共同体来为这种“人的依赖关系”奠基;近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呼唤主体意识的觉醒,要求彰显人的自由和独立性,所以近代哲学家们展开了对传统形而上学所悬设的“最高价值”的批判,并指认了基督教的虚无本质,但是,由于现代人的独立性依然是建立在对资本这个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整个的近代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并没有在根本上摆脱“抽象”对人的统治,更不可能彻底破解传统形而上学所悬设的“最高价值”的幻象。“黑格尔的哲学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态,这就是人们正在受‘抽象’的统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生存状态”[5]。
很显然,人类的价值诉求不可能是绝对主义的,它始终会随着现实历史的发展而表现出时代性和历史性,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人的价值诉求会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潭,恰恰相反,它会具有一种时代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就是人类价值诉求的历史性原则。历史不是抽象的过程性原则,而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每一代人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来进一步创造历史的,因而每一代人都会有不同的生存境遇和生命体验,进而就会有不同形式的价值诉求。马克思澄清了人类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而也澄清了人的价值诉求的历史性转换。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人类文明活的灵魂,根本上说,它是适应于人类历史性的存在方式的。《资本论》真切地表明,不仅人类的发展是历史性的,而且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人类价值诉求也是历史性的。人类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实现哲学家们所设定的“最高价值”,哲学家们所设定的“最高价值”只是人类所无法企及的价值幻想,它必然导致价值虚无主义。正因为如此,只有积极建构符合时代发展的价值理想,才能真正指引人类的现实发展。
《资本论》立足于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最高价值”的幻相,而且还确证了人类价值诉求的历史性原则,这就为彻底规避价值虚无主义提供了可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人的解放”的价值理想,并不是游离于历史之外的抽象目标,而就是现实的历史的运动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87。
三、解放的旨趣与价值虚无主义的克服
从思想史上看,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实质的诊断最为引入注目。在尼采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实质就是“价值形而上学”,这种“价值形而上学”设定了最高价值的存在,但也同时设定了最高价值自我贬黜的可能性。换言之,传统的价值形而上学潜在地暗含了价值虚无主义的可能,“而当这些最高价值表明自己具有不可企及的特性时,它们的贬黜也就已经开始了。生命因此就显得是不适宜于这些价值的,根本无能于实现这些价值。因为这个缘故,本真的虚无主义的‘预备形式’就是悲观主义”[6]910。尼采由此认为,对价值虚无主义的克服,必须突破传统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视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根本上规避“最高价值”的幻想,彻底抵制任何形态的价值虚无主义的可能来袭。这就是为什么尼采会对近代以来那些启蒙哲学家们所高歌的理性和自由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尼采说:“虚无主义不能从外部来加以克服。仅仅用另一个理想,诸如理性、进步、经济和社会的‘社会主义’、单纯的民主之类的东西,来取代基督教的上帝,从而试图把虚无主义强行拆毁和排除掉——这样做,是克服不了虚无主义的。”[6]431然而,尼采以反传统形而上学的方式来克服价值虚无主义的思路——以权力意志的绝对价值来取代传统形而上学的最高价值——也并不成功,所以后来的海德格尔深刻地批评了尼采克服价值虚无主义的设想。
马克思尽管在其全部著作中没有像后来的尼采那样系统地讨论价值虚无主义的问题,但在对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批判中,他已经深刻地体认到了现代人的价值虚无主义命运。马克思说:“宗教就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的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3]1-2但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作为世俗国家基础的宗教就消解了,人们的现实生活由此而失去了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3]274-275《资本论》表明,资产阶级之所以会彻底摧毁以往的神圣形象和最高价值,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内在运作的资本逻辑。正是资本逻辑的运作,以往一切形而上学所设定的“最高价值”都被瓦解了,人类陷入无所适从的价值虚无主义困境之中。但如马克思所说,“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伤感的眼泪,我们可没有”[7]150。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摧毁以往封建主义的等级秩序及与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是积极的和进步的,问题只在于,资本主义在瓦解“人的依附性关系”的同时,并没有真正挺立起人的自由和尊严。毋庸置疑,现代人的自由和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之上的,离开资本这个物,现代人的一切价值理想都是空谈。马克思说:“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7]28
可以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在一开始就决定了资产阶级所宣称的所有价值理想都具有伪善的性质。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所谓的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7]40。在这里,“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离的基础上”。“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7]41。正因为如此,当人们热情高涨地呼喊资产阶级所主张的平等、人权、自由的时候,马克思则开始着力于揭露这些价值的伪善本质。
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限度在根本上决定了现代人不可能获得真实的尊严和价值,而只会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价值虚无主义困境之中。尼采对现代性的价值虚无主义的洞见,可以说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作为尼采的先行者,马克思早已经不再像那些“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们”那样,企图通过重建某种“最高价值”来抵制价值虚无主义的来袭,而是直接诉诸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力求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资本论》最终通过瓦解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的资本逻辑,以“人的解放”的旨趣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现实的道路。
海德格尔指出,尼采仅仅探讨价值而遗忘了价值的来源即存在,因而尽管他深刻地揭露了现代人的价值虚无主义命运,但却没有能够真正完成对价值虚无主义的克服。对于马克思来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72。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真正深入到现实历史的本质性之中,它通过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伪善性质,而且还为人类真正走出价值虚无主义的困境提供了可能的道路。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0(2).
[5]孙正聿.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与后形而上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8(3).
[6]海德格尔.尼采(上册)[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16366/j.cnki.1000-2359.2016.02.002
2015-10-17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BS10)
B018
A
1000-2359(2016)02-0006-05
刘雄伟(1983-),男,陕西绥德人,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哲学基础理论、历史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