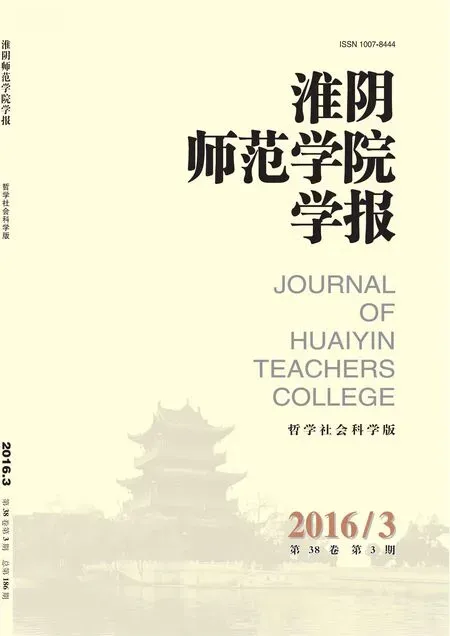“诗世界里先维新”
——林纾《闽中新乐府》的诗歌史意义
胡全章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诗世界里先维新”
——林纾《闽中新乐府》的诗歌史意义
胡全章
(河南大学 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戊戌变法前夕,在梁启超参与筹划并遥控指挥的澳门《知新报》连载的畏庐子《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以时政纠弹和陋俗批判为两大主题类型,旨在振民气、启民智、新民德以救亡图存,表现出鲜明的启蒙动机和近代色彩,属于“新派诗”序列。《知新报》其后成为诗界革命延展到华南地区的新阵地;《闽中新乐府》大体符合梁启超其后提出的“诗界革命”的创作纲领与革新方向,且对梁氏策划《新小说》“新乐府”栏目及该杂志刊发的一批新乐府诗歌起着示范作用,洵为诗界革命之先声。
关键词:林纾;《闽中新乐府》;《知新报》;诗界革命
林纾不以诗名。他早年自认不会作诗,晚年刻诗集时却自视甚高,自言“吾诗七律专学东坡、简斋;七绝学白石、石田,参以荆公;五古学韩;其论事之古诗则学杜。惟不长于七古及排律耳”[1]。不过,畏庐老人晚年刻印的《畏庐诗存》,并不包括壮年时写作的《闽中新乐府》。然而,林纾去世不久,胡适却对其30年前的旧作《闽中新乐府》刮目相看。历史的吊诡之处常常在于,作者的自我体认和后世史家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乃至完全相左,林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林纾心目中,他的古文第一,翻译小说只能忝列末席;然而,他以“林译小说”垂史,晚年则因为桐城古文护法而被新文化阵营斥为“桐城谬种”。就其诗歌而言,后世史家鲜有对他颇为得意的《畏庐诗存》感兴趣者,而他自言“目不知诗,亦不愿垂老冒为诗人也,故并其姓名逸之”[2]的《闽中新乐府》,却因种种原因而得以为世人所知;尽管如此,该组诗的诗歌史意义至今尚不甚明了。本文所着重探讨的,就是畏庐子《闽中新乐府》的诗歌史意义。
一、“很通俗的白话诗”
1924年金秋时节,林纾走完了充满传奇色彩却在晚年饱受新文化阵营诟病的不平凡的坎坷人生路。当他活着的时候,新文化阵营的一批干将们对他口诛笔伐,斥其为“妖孽”和“谬种”;当他带着对古文的眷恋和无限的遗恨溘然长逝,新文化阵营却又有不少人发文表示感念之情,说起他的好话来。是年,胡适从高梦旦处借阅《闽中新乐府》后,很受触动;干了多年笔仗,蓦然回首,已然誉满全球的适之先生突然发现这位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反对派,原来早在30年前就曾写过“很通俗的白话诗”,可说是近代白话文学的先驱者和老前辈。于是,这位几年前林纾在小说《荆生》中所描写的被一伟丈夫痛打的自美洲留学归来而能哲学的狄莫所影射的冤家对头,现在宣称要做一件“林先生梦想不到的”事,那就是在《晨报》披露一批“林琴南先生三十年前做的白话诗”;不仅如此,他还特意撰写了《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一文,为这位昔日文化战线上的老对手说了一番公道话:“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3]
作为新文坛和新学界的领军人物,胡适这一评价自然非常重要。林纾作为公然对抗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臭名昭著”的“桐城谬种”,原来曾经是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这对于五四新文学界和其后的新文学史家重新认识并非仅仅是卫道的古文家和不懂西文的小说翻译家的林纾,无疑产生了积极影响,发挥了正面效应。然而,就诗言诗,胡适只字不提晚年林纾颇为看重的《畏庐诗存》,而单单拈出壮年林纾教书之余写就的以少年儿童为拟想读者的《闽中新乐府》予以褒扬,赞其为“很通俗的白话诗”,这一选择和定位,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或者说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胡适是五四新文学界公认的白话新诗运动的发起人和最早的白话新诗尝试者,他评价《闽中新乐府》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其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维新党,二是“这些诗都可算是当日的白话诗”。[3]前者是思想尺度,后者是语言艺术法则。两条评价标准之中,胡适看好的自然是后者;如果够不上“白话诗”的条件,胡博士是不会对它高看一眼的。照适之先生当时的标准,只要是“白话诗”,就是“活文学”,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诗歌;反之就是“死文学”,至少也是“半死的文学”。用这一标准来定位十几年前林纾的《闽中新乐府》,显然是用五四的眼光和标准来重新选择和评判前人的文学创作,旗帜鲜明的先见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偏见,其结论之以偏概全在所难免。
尽管胡适在为林纾盖棺论定时肯定了其《闽中新乐府》,然而在近百年来的文学史书写中,《闽中新乐府》却很少被述及;即便提及,亦多一笔带过。1922年,胡适在那部被后世史家奉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开山之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也只是从“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这一方面立论,言其小说翻译成绩“替古文开辟了一个新殖民地”,而对其诗歌创作则只字不提。[4]这一最早出现在文学史论著中的关于林纾的评判文字,对此后林纾以何种面目出现在中国近世文学史叙述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叙述视角与基本论调,至今仍被文学史家所沿用。此后,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大体接续胡适的学术眼光,只讲林译小说;卢冀野《近代中国文学讲话》(1930)认为林纾“在近代文学上的地位,是他的翻译小说”[5],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1940)亦认为“林氏的翻译西洋小说,正是他对于近代文学的大贡献”[6],而对其诗歌均只字不提。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则着意突出作为古文家的林纾。建国后的主流文学史和几种专门的近代文学史著作,如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1960)、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王飚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近代文学》卷(1997)、关爱和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2013)等,述及林纾,亦大体只讲林译小说,至多在桐城派古文的衰变脉络里再顺带提一下林纾。只有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述及林纾《闽中新乐府》,言“林纾的诗,以《闽中新乐府》影响最大”,并列举《兴女学》等例,将其定位在“歌诀”,言其“从艺术上看并无太高的成就”。[7]
那么,林纾《闽中新乐府》到底有没有在近代文学史书写上一笔的价值?如果有,其独到的贡献或突出的意义何在?笔者以为,《闽中新乐府》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其艺术成就之高低和是否能传之后世,而在于其在当时的启蒙功效和诗体探索意义。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原本就是两回事;许多文学价值不高的作品,反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时至今日,我们该如何定位这部胡适称之为“很通俗的白话诗”呢?这就要回到晚清的历史语境,从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脉络中——尤其是诗界革命运动和新派诗的渊源流变以及近代报刊视野中——予以关照,方能看清楚其在当时趋新的诗歌创作潮流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值得进一步发掘的文学史意义。
二、“以歌诀感人”
林纾《闽中新乐府》写于甲午败绩、马关签约之际,1897年由魏翰出资在福州刻印成书,1898年3至5月又在维新派主办的澳门《知新报》旬刊上连载,署名“闽中畏庐子”。多年以后,知友高梦旦交代其写作动因道:在“甲午之役,我师败于日本,国人纷纷言变法,言救国”的危亡之秋,林纾“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已”,“以为转移风气,莫如蒙养,因就议论所得,发为诗歌”。[8]启发蒙昧,救亡图存,是壮年林琴南创作这组新乐府诗的直接动因。作者在开篇交代其创作宗旨道:“儿童初学,骤语之以六经之旨,茫然当不一觉,其默诵经文,力图强记,则悟性转窒。故入人,以歌诀为至。闻欧西之兴,亦多以歌诀感人者。闲中读白香山讽喻诗课少子,日仿其体,作乐府一篇,经月得三十二篇。”[2]此时的村学究畏庐子,何以知晓“欧西之兴”亦“多以歌诀感人”?可见,林纾创作《闽中新乐府》的动因及其所选择的文学形式,既有危亡时局的刺激和白居易乐府诗的熏陶,又有域外文学思想的启迪。
关于林纾甲午前后所受域外文化观念和文学思想影响的情形,邱炜萲在1901年问世的《挥麈拾遗》中谈到林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时,写过一段非常重要却至今仍不太受人关注的回忆文字:
最后讲时务经济之学,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各后起英隽所矜式……若林先生固于西文未尝从事,惟玩索译本,默印心中,暇复昵近省中船政学堂学生及西儒之谙华语者,与之质西书疑义,而其所得,以视泛涉西文辈,高出万万。观此,并可愧膠庠旧学者固步自封者矣。间出绪余,直柕胸臆,如《闽中新乐府》一书,养蒙者所宜奉为金科玉律……又闻先生宿昔持论,谓欲开中国之民智,道在多译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始,故尝与通译友人魏君、王君,取法皇拿破仑第一、德相俾士麦克全传属稿,草创未定,而《茶花女遗事》反于无意中先成书,非先生志也。[9]
壮年林纾讲求时务经济之学,遍览东西洋书刊译本,还曾尝试过翻译当时属于“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范畴的泰西近世伟人传记,可谓梁启超后来倡导著译政治小说的先驱人物。
假如当年林纾译著的《法皇拿破仑第一》《德相俾士麦克全传》率先完稿,并在戊戌前后问世,林纾的命运和近世西洋小说翻译的历史走向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那时,梁启超东渡后创办了《清议报》,开始倡导“译印政治小说”,并将译著政治小说的计划付诸实施;林纾上述“草创未定”的作品自然属于广义的政治小说序列。康门弟子邱炜萲私下里引林纾为同道,这一点从上述谓《茶花女逸事》“非先生志也”的断言中不难看出。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事实是:林纾译著的《法皇拿破仑第一》《德相俾士麦克全传》草创未定,反而让“非先生志也”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占了先机,出版后一纸风行,林纾作为小说翻译家的基本面目因此而被定格;而梁启超则以政治小说为主打品牌,此后又依托《新民丛报》《新小说》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小说界革命”。这一结局,使得本来可能成为西洋政治小说译著先行者的林纾,最终与梁氏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失之交臂。
林纾欲“以歌诀感人”的《闽中新乐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传甚广,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1897年魏翰出资在福州刻印后,很快邱炜萲又出资在南洋翻印,“赠贻岛客,复採其专辟乡里陋俗之数题,载入《五百石洞天挥麈》”,誉其为“养蒙者所宜奉为金科玉律”。[9]而戊戌变法前夕连载《闽中新乐府》的澳门《知新报》,其发行地点除澳门本埠外,在上海设有分馆,在香港、广州、福州、天津、星架波(新加坡)、仰光、暹罗(泰国)、横滨、神户、雪梨(悉尼)、鸟丝仑其利茂(新西兰商埠)、威灵顿(惠灵顿)、檀香山、域多利、温哥华、旧金山、满地可(蒙特利尔)、舍路埠(西雅图)、砵仑(波特兰)、猫失地埠(北美港口)、气连拿(海伦娜,美国蒙大拿州州府)、波士顿等地设有代派处;[10]“于五洲大小各埠皆週通遍达”[11],在华南、华东地区和南洋、北美的海外华人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三、时政纠弹和陋俗批判
照其门弟子朱羲胄的说法,畏庐子《闽中新乐府》“皆由愤念国仇,忧闵败俗之情,发而为讽刺之言,亢激之音”[12],体现出强烈的民族危亡意识、政治改革意念和社会批判精神。《闽中新乐府》计29题32首,仿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之式,一诗一事,一事一议,均含讽喻之旨;其取材倾向和主题意向,大体可归结为时政纠弹和陋俗批判两大类型。
《闽中新乐府》组诗中的时政纠弹主题,机锋所向,涵盖内政、外交、教育、兵制、宗教、吏治、税收等领域。如《国仇》篇旨在“激士气也”,《渴睡汉》旨在“讽外交者勿尚意气也”,《五石弓》旨在“冀朝廷重武臣也”,《村先生》旨在“讥蒙养失也”,《兴女学》旨在“美盛举也”,《獭驱鱼》旨在“讽守土者勿逼民入教也”,《关上虎》旨在“刺税厘之丁横恣陷人也”,《破蓝衫》旨在“叹腐也”,《谋生难》旨在“伤无艺不足自活也”,《哀长官》旨在“刺不知时务也”,《饿隶》旨在“讥役人失其道也”,《郭老兵》旨在“刺营制也”,《知名士》旨在“叹经生诗人之无益于国也”,《番客来》旨在“悯去国者之怀归也”,《灯草翁》旨在“伤贫民苦于税券也”……寄寓着振砺民气、张我国权、爱国尚武、兴办女学、改良吏治、重视工商、发展经济、税制改革、兵制改革等思想主张,要皆以爱国自强、雪我国耻、变法图强为旨归。
我们选《知名士(叹经生诗人之无益于国也)》一篇看看:
知名士,好标格,词章考据兼金石。考据有时参说文,谐声假借徒纷纭。辨微先析古钟鼎,自谓冥搜驾绝顶。义同声近即牵连,一字引证成长篇。高邮父子不敢击,凌轹孙洪驳王钱。既汗牛,复充栋,骤观其书头便痛。外间旁事烂如泥,窗下经生犹作梦。白头老辈鬓飘萧,自谓经学凌前朝。偶闻洋务斥狂佻,此舌不容后辈饶。有时却亦慨时事,不言人事言天意。解否暹罗近渐强,一经变法生民康。老师枉自信干羽,制梃岂堪挞秦楚?既适裸国当裸身,变通我但专神禹。方今欧洲吞亚洲,噤口无人谈国仇。即有诗人学痛哭,其诗寒乞难为读。蓝本全钞陈简斋,祖宗却认黄山谷。乱头粗服充名家,如何能使通人伏?卢转运,毕尚书,昨有其人今则无,名士名士将穷途。[13]
既嘲笑埋头故纸堆、头脑冬烘、不问时事、不识时务的汉学家,又讥刺作诗以宗宋为风尚的学宋诗人,在倡导时务经济之学和变法自强主张的同时,流露出对不能学以致用的名士之学和学古不化的名士之诗的鄙薄之情,其思想见解和报国志向可谓超越流俗。
《闽中新乐府》组诗中的陋俗批判主题涉及面很广,举凡缠足、溺女、虐婢、齐醮、看相、跳大神、看风水、检日子等社会百相,以及鸦片流毒、庸医误人、士夫迷信、术家青盲、道士敛财、和尚富足等怪现状,都在闽中畏庐子针砭之列。如《小脚妇》旨在“伤缠足之害也”,《水无情》旨在“痛溺女也”,《棠梨花》旨在“刺人子惑风水之说不葬其亲也”,《非命》旨在“刺士大夫听术家之言也”,《跳神》旨在“病匹夫匹妇之惑于神怪也”,《灶下叹》旨在“刺虐婢也”,《生髑髅》旨在“伤鸦片之流毒也”,《杀人不见血》旨在“刺庸医也”,《检历日》旨在“恶日者之害事也”,《郁罗台》旨在“讥人子以齐醮事亡亲也”,《肥和尚》旨在“讥布施无益也”等,寄寓着反迷信、讲科学、反缠足、倡女权、反陋俗、倡新风、反特权、倡民权等思想意蕴。
我们以《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为例,全诗共三段,开篇一段言:
小脚妇,谁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左靠妈妈右靠婢,偶然蹴之痛欲死。问君此脚缠何时,奈何负痛了无期?妇言侬不知,五岁六岁才胜衣,阿娘作履命缠足。指儿尖尖腰儿曲,号天叫地娘不闻,宵宵痛楚五更哭。床头呼阿娘,女儿疾病娘痛伤,女儿颠跌娘惊惶,儿今脚痛入骨髓,儿自凄凉娘弗忙。阿娘转笑慰娇女,阿娘少时亦如汝,但求脚小出人前,娘破功夫为汝缠。岂知缠得脚儿小,筋骨不舒食量少。无数芳年泣落花,一弓小墓闻啼鸟。[14]
以明白如话之语,状写出女儿缠足的痛苦情状,极具感染力和启蒙功效。该篇虽无新名词和新意境,但有新情感和新眼光;民间口语的大量采用,通俗易懂,活泼清新,易于传诵。
无论是时政纠弹主题,抑或是陋俗批判主题,其核心宗旨均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报国仇、雪国耻、强国基、张国权,成为贯穿《闽中新乐府》组诗的一条红线,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19世纪末年呐喊出时代先觉者的悲怆的呼声,奏响了时代的强音。首篇以《国仇》命名,系开篇点题,开宗明义:“国仇国仇在何方,英俄德法偕东洋”,“我念国仇泣成血,敢有妄言天地灭”。[15]念及国仇,诗人悲愤难抑,大有不报国仇誓不为人、不雪国耻死不瞑目之势;报国仇、雪国耻,实乃林纾创作《闽中新乐府》的思想情感原点。“方今欧洲吞亚洲,噤口无人谈国仇”[13],此情此境令一介书生闽中畏庐子大为愤慨。第四篇《村先生》有言:“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法念德仇亦歌括,儿童读之涕沾襟”,“强国之基在蒙养,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16]国仇似海深,雪耻靠少年,所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此之谓“国之基在蒙养”;“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17],此之谓“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兴女学》有言:“母明大义念国仇,朝慕语儿怀心头。儿成便蓄报国志,四万万人同作气。女学之兴系匪轻,兴亚之事当其成。”[18]倡导女学的动因,亦在报国仇、雪国耻;而其最终目标,在于振兴中华。
四、诗界革命之先声
白居易的新乐府讽喻诗追求妇孺能晓的通俗平易效果,林纾《闽中新乐府》亦以质朴自然、平易畅达为基本风格。或许正因如此,胡适将其定位为“很通俗的白话诗”。然而,从其创作面貌来看,《闽中新乐府》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白话诗”,而是半文半白、中西兼采的较为通俗的近代歌诗,语言的近代化与白话化是其鲜明特征,与不久之后梁启超提出的“新意境”“新名词”“古人之风格”三长兼备的“诗界革命”创作纲领[19],倒是有几分暗合;尽管并非所有32首诗作都采用了新名词,亦非每篇都有“新意境”,要皆时代色彩浓郁,无论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考察,抑或从诗体语体方面来衡量,多数诗篇均可纳入“新派诗”行列。
我们以首篇《国仇(激士气也)》为例,看看其鲜明的新派诗特征:
国仇国仇在何方,英俄德法偕东洋。东洋发难仁川口,舟师全覆东洋手。高升船破英不仇,英人已与日人厚。沙侯袖手看亚洲,旅顺烽火连金州。俄人柄亚得关键,执言仗义排日本。法德联兵同比俄,英人始悔着棋晚。东洋仅仅得台湾,俄已回旋山海关。铁路纵横西伯利,攫取朝鲜指顾间。法人粤西增图版,德人旁觑张馋眼。二国有分我独无,胶州吹角声鸣鸣。闹教閧兵逐官吏,安民黄榜张通衢。华山亦有教民案,杀盗相偿狱遂断。蹊田夺牛古所讥,德已有心分震旦。虎视眈眈剧可哀,吾华梦梦真奇哉。欧洲尅日兵皆动,我华犹把文章重。廷旨教将时事陈,发策试官无一人。波兰印度皆前事,为奴为虏须臾至。俄人远志岂金辽,德国无端衅屡挑。英人持重迟措手,措手神州皆动摇。剖心哭告诸元老,老谋无若练兵好。须求洋将练陆兵,三十万人堪背城。我念国仇泣成血,敢有妄言天地灭。诸君目笑听我言,言如不验刳吾舌。[15]
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新名词与流俗语冶为一炉,新思想与旧风格相互交集,可谓词驳今古,理融中外。林纾以乐府歌诀的旧形式抨击时弊、发抒时感,以达到振民气、启民智、新民德功效的创作活动,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作,而是经过长期酝酿和对诗歌艺术形式的认真探究,才选择了这种可以容纳更多时代内容、诗体语体又较为平易自由的诗歌形式。
1902年8月,梁启超在为即将问世的《新小说》规划栏目时,拟将“有韵之文”设置为“新乐府”专栏,并明确指示“专取泰西史事或现今风俗可法可戒者,用白香山《秦中》《乐府》、尤西堂《明史乐府》之例,长言永叹之,以资观感”。[20]在《新民丛报》刊发《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宣传广告不到半个月,梁氏又迫不及待地专门为计划中的《新小说》“新乐府”栏目刊发《征诗广告》,言“《新小说》报中有新乐府一门,意欲附輶轩之义,广采诗史,传播宇内,为我文学界吐一光焰”,并将其分为“咏史乐府”和“感事乐府”两大类,指出前者“如尤西堂《明史乐府》之体,论西史尤妙”,后者“如白香山《新乐府》之体,专以直陈中国今日时弊为主”。[21]可见,在梁氏的最初规划中,题咏中西史实的“咏史乐府”和“专以直陈中国今日时弊为主”的“感事乐府”,是《新小说》诗歌专栏的基本特色。这一设计,其实是畏庐子《闽中新乐府》的扩大版,不过将其题材和地域扩大到全国和泰西而已。
尽管梁启超最终听取了黄遵宪的建议,将《新小说》诗歌栏目定名为“杂歌谣”而非初拟的“新乐府”,但新乐府歌诗仍然是“杂歌谣”专栏非常重要的板块。白居易《新乐府并序》所言“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的指导思想,本身就体现出诗体解放精神,其“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的创作宗旨[22],也与梁氏重“革其精神”而非“革其形式”的诗界革命指导思想有着深度的契合。明乎此,就不难理解饮冰室主人缘何对“白香山之《新乐府》”如此推许,也就明白了壮年林纾缘何选择这种诗体创作《闽中新乐府》。
《新小说》“杂歌谣”专栏刊发了燕市酒徒《辛壬之间新乐府》、哀郢生《汨罗沉乐府四章有序》、金城冷眼人《潮州报效新乐府有序》、水月庵主《支那新乐府三十章》、雪如《新乐府十章》等新乐府体组诗,均系“以古韵谱近事有关时局之文”[23],约占该栏目三分之一版面。我们以雪如《新乐府十章》为例,只消浏览一下十个小标题及其标示的题旨,便可知晓其题材倾向与主题意向。其一题《麟在槛》,旨在“思自由也”;其二题《怪咄咄》,意在“思张女权也”;其三题《赤帝子》,旨在“痛民智之不开也”;其四题《教民案》,旨在“悼同种之戕害也”;其五题《梅瑟约》,旨在“悲宗教也”;其六题《檀香山》,旨在“悯华工也”;其七题《朱门开》,旨在“刺巧宦也”;其八题《官不世》,旨在“病苛法也”;其九题《耕无器》,旨在“悯拙农也”;其十题《金满箧》,旨在“思开矿也”。[24]其所表现的铲奴性、张女权、开民智、新民德、讲群治、振国威、倡廉耻、清吏治、学科学等思想主张,《闽中新乐府》基本上都涉及了。忠君观念与爱国思想两位一体,新名词与流俗语并行不悖,思想半新半旧,诗体不今不古,内容和形式上均体现出过渡时代特有的过渡形态,亦与林纾《闽中新乐府》相仿。
近代报刊视野中的《闽中新乐府》,有着诸多耐人寻味之处。这一组诗在澳门《知新报》刊出两年之后,梁启超领衔发起的诗界革命运动才依托《清议报》《知新报》等近代报刊开展起来;又过了两年,梁氏在《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专栏谈及中西合璧的学堂乐歌创作中的甘苦,深有感触地说:“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25]对照几年之后饮冰室主人此番感慨,方知畏庐子《闽中新乐府》不仅在题材题旨方面开风气之先,而且在诗体试验与探索方面,亦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闽中新乐府》在梁启超参与创办并遥控指挥的澳门《知新报》连载一年半之后,丘逢甲《海上观日出歌》见诸《知新报》,其中有“完全主权不曾失,诗世界里先维新”[26]之句;又过了半年,康有为《闻观天演斋主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刊发在《知新报》,其中有“以君妙笔为写生,海潮大声起木铎”[27]之语。用这几句诗来评价畏庐子《闽中新乐府》的先锋作用和时代意义,亦堪称允当。“海潮大声起木铎”,敲响的是警世和醒世的警钟,吹奏的是革新图强的觉世之“潮音”;“诗世界里先维新”,体现出甲午败绩之后近代诗歌求用于世的功利性和词驳今古、理融中外的诗体解放精神。
丘逢甲和康有为这两首诗作见诸《知新报》时,历史的车轮已经走到了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揭橥“诗界革命”旗帜的《汗漫录》一文已于是年2月在《清议报》发表,梁氏领衔发起的诗界革命运动已经依托主阵地《清议报》开展起来;而澳门《知新报》几乎在同一时间(1900年2月)率先响应梁氏“诗界革命”之号召,开辟了“诗词随录”诗歌专栏。《知新报》这一举措,改变了此前林纾《闽中新乐府》只是作为一个特例和个案发表的状况,诗歌专栏自此成为其常规性栏目,在此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刊发了康有为、潘飞声、丘逢甲、邱炜萲、秦力山、蒋同超、李东沅等约50位新派诗人175首诗作,成为诗界革命运动起步阶段所依托的华南地区的报刊重镇。
我们再作一个假设:假如畏庐子《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见诸《知新报》的时间向后推迟一两年,不是在戊戌之年作为一个孤立的个案推出,而是在庚子之年梁启超揭橥“诗界革命”旗帜之后刊登在《知新报》辟出的“诗词随录”专栏,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效应呢?果如此,发表在“诗界革命”延展到华南的新阵地上的《闽中新乐府》,自然可以纳入诗界革命运动的脉络里被后人评说。然而,历史不能假定。林纾曾花费心血译著的政治小说因“草创未定”而未能成为近世西洋政治小说译著的先行者,致使林译小说与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失之交臂。《闽中新乐府》原本是梁氏倡导的“诗界革命”之先声,却又因其刊行过早,加之澳门《知新报》长期以来难见其真面目,直到最近几年,方有学者指出《知新报》作为“诗界革命”新阵地之基本史实[28],以致后世文学史家鲜有将《闽中新乐府》与“诗界革命”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者。
如果说黄遵宪19世纪70年代即已付诸实践的“新派诗”乃诗界革命之先导,1896年前后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试验小组一年多时间里秘密尝试的“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29]的一批晦涩难懂的“新学诗”为诗界革命之前奏,那么,与“新学诗”同期问世而在戊戌变法前夕刊发在其后成为诗界革命延展到华南地区的新阵地——澳门《知新报》——的畏庐子《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其题旨和诗体特征又大体符合梁启超其后提出的“诗界革命”的创作纲领与革新方向,且对其后梁氏策划《新小说》“新乐府”栏目及该杂志刊发的一批新乐府诗歌有着示范作用,洵为诗界革命之先声,这才是最有价值的诗歌史意义。
如果说黄遵宪的“新派诗”为梁启超领衔发起的诗界革命运动提供了符合“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诗学标准的新诗样板,夏、谭、梁三人尝试的“新学诗”为梁氏此后发起诗界革命运动提供了打破传统诗学网罗的精神力量和引新学语入诗的经验教训,那么,畏庐子《闽中新乐府》则在以传统新乐府体输入崭新的时代内容并对其进行近代化改造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闽中新乐府》所传达出的新思想、新情感、新意境及作为其表现手段的新名词、新语句,表征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晚清特有的近代化特征;其所体现出的通俗化、白话化、散文化趋向,既是晚清梁氏倡导的诗体多元化发展的“诗界革命”题中应有之意,亦是五四时期胡适倡导的白话新诗的创作方向。胡适所谓“很通俗的白话诗”,只是道出了其白话化特征;而其“新意境”“新语句”所体现出的近代化趋向,则未被提及。白话化并不代表近代化,白话文和白话诗自古有之;而近代化或欧化的取范路径,才是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为中国诗歌的近代化改造乃至现代化转型指出的更为重要的根本出路与革新方向,不过他自己将重心放在了“革其精神”,而将“革其形式”的历史任务留给了后来者。“诗世界里先维新”,在诗歌革新道路上,壮年林纾无疑是一位先行者和探索者。
参考文献:
[1]林纾.与李宣龚书[M]//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51.
[2]闽中畏庐子.闽中新乐府三十二首[J].知新报,1898(46).
[3]胡适.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N]//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北京:晨报社出版部,1924:267-268.
[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M]//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95-98.
[5]卢冀野.近代中国文学讲话·第二讲[M]//上海: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0:9.
[6]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J].学林,1940(1).
[7]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570.
[8]高梦旦.书《闽中新乐府》后[M]//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127.
[9]邱炜萲.挥麈拾遗[M]//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408.
[10]本馆各地代派处[J].知新报,1900(128).
[11]本馆告白[J].知新报,1900(128).
[12]朱羲胄.林畏庐先生年谱[M].上海:世界书局,1949:19.
[13]闽中畏庐子.知名士[J].知新报,1898(55).
[14]闽中畏庐子.小脚妇[J].知新报,1898(46-47).
[15]闽中畏庐子.国仇[J].知新报,1898(46).
[16]闽中畏庐子.村先生[J].知新报,1898(46).
[17]任公.少年中国说[J].清议报,1900(35).
[18]闽中畏庐子.兴女学[J].知新报,1898(46).
[19]任公.汗漫录[J].清议报,1900(35).
[20]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J].新民丛报,1902(14).
[21]征诗广告[J].新民丛报,1902(15).
[22]白居易.新乐府并序[M]//张春林.白居易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25.
[23]《新小说》第三号之内容[J].新民丛报,1903(25).
[24]雪如.新乐府十章[J].新小说,1903(5).
[25]饮冰子.饮冰室诗话[J].新民丛报,1904(57).
[26]南武.海上观日出歌[J].知新报,1900(113).
[27]更生.闻观天演斋主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J].知新报,1900(129).
[28]左鹏军.澳门《知新报》与“诗界革命”[M]//左鹏军.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论丛.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268-277.
[29]饮冰子.饮冰室诗话[J].新民丛报,1903(29).
责任编辑:刘海宁
作者简介:胡全章(1969-),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11&ZD110);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研究”(14FZW044)。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3-0367-07
收稿日期:2015-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