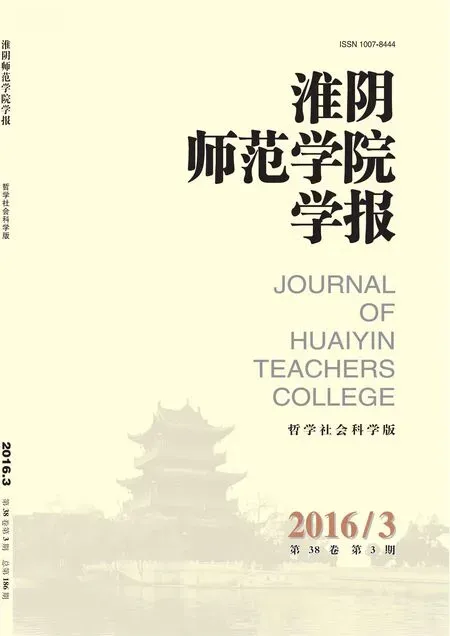明清慈善组织述论
赵海林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社会学】
明清慈善组织述论
赵海林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摘要:明清慈善组织主要有官办、民办两种类型。其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拨付,官员、乡绅和商人的捐献,田产与屋产的租赁,银款存典生息,分摊集资,行业抽提,等等。慈善机构的管理模式有董事制、半董事制、轮值制、委任制四种;救助管理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救济对象从本籍居民到流民、救助内容从分散到整合、救助对象筛选、在监督制度方面更加严格。明清慈善机构的发展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救助理念发生了变化,二是在清代组织出现了联合和协作,三是教养并重,四是慈善家群体出现;明清慈善组织发展进程呈现先官办再到民办,民办再到官办的一个波浪型过程。
关键词:明清时期;慈善组织;运作模式
中国慈善事业在元代一度衰落,明清时期(明代和清代中前期),随着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统治者的重视,慈善机构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一、慈善组织的性质
明清时期不仅出现新的官办慈善机构,而且涌现出大量的民间慈善机构,区分官办与民办慈善机构,一是看经费来源,二是看创建者和管理者的身份。
(一)官办性质。
官办慈善机构主要有养济院。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诏天下郡县设立孤老院,后改名为养济院。一般来说,养济院作为官办的慈善机构,其规模大小和维持时间的长短与政府所拨经费有极大的关系。明代各州县设一所养济院,个别财力宽裕的州县有两所。清代基本上沿袭明代旧制,顺治五年(1648)饬令:“各自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举行,月粮依时给发,无致失所,应用钱粮,察明旧例,在京于户部,在外存留项于动支。”(《清实录》顺治五年十一月辛未)清代养济院的设立已扩展到中国西部边陲地区,如四川、广西以及西北地区。设立养济院对边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政府在全国各地建置三种特别设施,即惠民药局、栖流所(留养局)和漏泽园。史载:“太祖高皇帝统一四海,即诏天下郡邑立养济院,设惠民药局,立义冢……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之政,无所不至。”(嘉靖《徽州府志》卷5《恤政》)由于统治者的倡导,惠民药局很快遍布全国各地,基本上也是每州县一至两所,经费由常平仓支出。入清后惠民药局便寂然消失[1]163。栖流所(留养局)作为官办的慈善机构,主要是收留外来的人口。当时大量的流民已经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栖流所是社会控制的产物,同时也说明明清社会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分化,由于城市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大量破产的农民进入城市,加上城市破产平民,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栖流所相当于收容遣送制度时期的收容遣送站。到清朝乾嘉之后,国家财力日趋困竭,栖流所开始逐渐由官办转为民间经营。
明末官办慈善机构奸弊深重。高攀龙曾斥之曰:“近来竟成弊薮,茕独不沾实惠,皆由吏胥添控诡名混冒。”(《高子遗书》卷7)明王朝采取过一些补救措施,如政府加强监管,以及提倡民间社会设善堂善会,救济贫者残疾之人。明后期,官办慈善组织逐渐式微。
(二)民办性质。
民办慈善机构有收容病人及无家可归老人的普济堂,收养弃婴的育婴社,有从事地缘性慈善活动的会馆,宗族慈善活动的义田(族田),还有惜字会、放生会、救生局、义渡局、清节堂、恤嫠会、掩骼会、白骨会等各种善堂善会。
清代普济堂为了弥补养济堂之不足而创立,最初由地方绅衿集资捐助创建,属于民间社会性质的慈善机构。王廷献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倾尽家产,在京师广宁门外建立普济堂,专门收容“老疾无依之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顺天府尹钱晋锡向朝廷汇报普济堂事迹,康熙帝深受感动,亲题御制碑文,并赐“膏泽回春”匾额,以示鼓励与支持,此举震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由于得到统治者的首肯和赞许,加上地方绅士、商贾鼎力支持,同时各州县“时加奖励,以鼓舞之”,普济堂得到迅速发展,遍及大江南北,成效远超出官办的养济院。在乾隆前期,普济堂主要靠地方绅士商贾的支持;乾隆中后期,由于行政力量的介入,普济堂的性质也悄然发生变化,逐渐由纯民间慈善组织转变为官督民办、官民合办的慈善组织(也有个别的甚至完全成了官办的慈善组织)[1]155。夫马进指出,由于新型的善堂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国家随即有意识地将之官营化,并认为近代中国的国家灵活性促使其吸收这些新型的善堂,反过来又增强了自身的灵活性,维持长治久安[2]。乾隆七年(1742)江苏高邮普济堂、育婴堂出现400两白银的赤字,便请求户部投入官产以资援助。民办的慈善组织在成长中也需要国家庇护和财政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善会和善堂,从公共事业成长这个观点来看,本身就包含着很大的矛盾。因而夫马进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
民间育婴事业在明后期开始恢复,约1634年蔡琏在扬州创办育婴社。扬州育婴社最初作为纯粹的民间慈善机构,主要依托定期的集会来发展会员和募集经费。清代开始普遍设立育婴堂,并逐渐向偏远的州县扩张,慈幼机构遍及全国。雍正二年(1724)颁布诏令,要求各府州县“养少存孤与扶衰恤老”,“照京师例推而行之”。乾隆之后,由于行政力量介入育婴事业,育婴堂已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逐渐演变为官督民办的慈善机构。经过雍乾时代的官僚化后,虽然大部分善堂发展得更有规模,但日后没落的种子也就此种下。问题之一就是冗员增加,贪污舞弊不断;二是善堂渐渐偏离原来济世的目标,成为衙门化的行政机构[3]。
二、慈善组织的经费来源
(一)政府拨付。惠民药局经费主要于常平仓支出。清代养济院设于州县一级,由政府拨款经营,各省州县俱设孤贫口粮,于正项内留支,遇闰加增(《正定府志》卷14)。恭城养济院于雍正三年建成,当时收养鳏寡孤独15名,由省拨给口粮,后定额为26名(同治《恭城县志》)。乾隆四十二年创办善化普济堂,湖南巡抚颜希深经奏请皇帝批准,动拨藩库银四万两(嘉庆《善化县志》卷5)。江西南昌普济堂也是“岁动公项及厘费银两,并节备仓谷石”(同治《南昌府志》卷12)。苏州府元和县育婴堂在乾隆时一次即得到官助银12 000两(同治《苏州府志》卷24)。政府还把田地划拨给善堂,如元和县广仁堂官府给土地5 966.06亩。
(二)官员、乡绅和商人的捐献。官捐在清代主要是捐养廉银,有士绅捐赠房屋田产,也有耆老捐献生日筵席费,民间捐献的内容和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在官捐方面,官带绅捐是主要形式,主要是地方官劝捐的乡绅银,乾隆十九年,知县吴慎捐傣50两,劝捐乡绅银800余两,各所建屋五间,余银750两(光绪《顺天府志》卷12)。民国24年编撰的《顺义县志》记载:“知县刘梦赉输银一百五十两,于乾隆二十九年商领劳动营运,后复劝输银七百两。”(《巴县志》卷17)
1710年,苏州士绅陈明智、顾如龙等集资在虎丘建普济堂,以收养病民,供给衣食药饵,略如京师善堂之制。初创时,普济堂均为民间力量兴办,仅依赖地方绅士、商贾鼎力支持,并无政府资助,但其绩效远远超出官办的养济院。同善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会员的捐献,每次捐献的金额,按照规定,从银九分到九钱不等。在聚会日由会员交给会计(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5)。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开始繁荣,商人成为地方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江淮盐商、晋商、徽商、粤商及江西商帮积极参与慈善事业,踊跃向慈善机构捐赠。在苏州义庄有5处为商人捐资兴办[4]。如红木梳妆业三义公所“无论开店、开作,归开主每月自愿,出捐一文善愿,并不外募,作为生养葬之费”[5]。
(三)田产与屋产的租赁,银款存典生息。如嘉善同善会置办土地,以地租收入来维持运营的需要(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5)。巴县体仁堂每年可收得田房租银约7 000元。沅陵救生局照将救生船经费,置产收租为每年所用(同治《沅陵县志》卷12)。同善会的经费主要依赖会员捐献。后来随着申请救济人数的增多,开始置办土地,以地租收入来维持运营[6]。乾隆十三年,直隶省各地普遍建立留养局,通省设局561处……通计140州、县、卫、厅,交商生息之银共45 500余两,收租土地143顷9亩[7]。
(四)会员捐赠与分摊集资。同善会的经费主要依赖会员捐献。每次捐献的金额,按照嘉善同善会的规定,从银九分到九钱不等,在聚会日由会员交给会计。崇祯五年嘉善同善会春季聚会时,共收到70份捐款,计银19两,平均每份银2钱7分左右。崇祯十三年春季聚会,共收到459份捐款,计银93两4钱1分、钱11 630文[8]。如在京江西会馆所定折席银,按京官、外官的官秩卑尊捐6—100两银,对科举及试职人员也有相应的规定。对入馆寄留者上及督抚,下及守备,都要捐赠相应的款额,作为会馆的慈善基金。到清中后期,分摊集资被会馆普遍采用。
(五)行业抽提是工商业会馆筹集善款的重要途径,即在工商业买卖收入中,每月抽提一定数额的收入作为善举之资。如苏州公所各业的善捐,纸业进货每两提捐五厘,石作业每做1 000文生意,提出钱20文(《天津府志》卷7);又如天津全节堂,于船捐项下酌提二成,各盐商按包捐制钱一文。上海徽宁思恭堂在同治年间“诸茶商助施衣食,复捐厘置产以裕经费”。清代商业发达的都市里的会馆,往往有赖于“各就所业抽厘,以扩充善举”[9]262。
善款来源日趋多样化,为慈善组织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慈善组织在筹资方面作了许多有效的探索,如小额捐赠,日常化捐赠。又如简捐,即商业店铺在门前挂一个竹简,任店主日捐钱若干,相当于现在慈善机构在一些公共场所设置的捐款箱。在劝募方面,有民劝,也有官劝;捐赠者重心下移,普通民众加入捐赠行列。恤政税的推行体现了从国家制度层面探索慈善组织发展的路径。但乾隆之后,慈善组织的经费更多来源于官府,受官府的控制也更加明显。
三、慈善组织的运作模式
(一)管理模式。
1.董事制。会首制、董事制是明清慈善组织的基本管理模式。会首、董事常不支薪水,或是象征性支取。会首、总董、总理及董事由内部共同选举产生,然后再选聘职员。如民办平湖普济堂设司岁一人,“择人品端方,身家殷实者,于四月初公举接办”(光绪《平湖县志》卷4)。另有司月六人,司旬三人,司堂一人,其中司旬以上为义务,司堂酌给薪。会首、会董值年值月轮值,具体事务由会首或会董聘请专职人员专司其职。
2.半董事制。苏州丰备义仓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其管理方式是“出纳官主之,士绅不与”,地方士绅只发挥监督与协助的作用,并不直接参与义仓的管理。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义仓重建,冯桂芬、潘遵祁等人提出在管理体制作了一定的变通,由官方直接经营管理改为“官绅互为经理”,江苏巡抚郭柏荫先后两次批示:“征收田租,由官由绅,均不免有流弊,今据请官绅,自属可行”,“今请官绅互为经理,虽与从前奏案稍有未符,而互相稽查,公事公办,洵足以昭慎重”[10],同意采取这种管理方法。
3.轮值制。轮值制是清初育婴堂重要的管理制度,在雍正帝没有大力推广育婴堂前,这种组织形态已经相当成熟,并被普遍采用[11]106-107。康熙初期的地方官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育婴堂轮值制度的标准化模式:“延请绅衿好义者董其事……每年十二人为会首,每月轮一人,使值一月之事,然会首未暇夙昔在堂,又必聘一老成有德者,居住本堂……其会首及硕德诸先生,凡有所劝募乐施组织者,每月择定某日会收,于三日前各会首及诸先生,即各用本堂知单传请,于是日早临本堂。值月者就本堂设馔恭候……不必用酒所以敬事……其乐施金钱,住堂管事及值月会首同收,按名登记,于收数后结一大总,以示同事……[每月收支帐目]于次月会收之日,当众交待下月会首接管……”司总每年由不同的人轮流担任,称为司年;事务主管每月由不同的人轮流担任,称为司月。司年只负总责,不须每天到堂管理,而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到堂检查工作,或遇有大事需要决策时到堂开会讨论。司月须每日在堂,管理善会善堂的日常事务。如无锡同善会是高攀龙等若干志同道合的人自发组织行善的团体,会首(称作“主会”)由会员(也称作“会友”)推荐产生,每年一换,轮流负责同善会的管理事务,他们要品行端正且具备管理能力。会员之间是松散、平等的关系,每季相聚一次,开展募捐和施善活动。
4.委任制。委任制实质上是政府对慈善事业直接干预的产物。在清代,规模较大的善堂承担了各地的主要救助任务,如果管理不善,救助水平下降,将会给社会治理带来严重影响。当民间士绅——董事管理不善时,政府会直接干预,派员进行管理。苏州府育婴堂一开始实行的是董事制,后因“司事经管失宜,房屋亦多倾圯”,在道光十六年(1836)改为委任制。苏州育婴堂管理层的分工如下:藩司代表政府对育婴堂进行管理,负责遴选委员,委员是育婴堂的总管,负责育婴堂具体的行政事务。总捕、同知负责育婴堂的监督。委任制适于层级多、分工细、管理复杂的组织结构,它能够适应大规模组织的管理需要,有利于集中权力和资源,但主要领导的权力过于集中,对藩司约束较少,经常会发生专权和贪腐事件。
(二)救助管理。
一是救济对象从本籍居民到流民。养济院主要救济对象是本籍居民,栖流所、留养局主要收容过往的贫困游民,会馆则主要救助同乡人士,实现“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11]67。养济院设于州县一级,一般只收养本籍孤老,乾隆初年还规定各省应收名额,这方面清代继承了明代传统[12]。乾隆年间下诏:各州县设立养济院,原以为收养孤贫,但因限于地额,不能一同沾惠,嗣后,如有外来流丐,察其声音,讯其住址,即移送各本籍收养。清代开启了对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的先例。救助管理强调地域性,以地域为主,但也考虑社会流动带来的游民。清代养济院,除额内孤贫(正额)外,还有额外孤贫,如云南、广东等地。广东的额外孤贫数还相当多。不过,无论额内还是额外孤贫,其享受的待遇大体相同,均有口粮,大都“遇闰加增,小建扣除”,另外冬令时节有棉絮,夏令时节给蚊帐[1]151-152。
二是救助内容从分散到整合。慈善机构的救助项目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明清会馆兴办了多种救助项目,涉及助学、助丧、施医、济贫四个方面。义庄慈善活动也是多方面的,以赈济同族贫困者为中心,涉及赡贫、恤病、助婚丧、养老、劝学、救急和恤嫠等项内容。明末,嘉善同善堂开展保洁、掩埋、济贫等活动,太平天国后,左宗棠重整慈善组织,以同善堂、普济堂为中心,统筹杭州善后事宜,同善堂下设施棺局、掩埋局、医局、牛痘局、义塾、给米所、城内外七粥厂,此外还有城乡报验、钱江救生及保甲、巡更、公举外省赈捐(宣统《杭州府志》卷73)。从分散到整合反映了慈善组织的发展壮大,同时慈善组织也意识到分散的状况不利于整合资源,不利于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三是救助对象筛选。同善会所救济的对象有所侧重,一般是贫困无依的孝子、节妇或迹行甚佳的极贫户,至于不孝不悌、赌博健讼、酗酒无赖及年少游手游食以至赤贫者一律不予救济。救助方面关注救济者的道德品行。明代的吕坤甚至主张在宗族内部也要对救济对象进行道德审查,“别贤不肖,不记恩仇,所以示公。不别贤不肖,无以示欢”。在此基础上,根据贫困程度分别进行救济,“赈贫分甚次,老疾分有无侍养”[13]。
(三)监督制度。
为了保证养济之政的推行,朱元璋将其载入《大明律》。《大明律·户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明后期,政府针对养济院出现的问题和弊端,派遣巡使、御史等官员赴州县加强督查,要求本县正佐官按月躬亲点阅给散,府官则一月两次巡视二者。到了清代管理制度更加严明,乾隆二年诏令:“按年造册报销,如冒滥克扣奉行不当,归例参处。”乾隆六年诏令对种种舞弊做出明确而具体的处罚。
四、慈善组织发展的新变化
(一)救助理念的变化。救济不仅仅是为了助贫,也有助于社会稳定。道光十一年(1831)邑令郭彬园在记文中提及扩建养济院对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夫川东为全蜀门户,江津又居重庆上游,贫民不安则富民不靖。”救助不仅仅是为了救助贫困者,也是为了整个社会。齐美尔从功能主义指出:援助穷人有助于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行;社会需要援助穷人,以便穷人不至于成为危害社会的危险的敌人,以使他们已衰弱了的力量转化为生产性的力量,以避免他们的后代进一步下滑[14]154。郭彬园对救助贫民的态度反映了当时对贫困问题的认识有较大的改变,认为贫困问题已经社会化,不再是个别人的贫困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因而救助贫民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二)清代慈善组织出现了联合和协作。清代慈善组织的功能逐步拓展。一方面是善堂内部分工日益细化和深化,从而提高了施善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是善堂开始涉足地方上如义学、禁烟会、水龙公所等公益性活动,丰富了慈善与公益的关系。慈善组织间功能整合趋强。乾隆年间育婴圈已在江南地区形成,但就其实效仍不理想,桐乡育婴堂自1866年至1876年,共死婴孩3 128口,几成“杀婴堂”。后来在邑绅严辰的建议下,于青镇成立了保婴总公所,下辖21分所,分产家自育、堂内乳养和堂外寄养3种形式,由此加强了育婴堂、保婴会与穷困产家的链接。“十四五年中共保婴四千有余,报殇不及一成。”清代江南地区的育婴机构不仅立足于以县治为中心的城区厢关,而且延伸到都图里甲一级,城有育婴堂,乡村亦有留婴堂、接婴所、保婴会等慈幼机构,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体系完善的育婴网络体系[1]163。
(三)教养并重。慈善组织从囿于重养轻教的传统救济模式开始转向关注教育及技能培养。育婴堂、普济堂、栖流所、清节堂都开展一定的劳作活动,虽然劳动规模有限,但其蕴含了近代社会救济的雏形;有条件的育婴堂把堂中男孩送入义学就学。同光杭州普济堂下设七斋,同善堂下设六斋,与普济分为上下塾,标志善堂直接从事社会教育,同时善堂间链接的加强也为育婴事业的创新奠定了基础。这种新型救济模式和理念对晚清慈善性工艺局的出现也有一定的积极影响[14]156。
(四)慈善家群体出现。在明末以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涌现出一大批热心慈善事业的慈善家。从明末的袁黄,至乾隆时期的彭绍升、道光年间的潘曾沂,以及稍后的冯桂芬、余治、谢家福等。从袁黄劝善开始,为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之后,慈善人物代有所出,前后踵继,虽各具影响,却是一脉相承,体现出劝善施济的传统,形成一个脉络清晰、相对完整的慈善家系谱。明清时期,在其他地区也有一批有影响的慈善家活跃在慈善事业上。
五、明清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简评
明朝初期官办慈善得到了发展,到明后期官办慈善逐渐式微,民间慈善组织迅速发展;而清代特别是乾隆之后,慈善组织逐渐官营化,民间慈善受到很大的抑制。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作为区域性中心,往往聚集了大量人口,尤其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从农村或其他地区来城镇谋生的人很多。那些无正当职业的流民和依靠微薄工资过活的雇工,形成了城镇中的贫民阶层。他们一旦遇到天灾人祸,或是生老病死等人生紧要关头,往往由于赤贫而处于无助的境地。针对此种状况,社会性与服务性、蠲恤救济性、公共设施性的社会组织就应运而生。
民间慈善得到较好发展后,国家便有意识地将之运用到传统的鳏寡孤独政策中去,雍正帝的上谕,杨名时的上奏和王士俊的实践[2]425都体现了这一点。从明初政府推行官办慈善组织到清代再次官营化,反映了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慈善组织设立是作为国家教化民众的一种方式,国家也将之视为半官办的组织,雍正要求有“地方之责”的人“宜时加奖劝以鼓舞之”,在位之人“倡率资助”,并下令“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可照京师例推而行之”(《世宗实录》卷19)。乾隆九年(1744),浙江布政使为同善会立案,并颁布会规大旨,刊示晓谕鼓励全省十一府一州仿办:“无论绅衿士庶,务访平日品行端方者,俱准创行”,但是需严防“经由役吏以耆民乡正之手”(民国《丽水县志》卷4)。因此,即使对于大量依靠私人资助的慈善组织,现有资料并未表明政府影响力有所减弱或是较不得力。在许多由地方官鼓励建立但资源主要来自地方的慈善组织中,地方官吏要么亲自进行管理,要么任命绅士和耆民进行管理,即使有些管理人员是公选的,也大多得到官员的承认,其管理活动也往往受到政府的监督[15]。
参考文献:
[1]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夫马进.中国善堂善会史研究[M].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46.
[3]李芳.清朝善会善堂自治制度探悉[J].河北法学,2008(6).
[4]刘铮云.义庄与城镇——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7,58(3).
[5]王卫平.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J].中国史研究,1997(3).
[6]苏简亚.苏州文化概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7]元氏县志——艺文志[M]//中国地方志丛书.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
[8]苏州历史博物馆,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9]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262.
[10]王卫平.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J].社会学研究,2007(4).
[11]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06-107.
[12]梁其姿.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J].食货月刊,1986(7-8).
[13]王国轩.吕坤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4]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15]颜晓红.清代浙江地区城镇发展与慈善组织[J].江汉论坛,2007(11).
责任编辑:仇海燕
作者简介:赵海林(1971-),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慈善组织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3-0356-06
收稿日期:2016-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