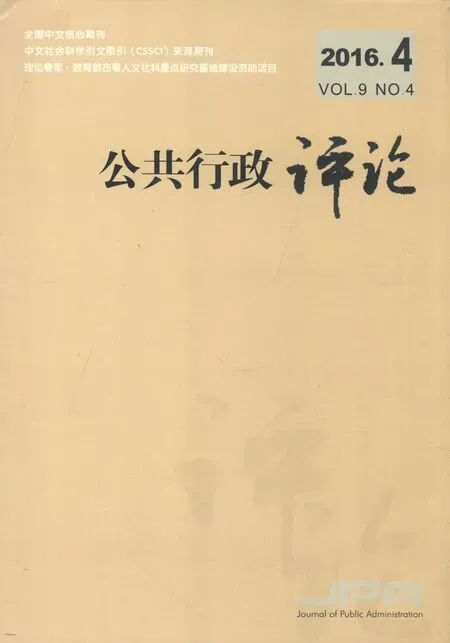政府购买服务的美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基于对一个公共服务个案的观察
吴 帆 周镇忠 刘 叶
政府购买服务的美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基于对一个公共服务个案的观察
吴帆周镇忠刘叶*
目前中国正在快速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与实践。服务提供模式的转变绝非简单地将公共服务移交专业的社会组织,而是要在能力建设、政府角色转换、潜在风险防范、服务传输质量保障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构建等方面,做出系统性的制度安排。美国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通过政府购买方式拓展公共服务的供给渠道,现已发展为公共服务提供的主导模式。论文根据对中国一项政府购买服务个案运行全过程的观察,以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和实践作为参照,对中国政府购买服务亟需解决的问题、理念构建和制度安排进行了深入探讨。
政府购买服务公共服务合作理论评估
一、引言
政府购买服务即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Purchase of Service Contracting,POSC),是指政府将原来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拨款和公开招标的方式,交由具有资质的企业或服务机构来完成,最后根据择定者或中标者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来支付服务费用(王浦劬、萨拉蒙,2010)。从运作方式上看,政府购买服务是社会福利供给民营化(Privatization)和市场化的主要方式,即通过民营化吸引社会资源进入公共服务领域,通过市场化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传输过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构建了一个包括服务卖方(政府)、买方(社会组织)和接受服务者(服务对象)的三方市场,也重新定义了这三方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角色和功能。这种准市场(Quasi-market)的运行模式几乎彻底改变了公共服务传统的传输方式和途径,重新形塑了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角色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同时避免“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取向基本达成一致:既能降低服务成本和行政成本,又能提升服务的传输质量与效率(罗观翠、王军芳,2008;苏明等,2010;关信平,2013)。但需进一步思考的是,购买服务过程本身并不会自动生成一个有效的运行机制来实现上述功能。服务效果的好坏取决于一系列要素的综合效应,包括制度设计、社会组织发展状况、政府角色转换及其实现程度、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化关系,等等。随着中国政府购买服务在政策和实践层面的推进,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入(韩俊魁,2009;许芸,2009;冯俏彬、郭佩霞,2010)。一是针对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理论探讨,如将现行模式归纳为社会组织发展说、行政职能委托说和传统采购延伸说(马俊达、冯君懿,2011);二是针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模式多元化的研究,将两者关系概括为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模式、独立关系非竞争性模式、依赖关系非竞争性模式(王名、乐园,2008),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既可能发展出市场交易关系,也可能存在依附关系和伙伴关系(郭小聪、聂勇浩,2013),并有学者在国家法团主义理论的框架下将双方关系归纳为强控性、依附性、梯次性和策略性四种类型(范明林,2010)。
另一方面,公共服务涉及的领域广泛,既包括硬件设备购买、公共交通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与提供等较易通过市场操作的服务,也涉及儿童福利、老年人照顾、职业培训等社会服务领域,而不同领域公共服务购买的运作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所探讨的公共服务聚焦于专业化的社会服务领域,即由政府或社会组织向家庭或个人,尤其是向弱势群体提供旨在改善社会福利水平的专业化服务。这类公共服务的主要特点是难以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成本核算难、专业化能力要求高、监管成本较高,因此容易出现监管制度不健全、评价监管体系缺失、政府的缺位或越位导致监管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邰鹏峰,2013)。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从制度建设、监管、加强沟通及评估等方面在理论层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探索,如构建购买者、承接者、使用者、评估者四元一体的政府购买操作框架(徐家良、赵挺,2013),通过提升行政环境(完善政策、法律、提升经济的开放程度等)、加强政府管理(建立合同管理、问责机制及购买方式与程序等),进而提升购买服务的最终绩效(王春婷,2015),以及采用项目化的过程管理模式来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即通过项目招标、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等形式,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由于这些探讨整体上缺乏实证资料支持,导致直接借鉴和参考的意义不大。另一方面,一些基于个案探讨政府购买运作模式的研究更多关注具体服务内容的确定和服务传输本身(李凤琴、陈泉辛,2012;胡科、虞重干,2012),缺乏对服务运行过程、政府功能定位转换、双方合作制度设计等内容的深入探讨,因此对策建议的可推广性也略有欠缺。诸如在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过程中,如何建立信息平台?在服务传输过程中,如何建立和维持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合作关系?如何加强政府在社会服务领域的专业化角色?等等这些议题,都需要研究者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总之,政府购买服务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发展模式,也未能确定一致的发展路径。与此同时,制度环境不完善、社会组织发展程度低、服务主体的技能缺乏等问题也比较突出。因此,其他国家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和经验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国家之一,社会组织(主要是非营利组织)发展比较成熟,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形成了一些重要理论,值得参考和借鉴。基于此,研究通过对中国的一项政府购买服务个案的观察,并以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和实践作为借鉴,对中国政府购买服务亟需解决的问题、理念构建和制度安排进行探讨。
二、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历程与理论基础
政府购买服务是目前美国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主导方式。在早期阶段,虽然政府直接输送服务被认为可以确保服务的持续性和公共责任的实现,但因财政投入限制和竞争机制缺乏等制约因素,导致服务效率低下,且相对于其他类型服务的成本投入也更高(Niskanen,1971;Savas,2000)。美国政治长期存在着一个悖论:政府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是众所期待,但同时,民众对政府提供的服务普遍缺乏信任。由于美国慈善领域长期积淀的民间自觉行动,志愿主义的发展、政治多元化,以及民众对政府的矛盾心理,促使美国政府逐渐从直接服务提供者中脱离出来,一个建立在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被称为“第三方治理”(Third-party Government)的合作体系应运而生。“第三方治理”成为调和这一政治悖论的有效方式:在增强政府承担社会福利角色的同时,又不至于过度扩大政府的行政机构规模,还能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Salamon,1981)。因此,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阵营达成共识,都倾向于通过民营化,即主要运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实现公共服务的高效传输。
在政治领域变革的推动下,美国的政府购买服务兴起于1960年代,是发达国家中率先在公共服务领域开展这一改革的国家。1962年,《社会安全法案》(SocialSecurityAct)一系列修正案允许州政府的福利部门从具有一定资质的公共机构购买特定的社会服务(Willis,1984),开启了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时代。1964年,《经济机会法案》(EconomicsOpportunityAct)的实施,促使政府购买服务普遍推广(Wedel,1976)。1967年,《社会安全法案》修正案允许州及地方的政府福利部门从非营利组织或私营机构购买服务,并享有联邦政府的配套资金(Gilbert,1977)。1972年,联邦政府向公共服务提供的预算上限达到了25亿美元(Willis,1984),随后又数次提高对社会服务的财政投入,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了充分的资金保障。这些改革措施的核心是通过签订合同将公共服务项目的一部分或全部,委托给政府部门之外的非营利组织来实施,并从开始的少数领域逐渐扩展到健康、贫困、儿童福利、家庭支持、老年人福利、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服务等诸多领域。1971年至1978年,美国《社会安全法》中涉及社会服务购买资助的比例由25%上升到54%(Mueller,1979),增加了一倍多。1990年代,政府购买服务已成为美国公共服务供给的首要方式。1977年至1997年,美国政府向非营利组织提供的资金支持增加了195%(Salamon,2002),20世纪末政府财政投入达到2 078亿美元(Independent Sector,2002),大约占社会服务部门资金来源的52%(Salamon,2002)。以旧金山市为例,2013年有160个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签订了460个服务合同,平均每个组织购买政府的项目达到了2.9个*数据来源于美国加州旧金山公共服务部的内部资料。。这种非营利部门与政府间的合作关系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合约政府”或“非营利的联邦制”(Smith,1975)。在这一合作体系中,政府决定公共资金的投入方向,并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共同践行公共权力以达成公共目标。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购买服务展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服务购买依然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途径。根据美国国际市/郡管理协会(International City Coun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ICMA)的调查*美国从1982年开始,每隔5年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展开调查,其调查对象涵盖了人口为25 000以上所有的郡和人口超过10 000的所有城市,主要调查内容为公共工程、公共安全、公共事业、健康与人类服务、公园和娱乐、文化艺术和支持功能等67项服务。,美国地方政府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以及与非营利组织签订服务合同的比例为69%,接近7成(Hefetz et al.,2012)。另一方面,调查还显示,美国公共服务的民营化趋势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变,即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的完整合同(Complete Contract)开始减少,地方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共同提供服务的混合模式出现了急剧的增长。这表明美国的公共服务已经超越了单纯由公共部门或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二分法,而是在市场、效率、服务质量和民众呼声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Warner & Hefetz, 2004),即服务提供的公私混合模式(Mixed Public/Private Contracting)。这种方式既向非营利组织直接购买服务,又在辖区范围内结合公共和私营部门,实施公私服务混合模式为本地的公共服务创建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市场(Warner & Hefetz,2008)。这种变化不仅旨在保持公共服务市场领域的竞争性,同时还力图保持当地政府对服务传输的掌握和公共责任的实现。
然而,在美国政府购买服务发展过程中,支持者和批评者之间的争执从未平息。支持者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购买服务能够提升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扩大服务对象范围、节省政府成本、增强服务传输的灵活性,且公共责任也更为透明,可以避免“政府失灵”(Bennett & Johnson,1980;Stein,1990;Milward & Provan,2000;Campbell & McCarthy,2000;Bowie,2004)。批评者基于一些案例分析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由非营利组织承担公共服务是一个误导,不仅缩小了政府规模,降低了政府能力,也损害了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尤其是增加了寻租腐败和裙带关系的风险,导致公共责任的断裂,也可能降低公共服务的质量(Manser,1974;Milward,1996;Boyne,1998;DeLeon & Denhardt,2000;Sclar,2000)。虽然存在各种争议,美国在公共服务实践中不断地通过制度建设和改革来降低和规避负面影响与风险,政府购买服务最终发展成为美国公共服务供给的主导模式。
美国政府购买服务源于政治领域的改革,有三个理论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一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竞争和效率的重要性,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领域中,是美国政府购买服务开始推行的核心理论基础;二是交易成本理论,强调购买服务后对政府在合同管理、成本增加方面的挑战,关注服务购买后成本控制的过程与效果;三是新公共服务理论,关注公民对整个公共服务的参与,主张政府应该通过服务购买,推进非营利组织为公民参与服务提供畅通的渠道。这些理论对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都起到了引导作用。在本研究的语境下,我们更为关注美国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间关系界定的理论框架。在中国,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往往是一种主导—依附的关系,尤其是在非营利组织获取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对政府的依赖性会进一步加剧。即使在美国,也有研究证明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与政府资金来源占比呈反比关系,即获取政府资金越多,其独立性越差(Manser,1974)。但是,这种关系定位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利于服务质量的保障和专业化程度。因此,美国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过程中,合作治理成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关系的主要理论视角,强调政府应以一种更为平等的地位去管理自身、以及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重视双方的资源依赖、互动和协商过程。在合作治理的视角下,发展出了两个主要理论:“伙伴理论”(Partnership Theory)与“合作理论”(Collaboration Theory),它们为美国政府购买服务实践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认识框架和价值取向(Salamon,1987;Wood & Gray,1991;Alexander & Nank,2009)。所谓“伙伴”(Partnership)是指基于法律或协议进行合作的正式工作关系,双方在一定的制度规范里实施互惠的计划。这种伙伴关系不仅意指对政策、项目和目标的认识达成一致,也包括在特定的时间内共享责任、资源、风险和收益。所谓“合作”(Collaboration)是一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和行动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通过共同的规范、规则和结构来采取行动,共同决定相关事宜。伙伴理论与合作理论所关注的议题有所不同,前者更加强调所涉及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建构,后者重在阐释利益主体如何合作的过程,以及不同参与者的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平衡(Wood & Gray,1991)。但二者都强调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参与的各利益主体是一种共生关系,对目标达成负有共同的责任。基于这两个理论,美国政府确立了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基本关系架构,即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相协作,对公共责任负有共同承诺,但承担着不同角色。其中,政府部门对社会公众负责,确定公共资金使用的优先顺序,对服务质量的保障负主要责任;而非营利组织确认社区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优先顺序,负责发展专业服务能力,并及时回应服务需求及其变化。协作关系建立的前提是双方对社会需求有正确认识并能够达成共同理解。因此,在美国,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被政府用以执行公共政策,传统社会福利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区别开始变得模糊(Kramer & Grossman,1987),更多的社会组织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意味着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对服务内容和运行的规划都缺乏完备性,一纸合约无法规定非营利组织在合同期内所要做的一切事情,也无法充分预期由环境变化所引发的问题和困难。如果服务合同运行失效,预期的双赢结果会最终演化为一方或双方的损失(Brown et al.,2007)。此外,合同管理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往往加剧了双方在谈判、执行和监管合同关系的交易成本(Gazley,2008)。因此,政府也必须加强各种监管技术,提升监管能力,及时矫正非营利组织的不良绩效(Brown & Potoski,2003)。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理论界开始强调综融合作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试图在服务传输过程中将竞争、合作、成本监管以及公民参与有机结合起来(Warner & Hefetz,2008)。
三、可资的借鉴: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经验
虽然中美两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政策价值导向有别,社会福利的主要承担者及其关系的历史积淀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但政府购买服务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公共服务的主要领域和基本性质也大致相同。因此,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式与工具,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程序、制度设计等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教训都值得借鉴。本节通过对美国加州政府购买服务相关政策的分析*美国州一级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政策在联邦政策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细化,虽各州在某些环节操作上有差异,但各州具有较强的共性。,并结合对美国政府官员的个案深度访谈*研究运用半结构化方式对美国加州某市公共服务部信息综合处(Information Integration Division, Human Services Department)的主管进行了个案深度访谈。公共服务部负责该市大部分的政府购买合同项目,该主管自2007年开始在这一部门任职,主要负责服务项目的设计、监管和评估。访谈内容主要覆盖政府购买服务的一般流程、现有的制度规范、具体操作环节和目前面临的困境等方面。,梳理和讨论美国政府购买服务运行过程中一般性的制度安排、程序和管理机制。这些政策文本具体包括服务计划书要求(Requests for Service Proposal)、服务需求调查要求(Requests for Needs Assesment)、服务合同标准(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双方的权、责、利)(Standard Aggreement for Contract)、服务预算格式(Budget Forms)、资金分配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of Funding Allocation)、评估标准细则(Standard for Evaluation),以及投标过程中所涉及评估专家的利益相关性声明的规定(Impartiality/Disclosure/Conflict of Interest Statement)。通过对政策文本和个案访谈资料的内容分析,我们得到了美国总体上在专业化社会服务购买领域的一些主要做法和基本特征。
(一)程序规范
程序规范是一种制度性保证,虽不一定必然带来高效和高质量的服务,但规范的程序是防范与规避风险的有效方式。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的程序从明确社会服务需求开始,到最终评估服务效果的全过程,每个环节都辅以严格的制度规范,具体如下:
1.需求评估。规定以政府为主导进行需求评估,既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直接实施,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实施第三方需求评估。在这一过程中,由政府部门负责召开需求分析会,并邀请相关的非营利组织参加。
2.信息发布。根据需求评估结果,向所有非营利组织发布政府决定购买服务的信息和参与流程,明确招标信息和相关要求,并确保信息通畅。
3.资质审查与竞标。政府审查非营利组织提交的服务计划,一般包括两个步骤:一是由政府进行基本资质的审核(Minimum Qualification);二是外聘专家成立评审小组(Review Panel),依据一定的评估标准审核服务计划。
4.签约前的协商(Negotiation Process)。根据评审结果选定非营利组织后,双方将围绕着两个议题进行讨论,一是政府应提供多少资金以及如何使用;二是非营利组织应该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内容。
5.签订合作协议。充分沟通达成一致后,在明确服务目标和服务内容的基础上,双方签订协议,建立合作关系。
6.服务评估。服务过程中,政府运用第三方评估进行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掌握有关服务传输过程、效果和质量方面的信息,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终结或继续服务合同。
政府在购买服务的每一个环节,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来规范具体的操作过程。尤其值得借鉴的是,协议签订之前有一个充分的协商和谈判阶段,这不仅有助于双方的信息交流和意见交换、加强理解,也为后期的服务开展建立了稳固的基础。
(二)合作关系的制度建设
基于合作理论与伙伴理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不仅是资金支持者和被支持者的关系,更是合作者的关系,双方的利益统合于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利益的满足。换言之,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导向,双方协作共同实现社会福利领域的公共责任。通过对个案访谈和政策文本分析,我们发现在购买服务的初始阶段,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就会建立一个“联合体系”(Aassociate System),通过制度安排和岗位设置来保障双方的持续沟通、平等对话与协商关系。这一“联合体系”的制度规定双方必须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定期的交流与沟通,分享服务传输中的信息与问题,共同应对变化,并在特定的情况下共同协商调整服务计划。这一合作体系为服务的顺利传输,应对可能出现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等提供了制度支持,并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双方共同参与服务传输的决策过程。
(三)政府角色加强
购买服务使政府参与服务过程的责任和角色发生了变化,不再提供直接的服务,但这并不意味政府脱离服务传输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政府的专业化角色得以加强,需要具备谈判、协商、监督、信息沟通、管理服务计划多方面的能力。在合同签订之前,明确服务需求并主导服务需求的认定;在服务传输阶段,设立专门的工作人员,保持与非营利组织的持续沟通。换言之,政府并非将服务完全交由非营利组织,而是以管理者、支持者和监管者的角色参与服务提供的全过程。一般在美国地方政府部门中涉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运作的有两类工作人员:一类是项目人员(Program Staff),负责服务监管和支持,确认服务内容和范畴等与服务相关的事宜;另一类是行政人员(Administrative Staff),负责确保非营利组织是否遵循法律,是否为员工提供保险,人力资源体系是否合理等与组织运行相关的事宜。前者是专业人才,一般由具有社会工作教育背景与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构成;后者是专事管理人才,往往由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专业人员来承担。而目前美国由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通力合作开展公私混合服务提供模式的盛行,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府部门专业化角色的要求。
(四)弹性管理模式
弹性管理模式是美国政府购买服务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虽然服务周期也会视具体的情况而有所不同,但出于对非营利组织持续且稳定开展服务的考虑,地方政府购买专业化社会服务的合同期限多为3年。当服务项目开展一段时间后,服务对象的构成和需求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服务效果和效率也会初步显现。因此,基于上述变化和服务结果重新厘清新的服务对象、调整资金投入、制定新的服务计划等,都可能导致服务项目开展后的具体内容与签订合同时有较大的差异。因此,美国政府采取了“以证据为本”的管理模式(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del),双方在充分沟通信息的前提下,共同商议和决策,并可依照相关规定基于变化调整合同里的服务内容。这种弹性的管理模式,不仅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也促进服务传输过程能够更为高效地回应社会需求的变化,更好地实现公共责任。
(五)科学评估
在美国,无论是明确需求、评审非营利组织,还是判断服务效果,政府通常都采用第三方评估模式。尤其是在服务效果评估环节,美国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人们一般认为,第三方评估应该将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承担服务的社会组织)排除在外,但在美国则不然。一方面,评估专家非直接服务者,难以深入了解服务的全过程,因此在确定评估指标和制定计划时,需要从服务传输者和管理者处获取信息来确保评估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另一方面,在评估开展的过程中,信息和数据采集任务往往依托非营利组织内部提供服务的一线工作者来完成。因此,美国政府要求第三方评估要充分纳入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评估专家应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一线服务提供者一起讨论,共同商议确定可测量的评估指标并制定评估计划。这种方式可以使第三方评估更加客观,也更为合理。
美国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沟通障碍。尽管在政府部门建立了专门岗位来负责监管和支持,并保持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沟通。但是,双方的顺畅沟通仍面临着巨大挑战。政府人员非直接的服务提供者,双方对问题的理解差异造成沟通不畅时有发生;第二,寻租行为。在政府部门和特定的非营利组织之间往往建立了稳定而持续的合作关系,虽然保障了服务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且有利于双方的有效沟通,但寻租行为也时有发生;第三,评估信息共享不足。由于许多非营利组织都与政府有服务合约,所以同一个服务对象可能同时接受来自不同组织的服务,但由于服务对象的信息与数据在非营利组织之间没有实现共享,因此给对某一特定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效果做出准确评估带来困难。
四、中国政府购买服务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基于一项服务购买的个案分析
与美国的情况不同,政府购买服务在中国尚处于发展初期,但已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需引起警惕。需要做出说明的是,中国的政府购买服务尽管在形式上采取了竞争性投标,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依靠直接指定而非通过招标确定服务购买合同的案例比比皆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内部化”和形式性特点明显,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许小玲,2012),即使如南京市鼓楼区这样在政府购买服务中经常被提及的优秀案例也属于这种情况(白友涛、葛俊,2011)。这种现象与我国政府购买服务所处的发展阶段、社会组织发展情况等都密切相关。而学界对于这种“非竞争性”直接委托现象的理解也存在着争议,有学者支持竞争机制在效率和机会公平方面的价值,认为须通过竞争性招标才能实现服务购买的意义与效果;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竞争未必能够带来社会服务的效率,应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的特点以及现实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基于信任的合作对象选择同样有其合理性(郭小聪、聂勇浩,2013)。所以,在政府购买服务发展初期,选择具有较好信誉和服务能力的社会组织进行服务委托有其合理之处。此外,直接委托模式目前在美国政府购买服务领域中也比较常见,尤其是在双方已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非营利组织具有良好的信誉、资质和能力情况下往往会采用这一方式。总之,无论何种认知导向,非竞争性的直接委托成为目前我国政府购买专业化社会服务领域中的一个常态,因此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此,我们选择了一个跟踪观察一年的个案,作为政府购买专业化社会服务的缩影,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政府购买服务的现状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该个案是政府委托某一社会组织W机构开展的服务项目,始于2012年10月,持续了一年。我们通过个案深度访谈、机构调查和资料文本分析等方法,长期观察并深入掌握了这项政府购买服务运行的全过程。我们将从合同签订、服务需求厘定、服务开展、政府监管、结果评估与服务终结的全过程,深入探讨所表征的主要问题、可能的风险以及制度化建设的任务。
(一)项目背景与合同签订
该项目的服务对象是某经济开发区集中居住于某公寓的外来务工人员*这类公寓是以当地政府为主导为来此经济开发区企业务工的流动人口专门建造的集中居住区域,一般是4人或6人共享一个房间。,共1.3万人,大多为19~25岁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本地户籍,工作忙碌,互动空间和工作之外的娱乐活动非常缺乏,社区归属感和城市生活融入程度都比较低,因而对城市适应、人际交往、职业发展和情感关系等方面都有诸多需求。该社区虽有建筑面积4 224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包括食堂、图书阅览室、培训室、放映室、舞蹈教室、乒乓球室和心理咨询室等服务设施,并由政府工会派出人员进行管理,但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经常加班,对服务中心设施的使用率并不高。此外,由于服务中心缺少专业人员,诸如心理咨询、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服务始终未能开展。出于上述原因,当地政府决定通过购买服务直接委托W机构来提供相应的服务。
W机构成立于2006年,主要从事社会服务提供和公益组织孵化培育,是一个在业内资质和口碑都很好的机构。政府与之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服务合同,由W机构承接社区服务中心,将之发展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平台,政府负责提供基础场地和资金支持。政府要求机构在服务项目开展之前明确角色定位、策划整体项目实施方案和组建专业人员团队,并强调机构要采取与政府协商式的服务推进方式。在一年合同期结束后,政府对W机构进行评估,并据此决定是否续约。
(二)服务需求厘定
服务开展前期,W机构通过问卷进行了需求调查,初步确定了公寓居民排在前四位的需求,分别为心理咨询、文化娱乐活动、职业规划和就业维权。调查结束后,W机构召开了需求调研报告发布会,邀请相关政府部门、用工企业参加,探讨下一步服务开展的具体内容。虽然W机构在需求预估阶段的操作过程科学且规范,但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需求评估是在服务合同签订以后进行的。换言之,在尚未认定服务需求以前,双方根据主观经验已经确认了资金的具体使用去向;二是需求确定的整个过程中,政府部门的参与度不高,仅要求W机构开展系统的需求评估,并在需求明确后才有一定的沟通。
(三)服务开展
在项目执行阶段,W机构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服务,主要包括大型活动、工作坊和常规活动。其中,大型活动是年度或季度的大型体育活动,具体包括不同的球类比赛和趣味运动会;工作坊提供心理支持和交流平台,具体包括心理减压工作坊、女性工作坊、即兴话剧活动、梦想分享会、企业见面会等;常规活动是每周定期举行的日常活动,以兴趣小组的形式展开,具体包括电影小组、舞蹈小组、英语小组、电脑小组、书法班、摄影大讲堂等。根据需求评估结果,我们发现机构开展的服务主要集中于文化娱乐活动和心理咨询两个方面。在为期一年的服务周期中,该机构为公寓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428次服务活动,参与人数达到了11 250人,占服务对象总数的86.54%,总体受益人次达 40 600 人次,平均每人3次。
这项服务受当地政府和W机构总部的共同监督,涵盖两个沟通层次:一是在机构内部,服务人员与机构总负责人之间的沟通,主要涉及调整服务设计和开展方式等内容;二是在W机构与政府之间,工作人员向政府的项目负责人员及时反馈服务开展的各种信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与机构之间仅在初期的需求调查和后期服务效果认定上有一定的沟通,服务过程中的交流十分有限。双方虽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缺乏对合作的制度性保证和专业支持,具体体现为:一是,政府并未设立专门的岗位,由具有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来承担服务项目的监管;二是,双方合作缺乏制度化保障,沟通往往随意发生,无法确保信息交流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四)结果评估与合同终结
在项目结束前,为了解服务效果,W机构首先展开了内部评估,以“滚雪球”式的抽样方法对1 000名服务对象进行了满意度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了解机构开展活动的比例为85.24%,选择“经常参加”和“偶尔参加”的人数分别为30.59%和46.58%,其中五成多(54.95%)的受访者平均每月参与各种活动与服务的次数在1~5次之间,对服务的满意比例达到了八成以上。但是,仍有16.67%被调查者不了解机构开展的各项活动,15.98%的服务对象表示对活动并不满意。
在服务结束后,政府部门没有运用评估来判断服务效果,仅通过主观判断做出了终止服务的决定。W机构工作人员在与政府部门沟通时,得到了如下回应*我们对W机构负责此项目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个案深度访谈。:一是W机构的团队建设和管理不到位;二是W机构缺乏工作人员,活动开展不到位。但当工作人员尝试进一步了解具体细节时,但却沟通无果。总之,缺乏评估环节,难以对服务效果与质量做出科学的评价,政府作为监管者和支持者的角色也难以实现。
如前所述,尽管这一个案属于委托性质的服务购买,不涉及政府发布信息、评审服务计划书等部分流程。但是,这一个案对我国目前政府购买服务状况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反映在程序和制度构建方面的问题仍具较强的启示意义:一是政府没有开展科学的需求评估,而是在签订合同以后,由社会组织自行组织调查,政府只被告知了需求调查结果,这可能会导致服务并未针对服务对象的真正需求,而只是社会组织擅长的服务领域。二是在签订合同之前,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缺乏沟通与协商,对资金使用和服务内容的提供都没有深入的探讨。如果双方对服务需求的认识缺乏一致性,不仅会导致服务传输与服务对象的需求之间有较大偏差,也会影响最终的服务效果;此外,政府缺乏对资金使用的规范性说明和过程监管,不仅无法通过购买服务来节约成本,可能还会造成资金浪费。三是没有建立规范的合作流程和监管制度,致使政府角色相对缺位。一方面,政府部门缺乏相关的专业人员很好地监管服务,并对服务进行有效引导;另一方面,没有对合作关系和流程的制度规定,导致双方的沟通随意性比较强,缺乏针对性,影响服务成效。四是政府部门没有对服务效果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只根据主观判断就终结了服务合同。虽然目前中国相关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对服务效果进行评估认定,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在评估理念、方法和工具运用等方面都相对滞后,形式大于内容的情况比比皆是。
五、中国政府购买服务的认知与制度建构
对上述个案的分析表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尤其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建设和公共服务市场的建构。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状况,并借鉴美国的经验,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在政府购买专业化社会服务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府购买服务是工具而非目的。政府购买服务是提高公共服务传输效率与质量的工具,是政府对公共服务进行委托的过程,包含一定程度上的权力下放。换言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一种工具性的私有化,但绝非是社会福利的私有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为了更好实现政府对公共责任的承担,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激励社会组织发挥传输公共服务的效率、创新和专业能力。因此,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发展过程中,要注意防止把工具异化为目的,把手段异化为目标。
第二,明确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从市场角度看,政府和社会组织是专业化社会服务市场的两个主体,二者之间是服务购买者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因此,受市场机制的调节。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中的关系远不止于此,甚至可说二者关系的本质并不在于此,因为公共服务的性质和目的都要求政府作为监管者、协调者参与服务的全过程,因此还需要制度规范与合作机制。前文提到的美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合作关系值得借鉴。对于中国而言,亟需立法对政府购买服务各个参与方的角色、责任、权利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做出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
第三,政府的专业能力是强化而非弱化。政府购买服务是将政府从直接提供服务主体中移除,但绝非是从公共服务中移除。这一转变并不意味政府摆脱公共服务的责任,而是对进一步优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政府对公共服务责任的承担能力不仅不会弱化,而会得到进一步加强。有研究表明,保证政府购买服务执行效率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政府部门的管理人员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包括谈判、协商、监管、沟通期望和技术信息等方面的能力支持(Kettl,1993),非营利组织传输公共服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管理服务合同的质量(van Slyke,2007)。
第四,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市场。在中国,政府通过市场机制传输公共服务的重要前提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公共服务市场。这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明确服务购买者(政府)、服务提供者(社会组织)、服务接受者(个人或家庭)三方的权利和责任,建立合理、有序、高效的三方市场关系架构;二是积极培育具有资质的社会服务组织,提高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实现公共服务市场的供求均衡;三是建立畅通的三方沟通渠道和公共服务市场信息系统,及时回应公共服务需求,提高公共服务市场效率。
第五,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政府购买服务是福利提供方式的民营化和市场化。因此,在公共服务运行过程中,既有市场力量的驱动,也有行政力量的驱动,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机会主义,寻租行为和裙带关系等风险也会出现。由于购买方并非服务接受者,而服务对象又不支付费用,因此,在政府、服务对象和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会导致“合约失灵”(Contract Failure)。美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审计总署(General Government Accounting Office)曾多次颁布加强监管购买服务的管理条例(GAO,2002)。实际上,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滋生的腐败和职权滥用问题在中国也有发生。因此,中国目前亟需建立一个覆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整个过程的监管制度。
第六,运作流程与模式应兼顾规范与灵活性。购买服务需要规范且科学的操作程序,并在每个阶段辅以相应的制度保障。但是,公共服务本身是一种复杂的行为,涉及不同领域、不同群体。而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也有很大差异,尤其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程度普遍不高的中国而言,目前还难以采取完全统一的模式。即使在政府购买服务高度发展的美国,虽然竞标(Competitive Bidding)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购买服务形式,但协商模式(Negotiation)与合作模式(Cooperation)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可能更为适用(Dehoog,1990)。而且,如果政府过于强调成本控制,并以此作为考量社会组织服务计划的主要标准,也会造成缺乏对其他价值,尤其是公共责任实现的充分考虑,最终导致对人类基本需求的忽略(Aman,2007),这也就违背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准则。因此,在规范政府购买服务操作流程的同时,也需要有合理的灵活性。
第七,对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角色的塑造。美国的经验证明,政府资金对于提升非营利机构的能力起到了系统性的角色,政府购买服务也塑造了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方式(LeRoux,2009)。美国非营利组织对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称之为公民社会。但是在政府购买服务发展过程中,美国依然面临着来自社会组织发展困境方面的挑战,因此在培育社会组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协助同质性较强但规模不大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合并与优化功能等。在中国,目前社会组织发展普遍不够成熟,亟需在建立合作关系之后,政府在其能力建设、技术发展和在公共责任实现等方面给予支持与引导。从这个意义上讲,培育和发展具有良好资质的社会组织和专业人员是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发展的当务之急。
白友涛、葛俊(2011).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实践与思考——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理论与现代化,2: 73-78.
范明林(2010).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基于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视角的比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3: 159-176.
冯俏彬、郭佩霞(2010).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基础与操作要领初探.中国政府采购,7: 70-73.
关信平(2013).政府购买服务:我国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新起点.中国社会报,8月16日.
郭小聪、聂勇浩(2013).服务购买中的政府一非营利组织关系:分析视角及研究方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155-162.
韩俊魁(2009).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6: 128-134.
胡科、虞重干(2012).政府购买体育服务的个案考察与思考——以长沙市政府购买游泳服务为个案.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 43-51.
李凤琴、陈泉辛(2012).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探索——以南京市鼓楼区政府向“心贴心老年服务中心”购买服务为例.西北人口,1: 46-50.
罗观翠、王军芳(2008).政府购买服务的香港经验和内地发展探讨.学习与实践,9: 125-130.
马俊达、冯君懿(2011).政府购买服务问题研究.中国政府采购,6: 64-66.
苏明、贾西津、孙洁、韩俊魁(2010).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财政研究,1: 9-17.
邰鹏峰(2013).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管成效、困境与反思——基于内地公共服务现状的实证研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95-99.
王春婷(2015).政府购买服务绩效的影响因素与传导路径分析——以深圳、南京为例.软科学,2: 1-5.
王名、乐园(2008).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购买的模式分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4: 5-13.
王浦劬、莱斯特·M.萨拉蒙等(2010).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徐家良、赵挺(2013).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与路径创新:上海的实践.中国行政管理,8: 26-30,98.
许芸(2009).从政府包办到政府购买——中国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的新路径.南京社会科学,7: 101-105.
许小玲(2012).政府购买服务:现状、问题与前景——基于内地社会组织的实证研究.思想战线,2: 75-78.
Alexander,J. & Nank,R.(2009).Public-Nonprofit Partnership Realizing the New Public Service.Administration&Society, 41(3): 364-386.
Aman, A. C.(2007). An Administrative Law Perspective on Government Social Service Contracts: Outsourcing Prison Health Care in New York City.IndianaJournalofGlobalLegalStudies, 14(2): 301-328.
Bennett,J. & Johnson,M.(1980). Tax Reduction without Sacrifice: Private-SectorProduction of PublicServices.PublicFinanceQuarterly, 8: 363-96.
Bowie, S. L.(2004). Privatized Management in Urban Public Hous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Service Availability, Utilization, and Satisfaction.SocialWork,49(4): 562-571.
Boyne, G.A.(1998). Bureaucratic Theory Meets Reality: Public Choice and Service Contracting inU.S. Local Government.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58(6): 474-484.
Brown, T. L., Potoski, M. & Van Slyke, D. M.(2007).Trust and Contract Completeness in the Public Sector.LocalGovernmentStudies, 33(4): 607-623.
Brown,T. L. & Potoski, M.(2003).Contract-Management Capacity in Municipal and County Governments.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63(2): 153-164.
Campbell, G. J. & McCarthy, E.(2000). Conveying Mission through Outcome Measurement: Services to the Homeless in New York City.PolicyStudiesJournal, 28: 338-352.
DeLeon, L. & Denhardt, R.(2000).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Reinven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60(2): 89-97.
Dehoog,R. H.(1990).Competition, Negotiation, or Cooperation: Three Models for Service Contracting.Administration&Society, 22: 317-340.
Gazley, B.(2008). Beyond the Contract: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Informal Government—Nonprofit Partnerships.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68(1): 141-154.
Gilbert, N.(1977).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ervices.SocialServiceReview,51(4): 624-641.
Hefetz, A., Warner, M. & Vigoda-Gadot, E.(2012).NeitherPublicnorPrivate:MixedFormsofServiceDeliveryaroundtheGlobeBarcelona. Available at(July 29, 2016): http://www.ub.edu/graap/Final%20Papers%20PDF/Warner%20Hefetz.pdf.
Independent Sector.(2002).TheNewNonprofitAlmanacandDeskReference:TheEssentialFactsandFiguresforManagers,Researchers,andVolunteers. New York: Wiley.
Kramer, R. M. & Grossman,B.(1987).Contracting for Social Services: Process Management and Resource Dependencies Source.SocialServiceReview,61(1): 32-55.
Kettl, D. F.(1993).SharingPower:PublicGovernanceandPrivateMarket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LeRoux, K.(2009). Paternalistic or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Examining Opportunities for Client Participation in Nonprofit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69(3): 504-517.
Manser,G.(1974).Further Thoughts on Purchase of Service. Social casework,55: 421-474.
Milward, H.B.(1996). Symposium on the Hollow State: Capacity, Control and Performance in Inter Organizational Settings.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andTheory, 6(2): 193-195.
Milward, B.H. & Provan, K.G.(2000). Governing the Hollow State.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andTheory, 10(2): 359-79.
Mueller, C. P.(1979). Purchase of Service Contracti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Provider. In Wedel, K. R., Katz, A. J. & Weick, A. Eds.SocialServicesbyGovernmentContract:APolicyAnalysi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Niskanen, W.(1971).BureaucracyandRepresentativeGovernment. Chicago: Aldine Atherton.
Savas, E.S.(2000).Privatizationand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 London: Chatham House.
Salamon, L. M.(1981).Rethinking Public Management: Third-Party Government and the Changing Forms of Government Action.PublicPolicy, 29 :255-275.
Salamon, L. M.(1987). Of Market Failure, Voluntary Failure, and Third-Party Government: Toward a Theory of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NonprofitandVoluntarySectorQuarterly, 16(1): 29-49.
Salamon, L. M. Ed.(2002).TheStateofNonprofit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Sclar, E.(2000).YouDon’tAlwaysGetWhatYouPayfor:TheEconomicsofPrivatiz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mith, B. L. R.(1975).TheNewPoliticalEconomy:ThePublicUseofthePrivateSecto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Stein,R.(1990). The Budgetary Effects of Municipal Service Contracting: A Principal-Agent Explanation.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 34: 471-502.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2002).Report to Congressional Requesters, WELFARE REFORM: Interim Report on Potential Ways to Strengthen Federal Oversight of State and Local Contracting. Available at(July 29, 2016): http://www.gao.gov/new.items/d02245.pdf.
van Slyke, D.(2007).Agents or Stewards: Using Theory to Understand the Government-Nonprofit Social Service Contracting Relationship.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andTheory,17(2): 157-187.
Warner, M.E. & Hefetz, A.(2004). Pragmatism over Politics: Alternative Service Delivery in Local Government, 1992—2002.InTheMunicipalYearbook2004.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City/Coun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Warner, M.E. & Hefetz, A.(2008).Managing Markets for Public Service: The Role of Mixed Public-Private Delivery of City Services.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68(1): 155-166.
Wedel, K. R.(1976). Government Contracting for Purchase of Service.SocialWork,21(2): 101-105.
Willis, D. C.(1984).PurchaseofSocialServices:AnotherLook.Social Work, 29(6): 516-520.
Wood, J. & Gray, B.(1991). Towards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Collaboration.JournalofAppliedBehavioralSciences, 27: 139-162.
D035
A
1674-2486(2016)04-0004-19
*吴帆,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院,访问学者;周镇忠(Julian Chun-chun Chow),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院,教授;刘叶,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和社会政策系,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