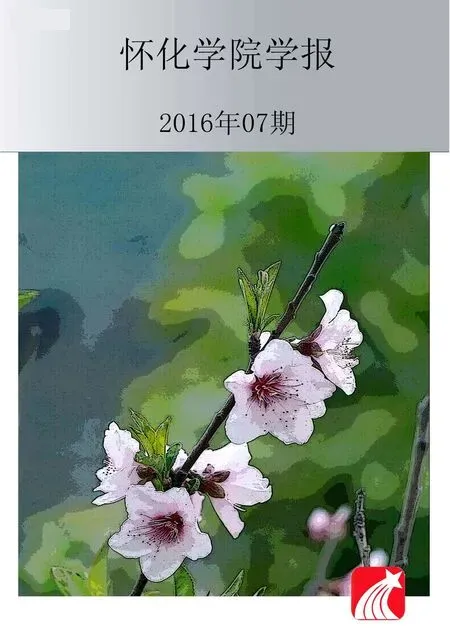哈代小说的生态宇宙意识探析
林晓青
(三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三明365004)
哈代小说的生态宇宙意识探析
林晓青
(三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三明365004)
为了更深层次地了解哈代所精心构筑的文学版图上不朽的威塞克斯王国,从人类与宇宙冲突对立所付出的代价、小说创作中运用星座距离来折射人心亲疏、人类和宇宙万物和谐相处之时的欢欣几个方面分析了属于哈代的生态宇宙意识,从而意识到人只是宇宙整体中渺小的存在,唯有秉持和谐共存的观念,以一种系统、整体论的眼光,承认并尊重宇宙当中各种生命以及非生命体所具有的内在均等价值,人与宇宙万物方能实现生生不息、相亲相携的最佳生存模式。
托马斯·哈代;生态宇宙意识;和谐共存
就英美文坛而言,作家的声誉在学术界和一般读者中往往难以取得一致,而能够同时被学术界和广大读者肯定的经典作家寥若晨星,而托马斯·哈代正是其中之一。哈代从多塞特乡下寂寂无名的建筑学徒成长为英国殿堂级的作家,其诗歌和小说的价值得到了文学界一致的好评,实属难得。哈代成长于家乡多塞特这个具有浓郁的牧歌情调和田园色彩、风景如画的村庄,目光所投之处均是醉人景色,在和自然长期的亲密相处中,他深刻体悟了自然的独特魅力,这成为其日后创建独属的“威塞克斯”王国的依托。在音乐般柔曼的风景之中哈代喷涌着生命的热情,深情地倾诉着自己的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与思考,并在对自然长期的观察与描摹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宇宙意识,而且贯穿着整个创作历程。从1866年的创作之初到1928年的创作终结,从诗歌到小说又回到诗歌,哈代取得累累硕果,在这些创作成果中反复出现“望星空”的意象,且天体现象高频率出现。哈代的小说不是以《远离尘嚣》开始的,但它却是威塞克斯系列小说的开端,在他的作品中占有独特的地位;《还乡》是哈代创作中期的转型之作,具有自属的风格和特色;《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最受欢迎且最具个人化的作品;《无名的裘德》是哈代构思了8年的作品,是其小说的封笔之作,代表着其小说创作艺术走向巅峰。因此,选取了这四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作为分析的依据,解读哈代独有的生态宇宙意识。
“所谓宇宙意识,是指一种宇宙化的生命意识,亦即人对宇宙和人在宇宙中之地位的认识。”[1]94哈代虽然未能身处生态文明的时代浪潮之中,却因对自然有着敏锐的感受力而具备超前的生态意识。哈代在青少年时期就搜罗了许多“自学类教育读物”,诸如卡塞尔的《大众教育家》、《男孩的科学读本》还有约翰·廷布斯的《大众不知的,通俗解释之》,这些读物在他去世时依然存放在他的图书室里。哈代在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途径的同时探索宇宙神秘奥义,逐渐形成了生态宇宙意识,并且将这种思考融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哈代的作品充斥着最广泛意义上的对知识的寻求,对自然、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梳理方面有着深层的思考。
一、和宇宙冲突的痛苦与代价
在哈代的创作中,内在意志与自然和社会一直处在冲突之中,大意志始终支配着内在意志。“就宇宙意志而论,哈代指的是必然性、规律或必然的客观运动过程,主要指自然和社会环境。就内在意志而论,哈代指的是一种意志力,一种精神力量,包括人的思想、感情、理想、欲望和追求等。”[2]222在宇宙力量的支配之下,人的内在意志往往处于下风,因而哈代小说中的人物理想难以实现,事业无法成功,环境无望改善,死亡与毁灭几乎成了哈代作品的基调和终结。例如,在《远离尘嚣》中,奥克的理想生活是经营自己的农场,娶一娇妻过着传统的农耕生活,然而,羊群意外死绝,他只能远走他乡,从事农夫、羊倌、管家多重身份的工作。最后虽然与心仪的女子成婚,但却表明两个人的理想都没能实现,因为妻子拔士巴的婚姻理想是不依附于男人,独立、坚强。虽然,她拥有这样的特质,但最后还是屈服于需要依靠奥克的帮助才能度过重重难关的现实,与之结婚。又如,《还乡》中那个满怀理想主义的克莱姆从巴黎回归埃顿荒原,意欲改造荒原人民文化水平低下的状况,然而壮志未酬,却因持续在夜间看书而视力大受影响,几乎失明,最后只能放弃理想。而他的妻子尤斯塔西雅一心盼望着能够离开冷傲、不理人事的荒原,却忽略了自身与荒原是如此契合的真相,离开了荒原就如同一棵树的连根拔起,于是在深夜逃离的过程中溺水而亡。再者,《德伯家的苔丝》里那个清丽动人的苔丝与爱人情深缘浅,被命运几度捉弄,落了个杀人偿命的结果。另外,《无名的裘德》中,裘德立志要进入基督寺学院学习在有生之年成为神学博士,然而命运多舛,甫届三十,郁郁而终。究其实,哈代小说的基本冲突正是人和环境的冲突亦即内在意志和宇宙意志的冲突。在宇宙意志的面前,人类的思想、情感、理想、欲望都显得微不足道。
《还乡》中荒原的景象可谓波澜壮阔且亘古不变,神秘而伟大:“四周和底下的一切,从史前到现今一直没发生过变化,犹如苍穹中的繁星一样,这一来,因世事变迁而产生的心神不宁、被新事物的发展而搅得心烦意乱的心绪便顿时会变得平稳沉静下来。”[3]7哈代笔下的荒原体现出对人类的疏离,它面对沧海桑田、日新月异的人间巨变无动于衷。这岿然不动、傲视人类群体的荒原展现出哈代文学世界中宇宙某一个局部的实际情况,荒原成了宇宙无意识力量的一个载体。
“站在雨冢上的人虽然看不见周围的景色,却可以根据这些篝火的方位来确定每一处地点”[3]17这与《远离尘嚣》中的奥克凭星星所处的位置来判断时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哈代把篝火比喻成“就像星星那样稳定不变”又描述道:“只有一堆篝火,是所有那些光亮最持久的篝火中离这儿最近的,成了闪闪耀眼的篝火群中的一轮明月。”[3]32说明哈代有意无意地让暗夜之中的荒原和夜空遥相呼应,而且“点燃篝火的人们就好像站在世界的某层明亮璀璨的楼层上面,完全脱离了下面那片黑压压的广漠荒原而独立存在。底下那片荒原现在成了一个巨大的深渊,跟他们的站立之地毫无联系。”[3]17-18这些人似乎也漂浮起来了,荒原被上升到了天空的高度,坚固的地球被哈代虚化为无,人们在荒原的活动幻化成在宇宙中进行,篝火成了星辰、明月,天地实现某种意义上的融合,万物合一,和谐生存。而在哈代的眼中每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行星,有自己的人生方向与自由意志:“凡有个性的人,就同行星一样,总带有他们自身运动轨迹的特定气质。”[3]37这恰好说明人类与宇宙是一个整体,人类如同行星是宇宙构成的一个部分,因为宇宙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其相对独立的时空体系。哈代遵循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观点,“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宇宙观认为,宇宙和人为一体,宇宙是无限、永恒和无边无际的。”[4]62尽管人类在宇宙中活动,却对其感到神秘,只能去想象、揣测却没有改变宇宙的力量,可以说,人类是渺小的。因为作为个体的生命是短暂的,但象征着宇宙的荒原却可以继续并且一直存在。总的来说,“哈代以荒原的巨大与神奇来对照人的渺小、微贱、柔弱,表现人的命运被荒原巨人所左右,显得不堪一击。”[5]35这种强大的宇宙意志让人类无所适从的情形在《无名的裘德》中同样有所体现。
基督寺是裘德毕生的梦想:“它对我来说是宇宙的中心,因为我早年曾梦想过它”[6]368。从主流的理论物理学和宇宙学的角度来讲,宇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扭曲空间,并不存在三维意义上的中心。也就是说裘德的梦想不过是虚空的幻想,哈代一开始就没有赋予他去实现的可能。所以当历尽沧桑、大病初愈的裘德与淑重返基督寺之时,或许有阳光照耀在他们身上,然而并没有温度“那些荒废的垣墙确实把阳光反射到了他们身上”[6]369阳光通过“荒废的垣墙”来反射,不过预示着他们此行的命运将是走向支离破碎。阳光代表着宇宙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炽热地执行宇宙的意念。然而在《无名的裘德》里,阳光通常伴随着某种阴暗出现,致使裘德的梦想迟迟不能照进现实。当他勤奋地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时候“透过帽子间隙看着狡诈地注视他的太阳”[6]16此刻,太阳是“狡诈”的,对他学习语言的努力抱着嘲笑的心态,并不以为他会获得成功。当他远眺魂牵梦绕的基督寺时“太阳露出部分身影,束束阳光清晰可见,从两块阴云间直泻而下。”[6]17太阳穿透阴云独自灿烂,却把阴云留给了裘德。当他眺望梦想之地时“那地方上空只有一片光辉或一团白晃晃的烟雾,后面是黑暗的天空,使那里的光亮和城市仿佛只有一英里左右。”似近却远,只可远观而不可企及。可以说,在强大的宇宙面前,个人的意志微不足道。
二、星际距离折射人心的亲疏
星体也常常被哈代用来隐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离尘嚣》中刚直却不善表达的博尔德伍德年过四十仍然单身,对女性的认知几乎为零,“对于博尔德伍德,女人根本就不是必不可少的附属物,而是一些远远的现象——是相貌、运动、恒性都那样变化不定的彗星。”[7]98彗星是由冰冻着的各种杂质、尘埃组成的,它的轨道与行星很不相同,行星有自身固定的轨道,但彗星的运行轨迹呈抛物线或双曲线少数为椭圆形,因而被认为是行踪不定且难以把握的天体现象。博尔德伍德把女人比喻成彗星认为她们变幻不定又遥不可及,可见博尔德伍德对女性知之甚少,因而对拔士巴的追求显得简单粗暴,理所当然又势在必得的态度为最终求爱失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在《还乡》中,哈代运用天体之间的互有引力但又相距遥远这一点来表现克莱姆和尤斯塔西雅由婚姻联结看似交融实则疏离的关系。因为母亲强烈反对俩人联姻,克莱姆决绝地搬离母家,定居在荒原上一处与世隔绝的小屋过起了新婚后短暂甜蜜的日子。然而哈代在形容他们的时候说:“他们就像天上那些成对的星星,互相围绕着对方不停地转啊转的,从远处望去,两颗星似乎就合成了一颗。”[3]283两者互相围绕,并且互相间有引力作用,看起来靠的很近,其实际距离却非常遥远在天文学上称之为“双星”。哈代用双星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关系,实则暗指二人之间虽有婚姻的联结,也有吸引彼此的特质,看起来关系亲密,但他们的心灵却是遥遥相望,难以靠近。更何况他们之间还围绕着让彼此关系更加迷离的星云:“他们眼中所见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光辉。”[3]283星云是由星际间的气体和尘埃结合成的云雾状的天体,横亘在双星之周,用美丽的假象暂时掩盖了两人之间的重重问题,当现实冲破迷雾露出真实面目,两人看清自身在彼此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他们只能是走向破裂的结局。“双星”的光芒或许会有交汇的时刻,却永远不会有真正的交集。
《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在新婚之夜讲述了自己从前受辱的遭遇,却没有得到丈夫克莱尔的谅解,丈夫在雨后的夜晚行走,苔丝紧随其后,夜色清朗,星星倒影在小水凼里,“映在这些小水洼里的星星在她走过时匆匆地闪着光。她要是没有看见水里的星星是想不到头上还照耀着星星的——那些宇宙之间最为浩大无垠的东西现在却反映在这样渺小卑微的东西里面。”[8]233这一方面说明作为宇宙表征物之一的星星,客观独立存在,并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放眼广袤苍穹,不难体会“寄蜉蝣于天体,渺沧海之一粟”的微小感。另一方面意指苔丝与克莱尔之间的婚姻如镜中花水中月,是一个美丽的幻象,即便有婚姻联结却也不过一个是天上的星星,一个是水中的倒影,可望而不可即。而他们的婚姻就如雨后形成的小水洼,终会挥发消散。
三、和宇宙亲近的和谐与欢欣
哈代赋予《远离尘嚣》中的奥克诸多高尚的品质,是哈代塑造的完美的传统威塞克斯人的形象之一。奥克过着诗情画意、悠然淡泊的生活,这正是哈代在早期小说中极力歌颂的生活模式,奥克成了哈代田园理想的化身。奥克对宇宙变化带来的暗示感知敏锐,使得他能够未雨绸缪,积极面对人生里的困境,利于他开阔自己的职业天地。奥克不仅能通过观察太阳与星星或是根据星体所处的位置、发出的光亮来确定时间,还能和星星进行心灵上的交流,让自己的精神意志在宇宙星球中遨游。“先将天空当成一个有用的工具看了一阵儿以后,他静静地转移自己的目光眺望着,仿佛在欣赏一件无比精致的艺术品。他对沉寂的、变幻莫测的景致,也许应该说对这种完全超脱尘世的纷扰世界,一时间好像产生了深刻的感受。世人、纷扰、烦恼和快乐似乎都消失了。”[7]9在奥克的眼里,此刻的星空犹如超然尘世之外的无忧岛,神秘莫测充满诗意,他沉浸在这种壮丽的诗意中,心灵在夜空中漫步,难以返回人世。神秘的宇宙使奥克深深地震撼,同时也对“人的小小的身体居然能产生出对这种宏伟运动的意识”[7]6感到讶异。奥克虽然认为在星辰映衬之下的人类世界显得黯淡无光,却不妄自菲薄,为人类发现星空诗意的运动而自豪。他既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宇宙所呈现出来的美感,也赞美人类发现神秘莫测的宇宙的能力,感受人和宇宙亲近的和谐与欢欣。
在哈代所塑造的女性当中,他十分推崇苔丝并加以“一个纯洁的女性”这样的副标题来为苔丝定位。“哈代曾经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不想显得‘过于个人化’,小说的题目可能就会是《哈代家的苔丝》。”[9]53如此可见哈代对苔丝的偏爱。哈代所倾心的人物形象都和他本人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对自然的无比热爱以及敏锐的感受能力。苔丝这样向众人描述自己的心灵因为星星的美丽而悸动:“晚上躺在草地上,眼睛笔直望着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一心想着它不转念,你马上就会发现自己离开身子好几百里路远,你似乎并不想飞,却已经飞走了。”[8]121这既是清灵纯洁的苔丝对星空的向往,也表明苔丝的灵魂与宇宙契合,能够在卑微的境地里感受到宇宙的无穷的魅力。苔丝对宇宙的认知处在初级阶段,是一种好奇与欣赏的心态。这种人与自然的心灵相契合的能力是哈代生态思想的一个体现。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就是从这种初级阶段开始,从无知到认知,在认知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一些常规性的自然规律,并且逐渐应用到生活实践中。如奥克可以根据天体位置判断时间,自然现象判断天气。《还乡》里的荒原居民可以根据火堆的明亮度、火焰的颜色,以及火苗蹿出的高度而了解燃烧的是什么种类的柴火。这便是光谱知识的实际运用。
奥克与苔丝成为哈代笔下接受度颇高的人物角色和他们身上的自然属性脱不开关系。哈代自幼深受大自然的熏陶,对大自然有着细腻而敏锐的感悟,弗吉尼亚?伍尔夫赞赏他:“是大自然的一位细致入微、炉火纯青的观察者;他能够区别雨点落在树根或耕地上的差异;他能够分辨风儿吹过不同数目枝桠的声音”[10]81。足见自然之子哈代对大自然的观察是何等敏锐与独特,他把这种对自然特别的感知能力与对科学的热望相结合,形成了独有的生态宇宙意识,并把这种意识融注到文学创作中。之所以说哈代的宇宙意识是生态意识也是因为他对自然难以割舍的情感、不吝言辞的赞美、真心实意的尊重,在体悟自然庄严圣美的同时,呼吁人们正视现代文明和社会生活的弊端,去除一切功利思想,做个自然人,感受生命中应该有的纯净与美好。哈代往往将人的心情和感悟与宇宙意象或是其他自然物相联系,表达对自然的尊重与向往,这种人与自然心灵交融的场景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可以说哈代的生态思想与宇宙意识紧密联结,形成独特的生态宇宙意识。
现代工业文明在人与宇宙关系的认知上,高扬人的主体性,对宇宙怀有征服之心,这是一种不自量力而且荒谬的想象,人是宇宙整体的一个微小的成员,宇宙不因人类而存在,相反的,人类却因为宇宙的存在才有生活的空间,生命才有延续的可能。无论是在探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哈代都秉持和谐共存的观念,主张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以一种系统、整体论的眼光,承认并尊重宇宙当中各种生命以及非生命体所具有的内在均等价值。找到人在宇宙中恰当的位置,正确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侵扰、不破坏,可远观、可探索,偏安一隅,自守阵地以达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存理想。虽然哈代在1912年出版的威塞克斯散文集的序文发表免责声明,表示:“延伸四十多年的想象性作品不可能表现出关于宇宙前后一致的科学理论。”但哈代超前的生态宇宙意识伴随着其文学创作的过程,可以说,参悟了哈代的生态宇宙意识才能真正洞穿他笔下所构筑的文学版图上不朽的威塞克斯王国。
[1]张一鸣.论哈代小说中的宇宙意识[J].外国文学研究,2014(4):93-100.
[2]聂珍钊,刘富丽,等.哈代学术史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22.
[3][英]托马斯·哈代.还乡[M].孙予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4]金长发.“弥漫宇宙的意志之谜:哈代哲学思想的一个观察点”[J].扬州师院学报,1988(1):59-64.
[5]吴笛.哈代新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35.
[6]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M].刘跃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7]托马斯哈代.远离尘嚣[M].杨静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8]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孙法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9]何宁.哈代研究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53.
[10]弗吉尼亚·伍尔夫.论托马斯·哈代的小说[A].瞿世镜译.论小说与小说家[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81.
An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Cosmic Consciousness in Hardy’s Novels
LIN Xiao-qi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Sanming College,Sanming,Fujian 365004)
In order to ge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ardy's literary works which built on the immortal kingdom of Wessex,the analysis of Hardy's ecological cosmic consciousness is conducted with respect to the cost paid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mankind and the universe,the interpersonal affinity or estrangement reflected in the distance between constellations,and the delight humans take in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verse.In Hardy's exploring process,no matter in the aspect of man's position in the universe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he insisted to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advocated people to accept and respect the fact that all kinds of lives and nonliving objects have the same values.This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humans are only tiny beings in the universe and thus the best achievable lifestyle is to harmoniously coexist with and give mutual help to all beings in the universe.
Thomas Hardy;economical cosmic consciousness;harmonious coexistence
I106
A
1671-9743(2016)07-0089-04
2016-01-05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项目“哈代与福克纳的文学伦理学比较研究”(JAS160497)。
林晓青,1981年生,女,福建三明人,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