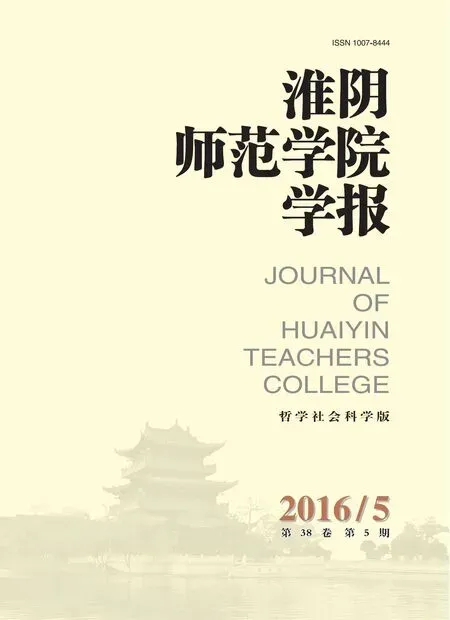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互动体系研究——以华人流散文学现象为启示
朱盈蓓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 福建 漳州 363105)
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互动体系研究
——以华人流散文学现象为启示
朱盈蓓
(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 福建 漳州 363105)
文化生态共荣圈考察处于每一个生态位上的文化形态,研究在特定区域中每个文化形态生态位之间的互动和平衡,并试图保持整体区域文化的全面发展和共同繁荣。沿海上丝绸之路的亚洲国家形成特有的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通过海洋亚洲文化圈中的华人流散文学现象,考察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特质,建立海洋亚洲文化丛,并以此作为海洋亚洲各亚文化特质区隔的重要指标,完成在这一大型文化圈中进行文化生态位竞争和平衡最重要的任务:传承和传播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亚洲文化积淀。
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文化生态位;华人流散文学;海上丝绸之路
一、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
(一)生态位和文化生态共荣圈。
文化生态共荣圈的概念来自于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这一基本衡量单位。生态位本来是生物生态学的界定,考察的是每一个种群/物种实际上或潜在地能够占据的生存空间和地位,强调的是种群/物种与种群/物种之间相互区别的独特的存在地位。种群/物种与种群/物种之间依靠着生态位的相互独立而存在,并因为生态位的偶然重合而竞争,直到各自的生态位扩大或缩小甚至让位、消失,最终又恢复每个物种生态位的独立存在,从而使得生态系统再次获得平衡。文化研究视域中的“生态位”由此引申并模拟出各个文化形态的存在模式:不同的文化形态处于不同的文化生态位上,比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等,都相对地处于独立的存在地位,并通过不同的文化生态位的组合、对立、配置,产生出不同的社会文化样貌。文化生态位尽管与生物生态位同样残酷,每种文化形态面临另一种文化形态时都不免要彼此竞争,去争取存在地位上的优势,但与生物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位不同的是,文化生态位是可以重叠存在的,并且因为不同的重合方式还能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形成新的文化生态环境。
对文化生态圈,即文化生态体系的考察,需要在一定历史、地域条件下进行。对于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圈的考察也就有了现实意义,是在以国别为考量单位的亚洲研究成果基础上,考察超越国界的历史联系和文化交融的尝试,是对海洋亚洲文化整体发展环境的探索,也是对海洋亚洲文化中独特的各类文化形态的保护和促进。因此,在人文生态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化研究主题的情境中,文化生态共荣圈的提出即是进一步考察处于每一个生态位上的文化形态,研究如何在特定区域中极力保持每个文化形态生态位之间的平衡,并保持整体区域文化的全面发展和共同繁荣。
(二)考察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的必要性。
文化生态型资源开发与利用应该考量并基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三者中间进行合理的协调发展,追求高效、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海洋亚洲从广义上看,涵盖着欧亚大陆东部沿海、半岛及岛屿地域,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它既是一种地理概念,也包含深刻的文化和族群内涵。伴随着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构筑的过程,作为地域空间的海洋亚洲和作为文化行动者和接受者的各文化位上的人口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与共生仍在不断演进之中,考察这些联系和变迁的动力与模式是具有必要性的。
第一,对于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圈的考察既是对海洋亚洲文化整体发展环境的探索,也是对海洋亚洲文化中独特的各类文化形态的保护和促进。在呼唤“人文生态”的文化研究时代情境中,文化生态共荣圈研究即是进一步考察处于每一个生态位上的文化形态,研究如何在特定区域中极力保持每个文化形态生态位之间的平衡,并保持整体区域文化的全面发展和共同繁荣,从而实现文化生态美的建构。
第二,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的发展可促生海洋亚洲各个文化生态位竞争优势的展现。不同的海洋文化生态环境、不同民族文化影响下的海洋文化圈也具有不同的特色和发展模式。海洋亚洲文化是多元结构文化组合体。在此文化圈中,多元态势组合呈现跨越政治意义、地域划分的多样性、时代性,也就更需要分解和考察各文化生态位上相对应的文化内核的生成和发展线索带来的竞争优势。海上丝绸之路在此文化生态圈中,以交通路网的形式,从大陆到海洋到岛屿,途经无数城邦、古国、人口集散地,沟通了各个文化位上的经济、政治、人口、文化和思想。
第三,文化生态位竞争和软实力竞争。时代的关注点从“硬实力”比拼向“软实力”的文化、价值观等靠拢。“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1]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结合,大国核心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融合,本土文化与移民文化的汇通,岛屿/半岛文化与大陆架文化的综合发展,以及都市文化与乡野文化的共建,等等,都体现出以多元形式呈现的海洋亚洲文化的区域模式。全球化时代,海洋亚洲文化因其具有历史文化集中发展的区域性特点,又以独特的自有东方文化集中反映着在构成形式上看似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文化形态在海洋亚洲区域文化生态圈中逐渐融汇、磨合、叠加、交错的过程。分析和研究海洋亚洲文化的生成、衍生、发展所产生的历史样貌,以及相应可产生的文化效应,即可将途经海上丝绸之路的某单一区域文化看成一个特定文化生态位,则观察这些文化位上所发生的文化要素的继承、传播、转型,就可考察在文化传承中该文化生态位自身发展的线索,也就对整个文化圈的建设提出参考,并将文化生态位竞争的任务转换成如何传承和传播文化积淀,并将其转化为对软实力比拼的目标任务作出相应的理解和反馈,建立起整个海洋亚洲区域各文化生态位上独特的文化形象。
二、海洋亚洲文化生态互动研究中的华人流散文学现象
(一)华人流散文学在海洋亚洲文化交融中的典型性。
“流散”(Diaspora)来自古希腊语的转译,原本意指在较小地理范围内同源人口的分散情况,后来才指向从原始出生地出发具有一定人口规模迁徙的情况。*“Diaspora can also refer to the movement of the population from its original homeland.”Melvin Ember,Carol R.Ember and Ian Skoggard,ed.(2004).Encyclopedia of Diasporas:Immigrant and Refugee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Volume I:Overviews and Topics;Volume II:Diaspora Communities.这一词语的翻译相对含混,可见有“族裔散居、离散、飞散、大流散”等,又可译作“离散”或“流离失所”。2011年中国比较文学协会会长乐黛云指出“华人流散文学中母语与非母语文学的比较研究已引起世界性关注,正在成为文学欣赏和文学研究的热点”[2]。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便被称为“流散研究”(diasporic studies)。华人流散文学包括华侨文学和华裔文学,是指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由海外华人华侨创作的文学作品,包含汉语写作和所在区域语言写作两种形式。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华人流散作家群体集中在欧洲、澳洲和北美,并“就其文化和文学上的成就而言,居住在北美的流散作家成绩最为卓著”[3]。但对华人流散文学的研究重点在于观察和分析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文学想象,并以作家、作品为核心,展开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诠释。它所指涉的多元文化社会、全球化问题、文化身份认同、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跨文化研究、族裔研究等话题正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情境发展中建构起来的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需要讨论的话题,它本身已经从学科、民族、语言、文化、人类学种种层面上跨越了固有界限,因此在这一文化生态圈中所产生的华人流散文学现象就成为考察在此文化境遇的共荣生态互动关系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二)海洋亚洲文化圈中的华人流散文学主题渊源。
海外华人是海洋亚洲多元和复杂场景中之重要一环,两者之间长期的和有机的互动对亚洲乃至全球历史的变迁均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以海西区域出生或自此源起的海外华人进行的文学创作情况来看,作家们所受到的影响可回溯到闽南文学的形成。中原文化与古越族土著文化自唐以来的逐步结合直接形成了闽南文学的最初模样,同时宋元时期,海西地区以泉州为盛,刺桐古港大兴,泉州一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并成为东方的国际大海港,如此一来,古时海西之地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途,大量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到泉州等地经商,伊斯兰教和各种宗教艺术也由泉州向周围各方传递,丰富了闽南文化,亦为其自始即有的开放文化姿态打下基础。这种绵长的深厚的文化传承与众多异质文化的渗透,让华人在文学书写中处处体现出一种对自身历史身份归属的深度念旧,在题材选择上诸如漂泊海外的人流遭遇,战争年代的失落人群,离家远行的隐性痛楚都成为海西流散作家们的固定选择。海西地区文学历来擅长写史、尤以人物传记为优,这也影响到华人流散作家的创作,他们一方面称颂自身乡土人情的独立和优异,带着强烈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的意识;另一方面又借之图谋“在边陲区域传承和固守中华文化早期的核心价值观念”[4]。在此文化情境中所形成的侨乡文学、华侨文学是来自于众多归侨的书写。从海西沿岸离家到南洋发家的华侨,唱着“漂洋过海卖呀杂货”踯躅在异域陌生土地,再到多年后叶落归根的故乡情愁,是这类作家们善于抒写也是乐于书写的题材。以黄奕柱(民国时期著名闽商,爱国归侨)为原型的长篇小说《鼓浪烟云》[5]因其与旅游热地鼓浪屿的关系在2007年被关注,体验式的旅游经济让人们关心海外华人生存境况。也因为同根同宗,华人流散作家们放眼世界,关注全球华文文学创作情况,在海洋亚洲文化范围内的华文文学的研究成为文化交融的一个有力参考。
“在散居海外的华人中出现了五种身份:旅居者的心理;同化者;调节者;有民族自豪感者;生活方式已彻底改变者。”[6]持有这些特定身份的华人书写使得流散文学的主题有时难以辨识。如2001年,旅居新加坡的一个中国女人以“九丹”为笔名写作的小说《乌鸦》热销所引起的全球华人大讨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发生的。这部小说“成为母语小说在新加坡出版发行的一个神话……媒体竞相报告,新加坡地位最高的英文大报《海峡时报》竟连续几周把这本中文书的文章作为头版的重要新闻,这对中文书来说是非常罕见的”[7]。小说描写了一群中国女孩在新加坡谋生的故事,以在海外境遇中追求所谓理想生活的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种种罪恶以及忏悔为核心内容,试图进行在异质文化的恶性侵蚀中的自省和忏悔。文本中的主要意象生成来自于大量“身体写作”的纪实性描写,作者亦自称“妓女作家”,如此设置所造成的众声喧哗最终成为探寻所谓“民族身体”(national body)在跨国语境(transnational context)中的悖谬置换,解读出“岛国心态”“经济动物”等异化式的概念[8],抑或简单地从金钱与性的关联对异质文化进行解读和想象[9]。这样含混的主题表达是因为在流散文学的创作中,既有对所在的他文化中心区域的靠拢和亲近,但同时又受到文化排他性的边缘化地位影响,在思想意识深处自觉或被动地产生新殖民主义的想象,对他文化同时产生出抗拒、抵制、反击和接纳、投诚、向往的两种对立态度,形成“他乡美梦”与“异质文化地狱”的两重语境。正如赛义德所言:是处在“反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双重意识形态的夹缝中。*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评价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论述。
三、华人流散文学现象对于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圈建设的启示
如何发展平衡的文化政策成为海洋亚洲文化共荣圈建设的关键。华人流散文学中所展示的对于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中各个亚文化的关切,使得各类亚文化虽然来源不同、发展脉络不吻合、时间前后不一致,但流散文学书写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保自有文化传统、护本族文明、适异域境遇、熔异质文化的特点,会构筑各自独立存在、又相互交叉的立体多层次文化生态体系,它所体现出来的“本土性”“流散性”与“现代性”“边缘性”与“跨文化性”等特点能够通过区域文化内部的自身协调、文化合作帮助构建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的互动体系。一个完整文化圈的竞争力要求与其他区域相比较时,在文化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所具有的抗衡要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获取持久的竞争优势,最终实现该圈文化价值的能力。打造海洋亚洲文化共荣圈,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所构建起来的海洋亚洲文化,对于处在文化共荣圈中的各个亚文化而言,它们的文化竞争力一方面体现着海洋亚洲文化发展的总体特点,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反映着海洋亚洲文化的特殊性,并回应着全球化对此文化共荣圈的影响和理解。
第一,求同存异与本土化。流散的生存本身面临的是身份认知的格局差异、文化冲突、意义分裂,因此对于任何与此有关的文学书写而言,“认同是移民文学的中心问题,对于认同的关切支撑着移民文学的存在”[10]。在海洋亚洲文化圈中可逐渐借由对同一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同一文化特质的复原,通过数个文化共同体的建立最终形成既保有文化特质又相互扶持的亚文化生态圈。如东亚区域文化即是基于儒家文明同质化的文化共同体,“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也是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文化。作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它养育了中国有别于西方的古代文明。作为人类普遍的价值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东亚儒家文化圈”[11]。这一处于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中的亚文化圈由中日及朝鲜半岛构成,由儒家文化的来源地中国提供原始思想资源,即孔子儒家、老子道家和释迦佛家三者的融合、汇聚,然后经由儒家文化的接受者日、韩将这一文化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通过各自文化生态位上的特质加以本土化,于是将儒家文化内在的各种文本功能在不同的文化生态位主体上作出了相应求同存异的现实的多种诠释,从而将各文化的创造和贡献提升并提炼成了带有共同性的儒家文明体系。这一体系又反过来影响到各个文化生态位上的文化个体。这样,通过沟通和协调、复原共通的文化特质,就可以建立文化丛关联。一种基本的文化特质产生出来后,相应地会丛生出相关的文化特质来。这些彼此关联的文化特质生成交错的文化丛,关系密切,在功能上相互整合,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一同丰富和发展了亚文化。利用这些文化丛,复原或发展其中的一支,便可以扩大文化丛关联,使得文化生态共荣圈逐步实现。
第二,交互流动与国际化。在原乡情结、跨文化网络、本土化融入所交错形成的张力之中,流散华人作家同时受到家庭、国家、市场三大机制的影响。*Donald M.Nonini and Aihwa Ong.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s an Alternative Modernity,in Aihwa Ongand Donald M.Nonini(eds.).Ungrounded Empires: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7),P23.三大机制通过其所隐含的外交互动与政策互动等具体的现实的影响出现在文学的表达当中,因此华人流散文学展示出的是向各亚文化不断示好/批判的纵横交错的网状体系的发展轨迹,以及在此轨迹描画过程中的身份认知意识的渐趋明晰或失落。对于文化消费者或者急于攻占文化生态位的他者而言,有的特性必须经由干涉或操作进行占有和号召,才能成为同一文化生态圈中的重要特性持有者。就拿前文例证九丹的《乌鸦》而言,华人移民在新加坡的遭遇原本因人而异,融入原本就应分层为向上、平行、向下三种[12],但在跨越实体的国境和面临虚拟的文化疆域时,读者对于异域想象的生成牢牢附着在对文本叙写的意象之上,因此大量的关于华人女性生存的不适结论基于本小说的审丑写作而得出。这一事实说明,对于外来文化持有者到异质文化情境中进行在地化自我教育时交互流动的文化交流和国际化眼光培养的必要性。
第三,国别消界与族群化。考察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的历史渊源,可知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海洋通道在亚洲地域所建立起来的超国家的非正式帝国秩序,所谓“海洋帝国”。20世纪80年代滨下武志等人倡导海洋亚洲观,强调的是亚洲的整体性和主体性,强调亚洲整体地域的主体意识,注重亚洲内部的网络互动关系,以及近代与前近代的内在连续性。[13]再借由吉登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考察来看海洋亚洲区域内现代化的进程。吉登斯超越了传统国家概念对于领土和居民的固着要求,提出“想象的国家”的重要性,强调“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指出现代民族—国家其推动力在于行政力量、公民观(citizenship)以及全球化,主要的基础是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和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的增长。[14]这样一来,随着文化生态位上的单个文化主体的流动,单纯地坚持国家国别界定与相应的国别文化本质论是难以立足的,因此,从文化上探讨国别消界,以相似的文化族群为生态位主体群落的考察就具有了一定的可行性。在考察华人流散文学现象时,注意到纯粹以文学本身的需求作为身份认同建立群落关联、团体互助的情况众多。有学者观察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写作团体,一群商人组织、赞助文学的创作与出版,同时本身还兼任写作者和编辑,即是一例。[15]推崇变通与多元、消界与族群的文化生态共荣圈就提供了可以依据的发展方向。
当然,需要正视海洋亚洲文化生态共荣圈构建的阻碍颇多,如历史问题、领土争端、主导权争夺及大国因素等长期累积的屏障,但在区域性经济合作的外溢范围内探索该文化生态共荣圈的发展是具有意义的。
[1]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1.
[2]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R].2011-04-16.
[3]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J].社会科学,2006(11).
[4]朱水涌,周英雄.闽南文学(闽南文化丛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08.
[5]泓莹.鼓浪烟云[M].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7.
[6]Cf.Wang Gungwu:“Roots and Changing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in Daedalus(Spring1991),P.184.
[7]张靖.东南亚出版商争抢《乌鸦》版权[N].中华读书报,2001-06-20.
[8]朱崇科.民族身体的跨国置换及身份归属偏执的暧昧[J].中外文化与文论,2008(2).
[9]赵小琪.金钱与性影响下的文化景观[J].文艺评论,2003(6).
[10]张颐武.认同的挑战[N].羊城晚报,1998-11-24.
[11]潘畅和.论日本与韩国文化机制的不同特色[J].日本学刊,2006(5):107.
[12]游俊豪.主体性的离散化——中国新移民作者在新加坡[J].长江学术,2000(1).
[13]李长莉.海洋亚洲网络化的地域史[J].读书,2002(7).
[14]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47.
[15]陈舜贞.文学杂志马华作家探析[M]//林明昌,周煌华.视野的互涉——世界华文文学论文集.台北:唐山出版社,2007:308-362.
责任编辑:刘海宁
I207.6
A
1007-8444(2016)05-0649-05
2016-05-18
福建省高等学校科研创新平台重点项目“两岸语言应用与叙事文化研究中心”(LAYY2016004)。
朱盈蓓(1978-),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文艺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