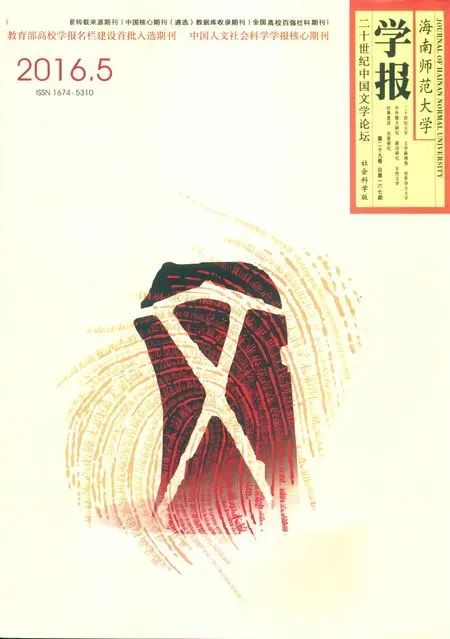黎族文明的失落与重寻
——评《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
朱 琳
(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黎族文明的失落与重寻
——评《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
朱琳
(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是对曾被遗忘的《海南岛民族志》及其作者的重新发现与研究,此书作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史图博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印证、矫枉与补编、增进,对这一在海南岛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史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著作,进行了重评与研究。此书以史图博的研究为索引,对海南岛黎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将海南岛黎族研究推进到了新的深度与广度,是近年来此研究领域不可忽略的扛鼎之作。
关键词:《海南岛民族志》;史图博;黎族文明
郭小东等人所著的《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主要是对德国教授史图博1937年在柏林出版《海南岛民族志》进行重新的研究,依据当年史图博的调查路线进行实地调研,对相关错讹之处进行证伪,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海南黎族研究。
一、《海南岛民族志》在海南岛黎族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海南岛民族志》的德文版原名是《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此书是曾在上海吴淞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人史图博,在1931年与1932年两次赴海南岛进行实地调查,在获得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所作的,1937年在柏林出版。出于侵华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非常重视此书,1943年东京亩傍书房出版了由清水三男翻译的日文版。1964年,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出于“供有关方面研究批判之用”*[德]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广州: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1964年,《说明》第1页。的目的而从日文版翻译为中文,内部印行,书名改为《海南岛民族志》。
作为一个德国学者,史图博为何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对尚属偏远的海南岛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他在海南岛进行调查的路线“多数是过去欧洲人所未尝试过的”,之所以如此细致的调查,源于史图博对海南岛在地缘政治中处于特别地位的认知,他认为“海南岛一方面把印度支那,一方面把印度尼西亚同中国连在一起,在形势上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史图博也看到了民族融合与文明进步的趋势,海南岛也不可避免地走入文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汉族文化今天正处在变化之中,它吸引着欧洲的文化财产,许多古老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消失着”,因此,“在没有全部失去尚可窥视其原始状态之前”,必须记录下他在海南岛的所见所闻,“因为这是最后的时机了”。*[德]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序论》第8-10页。史图博的努力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与认同,早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尾邦高雄就说过:“史图博从整体上给我们一把打开黎族研究的钥匙。”
事实上,研究海南岛及黎族等少数民族的学者并不在少数,就国外研究者而言,19、20世纪之交,许多传教士涌入海南岛,还有不少探险家、人类学家也加入了对海南岛的叙述之中,例如美国传教士香便文(Benjamin Couch Henry)出版于1886年的《海南纪行》。但是这些著述与《海南岛民族志》相比,普遍缺乏民族学研究所具备的学术性和科学性。而国内学者对海南岛黎族进行的人类学研究,数量也并不少,在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一直都是人类学研究的热点。如刘咸所著的《海南岛黎族文身之研究》、《海南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讨》、《海南黎人刎木为信之研究》、《海南黎人面具考》;罗香林的《海南岛黎人源出越族考》;王兴瑞的《海南岛黎人研究》、《海南岛的汉黎交易》、《海南岛黎人来源试探》等,皆为这一时期较有分量的学术论著。
虽然一直以来海南岛黎族的研究工作,并非只有史图博一人,但因其研究所具有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造就了史图博海南岛黎族考察研究的开拓性与丰富性,而从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和专业性两方面来看,史图博的研究更是具有里程碑色彩,即使从批判的角度来看,“作为反映黎族情况的著作来说,这本书算较早的。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外许多资产阶级学者都把它捧为研究海南岛黎族的‘权威性著作’”*[德]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说明》第1页。。
二、 重启对《海南岛民族志》的研究
史图博在1937年于柏林出版的《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中,声言自己的籍贯为“中国宝山县”,可见他对中国的身份归属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海南岛的黎族——为华南民族学研究而作》一书,直到现在也没有由德文直译的中文版本面世,使我们失去了与史图博跨越时空来进行直接对话的机会。另外,由于一些相关文献资料仍然没有公诸于世*黄能《史图博和他的里程碑式贡献<海南岛民族志>》指出:“由于目前对史图博及其《海南岛民族志》的研究刚刚起步,许多文献资料尚未公诸于世。据德国驻广州领事馆副总领事昆宙介绍,德国外交部浩瀚的政治档案中保存着不少关于史图博的原始资料,有待发掘。”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14/03/03/016496204.shtml.,以及期间经历的时间波折与阻隔,导致目前对史图博及其《海南岛民族志》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空白。《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以下简称《〈海南岛民族志〉研究》)一书正是现阶段填补这一空白的扛鼎之作,诚如本书主要作者郭小东所说:“直到21世纪的今天,凡研究黎族的专家学者或热心于黎族文化的人,基本都是沿着史图博所构建的框架来对黎族社会文化历史进行研究的。”*郭小东等:《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1页。
1.对《海南岛民族志》的价值重估与评价
在1964年作为内部批判材料而出版的《海南岛民族志》中,编印者首先对此书的阶级立场作了界定,“这本书不仅在立场上是反动的”,根本上的“反动”决定了当时学界不可能对《海南岛民族志》进行客观的学术研究与评价,因此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对民族关系的描述,对其都作了全面的批判,“贯穿着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而且在方法上也是主观主义的,就是有些资料,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科学性……”随后,对全书重大错误的列举上,认为“全书反映出资产阶级的‘白种人优越’的种族主义观点”,“对于解放前黎族内部和黎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作了很多歪曲和挑拨”*[德]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说明》第1-2页。。意识形态场域的学术研究遮蔽了《海南岛民族志》对海南岛及其岛上民族研究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而郭小东等所著的《〈海南岛民族志〉研究》则是从严谨客观的学术角度,不仅对史图博的海南民族研究进行价值重估,更是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与扩展。
首先,《<海南岛民族志>研究》一书认为,史图博开创了黎族研究田野调查的先河。史图博两次深入海南岛中西部地区,自北向南,从南丰等处开始,穿越今儋州、白沙、琼中、五指山、乐东、三亚、东方等黎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观察和采访,通过实证的民族学资料记录,改变了前人对黎族浮光掠影、道听途说的认识,对以偏概全、主观性随意性强的认知进行了矫枉。
第二,史图博运用体质人类学等现代科学手段,对黎族族人进行了人体现察和测量。通过这种手段,史图博将黎族与高山族以及东南亚的许多民族进行了比较,从生理学角度溯本清源地对黎族的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假设。由此发源,开始了民族学界对于黎族来源问题的长久争论。
第三,对黎族进行了科学的分类,成为日后辨识黎族分枝奉行不悖的圭臬。史图博运用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知识,将黎族分成本地黎(润方言)、歧黎(杞方言)、侾黎(哈方言)、美孚黎(美孚方言)四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认定的加茂黎(赛方言),基本涵盖了黎族各族群。
第四,史图博对黎族的研究,从民族学和人类学视角来看,范围比较全面。从物质文化如体质特征、服装饰品、房屋建筑、经济交易、生产用具、饮食、工艺等,到精神文化如宗教信仰、音乐歌谣、造型艺术、语言、传说等,再到制度文化如村峒组织、村长职责、习惯法、取名、械斗等,《海南岛民族志》几乎面面俱到。
最后,本书还认为,史图博秉持华南文化的大范畴概念,因此他在研究黎族的同时还对海南的苗族、儋州人、临高人、客家人、海南本地汉族、伊斯兰教人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2.比照中的民族志印证、矫枉与补编、增进
在间隔近乎一个世纪之后,郭小东团队通过重走史图博当年的海南黎区研究之路,在黎区展开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对《海南岛民族志》进行了印证与修正,以及补编与增进。“我们这里所研究的是史图博在《海南岛民族志》中对于海南岛地形、地貌、山川、植被、黎族及其语言和民俗等方面的记载与21世纪初期所呈现的不同,以便勾勒出海南岛80年来生态、物种、民族、民俗的变化轨迹,展现边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商品经济大潮中逐渐走向没落,难以新生的窘态。”*郭小东等:《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第32页。《<海南岛民族志>研究》一书通过对黎族文身文化、民间文学、方言支系、宗教文化几个方面的重新调查来进行。这种印证,不但是推翻《海南岛民族志》长久遭遇的内容误判与价值扭曲的有力证例,也是对史图博的科学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史无前例的研究成果的肯定。从印证的结构框架审度,包括郭小东研究团队在内的黎族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路径,无疑是在史图博当年条分缕析架构的黎族研究框架下进行的。从印证的结果上看,也再次证明了史图博对黎族的考察与研究所具备的科学性与权威性。
当然,《<海南岛民族志>研究》也修正了史图博研究中的谬误。例如,在述及美孚黎妇女的文身时,史图博认为“文身是由母亲或哥哥进行,需要继续三年之久”*[德]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第128页。。通过“先后采访了近200位文身老人”的大规模田野调查,《<海南岛民族志>研究》一书得出了与史图博调查完全不一样的结论:“答案是一致的:都说文身时请女性文身师刺肤,个别是由母亲刺肤,而文身时男人不能接近,从来没一例说是由哥哥文身的。”*郭小东等:《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第67页。另外,《<海南岛民族志>研究》针对史图博在对黎族文化研究时出现遗漏,也作了补充性研究考察,特别是对《海南岛民族志》中所匮乏的黎族民间文学的考察,是在田野调查中的重头戏。通过民间口头文献和纸质文献的调研和查考,《<海南岛民族志>研究》对黎族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与概况评述。
《<海南岛民族志>研究》也对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及时的补编研究,例如,对黎族文身研究。郭小东等人指出了史图博研究的不足,除了对其缘起的表述不足外,对待文身现象本身的考察也存在研究的遗漏。史图博“只是把文身作为‘华南文化史标本’的海南岛上所存在的很多现象之一种,因此没有以浓墨重笔描述文身的方方面面”*郭小东等:《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第79页。。对文身的研究,停留在“起源于图腾信仰,明显地显示了母权制的特征”的论断上,而忽视了对文身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论述。有鉴于此,郭小东团队提出了文身的现实意义与价值:“黎族妇女把文身作为性成熟并与外部异性婚姻的标志。也只有文身的妇女,才能被族群所认同,并以文身之美来吸引异性的情爱。”因此,“文身最根本、核心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避免血亲婚配,保证族群能世代健康地繁衍”*郭小东等:《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第82页。。
而在对于文身这一风俗渊源的研究中,郭晓东等人在史图博研究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发现。史图博认为虽然不确定纹身是否与巫术信仰有关,但是就调查的情况来看,纹身这一风俗似乎来源于一个神奇的故事,“黎族祖先有一个女儿,她的母亲在她出生后不信就去世了,其后‘约加西拉’(鸟名)就含着谷物来养育这个婴儿,为了不忘记这个养育之恩”,黎族妇女就涂上各种颜色以“仿效鸟的样子”*[德]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第48页。,史图博基于实地的调查应该说可信度比较高。《<海南岛民族志>研究》在肯定史图博采用此种传说来解释黎族妇女纹身之谜所具有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也对此说予以了补充说明:“问她们为什么文身,回答大同小异,大致有几种说法:1.文身才美;2.死后灵魂祖宗相认,不致成为孤魂野鬼;3.怕给外部落或敌人抢去;4.族群的识别。”*郭小东等:《失落的文明: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研究》,第68页。使这一纹身风俗由来在故事性原因之外,更多地具有属于黎族本身的内部文化原因,可以说更加全面与科学。
三、结语
现在距离史图博撰写《海南岛民族志》已近百年,但是此书在海南岛黎族研究方面仍然有着索引的开拓价值,郭小东团队沿着史图博的研究路线,以《海南岛民族志》为“路书”进行黎族田野调查,采用现代性的全新视野系统阐释黎族文化,从而使《<海南岛民族志>研究》成为了新世纪海南岛黎族研究的工具书,也是了解海南岛黎族文化及历史的重要读本。《<海南岛民族志>研究》一书,以史图博的研究作为黎族文化的基本学术版图,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了黎族的百年沧桑,将此学术版图向纵深挖掘和横向扩展,对黎族文化了解的深度与广度都有了大幅度的拓展。特别是《<海南岛民族志>研究》对于海南黎族文化风俗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变化,还有黎族聚居区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的进步,也给予了重点关注。在对昌江县王下乡的杞方言支系、白沙县南开乡的润方言支系、五指山地区杞方言支系、三亚市回族等地村寨的实地调研中,可以看到,黎区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特性随着时代的进步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当年史图博所见到的黎族社会生活的落后场景早已改变,再也不见因营养不良而肚子肿胀的黎族儿童,聚居于深山之中的黎寨人大多数健康强壮。在文化方面,受现代审美观念的影响,黎族女性中接受文身的越来越少,几近绝迹,更多的黎族女性的生活不再局限于相对封闭的黎寨之中,她们开始走出大山,进入繁华都市,接触到更多的新知识、新观念。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黎族人渐渐离开村寨、进入城镇并适应城镇生活,不再定居于黎寨,村落中的黎族传统建筑也呈现出凋落的状态。
黎区社会与黎族人生活方式的变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现代文明始终会影响到曾经偏僻而边缘的黎族地区,也会将黎族人纳入现代文明的浪潮之中。一方面,改变黎区落后的生活状态,使黎族人接受现代进步的思想观念,无疑是有着巨大的社会进步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进步的同时,不仅摒弃了黎族文化中那些落后的部分,也极有可能抛弃了黎族文化中具有民族特征与悠久历史的传统,如何保存这些属于历史与民族的记忆,将是海南黎族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海南岛民族志>研究》正是这个课题的一次有价值、有意义的尝试,正如莱维-斯特劳斯在《人种与历史》中所说的那样,“当世界受到单调划一化的威胁的时候”,必须要有加强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意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我们的后面、四周,也在我们前面。……每方都以给他方提供更大更宽容的方式来实现其自己”*[法]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人种与历史》,俞宣孟等译:《结构人类学》第2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96页。。《<海南岛民族志>研究》一书以中国当代学者与史图博研究对话的方式,对黎族文化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考察与研究,为黎族文化传统留下了宝贵的文本记忆,这也正是此书最大的现实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王学振)
OnTheLostCivilization——StudiesonShiTubo’sEthnographyofHainanIsland
ZHU Li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The Lost Civilization—Studies on Shi Tubo’s Ethnography of Hainan Island, a rediscovery and study of the forgotten Ethnography of Hainan Island and its author Shi Tubo, is a further verification, redressing, suppl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hi Tubo’s studies on the basis of the fieldwork as well as a reevaluation and study of Ethnography of Hainan Island—a book enjoying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studies on anthropology and ethnography of Hainan Island. With Shi Tubo’s studies as its reference, The Lost Civilization—Studies on Shi Tubo’s Ethnography of Hainan Island has analyzed the Li people in Hainan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thus having upgraded the studies on the Li people of Hainan to a new depth and width. The book is a classic not to be neglected in this aspect.
Key words:Ethnography of Hainan Island; Shi Tubo; civilization of the Li people
收稿日期:2016-01-22
作者简介:朱琳(1988-),女,江苏徐州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发行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国期刊出版史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5-014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