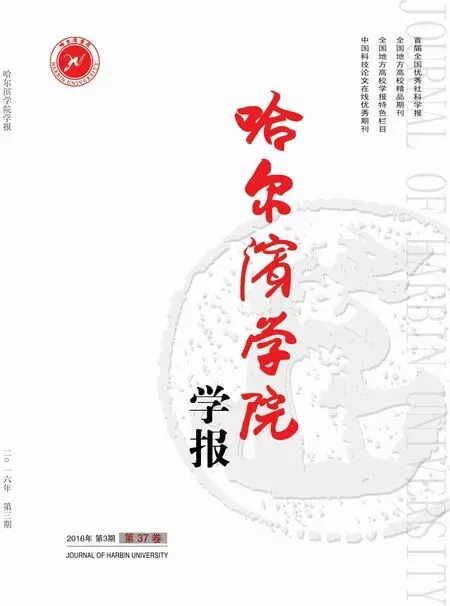西汉中后期对匈奴政策之争的探析——以《盐铁论》为中心
袁 亚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西汉中后期对匈奴政策之争的探析
——以《盐铁论》为中心
袁亚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230039)
[摘要]召开于西汉中后期的盐铁会议,可以看作是士大夫与贤良文学激烈角逐的政治舞台。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上,以桑弘羊为代表的西汉士大夫与贤良文学对诸多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其中就包括对匈奴政策的争论。文章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桑弘羊与贤良文学对匈奴政策的争论,探究其内容、原因和影响。
[关键词]《盐铁论》;西汉中后期;匈奴政策
一、政策转变:从和亲到征伐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经济和社会亟需重新步入正轨,而此时处于冒顿单于统治下的匈奴,已是“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威服诸国”、[1](P373)“匈奴贵人大臣皆服”[2](P2893)的强盛之势。西汉王朝难以与匈奴在军事上直接对抗,所以汉高祖在军事上采取守势,着力避免与之发生战争。然而,“韩王信降匈奴”[2](P2894)使得匈奴犯边,进而引发“白登之围”,汉高祖刘邦暗中送予单于阏氏厚礼之后,汉军才侥幸脱险。“白登之围”发生之后,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和亲成为西汉迫不得已的政策。在吕后操权的时代,樊哙夸口道“愿得十万兵,横行匈奴中”,[3](P3755)但这番言论遭到了众臣的一致驳斥,“于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2](P2895)
到武帝登基时,西汉已步入繁盛阶段。刚刚即位的武帝,并没有立即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而是因循前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但是,“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2](P2904)的和平局面并未继续得以维持,“马邑之谋”的出台宣告了汉匈和亲的结束,这标志着西汉对匈奴政策从和亲到征伐的转变。此后,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击,迫使匈奴放弃漠南地区,向西北边远地区迁徙,基本上解除了北方边患。通过匈奴战争,西汉在军事上获得了巨大战略优势,但也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4](P333)的沉重代价。“汉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5](P1138)放弃了征伐政策。昭帝即位后,对匈奴是“征”是“和”的争论随之出现,而盐铁会议的召开恰好为桑弘羊等士大夫和贤良文学提供了争论的舞台。
二、“武”“德”之争和“利”“弊”之争
1.“武”“德”之辩
汉朝处理与匈奴的关系究竟是以“武”待之还是以“德”待之,这是桑弘羊等士大夫与贤良文学争论的焦点。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士大夫的主张以“武”对待匈奴,而贤良文学却主张以“德”对待匈奴。
(1)桑弘羊主战的观点
第一,推行几十年的和亲政策给中原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屈辱感,基于这一原因,桑弘羊认为:现在的汉朝已处于强盛局面,决不能与生活在蛮夷之地的匈奴和亲,否则就是自取其辱,应该以强大的武力使之彻底归顺,这是他的第一个理由,并认为“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6](P133)即汉朝现在的实力强于匈奴,所以让匈奴臣服于大汉朝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对此,桑弘羊以历史事例加以说明:秦、楚、燕、齐初被周天子分封时,只是弱小的国家,后来它们通过攻灭不仁不义的小国而不断壮大;东周出现的三晋、田齐也是通过征伐不怀好意的邻国而崛起的;秦朝的“立帝号,朝四夷”[6](P133)也是通过强大的武力向周边少数民族示“威”所取得的结果。相反,擅长“修礼长文”的宗周却是“国翦弱,不能自存,东摄六国,西畏于秦,身以放迁,宗庙绝祀”[6](P133)的悲惨境遇。所以,只有征伐匈奴,汉朝才能大展宏图。
第二,匈奴不识华夏之礼、异常贪婪。匈奴通过汉匈双方几十年的和亲捞取了不少好处,“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7](P130)虽然汉朝对匈奴采取了和亲的让步之策,不仅给予其巨大的物质利益,而且尽力在其他方面满足匈奴的欲望,但是其贪婪的本性仍无任何改变,依然肆无忌惮地侵扰汉朝。从民族性格上来说,正是因为“匈奴以虚名市于汉,而实不从”[7](P131)才导致了汉朝被反复捉弄和欺骗。桑弘羊愤怒地反问道:“闾里常民,尚有枭散,况万里之主与小国之匈奴乎?”[7](P131)他认为,汉朝与匈奴有着明显的贵贱之分,高贵的大汉天子应当居于卑贱的匈奴单于之上,给匈奴送财物只会助长他们狂妄自大的嚣张气焰。所以,必须以武力严厉回击匈奴的不仁不义之举。
第三,从边境与内地的关系上说,征伐匈奴也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桑弘羊运用非常形象的比喻阐释了北方边境的安危对内地安全的重要性,即“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6](P134)在他看来,“无边境则内国害”,[6](P134)边境与内地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只有先把边境地区稳定下来,才能使内地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无论是内地的百姓还是边境地区的百姓,他们都是大汉皇帝的子民,二者的安危都是天子心之所系。从体恤民情的层面上讲,出兵讨伐祸害边民的匈奴也是非常合理的。边境的百姓“处苦寒之地,距强胡之难,烽燧一动,有没身之累”,[8](P55)他们时刻处在匈奴南下的兵火危险中,为了使他们摆脱这种灾难就要以武力威慑匈奴。
第四,面对匈奴肆意侵夺的行径,应当用军事手段予以惩戒,以彰显大汉天子的英明。《忧边》中说道:“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民流而弗救,非惠君也。”[9](P45)在桑弘羊看来,如果天子得知百姓处于困境而熟视无睹,就不能被称作“惠君”,就不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从历史上看,商汤和周武王兴兵都是英明的举措,汉武帝举兵讨伐匈奴的行为亦是如此,都是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的正义之举,汉武帝通过此举充分证明了自己是一代“明君”。桑弘羊认为,当朝皇帝应当继承汉武帝未完成的正义事业,只有继续征伐边境的匈奴,才能不失一代明君的威严,才能流芳百世。
(2)贤良文学主和的理由
第一,战争导致汉朝损失数以万计的战马,进而严重削弱了汉朝骑兵的作战能力。贤良文学明确指出了由于“师旅数发”而导致的“戎马不足”的问题。在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出击匈奴的汉军基本上掌握着战略主动权,但是每次交战都会损失大量的战马,例如在元狩四年(前119年)的一次战役中,竟然付出了“军马死者十余万匹”[9](P681)的惨重代价。“这确实是当时汉朝政府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古代之战争,缺乏了军马,就好像今日的战争缺乏了飞机、兵舰和坦克车一样。”[10](P47)再者,匈奴是游牧民族,其特点是居无定所、骑兵力量异常强大。“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其势易骚动也”,[11](P122)生动地说明了匈奴军队的机动性非常强,在战争中握有先天优势。反观以农耕为主的汉朝,其境内适宜养马的牧场极为稀少,一旦出现战马损失惨重的紧急情况,便无法及时向军队补充马匹。倘若战马数量过少,汉朝骑兵部队的战斗力便会受到严重削弱。
第二,汉朝应当尊重匈奴人的生活自由。匈奴人有其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不能因为他们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与汉朝不同就认为理应被汉朝征服。诚然,如桑弘羊认为,“不知礼义”的匈奴在经济、政治、社会上都落后于汉朝,但是他们也有值得被称赞的地方。贤良文学认为,匈奴“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12](P156)可见,贤良文学在评价匈奴社会制度时并不像桑弘羊那样给予过度的贬低,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他们社会制度中的可取之处,这体现了贤良文学民族平等主义的风范。
第三,处理与匈奴的关系应该本着平等、友好、共存、互利的原则,以仁义、道德去感化匈奴,努力避免战争的爆发。只要“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13](P6)就可使匈奴主动亲附,心甘情愿地接受汉朝的教化。贤良文学认为,用道德的力量就能够使匈奴彻底放弃对汉朝的入侵。“三王之所以昌,下论秦之所以亡,中述齐桓所以兴”,[14](P140)充分证实了这一推论。三王不以武力蛮横地对待邻族,所以取得兴旺昌盛的局面;齐桓公以文德、仁义对待周边的诸侯国,所以使齐国成为东方霸主;秦国则因劳民兴军而亡国。按照这一逻辑推论,只要“中国”向匈奴施以仁义,边境就没有被入侵的隐患;反之,对匈奴频繁地发动战争,就一定会削弱汉朝的国力甚至会导致其灭亡。《忧边》语:“蛮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烦虑,而有战国之忧哉?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9](P46)所以,晓之以道德即可让匈奴沐浴汉朝恩德并朝贺“中国”,以德退敌的效果远远大于以武却敌的作用。
第四,文学以“本”“末”之辩反击桑弘羊主战的观点。“夫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无本以统之,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夫治乱之端,在于本末而已,不至劳其心而道可得也。”[9](P46)在文学们看来,“本”即礼义,“末”即桑弘羊为增加边防费用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桑弘羊没有把握“本”“末”的先后和轻重,非但不把礼义置于首要地位,反而把推行针对匈奴的战争放在优先位置,但他所坚持的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其殚精竭虑地筹划战争的行为也是徒劳的。他们重视礼义的作用,认为修治礼义是“安民富国”的最佳方式,当汉朝处于国富民强的状态时,匈奴心向“中国”便是顺其自然之事。
2.“利”“弊”之辩
(1)征伐匈奴之“利”
桑弘羊认为“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8](P55)对外征伐固然需要付出士兵死亡、财政不足的代价,但是汉朝因此赢得了安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贤良文学只关注征伐匈奴带来的皮肤之痛,没有从长远的角度体会征伐匈奴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这是桑弘羊从宏观的层面对此事的考量。从具体层面来说,征伐匈奴确实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桑弘羊认为,匈奴等蛮夷“兵敌弱而易制”,[15](P22)这是进行战争极好的外部条件。在这一绝佳的外部条件下开疆拓土,必然“用力少而功大”,[15](P22)非常容易从战争中获取巨大收益。汉武帝适时地抓住征伐匈奴等蛮夷的机遇,取得了“地滨山河以属长城,北略河外开路匈奴之乡”[15](P22)的武功。对此,他举例加以阐述:伯翳初为国君时,秦国所辖土地只有七十里,后来经过雄才大略的穆公和孝公等君主的开疆拓土,秦国才走完了“自卑至上,自小至大”[7](P132)的蜕变历程。所以说,只有通过发动战争,才能拓展大汉版图,而且这一举措乃“当世之务,后世之利也”。[7](P132)另外,他还以对比的方式说明其中的道理。在“开路匈奴之乡”前,汉朝只是拥有地少人多、不适宜放牛养马的内郡,百姓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而在此之后,汉朝以百越为园圃、羌胡之地为园囿,长城北面的游牧区可使得“騊駼、駃騠实于外厩”。[16](P52)总之,新占领的领土对于发展社会生产会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
(2)征伐匈奴之“弊”
贤良文学认为“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冬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17](P51)边郡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根本不适合汉朝百姓生存,更无法开垦土地。所以,对于以农立国的汉朝来说,以武力夺取的大量新土地是毫无意义的。而“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17](P51)中原地区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适宜发展农业生产,汉朝利用已有的土地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对匈奴开战前,“繇赋省而民富足,温衣饱食,藏新食陈,布帛充用,牛马成群”。[16](P52)而师旅数发之后,“戎马不足,牸牝入阵……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民不足于糟糠”。[16](P52)连年兴师不仅阻碍农业生产,还造成百姓忍饥挨饿的现象。此外,征发百姓到边郡服徭役造成“父母延颈而西望,男女怨旷而相思”[18](P125)的离别之苦。
武帝即位初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19](P1420)此时的西汉经济实力还是值得称道的。然而,武帝初期的经济繁荣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对匈奴战争的开展,西汉政府的财政压力便与日俱增。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取河南地为朔方郡”,[20](P2743)驻守朔方郡导致了“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19](P1422)财政危机在此时初步发酵,后来又经过多次大规模战争的消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19](P1422)的局面便出现了。
由于广大人民苦于徭役、兵役等负担,人民的反抗活动经常发生,社会不稳定因素随之增加,史载“东方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道路不通。”[21](P717)对于贤良文学们来说,汉武帝末年的颓势是他们亲身感受过的,他们认为应当以史为鉴,所以说“秦南禽劲越,北却强胡,竭中国以役四夷,人罢极而主不恤,国内溃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陈涉,地夺诸侯……秦知进取之利,而不知鸿门之难。是知一而不知十也。”[7](P132)所以,贤良文学秉持的观点是:加重人民的负担有可能引起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百姓揭竿而起,进而导致王朝覆灭。
三、双方意见大相径庭的原因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士大夫坚决秉持军事打击匈奴的观点,而贤良文学则坚决反对这种以暴制暴的政策。双方在对匈奴政策上的意见大相径庭,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首先,应该从桑弘羊着手。桑弘羊为洛阳商人之子,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其出身是很卑微的。后来,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让东郭咸阳、孔仅筹备盐铁事务,“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19](P1428)此时的桑弘羊年仅十三岁。从常理来说,出身不好的桑弘羊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受到汉武帝的重用,为了报答皇帝的垂爱,其定会竭尽所能地做好分内之事。在协助东郭咸阳、孔仅整顿财政、增加政府收入方面,桑弘羊显示出了其个人优秀的一面,其作为兴利之臣,后来不断获得升迁,直至全面掌握盐铁事务。由此可见,桑弘羊能在最后身居要职,与武帝时期兴盐铁的措施有着直接的关联,而这一措施的实施主要服务于武帝征伐匈奴的战争。“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帝制时代,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兴利之臣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避免鸟尽弓藏的命运,坚持征伐匈奴的主张是不难理解的。”[22]
其次,朝廷内部的权力争夺将盐铁会议变成了政治角逐的战场。鉴于太子年幼,武帝在临终时“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23](P2932)起初,“霍光与上官桀相亲善”。[24](P754)不久,上官桀的孙女成为皇后,上官桀的政治地位因此得到了极大地增强。这样一来,霍光与上官桀的矛盾由此出现,加之后来双方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致使上官桀“繇是与光争权”。[23](P2934)“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23](P2935)桑弘羊由此加入了反对霍光的阵营,作为首席辅政大臣的霍光当然不会坐以待毙,盐铁论会议便成为其反击桑弘羊的突破口。对于百姓来说,他们自然是不会支持战争的,对于深受儒家治国思想熏陶的贤良文学来说,继续进行百弊丛生的战争也是不可接受的。于是,霍光以“问民所疾苦”[4](P233)的名义邀请贤良文学参加盐铁会议,将桑弘羊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四、此次争论的作用
首先,从个人层面来说,霍光通过盐铁会议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通过贤良文学之口表达反对桑弘羊的立场,利用强大的社会舆论孤立桑弘羊,让人们认识到多年承受的兵役、徭役等负担皆来自他拥护的兴兵政策,从而为彻底消灭桑弘羊一派势力作铺垫。就在盐铁会议召开之后的第二年,桑弘羊就因谋反事件被诛杀。虽然,我们无法判断此次谋反的真实性。
其次,此次的争论为西汉统治者制定新的统治政策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舆论信息,这为霍光调整和转变民族政策提供了强力支持。虽然“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大夫和文学、贤良两方面都表现出正确和错误的思想主张”。[25](P167)但是双方的辩论“对汉武帝时代政策的全面审视,包括对汉武帝本人的批评,为昭宣之世实现治国政策的转变,起了解放思想、探索方向的作用,功不可没”。[26](P191)这是我们应该给予肯定的。实际上,早在《罢轮台屯田诏》颁布的时候,汉武帝已经开始着手收缩北部边境的军事力量,减轻人民的兵役、徭役等负担,以顺应国内百姓的要求。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的言论显然不符合汉武帝晚年改弦更张的愿望,更难以向汉朝的广大百姓交待。与之相反,霍光顺应民意,以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为第一要务,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4](P233)的守成之法,“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24](P760)因此,转变对匈奴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对于开启“昭宣中兴”局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卷一百十[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班固.汉书·匈奴列传:卷九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班固.汉书·昭帝纪: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
[5]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卷二十四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桓宽.盐铁论·诛秦:第九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桓宽.盐铁论·结和:第九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8]桓宽.盐铁论·地广:第四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桓宽.盐铁论·忧边:第三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五十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0]马非百.桑弘羊传[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1.
[11]桓宽.盐铁论·备胡:第八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2]桓宽.盐铁论·论功:第十一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3]桓宽.盐铁论·本议:第一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4]桓宽.盐铁论·世务:第九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5]桓宽.盐铁论·复古:第二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6]桓宽.盐铁论·未通:第四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7]桓宽.盐铁论·轻重:第四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8]桓宽.盐铁论·执务:第九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9]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卷三十[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0]班固.汉书·卫青传:卷五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2]任宝磊.从“轮台诏”到“盐铁会议”——以《盐铁论》观西汉中后期对匈奴政策的重大转变[J].新疆大学学报,2009,(3).
[23]班固.汉书·霍光金日磾传:卷六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5]祝瑞开.两汉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6]孙家洲.两汉政治文化窥要[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魏乐娇
Analyzing the Policy Argument on Xiongnu at the Middle-late Western Han Period——A Case Study of “On Salt and Iron”
YUAN Ya
(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039,China)
Abstract:The conference of salt and iron,at the middle-late Western Han Period,made a political stage for the scholar officials and talented literature scholars to take an intensive game. The two-day conference saw heated argum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n many issues,in which the policy to Xiongnu was included. It is analyzed based on their argument the content,reason and influence.
Key words:“On Salt and Iron”;at the middle-late Western Han Period;the policy to Xiongnu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3.019
[文章编号]1004—5856(2016)03—0081—05
[作者简介]袁亚(1991-),男,安徽涡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