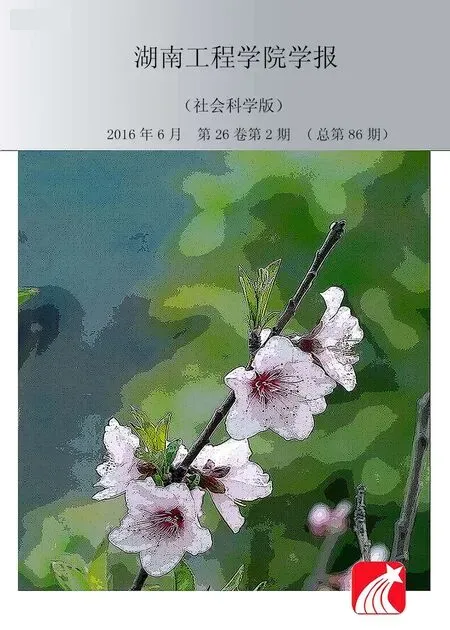歌谣叙事:经典电影《刘三姐》生态审美建构
金乾伟
(广西科技大学 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6)
歌谣叙事:经典电影《刘三姐》生态审美建构
金乾伟
(广西科技大学 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6)
摘要:电影《刘三姐》属于民间文艺生成的经典范本,壮族歌圩文化以刘三姐歌声为代表完成了电影文本的全部叙事,歌谣叙事成就了刘三姐歌仙的最美艺术形象,以此表达了我口传我心的主体自在,现场对歌展演获胜体现了艺术自在,美奂美仑的山山水水讲述了壮族民间生活劳动、爱情婚恋的迷人故事,呈现了审美建构的生态自在,从而电影文本声画组合创造了歌仙刘三姐歌谣叙事的永久艺术魅力。
关键词:歌谣叙事;《刘三姐》;审美;生态
民间文学包含歌谣、神话、传说、史诗、戏曲等各种形态,欣赏主体较容易共鸣的莫过于歌谣,大致因为发自心腹、出口为歌的交流方式,对于表演主体和欣赏主体都容易在听觉刺激下达到艺术形象建构,触动听觉就会使欣赏主体马上进入审美想象的境界。电影《刘三姐》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歌谣在很大很程度上实现了欣赏主体审美建构的效果,此外,笔者还要强调建构文艺世界的审美和生态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存在的前提就是凸显“人”在其中的价值,而这里的“人”是一个复数,代指一个类别、一个集团、一个族群等等,属于集体创作、传承、发展的民间文艺传播方式。刘三姐歌唱活动的空间迥异于江南美景,活动的桂林山水就在歌谣叙事中从欣赏主体眼睛、脑海、心田中自然转换,就在这美妙类似世外桃源的图景中,以刘三姐为代表的歌谣创作主体在诗情画意的山水中营造了歌圩文化美誉天下的奇迹,也就是电影《刘三姐》艺术生命力源自集体无意识升华——人的价值——建构生态审美的结果。
一歌谣叙事——口传我心的主体自在
壮族以歌圩文化著称,这个天生爱唱歌的族群造就了族群突出的特色文化,笔者始终以为民间文艺的生命力在于创造者主体内心情感、艺术才华的全部张扬。歌谣的创作主体看似随意,其实随心哼出的话语,口头传承是民间文学的非常突出的外在表征。底层民间劳动者一般都会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哼唱,狭小、封闭的空间给人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这种感觉会让主体性最大的显现出来,因为空间狭小而又封闭,在外来者不愿关注、干涉的情况下,又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油然而生,因此,民间劳动者往往会感到生活很美好,自得其乐就是这样情景的最好概括,无论生活的时代是多么久远,生活的社会是多么冷酷。那么,不但在悠闲的时刻,民间劳动者会集聚在村寨的某个空闲之地,采用民间文艺的表演形式来一场娱乐狂欢,哪怕在忙碌时候只要有一定自由的空间,他们也会边劳动边歌唱,歌唱成为劳动的见证,唱歌又会成为叙事的载体,所以,歌谣叙事有两种情况,一是劳动者哼唱歌谣,歌谣叙事带有现场的参与性,一是以歌谣的形式讲述故事,成为叙事诗的表演形式。
刘三姐以歌仙称誉天下,意味着所在族群对歌唱艺术的崇拜,普通民众没有不是歌圩文化的建设者,电影《刘三姐》作为民间文艺形态的集大成者,歌谣叙事凸显了劳动者的参与性,同时,又用歌谣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歌谣动听的旋律讲述的故事触动欣赏者的听觉,舞蹈动作、神态表情、场景变换等打动欣赏者的视觉,民间文艺的纯粹讲故事因为时代技术的应用,变为电影文本表现的综合艺术致“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交融一起的是主体内心情感共鸣,就是指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因为文艺展演体现真善美的情感而合二为一。“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1]75电影文本应用歌谣叙事既是表现壮族歌圩文化先天特质,又是塑造刘三姐形象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因为这个天生爱唱歌的族群就是以符合旋律的口头歌谣展示内心世界的一切,也就在这个歌唱的艺术世界里再次体现创作活动主体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归纳为口传我心的艺术自在。

人活在世上或因时代、地域不同,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对于现实生活、未来生活的美好幸福追求却大致相同,而底层民间由于生活条件所限,即使歌唱期盼的年年有余、家庭美满,也大多利用节庆农闲之时,省时省力地展示族群的审美旨趣,歌谣展演特别符合这样的艺术形式。电影文本完全张扬了壮族艺术诉求的趣味,刘三姐成为劳动者的代言人,就在劳动中、休闲中、困境中用歌声传递内心的追求,眼中之物、身外之景、心中之情、心中所感等等都可以自由歌唱,歌谣在电影中成为人的情感和艺术体现的融合,可以赞扬家乡故土的种种美好,可以赞扬艰辛劳动的甜蜜收获,也可以反抗命运不公,也可以抨击社会阴暗。岭南特有的旋律与歌声成就了刘三姐,刘三姐也成为岭南歌圩文化的集大成者,歌唱甚至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说话,特别是电影声光画像综合应用,让欣赏主体全身心沉醉在——歌仙就是刘三姐——刘三姐即是歌仙的声乐世界里,因此,歌谣叙事在电影文本中呈现的是劳动者热爱家乡、勤劳能干、机智勇敢、婚恋幸福……就在种种诉求中成就了我口唱我心的艺术自在。
二歌谣叙事——现场展演的艺术自在
现场感在空间领域就是主体在其中的直接观感,人类不断更新交通工具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达到现场感的主体在场。壮族族群歌圩文化就是把族群整体融合在歌谣叙事主体的展演中,这里的现场展演需要看重:时间、地点、参与者、过程及结果。电影文本将这种展演放置于双双的对歌中,原因是财主不许百姓唱歌,但天生喜好歌唱的族群无法压制,采用对歌来决定能否自由歌唱,电影传承了民间文学的表达话语,世上只有真正热爱歌唱的族群才可能用对歌论输赢,这个情节其实再次把壮族族群的民间文艺呈现出来,而电影文本也恰到好处借助对歌来完成对歌谣叙事的单元组合,以刘三姐为代表的底层劳动者,以秀才为代表的上层官僚者都同构在欣赏者的艺术世界里。
美国学者强调“场域性”(contextuality)[2] 24,电影文本正是用艺术形式提供现场性,影像动感中的刘三姐形象诗意的完成了劳动者成为命运的主人、劳动者最光荣的形象建构。本来历史上,大多数的民众处在社会底层,劳累无比、艰辛无比并不一定换来满意的好生活,所以,面对统治他们的上层官僚地主阶层就会因不公平造成双双对立,也许是劳动分工的不同,底层民众大多是劳者耕其田、狩其猎、采其茶、织其布,而统治者一方代表读其书、做其官、食其肉、饮其茶……电影文本同样是赞颂刘三姐为代表的劳动者,立足于劳动者动手获取的实践知识,来攻击秀才为代表的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比如电影中对歌的选段:
秀才:你发狂,开口敢骂读书郎;惹得圣人生了气,从此天下无文章。
三姐:笑死人,劝你莫进圣人门;若是碰见孔夫子,留神板子打手心。
秀才:真粗鲁,皆因不读圣贤书;不读四书不知礼,劝你先学人之初。
三姐:莫要再提圣贤书,怕你越读越糊涂;五谷杂粮都不种,饿死你这人之初。
除了直接赞颂大多数劳动者直接参与劳动,还会讥讽财主仗势欺人、贪财好色、愚蠢歹毒等等,歌谣叙事展现了刘三姐为代表的劳动者大获全胜,她非但善于唱歌,还机智灵活,远远超过一群酸秀才。歌圩文化的主体是族群的大众百姓,属于民间底层狂欢式的情感展演,这种歌谣巧妙融汇生活经验、为人处世的技巧等等,可能是书上无法学到的,所以,对歌是底层民众的喜好形式,其雅俗共赏决定了生活体验的审美特质,不但要有丰富的生活底蕴,还应有高深且灵活运用的学识。电影歌谣叙事以刘三姐为代表的民众击退了卖弄死学问的酸秀才,足以说明刘三姐不只是有实际的生活经验,还有相当的文化基础,正是这样,对歌赛歌体现了创作主体驾驭民间艺术的奥妙。
歌圩文化创造主体只有歌唱才能体现艺术存在的价值,也只有成为这样艺术的表演者才能显示个体艺术魅力的存在。换言之,歌唱者通过族群传统的文化传承方式展示了艺术的魅力,而这种魅力可以看作一种力量,参与者寄希望击碎可能存在的困境,也呼唤带来美好的希望,即歌唱者全身心的投入完成了族群集体无意识的艺术之旅。奥地利爱·汉斯立克认为音乐给人直观的效果:“即音乐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用原始因素来塑造特定的形式,而产生纯观照效果。”[3]87电影文本以刘三姐为代表的歌唱者放开心扉歌唱,直抒胸臆表现族群的精神向往、情感诉求,壮族族群用天才般的才华构建了特定的艺术自在。
三歌谣叙事——审美建构的生态自在
寻找生命体适宜的生存生活的环境,一直是人类文明进程前进的动力,一旦牵扯到生态领域的问题,大都立马会想到自然环境,电影文本提供了美比江南的另一种自然山水风光,笔者以为生态问题还要包括人在其中的具体生活状态。就电影文本来讲,可以探讨刘三姐为代表的族群劳动,以及她们的爱情婚恋生活,因为“审美的天地是一个生活世界,依靠它,自由的需求和潜能,找寻着自身的解放。”[4]4只有全方位反映那片美丽富有生气大地上的壮族劳动者真正的生活,才能提供电影文本风靡全球的个中原因。
首先,美丽如画的桂林山水冲击了欣赏主体的视觉。就我国历史文化的运行轨迹来讲,提供物质生活保障的重任渐渐南移,由黄河流域向江南水乡位移,而江南鱼米之乡不仅供给了赖以生存的吃食,更为华夏族群提供了人文素养意义的情感寄托。唐诗宋词写就了江南醉人的意象,烟花三月下扬州叩开了几多春梦的心扉,杏花春雨江南又让多少梦想睁开了睡眼。电影文本以特有的影像画面给了江南不曾有的秀气,常绿碧青的山水绝对是如诗如画,这片相对于江南更富有特色的山水一下子就让观众着了迷,山山水水真是绝对的诗意,当然,这特有的天地之间醉人的真实的瑰丽风光,也是真正的蓝天绿地碧水的生态乐园。
其次,歌谣叙事中的采茶划船的劳动场面动人心扉。电影文本设置了刘三姐和众姐妹采茶的劳动画卷,正是这样的歌谣叙事集聚了壮族民众的勇气和智慧,也可以这样讲,歌谣本身带有莫大的神秘力量。采茶的刘三姐带领众姐妹拔掉了禁茶的牌子,又在船上用歌声战胜了财主御用的秀才,又是乘船逃离了囚禁刘三姐的财主莫家,其实刘三姐及众乡亲的劳动和他们生活的山水融合在一起,因为在这片大地上依靠山水生活,故而成为热爱这片土地的主人,为脚下大地的丰收,更为活着的族人用歌声诉说这一切,热爱生活而歌唱自然万物,歌唱产生了人心凝聚的莫大力量。歌谣叙事就其劳动生活及情感诉求表达了生态相关的环境和人际关系,热爱歌唱的人们离不开山水大地,山水大地也因劳动者的歌声增添了生命的魅力。
再次,歌谣叙事共鸣年轻人的莫过于刘三姐和阿牛的以歌传情,他们在共同抗争中历经艰难险阻,一对有情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而广西壮族享有一定传统的婚恋自由,当其时电影产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反而是当时汉族百姓羞于公开谈情说爱,但是汉族年轻人对于真挚甜蜜的爱情向往却是一样的,欣赏主体陶醉于电影文本青年男女自由浪漫的爱情,在他们看来,欣赏纯真的婚恋故事也是寄托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因此,刘三姐和阿牛相爱情节特别的重要,这也是人们喜欢的一个因素,因为只有重视婚恋的民族才是看重未来的民族,子孙繁衍才是人类生命薪火相传的最大可能,这也是人类自身生态意义上的重要内容。爱情的收获意味着纯洁高贵的真情得到了认可,电影文本歌唱纯美的爱情、婚恋就是肯定、赞扬热爱歌唱的劳动者幸福的未来,由此,歌谣叙事完成了很重要的歌圩文化以歌传情的特有传播。
电影《刘三姐》歌谣叙事以族群最突出的歌圩文化成就了经典,刘三姐为代表的歌唱者作为创作主体,可以歌唱劳动、歌唱爱情、歌唱人生各种遭遇,实属我口唱我心;与秀才对歌现场展演再次验证了歌圩文化的力量,艺术自在就是歌仙刘三姐为代表的族群诉求歌声的标志,歌唱在那片大地上的劳动对抗,歌唱迷人风光中的机智挑战;歌唱诗情画意的山山水水,歌唱在青山绿水中的相亲相爱,歌谣叙事让壮族刘三姐作为歌圩文化的代表“成为你自己”,[5]153也成为电影艺术珍品中的自己。
参考文献
[1][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美]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个人文学科的试验时代[M].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8.
[3][奥]爱·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M].杨业治,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
[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5]海德格尔.尼采十讲[M] .苏隆,编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
Ballad Narration: Ecological and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the Classic FilmLiuSanjie
JIN Qianwei
(School of Art and Culture Transmission,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545006, China)
Abstract:The movie Liu Sanjie belongs to the classical model generated from the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Liu Sanjie’s songs constitute the text narration of the movie, which represents the culture of the Zhuang nationality. Ballad narration presents the most beautiful artistic image of Liu Sanjie to show the main body, the artistic performance, and the great story of the Zhuang nationality’s life, work and love in the fantastic surrounding. Such a narration also presents the ecological and aesthetic construction, so as to create the everlasting charm of the singer Liu Sanjie through the classic film.
Key words:ballad narration;Liu Sanjie; aesthetics; ecology
收稿日期:2015-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桂学研究”(12&ZD164)。
作者简介:金乾伟(1974-),男,山东临沂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民间文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81(2016)02-003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