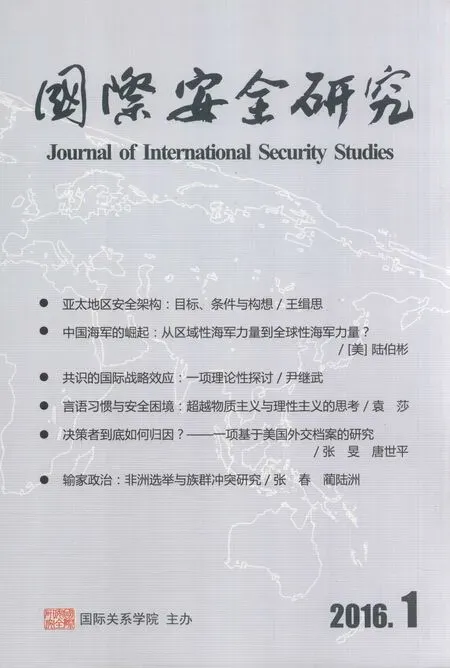言语习惯与安全困境:超越物质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思考*
袁 莎
言语习惯与安全困境:超越物质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思考*
袁 莎
【内容提要】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追求安全的行为体往往陷入“安全困境”的悲剧。国际关系文献强调,理性行为体为了保障物质安全而采取的物质行为最终导致自身安全的下降,这种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却不足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一方面,行为体之间的冲突不能完全归咎于物质因素,也需要从非物质因素,如从言语行为中寻找原因;另一方面,行为体的行为有很大一部分源自习惯,而非有意识的理性。因此,文章试图超越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框架,从言语习惯的角度探究安全困境的形成机制,指出旨在寻求安全的行为体会形成特定的言语习惯,而按照言语习惯说话行事却容易使其他行为体感到不安全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最终导致行为体自身安全的恶化,文章以冷战为例说明言语习惯如何导致美苏陷入安全困境。强调言语习惯的存在和作用,不仅可以丰富安全困境研究,还可以促使行为体反思、改变和建构自己和他人的言语习惯,以期化解安全困境及构建安全共同体。
言语习惯;安全困境;物质主义;理性主义
【DOI】10.14093/j.cnki.cn10 1132/d.2016.01.004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追求安全的行为体往往事与愿违地陷入“安全困境”。国际关系学界大多从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理解安全困境,认为理性行为体为了追求物质安全而采取的物质行为最终会导致自身的不安全。但是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却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行为体不仅有物质性的安全需求,还有非物质性的安全需求,而且行为体不仅通过物质行为,也通过言语行为来追求安全;另一方面,行为体的行为有很大一部分源自习惯,而非有意识的理性。在国际关系现实中,许多冲突并非源于行为体因物质安全需要而采取的物质行为,也常常源于习惯和言语冲突。因此,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安全困境的发生机制,需要超越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理论框架。
本文认为,非理性的言语习惯也是引发安全困境的一个因素,因为追求安全的行为体会形成独特的言语习惯,并往往不假思索地按照言语习惯说话,使其他行为体感到不安全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由此引发行为体之间出现误解和冲突的恶性循环,最终致使行为体自身安全下降并陷入安全困境。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思考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安全困境研究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从言语习惯的角度探究安全困境的形成机制;第三部分以冷战为例说明言语习惯在美苏陷入安全困境过程中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思考化解安全困境的可能途径;第五部分是对文章的小结。本文通过研究言语习惯在引发安全困境中的作用,以期对安全困境理论进行补充,并对理解及解决国际关系现实中的冲突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 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安全困境研究的不足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概念,现有文献大多从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探究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行为体如何陷入安全困境,但是局限于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理论框架不足以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
第一,既有安全困境理论认为,行为体为追求物质安全而采取的物质军事行为会导致物质性的困境,但这一物质主义理论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物质主义理论只关注行为体的物质安全需要,如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生命财产安全。但是,行为体不仅有物质安全的需求,也有心理、身份、认知上的本体安全需求,对于统治精英而言,还存在统治安全需求。此外,行为体需要多少安全,如何对安全进行测量,也不仅仅是客观的物质问题,还涉及主观的非物质因素。对此,现实主义内部也出现分歧。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追求最小安全,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追求最大安全。①防御性现实主义参见Charles L.Glaser,“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World Politics,Vol.50,No.1(October 1997),pp.171-201;进攻性现实主义参见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5(Winter 1994/1995),pp.5-49。对于现实主义的批判者而言,这一问题更具意义,后实证主义否认安全具有本质内涵,认为安全的内涵是语言建构的。②Ole Wæver,“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in Ronnie D.Lipschutz,ed.,On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54.
其二,物质主义理论只关注物质军事行为,如军备增加、武装动员、领土扩张等。但是,物质军事行为不一定导致安全困境,“民主和平论”和“安全共同体”理论表明,在一些国家间,即使一方武力增加,也不会引起另一方的疑虑。③民主和平论参见Michael Doyle,“Kant,Liberal Legacies,and Foreign Affairs,”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2,No.3(Summer 1983),pp.205-235。安全共同体理论参见Karl W. Deutsch,et a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此外,引发安全困境的也不一定是物质行为,观念、言辞、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因素也可能引发误解与冲突,正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指出:“500件英国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还不如5件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大”。④[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页。
其三,物质主义理论强调安全困境的物质性后果,如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名言常被用来描述安全困境:“让战争不可避免地是雅典权力的增长和由此在斯巴达引发的恐惧。”⑤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ranslated by Rex Warner,London:Penguin Books,1972,p.49.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更是断言安全困境让大国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悲剧。⑥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Norton,2001,pp.35-36.但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尤其在冷战后,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大为降低。⑦Christoph Bluth,“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A Paradigm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Vol.15,No.8(December 2011),p. 1363.安全困境也不再只是物质形式,也会以非物质形式出现,例如意识形态战争、网络战争、话语战争等,非物质安全困境更容易激发仇恨情感、煽动负面民意、固化敌对关系。
第二,既有安全困境理论探究无政府状态下的理性行为体为何及如何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这种理性主义理论极具启发价值,但是也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理性主义研究认为,安全困境的核心在于国际无政府体系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是偏好和平的理性行为体也会害怕对方突然袭击,而不得不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措施,这却让对方确信战争不可避免,并由此引发安全困境。①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207-229.但是不确定性并非国际体系中的常态,行为体往往可以确信彼此的意图——虽然多数时候这种确定性是错误的,但正是这种主观的确定性让行为体之间得以形成持久稳定的互动关系。②Jennifer Mitzen and Randall Schweller,“Knowing the Unknown Unknowns:Misplaced Certainty and the Onset of War,”Security Studies,Vol.20,No.1(January-March 2011),pp.2-35.因此,安全困境也非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必然结果,只有当“一国的军事准备在另一国心中产生无法解决的不确定性”时,安全困境才会出现;③Nick Wheeler and Ken Booth,“The Security Dilemma,”in John Baylis and Nick Rengger,eds.,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30.而当行为体可以确信彼此是否构成威胁时,就不存在困境了。④Robert Jervis,“Was Cold War A Security Dilemma?”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3,No. 1(Winter 2001),pp.39-60.
其二,理性主义研究假设行为体具有工具理性,会不断根据新的信息调整成本收益计算,即进行贝叶斯更新,罗伯特·杰维斯 (Robert Jervis)用“猎鹿困境”来描述拥有合作愿望和利益的理性行为体如何背离初衷并陷入安全困境。⑤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January 1978),p.167.虽然杰维斯坚持“安全困境具有理性基础”,但是他也多次强调真实的行为体对安全和威胁的判定并非建立在理性考虑之上,而是深受信念和偏见等非理性因素影响,并由此对不同的对象产生不同的威胁感知。⑥Robert Jervis,“Understanding Beliefs,”Political Psychology,Vol.27,No.5(October 2006),pp.641-663.
其三,安全困境的理性主义逻辑也自相矛盾。如果行为体是完全理性的,就不会只顾眼前利益,而无视长期安全,至少在多次博弈之后,理性行为体应该能够预见安全困境的出现,那么,为何在国家经历多次互动后并没有握手言和,甚至明知会招致更大危险,却依然纷纷加强军事安全措施呢?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认为,安全困境理论假设行为体既将对方看成无法遏制的安全威胁,又认为可以速战速决打败对手,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其实是一种非理性的虚幻。①Jack Snyder,“Imperial Myths and Threat Inflation,”in A.Trevor Thrall and Jane K.Cramer,ed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Threat Inflation Since 9/11,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40.
鉴于以上问题,本文试图超越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理论框架,从言语习惯的角度探究安全困境的形成机制。第一,本文试图超越物质主义,将言语行为纳入安全困境研究。一方面,安全困境的经典定义指出“一国为增强安全而采取的多种手段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增强安全所采取的手段不一定是物质行为,也可以是非物质的言语行为;②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January 1978),p.169.另一方面,国家不仅从物质行为,也从文化、③Richard Ned Lebow,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1-15.身份、④Marilynn Brewer,“Social Identity,Distinctiveness,and In-group Homogeneity,”Social Cognition,Vol.11,No.1(March 1993),pp.150-164.政权形式、⑤Andrew Kydd,“Sheep in Sheep’s Clothing:Why Security Seekers Do Not Fight Each Other,”Security Studies,Vol.7,No.1(Autumn 1997),pp.114-155.政治辞令⑥Adam P.Liff and G.John Ikenberry,“Racing toward Tragedy?China’s Rise,Military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and the Security Dilemm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9,No.2(Fall 2014),p.54.等非物质因素中感知意图并判断威胁。⑦Stephen Walt,“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2(Spring 1988),p.281.言语行为作为沟通交流的主要手段,是行为体发出并诠释意图的重要方式,而物质行为也需要在言语行为创造的语境中被赋予意义。⑧孙吉胜:《国际关系中语言与意义的建构——伊拉克战争解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43-55页。因此安全困境研究不应忽略言语行为的作用,尤其是公开的强硬言辞更容易引发并加剧安全困境。⑨Shiping Tang,“The Security Dilemma:A Conceptual Analysis,”Security Studies,Vol.18,No.3(July-September 2009),p.623.第二,本文也试图超越理性主义,强调习惯在引发安全困境中的作用。理性主义假设已经面临质疑与挑战,因为行为体的行为不仅受理性选择决定,也受国际规范、国内政治惯例、决策者性格和习惯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些因素的存在让行为体不一定选择最优行为,而往往根据“满意度法则”做出次优行为,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甚至说行为体“没有理智,也没有智慧发现最佳道路”。⑩Herbert A.Simon,“Rational Choic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Environment,”Psychological Review,Vol.63,No.2(March 1956),pp.129-138.一些学者借鉴心理学研究,指出非理性因素会加剧行为体之间的猜忌和冲突,例如人脑构造倾向于短视思维和行为;①Paul Massari,“Of Two Minds,”Harvard Gazette,December 7,2010,http://news.harvard. edu/gazette/story/2010/12/of-two-minds.“定向性认知偏见”让人喜欢夸大威胁;②Daniel Kahneman and Jonathan Renshon,“Why Hawks Win,”Foreign Policy,No.158 (January/February 2007),pp.34-38.“根本归因错误”则让人将冲突归咎于对方的意图和性格,而低估情境和制约因素的作用。③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Vol.185,No.4157(September 27,1974),p.1128.理性主义博弈论大师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也承认,混乱和失调的价值体系、错误计算、缺乏信息、缺乏有效沟通、偶然因素等情况都会让真实的人从多个方向偏离纯粹理性。④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16.新古典现实主义还指出国内因素,如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的惯例,容易形成冲突倾向,引发军备竞赛,导致战争。⑤Graham T.Allison,Essence of Decision,New York:Little Brown,1971;Jack S.Levy,“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nd the Causes of War,”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0,No.2(June 1986),pp.193-222.特德·霍普夫(Ted Hopf)进一步提出在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行为选择不仅遵循工具理性和规范理性,还受习惯影响,而习惯也会导致行为体陷入安全困境。⑥Ted Hopf,“The Logic of Habi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4(December 2010),pp.539-561.鉴于言语行为和习惯在引发安全困境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试图探究“言语习惯”与安全困境之间的关系,以期加深对安全困境的理解。
二 言语习惯与安全困境
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引发安全困境的不一定是理性的物质行为,也可能是习惯性的言语行为。本文借鉴霍普夫对习惯的界定,提出言语习惯是不假思索地从已有观念出发进行的言语行为选择。⑦Ted Hopf,“The Logic of Habi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4(December 2010),p.541.追求安全的行为体会形成独特的言语习惯,并倾向于无意识地按照言语习惯说话,引发其他行为体的不安全感,最终导致行为体自身安全的下降。
(一)追求安全的行为体会形成言语习惯
追求安全的行为体会形成、使用并维持特定的言语习惯,因为言语习惯有助于增强行为体的安全感,包括物质安全感、本体安全感和统治安全感。
第一,言语习惯有助于增强物质安全感。行为体之间交往效率和效果的提升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语言,理性主义假定行为体之间无语言交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语言的存在让行为体更好地表达和沟通,促进事务的处理和解决;二是习惯,理性主义假定行为体是完全理性的,忽略了习惯在现实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而作为“基于刺激环境与反应之间习得联系的无意图、无意识的反应”,习惯可以将有用的知识和经验保存下来,有助于行为体的生存和发展。①Wendy Wood and David T.Neal,“The Habitual Consumer,”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Vol.19,No.4(October 2009),pp.579-592.言语习惯作为人类的本能,是行为体发出、接收、理解并诠释信息的高效工具,通过提高信息处理效率,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简单化、模式化、程序化,大大缩短了行为体之间猜测、考虑、权衡的时间,让行为体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内处理更多、更复杂的任务,有助于增强物质安全感。②C.Neil Macrae,Alan B.Milne and Galen V.Bodenhausen,“Stereotypes as Energy-Saving Devices:A Peek inside the Cognitive Toolbox,”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66,No.1(January 1994),p.37.
第二,言语习惯有助于增强本体安全感。人对自我保存的愿望不能简化为对物质生存的欲望,许多研究指出人也有非物质安全的需要,例如“前景理论”认为人是损失厌恶者,相对于新的东西,愿意付出更大代价保住已有的东西。③Robert Jervis,“The Implications of Prospect Theory for Human Nature and Values,”Political Psychology,Vol.25,No.2(April 2004),pp.164-167.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也关注行为体的“本体安全”需要,即“稳定的自我身份认同”。④Jennifer Mitzen,“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No.3(September 2006),p.341.维持认知系统平衡和身份认同稳定往往比物质安全更为重要。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指出,当人们“感受到主体性出现内在的严重失调”时,就会产生严重不适感,并启动自我保卫机制。⑤Yehudit Auerbach,“Turning-Point Decisions:A Cognitive-Dissonance Analysis of Conflict Reduction in Israel-West German Relations,”Political Psychology,Vol.7,No.3(September 1986),p. 539.这种自我保卫机制体现在建立言语习惯上,因为一方面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会建构自己的身份认知和认同;⑥后实证主义关注语言对身份的建构,详见孙吉胜:《语言、身份与国际秩序:后建构主义理论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5期,第26-36页。另一方面,社会交往的惯例化也有助于建构身份认同,提高互动效率,维护本体安全。①Anthony 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50-51.因此,维护本体安全的需要也促使行为体形成特定的言语习惯。
第三,言语习惯还有助于增强统治安全感。统治精英除了要保障国家的物质安全和本体安全,还需要维护自身的统治安全。统治精英会通过权力、制度和文化形成社会主导言语习惯,建立沟通交往的稳定预期,建构个人和集体的身份认同,以维护统治地位和合法性。统治精英尤其会使用具有强烈意识形态、道德规范、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话语来表达国家的身份和政策,给国家和统治政权赋予一种目标和意义。社会主导言语习惯并非是所有个体言语习惯的简单加总,而是充满权力、竞争和争议的结果,言语习惯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约束统治精英的言语行为。尤其在危机之时,统治者使用社会言语习惯有助于赢得精英和公众的支持,而偏离社会言语习惯则会威胁统治安全。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统治者还需要在国际和国内“双层语言游戏”中尽量维持言语习惯的一致性,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安全。②EinarWigen, “Two-LevelLanguageGames:InternationalRelationsasInter-lingu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1,No.2(June 2015),pp.427-450.
在国际关系现实中,言语习惯普遍存在,对于行为体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例如,西方和伊斯兰世界都有各自独特的言语习惯,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伊斯兰世界的宗教神圣不可侵犯言语习惯的存在帮助各自的决策者判断时局,制定政策,开展实践,增强物质安全感;也有助于人们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增强本体安全感;还通过维护社会言语结构的稳定而维持统治精英的统治合法性和统治安全感。
(二)言语习惯容易引起其他行为体的不安全感
行为体的言语习惯在增强自身安全感的同时,却容易导致其他行为体感到安全遭受威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言语习惯会阻碍行为体的理性思维,容易导致行为体说错话、做错事、做错判断,引发其他行为体的不安全感。根据神经科学的研究,人的认知神经系统由控制习惯的反射系统、控制理性的反思系统以及警报系统组成,反射系统先于反思系统运行,只有当反射系统无法处理问题时,警报系统才会对反思系统发出信号并要求其启动。③Mathew D.Lieberman et al.,“Reflection and Reflexion:A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pproach to Attributional Inference,”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Vol.34,2002,pp. 199-249.人脑的认知结构让习惯比理性更容易、更快速地到达大脑的思维和语言处理中心,因而容易跳过有意识的思维,不假思索、自然而然地依赖无意识的言语习惯思考、说话、行事。①Ted Hopf,“The Logic of Habi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4(December 2010),p.541.因此,虽然言语习惯可以节省资源和能量,但是一旦有任务就会跳出“认知工具盒”的工具,可以帮助简化信息处理和反应过程;②Daniel T.Gilbert and J.Gregory Hixon,“The Trouble of Thinking:Acti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tereotypic Belief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60,No.4(April 1991),pp. 509-517.言语习惯无意识的特点又会对认知对象进行自动、迅速,却不一定准确的分类、界定和评价,在时间、信息、精力有限时更容易如此,容易引起其他行为体的疑虑和不安全感。③Ted Hopf,“The Logic of Habi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4(December 2010),p.541.
第二,行为体之间言语习惯的差异也会阻碍有效沟通,产生“主体间认知差异”,并导致对彼此意图的错误感知。④秦亚青:《主体间认知差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第3页。有学者在研读霍布斯时发现,这位现实主义大师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战争并非源于人们对物质权力和生存的追求,而是源于缺乏共同的道德语言,建立利维坦不仅是为了发挥强制性权力,更是为了通过建立中央权威,确定社会生活中最具争议的词语意义、将公共分歧最小化、将荣誉中立化、将对死亡的恐惧最大化、将破坏性的教条消灭。⑤Arash Abizadeh,“Hobbes on the Causes of War:A Disagreement Theor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5,No.2(May 2011),p.298.虽然行为体可以通过学习和翻译来了解对方的语言,但是要完全了解彼此的文化和言语习惯却很难,现实中的行为体甚至根本不会试图用理性理解彼此的言行,而会通过自身的言语习惯和背景知识来进行诠释。即使行为体运用理性正确理解了其他行为体言辞背后的真实意图,也有可能利用双方言语习惯的不同,故意歪曲对方的言辞。
第三,行为体容易形成让他人感到威胁的言语习惯。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都希望拥有一个积极而独特的身份认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称之为“微小差异的自恋”。⑥Sigmund Freud,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edited by Ed.J.Strachey,New York:W. W.Norton,1989,p.72.行为体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和平的,并认为这一点显而易见,因此对于他人的指责,不仅会产生不解和愤怒,还会归咎于他人的邪恶意图。⑦Daniel Kahneman and Jonathan Renshon,“Why Hawks Win,”Foreign Policy,No.158 (January/February 2007),pp.34-38.此外,统治精英也往往夸大本国与他国的不同,以建构国家身份认同、凝聚力和自豪感,甚至故意建构威胁他者,夸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以获得民众的支持。①Jason G.Ralph,Beyond the Security Dilemma:Ending America’s Cold War,Burlington,VT: Ashgate,2001,p.3.行为体往往将自己说成是真、善、美的代表,将他者说成假、恶、丑的化身,这些言语习惯在建构行为体安全感的同时,也会引起其他行为体的反感、疑虑和敌视。②David Campb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p.3.行为体从彼此的言语行为中感知意图,进而判断对方是否构成威胁,而言语行为可能是有意为之,也可能是习惯使然,把无意识的言语习惯当成是有意识、有意图的言语行为,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
因此,虽然言语习惯有助于增强行为体自身的安全感,却容易引起其他行为体感到不安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言语习惯的差异会阻碍相互理解,例如对于人体炸弹,西方将其称为“自杀式恐怖主义”,而在中东地区却普遍将其称为“烈士行动”,不同意义促使不同的行动,也建构自我与他者的不同身份认同,给彼此带来不安全感。③Karin M.Fierke,“Agents of Death:the Structural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and Martyrdom,”International Theory,Vol.1,No.1(March 2009),pp.155-184.
(三)言语习惯将行为体锁入安全困境
言语习惯的自我证实性还会引发冲突螺旋,通过不断的自我强化将敌对的言语习惯内化成事实,并由此将行为体锁入安全困境。④Ted Hopf,“The Logic of Habi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4(December 2010),pp.549-554.
第一,言语习惯的自我证实性容易引发冲突螺旋。行为体的言语习惯让其他行为体感到不安全,促使其他行为体也采取言语或物质上的安全措施加以回应,而行为体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被他人看成威胁,还认为他人的敌意只能由他人本身的攻击性来解释”,因此会更加确信安全威胁的存在。⑤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75.敌对信念一旦形成,人脑的“证实偏见”就会继续寻找证明这一信念的证据,并会抵制相反的信息。⑥Michael Shermer,The Believing Brain,New York:Henry Holt,2011,p.82.因此,行为体会进行“以牙还牙”式的行动—反应互动,促使冲突呈螺旋升级,最终陷入一种“自证预言”。温特说:“这种信念产生证实这种信念的行动……国家是否真的对彼此构成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重要,因为一旦敌对逻辑开始,国家就会进行让他们成为真实威胁的行动,因此行为本身就成为问题的一部分”。①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63.言语习惯的自我证实性让行为体相信对方确实构成威胁,并引发冲突的螺旋升级。
第二,言语习惯的自我强化性将行为体锁入长期互动模式之中。习惯有强烈的现状偏好,任何习惯一旦形成,就会出现抵制变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来自人脑结构、安全需要以及宏观社会结构的固化作用,随着在同一刺激环境下不断重复某种反应,习惯会进一步加强,以后一旦接收到同样的刺激,就会在记忆中被激活,超越理性成为主要行为模式。②Nick Crossley,“Habit and Habitus,”Body&Society,Vol.19,No.2/3(June 2013),p.152.当人们不断使用某种言语习惯,将其内化成事实或真理,就会阻止理性反思,还会在无意识中框定思维,建构身份、利益和偏好,影响安全需求和威胁感知。③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January 1978),p.174.当行为体习惯于将其他行为体说成安全威胁,就将自我与他者建构成互为敌人的身份,也将对外政策的选择范围缩小至冲突和战争,将原本“虚幻的冲突”变成“真实的冲突”。④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80.即使决策者通过理性思考,试图改变言语习惯,也会受到来自国内民众施加话语的压力。⑤James D.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1,No.1(February 1997),pp.68-90.由此可见,消极的言语习惯通过不断加强和内化,会将行为体锁入安全困境之中。
综上所述,行为体旨在追求安全而形成的言语习惯最终会导致自身安全的恶化,而如果偏离或改变言语习惯,又会危及自身的安全感,言语习惯的自我证实性和强化性还会进一步将行为体锁入冲突螺旋之中,一旦陷入这种“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就会带来严重的安全困境。⑥Nick Wheeler and Ken Booth,“The Security Dilemma,”in John Baylis and Nick Rengger,eds.,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65.言语习惯导致的安全困境往往会比理性物质行为导致的安全困境更具深刻性和破坏性,本文将以冷战为例说明言语习惯如何将美苏两国锁入安全困境。
三 言语习惯与冷战
冷战一般被看作是安全困境的经典案例,在二战结束时国际体系不确定的情况下,美苏为了增强物质安全而采取的军事措施让两国陷入安全困境。①Andrew H.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101.但这一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解释却不足以解释冷战的现实,本文试图从言语习惯的角度来理解冷战的起源、深化和最终的结束。
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英三巨头举行了友好而成功的峰会,但到了当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时,美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不久后就爆发了冷战。而事实上,美苏两国地大物博,相隔遥远,没有领土争端,还存在防范德国威胁、建立战后秩序、避免核战争等共同利益。②Deborah Welch Larson,Anatomy of Mistrust:U.S.-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234.战后初期,两国在军事上也极为克制,新上台的杜鲁门总统宣布将沿袭罗斯福的美苏合作政策,并没有采取实质的敌对军事措施,也没有迫使苏联遵守雅尔塔会议关于东欧的三方原则,甚至还考虑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撤军;③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rinceton,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p.176.苏联也尽力缓解美国的安全顾虑,1943年斯大林废除了共产国际,还试图阻止共产党在法国、意大利、希腊和中国夺取政权。④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Foreign Affairs,Vol. 52,No.2(January 1978),p.388.那么,为何两国却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伙伴变成敌人,并陷入了一场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说:“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希望和平,但是强大的内部影响让它们以相互矛盾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从胜利的那一刻起,对共同目标的不同观点就破坏了伟大联盟,产生一个讽刺的结果,即双方追求和平的努力最终导致冷战”。⑤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p.3.由此可见,冷战并非只是物质理性的困境,在这个时期内,美苏两国间发生了频繁而激烈的言语冲突,这种源于言语习惯的冲突在冷战的形成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一,旨在寻求安全感的美苏两国形成了独特的言语习惯。二战即将结束之时,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不确定性愈发凸显,美国和苏联的不安全感也与日俱增,纷纷使用各自的言语习惯进行表达、思考和诠释,以增强自身的安全感。
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有说话果断和强硬的习惯,尤其当面对强大对手时,他会遵循一种“让他们去死吧”的台词,以掩饰自己内心的胆怯和不安,这一言语习惯帮助他步入政坛并当上总统,在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不确定的情况下,杜鲁门更加频繁地使用这种言语习惯,以增强自己在处理复杂局势中的安全感。①引自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131。美国领导人的言辞不仅出自个人言语习惯,也源于美国的社会言语习惯。美国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美国例外论”的言语习惯,表现为“上帝选民”“天定命运”“山巅之城”“不可或缺的国家”“美国梦”等话语形式,强调美国的独特地位和责任以及因邪恶的敌人和危险的外部世界而具有独特的脆弱性,这种言语习惯为美国这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建立了身份认同。②Siobhan McEvoy-Levy,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Basingstoke:Palgrave,2001,p.23.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冷战爆发,这一言辞并非美国社会话语的分水岭,而是对美国社会言语习惯的传承。③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6.随着冷战的进一步深化,言语习惯也日益强化,不仅框定了人们的思维,还抵制变革。杜鲁门曾试图改变对苏联的强硬言辞,却屡遭失败,他后来对此表示后悔,责怪顾问们的施压,还责怪媒体的煽动。④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176.尤其在“麦卡锡主义”横行之时,美国人都害怕被扣上“共产主义同情分子”的帽子,连总统说话也须小心翼翼。“麦卡锡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后,反苏反共的言语习惯却没有消失,肯尼迪总统就曾因同情苏联的言论招致国会共和党的抨击,最后不得不重新回归敌对的言辞上来。⑤引自Deborah Welch Larson,Anatomy of Mistrust:U.S.-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p.28。
二战后,苏联也开始形成并使用独特的言语习惯以增强安全感。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有鲜明的个性和领导风格,他大量使用共产主义和斯拉夫民族的言语习惯,建构并维护苏联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还建构以“危险”为主旋律的社会话语,强调苏联面对一个二元对立、黑白分明的危险世界,而苏联永远站在正确的一方,并有责任引领颠覆资本主义的力量。⑥Ted Hopf,Reconstructing the Cold War:The Early Years,1945-1958,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9.苏联领导人的言语习惯也来源于苏联社会根深蒂固的主导话语,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指出苏联人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意识形态都是苏联行为的根源。⑦George F.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Vol.65,No.4(Spring 1987),p.852.随着冷战的开启和深化,苏联的这种言语习惯也日益不容打破。斯大林原本希望与美国妥协合作,但是受制于国内已经形成的反美言语习惯,他的公开讲话却突出了冲突,掩盖了和平意图。后来的苏联领导人也曾多次试图改变对抗的话语,但是均以失败告终,斯大林逝世后马林诺夫的缓和言辞、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的妥协言辞等,都沉重地打击了他们在国内的权威,并在一定程度上过早结束了他们的政治生涯。美苏两国的统治精英、利益群体、知识分子、媒体和公众的日常话语实践共同维持了美苏言语习惯的稳定。①Ron Robin,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Enem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Military-Intellectual Complex,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第二,美苏两国的言语习惯导致彼此安全感的进一步下降。战后初期,美苏两国国内都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主导话语,仍有话语竞争的空间。②Ted Hopf,Reconstructing the Cold War:The Early Years,1945-1958,p.41.但是言辞上的交锋让两国相互疑虑和恐惧,逐渐形成敌对的言语习惯,并导致安全的恶化。
美苏两国决策者经常自然而然地从各自的言语习惯出发说话行事,面对对方发出的妥协信号,也不假思索地判定是对方的阴谋诡计,导致对方的疑虑和不满。例如,杜鲁门上任第十天,就因波兰问题呵斥来访的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引起苏联人的不满,并开始怀疑美国对苏敌对的意图。后来,苏联领导人曾多次试图缓和冷战局势,例如马林科夫提议与美国举行峰会,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裁军等,对此,美国人却认为这是苏联迫于外部压力而做出的选择,并不能证明苏联愿意妥协的意图。艾森豪威尔也曾经提议与苏联建立“开放天空”的计划,但是苏联人却认为美国试图通过这一计划对苏联开展间谍活动。1960年美苏两国领导人计划在莫斯科举行首脑峰会,冷战似乎出现缓和迹象,但是美国派U-2侦察机前往苏联,而苏联击落侦察机的事实最终导致两国首脑峰会流产。两国的言语习惯也屡次导致战略误判,20世纪50年代苏联习惯性地夸大自己的军事实力,让美国认为美苏之间存在“轰炸机差距”,美国又在每年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夸大苏联的军事威胁,虽然后来美国承认高估了苏联实力,但是这一言语习惯又推动了60年代“导弹差距”话语的出现,肯尼迪政府为此大大增加了美国的国防开支,这又让苏联陷入担忧,并冒险在古巴布置中程导弹,引发古巴导弹危机,将两国推向核大战的边缘。③James H.Lebovic,“Perception and Politics in Intelligence Assessment:U.S.Estimates of the Soviet and‘Rogue-State’Nuclear Threats,”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Vol.10,No.4(November 2009),p.395.
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美苏之间原来共有的反法西斯言语习惯退出历史舞台,两国言语习惯的差异迅速显现,导致误解和冲突频发。美国将自己说成是自由世界的捍卫者,将苏联说成是极权主义,指责苏联寻求世界霸权,而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是苏联的傀儡,并将苏联的行为归咎于俄罗斯民族的本质和斯大林本人的性格,因而美苏矛盾不可调和。苏联则将自己说成是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将美国的行为归咎于帝国主义,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国内财富分配不均而产生的危机迫使其向国外寻找市场,向国外发动侵略和剥削,因此开展“仇恨美国”的运动。对于美国试图实现的“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设想的国际秩序,苏联将其看作是对自身利益的挑衅;对于苏联致力于颠覆世界资本主义的言辞,美国也将其看作为安全威胁。对于同一份《雅尔塔协议》,美苏两国也从自身的言语习惯进行解读,苏联的解读促使其在东欧采取一系列行动,而美国却认为这是苏联恶意违反《雅尔塔协议》,造成两国之间的龃龉。①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pp.114-118.对于美国建立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苏联起初对于是否加入犹豫不决,而美国将苏联迟迟不加入看成是苏联拒绝与自由世界合作的信号,并因此进行指责,这些强硬言辞又促使苏联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看成是侵犯国家主权的霸权和帝国主义,最终选择不加入,造成两国进一步失去互信。美苏都将自己说成拯救世界于纳粹铁蹄之下的救世主,因而值得拥有对世界及欧洲事务的主导权,并将冷战爆发归咎于对方,两国的言语习惯相互排斥和冲突,引起彼此的疑虑、敌视和不安全感,深化了彼此的负面印象和敌对身份。
第三,言语习惯将两国锁入安全困境。言语习惯的自我证实性引发冲突呈螺旋式升级。杜鲁门呵斥莫洛托夫的强硬言辞惹怒了斯大林,斯大林即刻做出强硬回应,谴责美国对苏联发号施令。1945年8月波茨坦会议上美苏首脑的强硬言辞又引发了对彼此的负面印象,导致苏联在同年9月伦敦会议上拒绝就东欧问题进行妥协。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公开讲话中重拾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无法协调”的辞令,指出二战是资本主义本质的结果,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战争就无法避免,并呼吁苏联不可放松警惕,应时刻准备好为国而战。②Andrew H.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101.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宣布“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自由人民反抗武装少数或外部压力的颠覆阴谋”,宣告了“杜鲁门主义”的诞生和冷战的开启。③Michael Beschloss,Our Documents:100 Milestone Documents from the National Archiv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194-199.这些言辞上的交锋推动了两国疑虑和矛盾的急剧升级,美苏还不断从自身的言语习惯出发发出、接收和诠释信号,让事态不断自我证实,使两国更加相信对方确实构成威胁。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做出缓和的努力,提出核武器不仅会毁灭资本主义世界,还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呼吁与美国和平竞争、和平共处,削减重工业投资,增加消费商品投资,暗示愿意让德国统一,认为美苏之间的争端没有“不能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用和平途径解决的”。①Deborah Welch Larson,Anatomy of Mistrust:U.S.-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p. 42.艾森豪威尔却习惯性地认为苏联人在本质上不可信赖,并采取不妥协的策略,美国的态度让马林科夫受到苏联国内强硬派的指责,被迫回到反对资本主义和美国的言语习惯上来,并最终被赫鲁晓夫赶下台,而苏联又转向与美对峙的态度,这让美国相信此前决策的正确,更加坚定了反苏道路。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当初艾森豪威尔与马林科夫会面,冷战可能会更快结束。②Jerald A.Combs,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rom 1895,Armonk,NY;London,England:M.E.Sharpe,Inc.,2012,p.240.加迪斯指出,美国的一大错误就是“杜鲁门及其高级顾问继续使用普遍性言辞来为不具普遍性的政策辩护”,极大缩小了对外政策的选择范围。③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394.
一旦敌对的言语习惯形成并不断强化,就会建构相互敌对的身份和利益,将两国锁入安全困境。美国起初并不愿意介入东亚问题,1950年1月,杜鲁门的“防御圈”演说表明将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地区排除在美国的防御线之外,但是随着“杜鲁门主义”和“遏制”等言辞日益根深蒂固,美国人开始将“共产主义”当做侵略的同义词。④[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中的夸张言辞更是将苏联说成是全球的威胁,为遏制战略进行辩护,并要求大幅增加美国国防开支。⑤Ken Young,“Revisiting NSC 68,”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15,No.1(Winter 2013),pp.3-33.这些文件更将反苏和反共的言语习惯法律化、制度化和内化,并促使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推动遏制政策转向“解放政策”和“击退战略”,也促使美国参与越南战争。而苏联的反美言辞也通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勃列日涅夫主义”等成为既定辞令,苏联的对外政策也逐渐失去灵活性,反美和反对资本主义成为苏联的首要任务,甚至愿意以牺牲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为代价,促使苏联走上与美国军备竞赛的道路。冷战开启后,美苏两国也曾多次试图进行缓和,以改变相互对抗的困境,但是因为言语习惯抵制变革,导致两国错失了很多绝佳的机会,重新回归安全困境之中。⑥Deborah Welch Larson,“Trust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olitical Psychology,Vol.18,No.3(September1997),pp.701-734.20世纪70年代,两国都获得了二次核打击能力,按照理性主义推断,国家本可以更加可信地表达意图,安全困境也应该得以缓解。①Charles L.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Cooperation as Self-Help,”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Winter 1994/1995),pp.50-90.在这段时间内,美苏两国确实做出了缓和姿态和武器控制等理性措施,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冷战的轨迹。②Barry Buzan and Eric Herring,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Boulder,Colo.:Lynne Rienner,1998,p.215.偏离言语习惯带来新的不安全感,美苏“缓和”言辞虽然让70年代看似相对“礼貌”,然而这段时间却成为冷战最危机四伏之时,最终两国不得不回归军备竞赛,并陷入一场“新冷战”。③[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页。
关于冷战结束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现实主义指出实力衰退和海外负担导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④William C.Wohlforth,“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9,No.3(Winter 1994/1995),pp.91-129.建构主义则认为,苏联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深刻改变重塑了苏联的身份和利益诉求。⑤Robert G.Herman,“Identity,Norms,and National Security:The Soviet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 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271-316.两派的解释都有不足之处,苏联的政策转变不能完全用物质能力解释,而苏联人也从未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概念并没有得到苏联国内利益群体和民众的全力支持,甚至遭受强烈谴责。⑥Matthew Evangelista,“Norms,Heresthetics,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3,No.1(Winter 2001),pp.9-10.从美苏缓和敌对言语习惯的角度来思考冷战结束的原因,可以得到新的启发。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跨国信息网络的兴起,苏联新的领导集体日益接触到西方的言语习惯,逐渐形成“共同安全”“防御性防御”“合理充分性”等新式话语。⑦Thomas Risse-Kappen,“Ideas Do Not Float Freely:Transnational Coalitions,Domestic Structur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Spring 1994),pp.185-214.1983年11月,北约“优秀射手演习”酿成的美苏核战危机也极大地转变了美国总统里根的思维,他开始意识到美苏之间安全困境的可怕后果,并对美国一直以来的言行进行反思。⑧Beth Fischer,The Reagan Reversal,Columbia,MO: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7,pp. 133-143.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动了“开放”“改革”“新思维”等新概念的传播,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也不再用“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式的言辞描述美国。①Nicholas J.Wheeler,“‘To Put Oneself into the Other Fellow’s Place’:John Herz,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Nuclear Age,”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2,No.4(December 2008),p.501.虽然戈尔巴乔夫提出终止核试验的计划并没有打消美国的顾虑,但是在美国未能积极回应的情况下,苏联继续发出缓和的言辞,这让美国开始理解苏联和平的意图,并促成1987年美苏《中导条约》的签订。②Alan R.Collins,“GRIT,Gorbachev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4,No.2(April 1998),pp.204-205.正是在这种缓和的语境下,1988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会议上宣布削减苏联驻东欧的常规军等物质行为才能进一步打消美国的疑虑,促成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接触和合作。但是两国并没有完全改变各自的言语习惯,戈尔巴乔夫的言辞并未完全与苏联主导言语习惯割裂,他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话语中吸取言语要素才得以获得国内支持,并且随着新的言辞极大偏离苏联社会根深蒂固的言语习惯,他失去了国内的支持,苏联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的崩溃。③Matthew Evangelista,“Norms,Heresthetics,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3,No.1(Winter 2001),pp.5-35.如今,经历了冷战后的经济低迷和北约东扩,旨在增强安全感的俄罗斯重新形成了反对美国霸权、大国复兴等言语习惯,又将其与美国及西方世界拉入了安全困境的边缘。而老布什成为“冷战英雄”和举国上下对冷战胜利的狂喜表明,美国也没有改变自身的言语习惯,甚至进一步加深了既有言语习惯,而近年来的反恐战争又是对这一言辞的延续。④Carol K.Winkler,In the Name of Terrorism:Presidents on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Post-World WarⅡEra,New York:SUNY Press,2006,p.166.美苏两国的这种言语习惯都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埋下隐患。
四 如何避免安全困境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似乎是国家无法逃避的悲剧。但是,正如杰维斯所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灭绝呢?”⑤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 (January 1978),p.170.理性主义提出一系列缓解安全困境的途径,例如冲突缓解的渐近互惠策略(GRIT);⑥Charles Osgood,An Alternative to War or Surrender,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2.“一报还一报”的策略;⑦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高成本信号”保证策略;①James D.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1,No.1(February 1997),pp.68-90.区分及平衡进攻性和防御性军事能力策略等。②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 (January 1978),p.209.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些策略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很罕见且大多以失败告终。③Evan Braden Montgomery,“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Realism,Reassurance,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2(Fall 2006),p.152.高成本的物质行为不一定获得其他国家的理解和信任,也容易将自己置于弱势地位,而进攻性军事能力和防御性军事能力更是无法区分,且易受行为体的主观感知和偏见影响。④Charles L.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4(Spring 1998),pp.44-82.本文则从言语习惯的角度,思考如何避免安全困境,并走向安全共同体的可能路径。
(一)认识到国际关系中言语习惯的普遍存在和影响
鉴于言语习惯在引发安全困境中的重要作用,应充分认识到自身、他人及国际社会的言语习惯普遍存在。
第一,认识自身的言语习惯。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认为人应该“有意识地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时刻警觉和反思自己的“惯习”。⑤Chengxin Pan,Knowledge,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2,p.151.行为体也应意识到言语习惯是自己重要的言语行为方式,是提高效率的内在本能和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言语习惯不仅会深刻地影响自己的认知、理解和表达,还会建构自己的观念、身份和利益,同时言语习惯也会阻碍有意识的理性思考,容易造成自己说错话、做错事、做错判断,导致行为体之间的猜忌与误解。因此,外交实践者在互动过程中需要时刻跳出自我,进行自我观察、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而学术界更应有意识地警觉社会的言语习惯,并通过“集体知识分子”共同承担这一任务。⑥Pierre Bourdieu,“Viva la Crise!For Heterodoxy in Social Science,”Theory and Society,Vol. 17,No.5(September 1988),p.778.行为体还应建立制度性的反思机制和怀疑机制,在各种行为模式之间形成相互制衡,及时发现新问题和新趋势,避免导致言语习惯僵化并陷入恶性循环。⑦Raghu Garud,Arun Kumaraswamy and Peter Karnoe,“Path Dependence or Path Creation?”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Vol.47,No.4(June 2010),pp.766.
第二,认识他人的言语习惯。杰维斯认为,“同理心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可以缓解安全困境。①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 (January 1978),p.212.行为体应认识到他人的言语行为也可能出自言语习惯,或受制于社会言语习惯,避免不加辨别地将他人的言语行为与真实意图画等号,增进对其他行为体言语习惯的了解,减少误解。国家可以增加翻译、培训和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投入,来缓解国家间交往产生的成本;开展区域和国别研究,了解他国的历史、文化、战略以及决策者的背景、经历和风格,了解其他国家决策者及公众的言语习惯,提高言语习惯的敏感性,并由此预测其行为选择;积极与其他国家建立沟通机制,深入了解彼此的言语习惯。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两国建立了首脑热线,方便两国元首在危机之时直接沟通以避免核战争的爆发。到了海湾战争期间,老布什总统的电话外交成果已经表明这种直接沟通机制确实有助于国家首脑之间交流理解,管控分歧,建立信任。②Jeffrey Crean,“War on the Line:Telephone Diplomacy in the Making and Maintenance of the Desert Storm Coalition,”Diplomacy&Statecraft,Vol.26,No.1(January 2015),pp.124-138.
第三,认识国际社会中的言语习惯。夏洛特·艾伯斯坦(Charlotte Epstein)指出国际行为体是一种“分裂的主体”,无法用主体间共通的语言来准确地表达自己独特的欲望,对于初入国际社会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③Charlotte Epstein,“Theorizing Agency in Hobbes’s Wake:The Rational Actor,the Self,or the Speaking Subjec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7,No.2(Spring 2013),pp.287-316.但是国家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交往、加入国际制度、主动习得并遵守国际规范,将国际社会的言语习惯制度化、规模化和内化,以此减少互动成本,促进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国家在参与国际社会交往时往往采取三种方式——全面排斥、全盘接受和改良主义。④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Schuster Paperbacks,2011,pp.72-74.鉴于现代国家无法闭关锁国,还可能因此招致他国的疑虑,而全盘接受国际社会的言语习惯却需要放弃自身的独特性和身份认同,因此,既保留本国独特的言语习惯,也充分理解和学习国际社会的言语习惯,才是这个多元化世界中更加理想的交往方式。
一言以蔽之,行为体应该建立一种“安全困境敏感性”意识,通过认识到自己、他人及国际社会言语习惯的普遍存在和重要作用,避免引发并陷入不必要的安全困境。⑤Ken Booth and Nicholas J.Wheeler,The Security Dilemma:Fear,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8,p.7.
(二)改变引发误解与冲突的言语习惯
言语习惯很难改变,但是语言内在的不稳定性意味着言语习惯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行为体可以有意识地改变容易引发误解与冲突的言语习惯。
第一,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言语习惯。皮埃尔·布迪厄认为只有在面对不同、新奇或竞争性的话语和实践时,“言语习惯”才会进入人的意识,也才有可能被打破。①Nick Crossley,“Habit and Habitus,”Body&Society,Vol.19,No.2/3(June 2013),pp.150-151.国家要改变根深蒂固的言语习惯,就需要营造开放健康的言语环境,建立社会的基本信任体系,推动跨文化的交流合作,在言语习惯的接触与碰撞中不断进行反思。国家还应认识到,虽然对立性的言语习惯会给自己带来安全感,但是也会给他人造成不安全感,最终会危及自身安全,因此应避免使用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语言,而应超越边界思维,“将他者看成自我的延伸”,建构更为良性的言语习惯。②Jason G.Ralph,Beyond the Security Dilemma:Ending America’s Cold War,p.108.例如,欧洲曾经因为相互冲突和排斥的身份认同陷入长期战乱,但是二战后欧洲国家开始将自我与他者对立的身份话语转变为“现在和平的欧洲”与“过去战乱的欧洲”相对立的身份话语,并推动安全共同体的建立。③Ole Waever,“European Security Identitie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34,No. 1(March 1996),pp.103-132.国家还需要结合其他行为,发出高成本信号,以有效表达自己和平意图。④Andrew H.Kydd,“Game Theory and the Spiral Model,”World Politics,Vol.49,No.3(April 1997),pp.371-400.同时,国家也需要考虑到社会言语习惯的约束,应引导并塑造公众的言语习惯,避免剧烈变革导致的动乱。
第二,积极改变其他行为体的言语习惯。行为体可以通过“后果逻辑”和“恰当逻辑”改变其他行为体原有的言行。⑤James G.March and Johan P.Olsen,“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Autumn 1998),pp.943-969.但是心理学研究指出,强权或战略性的妥协与交换无法改变他人的深层观念,因为纠正对象会抵制与自己观点相矛盾的论证和证据。⑥Brendan Nyhan and Jason Reifler,“When Corrections Fail: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Political Behavior,Vol.32,No.2(June 2010),pp.303-330.国家可以借鉴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的见解,通过满足人格诉求(ethos)、情感诉求(pathos)和逻辑诉求(logos),说服其他国家改变既有言语习惯。⑦Robert Hariman,“Henry Kissinger:Realism’s Rational Actor,”in Francis A.Beer and Robert Hariman,eds.,Post-Realism:The Rhetorical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6,p.36.例如,冷战后,“保护的责任”成为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主要话语,这一言语习惯为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建构了必要性和正确性,但是巴西通过提出“保护中的责任”概念,利用权威人士极具逻辑性的话语,引发西方和国际社会的情感共鸣,成功地引领了干涉主义言语习惯的变革。此外,国家往往从其他国家内部特征表达出的“表征”(indices)中判定其真实意图,而不愿意相信其他国家有意发出的“信号”(signals)。①Robert 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p.281.因此,国家不仅需要有意识、有意图的对外战略话语,还应有意识地反思并改变政府和社会各部门的日常言语习惯和思维观念。但是即使有时国家改变了自己的言语习惯,也很难立即改变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和言辞,需要认识到言语习惯的改变具有滞后性,应避免急于求成,更不应因此武断地判定他人的意图。
综上所述,国家应扩大并深化国际交流,积极改变容易引发误解与冲突的言语习惯。需要注意的是,国际交流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理解和信任,国家间交往不是单方面文化输出,不是进行文化比较,不是宣扬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而是需要批判性的反思和文化的双向互动,否则就会流于肤浅的形式主义,甚至适得其反。
(三)利用言语习惯建立安全共同体
言语习惯容易引发安全困境,也可以促进安全共同体的建立。应积极利用并发挥言语习惯的特性,建构有利于相互理解的言语习惯。
第一,打破不利言语习惯自我证实和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有意识地打破言语习惯的自我证实逻辑。杰维斯指出,当决策者理解了某一理论后,就可能规避这一理论所预测的结果,并对理论进行“自我证否”。②Robert Jervis,“Thinking Systemically about Geopolitics,”Geopolitics,Vol.15,No.1(January 2010),p.169.最早提出安全困境概念的约翰·赫兹(John Herz)也认为,行为体通过理解安全困境的机制,就可以积极缓解疑虑并避免安全困境。③Nicholas J.Wheeler,“‘To Put Oneself into the Other Fellow’s Place’:John Herz,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Nuclear Age,”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2,No.4(December 2008),pp.493-509.当人们认识到言语习惯会引发安全困境,就有望避免安全困境的悲剧出现。另一方面,还需要打破言语习惯的自我强化逻辑。国家应鼓励社会内部的话语竞争,因为持不同观点的群体是推动话语改变的主要源泉。国家还应积极利用权力结构变化、危机、灾难等外界刺激带来的“机遇窗口”促进言语习惯的改变和创新。④Nick Crossley,“Habit and Habitus,”Body&Society,Vol.19,No.2/3(June 2013),pp.150-151.“机遇窗口”往往由可预计的事件开启,如领导人更迭、政策更新、实力变化等,因此需要具备政策敏感性和洞察力,预测机遇窗口何时及如何开启,及时且强力打破言语习惯的自我证实性,开启“路径创造”,创建新的言语习惯。①Raghu Garud,Arun Kumaraswamy and Peter Karnoe,“Path Dependence or Path Creation?”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Vol.47,No.4(June 2010),pp.760-774.
第二,积极利用言语习惯的自我证实性建构“安全共同体”。言语习惯的存在可以起到促进交流的作用,并通过刺激—反应机制不断强化,内化成自然而然的行为方式,并建构行为体更深层次的观念、身份和利益。理性主义学者认为,“互惠”是打破安全困境的最好方式,建构有利于和平的言语习惯可以作为互惠的第一步,如建构“和平共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等积极的言语习惯,发挥言语习惯的积极影响,促进行为体之间的有效沟通与交流,建构互相理解、互相认可、互相尊重、互为朋友、平等互惠的身份认同,打破恶性循环而走向良性循环,建立安全共同体。二战后的德国就是一个典范,通过将德国传统的不安全感、“生存空间”和“地缘政治”等言语习惯转变成和平的言语习惯,德国也日益将自己看成是欧洲国家和欧盟安全共同体之中的一员,并与欧洲宿敌走向了和平。
第三,积极发挥言语习惯的自我强化性,建构更加公平、公开、公正的国际社会语言游戏规则和更加“成熟的无政府状态”。②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2nd edition,Her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1991,p.177.建构语言游戏规则需要权力的参与,语言游戏规则也会反过来发挥权力作用。③Nicholas G.Onuf,World of Our Making: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9,pp.196-248.在西方言语习惯主导的国际语言游戏之中,非西方国家不可避免地容易被误解。随着非西方国家的觉醒和力量的逐渐壮大,要求改变西方国家的偏见并建构更加公正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要想改变旧的国际社会语言游戏,建构更加公正的国际语言游戏新秩序,首先需要非西方国家增强自身的实力,改变国际权力结构格局。非西方国家也可以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讨论,通过“更好的论证”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④Thomas Risse,“‘Let’s Argue!CommunicativeAction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1(Winter 2000),pp.1-39.虽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有诸多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在许多领域,行为体之间的交往不能直接用权力说话,或者用权力说话的代价很大,具有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论证更容易赢得理解与认可。
由此可见,国家应打破不利言语习惯自我证实和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并利用言语习惯的积极作用,形成有助于相互理解的言语习惯,打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社会言语习惯,推动安全共同体的建立。
五 结语
当今世界许多冲突的症结都可以从言语冲突的角度来解释。①John S.Dryzek,Deliberative Global Politics:Discourse and Democracy in A Divided World,Cambridge,UK and Malden MA,USA:Polity,2006,p.1.言语习惯尤其容易导致误解和敌意,也是引发安全困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和冷战的结束,大国之间军事冲突和战争的风险越来越小,但是国家日益诉诸强硬言辞以追求安全感。虽然言语交锋貌似廉价,却会深化国家之间的相互疑虑和敌视,大为缩小对外政策范围,让管控分歧的任务更加困难,甚至比武力主导的安全困境更具深刻性和持久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兴起一股“中国强硬论”的话语,并在美国政策界、学术界和传媒界快速并广泛传播,这一言语习惯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理据。②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Spring 2013),pp.7-48.在日益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下,遵循“中国强硬论”的言语习惯有助于提高美国的安全感,却极大地损害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缩小话语空间、建构敌对身份,让中美两国面临陷入安全困境的危险。由此可见,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并没有终结,理解言语习惯与安全困境之间的关系对于今天的国际关系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正如温特所说:“安全困境并非是无政府状态或自然状态下的既定情况”,而是行为体在互动中建构的。③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407.国际关系现实中也并非只有安全困境,还有许多冲突和解的例子,例如英美合作、法德和解、中美建交等,这些从敌到友的案例为国家逃脱安全困境提出希望。因此,有必要认识国际关系中言语习惯的存在和作用,有意识地改变容易导致误解和冲突的言语习惯,积极建构有利于相互理解的言语习惯,避免陷入安全困境的悲剧。
【责任编辑:谢 磊】
袁莎,外交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北京邮编:100037)。
D815.5
A
2095-574X(2016) 01-0056-24
* 本文系“外交学院2015年度学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成果”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编号ZY2015YA22。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外交学院孙吉胜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教授的指导以及《国际安全研究》编辑老师和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特此感谢,作者文责自负。
2015-10-08】
2015-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