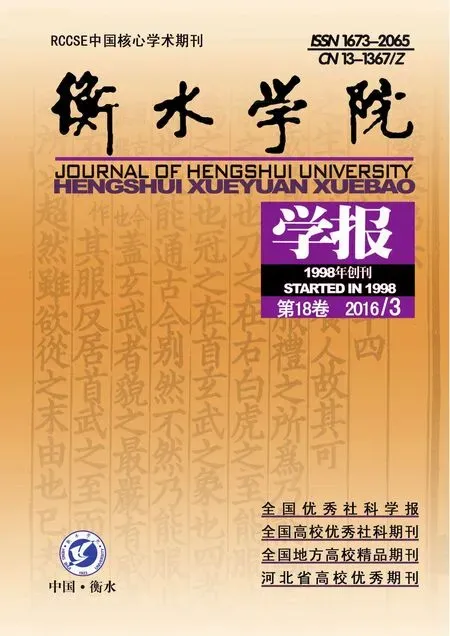宋翔凤的孔子素王说
黄 开 国(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00)
宋翔凤的孔子素王说
黄 开 国
(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00)
摘 要:在清代今文经学从照着说到接着说的转变中,宋翔凤是第一个明确区分微言大义的经学家,他不同于刘逢禄的三科九旨统宗经学,而是以孔子素王说为经学微言的核心。有人说宋翔凤经学微言的核心是性与天道,是不正确的。正是宋翔凤的重视孔子素王说,直接开启了廖平、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
关键词:宋翔凤;经学;微言;孔子;素王说
在清代经学史上,刘逢禄尽管是言公羊学的学者中将重大义转向重微言的关键性人物,但他并没有明确区分微言与大义,虽然他实际上已经是以微言为宗,却常常将微言与大义混而不分。故他只能停留在照着说的阶段。宋翔凤则较为清楚地意识到微言大义之分,是清代讲今文经学的经学家中第一个明确此点的思想家,所以,他能够在某些方面超越照着说,并特别重视孔子素王说的发挥,而为廖平、康有为以孔子改制说的接着说提供直接的理论素材。
一、明确区分微言大义
宋翔凤区分微言大义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最早明确区分微言大义见于 26岁时所著的《经问》,该书的《自序》说:“夫六经定而异端绝,传注出而圣学明。……按经者,常也,恒久而不已,终古而不变,谓之曰常。故圣人之言曰微言,传记所述曰大义。微者至微无不入也,大者至大无不包也。原其体类,皆号为经。……盖道德统纪、治乱条贯,六艺之本也。门户别立,师传互异,又其枝流也。”[1]6这基本上是对《汉书·艺文志》说的“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题中之义的发挥。是从圣与贤、经与传、本与流来区分微言大义,以圣人之言、六经、本源为微言,以贤人所述、传注、支流为大义。这一微言大义说,既强调二者的区别,微言带有根本性,微言先于大义,又强调二者的一致性,认为都是圣人之道的体现。
在后来的《汉学今文古文考》,宋翔凤又提出了新的微言大义说:
微言者即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易》《春秋》皆具性与天道之原,利与命与仁之理备于二经。《论语》二十篇多言《易》《春秋》之微而未尝显,故《论语说》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大义即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如《诗》《书》《礼》《乐》是也。故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此夫子所正言以告弟子,当时并口授其大义。所谓微言大义并汉世博士所传。[1]9
这是从六经与内容来区分微言与大义。就经典而论,微言为《易》《春秋》《论语》,大义为《诗》《书》《礼》《乐》;就内容论,微言即不可得闻的性与天道,大义即可得而闻的文章。从宋翔凤特别强调《论语》多微言,并与《春秋》相发明来看,这一微言大义说与《论语说义》的基本思想相一致,是宋翔凤言孔子素王说的微言的理论依据。
宋翔凤虽然以《易》与《春秋》为孔子言微言的经典,但是,他又认为孔子经学的微言备于《论语》所谓“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备于《论语》”[2]1985上。所以,探求孔子的微言,最应该重视的是《论语》一书。他认为,《论语》各篇都是发挥孔子微言的作品。在孔子微言的论说上,刘逢禄以微言集中见于公羊,《论语》只是公羊微言的发挥,可以说是重公羊,而宋翔凤则是重《论语》,二人对经典的重视是各不相同的。
《论语说义》以性与天道、文章分梳微言与大义,故《论语》中凡是有性与天道的语言,都被宋翔风作为论说孔子微言的证据。并据孔子“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以“不可得而闻”确定为孔子微言的标记,而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予欲无言”也异议附会为孔子的微言。这一用“罕言”“不可得而闻”“无言”之类,来证成所谓孔子微言,完全是一种文字的附会。而附会就必然出现矛盾。借用牵强附会的手法,以论说性与天道为孔子微言,是《论语说义》的主要内容。关于性与天道的发明,我在《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第三章第三节已有详细的论说。而从宋翔凤发明的孔子微言中,他言性与天道,并不是对人性与天道的学术研究,也不是对道德伦理问题的讨论,而是着眼于政治,是希图从孔子的微言中寻求所谓百世不易的根本大法。
二、宋翔凤发明微言的核心
宋翔凤在《论语说义》发明的经学微言,除了性与天道,还沿袭刘逢禄以公羊学的三科九旨说《论语》,来发明经学微言。他说:“《春秋》之作,备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轻重详略,远近亲疏,人事洽,王道备,拨乱反正,功成于麟,天下太平。”[2]1987上在这些微言大义中,宋翔凤论说最多的就是公羊学的张三世、异内外等内容。宋翔凤的这些论说,基本上是对公羊学的重申,但也有自己的特色。
譬如论公羊学的张三世,宋翔凤除了承袭已有之说,还与人君之道联系在一起为说。如他说:“求张三世之法,于所传闻世,见治起衰乱,录内略外;于所见世,见治升平,内诸夏,外夷狄;于所见世,见治太平,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此仁之能近取譬,故曰为人君至于仁,此南面之道,中庸之至也。”[2]1998上而他论张三世最有价值的是特别强调了新陈代谢之义:
《春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月,有星孛于东方”。公羊说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说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谓文公继所传闻之世,当见所以治衰乱,昭公继所闻之世,当见所以治升平,哀公终所见世,当见所以治太平者,于此之时,天必示以除旧布新之象,而后知《春秋》张三世之法。圣人所为本天意以从事也。[2]2009中
他强调《春秋》的张三世之法,本于天象的除旧布新,而除旧布新也就是新陈代谢,这一突出新陈代谢的意义,是宋翔凤的张三世说最具价值的所在。将此运用到历史的发展中,就是主张新社会、新制度取代旧社会、旧制度,这显然是一种具有改革意义的理论。只不过宋翔凤没有明确表达出来而已。
异内外是公羊学微言的另一重要内容,一般谈公羊学者都忽略了如何由内及外的问题,宋翔凤言的《论语说义》则特别重视这一方面的发挥。他说: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合,无莫也,义之与比。”谨案:此章明君子之义内也,董子曰:“《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积毫毛之善,绝纤芥之恶是之谓密,《春秋》治起衰乱,则内中国而外诸夏,亦始于以义治我,故义先于治我,则仁达于天下,……(董子)又曰:“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闲,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逆顺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按:董子言《春秋》之法治衰乱而立太平,故分仁义为外治内治,其实仁义皆具。于性,用之以治则为法,仁义之法有外内,仁义之性无外内也,《论语》言治人之道,故反复言仁,而仁必合乎义,犹治人者必始于治己,如仁者安仁,则生知之圣已不待治,如知者利仁,利以和义,始于以义治我而后以仁治人,是之谓利仁,仁义之相因为法,五行之相代为用,合之于天命之性,分之于人己之治也。[2]1994上
这段话主要采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第二十九篇《仁义法》之说,强调了公羊学的异内外与仁义的关系,肯定了异内外是依靠道德的作用,通过人君自身的道德修养,由我及人,由鲁国而诸夏、由诸夏而四夷,即由小到大的空间扩张,来实现天下太平,这是对何休《公羊解诂》的以人君的道德楷模作用的扩充来实现天下太平的思想的发展。而宋翔凤把仁义分为仁义之法与仁义之性的论说,更是对董仲舒仁义学说的改造与深化。
对公羊学的“通三统”、文质递变说等,宋翔凤也有所论及,但主要是沿袭其说。在论宋翔凤的经学时,人们常常依据宋翔凤的上述论说,来判定宋翔凤的经学是对公羊今文经学的发挥,认定是刘逢禄经学的继续。这有一定道理,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宋翔凤的经学虽采公羊学之说,但是,他并没有像刘逢禄那样以发挥三科九旨为宗。而且,他谈到公羊学某些观念时,与公羊学的传统说法也有所不同,如论“王鲁”说,他不取假鲁国君为王的论说,而是以思周公为说:“《春秋》托王于鲁,以天下之思周公也。”而且,宋翔凤即使是在论公羊学的观念时,也有取古文经学为说的情况,如取《左传》之说以论张三世的除旧布新之义。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从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等说去过分强调宋翔凤的经学与公羊学的联系,也应该看到其不同与差异。
可以说,公羊学的三科九旨尽管是《论语说义》的重要内容,但绝非宋翔凤所言经学微言的核心。在《论语说义》中最具时代意义的东西,是他的孔子素王说。他在《论语说义序》中说:“《论语说》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微言者,性与天道之言也。此二十篇,寻其条理,求其指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备焉。”我在《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中,早已经提出这一观点。
但有人提出异议说:“笔者不同意黄开国教授讲:‘尽管宋翔凤在这里将孔子素王说与性与天道都等同于微言,但是两者的含义是不同的,只有孔子素王说才是《论语说义》微言的根本所在’的观点。”[3]38该文在引用宋翔凤对《论语·宪问》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的注语之后分析说:
宋翔凤认为:孔子之所以为“素王”的真正原因在于:“尧、舜与天合德,孔子亦与天合德。”“与天德合”即“性与天道”,尧、舜、孔子都是性合天道的王者(只是孔子无位而已)。另一方面,孔子作《春秋》,立《春秋》制的原因也只是“治太平以上应天命,斯为下学人事,上知天命也。”《春秋》制只是孔子领悟并践行“性与天道”后德参天地的产物。可以这样说,“性与天道”不仅是孔子成为“素王”的根本原因,也是孔子立《春秋》根本原因[3]38。
并由此得出其结论:
由是观之,无论是“三科九旨”,还是孔子“素王”说,宋翔凤均以“性与天道”贯穿之,“性与天道”是宋翔凤贯穿其整个公羊学的核心[3]39。
这里犯了一个偷换概念的错误。宋翔凤的“性与天道”是指孔子微言,与孔子文章的大义相对而言,而不是讲的尧、舜、孔子的德行合于天的问题,所以,说“与天德合”即“性与天道”,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孔子之为素王,可以说是与天合德所致,孔子立《春秋》也与之有必然联系,但却不能说孔子的性与天道的微言,才使之成为素王。相反,是因孔子为素王,才能够有性与天道的微言。无论是公羊学的三科九旨之说,还是宋翔凤强调的性与天道,都可以而且只能用孔子素王说来统宗,因为它们都是孔子素王之道的体现。《论语说义》说明经学微言的核心是孔子素王说,而非三科九旨,更非性与天道。
三、孔子素王说的发明
宋翔凤在《论语说义》所发明的孔子素王说,以孔子是受命于天之王为出发点。
《论语说义》在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时说:
天命者所受之命也。德有大小则命有尊卑,大夫命于诸候,诸候命于天子,天子受命胥此命也,孔子知将受素王之命,而托于学《易》,故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盖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穷理尽性、知天命有始终,大过者,颐不动,死象也,孔子应素王之运,百世不绝,故可以无大过。[2]1995下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出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根据董仲舒的理论,宋翔凤以孔子为最高德行之人,但又因孔子无帝王之位,故只能受命为素王。宋翔凤的所谓素王,一是指孔子受命于天,一是指有天子之德而无其位。并将孔子自许五十知天命,学《易》,无大过,作为孔子为素王的证据。
以此既定观念,宋翔凤发现《论语》中有许多孔子素王说的证据,这些证据不仅出自孔子本人,也见于孔子的弟子,甚至是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无不承认孔子为素王。如,他说《论语》中的孔子“自谓窃取之”“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等说法,皆为孔子自知素王的自道。他说:“故孔子为素王,七十子皆奔走疏附,先后御侮。”[2]1997下七十子之所以先后奔走于孔子门下,也是出于对孔子为素王的认知。他还借达巷党人之言,仪封人告二三子之说,来论证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对孔子素王说的认可。总之,在宋翔凤看来,孔子为受命于天的素王在春秋时期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为此,一切否定孔子受命于天的说法,都受到他的严厉批评。
通过孔子受命于天的论证,宋翔凤对孔子素王的身份作出了公羊学的说明。同时,他通过孔子著《春秋》,进一步论证了孔子素王说。但他在这方面的论证,与以前的春秋公羊学有着某些差异。这就是,春秋公羊学讲孔子著《春秋》,直接以孔子改制或素王改制说来言说,而宋翔凤则绝无改制一说。
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中说,唯天子受命于天,王者必改制,认为天子通过改制体现其受命于天。孔子虽然受命于天,但只是有德无位的素王,不能在实际政治中改制,而只能通过作《春秋》来实现。这一理论被称之为孔子改制说或素王改制说。但改制一词,容易引起改朝换代的猜忌,所以,汉代以后公羊学的孔子改制说或素王改制说几乎无人提及,即使是以公羊学为宗的刘逢禄,也没有明确的孔子素王说,更没有孔子改制、素王改制之说。清代严酷的文字狱到龚自珍时还使许多知识分子心有余悸,以至于龚自珍还在《咏史》的诗句中哀叹:“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宋翔凤则更带有对言“改制”的忌讳,虽然他已经以孔子素王说统宗经学微言,但还不敢明确说孔子著《春秋》就是孔子改制或素王改制,而只是将改制称之为制作。如他说:
孔子生于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四年,适七十,故《春秋说》云:“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得瑞门之命,作《春秋》,适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类书,九月,经立。”按《春秋》之作,备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轻重详略、远近亲疏,人事浃、王道备,拨乱反正,功成于麟,天下太平,故曰:从心所欲不逾矩。矩者,数也。……《大学》絜矩之道,《春秋》之致太平,追尧舜之隆者,唯不逾矩而已矣。[2]1987上
《春秋》之作,备阙疑、阙殆之义,应天制作,号令百世,仪封人知之,故以何患于丧告二三子,素王、素臣昭然可知,当时圣贤作述之意,唯求寡尤、寡悔而己[2]1987中。
孔子成《春秋》,以当素王[2]2003中。
孔子著《春秋》是受天命,应天制作,故有西狩获麟、瑞门之命的瑞祥。孔子素王,即以《春秋》号令百世。这些大都是春秋公羊学已有之说,但春秋公羊学是以孔子改制或素王改制来统宗,宋翔凤则只说是孔子受命制作的体现。尽管宋翔凤不敢直言“改制”,但由孔子素王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公羊学的孔子改制说或素王改制说。
在春秋公羊学中,孔子素王说是公羊学全部微言的根据,有了孔子素王说,孔子才有改制的资格,有孔子改制,才有三科九旨的微言及其笔法;没有孔子素王说,三科九旨、性与天道等微言,及其可得而闻的大义,就无统辖、无根据。刘逢禄说无三科九旨就无公羊,更进一步就应该说无孔子素王说就无三科九旨。所以,宋翔凤论《春秋》微言虽远远不及刘逢禄,但是,却具有刘逢禄所不及的深刻意义。宋翔凤的经学与公羊学的联系,主要在于孔子素王说,而不在三科之说。
宋翔凤在《论语说义》中虽然也没有孔子改制、素王改制的明确用语,但是,他是清代经学史上第一个大讲特讲孔子素王、素王制作的人,而且以孔子素王说作为他论说经学微言的根核。正是有了宋翔凤的突出孔子素王说,人们才有可能利用孔子的偶像形象,依托孔子制作《春秋》,来建立起自己所需要的理论。而且,由大谈孔子素王说以论制作《春秋》,到了合适的时机,就很容易直接引发到孔子改制说、素王改制说。而在历史急剧变动的时期,孔子改制说往往成为人们附会新理论的形式,这在晚清的廖平、康有为的经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清代今文经学发展中宋翔凤突出孔子素王说,其意义并不亚于刘逢禄的建立起以公羊学为中心的今文经学体系,这也是清代今文经学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过渡中宋翔凤的理论贡献。
参考文献:
[1] 宋翔凤.朴学斋文录[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 宋翔凤.论语说义[M ]//阮元,王先谦.清经解·续清经解:第十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3] 王光辉.宋翔凤《公羊》学新探——以《论语说义》为中心[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2012.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Song Xiangfeng’s Studies of the Theory of Confucius as an Uncrowned King
HUANG Kaiguo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ies of Confucius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00, China)
Abstract: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from loyally retelling to creatively saying somethign more in the Qing Dynasty, Song Xiangfeng was the first scholar of the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who made a clear distinction of the sublime words with deep meaning. Different from Liu Fenglu’s view of “there are nine meanings in three paragraphs in Confucian classics”, he took the theory of Confucius as an uncrowned king as the core of the sublime word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t is said that the core of Song Xiangfeng’s views of the sublime word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s nature and providence, which is not correct. It is Song Xiangfeng’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theory of Confucius as an uncrowned king that directly started Liao Ping’s and Kang Youwei’s studies of Confucius’s reform theory.
Key words:Song Xiangfeng; the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sublime words; Confucius; theory of an uncrowned king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6)03-0019-05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6.03.004
收稿日期:2016-0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3BZX046)
作者简介:黄开国(1952-),男,四川大英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