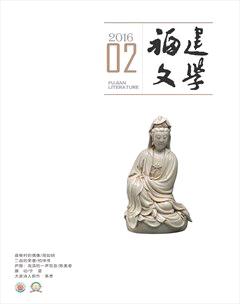健民短语
◎杨健民
健民短语
◎杨健民

杨健民,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首届“福建省文化名家”称号。著有《艺术感觉论》《中国古代梦文化史》《论茅盾早期文学思想》《批评的批评》等。曾数次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省文学奖。
斗茶
斗茶是男人的本事,女性一般不斗茶。见过几次斗茶,基本上是男人。
斗茶的玩法就是对比,有对比才有区别,才能斗出个胜负。然而,斗茶是按照同一茶叶种类来斗的,岩茶不跟铁观音斗,红茶不跟绿茶斗。见过几次斗铁观音,清香型、浓香型和陈香型各自上阵。
某日下午,几位好饮者想起来斗岩茶,有陈年铁罗汉,乾隆老茶,五星和六星曦瓜版大红袍,牛栏坑肉桂(简称牛肉),还有老枞水仙等。岩茶种类多,比较丰富多彩,斗得也就有趣味,也算长了一些见识。岩茶底蕴深厚,饱满沉着,有一种被称为“岩韵”的意味在其中。岩茶一直是我近年来的最爱,无论是它们中的哪一种,只要你抿上一口,咂出味来,便完全没有那种草本的微涩,只觉得岩韵里空间幽深,曲巷繁密,忽然就有了一种徜徉、探寻的余地。那个下午,数巡过后,一泡号称乾隆老茶被撕开了,一团黑糊糊的茶块被抖了出来,放到鼻子底下闻一闻,没有什么香气。泡在茶盅里,有浅棕色渐渐漾出,随后很快便荡出了深黄色。凑上闻香杯一闻,整个像是普洱的味道,还有些药香;喝上一小口,竟然是木头的香味;等过了喉头,便有一种岩韵慢慢释出了。几通过去,口感逐渐细腻,越喝越甜,然而不腻。老茶在腹中蠕动,胸间顿时通畅,舌下生津。这是什么老茶呀?一看茶盏里的茶渣,都已碳化碎裂,没有了那种粗枝大叶的形状。如此陈酽、透润的老茶,大家还是第一次品到的,于是欣喜莫名,惊呼这才是今天斗茶的“终极版”。收藏者说,其实它不过是1950年代的佛手。佛手不是铁观音吗?怎么也拿来跟岩茶斗呢?待喝够一大把了,众人才醒悟,即便是几十年前的什么茶,到这个时候骨子里的那种“老”的味道,释放出来的一定就是三分甘草、三分沉香、二分药香、二分草野霸气。这就是老茶的“茶格”。
斗茶到如此境地,就不知如何来安顿自己的感觉了。过去的文人常以“好茶至淡”、“真茶无味”等句子来形容好茶,其实这是一种感觉的失落。不管怎么说,老茶是有“大味”的。有人说,老茶是老男人的茶。也许,只有男人、特别是老男人才真正知道老茶的韵味。老茶的深厚,没有了绿茶的鲜活清芬,却把香气藏在里面,让喝的人觉得年岁陡长。在陈酽、透润的基调下,老茶变幻无穷,从药香、木香、虫味进入到普洱味,最后是甘甜,每一种重要的变换,都带来新的的感觉和记忆,就像一个老男人一生的历程。
静气
弟子从漳州寄来几粒雕刻好的水仙,我把它养在水里。可能是干燥了几天的缘故,一入水,它们竟然发出嗤嗤的声响。我好奇地盯着水在冒出一圈一圈的细泡,觉得有些神秘。
这些水养的仙子,它们凌波的姿势总不会是凝固的。水仙需要水,其实更需要的是静气。数年前,我办公室里的一盆水仙,在开放二十多天后突然倒伏了。倒伏的原因并不在其自身,而是一位好心的女同事发现水有些浑了,把它端到水龙头下从头到脚冲洗了一遍。结果摇摇欲坠的花朵经不起折腾,全垂下高贵的头颅。同事很内疚,我也有点沮丧。贾平凹说过:女人不说话就成了花,花一说话就成了女人。水仙本无语,只是静静地、默默地开放着,直到慢慢变老。有些美是不能惊动的,你一旦惊动了它,它就倒了。水仙是淡雅而宁静的,无语的花是下自成蹊的静美,但是它一开口便成了女人,这时还会有静美吗?由此,我才感觉到贾平凹那句话的真正分量。
又是一年春来到,又将是一年一岁。变老是必然的,有些离开,是可以顺其自然的,就像我们告别了过去的一年。所谓告别,不过是目光的一次出走,一切都可以静止在生命走过来的甬道上。还记得那一杯喝得很慢很慢的玫瑰花茶吗?坐在时光的风中,往事被一滴滴稀释,烦事也一片片凋零。这个时候你还会想到什么呢?俄罗斯象征主义诗人勃留索夫有句诗:“他爱所有的大海,所有的码头,从无半点偏心。”我们也许不能做到巴赫无伴奏合唱曲那样的纯粹,但这句诗总是让我感动。李白当年游峨眉山时,曾在山上的万年寺毗卢殿听广浚和尚弹琴,下山后他写了首《听蜀僧浚弹琴》,其中有句:“客心洗流水,余响如霜钟。”说的是人要有“洗流水”那样的静气,有了静气就会有“如霜钟”般的力量。
斯人往矣,境界犹在;静气若兰,力量在心。人生中总需要有生命的温度,就像水仙需要水,也需要一定的温度。然而人也和水仙一样,更需要一种平和与静气,才会自如地开放,直到自如地结束。
思想的颗粒
多年前写过一篇《阅读咖啡》,把咖啡读成“思想的一种颗粒”。在我看来,苦与涩是咖啡的本质世界,然而咖啡真正的浓香又是从这苦涩中溢发出来的。我一直觉得,品味咖啡需要感觉和心境,需要有一种提纯生活本质的能力。
2011年冬天,我第二次去法国,在巴黎呆了有十多天时间。巴黎有一万两千多家咖啡馆,每年能喝掉18万吨咖啡。巴黎人每天上班前都会先饮一杯咖啡,那样就可以照亮他们一整天的时光。善于思辨并且崇尚理性精神和批判意识的法国人,他们那些庄严的思想多数是在咖啡馆里催生出来的。我读过科塞的《理念人》,这本书描绘了18世纪那一群被咖啡所点染的新人类——“理念人”。他们“几杯咖啡下肚,新鲜刺激、大胆妄为的言论便从嘴边蹦到桌上,又从桌上蹿到地上,随即便兴奋地跳起舞来”。18世纪的咖啡馆就被这群“理念人”称为一个思想表达的场所,它们以静谧与沉思闻名。卢梭、孟德斯鸠一直是咖啡馆的常客,伏尔泰在咖啡馆里一次可以喝下40杯咖啡,蒙田的“我怀疑”,笛卡尔的“我知道”,帕斯卡尔的“我相信”等,就连近年来很火爆的阿伦特,都是在咖啡馆里“研磨”出他们的思想颗粒。巴黎左岸咖啡馆里的“花神”菜单上,有的还印上萨特的那句话:“自由之路经由花神咖啡……”巴黎毕竟是巴黎,仅咖啡馆就可以按照哲学、诗歌、戏剧、电影、音乐甚至天文来划分主题,其中自然以哲学为盛。无怪乎徐志摩当年会说:“如果巴黎少了咖啡馆,恐怕会变得一无可爱。”
回到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茶馆、酒吧、咖啡馆说多也不多,我去过的就更少了。一段时间以来,我在一家叫做“在咖啡”的咖啡馆里虚掷了几次光阴,那里有书读,有人聊天,盯着眼前那杯被瓦解的深褐色的颗粒,觉得它似乎就溶化在我的感觉里,于是舌底开始波俏,开始澜翻,目光炯炯,并且已经被撩拨出一种想写点什么的冲动了。“在咖啡”是一座精神的渊薮,是一个同样带有“煤烟”般苦涩香味的咖啡的名字,当然,我更喜欢的还是那里时不时踅进去一群诗人,他们纷纷把诗句抵押在那里,然后孵化。从秋天喝到春天,又从冬天喝到夏天,他们谈海子,谈顾城,谈舒婷,谈余秀华,谈诗歌的时间的羽翼,以及诗的去向与归途……这个春天,那个写过《春天,十个海子》的海子,一个都没有复活,但是他身后的那些诗复活了,那些饱胀的诗的生命一句一句被搅活,被沉浮在“在咖啡”的咖啡里,就像海子笔下的《亚洲铜》那样,藏匿着一个诗的燃灯人的痕迹。“在咖啡”,其实就是诗人的一个存在,一个诗意地栖居的场所。我还会来这里,在那种深褐色的浮沉中,寻找我的追问和语言,寻找属于我的“思想的颗粒”。当然,我还会继续寻找或追究咖啡最初的和最后的故事。
小巷的历史和哲学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谁没有低吟过戴望舒这首荡气回肠的《雨巷》?那位“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哪里去了?这种煎熬的旋律显然不只是一个关于寻找的话题。我常常在小巷里一边蝺蝺穿行,一边在问自己:你在寻找什么?其实,我并不寻找什么,我只是徜徉,只是等待着城市人时常会目击到的那一场遭遇。
2007年夏季的一天,我游走在布拉格著名的黄金小巷里,找到一座水蓝色的房子。一百多年前,一个英俊而又忧郁的小伙子不堪忍受旧城区的嘈杂,搬进了这座房子。他就是法兰兹·卡夫卡。在这条童话般的小巷里,卡夫卡逃离了现实,躲进自己的世界,写出了著名的《城堡》。他孤独、漂泊、恐惧、焦虑,这一切都写进了他的字里行间。布拉格是个绝美而神秘的城市,有着众多的小巷,在这里你随时可以看到卡夫卡的脚印和昆德拉笔下的特蕾莎的背影。尽管卡夫卡说,布拉格就是“我的狱所,我的城堡”,尽管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丑陋和绝望,但是只要在这条黄金小巷里走过,我都相信卡夫卡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美丽、寻找希望的。布拉格的神秘在于它充满童话般的灿烂,灿烂到人们很容易就忽略它的过去,以至于尼采发出如此的赞叹:“当我想以另一个字来表达音乐时,我只找到了维也纳;而当我想以另一个字来表达神秘时,我只想到了布拉格。它寂寞而又扰人的美,正如彗星、火苗、蛇信,又如光蕴般传达了永恒的幻灭之美。”如此绝美的城市,让我觉得它离卡夫卡小说中所描绘的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境遇竟然是如此之远。
在黄金小巷里巡游的那个下午,我没有迷失。我在读这一条小巷的历史和哲学。历史是持久而又断续的,哲学是透明而又混沌的。那几天布拉格遭遇到几十年来最干热的天气,在四十余度的高温下我挥着汗雨打量着这里的深街老巷。风嘶哑了,像玻璃杯中的水,归于沉静。那么,什么是不沉静呢?只有迷离,只有恍惚,只有那些难以承载的心理重量。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福州的三坊七巷。其实,福州原来就是淹没在小巷之中的。小巷多少年来一直无声地聆听着城市的呼吸,而现在一个喧嚣的城市就要将它无声地抹去。我似乎听到了小巷的如泣如诉,宛如天鹅的绝唱。然而,小巷依然达观依然淡泊。谁听过小巷一丝一缕的抱怨呢?不能想象小巷从这座城市撤走,丧失了小巷的缠绵和曲折,福州一定会失去许多的情韵。悠悠的小巷使得这座城市有了一种古老和沧桑,从而再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应地切除了一些小巷。幸好,城内的那些小巷还被保留着。如果不是这些熟悉的小巷为我留下相应的记忆,我真要怀疑我脚下站着的,还是这座城市吗?
诗歌的尖峰时刻
谢冕评论福建的四位女诗人冰心、林徽因、郑敏和舒婷,末了引用了林徽因的诗句:“菩提树下清荫则是去年”,有其深意。我一直琢磨着这一句诗,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寂寞而伟大”,这注定是中国现代诗歌史的一种面相。
余英时曾经说过,胡适生逢其时,“在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有一段空白而恰好被他填上了”。我时常在中国文化究竟哪一段是属于轴心时代这个问题上犯困。这个问题太大了,我的确说不清楚。我想到的只能是这样一个词:“尖峰时刻”。这个词现在多用来比喻上下班的车水马龙,我或许可以用它来比喻现在的诗坛。诗的“尖峰时刻”来临了么?当代诗坛似乎就是一场变形记,词语的尸骨和感性的妖魅正在不断地撕裂诗歌的文本,甚至我们都来不及躲避它那闪电一般的炫目。
我读诗,也读诗人,却总是无法忍受诗人生命的脆弱。在海子离世了二十五年之后,一位原本比他还要年长的诗人,怀着中年的荒寒与悲凉,在彻悟中飞跃向黑暗的一刻。他就是陈超。他在当代诗歌的“尖峰时刻”远离了诗,远离了诗歌的精神现象学,从而成为了一个敏感而无解的话题。再一次捧读陈超的《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我突然意识到他的修辞是那样精准和完美,如同他的那些刀锋般精准的诗学评论。“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四月的歌手,血液如此浅淡。/但桃花的骨骸比泥沙高一些,/它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古老东方的隐喻。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只要读一读这几句,大概就可以看出生命中那种血的悲怆,正绽放在时光与历史的黑暗与恍惚之中。陈超以他的诗句,宿命般验证了不可躲避的悲剧意味,以及谶语一样不可思议的先验性。
诗歌其实是很残酷的语言游戏,它可以残酷地让情感的伤口在闪电中飞翔,然后纵身下落;它可以在风和日丽的林间小溪狠狠剜下一刀,然后冻结隐喻;它还可以让深秋退回阳春,让泥土跃上枝头,完成生命的一次轮回。我始终敬畏诗歌,敬畏诗人,敬畏诗是如何听从死亡与黑暗、创痛与伤悼的魔一般的吸力。但无论如何,诗还是诗,它不会失忆,不会以一块简单的灵魂拼图的七巧板形式锁住诗人的想象力。菩提树下的清荫尽管已经成为了去年,成为了昨天,却依然是诗人精神历险的完成式。“尖峰时刻”——我们这个时代诗歌的精神肖像,既有从前诗人的热爱,也有当代诗人的欢愉。我们只要凭着一些词语,就可以将诗与生活的手握紧。
乡愁
“乡愁”一词,颇具意味但是不容易触碰,因为它深含着生命的许多内容。忍不住寻思下来,发现诗人是最“乡愁”的。郑愁予的乡愁:“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余光中那一枚“小小的邮票”,几乎成了“乡愁”的代名词。而作为小说家的阿城则在《威尼斯日记》里这样写道:“所谓思乡,我观察了,基本是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开始闹情绪。”阿城从亚利桑纳州开车回洛杉矶,路上带了一袋四川榨菜,嚼过一根,家乡的“味道就回来了”。把榨菜腌成了故乡,情感就变成一种荣耀。每一次出国,都有朋友提示多带些榨菜,身在异地,只要榨菜在,那种熟悉的家园的味道就在。所以说,故乡不是别的什么,故乡就是一种味道、记忆和感觉。
莫迪亚诺的小说《夜巡》里有一句对于巴黎的描述,一直触动着我:“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而脂粉满面的情妇。”思乡的情结无论多么坚韧,都是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小时候生活在乡下,一到夏日傍晚,坐在溪边那一丛石崖上,给小伙伴们讲“三侠五义”,讲“水浒”,始于一个故事的谜,结束于另一个谜,总是有一群热切的期待和守候。所有的未知和未明,不断地被更广阔的消逝和疑问所笼罩。离开故乡近四十年了,我时时在拣回那些无法忘却的记忆的碎片。那是属于我的“达达的马蹄”,是属于我的“美丽的错误”。
有时候想,面对故乡,我可能就是一只迷离的鹿,但在我的文字感觉里,我觉得又有一只鹰以及无尽的夜色在盘旋着。家乡对我一直是一种延宕,一种闪烁,无论追忆还是探寻,我都感到人与自然、人与历史正在发生一种巨大的断裂。我曾经为家乡那条变黑的溪流写过一首悼念的诗,那一丛石崖哪里去了?那些游动的鱼哪里去了?这还是我的“美丽的错误”吗?它最终成了我的忧伤和我的痛苦。人到中年,真的只是开始“关怀自身”了吗?我不断地跟家乡的土地和草木邂逅,追寻它们的漫漶和斑驳。其实,就像莫迪亚诺在他的另一部小说《暗店街》里所说的,我们都是“海滩人”,“沙子把我们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
然而,我们所有的思乡说白了,就是追溯那些脚印。那么,“乡愁”中的历史会重演吗?或者说,有多少“乡愁”可以重来吗?这就是我的一点可怜的想象。我想起马克·吐温说过的一句话:“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也许,这就够了。
回望小柳村
小柳村拆了,又有一条街巷被切除了。说不清在这里的多少个曾经:曾经骑着自行车载着女儿去附近的幼儿园时路过这里,曾经去省画院找画家谋哥聊天时蝺蝺独行过这里,曾经在夜晚散步时抄近路斜插过这里……曾经,曾经其实就是路过,无论在脚下还是在心里。
此时,我突然就闻到昔日的某种气息,令我不由得有点心悸地打量了它一下。这里的一家理发店终于搬走了,不知搬到何处。从八十年代初起,我数不清在这家理发店踯躅过多少时光。不能说对这里没有感情,街巷的历史顷刻就要擦肩而过,早晨的风不会再让人感受到它的更多的内容。2000年时搬进更靠近它的一座楼居住,从楼上一眼望去,无规则的错落而显得杂乱的民房,从早到晚市声攘攘,不时在深夜会传来一声摔杯子的脆响,或是一两声奇怪的尖叫,时而还有犬吠和母猫叫春的哀嚎。
滚滚红尘,风吹云散,我相信这一带的深巷是有记忆的。这个记忆让我在这座城市的这条街巷迂回了三十多年,它的每一处轮廓都深刻着一种属于它们的乡愁。的确,不需要太多的历史事件的陈述,我都能触摸到它的某些有意思的局部。比如,我妹妹曾经在这里租住了几个月时间,每一次我去探望她,都会感觉到留存在这里的一些时间的空隙和事件的悬疑。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什么神秘地带,而是让人觉得可能存在着某些晦暗不明的东西,如同这个并不古老的街巷,在今天的最后一次负痛的挣扎。
我移居闽江边也将近十年了,那里的深夜常常安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于是有时就会回忆并怀念起小柳村的喧闹。如今,这里的一切正在一步步地隐退,它几乎连躯壳都不会留下。至于这里将会矗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期待,坦率地说,我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不是因为我已经移居别处,也不是因为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而是缘于对这座城中村的历史乃至一条街巷的记忆和气息的追溯和回望。甚至,我会无端地在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幕:某日阳光灼热,一位高龄老婆婆佝偻着身子,坐在巷口的一张歪斜的石凳子上,呆望着匆匆来去的行人。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某些黑黝黝的乡愁的节点抑或断点,密集地在我脑海里浮现。推土机正在亢奋地来回穿梭着,我看着它,看着这里的每一个暗角,想着我的这些小感慨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还是决定动手写下这则短语,记录下这个夏天的这些炽热的动静。
责任编辑林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