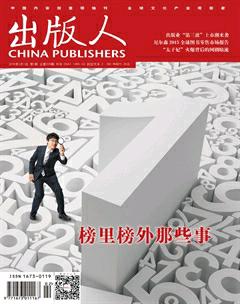迟子建:文学创作没有“群山之巅”
周丹

2015年,《群山之巅》为迟子建和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斩获各类奖项十余个。《群山之巅》是迟子建的第七部长篇小说,而这一年她迈入天命之年,从事写作也满了三十个年头。
“当初,我们都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就读,迟子建是我们的小师妹,年龄虽小,人很高傲。今年她50岁了,有差不多30年时间在写作,成果累累,就好像一个人在垒一座高山,现在已经到了‘群山之巅了。”作家莫言在不久前举行的“极地的出发与远行——迟子建创作三十年研讨会”上,对于迟子建和她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获评“2015书业年度评选·年度作者”,迟子建却低调说:“作品的名字可以叫《群山之巅》,(但)文学创作永远没有群山之巅。” 她一直安静地走在自己的创作路上,作品沾染了岁月的痕迹,而她依旧初心未改。
收割过的麦田里,又拾到几株麦穗
《群山之巅》是迟子建的转折之作,小说描绘的依然是黑土地上的现实风景画卷,却超越了以往的温婉柔情,写出了一部“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与赎的灵魂独白”。书中,一个个卑微却有梦想的小人物努力活出人的尊严,觅寻爱的幽暗之火。
有评论家说,2015年是文学小年。但《群山之巅》让中国的严肃文学在过去的一年中并不荒芜。对于在文学园地耕耘了30多年的迟子建来说,“不管小年大年,都是平常日子”。她谦虚地说:“《群山之巅》所获得的奖项,不过是一个农人,在收割过的麦田里,又拾到了几株麦穗,不足以果腹,但能给一个农人以喜悦,照耀一个写作者的生活”。
《群山之巅》再次把迟子建带到了聚光灯下,但她仍在坚持着自己相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她不用微信,给《出版人》录制的视频是由侄子帮忙的,视频里,并不常在媒体上曝光的她显得有些羞涩。
30年前,迟子建并没有立志要当作家,只是因为喜欢,开始抒写内心的情怀。30年间她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600多万字作品。“它们只是我写作历程留下的脚印而已”。迟子建称,“我的文学脚印,不管深浅,是泥土里的脚印。未来的写作,我留下的脚印,注定还会是泥土里的脚印”。只是,“以前的脚印里,可能更多浸润着露珠和阳光,而以后的脚印,更多的是霜雪和忧伤的月光”。
迟子建有个习惯,作品发表之后,她都会再读一遍。“我读它是为了给自己找不足。我在很多作品中都能找到不足,所以总是寄希望于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可下一部作品出来后,我读后又发现了不足”。迟子建说很难对自己的创作划分明确的阶段,“因为创作是有延续性的,我所有的变化都是渐变,不是一夜之间的突变。”但迟子建承认她的写作是有变化的,“所有的转折可能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就像一个人的衰老一样,当作品渐渐长了皱纹,你是不知道的。它对现实的关注,对现实的痛,对光中的阴影,你会有切肤之痛,有苍凉感”。迟子建说。
“《群山之巅》只是我50岁的一个阶段性作品”,迟子建寄希望于以后还能写出更好的小说。
时代用卷扬机输送的故事
在2015书业年度评选揭晓典礼上,谈起2015年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时,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提到他的老朋友迟子建,“《群山之巅》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人性的)罪恶、善良交织在一起,读来很受触动。”
有文学评论家称,2015年的长篇小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作品都偏向传统,小说向传统回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注重故事性,并建立起一种特有的“讲述的语调”。其中,迟子建《群山之巅》描绘边地小镇的故事,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小世界里,作者塑造出一系列诡异变形的人物形象,在他们之间,有杀人强奸案、逃亡与追捕、情感抉择、阴谋与揭秘等故事性要素。“这样建构起来的小说,让我们联想起古代的奇书传统”。评论人于文说。
“一个飞速变化着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故事,可以说是用卷扬机输送出来的,量大,新鲜,高频率,持之不休”。迟子建说,她在故乡积累的文学素材,与她见过的“逃兵”和耳闻的“英雄”传说融合,形成了《群山之巅》的主体风貌。
2001年8月下旬,迟子建和爱人下乡,在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庄,他们遇见一位老人。在当年的日记中,迟子建这样记载:“进得一户农家,见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衣衫破烂,家徒四壁,坐在一块木板上,望着他家菜园尽头苍茫的黑龙江水。他对我说他是攻打四平的老战士,负伤时断了三根肋骨,丢了半叶肺,至今肺部还有两片弹片未取出来。他说文革时他挨批斗,揍他的人说,别人打江山都成烈士了,你能活着回来,肯定是个逃兵!老人说到此气得直哆嗦。他说政府每月只给他一百多块的补助,连饭都不够吃,前两年有记者来访,走后也是不了了之。我觉得很悲凉,一个打江山的人,是不该落得如此下场的。我给了他一点钱,他坚决不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说这只是让你买袋米的钱,他这才泪汪汪地收下。”
可是八个月后,爱人在归乡途中遭遇车祸,与迟子建永别。与爱人相关的人和事,在那个冰冷的春天,也就苍凉地定格了。直到几年前,迟子建听说某驻军部队的一名年轻战士,因陪首长的客人,在游玩时溺亡,最终却被宣传成一个救落水百姓的英雄。这个故事,唤醒了迟子建对那位老人的记忆,也唤醒了她沉淀的一些素材。闯入《群山之巅》的人物,很多是有来历的。比如安雪儿,“离我童年生活的小镇不远的一个山村,就有这样一个侏儒。她五六岁孩子般的身高,却有一张成熟的脸,说着大人话,令我们讶异,把她当成了天外来客!”迟子建曾在少年小说《热鸟》中,以她为蓝本,勾勒了一个精灵般的女孩。“也许那时还年轻,我把她写得纤尘不染,有点天使化了”,迟子建说,“生活并不是上帝的诗篇,而是凡人的欢笑和眼泪”,所以在《群山之巅》中,迟子建让她从云端精灵,回归滚滚红尘,弥补了这个遗憾。
迟子建称,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的微妙融合,形成了一个作家的写作世界。“没有生活,缺乏历练,作品就缺乏气韵。而有了气韵,作品就有呼吸了”。但生活不是写作的全部,迟子建认为,一个作家的修养,比如读书的积累,对想象力的有效保持,悲悯之心等,都是可持续写作不可或缺的元素。写作帮迟子建度过了人生的难关,爱人离世后,是这支笔给了她强大的支撑。
写完《群山之巅》,迟子建没有如释重负之感,而是愁肠百结,仍想倾诉。“这种倾诉似乎不是针对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而是因着某种风景,比如滔天的大雪,不离不弃的日月,亘古的河流和山峦。但或许也不是因着风景,而是因着一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所以写到结尾那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迟子建的心是颤抖的。
对于获评2015书业年度评选·年度作者,迟子建表示,“作品的名字可以叫《群山之巅》,(但)创作永远没有群山之巅”。在过去的一年中,迟子建对于同行的新作也有关注,其中有两部作品让她印象深刻,分别是阿来的小说集《蘑菇圈》和余秀华的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这两部书有相似的文学品质:疼痛中的诗意,悲凉中的不屈,非常打动人”。巧合的是,余秀华与她一起分享了“年度作者”的荣誉。迟子建说:“我愿意和同行们继续在创作之路上跋涉,在泥中发现光,也在光中洞悉它折射的阴影”。
迟子建把自己比作一个农人,之前创作的作品带来的所有收成,“都是上一季的事情”,迟子建说,“一个好的农人,会把眼光放在下一季的耕作上”。迈过了2015年,她已经 投身到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