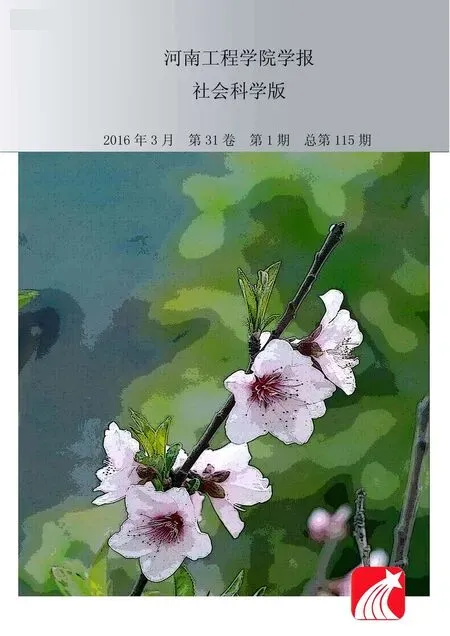从《腓尼基妇女》看欧里庇得斯的道德理想
高云霄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从《腓尼基妇女》看欧里庇得斯的道德理想
高云霄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摘要:欧里庇得斯可以说是一位苏格拉底式的道德家,一位“歌队教师”“剧场里的哲学家”“思想家”,他并非真正的悲剧诗人,而是与苏格拉底精神一起导致悲剧的人。从“僭主”与正义,理性的萌发与神性的沉沦及欧里庇得斯对女性的道德关怀这三个方面可以探讨欧里庇得斯在《腓尼基妇女》中所体现出的关于公平正义的王权统治、公民理性的思考及对女性和其他弱小者的关怀的道德理想。
关键词:欧里庇得斯;《腓尼基妇女》;正义;理性;女性关怀
作为古希腊最后一位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历来备受争议。评论家往往对他大肆抨击,指责他的作品失去了“神性”,并且处处洋溢着现实主义的说教,背离了“狄奥尼索斯精神”,甚至由此导致悲剧。但事实远非如此,就像吉尔伯特·默雷指出的那样:“在希腊,他是一位最有名望的诗人,他的同代人斥他为愚钝,因为他揭人隐私,触怒了他们;他们攻击他,说他居心叵测,因为他要他们理解他们不愿理解的真理;他们又说他亵渎神明和心地不纯,因为他对他们在宗教上精神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他们往往既不能达到这种要求,又不能等闲视之。”[1]267
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芸芸众生通常不是因为忤逆了神的意旨而走向灭亡,而是由于背离了现实的道德准则罹获苦难,《腓尼基妇女》便是一部这样的作品。
一、僭主与正义
僭主(Tyrants)是指通过不正当手段夺取政权的篡权者。僭主一般出身贵族,却通过打击贵族确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僭主虽然是在利用平民阶层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但又实实在在地颁布和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措施。所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这样写道:“僭主所亲近的这些新公民赞美他,而正派人则厌恶他,躲着他。”[2]349在《腓尼基妇女》中,儿子们害怕父亲的诅咒而达成协议:弟弟波吕涅克斯自愿流亡,哥哥埃特奥克勒斯留在国内执掌王权,以一年为期互相轮换。一年期满之后,登上王位的埃特奥克勒斯违背当初的约定拒不交出政权,并且把波吕涅克斯驱逐出境。流亡在外的波吕涅克斯在阿尔戈斯人的帮助下兴兵来伐。波吕涅克斯的行为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并且为自己做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辩解:
我自愿离开祖国一整年,
然后轮流由我来执掌这权利,
免得产生仇恨和流血,彼此
一个为害另一个,像现在这样。
但是他虽然统一了,并对神立了誓,
却不遵守诺言,依旧占有着
王位和我的那份家产。
我请天神来作证: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公正的,
我被剥夺了祖国是违反正义违反天理的。[3]335
但是,他的这番话是很值得推敲的。埃特奥克勒斯作为奥狄浦斯的嫡长子来继承王位是合理合法的。波吕涅克斯作为次子提出“轮流执政一年”的方案本身就很可疑,如果如他所说是为了守护他们兄弟两个的利益,免得其父的诅咒应验,他大可不必要求王权而作为忒拜城一名普通的公民居住下来。多年之后,他带着阿尔戈斯人来攻打自己的祖国,理由是其兄违背了当初的誓言,是“不义”的,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为人弟而向兄长提出“轮流执政”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僭越”行为。由此可见,波吕涅克斯当初自愿离开祖国就是为了一年后回来执政,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僭主”愿望。苏格拉底曾在一些意味深长的言辞中说过有智慧的僭主与有智慧的人为伍。那么,波吕涅克斯是否可能成为一位有智慧的僭主,给城邦带来福祉呢?答案看来也是否定的。在第一场中,虽然“波吕涅克斯回来得很有威势呀!战马如云,兵器无数,叮咚作响”[3]338,但当他独自走进城邦与埃特奥克勒斯议和时,却无一点坦荡荡的英雄气概,反而畏首畏尾,像个猥琐的小人,生怕自己中了兄长的奸计。如果他真的像自己所言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神明也会给他庇佑,而且还有城外阿尔戈斯的军队给他当靠山,那为何还会心生恐惧呢?大概是因为他内心也觉得自己是非正义的一方(虽然他不愿承认),而且敌对势力太过强大,从而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担忧。
那么,作为兄长的埃特奥克勒斯是否就是正义的一方,应得到大家的同情呢?事实也非如此。首先,为人子却把父亲禁闭起来,为人兄长却把弟弟放逐,虽然理由看起来无懈可击,但也是有违道义的。其次,埃特奥克勒斯虽不是僭主,却有着僭主的疯狂。虽然接受母亲的调解,但是决不肯放弃自己的王权,并且对于权力的欲望使他说出了如此反动的话:
王权我决不愿放弃
权利在我手里,别想叫我做他的奴隶
……
如果需要不公正,那么,为了王权
不公正是最善的,但在别的事情上必须敬神。[3]362
他的这番言论亦遭到歌队长的严厉斥责:行为不善的人说得好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不是美,是违反正义。伊奥卡斯特也痛心疾首,责怪埃特奥克勒斯不应该紧跟“爱荣誉”神,这神只会给人类带来毁灭,而应该敬重“平等”,“因为平等是人类天赋的法律”[3]363,并且要求他在“做国王”与“救城邦”之间做出抉择。可是母亲的劝导没能打动一心要“执王杖”的埃特奥克勒斯,战争以两兄弟的死亡而告终。
关于埃特奥克勒斯与波吕涅克斯之死,欧里庇得斯在这里极力向我们传达这样一种观点:他们的死亡不是由于神的诅咒,而是违背了人世间的道德。弟弟觊觎哥哥的王权,而哥哥僭越父权,将弟弟驱逐出境,都违背了“平等与正义”这人世间最伟大的法律,更违背了“善”的道德要求,因此,两兄弟都是有罪的,必然受到惩罚。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两兄弟的悲剧又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于是,我们可以想见:世事纷陈,要用公正和道义来衡量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就是在这种对国家及其一切实施方针抱着不信任的思想中又实实在在寄寓着作者的道德理想。
二、神性的沉沦与理性的萌发
尼采曾说古希腊悲剧“既是酒神的又是日神的艺术作品”[4]3。剧中的主人公都是戴面具的神祇,就是在这种神性与人性的统一中,希腊人进入一种完满的境界。但是到了欧里庇得斯这里,“酒神已被逐出悲剧舞台……借他之口说话的神祇不是酒神,也不是日神,而是一个崭新的灵物,名叫苏格拉底”[4]50。苏格拉底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似乎总不能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纯朴的希腊民众认为他“不敬神”并且“败坏青年”,罗列了一系列罪状将他判处死刑,但是他面带微笑,留下自己的理性王国,从容赴死。在某种程度上,欧里庇得斯——这位“剧场中的哲学家”,的确是苏格拉底的亲密朋友,他在不止一部悲剧中表达了对苏格拉底学说的向往及对神的怀疑的思想。
在《腓尼基妇女》开场歌中伊奥卡斯特对诸神发出“如果你真的智慧,不应该让同一个人永远地遭受不幸”[3]336的疑问。埃特奥克勒斯更是大胆做出不敬神的举动——在与兄弟决斗前,他便对整个城邦下达了不许埋葬波吕涅克斯尸体的训令,并说:如果有什么亲友埋葬了他,必须被处死。死亡者的尸体被埋葬是神定下的律条,凡人自当遵守,就像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违背克瑞昂的法令要埋葬波吕涅克斯的尸体时义正词严指明的:
我不认为你的法令有这么大的效力,
以致一个凡人可以践踏不成文的
永不失效的天条神律。后者的有效期
不限于今天或昨天,而是永恒的,
也没人知道它们是何时出现的。
我不能因为害怕任何凡人的傲慢
去违反这种天条,以致遭到神的惩罚。[5]272
可是在欧里庇得斯这里,安提戈涅却只是辩解说埃特奥克勒斯的命令是错误的且是恶意的,不应该执行:“你进行这惩罚不合法。”[3]432唯一涉及神的理由也只是说:“神又命令:‘不可侮辱死人!’”[3]433完全没有索福克勒斯笔下安提戈涅谈起神祇权威时的义正词严与理直气壮。
欧里庇得斯悲剧中的主人公不仅对神强加给自己的命运感到不公,对神的信念产生动摇,而且在对神的质疑声中处处洋溢着理性的光辉。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奥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历尽苦难的奥狄浦斯说过这样一段话来告诫雅典城邦的乡民:
这世上从未有一个忤神者能逃过神的注意。
神所护佑的你们,请别用忤神的
罪恶,辱没了幸福的雅典城邦。[5]136
奥狄浦斯还劝诫他们要敬神爱神,无论经历怎样的苦难都要对神祇怀抱一颗虔诚与敬畏之心,只有这样才能得神庇护。可是在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妇女》中,同样是盲眼的奥狄浦斯,在诉说自己的罪恶时却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这不幸的人杀了自己的父亲,
上了不幸母亲的婚床,生了
儿子即兄弟,又毁灭了他们,
……
我生性不是如此的缺少理性,
如果没有某位神的插手,我不至于
会施暴于我的眼睛和我的儿子们。[3]429-430
寥寥数语,清晰地刻画出奥狄浦斯对于神祇的怀疑与埋怨,并且表现出他对于人的理性的信心。欧里庇得斯笔下的奥狄浦斯确实是一个充满理性的人物。《腓尼基妇女》退场歌中,奥狄浦斯听到妻儿去世的消息,并没有立刻悲叹自己的苦难,而是理智地向女儿询问他们的死因,而后感叹道:“我的儿子们的祸因是明白的。”[3]427这说明奥狄浦斯理智地认为儿子们的毁灭是出于他们对权力的欲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的,会引起大家的“恐惧与怜悯”之情的只有那种“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忒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的家族的著名人物”[6]38。显然这两兄弟并非属于上述之列,他们遭受厄运只会让人慨叹奥狄浦斯家族的罪恶及卡德摩斯子孙的堕落,却不会对之抱以过多的怜悯。
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一书中说:他(欧里庇得斯)很少坦率地直言不讳对什么表示怀疑;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总是出于道德的原因。对神的权威的质疑,对悲剧主人公理性的发现与肯定,都让他走在时代的前端,去思考,去质疑。所以他敢于公开地违反全希腊人一致相信的传说,将希腊人信奉的神像从神坛驱逐进现实生活中来,他在自己的国度做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思想者,他像一个固执的梦想家——但推动这个世界进步的也一直是这种人。[1]
三、女性关怀
欧里庇得斯最引人瞩目的地方便是对女性题材的深度挖掘,于是他笔下的妇女不再总是柔弱的、谦逊的、忠贞不渝的,而是热烈的、野性的、坚强的甚或是“道德败坏的”,比如敢爱敢恨的美狄亚、为爱痴狂的淮德拉。因为欧里庇得斯总是在戏剧中描绘这些所谓的“坏女人”,于是希腊人简单地认为他仇视妇女。全希腊的妇女联合起来准备在地母节期间惩罚欧里庇得斯,因为“哪里有剧场、悲剧演员和歌队,他就在哪里诽谤我们,管我们叫淫妇、男人迷、酒鬼、叛徒、长舌妇、废物、丈夫的大祸害”[7]101。对此,涅西罗科斯为欧里庇得斯做了完美的辩解——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欧里庇得斯是按照人物原来的样子把他们描绘出来的,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对妇女加以诽谤,而是通过塑造一系列敢爱敢恨、敢于反抗男权社会压迫的妇女形象,寄寓他对妇女的道德关怀。
正如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8]在欧里庇得斯的时代,母系社会被父系社会所取代,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从属于男子的妇女地位逐渐降低,受到的束缚也越来越多。妇女被严密地看管起来,男子却可以自由行动;妇女被要求忠贞不渝,男子却可以花天酒地,可以随时抛弃自己的妻子,而妻子却得不到什么法律保护。如美狄亚所说:
在一切有生命有灵性的生物中
我们女人是最不幸的。
首先,我们必须用重金购买
一个丈夫,而比这更糟的是,
他反而成了我们的主人。
……
丈夫接受婚姻的约束,命运便是
值得羡慕的;否则还不如死了。[3]461-462
妇女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丈夫和家庭,却得不到应得的地位与尊重,过着与奴隶无二的生活,所以才会有欧里庇得斯笔下女权意识萌芽的妇女,或对于丈夫的不忠起身反抗,或努力追求自己的爱情,对爱情矢志不渝。
在《腓尼基妇女》中,欧里庇得斯并没有着重去刻画这种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而是从另一角度来刻画妇女的苦难,并对其寄予深厚的同情。本剧中的伊奥卡斯特不像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那样具有一种肃穆的高贵精神,热爱自己的丈夫,而只是一位平凡的妇人、母亲。在伊奥卡斯特身上我们更多地可以看到人与邪恶的“原罪”的抗争,可以看到女子自古以来的舐犊人性。首先,伊奥卡斯特是一位不屈于命运的坚忍的女性。《腓尼基妇女》开场便是伊奥卡斯特对于神的控诉,指责神对于奥狄浦斯家族过于残忍,不应该让同一个人永远地遭遇不幸。在奥狄浦斯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后,伊奥卡斯特承受着“丈夫又是儿子”的耻辱与痛苦隐忍地生活下来,以自己柔弱的双肩扛起奥狄浦斯家族罪恶的过往与孩子们的未来。可是奥狄浦斯家族的苦难并没有就此结束,多年之后两兄弟为争夺城邦的统治权而兵戎相见。为了阻止兄弟间的自相残杀,伊奥卡斯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他们进行劝阻,虽然结果以失败告终,但是她至少为此而努力过。其次,伊奥卡斯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思念流亡在外的儿子,兄弟反目成仇令她痛苦不堪,她剪掉自己的头发,穿上灰黑的破旧衣裳,自责对波吕涅克斯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她希望儿子们重归于好,为此她愿意承担一切苦痛:“这些灾祸的痛苦都由我受了。”[3]351可是天神并没因她的舐犊情深而对她有所眷顾,她看着奄奄一息的孩子们,号啕痛哭:“儿子们啊,我来救你们迟了一步。”[3]421“她轮番扑到儿子身子上,哭叫着”,悲痛欲绝。在儿子们断气之后,她也自刎而死,“和两个最亲爱的儿子躺在一起,两只手搂着他们”[3]422。
欧里庇得斯善于刻画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他总是站在道德的高度谴责她们,又站在道德的高度赞颂她们。在这种谴责与赞颂之间,充满诗人对女性的道德关怀。他笔下的坏女人也是充满魅力的,让人无法憎恨;他笔下的好女人也不会让人感觉到不真实。
欧里庇得斯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剧场中的哲学家”。他具有爱国主义的情怀,但是对于国家及其一切施政方针的不信任思想引发他对于城邦统治与公平正义的思考;对于苏格拉底及普罗泰格拉学说的欣赏使他对古希腊人的信仰产生怀疑,并且用理性的光芒指引他的剧本创作;对于女性地位与命运的思考使他创作出第一部研究妇女心理的悲剧《美狄亚》。无论同时代人怎样对他冷嘲热讽,他都是对后世影响重大的悲剧诗人。在他死后,他的作品因为充满道德感而经常被选作课文。《腓尼基妇女》是作者后期创作的比较成熟的作品,他在剧中的思想主张也有比较明显的表达,或许公平正义的统治、公民理性的思考、对女性及其他弱小者的关怀,就是欧里庇得斯最高的道德理想。
[参 考 文 献]
[1]〔英〕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M].孙席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古希腊)欧里庇得斯,等.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卷四)[M].张竹明,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4]〔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36.
[5](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等.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卷二)[M].张竹明,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7](古希腊)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M].罗念生,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61.
On Euripides′ Moral Idealism fromPhoenicianWomen
GAO Yunxiao
(CollegeofLiterature,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1,China)
Abstract:Euripides is indeed a Socratic moralist, a "chorus teacher", "theater philosopher", "thinker", but not a really tragic poet, and a person of Socratic spirit leading to tragedy.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yrant" and justice, the germin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the sink of divinity, and Euripides′ moral concern for women, the paper discusses Euripides′ moral idealism of fair and just monarch, rational thinking about civilians, and concerns for women and the weak from Phoenician Women.
Key words:Euripides; Phoenician Women; justice; rational; concern for women
中图分类号:I545.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318(2016)01-0075-04
作者简介:高云霄(1991- ),女,河南驻马店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5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
收稿日期:2015-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