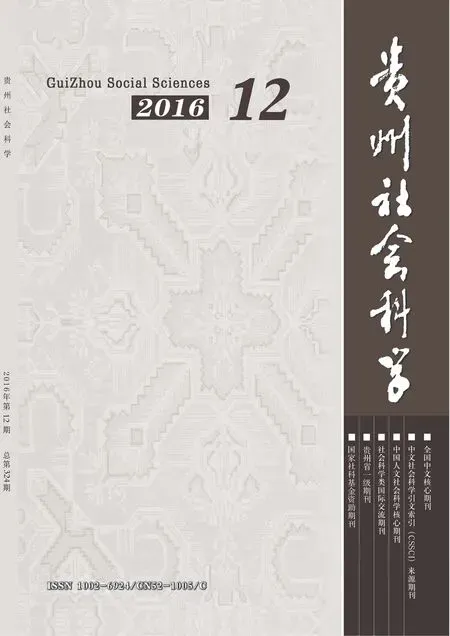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基础、历史经验与当下思考
黄前程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 长沙 410114)
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基础、历史经验与当下思考
黄前程*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 长沙 410114)
文化现代化、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动力机制问题,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深层关切。相应地,文化现代化理论、文化全球化理论和文化动力机制理论,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基础。从历史经验看,根据文化资源分类,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方式可分为创新发展、解析重构和移植再造三种。在这三种方式中又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最为基本的文化创新创造方法——诠释学方法;而 “格义”也是一种特殊的诠释学方法。关于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三个重要问题有待深入探讨:一是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创造性转化”的推进路径问题,三是“创造性转化”的本体论问题。函数表模型Y=F(M ,Z,X),可以用来表达中、西、马三者的总体关系;时代化路径、大众化路径和世界化路径,是推进创造性转化的三个基本路径;而实践本体论或许能满足关于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一个本体论追问。
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理论基础;历史经验
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要努力推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当前,结合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建设的现实问题,对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基础、历史经验进行检讨,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基础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可以作这样的表述,它“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2]“创造性转化论”本质上是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种理论模式,它接续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发展的时代问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它的核心问题。
当下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它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为目标,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积极因子的改造、重组,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文化转型与发展过程。它既要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又要充分吸收时代精神,既要立足本土又要面向世界。不难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兼具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同时,文化现代化也在加速促进文化的全球化发展。因此,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中华传统文化,其创造性转化,也必然是在全球化的观照下进行。
“创造性转化”是改造而不是捏造,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革新价值的成分、质素进行改造、重组。因此,发掘创造性因子,激发创造性潜能,是“创造性转化”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它实质上就是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文化生长点与历史接合点上,发掘其创造性转化的内生动力。同时,从整个文化生态视域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动力机制,也是“创造性转化”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文化现代化、文化全球化和文化动力机制问题,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深层关切;后者一系列问题的深入展开,都必然受到前者的根本约束。相应地,文化现代化理论、文化全球化理论和文化动力机制理论,也就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基础。
首先来看文化现代化理论。文化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整体进程中文化变迁方面的一个事实。不过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而言,它还有特殊的含义。虽然广义地说,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领域”[3]13。但对于广大后发展国家来说,“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3]13,它意味着承受外部冲击,向世界先进学习,它是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外诱性变迁,是外源性的现代化。如果说一般现代化是“古今”问题,那么中国现代化作为一种外源性的现代化,就又含有“中西”问题。中国现代化“一般”与“特殊”的纠缠,使得“古今中西”之争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新的世纪,应该是中国文化走出“古今中西”之争的时候了。为此,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思想方法上可采用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4]的主张。这包括如下一些要点:
一、现代化是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传统文化是建设现代文化的重要资源。要坚持古为今用,既要反对文化保守主义,也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特别注重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启蒙”意义的历史根芽,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培育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文化生长点。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既有民族性的,也有时代性的。要坚持洋为中用,既要反对文化中华优胜论,又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在学习借鉴西方文化时,一方面吸收其反映现代化的时代精华,一方面开掘其为我所用的民族特色。中华文化现代化虽有向西方学习借鉴的历史境遇,但并不等于“全盘西化”。
三、保持开放态度,对于中外一切文明的有用成果,都应继承下来,吸收过来,做到“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综合创新论”强调跳出“中西体用论”的思维范式,来做到中西会通。不过,弃置“体”、“用”、“本”、“末”诸范畴,并不等于放弃民族主体性立场,而是要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5]来做“综合创新”。这意味着中华文化,要在现代化的自我更新中保持自身民族性格。
所谓文化全球化,“就是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以信息全球化为依托,通过日益紧密而又频繁的交往,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更新自身,发展自身的文化整合过程”[6]。文化全球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它根植于文化的世界性,即特定民族文化都包含有对其他民族文化有益的成份。但文化全球化又从属于文化多元化;多元化是人类文化的价值诉求,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人类社会“一元多线”地发展,就显现了人类文明的共性与多元发展的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和而不同”的文化关系,建立“多元一体”的文化关系格局,应是全球化过程应有的“文化自觉”。[7]
要保持文化开放态度就要求我们要处理好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文化的世界性越发彰显的同时,每个民族又必然要探寻支撑其独立发展的民族文化根基。所以,当前世界上并行着两大文化思潮,即“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而这两种意识又构成了现代文化发展两极对立的必要张力[8],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一种动力。不过在这种动力中,推动民族文化自强不息的决定因素还是在于民族性。因此发扬民族特色、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文化传统,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应该具有的主体意识。
再来看文化动力机制理论。文化的动力机制是关于文化生成的动力及其激发条件、传运过程和作用方式等方面的系统内容。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进行创造性转化,离不开自身文化因子的转化潜能,也离不开文化主体的重新阐释与积极构建,更离不开该文化置身其中的社会土壤。因此,对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动力机制的探讨,适宜采用生成论的视角和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在生成论视角下,文化的“人化”属性从属于“化人”属性,这就要求将文化主体客体化,将文化创制视作一个个客观“生成”的事件。而文化生成的动力,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化生态综合体也决定了文化生成的走向,提供文化发展的基础。[9]
基于文化生态视域探讨文化的动力机制,是一种整体论的研究方式,它有利于矫治心智决定论、地理决定论和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偏颇。因此,对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动力机制研究,其宜采取的思索路径是:将文化事件视为一种自然事件,将文化发展当作自然历史过程,视为整体原因与结果的演变过程,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寻找“创造性转化”的动力来源及其运行机制。
二、历史经验
中华文化是较早以华夏文化为基干,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与各地域、各民族、各国家文化的接触、交流中形成的。其中,外来文化影响中华文化进程的重大事件有两次:第一次是自公元1世纪以来印度文化的传入,第二次是自16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因此,研究中华文化生成演变的丰富历史,特别是总结其创造性转化方式、方法的宝贵经验,可为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有益借鉴。
“创造性转化”的实质是要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能沟通古今、中外的文化因子,通过综合创新,创造与时代文化相融通、与现实社会相协调的新文化。从历史经验看,根据传统文化资源的不同类型,会有不同的创造性转化的方式。传统文化资源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体系完整,且其核心价值与时代要求相适应;一类是体系完全,但其核心价值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只是其个别成份有开掘价值;一类是非有完整体系,或仅为某种遗存的文化因子,但有挖掘价值。与此相应,其创造性转化的方式分为创新发展、解析重构和移植再造三种:
一、所谓创新发展,是借用了习近平论述中华传统文化提到的“创新性发展”一语。这里,“创新”是在旧有基础上发现、发明、创造,“发展”是在既有基础上开发、拓展、延伸。创新发展与第一类文化资源是相匹配的。第一类传统文化由于体系完整,且其核心价值与时代相协调,其文化创制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通过吸收外部资源,拓展意涵,创新形式,从而实现创造性转化。中华文化延绵几千年,有其一贯的核心价值,总能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形成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现代新学的学术历程,其最主要的创造性转化机制就是通过这种“创新发展”方式实现的。例如,原始儒学的心性之学,经过对佛教因素的吸收,形成宋明理学,到近代又通过学习西学,发展为现代新儒学。又如道家学说,在秦汉之际衍生出黄老之学,到魏晋之际又发展出魏晋玄学(新道家),之后又演变为道教经典。而且,中华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能力极强,既使对于系统的外来文化也能予以改造、同化。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汉晋依附于汉代方术、魏晋玄学,在东晋形成以般若学为核心的“六家七宗”;南北朝佛教形成了以涅槃学为核心的教派哲学;隋唐佛教形成以心性论为核心的中国化的宗派哲学;五代以后,在“三教同心”心性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三教合一,最终宋明理学取代佛教哲学,成了社会正统的意识形态。
二、所谓解析重构,是借助了解构主义的思想和术语。它指对现存理论的结构加以解体,打散诸成份,使之游离,然后重组,以谋求内涵的更新[10]。解析重构与第二类文化资源是相匹配的。第二类传统文化,虽然其核心价值已不能与时代相协调,但不排除一些文化成份具有挖掘价值。因此对原有文化体系进行解析,攫取其中部分因子,并对其进行再阐释、再组合,这仍是一条重要的资源发掘方式。以中国王权主义为例,它整体上是一种君主专制主义,并已随中国社会变迁而解体,但其民本思想却是近代中国民主生成的深厚资源。中国传统的“民本”,意为“为民作主”,而现代的民主,意为“人民作主”,两者本不相同。不过如果以“民有、民治、民享”来作民主注脚,那么它较民本思想为富的只在“民治”,而“民有”、“民享”并不为民本思想所缺[11]。也因如此,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兴起之初,少有直呼之以“民主”,而是多呼之以“民权”。民权概念表达了君主专制下人民参与政治的隐晦要求,它意味着由西方民主诱发的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唤起,也成为打通民本与民主之间思想脉络的桥介。[12]不难看出,仅就思想层面而言,如果将“民本”从君主专制主义中剥离,并将“民治”注入其中,则“民主”可成。此种重构之根据,就在于中国自古并非不知尊重民意(所谓“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之合理,而在如何实现(所谓“by the people”)之困惑。[13]
三、所谓移植再造,是借用现代新儒家“花果飘零”与“灵根再植”之意。现代新儒家认为,儒家文化自近代以来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儒学被解构,只有存世遗孑之“花果飘零”,游根无寄,但如果能笃定存亡续绝的信心与希望,以“创造性的理想与意志,创造性的实践”[14],定能使中华文化,“灵根再植”,花繁叶茂于世界。以此等意思来看,移植再造与第三类文化资源是相匹配的。本来,中华传统文化就有若干文化因素是缺乏系统化组织的;而若干传统文化固有体系,在悠远的历史中,特别是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也已解体,只留下了斑斑遗存。对这类文化资源如能随境所适,将其移植到新的文化枝桠上去加以培育,定可开出新的花果。例如,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如今可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进行新的诠释,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涵养,并在社会主义新人伦中展现出新面貌。再比如,对中华传统的“大同理想”、“实践理性”、“集体价值”,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嫁接。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展开,与中国上述文化传统是存有极大关系的。[15]
综上所述,创新发展、解析重构、移植再造是基于文化资源分类而形成的三种创造性转化的基本方式。而这三种方式中又存有一种共同的、最基本的创造方法——诠释学方法。诠释学方法是沟通古今、汇通中外不可缺少的文化创新创造方法。其实质是对传统文化基因进行发掘与阐释,以找到创造性转化的文化生长点与历史接合点。正如习近平所论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诠释学方法以对传统文化积极因子的创造性诠释为核心,具体包括对文化资源的挖掘、解析、选择、改造和重组等系列工作。挖掘要充分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广泛开掘;解析要利用文化分析方法,析取文化积极因子;选择要以时代眼光,萃取文化精华;改造要契合时代文化,诠释文化内涵、改变文化形式;重组要结合时代先进文化,借鉴人类文明成果,进行综合创新。
为了进一步探讨诠释方法的运用(类型),不妨以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为例来做一分析。首先就诠释的内容层面看,经典诠释包含了语言文字注释、文化背景揭示、人格心理探析和普遍意义解读[16]。既从语言文字方面弄清文字含义(文字注解)和文本内容(文意疏解);又从社会历史背景和人格心理因素方面来解读文本意蘊;还可就当下社会现实解读文本的普遍意义。这里,“文本意蕴”是文本内容的“言外之意”;而文本的“普遍意义”是文本在和历史与当下的联系中显示出的一般意义。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来说,挖掘这种“言外之意”与“普遍意义”,正是其工作重心。
其次,如果以是否建立思想体系为目标来看,经典诠释又分为诠释与建构。[17]33诠释包含注释但不等于注释,它是在注释基础上对深层意蕴与普遍意义的发掘。建构则指思想体系的拟构或创构,它是对文本中可能的思想体系进行模拟,或创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当然,经典诠释存在一个内在的紧张,即“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义”与建立诠释者自身思想体系的矛盾。这实际上就是诠释学方法两个定向的矛盾,即历史的、文本的、客观的定向与当下的、现实的、创新的定向之间的矛盾。[17]12这个矛盾对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来说,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诠释方法,那就是格义方法。格义方法发生在两种文化初步接触、交流之时,它是以熟知的思想、概念来解释尚未熟悉的思想、概念。例如,晋代高僧竺法雅与康法朗等,因门徒未善理佛,“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18]152格义又可分顺向格义(传统格义)与反向格义(洋格义)。传统格义是以大家熟知的中国本土文化经典中的概念,来解释尚未普及的外来文化的基本概念的方法;而洋格义是近代以西方文化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本土文化的方法。[17]97-102
顺向格义在中国较为自觉的运用,是在印度佛教文化传入过程当中,尤其是汉晋时期,佛教依附本土学术,多用格义、连类之法。如前述《高僧传》记载,除竺法雅与康法朗等运用格义方法解释佛理外,毗浮、昙相等 “亦辩格义,以训门徒”。[18]152在思想内容方面,以般若学比附玄学者尤为明显,这集中体现在《肇论》当中。反向格义是中国近现代学人出于对西学的倾慕,而希图模仿西学以建立本民族现代文化的学术努力。这种方法运用的早期代表性成果,要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如果说顺向格义是高水平的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一种方法,那么反向格义则是本土文化学习高水平外来文化的一种方法。目前,反向格义在中国学术研究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方法,但其对中国学术的影响还难以清晰评估。
三、当下思考
讨论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经验,最终要着眼于新时期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现实问题。关于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三个重要问题有待深入探讨:一是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创造性转化”的推进路径问题,三是“创造性转化”的本体论问题。
首先,中、西、马三种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一个原理性问题。当前,汇通中西马,已成共识[19]。不过,对中、西、马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具体作用,关注点自来不尽相同。例如,陈先达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指导地位。[20]有些学者如郭齐勇、陈来、朱汉民等,则强调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体性[21]。而方克立则主张以“马魂,中体,西用”三元模型来处理中、西、马三者关系。[22]实际上,从内涵来看,“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它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目标,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积极因子的改造、重组,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文化转型与发展过程。创造性转化的实质,就是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而时代化、大众化和世界化构成了创造性转化的三个基本维度,并由此形成创造性转化的总体架构。
因此,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总体关系由四个基本元素构成,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Y),马克思主义(M),中华传统文化(Z),西方文化(X)。它们之间的总体关系模型,不妨以函数表达为Y=F(M ,Z,X)。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Y)是目标,马克思主义(M)为指导,中华传统文化(Z)是基础,西方文化(X)为外来资源。在这个函数模型中,不是以“中西体用论”来评判一种文化,而是基于文化生态的视角,以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一种新型文化的生成。
其次,推进路径问题,是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目前,已有研究主要有四种观点。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创造性转化的基础和根本途径。[23]有的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以“传统文化的世界化”为中介,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现其创造性转化[24]。有的从文化特性出发,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由于不存在“自为文化”与“自在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因此,它的现代转型不能进行“内在创造性转化”,而只能走“外在批判性重建”之路[25];有的着眼于实践操作,认为创造性转化的具体方法与途径有赋予新义、改造形式、增补充实、拓宽延展、规范完善等等[26]。
总体看来,有关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路径研究,多局限于各种路径的分散讨论,未重视探讨“推进路径”的系统构建。实际上,如果基于“创造性转化”的时代化、大众化和世界化的三个向度,相应地,创造性转化的推进应有三个基本的路径。一是时代化路径,它要使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相适应,要反映时代精神、时代特征,要能吸收时代成果、解答时代问题。二是大众化路径,它要使传统文化为广大群众所认同,要关注大众生活,契合大众心灵,运用大众表达,解决大众难题。三是世界化路径,它要发掘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要能进行全球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和相互吸收。在此基础上,再对其他途径进行整合,则可形成推进路径的系统构建。
最后,本体论问题。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应该跳出“中西体用论”的思维范式。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创新创造既不应以中学为体,也不应以西学为体,它也不是中西互为体用,而是中西文化在共同参与世界文明的创造中,去贡献自己的价值。[27]但这并不等于主张“文化无体论”。因为虽然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并不宜以“体用论”来处理中、西、马三者的关系,但这种文化创造的动力源泉、最终根据等问题,仍然是期待回答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
对此,可以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来探讨社会实践在其中的本体意义。这意味着不是从某种单一文化、也不是仅从文化自身,而是从整体性的社会实践出发,来对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深层机理作出确切解释、科学判断。如果以“知识论”的视域来反省这一探索,它其实是以优先考虑“关系”和“过程”而弱化“实体”的视角转换,来为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本体论根据。这是一种整体论的思维方法,它试图以此来避免对“创造性转化”的根据作出还原论的解释。因此,在跳出“中西体用论”之后,关于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实践本体论或许能满足对它的一个本体论追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2]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364.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3.
[4]方克立.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4-7.
[5]陈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谈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N].光明日报,2011-05-22.
[6]李宗桂.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哲学省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6.
[7]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5.
[8]萧萐父.吹沙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7:85.
[9]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147.
[10]冯天瑜.解构专制[M]//冯天瑜文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121.
[11]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7.
[12]王人博.法的中国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47.
[13]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6.
[14]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1.
[15]李泽厚.中国哲学如何登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94-95.
[16]陈少明.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第2版[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17-24.
[17]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8]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9]孙正聿,陈来,韩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孙正聿、陈来、韩震先生中西马高端对话[J].中国文化研究,2013(3):7-30.
[20]陈先达.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6):8-12.
[21]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N].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6):62-68.
[22]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J].北京大学学报,2010(4):7-17.
[23]徐剑雄.论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6):85-88.
[24]郗戈,张梧.弘扬核心价值观要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N].光明日报,2015-02-26.
[25]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4-126.
[26]李军.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N].光明日报,2014-10-10.
[27]胡伟希.中国本土文化视野下的西方哲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59.
[责任编辑:明秀丽]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机理研究” (15YBA002);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推进路径研究”(15C0078)。
黄前程, 哲学博士,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G122
A
1002-6924(2016)12-092-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