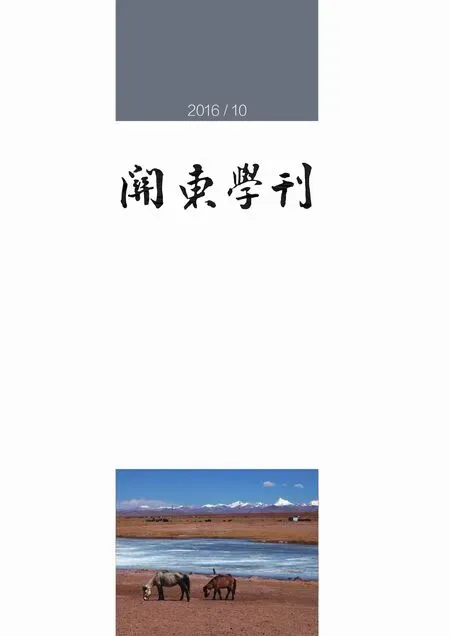“韵胜”:黄庭坚的人格诗学
付新营
“韵胜”:黄庭坚的人格诗学
付新营
“韵胜”这一审美标准来自佛学,到黄庭坚则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指向,在黄庭坚那里,韵胜不仅是一切艺术的审美标准,更是超越文艺范畴的人格标准。从人之道性出发,他追求诗歌的“道味”,追求艺术中人生的超越,使得这一审美范畴成为了宋代人格诗学的主要代表。宋诗的善写老境,瘦硬之骨,翻新求奇的创作传统,就来自于这一时代性的审美共识。
韵;黄庭坚;诗学
受江西后人的影响,历来说起黄庭坚的诗学思想,无不以“夺胎换骨”“以故为新”以及“点铁成金”等等为其思想的核心,这是有些偏颇的。实际上,同宋代所有的诗家一样,黄庭坚对诗歌的注意在于诗歌的超越性质,而不仅仅在于诗法、句法。只不过黄庭坚的论诗著作多在晚年写出,而这些著作都是向后辈介绍写作经验的,因此给人的印象就是他注重写诗法式而少重风韵。遍观黄氏著作,我们看到,他跟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一样,其诗学追求在于诗歌的“道味”,在于对“格”“韵”的传达。
一
黄庭坚在《论作诗文》中说:“小诗,文章之末,何足甚工?然足下试留意:奉为道之‘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后来学诗者,时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体得一处,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开眼,则全体见之。”(《山谷别集》卷六,四库全书本)如果不学习,就只能是像他自己少时作品一样“气嫩语坚”了。(《答王观复》,《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以下无特别注明者同)“气”格与“语”格是不可分离而又相为表里的。如果气格不是“嫩”而是老成,语格不是“坚”而是圆熟,那就达到了黄庭坚的要求。我们要特别注意他在《论诗作文》里的“全体”二字。气格不是“全体”,语格也不是“全体”,二者的结合才是诗的全体。《书刘景文诗后》说:“余尝评景文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文集》卷二六)为什么呢?因为读书可以使人开阔视野,进而使人增加识力,辨别什么是自己需要的,什么是不需要的,并不是要死读书。他说:“更能识诗家病,方是我眼中人。”(《荆南签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见慧次韵奉酬四首》,《文集》卷十二)苏轼也说过,黄庭坚诗“殆非悠悠者所识,能绝倒者也”,对事物的概括、识力不是常人可以达到的(《书黄鲁直诗后》)。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要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比较,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最终达到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学习古人就要学其作品中体现的这种不俗的人格境界。《书嵇叔夜诗与侄榎》:“叔夜此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凡学作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虽沉于世故者,暂而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矣,何况探其义味者乎?”(《别集》卷十)“义味”是人生境界的高妙之处。欧阳修、苏轼常说某某人或某某人说的话、做的事“有味”,也是这个意思。可以看出,这与宋代人们说的“道味”是同样的东西。黄庭坚在《题意可诗后》里专门讨论了不俗与道性的关系:
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道者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海暂举心,尘劳先起。”说者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渊明之诗,要当与一丘一壑者共之耳。(《文集》卷二六)
前面的话,跟陈师道信奉的以格法体现不俗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黄庭坚更追求由“道”体现的更为精微、弘深的不俗。所以,他接受了苏轼的观点,将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的真率看作以道观诗的理想目标,从陶诗之拙朴与自然的外貌中体会到主体对现象的内在超越。这说明,黄庭坚的诗学理念从根本上与苏轼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关于实现的途径,他认为读书—识力—创新的途径更为现实。他劝人学习老杜后期诗歌,其实也是为了学习与陶渊明诗歌一样的超越精神(《答王观复书》,同上)。只有才识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使诗歌创作达到以俗为雅、率性而合道的地步。
黄庭坚在中年以后,更加注重作诗的“韵胜”。黄庭坚六十岁时有《赠惠洪》一诗,云:“韵胜不减秦少觌,气爽绝类徐师川。不肯低头拾卿相,又能落笔生云烟。”(《文集》卷六。陈善《扪虱新话》以为是惠洪诈学山谷所作,未知确否。)按以“气韵”论艺,始于宗炳;而将气、韵区别运用,则始于五代的荆浩。荆浩《笔法记》说:“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黄庭坚的这首诗简直是荆浩这句话的韵语形式。这不是简单的词语差别,而是标志着艺术目标和审美趋向的变化。荆浩的观点其实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气韵”“神韵”的确定化,都是以气作为创作论的中心,而将韵作为作品论的中心。但是,在张彦远那里,神韵只是艺术表现的一个结果,而荆浩则同时将它当作了像气一样的创作前提。到了宋代,随着人们对道的不断强调,气与韵都成为道的基础上的艺术范畴,其内涵也有相当程度的交叉。气格之高与气韵之胜往往是不同角度看到的不同形态而已。而在将它们放在一起来看时,则会同时呈现出“不俗”的面目。
从“不俗”这个角度理解黄庭坚所提出的“韵胜”的艺术命题,就可以了解宋诗学“外枯而中膏”的特点。“气爽”是瘦硬的外表,而“韵胜”就是“中膏”的部分。在宋代(以及整个古代),黄庭坚是谈“韵胜”最多的人。从其使用的情况来看,他说的韵也同时包括了人格、风度、精神气质的内容:
第一,用在评价人物精神风貌。他明确提出要以韵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题跋》)我们上面所举的《赠惠洪》一诗,就是赞扬青年惠洪不恋富贵,而致力于诗艺建树的出尘风姿。他在《与俞清老》里又说俞秀清“慧根韵胜,已有退听返闻之功”,也是同样的意思。重要的是,这里的韵充溢着道德的精神。“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跋东坡墨迹》,《文集》卷二十九)韵当然主要是从书法的审美效应而言的,但此中又包含了宋人人格追求中超于世俗的德性因素,故而比唐人的神韵多了一层主观的东西在里面。这表明韵中蕴含着气格的因素。
第二,用以评价作者的诗歌作品,如《与王立之承奉帖五》:“惠腊梅并得佳句,甚慰!怀仰数日,天气骤变,固疑木根有春意动者,遂为诗人所觉。极叹足下韵胜也!”(《别集》卷十五)在这两方面中,形容人与形容诗都是出于同一种意思,而且往往不能分别得很清楚。
第三,“韵胜”一词绝大多数用在对书法的评价上。黄庭坚多是通过艺术鉴赏来表达对人物的风韵的赞扬,在艺术评论中使用的次数更多,比例更大。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可想见。……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文集》卷二十八)又:“若论工不论韵,则王著优于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论韵胜,则右军大令之门,谁不服膺?”(《书徐浩题经后》,同上)又“东坡简扎,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今世号能书者数家,虽规摹古人,自有长处。至于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所谓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与也。”(《题东坡字后》,《文集》卷二十九)这让我们想起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里对古代书法家、诗人的评价。韵胜的内容就是“萧散简远”,就是荆浩说的“备仪不俗”。在书画中,“韵”是从笔法中得到体现的。
第四,韵胜也用于对其他美的事物(无论是味觉的、视觉的、听觉的)的评价。苏轼用格韵来表示对江瑶柱、荔枝的喜爱,而黄庭坚也用韵胜来对家乡的茶叶表示由衷的热爱:“校经同省并门居,无日不闻公读书。故持茗碗浇舌本,要听六经如贯珠。心知韵胜舌知腴,何似宝云与真如。汤饼作魔应午寝,慰公渴梦吞江湖。”(《以双井茶送孔常父》,《文集》卷三)双井茶是黄庭坚很引以为骄傲的,经常拿来送给他的朋友,如苏轼、惠洪等人,苏轼也专门为此写诗称赞。另外,他在《白山茶赋》里也说:“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丽紫妖红争春而取宠,然后知白山茶之韵胜也。”(《文集》卷一)可见韵胜是一种风流萧散的姿态。
可能受黄的影响,后人也多以韵来形容一些美妙的事物,比如陈去非论腊梅“韵胜谁能舍,色庄那得亲。朝阳一映树,到骨不留尘”(《同家弟赋腊梅诗得四绝句》,《增广笺注简斋诗集》卷七,四部丛刊本)的清婉之态,杨万里论木犀“姮娥收去广寒秋,太息花中无此流。花品已高香更绝,却缘韵胜得清愁”(《木犀落尽有感》,《诚斋集》卷十四,同上),论雪景“晴光雪色忽相逢,雨滴空阶日影中。珍重北檐殊韵胜,苛留残玉不教融”(《雪晴》,《诚斋集》卷二十一,同上)等等,都是从形象看韵度,以韵观物的结果。当然,最多的仍然是用来论人物之韵,如刘克庄说朋友黄预“骨秀神仙数,诗清雅颂才。识高悬日月,韵胜绝尘埃”(《黄预挽词四首》之二,《后山诗注》卷八,同上),惠洪说老友“韵胜折松秋露骨,气和寒谷夜生春”(《道林喜见故人》,《石门文字禅》卷十一,同上)等等,这里不遑多举。
所以,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他看待事物时,既重形式,更重意味,创作者、创作形式和创作方法都要不俗,才能有不俗之韵。黄庭坚说:“凡书画当观韵。在时李伯时为余作李广夺胡儿马,挟儿南驰,取胡儿弓引满,以拟追骑。观箭锋所直,发之,人马皆应弦也。伯时笑曰:‘使俗子为之,当作中箭追骑矣。’余因此深悟画格。此与文章同一关纽,但难得人入神会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七《题摹燕郭尚父图》)不俗,就是“箭锋所直”,既是气格不俗,同时也是韵致不俗。从精神方面看,“韵胜”的提出,实际上也是欧阳修、黄庭坚等提倡的“道战胜”的翻版,而从其内涵来看,也实在是同一理念的不同表现方式。欧阳修在论述新旧的“道”之间的斗争时,曾经用战斗来形容高尚的道打败卑下的道的畅快淋漓的情景:“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与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读书》,《居士集》卷九)欧阳修多次说到“道胜”,就是那种正确的道战胜落后的、卑下的道的简缩语。宋人眼里的韵是与道联系在一起的,是道返本归正的精神境界。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宋庠“渴吻漱仙液,饥肠涵道腴”(《和答吴充学士见寄长韵》)和黄庭坚“心知韵胜舌知腴”(《以双井茶送孔常父》)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品尝的是同一种敷腴的“道味”。
二
格高、韵胜落实到诗歌创作上,那就是既要表现出诗意的清高脱俗,又要在表现方式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就有了对笔力的要求。
笔力是作品在写作上的特征,是作者的才力的体现。讲究笔力,是宋人对诗学的普遍认识:为诗需老到、雄健、圆熟,方显笔力之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有相当多的类似言论。黄庭坚对笔力的锻炼更是反复强调,他称赞洪炎“笔力可扛鼎”(《书舅诗与洪龟父跋其后》),都是将笔力作为创作才能的主要着眼点。与上面他称赞陈师道的话相比较,可以看出笔力的重要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创作旨趣。
在黄庭坚的审美理想里,作诗一定要有广大的规模,恢弘的气象,专注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只有这样,所作之诗才有存于世上的价值。规模窘促,气局不伸,没有人格上的力量,就不会有存在的道德价值;而没有专注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也不会有艺术上的价值。在黄庭坚看来,艺术上的成功与否,就像战争里的成王败寇一样。黄庭坚评论苏轼之诗说:“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以韵道之》,《文集》卷二)开头说的是作诗应具有的气象,中间说的是句法高低,最后是对上述两者的总结,赞扬苏轼的笔力巨大。无独有偶,苏轼也使用了同样的言语来赞扬黄庭坚。《答舒尧文书》:“午睡昏昏,使者及门,授教及诗,振衣起观,顿尔醒快,若清风之来得当之也。大抵词律庄重,叙事精致,要非嚣浮之作。昔先零侵汉西疆,而赵充国请行,吐谷浑不贡于唐,而文皇临朝叹息,思起李靖为将,乃知老将自不同也。晋师一胜城濮,则屹然而霸,虽齐、陈大国,莫不服焉。今日鲁直之于诗是已。”赞扬黄庭坚诗歌的老健笔力。“庄重”“精致”是说锻炼的精细,这说明他对李商隐、王安石的学习;战胜之喻,则又说明黄庭坚气格、笔力的雄奇。又《村醪二尊献张平阳》:“诗里将军已筑坛,后来裨将欲登难。已惊老健苏梅在,更作风流王谢看。□出定知书满腹,瘦生应为语雕肝。□□洒落江山外,留与人间激懦官。”风流与老健的统一,更说明他们对“老韵”的自觉认同。
以力战形容作诗,让我们想起了欧阳修、苏轼的“白战”。《六一诗话》曾载进士许洞使九僧作诗而不得用“风花雪月”等字的故事,而欧阳修、苏轼也仿效此事与门生辈作过同样的游戏:“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祷雨张龙公,得小雪,与客会饮聚星堂。忽忆欧阳文忠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尔来四十余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继公后,虽不足追配先生,而宾客之美殆不减当时,公之二子又适在郡,故辄举前令,各赋一篇,以为汝南故事云。”并写诗云:“汝南先贤有故事,醉翁诗话谁续说。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计持寸铁。”(《聚星堂雪(并叙)》)“白战”就是反晚唐派的做法,不用物象而以思致作诗。这正反映了宋人“以意为主”的诗学思想,甚至“黄、陈诗有四十字无一字带景者”(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五《拗字类》评黄庭坚《次韵答高子勉》)。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杜牧说的“凡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意全者胜,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确实感到“于艰难中特出奇丽”所具有的审美内容。
像欧阳修一样,黄庭坚也是将对道的坚定熔铸在句法之中:“句中稍觉道战胜,胸次不使俗尘生。”(《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三首》,《文集》卷六)苏黄在北宋政坛上少有得志的时候,其根本原因就是苏门诸人对自己信念的坚定与执着,从不作骑墙派。他认为:“行要争光日月,诗需皆可弦歌。着鞭莫落人后,百年风转蓬科。”(《再用前韵赠高子勉》)所以,黄庭坚才会在《答何静翁书》里称赞何议论历史事件“不随世许可取明于己”,写诗“醇淡而有句法”,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文章之法度盖当此”。
除了在总体原则上阐明立场,黄庭坚更探讨了才器笔力施之于创作的各个方面,从而提出了自己系统性的句法理论。对于这方面的问题,前人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本文不再重复。需要强调的是,对黄庭坚来说,句法不仅意味着法度,更意味着风格、笔力,甚至人格精神。具体来说,在黄庭坚的论述中,句法主要包含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命意、布置、遣词。而在每一方面的内容里面,都显示着“战胜”的内在骨力,是“韵胜”在创作中具体而微的表现。
三
命意是宋诗学的理论起点。之所以不是物象、物境而是立意,是因为宋代诗歌已经走出了六朝以来兴感的路子,欣赏习惯也由物我相触转向了涵泳咀嚼,所以后来不习惯宋诗这种习惯的人就很看不上宋诗的这种写作方式:“宋人必先命意,涉于理路,殊无思致。”又说“李白斗酒百篇,岂先立许多意思而后措词哉?盖意随笔生,不假布置。”(《四溟诗话》)而宋人认为,从命意里头,可以看出诗人的精神力量。《陈辅之诗话》云:“冯长乐七岁吟治圃诗云:‘已落地花方遣扫,未经霜草其教锄。’仁厚天性全生灵性命,已兆于此。寇莱公八岁吟华山诗云:‘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其师谓莱公父曰:‘贤郎怎不作宰相!’”(“冯寇二公诗”条,《宋诗话辑佚》本)再举个例子,南唐徐铉初见宋太祖,欲以舌解围,诵后主之诗以穷太祖,太祖吟“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之句,徐铉拜服。(《苕溪渔隐丛话》卷25引《后山诗话》)宋太祖是一粗人,但能受到宋初文人的齐声喝彩,就是因为他所作诗的意思比李煜境界廓大。王、苏、黄作为宋诗学的代表,不仅追求诗意的大,更追求诗意的的深,普闻《诗论》云:“天下之诗莫出于二句:一曰意句,二曰境句。境句则易琢,意句难制。境句人皆得之,独意不得其妙者,盖不知其旨也。所以鲁直、荆公之诗出于流俗辈者,以其得意句之妙也。”其中不难看到宋人对唐宋不同诗歌范式的认识。
由此形成了求奇求新的诗学观。《观林诗话》言:“《王立方诗话》记东坡十岁时,老苏令作《夏侯太初论》,其间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之语,老苏爱之。以少时所作,故不传。然东坡作《颜乐亭记》与《黠鼠赋》,凡两次用之。以上皆王记。予按《晋刘毅传》邹湛曰:‘猛兽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虿作于怀袖,勇夫为之惊骇,出于意外故也。’乃知东坡意发于此。”《西清诗话》:“鲁直少警悟,八岁能作诗,《送人赴举》云:‘送君归去明主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此已非髫稚语矣。”小小年纪就发如此宏大的喟叹。又吕本中《童蒙训》中说:人们评论黄庭坚诗歌哪首写得最好,都以为是那首“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但黄自己却认为是“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这一首。这不仅是因为立意不同常人,而句法也不着痕迹了。
在追求新奇的过程中,诗人们总结出了一些固定化的方法、原则。比如翻案和“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以及“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等。
“翻案”一语由南宋的杨万里提出,是“翻却公案”的缩写。周裕锴认为:
“这种‘翻案法’既是宋代思想自由的一种体现,也与禅宗精神的影响有关。禅宗否定外在的权威,突出本心的地位,以起‘疑情’为参禅的基本条件,以唱反调为顿悟的重要标志,‘即心即佛’可翻作‘非心非佛’,‘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可翻作‘本来无一物,何处著尘埃’,破关斩壁,转凡入圣,大抵都有点‘翻案’的精神。禅宗起疑情、唱反调一般都以一则公案、一个话头或一首偈颂为对象,这就启示宋诗人以前人作品为对象,从中翻出自己的新见解、新意境、新风格来。”
将翻案理解为一种写作的精神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灼有见地。杨万里说:
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如山谷《猩猩毛笔》是也。猩猩喜著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笔,用之钞书,故用惠施事。二事皆借人事以咏物,初非猩猩毛笔事也。……刘宽责吏,以蒲为鞭,宽厚至矣。东坡诗云:“有鞭不使安用蒲。”老杜有诗云:“忽忆往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东坡则云:“何须更待秋井塌,见人白骨方衔杯。”此皆翻案法也。(《诚斋诗话》)
在他举的这些例子中,苏黄皆能翻空出奇,将原始素材运用得新意迭出。同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其实唐代诗人们已经熟练地运用过这种方法,而且也提出“反用事”的法则(晈然《诗式》)。但宋人如此强调这种方法,除了是想找一个方便之门外,更是在以此发扬一种劲峭的力度,显示个性的精神。比如,前人描写花时多以美女作比,而黄庭坚则用美丈夫作比。(《冷斋夜话》卷四)
关于“夺胎换骨”,黄庭坚说:“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如郑谷《十日菊》曰:‘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气不长。西汉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气长故也。曾子固曰:‘诗当使人一览语尽而意有余。’乃古人用心处。”(《冷斋夜话》卷一引)为了显示个人超俗的气格,就不能使诗歌一览无遗,而应该用异于常人的意象选择、字句排列、音韵格律,使其产生生新瘦硬的感觉。《诚斋诗话》评苏轼《煎茶》诗云:“……‘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仍作泻时声。’此倒语也,尤为诗家妙法,即少陵‘红稻吸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也。‘枯肠未易禁三碗,卧听山城长短更。’又翻却卢仝公案。仝吃到七碗,坡不禁三碗。”这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夺胎换骨”实际是为了争取诗意、句法的新鲜而采取的方法,不应该是消极的东西。
黄庭坚认为,须下字无虚,才能锻炼精细,产生诗味。“老杜诗曰:‘黄独无苗山雪盛。’黄独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卬’。南州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黄精’。子美流离,亦未至作道人剑客食黄精也。如渊明诗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浑成风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状,学者不可不知。”(彭乘《墨客挥犀》卷一引黄庭坚语)他这里说的是文字传抄中的错讹现象,但一字的偏差就会使一首好诗变得卑陋而荒谬。所以他本人写诗极锤炼之功,使诗歌呈现出精严华丽的特点。这也是苏轼论其诗“格韵高绝”的理由之一。
从广义上讲,所谓的“以故为新”或者“点铁成金”等等,都可看作是“翻案”精神也即求新求工意念的扩展。惠洪《冷斋夜话》里,黄庭坚很明确地指出,句眼对诗歌的形式(语)与精神(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上面惠洪所引的那些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诗句,都是对仗工整又同时诗意拔俗的,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意念上,都是作品不可不具备的耀眼之处,不然,或是会落入句好而格下的毛病,或是会导致意新而体俗的缺点。对形式和个性的双重关注,使得他对写诗的要求比其他“为艺术而艺术”或者“文以载道”等等的想法都有所不同。
付新营(1971-),男,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