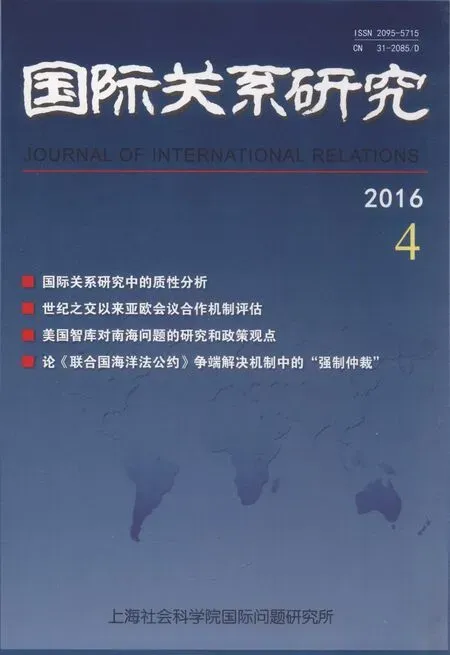超越地缘的全球治理理念创新
——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分析
谢婷婷
中国外交
超越地缘的全球治理理念创新
——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分析
谢婷婷
随着中国的崛起,由于其作为东亚大国在地缘上的敏感性,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提供广阔的市场、技术和投资虽然引起了沿线国家的热烈反响,但仍受到不少质疑。从地缘政治的现实利益考量来看,可以从地理身份和情绪化比较两个方面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面临的地缘挑战。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最终目标是要形成地区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化解中国在区域中的地缘困境,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提出以公共外交推动构建情感共同体,将关注点聚焦于人们对地理环境的主观因素构建,以此消解纯粹物质性的地缘要素在政治实践中的负面影响。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地缘困境公共外交
着眼于中国在新时期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以及东盟国家共同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面向中国与东盟合作长远发展,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构想,以实现中国—东盟的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新海上丝绸之路*日本学者三杉隆敏1968年在《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随后很快被众多中国学者所接受,开始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与印度洋之间海洋贸易历史的课题研究。有什么不同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以贸易为基础的,不包含任何强力和其他海上军事行动。从丝绸之路所引领的贸易交通和人员交流来看,新海上丝绸之路仍然发挥着传统的经贸和人员交流作用。但是,新海上丝绸之路最重大的区别在于,世界形势的变化使得我们不得不以21世纪的新视角去考察和探索这条“似是而非”的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即以超越地缘的治理理念创新为视角,探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能发挥的作用。
一、地缘因素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影响
1.地缘的影响
21世纪,中国所在的区域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在18世纪以前,中国是东亚地区的唯一大国,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挑战它,那么21世纪的亚洲格局早已发生了巨变,当今亚洲至少存在3个大国,即中国、日本和印度,而美国作为区域外大国在本地区不可磨灭的存在感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亚洲大国等新兴力量都影响着区域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因此,这些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本文选取其中之一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切入点,以便于分析,并不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次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或彼此截然独立,两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相互的互动和促进机制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倡议的态度和策略可能会有很大的冲突性,那些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质疑的声音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虽然中国提供广阔的市场、技术和投资引起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热烈反响,不少国家如斯里兰卡和泰国等都积极制定相关对应政策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相对接,但是仅仅关注经济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并且可能是短视的。随着中国的发展,由于其作为东亚大国在地缘上的敏感性,周边小国必然对此反应明显,而且即使在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同时也不免对中国产生疑虑,这是作为大国的中国难以避免的规模上的难题:由于地缘上的临近,周边小国都密切关注大国的一举一动并作出敏感的反应。*关于国家规模大小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研究,参见Brantly Womack,“How Size Matters: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Asymmetry,”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4,No.4,2001,p.123。显然,地理因素会对国家政治行为产生影响和作用,但是它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怎样起作用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地缘对于政治的影响可以划分为冷战前后两个阶段。冷战前的传统地缘政治学起源于地理政治学。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在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以后又发表有关“生存空间论”的论文,把达尔文物竞天择、优生劣汰的生物学概念应用于国家的成长和发展,认为国家像有机体一样有兴盛衰亡的过程,国家的兴盛需要广阔的空间。此后,1917年,瑞典政治地理学家契伦接受了拉采尔的思想,首次在其《论国家》一书中提出了地缘政治学一词,并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着重研究国家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规律,随后的“制海权”、“陆心说”、“边缘地带说”和“制空权”等关注不同地缘因素的理论都是在这个基本概念基础上发展出来的。*1890年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在其《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提出“制海权”理论,认为“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在于对世界重要海道和海峡的控制,参见[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冬初阳译:《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1914 年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大陆心脏说”,认为“谁控制东欧,谁就能统治亚欧大陆心脏,谁控制亚欧大陆地带,谁就能统治世界岛”,从而主宰世界,因而被称为“陆权派”,代表作是《历史的地理枢纽》,参见[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20世纪40 年代,荷兰裔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又提出了“边缘地带说”,建立了“陆权论”又一派的理论。到了20世纪50 年代,美国战略学家塞维尔斯基根据北极地区处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对空军日益重要的作用提出了“制空权”的理论,参见Alexander P.de Seversky,Air Power:Key to Survival,Jenkins,1952。1973年科恩提出地缘政治战略模型,将世界分为海洋贸易区和欧亚大陆区两个地缘战略区,参见[美]索尔·伯纳德·科恩著,严春松译:《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自地缘政治学理论产生以来,这些观点都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过分突出地理环境中某一部分或地区的重要性,认为控制某一地区便能支配全球。
冷战后,战略分析家开始探讨新的地缘政治理论,出现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达努奇的全球地缘政治或多极范式*[法]罗朗·柯恩-达努奇著,吴波龙译:《世界是不确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布热津斯基的失控世界范式*[美]布热津斯基著,潘嘉玢、刘瑞祥译:《大失控与大混乱: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卢特瓦克(Edward N.Luttwak)的地缘经济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和卡普兰(Robert D.Kaplan)的乱世将临论等。这些理论反映了新时期人们对地缘政治学的重新思考,被称为新世界秩序地缘政治学。新地缘政治学尽管试图从全球、多极、文化和经济利益等各种视角切入研究,但仍无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和决定论倾向,依旧把西方视为世界的中心,把地理状况固定不变的特征当作决定国家命运的核心。
除此之外,冷战后还出现了一类被称之为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方法。1992年,奥特瓦赛尔和约翰·阿格纽在美国《政治地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地缘政治与话语: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实践性理性》一文,随后出版了相关著作,揭开了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序幕。*Gearoid ó 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London:Routledge,1996,p.59; John Agnew and Stuart Corbridge,Mastering Space:Hegemony,Territ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John Agnew,Geopolitics: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London:Routledge,1998;Gearoid ó Tuathail,Simon Dalby and Paul Routledge,eds.,The Geopolitic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Gearoid ó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eds.,Rethinking Geopolitics,Routledge,1998.此后,一些地缘政治学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尝试把地缘政治视为一种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实践,而不仅仅是世界政治的一种清楚和合理的现实存在。如果说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是地理决定一国的权力,从而决定国家命运的话,那么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从分析纯粹物质性的地理因素如何制约政治活动转变为探究人类如何认识或想象地理环境,从而展开政治实践。对于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者来说,地缘政治的对象不再只是物质性的,而主要是表述性的。这种对人类主观因素(人们是如何认识或想象地理环境)的重视使得批判性地缘政治学具备了与传统地缘政治学完全不同的分析起点和路径,这显然是受到社会学转向和后现代发展的影响。学者希望从中发现特定社会是如何描述、衡量和评价特定的地理环境,从而塑造出诸如“自我—他人”、“安全—危险”、“同质—差异”等概念的,以及在这些概念形成后是如何开展相应政治实践的。*Klaus Dodds,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Prentice Hall Engineering/Science/Mathematics,1999,p.32.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该理论重在批判的特色使得其建构理论的努力并不出色,对于这种“主体间”的地缘政治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和决定国家行为缺乏分析和论证。随后,多米尼克·莫伊西作了新的理论探索,在其《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法]多米尼克·莫伊西著,姚芸竹译:《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第一次把情感因素引入地缘政治学领域,通过描述一个情感复杂融合而成的世界来理解全球化。
2.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地缘挑战
借鉴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多米尼克·莫伊西的创新性探索,本文从“主体间”的地缘政治出发探索地理因素对国家互动行为的影响和制约,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面临的地缘挑战。一是地理身份。地理身份是一种关系身份,由地理位置和互动文化所决定。也就是说,一国的地理身份不是单一、恒定的身份,而是在面对不同国家行为体时具备不同的地理身份,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对”地理身份。例如,对于巴基斯坦和印度来说,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历史上因宗教冲突和领土矛盾而产生的敌意,巴基斯坦具有“相邻的敌国”这个地理身份,印度对自己地理身份的认识也是如此;这与美国相对于其地理身份是截然不同的。二是情绪化比较。人类认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比较所塑造的。事实上,近期关于比较过程在决策和相似性判断中的关键角色的研究层出不穷。*相关研究见D.L.Medin,R.L.Goldstone,& D.Gentner,“Respects for Similarity,”Psychological Review, Vol.100,No.2,April 1993.pp.254~278;D.L.Medin,R.L.Goldstone,& A.Markman,“Comparison and Choice:Relations between Similarity Processes and Decision Processes,”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Vol.2,No.1,1995,pp.1~19;E.Shafir,“Choosing versus Rejecting:Why Some Options Are both Better and Worse than Others,”Memory & Cognition,Vol.21,No.4,1993,pp.546~556;Itamar Simonson,Amos Tversky,“Choice in Context:Tradeoff Contrast and Extremeness Aversion,”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Vol.29,Issue 3,1992,pp.281~295。人们总是通过比较事物之间的异同来判定对自身的利害关系以及偏好。例如,生活中对某种事物的偏好,经济行为中对某种货物的偏好,外交决策中对某种选择的偏好,等等,都是通过比较而得出的。但是,这种比较并不总是理性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情感所决定。因此,情绪化比较是指国家行为体在进行比较时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很大,并不是进行纯粹物质上的比较和衡量。传统地缘政治学强调边际效应: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倍增。*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但是,这只是纯粹物质利益上的衡量。当今世界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人们一提到情感往往会想到它的负面作用。情感和理性被当作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置于完全不同的地位:理性是好的,情感是疯狂的。那么在现实中,真的存在绝对分开的理性和情感吗?“纯粹理性”早就已经被学者批判和当作为了进行推理便利的理想假设,很少有人会把它当作真的,“有限理性”取而代之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然而,这个有限的意义在于理性只构成人们赖以行动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是情感这个事实却被人们视而不见。在承认情感作用的学者中又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情感和理性是共同作用于行为的;二是认为情感是理性的根源。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即情感激起理性,成为理性的发端,并发展了理性;理性的力量是从情感那里得到的。实验表明因手术而失去情感后仍然保持认知能力的人无法再保持理性。*Janathan Mercer,“Emotional Belief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4,No.1,Winter 2010,p.3.同样,实验证明失去情感的人不会在乎社会规范的存在,也不会遵守。因此,可以说情感是先于认知的,是先于理性存在的;而社会规范的维持和遵守如果没有情感的作用也是无法做到的。很简单,没有情感的人根本不会在乎遵守规范与否带来的赞赏或谴责。对于他们来说,规范起作用的一个重要机制“通过点名而让其感到羞愧”根本不起作用。情感赋予事物以价值,而社会化则赋予事物以意义。先在的情感必然为后生的理性设定可以从中起作用的框架。可以这么理解,情感需求赋予世界上各种事物以价值,满足同一种需求的事物可能有很多种,那么社会化的职能就是根据理性从中挑选某些事物来满足情感需求。因此,社会化的实现在于成功地把合适的事物与情感的需求用意义连接起来。实际上,凡是涉及选择即什么是好的这样的问题时都无法绕开情感因素。同样,怎样维持既有合作也涉及情感问题。正如建构主义学者所探讨的如何内化规范的问题,在这里,不管是内化还是社会化,都需要情感的支持。前文所提到的实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之所以会认为规范是好的,应该遵守,是因为情感的作用而不是理性的衡量。在没有情感的基础上,理性也不会存在。
具体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当中,从地理身份来看,中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者,对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有着不同的身份特性。从地缘相近的东盟10国来看,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地理身份界定具有很大差别,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反应和积极程度也有明显区别,而南亚4国、太平洋8国对此的反应则更是各不相同,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态度差别巨大。情绪化比较也很明显体现在这些地缘临近的国家,有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响应比较积极,期望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也不会过于担忧建设推进过程中中国影响力的提升,而新加坡的态度则要暧昧得多。从地缘上看,东盟10国与中国之间有着相近的地缘因素和压力作用,但是由于主观上对彼此地理身份的判断不同,再加上情绪化比较因素的作用,对中国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认识和反应往往出现迥异的现实状况。
二、以公共外交推动构建情感共同体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自然主要包含经贸发展的内容,但是若要真正实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五通目标,在东亚区域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商共建共享”构成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链条,缺一不可。共商就是集思广益,由全球所有参与治理方共同商议;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发挥各自优势和潜能并持续推进建设;共享就是让全球治理体制和格局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球各个参与方。该理念由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2日下午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上提出。的全新治理模式,需要以情感共同体的构建实践打破地理身份和情绪化比较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地缘限制。否则,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同时,也无法形成对中国形象的正面认同,反而时时警惕强邻的一举一动,作出过于敏感的反应。共同利益的塑造并不一定能够形成共同体,而共同关系和情感的营造则是构建命运共同体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
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有一个与经济合作同样重要的目的是促进民心之间的相通,公共外交所推动的信息沟通和交流与经济合作一起契合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五通的战略目标。如果说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300多年的一个核心理念是理性,那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关系性(relationality)。*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页。关系性的内涵是过程,重视关系的中国社会必然强调过程,因为关系在过程中发生、发展并得以体现。而过程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培育集体情感。理性社会对情感的重视较低,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往往有意排斥情感的作用;而在关系性社会中情感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72页。对于公共外交来说,其目的在于提升本国的国家形象,扩大影响力。如果能够建立稳固的集体认同感,那么公共外交所传播的观念和文化自然就会得到对方的接受,甚至成为一个享有共同观念的情感共同体。因此,要实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所推动的“共商共建共享”全新治理模式,需要沿线国家积极参与和融入,而在这个参与过程中,就需要公共外交发挥交流和沟通的重要作用。特别地,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有一类跨国行为体值得关注,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群体,他们作为“既在此处,又在彼处”真正意义上的跨国行为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特殊的桥梁,可以发挥带动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充当公共外交实践主体的重要作用。
实际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在汉代已形成,主要由两大干线组成:一条是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路,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另一条是南海航线,也称南海丝绸之路,是西汉时始发于广东徐闻港到东南亚各国再到西亚直至欧洲的海上贸易黄金通道。目前已知有关中外海路交流的最早记载来自《汉书·地理志》,当时中国与南海诸国已有接触,而出土的遗迹实物则表明中外交流或更早于汉代。在唐朝中期前,对外主要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之后由于战乱和经济重心转移,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的主要通道,在宋元时期是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和东西方文化和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发生经济贸易往来的海上通道。纵观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它不仅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历史,而且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走向世界进而走向全球化的恢宏历史,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华侨华人群体在这个进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更确切地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正是华侨华人走向海外、对外经济交往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中国走向全球化实际上肇始于华侨华人的对外交往,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是全球化的一个端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首先是面向东南亚国家,这里也是华人华侨比较集中的地区,他们的产业布局集中在这里,主要经营方向也在这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华人华侨可以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裘援平称建设海上丝绸之路 华人华侨将发挥难以替代作用》,http://gb.cri.cn/42071/2014/09/24/5931s4704192.htm。随着中国走向全球化,华侨华人可以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有跨语言文化、熟悉当地法律环境和营商网络等优势。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途经我国江浙、福建、两广、云南和海南等地区。由于地理因素和历史原因,这些地区华侨众多,侨乡遍布。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我国海外华侨华人有60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多年发展,海外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和社会各界,影响渐增,人才辈出。沿线丰富的华侨华人资源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优势,也是对接沿线国家双向投资合作的关键纽带。
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充分重视华侨华人,利用华侨华人与海外国家历史联系的优势,推动各方全方位的交流和合作,共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合作共赢。华侨华人作为重要的跨国行为体,他们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此也高度重视。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支持海外侨胞积极开展中外人文交流”,同年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2011~2015年)》,首次提出“侨务公共外交”的概念,并将“拓展侨务公共外交”列为“十二五”侨务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经济合作并不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根本目的,只是启动的钥匙,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最终目标是要形成地区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化解中国在区域中的地缘困境,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结合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以公共外交为路径开展关系治理,推动情感共同体的实现将是可行的一个创新治理模式,其中华侨华人融合了经济和文化的双重特质,将会是这一实践过程中最具有活力的一个群体。
三、治理理念和实践的创新
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来说,可以从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分析。首先,在理念层面,前述公共外交和侨务公共外交所诉诸的理念,其根基是重在交流和沟通,意在维系关系和营造氛围,而不只是体现在经济层面的互惠互利。其次,从实践层面来看,海上丝绸之路推进过程不以传统的国家层面正式合作制度的确立或签署合约为主,而更多是以项目带动的强调过程的非官方或半官方合作,非制度性的探索型实践成为主要模式,民间在其中的参与程度和效率远远高于传统的国家交往模式。中国与东盟各国地缘相近,又是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必然存在较大的敏感性,这也进一步影响了地缘政治可以发挥作用的成效。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以分享中国发展红利作为利益驱动可以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但无法提供安全感,这是地缘因素所带来的最大压力。因此,本文提出的以公共外交推动构建情感共同体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我们应将关注点聚焦于人们对地理环境的主观因素构建,以此消解纯粹物质性的地缘要素在政治实践中的负面影响。
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应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与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0/13/c_1116812159.htm。因此,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一个区域合作的新模式,而更重要的是旨在解决治理成果失效、治理手段失灵、治理方向偏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对全球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行探索和实践。如今的世界格局更多不是由政府而是由超政府的治理机制决定。我们在讨论“一带一路”倡议时,其实是在讨论一种涉及全球多个国家、地区、社会和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韩梁:《外国人眼里的“一带一路”:模式创新区域融合》,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7/7080588.html。全球治理本身是一个协商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18页。这种参与和身份塑造的过程强调的是文化的彼此融合,“是各种文化的自在、共在、融合和共同进化,而不是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基于对彼此差异的理解和包容,通过公共外交活动中的信息交流,就很有可能达成这样一种“成熟的理解和适应”。*Ray Eldon Hiebert,“Commentary:Challenges for Arab and American Public Relations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a Global Age,”Public Relations Review,Vol.31,Issue 3,September 2005,p.318.由此,各国公众在全球化的相互碰撞之中逐步形成对他国和国际社会的主导性情感和认同,而这种情感和认同一旦形成就会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不仅对单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和交往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决定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取向。因此,承担着与国外公众和世界舆论沟通和对话任务的公共外交越来越为各国所重视。
综上所述,以公共外交推动构建情感共同体的实现是治理理念和实践的创新。情感共同体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甚至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构建情感共同体的过程本身就足以成为努力的目标——以非对抗的关系协调取代传统的利益驱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带一路”所提倡的这种“共商共建共享”区域合作理念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是一脉相承且逻辑呼应的,都是对全球治理模式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强调的是关系的维护和氛围的营造。以此思想为基础的治理理念不会将国际社会的个体成员视为被动的管理对象,而是注重这些成员在国际体系中彼此关系的协调,实际上更强调个体成员的主观能动性。*谢婷婷:《新型大国关系构建需治理创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16日,第4版。如果说“新型大国关系”强调的是以伙伴关系的推进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新兴大国与原有大国在全球的有序竞争和合作共赢,那么“一带一路”倡议所推进的同样是强调关系协调的共同体建设,突破地缘所带来的主观和客观压力,实现区域的合作共赢。
谢婷婷,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