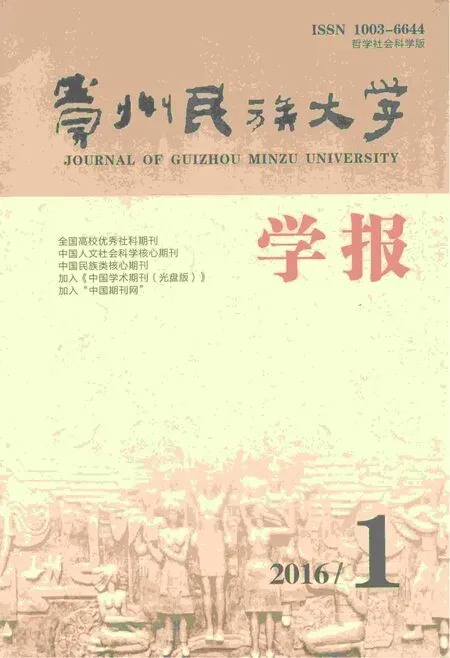把世界捧进纯洁、真实、永恒的境界———从《乡村医生》看卡夫卡的创作追求及其象征性表现手法
张 梦 瑶
把世界捧进纯洁、真实、永恒的境界———从《乡村医生》看卡夫卡的创作追求及其象征性表现手法
张 梦 瑶
卡夫卡惯于使用象征语言,来展现他对时代人生的切身体验,从而揭示人类生命所具有的本质性存在特征,以及人的生存所普遍具有的情感意愿、道德愿望、理想追求,以此实现他用文学创作探寻人生真理的艺术追求。《乡村医生》这部作品体现了卡夫卡在创作上形式与内容的完满结合。
象征语言;图像;主体人格;理性与非理性;精神创伤;生命的超越性追求
作者张梦瑶,女,汉族,河北唐山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在读博士(北京 100081)。
一、卡夫卡的创作追求
《乡村医生》是卡夫卡生前发表的作品中,自己较为满意的几个短篇之一(其它几个短篇是《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刑营》和《饥饿的艺术家》)。对这几部作品,卡夫卡在自己的日记、书信和谈话中,大多都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说明、评价。其中对《乡村医生》的评价是这样的:“我对如《乡村医生》这样的工作还能感到暂时的满足,前提是,我又成功地做出一点儿这样的东西(很不可能的)。但幸运只能是,如果我能把世界捧进纯洁、真实、永恒的境界。”[1]P421
“把世界捧进纯洁、真实、永恒的境界”,是卡夫卡文学创作的最高准则。那么,这个最高准则的实质性所指是什么呢?卡夫卡下面所说的话应该是对此所做的诠释:“文学要澄清纷乱复杂的刺激,把它上升为意识,加以净化,从而赋予它人性。”[2]P441;“诗人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3]P348;“作家的任务是把孤立的非永生的东西导入无限的生活,把偶然导入规律。他要完成的是预言性任务。”[4]P475这几句话所表达的观点是相互关联和一致性的:“纷乱复杂的刺激”是指纷乱复杂的生活现象,亦即生活中分殊有别、流转变化的各种人世景象——“事情”;“意识”即思想性认识;“加以净化,从而赋予它人性”是指通过对这些生活现象的切身体验和思考,从中获得对人性的真理性彻察。这样,“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无非是说,作家要通过切身的生存体验和理性的思考认识,澄明生活中各种纷乱变幻的事物现象,从中展现出具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人性特征,揭示生命存在的永恒真理,从而引导人的现实生存,即“把孤立的非永生的东西导入无限的生活,把偶然导入规律。他要完成的是预言性任务”。所以,卡夫卡也说:“创作是浓缩,是精华。它唤醒人们。”[5]P340;“艺术不是瞬即消逝的惊愕,而是长期起作用的典范。”[6]P465他这样评价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莎士比亚的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其实也是一部侦探小说。莎士比亚的《汉姆莱特》呢?那也是一出侦探戏。中心情节是:一个秘密逐渐被揭开。但是,还有比真理更大的秘密吗?文学创作向来都只是对真理的一次探索。”[7]P468这表明了卡夫卡的文学创作,目的在于对人性本真、人生真理的探究。卡夫卡对此也有过多次的申明:“我是一个爱编故事的人……当我反省自己的最终目标时,就会发现,我并没有努力去做个好人,没有努力去附和最高法官的要求,而是完全相反,通观整个人类和动物群体,以认清他们的基本爱好,愿望和道德理想,探究他们的一般规律,并且尽可能快地使我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段话分别出现在卡夫卡1917年9月28日日记、1917年9月30日致菲莉斯信和1917年10月致马克斯·勃罗德信中,只是译文因出自不同译者而有文辞上的差别。详见《卡夫卡全集第6卷·日记》第421页;《卡夫卡全集第10卷·致菲莉斯情书》第168页;《卡夫卡全集第7卷·书信·致马克斯·勃罗德》第225页。
二、以象征性图像揭示人真实的内在世界
一切生物有机体,外在的行为活动皆是受内部驱力推动发生的,而人类的生命,其内部实在是一个由情感、认知、目的或意义价值等方面构成的精神性(或意识性)活动系统。因而,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展现人的精神状态、揭示人的精神追求,可以达到对生命存在及社会生活的本真性认识。文学创作是探究、展示人类心灵世界的艺术,卡夫卡也确信通过文学艺术这一途径,可以寻获到生命存在的真实本相:“艺术围绕着真实飞翔,然而怀着坚定的意图:不让自身焚毁。它的能力是,在这片黑暗的空旷中找到一个地方,那儿能够在光线处于隐蔽状态的情况下,强有力地捕捉住它(即“真实”——引者)”[8]P960
那么,文学创作如何才能捕捉到生活的真实、展示人生的真理?在阐释意大利画家塞冈第尼的艺术创作观时,卡夫卡表达了自己的认识。塞冈第尼说过这样的话:“艺术不是那种存在于我们身外的真理。那样一种艺术没有、并且不可能有艺术的价值:它是、并且只能是对自然的盲目摹仿,就是说是物质自然的简单再现。然而,物质必须用精神进行加工,才能上升为永恒的艺术。”卡夫卡对此阐释说:“物质必须用精神进行加工。这是什么?这就是体验,不外乎体验和把握体验的东西。重要的是这一点。”[9]P460-461艺术家必须有对生活的切身体验,并借助某种艺术形式把他内在的切身体验形象地展现出来,这是文学艺术捕捉生活真实、展示人生真理的唯一途径,这也是卡夫卡所遵循的文学创作之道。
塞冈第尼是用色彩构成的图像展现内在的生活体验,卡夫卡则是用语言构成的图像展示他内在的生命体验。不过,卡夫卡的“图像”一般是象征性的,他惯常用动物故事、梦境或类似梦幻般的故事情节,以象征性方式来表现自己内在的生命体验。
美国当代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E.弗洛姆,曾经对以梦、童话和神话为代表的象征语言作过专门的研究,对这类象征语言的特征和作用有过如下的阐释:
象征语言是这样一种语言:其内在经验、情感、思想被表达出来,好像它们是外在世界的感官经验、事件一样,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白天讲话习惯逻辑的语言,象征语言的逻辑不是由时空这些范畴来控制,而是由激情和联想来组织。[10]P4
什么是象征?象征经常被定义为“代表其他事物的某种东西”。这个定义似乎有点令人失望。然而,如果我们关注于那些作为视、听、嗅、触等感官所表达的象征,关注那些它们代表的“其他东西”,亦即我们的内在经验、情感或思想,那么,这个定义就会更加引人入胜。这种象征是外在于我们的某种东西;但它所象征的却是我们自身之内的某种东西。象征语言是我们表达内在经验的语言,在这种象征语言中,我们的内在经验就好象是一种感官体验,就好象是我们的行为或作用于我们的物理世界。象征语言是这样一种语言,在它之中,外部世界是内部世界的象征,是我们的灵魂和心灵的象征。[11]P230
弗洛姆在这里指出,在象征语言中,“外部世界是内部世界的象征,是我们的灵魂和心灵的象征。”也就是说,象征语言是我们展示灵魂和心灵的方式。对象征的这种性质和作用,基督教存在主义思想家蒂利希也持相同的观点。在《文化神学》一书中,他在分析象征的作用时,指出象征的主要作用是“对实在层次的展示。实在层次如果不被展示就会隐藏着,并且不能以任何别的方式去把握它。”而所谓的实在层次,就是“灵魂的层次,我们内部实在的层次”。[12]P69-70卡夫卡在和雅诺施的一次谈话中也间接地表述了同样的认识:
雅诺施:“我以为,《变形记》是一个可怕的梦,一种可怕的想象(这里的“想象”是指作家的内在体验、主观认识——引者)。”
卡夫卡:“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蔽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的可怕的东西——艺术的震撼人心的东西。”[13]P324
这也是一个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对此,卡夫卡有透彻的认识:“形式不是内容的外在表现,而是它的刺激,是通向内容的大门和道路,这种刺激发生了作用,隐蔽的背景也就显现出来了。”[14]P459对于象征语言来说,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同样如此。
三、《乡村医生》对人内在世界的多重展示
从卡夫卡对《乡村医生》创作的自我评价看,这部作品,在以形式开启内容、以象征性图像揭示人的精神状态或“内部实在”这一道路上,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创作。
《乡村医生》中所叙述的故事,不是现实世界中可能发生的生活事件——它类似一个梦境(情节和人物活动不受现实生活中时空法则、思维逻辑、行为规则的限制),多数情节是超现实的幻景,如乡村医生在出诊前有两匹骏马和一个马夫从自家的猪圈里爬出、在出诊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迷离怪诞的事情等等。因而可以说,卡夫卡在《乡村医生》中,典型地使用了弗洛姆所阐释的那种象征语言。
(一)黑夜、严寒——时代生活的心灵体验
作品中,从事件的发生到结束,主人公所身处的始终是一个由暗夜、暴风雪、茫茫雪原构成的寒冷迷茫的时空界域,这样的时空图景象征着什么?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有一句表达自己生活感受的话:“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寒里,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赤裸着身体,坐着尘世间的车子,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我的皮大衣挂在马车的后面,可是我够不着它,我那些手脚灵活的病人都不肯助我一臂之力。”[15]P459而卡夫卡自己在和雅诺施的一次谈话中也直言过自己对时代生活的内心体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奇冷无比的世界,而我们既没有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基础,也没有他们的裘皮大衣和其他为生存而必备的辅助手段。和他们相比,我们大家都是赤身裸体的。”
再看他最重要的作品《城堡》的开头,那寥寥数语、意境深远的环境描写,同样也是以大雪严寒的黑夜,隐喻了主人公所置身的时代生活:“K到达时,已经入夜了。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堡山连影子也不见,浓雾和黑暗包围着它,也没有丝毫光亮让人能约略猜出那巨大城堡的方位。”
(二)乡村医生——主体人格的理性化、道德化及其生存困境
现代心理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通过对人心理活动、自我意识状态的深层研究,发现了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者,其内在的自我结构具有多重性和不稳定性。换言之,也就是主体人格或以自我意识为中性的经验性人格具有多重性和不稳定性。卡夫卡在大学时代及其后,对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对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和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有过深度的涉入,也因此,他的作品精于从主体人格的多重性及不稳定性上揭示人的内在世界,表现时代生活。
《乡村医生》的主人公是一个拥有现代医学知识和技能、受聘于乡村社区的公职医生,一个典型的为公众服务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理性的化身,而他的人格主体也确是理性化和道德化的:在私人生活中,他摒弃官能物欲、情欲,一直过着清寂淡泊的独身生活,既使家中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佣和他同处,也只是充作日常生活的帮手;在公共生活领域,“我是这个地区雇佣的医生,非常忠于职守,甚至有些过了分。我薪俸微薄,但却慷慨大方,乐于帮助穷人”。小说中,他在风雪漫天的冬夜,无马驾车去十几里外出诊而焦急万分的情境,也表明了他的“忠于职守,甚至有些过了分。”
摒弃个人的物欲、情欲,服务于国家和公众生活,在西方世界,是传统的柏拉图理性主义人生观和基督教人生观所遵循的理性抑或信仰的生活方式。就卡夫卡自己而言,他的生命价值观也是柏拉图主义的:“除了一个精神世界外,别的都不存在,我们谓之感性世界的东西,不过是精神世界中的邪恶而已,而我们谓之恶者,不过是我们永恒发展中的一个瞬间的必然。”[16]P328而乡村医生的形象也有现实生活中的影子:卡夫卡的五个舅舅中,有三个终生独身,这其中一个是西班牙铁路局局长,一个是酿酒厂的记账员,一个是乡村医生。尤其是这个医生舅舅,其性格和道德操守都让卡夫卡喜爱和尊敬。
但现在这个以理性化和道德化方式生活的人,生存陷于巨大的困境中。这种困境既出现在外部、在公共生活领域,也出现在内部、他个体的生命状态中。
外部的生存困境,是他的公共服务性工作和道德人格并不被社区居民理解和支持:暴风雪之夜,他急于去十几里外的地方救治危重病人,自己的马在昨天严寒的冰雪里因劳累过度而死了,现在女佣跑遍整个村子却无人肯借马给他提供方便。
外部的生存困境,也使他自身的生命存在产生了剧烈的内部分裂、冲突。小说开头部分,首先以象征的图像,揭示了主人公主体内在自我的结构性分裂和冲突:
雪愈下愈厚,愈等愈走不了了。……我又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不知所措。我心烦意乱,苦恼不堪,用脚踢了一下那已经多年不用的猪圈的破门。门开了,……有个人在这样低矮的用木板拦成的地方蹲着,露出一张睁着蓝眼睛的脸。“要我套马吗?”他问道,匍匐着爬了出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弯下腰来看看猪圈里还有什么。女佣人站在我的身边。她说:“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家里还会有些什么东西。”我们两人都笑了。
“喂,老兄,喂,姑娘!”马夫叫着,于是两匹强壮的膘肥的大马,它们的腿紧缩在身体下面,长得很好的头像骆驼一样低垂着,只是靠着躯干运动的力量,才从那个和它们身体差不多大小的门洞里一匹跟着一匹挤出来。它们马上都站直了,原来它们的腿很长,身上因出汗而冒着热气。“去帮帮他忙。”我说,于是那听话的姑娘就赶紧跑过去,把套车用的马具递给马夫。可是她一走近他,那马夫就抱住她,把睑贴向她的脸。她尖叫一声,逃回到我这里来,脸颊上红红地印着两排牙齿印。“你这个畜生,”我愤怒地喊道,“你是不是想挨鞭子?”但是我马上就想到,这是个陌生人;我不知迫他是从哪儿来,而当大家都拒绝我的要求时,他却自动前来帮助我摆脱困境。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所以对我的威胁没有生气,只顾忙着套马,最后才把身子转向我。“上车吧!”他说。的确: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我注意到这确实是一对好马,我还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好马拉过车呢,我就高高兴兴地上了车。“不过我得自己来赶车, 因为你不认识路。”我说。“当然啰,”他说,“我不跟你去,我要留在罗莎这里。”……“你同我一道走,”我对马夫说,“否则我就不去了,即使是急诊也罢。我不想为这事把姑娘交给你作为代价。”
“驾!” 他吆喝道,同时拍了拍手;马车便像在潮水里的木头一样向前急驰;我听到马夫冲进我屋子时把房屋的门打开发出的爆裂声,接着卷来一阵狂风暴雪侵入我所有的感官,使我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但这只是一瞬间的工夫,因为我已经到了目的地,好像病人家的院子就在我家的院门外似的;两匹马安静地站住了;风雪已经停止;月光洒在大地上;……
医生借不到马匹,自然无法在暴风雪的冬夜去治病救人,这使主人公理性化一面的主体人格陷于无能无力之境;但道德化一面的主体人格又催迫他应该立即去救治病人——这样,理性和道德有了冲突。理性的特征在于它越纯粹、越有力,就越压制、排斥情感;而道德意识的特征在于它越纯粹、越强烈,就愈有深厚的情感根基,就越不受理性的制约,就越趋向感性、激情。此时,主人公的理性受限,强烈的道德意志使他内心的意识活动非理性抑或感性化,下意识性地驱迫他释放生命的潜能和激情去冲破行动的障碍——在这幅由非理性意识活动形成的梦幻般图景中,主人公实现了理性所无法达成的意愿。这幅图景有如弗洛姆所说,事件的发生和人物活动都不受现实世界中自然法则、时空秩序、行为规则的限制,它深度展示了主人公内在的生命状态、情感愿望和矛盾冲突——理性的有限性及其对情感的俯就、生命中超越性激情的爆发、非理性的生理情欲的冲动……全部呈现出来。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有一个关于灵魂的著名喻说:灵魂好比一个双轮两驾战车,理性是驭马者,双手抓住白色骏马和黑色骏马的缰绳,白色骏马代表人的激情(或勇气),对理性的命令较为驯服,黑色的骏马代表着欲望或情欲,难以驾驭,必须受驭手鞭挞才肯循规蹈矩。在这个关于灵魂的神话喻说中,唯有驭手戴着人面,而人的其他部分,即非理性或感性部分,则以动物形体出现。柏拉图崇尚理性,视理性为人的神圣部分,它脱离人身上的动物性,是生命的本质性存在,而人的非理性或感性部分,必须受理性的驾驭:这样,理性、激情、欲望三者协调一致,人的灵魂(生命)就能在现世中达到完善的存在的境界。
卡夫卡一生对西方哲学、心理学有广泛的涉入,尤其是柏拉图理性主义思想传统对他有较大的影响。但卡夫卡的思想特质在于,他总是基于自己对人生的切身体验,反省和接纳传统思想,力求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在自己对现实人生的观察思考中,确认、把握生命的本真。这个象征图景无疑有柏拉图关于灵魂喻说的影子,但却是卡夫卡自己思想的象征性表达:骏马象征的是生命内在的超越性激情(追求生命超越性的情感自我),这种激情首先是要超越理性的有限性和自然法则对生命存在的限制——是这两匹骏马驾车在暴风雪的寒夜,载着乡村医生飞驰过漫漫雪原到达了十几里外的病人住地;其次是要超越世间的尘俗人生——小说中主人公明言骏马是上帝(神)送来的,是“非人间的马”,也正是这两匹马在病人死去后载着他逃离乡村、驶过雪原,丢掉了原有的职业、家和尚留在家中的姑娘罗莎、马夫,而四处流浪。用“神马”象征自我生命中追求超越性存在的意志性情感力量——“激情”,在卡夫卡遗留的作品中也出现过:“我们吃惊地看着这匹大马。它冲破了我们小屋的房顶。多云的天淡淡地沿着它强大的轮廓移动,鬃毛在风中沙沙作响。”[17]P48
而马夫从猪圈里爬出后的言行,则隐喻了生命机体的生物性能量和情欲(生理情欲自我):是他为医生套好了马车并放马驾车出行,也是他见到美丽的姑娘罗莎后爆发了强烈的性冲动和占有欲,先是粗鲁地猥亵罗莎,然后又抗拒医生一同前行的指令,无所顾忌地留下来要强行占有罗莎。
生命内在的超越性激情和生命机体的生物性能量及情欲都植根蛰伏在人的感性肉体之躯中(马夫呼叫两匹骏马时称其为“兄弟”,暗示了他们的同胞关系)。因此,“猪圈”无疑隐喻了人的物身肉体,小说中罗莎嘲讽医生的话——“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家里还会有些什么东西。”——也点明了这一象征的隐含义。“猪圈”是动物居处,也是污秽肮脏之所——这个隐喻既表征了植根于“猪圈”的人的生物性情欲具有低级、自私、卑污、丑恶的属性,也表征了人的超越性激情是非理性的、以及由非理性可能导致破坏性或毁灭性的恶。看一看今日世界仍在频频发生的各种大规模恐怖性“圣战”,就可以理解人的非理性激情,如果失去普世伦理道德的监控,就会导致邪恶。
人的生命,其内在世界是由理性和非理性的情感(超越性激情)、欲望(官能情欲)构成的整体性实在。在这个整体性存在中,理性和非理性两极之间的平衡统一是生命得以健全存在、完善发展的基础或前提。在这幅图景中,主人公的内在世界或主体的人格是处于分裂和冲突中的:理性(自我)无力、失去驾驭主体行动的能力;超越性激情(自我)爆发并引导主体的生命意志;而随着感性能量的冲动,动物性本能的情欲(自我)也肆意释放出来,不再受理性或道德的约束。
“人是理性的动物”——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始,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主流一向推崇人的认知理性,确信人在认知理性的主导下能够实现生存的完满。这种对人理性能力的乐观和信任,忽视了人内部根深蒂固的非理性激情和本能情欲的强大冲动力。启蒙时代的康德哲学虽然阐明了认知理性的有限性,并期望以普适性的价值法则(自由与道德法则)及立基于普世价值法则的宗教信仰促成人的超越性追求,驾驭人的动物性本能欲求。但康德哲学的价值观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他的普世性价值法则也止于纯粹的理论性说明,难以落实到具体的生存实践中;他所期冀的立基于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宗教信仰在西方世界也并不存在——这样,康德哲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统一、在自由与超越性存在这些问题上,仍没能给人的现实生存打开一条通路。这也是“乡村医生”所面临的自我存在的困境。
(三)对病人的误诊及离弃——理性的有限性和生命存在的情感体验张力
小说的第二幅图像,是医生诊病的过程。病人的居室封闭、陈旧、空气污浊(让人联想到前面出现过的“猪圈”)让医生有难以呼吸的窒息之感;病人是个少年,他的体温正常,只是很瘦、两眼无神;更怪异的是少年见到医生后,竟坐起身来,抱住医生的脖子,悄声对他耳语说“让我死吧!”。这一连串相关联的现象,都表明了少年患有严重的心理或精神疾病,生命失去活力、生活陷于绝望,但医生竟囿于自己的职业阈限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病人及环境的反应是机械性的——打开诊包,寻找医疗用具——这无疑隐喻着科技理性(科学知识、科学的认识方式)对的人精神存在领域是一个盲区。
医生理性能力的有限及受感性力量的影响还表现在接下去的诊病情景中:他此时找不到合适的医疗用具,而且还心不在焉、心猿意马:既被离家前后遭遇到的事件干扰着——面对病人,心里想的却是那两匹马的来由、难以驾驭和留在家里的马夫、罗莎,以及如何立即救出罗莎;又被动地受眼前事件的牵引——他不由自主地顺从着病人的姐姐、父亲和母亲请求他诊病的意愿。而他的心意烦乱也导致了一连串的错误判断(马从窗外先后两次把头伸进屋子做出不同的举动,都意在督促他诊断病情,但他却误以为催促他回家;然后又断定少年身体健康,是因为懒惰而卧床装病)。对病情的误判进一步引发了他内心深处的恶劣情绪——他开始悲叹自己在工作上忠于职守却薪俸微薄,哀怨自己对穷人的乐善好施及还要养活女佣罗莎而负担沉重,他此时竟认为“这男孩想死是对的,因为我自己也想死”——“善在一定意义上是绝望。”接着他又抱怨起自己在公共服务中的付出和艰辛得不到乡民的理解和帮助,怨恨社区居民总是在夜里按响门铃求诊,使他倍受折磨;他进而觉得此次为救治病人而“牺牲掉了罗莎”这个漂亮的姑娘的代价太大了,于是决定立即回家。医生此时的心理状态、意识活动,使人想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人的实存(“此在”)的时间性和情绪性特质的揭示——人的生命是具体的存在于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构成的连续性的时空界域中的,人的意识对这个时空界域内事物的反应是情境性和历时性的,这种情境性和历时性反应所产生的情感体验影响着主体对当下的认知和行为活动。
(四)致命创伤与无药可治——信仰缺失、生命根基的创伤
在医生收拾行装欲离开时,少年家人们失望、恳求、痛苦的神情及行为举动又感染了他,使他的道德人格浮现到前台并控制住了那些非理性负面情绪,他也恢复了正确的认知和判断能力,不但决定留下来再次检查病症,也意识到两匹马此时的又一次嘶鸣是催促他检查病人——这一次他也发现了少年确实有病:在他的大腿根部有一处已腐烂生蛆的硕大伤口。
作品中对伤口的描述,无论是它的位置还是它的状态,都显示这是致命性的伤口。卡夫卡在《致某科学院的报考》中写过主人公大腿根部遭受致命枪击的伤口;在一封给勃罗德的信中也把自己的肺病和《乡村医生》中这个少年的伤口联系起来,认为自己的肺病是致命的,且病根出在精神上。
小说中的一些情节也多方面显示着这个致命的伤口是精神创伤。少年对医生说:“我带着一个美丽的伤口来到世界上;这是我的全部陪嫁”。这个“美丽的伤口”无疑是指自我生命在精神上的发育、成长受到伤害,无法获得内在生命的自我实现抑或无法实现精神自我的超越性追求——亦即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所说的“出生创伤”。正因为这个伤口是精神创伤所致,所以它的形状、颜色非但不丑陋,还有如一朵盛开的红玫瑰那样美丽。
小说中的情节也暗示了造成这一精神创伤的根由:一是少年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和群体中;其次是对这个没有信仰的时代生活,少年过于敏感和痛苦,而一般人则处在麻木不觉中,所以医生才如此劝慰他:“你的缺点是不能总揽全局。我这个人去过附近所有的病房,我告诉你,你的伤并不那么可怕。伤口比较深,是被斧子砍了两下所致。许多人将半个身子置于树林中,却几乎听不到林中斧子的声音,更不用说斧子向他们逼近。”
然而可悲的是,面对这一致命的精神疾患,病人渴望得到救治而医生却医治无方。医生不能救治病人,是因为他也如同这个病人一样缺失信仰,缺失生命得以植根立足的精神家园。对此,医生自晓,病人亦明。所以,当医生被乡民剥光衣服、按倒在少年身边,强行要求他治病时,少年竟对他有所鄙视和怨恨:“我对你很少信任。你也不过是在某个地方被人抛弃了而不能自救。你不但没有帮助我,还缩小我死亡时睡床的面积。我恨不得把你的眼睛挖出来。”而医生也只能报以歉疚:“你说得对,这的确是一种耻辱。但我现在是个医生,你要我怎样呢?相信我,事情对我也不容易。”
卡夫卡在向密伦娜解释自己的内心为什么对时代生活总是充满巨大的恐惧感时,曾说过:“你说,你对此不能理解。假如你把它看作疾病,你就试着去理解它吧。这是心理分析学自称揭示了奥秘的许多病理现象中的一种。我不把它叫作疾病,我把心理分析学的治疗学那一部分视为一种不可救药的迷误。这一切所谓的疾病(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悲惨)都是信仰的问题,是处于危难中的人在任何一片感到亲切的土地上落脚扎根的问题。”[18]P417-419
(五)渴望得到救治的病人们和不能自救的医生
处于危难中的人们渴望“在任何一片感到亲切的土地上落脚扎根”——作品中,那个重病少年是如此,那些社区乡民也是如此——他们渴望获救的愿望是那样的强烈,以致强行逼迫医生治愈病人,这实在是危难中急于求生又无路可走的愚妄之举,就像医生所说:“住在这个地区的人都是这样,总是向医生要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已经失去了旧有的信仰;牧师会在家里一件一件地拆掉自己的法衣;可是医生却被认为是什么都能的,只要一动手术就会妙手回春。”
而医生自己呢,面对这样的时代生活和人的生存困境,就如他对少年所言:“我现在是个医生,你要我怎样呢?……事情对我也不容易。”——他只是个能治疗人的生理疾患的医生,他在这方面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既无力救治别人,也不能为自我生命找到一块落脚扎根的土地。小说的结尾,当医生在少年死去后,飞身上马,逃离乡村,急于返程回家去救罗莎时,两匹马却带着他在严冬的荒野上漫无边际地流浪。这一幅图像再一次展示了主人公主体自我的内在分裂及他对生命超越性存在的渴望:作为理性化、道德化一面的人格(自我)意欲返归到现实的社会人生中,他要救罗莎、要守住自己的职业,从而延续原有的生活方式;而追求生命超越性存在的激情(渴求人生终极归依的超越性自我)却不愿回到世俗生活中来,它要寻找一种可以满足这种强烈的情感愿望的生活方式、一块使这一超越性自我落脚扎根的土地——“坐在人间的车子上,而驾着非人间的马,到处流浪。”
人在现世的生存中,依靠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才能达成生命的超越性存在,从而获得人生永久的精神家园?——作品在围绕着精神创伤的情节展开中,无疑指向了某种展现了人生的终极真实、实现了生命终极价值的信仰化生活。这种信仰化的生活,就如康德的道德哲学所阐释的,应该是以普世的伦理道德和人的自主自由为基础的,既超越了人的生物性“自我”、也超越了以个体自我为中心的“小我”的信仰化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可以使人的内在世界达到理性与感性的平衡统一,使人的主体存在达到精神与肉体的和谐统一,使个体自我和群体他人及整个世界达到和谐统一。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坐在人间的车子上,而驾着非人间的马”,却不必“到处流浪”。但亦如康德哲学没能在实践上为人的现世生存找到这种信仰化的生活一样,“乡村医生”也不知道这种信仰化的生活在那种途径上能得以实现。
在现世生存中,人能够找到、并实现这种信仰化的生活方式吗?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却没有找到。但卡夫卡的同时代人,也和他同样出自德语文化区的阿尔伯特·史怀泽,以其“敬畏生命”的伦理哲学和终生践行,实现了那种超越性的生命存在。史怀泽的生命实践,可以让我们加深对“乡村医生”、对卡夫卡生命存在及人生追求的理解。
四、卡夫卡象征性表达方式所达到的普遍性高度
可以说,在《乡村医生》这个短篇中,卡夫卡借助一幅幅象征性的图像,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对时代生活、对生命存在的切身体验。作品透过对主人公心理状态、意识活动的深度揭示,展现了人的生命所具有的本质性存在特征,以及人的生存所普遍具有的情感意愿、对生命超越性存在的向往、对精神家园的渴求。这部作品在使用象征性表达方式时所达到的展示人生的程度,正如他所言,把世界捧进了“纯洁、真实、永恒的境界”。
卡夫卡终身的精神密友马克斯·勃罗德,对卡夫卡习惯于象征性的艺术表达曾做过如下的解释和评价:
为什么他作为作家始终只通过譬喻、只通过寓意或象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首先应该承认卡夫卡式思维方法的独特性,这种思维是在图像中,而不是在推理中展开的。即使在对话中、在辩论中这种图像也笼罩着一切。
卡夫卡从不用寓言,但在象征性方面却达到了最高程度。……象征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所代表的和意味着的东西,但同时也作为它自身、它具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它对我们叙述事件,并通过这种具体的叙述、这种特殊事实过程的呈现来表达某种遥远的、普遍的东西。……象征是精神上的出发,是使个别的有限之光射入无限之中的一种活力。人们便根据这道光线照耀切面的距离,可以感到这里涉及的是个性的、民族的或人类的事情。
卡夫卡报道的事件当然首先意味着事件自身,但同时却不仅仅是自身。从每一个细节中都放出一道光芒来,照耀着永恒,照耀着超越感官直觉的境界,照耀着理念的世界。这种通过人间的形式照耀永恒的现象在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中都存在着。可是在卡夫卡这儿,它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形式上的原则,简直无法将紧密结合着的内容和结构区分开来。[19]P76-77
勃罗德的上述解释和评价,有助于我们解读《乡村医生》、理解卡夫卡的创作追求及其象征性的艺术手法。
[1][2][3][4][5][6][7][8][9][13][14][15][16][17][18]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0]埃里希·弗洛姆.被遗忘的语言[M].郭乙瑶,宋晓萍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2007.
[11]黄颂杰主编.弗洛姆著作精选·被遗忘的语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2]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M].陈新权,王平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19]马克斯·勃罗德.卡夫卡传[M].叶廷芳,黎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杜国景
BringingtheWorldintoanAtmosphereofPurity,TruthandEternity:Kafka’sCreationPursuitandSymbolicDevicesin“ACountryDoctor”
ZHANG Mengyao
Kafka is good at using symbolic devices to display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imes and life, to reveal the features of human life, show common human emotions, moral desires and ideals, and to realize his pursuit of art through literary creation. “A Country Doctor” embodies his union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
symbolic device; image; subjective personality; rational and non-rational; psychic trauma; transcendental pursuit of life
I06
A
1003-6644(2016)01-007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