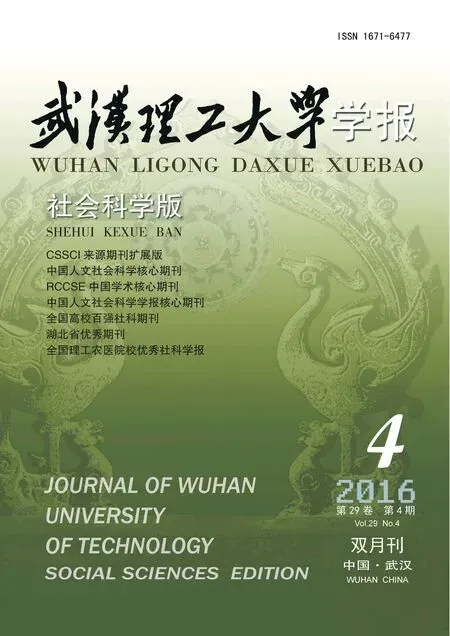论王安石道本体之嬗变*
胡金旺
(宜宾学院 历史与哲学研究所,四川 宜宾 644000)
论王安石道本体之嬗变*
胡金旺
(宜宾学院 历史与哲学研究所,四川 宜宾 644000)
王安石学术活动的前期是从儒家的立场来阐述他的天命、性等哲学范畴,只是认为佛道思想与儒家的天命寂然不动的思想有相近之处。总体而言,在前期,王安石对佛道思想的基本态度是排斥,而不是调和。但是后期王安石从天道的无声无臭来吸收佛道思想。因而,在道本体上,儒家的立场逐渐淡化,以至于认为佛道思想在道之体上与儒家一样,于是对佛道思想的基本态度由排斥转变为调和。当然,王安石在外王上对佛道仍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学界动辄以一种笼统的调和论来概观王安石的思想,是没有对其思想前后嬗变与分期作细致辨析的结果。从哲学史上看,对王安石道本体嬗变的正确认识有利于我们把握安石学术与二程学术关系演变的根源。
王安石;道本体;无思无为
一
我们将可以确定为王安石前期及后期与道本体思想相关的作品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其道本体的思想并非是前后一脉相承的,而是有了明显的演变。这些与道本体有关的早期文章有《答陈柅书》、《涟水军经藏记》与《答曾子固书》等,后期论述了道本体思想的文章有《老子》、《致一论》与《洪范传》等。
在《答陈柅书》[1]1383-1384中,王安石写道:“庄生之书,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祸福累其心,此其近圣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读圣人之说,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于周之说,则其为乱大矣。墨翟非亢然诋圣人而立其说于世,盖学圣人之道而失之耳。虽周亦然。……老、庄虽不及神仙,而其说亦不皆合于经,盖有志于道者。圣人之说,博大而闳深,要当不遗馀力以求之。是二书虽欲读,抑有所不暇。某之所闻如此,其离合于道,惟足下自择之。”王安石认为庄子“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祸福累其心,此其近圣人也”,即是说庄子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性命道德之说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它们只是与圣人之说相似,而实质上还是不同。因此,如果以为老、庄在道本体论上与圣人有相似之处就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地加以全然信服,就不能对其与圣人相睽违之处加以批判,就会将圣人“博大而闳深”之道与老庄之道混为一谈,最终就会与圣人之道渐行渐远。所以,王安石告诫友人要对老庄之说慎加抉择。李之亮先生认为,这篇书信作于庆历五六年间[1]1384,从其内容和王安石与陈柅的交游来看,是比较可信的判别。这篇书信表明王安石早年站在儒家圣人本位立场上对老庄的道本体论是持批判态度的。
而在写于庆历年间的《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中[1]1603,王安石也表达了相似的思想。他说道:“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既以此为教于天下而传后世,故为其徒者,多宽平而不忮,质静而无求。不忮似仁,无求似义。”王安石认为老庄与佛教在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上是有见的,这与儒家思想有相近之处。所以其徒“不忮”“无求”,这一点与儒家仁义相似。王安石是从佛道之徒有近似于仁义的表现而肯定佛道在无思无为上是有见的,所以,其无思无为是儒家的,是从仁义表现出来,与上文的不累于生死也是从儒家的思想表现出来的一样。仁义等内容是根本,其表现只不过是形式罢了,而佛道只是在这个表现形式上近似于儒家,其实质则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对佛道的思想持高度戒备的心理。可见,王安石早期是从儒家的仁义思想和立场上来看待佛道思想,因而对佛道本体论提出批评是必然的事情。
在同样作于庆历年间的《答曾子固书》中[1]1265,王安石说道:“杨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其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1]1264王安石明确表明异学不能乱其道,对其有所去取,是为了更好地阐扬儒家的大道而已。而去取的标准就是前面几篇文章所阐述的,坚持儒家的实质内容,而对佛道在形式上的相似性也予以认可。
王安石在后期作品《老子》中阐述的有关道本体论与前期此方面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该篇中,他说道:“道有本有末。……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故圣人唯务修其成万物者,不言其生万物者,盖生者尸之于自然,非人力之所得与矣。老子者独不然,以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为也,故抵去礼、乐、刑、政,而唯道之称焉……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1]1083-1084如果我们将此文与以上所提到的几篇杂论作一对比,其中有关道本体的变化就立即显现出来。在前期,王安石虽然对佛道之本体与儒家道本体的相似性有所认可,但是对它们差异的界限是严加坚守的。王安石认为儒家圣人之道与佛老之道有着实质不同,对佛道道本体总体上是持批判态度,告诫学者不要沉溺其说而远离圣人之道。而在《老子》这篇杂论中,王安石虽然对老子消极无为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但是却以先入为主的方式承认了老子的道本体,即王安石是在认可老子无为的前提下再来批判老子反对有为的消极的遁世态度。这充分表明王安石认可了老子的道之本,只是对其在道之末上不致用的做法加以批判。这表明,与前期相比,在后期王安石对佛道的内圣思想是认可的。而这种认可是在与其对佛道思想外王上的批评同时进行的。一方面王安石要用此表明他虽然接受了佛道内圣之学的思想,但还是有儒家立场的。一方面他也是通过此内圣外王的兼重力图构建其圆融的思想体系。这也是王安石对佛道既受之又批之的根本原因所在,接受的是它们的内圣思想,而批评的是其对外王的放弃。他在《老子》中对佛道本体态度的转变是其新学长期以来对佛道思想接纳的一种总结,也是其道本体论思想转变的一个明显表现。由此,我们可以根据王安石在《老子》中的思想而分析其思想的转变和相关杂论的写作时期。
二
我们先讨论王安石前期道本体论的特色。治平四年,王安石在《太平州新学记》中写道:“盖继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积善而充之,以至于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推仁而上之,以至于圣人之于天道,此学者之所当以为事也,昔之造书者实告之矣。”[1]1572天道是人道遵循的终极本源,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本体。不断遵循天道的人道就可以达到一种“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的境界,即体认到了道本体。
这里的“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与前文所说到的“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都是对天道无为特点的描述。很显然,王安石对天道无思无为特点的认识受到了孔子“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的影响而认为天按照它自身的规则运行,不需要有思有为。这种无思无为表明天看起来的有为就是无为,因为天所做的即是自身规则的体现。而在人间世界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完全符合天道,即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就与天的无思无为的实质完全一致了。所以天这种无为是作为它自然天成不需历练而言,原因在于天道为自己立法,并且不会违背自己的立法精神。天道相比人需要锤炼方可由有为达到无为就是一种形上的存在,就是一种无思无为的本体。人遵循了天命的有为实际上就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无为,因为有为是按照天道无为的准则去做的,但是人一般很难使其有为与无为完全一致,因此,一般人难以做到完全无为的程度。虽然从性与天道为一[2]的意义上讲,天道为自己立法,人道也是为自己立法,人遵循人道即是遵循了天道。但是人由于后天习染的影响而不能完全遵循人道,因此也就不能完全不需磨练就可遵循天道。所以,人是有为,是竭力要使自身的有为与天道的无为相一致。人道从总体上看是有为而非无为。
天道本体表现出的无思无为特性并非意味着其本质是无,恰恰相反,天道是有实质内涵的,而无思无为只是其实质内涵的外在表现。
天道本体的实质内涵首先表现为正义性和崇高性。王安石在作于庆历年间的《推命对》中说道:“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贤者治不贤,故贤者宜贵,不贤者宜贱,天之道也;择而行之者,人之谓也。天人之道合,则贤者贵,不贤者贱;天人之道悖,则贤者贱,不贤者贵也……”[1]1128“贤者宜贵,不贤者宜贱,天之道也”;人道符合天道,则人间秩序就是合理的,反之,则相反。可见天道的精神实质是正义和崇高的,人道只有副天道,才能够使天命流行于人间,从而避免德福错位的情形。这种具有精神实质内涵的天命富有鲜明的儒家特色,为道德性命的崇高性提供了形上依据,成为道德性命的终极根源。这一点我们通过下面考察天与道德性命之间的关系更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在谈到天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时,王安石在作于治平年间的《九变而赏罚可言》中说道:“万物待是而后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不属之天者,未尝有也。”[1]1049在作于嘉佑五年的《答王深甫》中,王安石也说道:“明其性命莫不禀于天也。”[1]1220
由以上二则引文可见,王安石认为天命都是道德性命之根源。既然道德性命都是禀于天,而天实质上是崇高和公正的。因此,道德性命从根源上讲其本质都是积极正面的。所以,在作于治平初年的《再答龚深甫论语孟子书》中,王安石说道:“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则命有顺有逆,性有善有恶,固其理,又何足以疑?”“夫古之人以无君子道为无道,以无吉德为无德,则去善就恶谓之性亡,非不可也。”[1]1217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凶,性有善恶,这是道德性命在现实层面的表现。道德性命多样性的表现由后天的习染所形成[3]。但从本质上讲,道是“君子道”,德是“吉德”,则性为“善”。
从道德仁义的一致性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安石虽然认为道德性命在现实层面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在本质上又是至善的。在作于治平元年的《答韩求仁书》中,王安石说道:“韩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义之无以异于道德,此为不知道德也。”[1]1202仁义是善的,而道德无以异于仁义,因此道德也是至善的。
总括而言,王安石学术活动的前期从天命到道德性命以至于仁义的看法全面地体现出其思想的儒家特色。天道的精神实质是崇高和正义的。天道的这种形上实质决定了形下的道德性命的含义的积极正面性。但是由于人之后天习得的影响,因而道德性命就表现为多样化的情形。人如果能遵循天命的精神特质就能够实现道德性命的本质特性。人通过这种有为就能体认天道的无为精神。儒家无思无为是指遵循天道精神有为后的无为,是有思后的无思。所以,王安石才说有思,然后无思才可无不得。人道的无为是指践履天命到了一个 “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程度。王安石批判了佛道贬低有思而片面追求无思无为是一种没有实质内涵基础之上的无思无为,因而前期王安石认为佛道思想只是在形式上与儒家思想相近罢了,自然就认为佛道没有儒学的闳深博大。因而,在学术上对佛道思想的吸取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对佛道总的态度是排斥而不是调和,盖王安石完全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看待佛道,坚持了儒学的本位意识。因而学界动辄以一种笼统的调和论来概观王安石的思想[4],是没有对王安石思想前后嬗变与分期作细致辨析的结果。
三
王安石在学术活动的前期认为佛道在“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上是有见的,所以其高尚之士的品行与圣人弟子有相近之处。庄子在“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祸福累其心”上与圣人之教也是接近的。但同时认为佛道不可能有儒家入世的精神,因而在精神实质上佛道与儒家大异其趣,这也导致了它们在道本体上与儒家的差异,而只是在形式上相近罢了。因而,从总体上讲,王安石在前期对佛道之体是持批判的态度。而在变法以后,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学派却对佛道持公开吸收的态度,注释佛道经典也是不遮不掩[5],毫无顾忌。俨然以不加选择的态度视之,而放弃了前期告诫友人要对佛道思想慎加择取的态度。正是出于对佛道本体的认同,后期王安石对道本体有较多的提及和论述,力图以此来吸收佛道思想,同时调和三教之间的关系。这比起前期对道本体只是偶尔简单涉及要详备得多。同时,为了与佛道出世与遁世的态度区分开来,他对佛道放弃致用的做法进行强烈的批判,这一点在前期反而很少出现。这表明王安石愈是在内圣方面要容纳与接受佛道思想,愈是要突出儒家与佛道在致用上的差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外王上使得儒家与佛道判然两别,从而不至于被批为阳儒阴释,又能在内圣的相同上做到对佛道思想公开大胆的接纳。我们如果从这个框架理解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以及对佛道二家态度的嬗变就能更加全面与客观。
前文说到王安石《老子》一文是透露其道本体论嬗变的关键篇章。在该文中王安石由前期在本体论上对佛道的排斥转向了对佛道本体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与其道本体论内涵的改变相一致的。事实上,王安石后期在道本体上的嬗变也反映在其他篇章之中。
在《洪范传》与《致一论》中,王安石认为仅有无思无为还不够,还必须有致用。在《洪范传》中,王安石如是言道:“由于道听于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于道听于命而知之者,君子也。道万物而无所由,命万物而无所听,唯天下之至神为能与于此。……志致一之谓精,唯天下之至精,为能合天下之至神。精与神一而不离,则变化之所为在我而已。”[1]994在该篇中,他接着又说道:“能谋矣,然后可以思而至于圣。思者,事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圣也。既圣矣,则虽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1]999王安石在《致一论》中也说道:“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则可以入神矣。既入于神,则道之至也。夫如是,则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之时也。虽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为者,则岂可以不通其故哉?此圣人之所以又贵乎能致用者也。”[1]1043王安石在《洪范传》中用“至精”、“至神”与“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等词语来论述道之体,而在《致一论》中,对道之体的议论所用到的词语是“入神”、“道之至”与“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之时”,非常相似。而对道之用的描述前者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后者是“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为者,则岂可以不通其故哉?此圣人之所以又贵乎能致用者也”,二篇杂论都强调了“通天下之故”。概言之,王安石在二篇杂论中都强调了道之体与致用,从立意到用词都高度相似,是王安石同一时期思想的流露。
何以见得王安石在此二篇作品中认为天道的含义只是具有无的特点,而像《老子》中的思想一样放弃了儒家的立场,并以此作为融摄佛道思想的一个途径呢?以上讲到王安石特别将“致用”拈之出来,其目的就是强调儒家不仅重视道之体,也重视道之用。言下之意是不像佛道只讲道之体,而对道之用置之不理。如果说这个结论还是有些武断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王安石的《洪范传》、《致一论》与《老子》作一下对比,就可立即感觉到这三篇杂论在讲到道之体和致用二者缺一不可方面是如此高度的相似,以至于我们相信王安石只是换了一种说法罢了。在《老子》中,王安石就明确提到了老子只是重视道之体,而没有致用的一环。王安石说道:“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1]1082-1083“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1]1083王安石认为没有道之用,道之体的作用也无法显现。而老子只是追求“无之为用”,舍弃了“毂辐”之于车子的作用,“礼、乐、刑、政”之于天下的作用。就是说老子只是重视道之体,而没有重视道之用。在此,王安石将儒家的道之体与道家的道之体相提并论,并且都用“无”来指称它。可见,王安石实际上认为儒家道之体与道家道之体是相同的。因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洪范传》与《致一论》中,王安石所说到的道之体不仅包含了儒家的思想,而且还包含了佛道思想。所以,我们认为,王安石这三篇作品中的道之体已经是作为一种融通儒释道的面目出现,而不仅是前期从儒家之天命具有无的特点,因而认为佛道思想与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有相近的一面来讲。在用道本体融通儒释道思想的同时,对佛道放弃致用的做法也提出了批判,即批判它们只是重视道本体,而放弃本体之用。很显然,这两篇作品与《老子》一样都是王安石后期的作品。
根据王安石后期道本体不仅重视阐述其体的特性,而且尤其注重凸显道之致用的特性,我们还可以判定其他阐述了相同思想的作品也是作于其学术活动的后期。这些作品包括《夫子贤于尧舜》、《礼论》、《礼乐论》与《大人论》等,因为这些篇章中的思想与前面所论述的三篇作品中的思想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对其相关内容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王安石道本体前后的嬗变不仅表现在其对道本体的直接阐述中,而且也表现在属于道本体的具体范畴“性”的演变之中。可以说,性作为道本体论的一个范畴,它的变化是道本体变化的一个实际例证。
王安石所论之性在前期主要是从儒家的角度来认识的,是有善有恶,这一点在前文已经论及。而在后期的性就演变为无善无恶的特性了,在《原性》中,王安石说道:“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性者,五常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1]1089将性与无极当作形而上的概念,而五常是形而下的概念,所以“五常不可谓之性”,五常有善恶,而性没有善恶。可见出王安石的这个性范畴已经由前期从本质上为善的性演变为后期无善无恶之性了。而佛道之性无与空的特性正与这种无善无恶的性得以会通,于是这种无善无恶之性就成为王安石融摄佛道思想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其无思无为的道本体在融通儒释道思想上的一个具体体现。
综观全文,王安石前期是从儒家的立场来阐述他的天命、性等哲学范畴。只是认为佛道思想与儒家的天命寂然不动的思想有相近之处,而这个寂然不动是从天命儒家的立场上来说的。而天道的内容佛道思想是没有的,所以说佛道思想只是在无思无为的特点上与儒家有相似性,而不认可佛道思想有儒家天命之内涵。总体而言,在前期,王安石坚持了儒家的立场,具有强烈的儒家本位意识,其所建立的以天道为本体的儒家哲学体系也是较为圆融的;对佛道思想的基本态度是排斥,而不是调和。但是后来王安石从天道的无声无臭来吸收佛道思想。因而,在道之体上,儒家的立场逐渐淡化,以至于认为佛道思想在道之体上与儒家一样,于是对佛道思想的基本态度由排斥转为调和。而天命含义中的儒家伦理由此而下降到形下的层面,例如认为性是无善无恶的,而善是后天形成的,与前期认为性为善,有善有恶是由后天的习染形成的看法森然对立。显示其道之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由前期具有实质内涵而在形式上表现为无思无为的道之体蜕变成为没有儒家的实质内涵只有无思无为的形式的道之体。于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这个形式特性就成为道之体的唯一特性。当然,王安石在外王上对佛道仍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从哲学史上看,对王安石道本体嬗变的正确认识有利于我们把握王安石学术与二程学术关系演变的根源。王安石前期的道本体坚持了儒家的本位意识的立场,因而得到了二程的认可,而后期的道本体表现出了对儒释道的融摄,因而与二程坚持儒家的本体论的学术观就变得不可调和。
另外,王安石在学术上对佛道态度的演变要与其在生活上对佛道的亲近态度区别开来。王安石终其一生对佛道都抱有好感,对佛道中的高尚之士更是褒扬有加。而在学术上对佛道的态度有一个很漫长的演变过程。王安石由早年对佛道的亲近态度,而认为佛道有近于儒学之处,这种看法为其后期对佛道无思无为的认可埋下了伏笔,盖从形式上的相似性迈向将这种相似性作为其道之体,只是一步之遥。王安石在本体论上的嬗变的实质是从学术上对佛道的谨慎认可一跃而变为对佛道道本体的接纳。这样,我们对王安石晚年皈依佛教的做法就丝毫不感到奇怪了,因为这扇大门在理论上已经敞开了。但其仍然不能对现实完全释怀,也可以从理论上得到解释,因为他认为致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总体来看,王安石的哲学体系与理学家是针锋相对的,因为二者对佛道的态度是根本对立的。
[1]李之亮.王荆公文集笺注[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
[2]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76-279.
[3]胡金旺.王安石人性论的发展阶段及其意义[J].孔子研究,2012(2):22-28.
[4]蒋义斌.宋代儒释调和论及排佛论之演进[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31-40.
[5]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2-98.
(责任编辑文格)
2015-12-16
胡金旺(1972-),男,安徽省安庆市人,宜宾学院历史与哲学研究所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学的超越性与时代性问题研究”(15XZX008);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现代新儒学及其文化影响研究团队”项目资助
B244.5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6.04.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