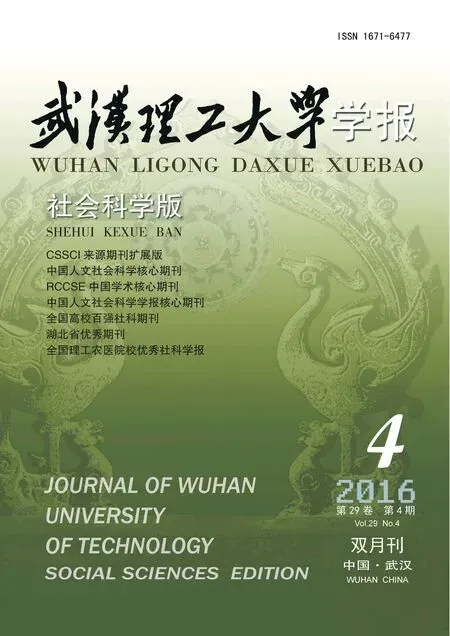审美偏见与艺术个性
——论顾恺之艺术美学思想中的“解构”意味
王赠怡
(1.四川文理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2.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审美偏见与艺术个性
——论顾恺之艺术美学思想中的“解构”意味
王赠怡1,2
(1.四川文理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2.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顾恺之善于突破惯性思维对于艺术创作的束缚,他很早就注意到“偏见”思想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对于他来说,只有基于明识的“偏见”,才能转化为有个性的艺术创作。事实上,真正具有艺术个性的创作对于艺术认识普遍滞后的大众来说,就是一种“偏见”。与大众艺术观念相比较,顾恺之的艺术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明显具有“解构”的意味。顾恺之“偏见”思想与解构主义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合拍亦昭示出其思想的现代意义。
顾恺之;艺术个性;审美偏见;解构
魏晋时期的五言诗、书法、绘画、琴、园林等艺术“都是在这一时期表达士人的心灵和美感形式,成为具有具体的士人心灵和个性的艺术体现”[1]。顾恺之的艺术思想也不例外,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肯定“偏见”之价值的艺术家。不过顾恺之这种超越时代、超越大众的艺术观却零星地散布于《论画》、《魏晋胜流画赞》、《话云台山记》、后世的绘画史论和类似《世说新语》、《京师寺记》这样的稗官野史之中;再加之翻译的晦涩等因素,致使他对艺术“偏见”所持存的积极态度被长期锁闭于历史之中。本文力图将顾恺之的“偏见”思想还原出来,分析它与解构主义思想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并以此彰显其偏见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顾恺之建构艺术个性的基本理念
最能体现顾恺之艺术个性思想的是《论画》评《北风诗》中“美丽之形”到“亦必贵观于明识”一段。不过对这一段的理解,学者们的分歧较大,这些歧义的存在往往遮蔽了人们对顾恺之艺术个性思想的认识。为了还原这段话的本真含义,笔者就以较有影响力的俞剑华、马采、陈传席、袁有根四位先生的断句和翻译为例,呈现其断句和翻译上的空白点和盲点,为我们拓展顾恺之的艺术个性思想提供文本理解上的新思路。
(一)俞剑华先生断句: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不然真绝夫人心之达。不可或以众论。执偏见以拟通者,亦必贵观于明识。
译文:形态很美丽,尺寸符合比例,明暗很合阴阳,细节也很纤妙,这些画上的优点,是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贵重的。上述这许多优点,虽然为世人所并贵,但画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要能把心中的思想情感在精神仪态上表现出来,才能算是真正的好画。手称其目,是看得见就能画得出,表现的艺术,十分高明。玄妙的欣赏,是要自己领会的,不能用语言文字来形容。若不能心领神会,那就只能看见实物的表面,不能到达人心的深处。看画要有独立的见解,不能人云亦云,为众人议论所迷惑。凡有偏见的人,自己总以为正确,必须向有明白见识的人去学习,见识不明,必然固执偏见,否则惑于众论。这种偏僻的见解与一般的见解,都不足以达内心而玄赏好画,也不能画出好画。[2]
(二)马采先生断句: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不然真绝夫人心之达。不可或以众论。执偏见以拟通者,亦必贵观于明识。
译文:画面上美丽的形体,尺寸的比例,明暗的度数,纤妙的细节,这些都是一般所觉得一可贵的,但是画的真正价值还不在此。画的真正价值却在于内心世界的表现。手称其目手目相称,“看”和“画”的互相联系。“看”就是“画”,“画”就是“看”。对于绘画深刻的鉴赏可以不言而喻。一个人达到了自由的心境,就不会为众论所迷惑,人云亦云,失去了自己的主张,有偏见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必须通过“明识”而把它克服。[3]
(三)陈传席先生断句: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不然,真绝夫人心之达。不可或以众论。执偏见以拟通者,亦必贵观于明识。[4]44
译文:美丽之形,准确的比例,男女之别、向背之分的合理,纤妙的行迹,皆为世人所推重。神态仪姿存于心,而手恰合于目者,深刻细致的观察则不待说了。不然的话,真不能至人心的通达之处。不可惑以众论。执偏见而自以为通达的人,也必须向具有明智识见的人请教学习。[4]54
(四)袁有根先生断句: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不然真绝夫人心之达,不可或以众论。执偏见以拟通者,亦必贵观于明识。[5]305
译文:那种追求美丽的造型,准确的比例尺寸、合乎物象的自然之理,细致入微的细节刻画,就成了世人所推崇重视的衡量绘画作品高下的标准。客观对象的神态仪容都装在画家的心中,而画家的手又能恰到好处地把画家眼睛所看到的表现出来,象这样的作品,对玄奥微妙的欣赏来说,是不需要画家明明白白地表现那么清楚的。不然,那就真正堵绝了人们通往广阔的想象天地的思路。切不可被众人的议论所迷惑。执有某种偏见,觉得自己什么都通晓的人,也必须请教于见识高明的人,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他们看。[5]313
上述学者的断句和译文,各有优长,但其译文在句意的连贯和逻辑方面所呈现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其一,如何理解“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句的所指及作用?笔者以为该句与上文的“美丽之形,……世所并贵”句在句意上应当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它们是顾恺之针对普遍大众的审美弊端而言及的。其二,“不可或以众论”句与“执偏见以拟通者,亦必贵观于明识”句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亦需要慎重对待。这两句应当是顾恺之针对如何确立艺术个性的问题,而向创作者提出的要求。正是由于在句意连贯和逻辑把握方面存在问题,才导致人们在该段话的理解上出现偏差,进而遮蔽了我们对顾恺之艺术个性的精辟见解和超时代的艺术思想的发掘。其三,“不然”之“然”应当作代词讲,译为“这样”或者“那样”,它与前面的否定词“不”一道形成转折话语的语境:它一面传达出顾恺之对普通大众的经验性审美认识的否定,另一面又引出了顾恺之自己的艺术创作主张。在这样的情境下,“真绝夫人心之达”句与“执偏见以拟通者,亦必贵观于明识”句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就很清楚了。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以为整段内容实际上涉及了两个方面:一是大众的艺术接受观念;二是创新性的艺术创作观念。顾恺之显然贬抑前者,而肯定后者。据此,笔者的断句及译文如下:
笔者断句: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世所并贵;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喻。不然,真绝夫人心之达,不可或以众论;执偏见以拟通者,亦必贵观于明识。
译文:漂亮对称的形象,尺寸大小的形制,阴阳错综的数理,纤细绝妙的笔迹,皆为世人所看重;只要神态仪姿符合他们的心思,描写的笔法与眼睛所看到的也相一致,那种玄妙的愉悦,对他们来说则不可形容。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创作不是一般人的心思所能理解,其创作不可以被众人的看法所左右;要把不被人们所理解的偏见转化为明白通达的看法,也必须注重基于神明之识的发现能力。
搞清楚这段文字的本义之后,我们探讨顾恺之艺术个性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因素才有最直接的依据和目标。在创作上顾恺之不主张拘泥于一般的艺术形式和程式的创作方法,他所注重的往往是超越翰墨、图画本身的东西。恰如张怀瓘所说:“顾公运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历代名画记》)。正因为如此,世人所推崇的诸如“美丽之形”、“尺寸之制”、“阴阳之数”、“纤妙之迹”这样一些艺术程式,虽然能达到“神仪在心,而手称其目者,玄赏则不待言”的审美效果,但是对于顾恺之来说这种被普遍推崇的艺术创作方法并非艺术个性之所在。大众所看重的眼与手的统一,大众所追求的符合视觉观感的形式效果,大抵不是艺术创作所追求的东西;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创作往往“绝夫人心之达”,即并不被人们普遍理解,故而他认为艺术创作不要被大众之观点所迷惑。这亦可以从他就《北风诗》评价卫协的话看出来。他首先肯定该作“巧密精思”,当为名作,然后话锋一转,指出此图之不足就在于“未离南中”艺术的共同性,言外之意是批评卫协缺乏创新。顾恺之反对将艺术视为纯粹视觉性的形式美的东西,他所看重的是艺术创作的个性化、一种与对象本质相关联的个性化。从《世说新语·巧艺》中我们也可以看见顾恺之为追求艺术个性的革新勇气和独创精神。如他画人肖像数年目不点睛,他认为“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多数人可能认为四体在视觉上的美丑好坏是绘画的重要方面,顾恺之则认为“四体”的外在描写在本质上与艺术的“妙处”无关,最重要的是对眼睛的刻画,所以他不敢随便画出人物的目睛。又如他画裴叔则,颊上加毛,其理由是“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那么,如何进行个性化的艺术创作呢?对于顾恺之来说,其根本法则就是创变。从其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喜欢变化多端的“道”性事物。如他描述雷电“太极纷纶,元气澄练。阴阳相薄,为雷为电”(《雷电赋》);刻画波涛“崇广而宏浚,形无常而参神”(《观涛赋》);赞美冰“托形超象,比朗玄珠”(《冰赋》);褒扬水“开神以质,乘风擅澜,妙齐得一”(《水赞》)。[5]330-340而“太极”、“元气”、“无常”、“玄珠”、“妙齐得一”等表述又突出了这些事物变化的玄妙。在绘画创作理论方面顾恺之更强调“变”的重要性,如《论画》就有如是之说:“若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也”;“然蔺声变趣,佳作者矣”;“以为举势,变动多方”。当然,顾恺之对“变”的重视又以“法”为基础,守法与创变是辩证的统一。《魏晋胜流画赞》就讲到绘画摹写时遵“法”的严谨。有的基于生活的原则:“轻物宜利其笔,重物宜陈其迹”;“譬如画山,迹利则想动,伤其所以嶷”。有的基于笔墨技法:“用笔或好婉,则于折楞不隽;或多曲取,则于婉者增折,不兼之累,难以言悉”;“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轻,而松竹叶醲也”。有的基于逻辑原则:“凡生人无有手揖眼视而前无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筌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对于顾恺之来说,守法与创变是建构艺术个性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没有守法,创变就会流于荒诞虚妄,没有创变,守法就会流于僵化。只有坚持守法和创变的结合才能形成艺术个性,并最终达到传神的目的。“神”是顾恺之刻画人物个性的最高艺术追求。姚最说他“如负日月,似得神明”,李嗣真说他“思侔造化,得妙物于神会”,张怀瓘说他“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历代名画记》)。顾恺之所说的“神”是指通过形体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气质、风度等。但是由于神具有无法具体指陈、不可触摸、靠感观感知的特征,所以顾恺之刻画人物个性的方法因人而变,没有常法,恰如张怀瓘云“神妙亡方,以顾为最”,正因为这样,艺术的个性也就产生了。可见,守法而又不拘常法的创变思想是顾恺之建构艺术个性的基本精神。
二、顾恺之将艺术偏见转化为艺术个性的一般原则
对于顾恺之来说,要建构艺术个性就必须重视艺术家自己的艺术偏见,艺术偏见往往是艺术个性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那么如何将艺术偏见转化为艺术个性呢?从顾恺之现存的艺术理论来看,大抵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其一,艺术审美个性的建构应不囿于普遍认同的观点。顾恺之承认人们在艺术审美方面有共同性,但是在创作方面,艺术的价值却表现在创作者的独特的审美个性上,在顾恺之那里审美个性的确立本质上就是审美主体的独创性、独特性的体现,而这种个性可能是多数人所不能理解的。尽管如此,顾恺之认为审美主体应当坚持自己的创见,不要因为不被众人认可而放弃自己的审美个性。如他将谢幼舆置于岩壑中的标新立异的绘画行为正是他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再如他在裴叔则面颊上画“三根毛”以此传达裴叔则的精神风貌;同时这一艺术行为亦体现了他挑战普遍认可的传统艺术观的勇气。《淮南子·说林训》曾说:“画者谨毛而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从《说林训》的内容来看,其所谈及的内容大都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现象,在当时应该是人们所熟悉、所认同的东西,对“画者谨毛而失貌”的批判大抵是那个时代的经验共识,其影响也很深远,刘勰《文心雕龙·附会》就有“夫画者谨毛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相类之说。而顾恺之则认为艺术的创造性及其由此所彰显出来的个性恰恰在于颠覆大众的传统经验,在创作实践中他就要通过“谨毛”而“不失貌”的方式刻画裴叔则,挑战传统共识。当然,顾恺之颠覆传统的方法,又不是天马行空的任性玄想,而是基于对创作对象内在精神气质的一种本质性的把握,我们通常把精神气质的本质性把握概括为“神”。而对“神”的把握,则与创作者活跃的艺术思想、敏锐的艺术视角、丰富的艺术经验相关。不过,顾恺之这种个性化的创作思想曲高和寡,不仅超越他所在时代,而且盛行“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六朝也不能理解顾恺之。孙畅之的《述画记》说他“画冠冕而亡面貌”,谢赫的《古画品录》批评他“迹不迨意,声过其实”。直到六朝末及隋唐才出现了姚最、李嗣真、张怀瓘等知音。
其二,基于明识的偏见就是艺术个性。在顾恺之看来,真正的创作是超越大众的,它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性往往很难引起大众的审美共鸣,他自己也以幽默的口吻戏称之为“偏见”。不过,顾恺之所强调的“偏见”是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它是个别的,我们今天说顾恺之的偏见思想能够通向艺术个性,正是据此立论。顾恺之对偏见在艺术领域中的作用虽然是只言片语地提及,亦未阐述偏见在艺术创作中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今天的人们大抵明白这样的道理:艺术语言与其所反映的复杂对象相比总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美术语言所构成的艺术作品与其所描绘的无限丰富对象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和误解,这就意味着在艺术创作中偏见和误解存在着客观必然性;从艺术创作的主体来看,作者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不过是对对象的一种主观印象,他必然诉诸于感性的表象形式,与对象的客观物理性相比较也是偏见和误解;就艺术个性而言,它就是要不同于人们普遍认可的经验惯式,这种个性与众人的普遍认识相比无疑也属于偏见的范畴。在中外艺术史上,许多具有创作个性的艺术家往往不会被人们认可和接纳的事实也不少。从艺术创新上讲,顾恺之与他那个时代是隔膜的,他被那个时代人们调侃为“痴”,《晋中兴书》也说顾恺之“博学有才气。为人迟钝而自矜尚,为时所笑”(《世说新语校笺》),这些恰恰从侧面证明了真正有创新的艺术家可能并不首先见容于艺术社会的共同体,其艺术思想往往也易被时人归于“偏见”一类。这种现象在西方艺术史上也很常见。法国印象画派就是典型代表。
其三,明识是偏见转化为审美个性的根本条件。在顾恺之看来,个性一定属于偏见,但偏见就不一定都成为艺术个性。他认为,要把偏见转化为艺术个性,艺术家就应当见多识广,必须贵于明识。什么是“明识”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明”作一个简要的剖析。从道家的哲学阐释看,“明”的涵义大抵可以从精微、本原、自然生命之和中见出:首先,能觉察精微细小之处就是“明”。《老子·五十二章》所说的“见小曰明”就是此意。其次,能认识万物的本原性,老子称之为“知常曰明”。老子两次讲到了“知常曰明”:一是在《老子·十六章》中,他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此处老子把认识万物复归本原的规律的能力称为“明”。二是在《老子·五十五章》中,他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结合该章老子对赤子的“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脧作,精之至也。终日號而不嗄”的阐述来看,此处的“和”是指生命本原之和,因此,它仍旧可以被涵盖在“复归本原”的命意之下。庄子亦以“明”作为准的,批判儒墨的狭隘而僵化的是非之辩。他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从庄子的阐述来看,“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是儒墨迷执于是非之辩、而不能观物“以明”的根本原因。那么如何对待是非才是“明”呢?庄子以为“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意即彼此是一并产生、一并存在的。他认为要像圣人那样“不由而照之于天”,走不辨是非的路子。具体方法上要像“道枢”那样“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因为“是亦无穷,非亦无穷也”。庄子虽然没有像老子那样给予“明”确切的定义,却与老子一样都从道的角度注重发掘其本原的意义。如《天下篇》在探讨“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的问题时,庄子的回答是“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与“明”并称的另外一个范畴是“神”,先秦两汉以来,人们总是将两者并提,“‘神’系天之精气,而‘明’系地之形物,神之在上,而明之出自下”[6]。“‘神明’是天地的交通过程,于是,‘神明’的作用即是天地之间的最重要的媒介,是天地之间的气化主宰者,故为‘生机’。”[6]“‘神明’之结合表达天地合德的之状态。天地合德才是万物的生机。”[6]顾恺之的“传神写照”理论可以说就是“神明”之哲学本原要义在艺术创作中的精彩呈现:“传神”传的是天之精气,属于“神”的范畴,“写照”写的是地之形物,属于“明”的范畴;创作本质就是天之精气和地之形物的交合过程,并最终形成生气灵动的艺术作品,注重人物的生气灵动是顾恺之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准的之一。如其《论画》评价《小列女》为:“面如恨,刻削为容仪,不尽生气”。当然,要突出人的生气灵动,则对眼睛的刻画无疑至关重要,故而有“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的经验之见。姚最对其“如负日月,似得神明”的评价,确实把握了顾恺之思想的精髓。不过,从道家的观点看“神”与“明”都体现了道的本原性,它们统一为“一”,而归于道。从上述分析看,“明”所包含的哲学意义大抵可以概括为三:一是觉察细微;二是复归本原;三是神明结合所产生的万物之生机。“明”所涵盖的这些意义都可以统一于道的名下,因为道是精微的、复归本原的、注重富有生机的生命的。而这些哲学思想与顾恺之的创作思想是统一的。以“精微”为例,从中国绘画史看顾恺之的艺术风格就属于“精微”一派,即便是对顾恺之颇为不满的谢赫也不得不承认顾恺之“深体精微,笔无妄下”(《古画品录》)。至于其它两方面的例证上文均有论及,下文在对“明识”的阐述中还将强调之,此处不再赘述。
顾恺之的艺术思想如此深刻,也难怪一般人不能理解,正如人们不理解老庄一样,看来要把握顾恺之的艺术创作,确实需要基于“明识”的认识积累。对“明”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我们再结合顾恺之的创作主张解读其“明识”的意义就水到渠成了。顾恺之所强调的“明识”大抵有这样几方面的意义:一是指敏锐灵通的艺术创作能力。这种创作能力能在一般人熟视无睹之处见出不同寻常的玄妙之处,它往往能使创作主体突破思维习惯定式而达到令人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顾恺之在性格上痴黠各半,好矜夸,好谐谑,率直通脱,这种性格使顾恺之在生活和艺术创作方面往往呈现出“自生人以来未有”(《历代名画记》)的独特性。《世说新语·排调》记载:“顾恺之噉甘蔗,先食尾,人问所以,云:渐至佳境。”可见其言行的个性魅力。又如他为有眼疾的仲堪画像,便“明点童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蔽月”(《晋书·顾恺之传》),达到化丑为美的艺术效果并获得与众不同的审美情趣。二是明识需要卓越的想象力。顾恺之《论画》称之为“迁想”。有学者认为“迁想”就是想。这种解释欠准确,应未能把握顾恺之的艺术创作特色。顾恺之在“想”前面加上“迁”字无疑是为了强调想象的跳跃性、超时空性、超习惯性。如他将谢幼舆置于岩壑中,在裴叔则的脸颊上加三根毛便属于艺术“迁想”的经典案例。当然“迁想”又不是任性玄想,它必须要以“妙得”为归旨。什么是“妙”呢?这可以从《老子》那里得到答案。《老子》篇有“故常无,欲以观其妙”、“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微妙玄通,深不可测”等表述,其“妙”含有微中有理、微中见道的含义,所以“迁想”最终是与体道的目的分不开的。
再次,“明识”亦指创作中的“置陈布势”的能力,它亦属于把握“地之形物”的重要方面。顾恺之把富有个性的创新与求变结合起来,如他在《论画》中认为“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也。”在《画云台山记》和《魏晋胜流画赞》中顾恺之对山水人物的“置陈布势”作了较详细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其四,明识是把握精微的认识能力。如《魏晋胜流画赞》说:“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小毫之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其五,“明识”要求抓住人物的“神”,它是人物独特性和生命性的体现。顾恺之并不对“神”作形而上的把握,他认为在艺术实践中有两种方式可以达到传神之趣:一是对形的借助,二是对“对”的把握。《魏晋胜流画赞》有这样一段话:
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
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筌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
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
对“对”的理解,我们可以从刘勰《文心雕龙·丽辞篇》的“造化赋形,肢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中得到启示,它至少表明了一种呼应关系的存在。因此,“对”实际上是为“形”的塑造作了规定,它要求“形”的存在必须是对象性的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存在。也即是说这个形的存在必须有逻辑上的联系。在顾恺之那里,“对”有实对与悟对之别。最基本的是实对,它是“以形写神”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在实际创作中就容易犯“空其实对”和“对而不正”的错误。这样的创作即便是“四体妍媸”,也无关于妙处,其结果最终是“筌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这里顺便再谈谈“筌生”的含义。“筌”是指手段,“生”是指目的;“筌生之用乖”意思是手段和目的之间关系相违背,这恰恰说明了“以形写神”与“实对”之间的关系,“实对”是手段,“以形写神”是目的。而袁有根先生把“筌生”解读为“全生”的做法[5]327,仍然偏离了顾恺之的原意。陈传习先生对“筌”理解是恰当的,而对“生”理解除参照《诗经·邶风·谷风》外,未予以明确的阐释。[4]64相对于实对来说,顾恺之认为“对”的最高程度是悟对,悟对则是强调“形”在“实对”、“对正”的逻辑基础上,与“对”建立一种情感上的内在联系,以此达到通神的目的。陈望衡先生说:“‘实对通神’只是说明这是个活人,‘晤对通神’则不仅说明这是个活人,而且是个有情人”[7],这种概括很到位。
三、顾恺之艺术个性理论中的解构意味
顾恺之的艺术“偏见”思想很具有现代美学思想的意味,它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20世纪西方解构主义关于“误读”的美学思想[8]:“误读产生洞见,洞见生出创意”。[9]解构主义是20世纪产生于法国而流行于世的一种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是德里达。解构主义对强调整体、结构、层次、权力中心的传统的结构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和颠覆性破坏。德里达认为,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和霸权的对抗”[10]16(《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并且相信自己的解构主张“对所有的情况都是共性的”[10]16。故而,在文艺美学方面结构主义所强调作品的中心、结构、旨趣亦受到解构主义的批判。解构主义认为每一个事物的实体之中都有歧异,也就是作品本身往往有着双重活动,其本身蕴含着自我瓦解的因素。于是,对于阅读和写作解构主义的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有意味的创见。美国耶鲁学派的德·曼“提出了批评家只有经过对文学、历史等本文的盲视,最后才能获得对本文的洞见。所谓‘盲视’,即阅读的‘偏离’和‘误读’。”[11]963同样属于耶鲁学派的哈罗德·布鲁姆认为“阅读总是一种误读”[11]969,他提出“影响即误读”的观点。布鲁姆相信“‘影响’不是指从较早的诗人到较晚近的诗人的想象和思想的传递承续”[11]970,相反,“影响意味着,压根儿不存在本文,而只存在本文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则取决于一种批评,误读和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11]970在耶鲁学派的努力下,解构主义建立了误读的合法性,他们有意识地把误读与创造联系起来,将“误读”与“创造”之间划上了等号,认为“误读即写作”。
顾恺之则是中国文艺史上第一个重视误读的美学价值的艺术家,这种误读思想在他那里被表述为“偏见”。在《论画》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偏见”观念与艺术创作个性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家族相似”性:对顾恺之来说,偏见就是创作,偏见就是创新,偏见就是对大众共识的一种“反叛”。这与解构主义的主张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合拍。以解构主义的思想来考量顾恺之的艺术偏见思想,其解构的意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其偏见主张就是对处于“中心”的普遍观念的一种“解构”。顾恺之对“偏见”的特征是从欣赏者和创作者两个角度来考虑的:对于大众来说,偏见往往不可理解,即他所说的“绝夫人心之达”;对于创作者来说,创作者应当勇于坚持自己的偏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即他所说的“不可或以众论”,“众论”即是处于权威地位的普遍观念。其二,“偏见”就是个性的体现。因为没有不同于普遍感受的偏见,就不会有审美的个别性,没有个别性的存在就没有艺术创新。可见,在顾恺之那里,偏见是对大众艺术共识的否定,偏见与艺术创造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这显然与解构主义的理论主张具有相似性。如德里达所推崇的解构就是一种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又是一种重构、重写,是在否定中确立起一种新的肯定。正如德里达自己所说的:“我常强调解构‘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种肯定,一种投入,也是一种承诺。”[10]16虽然顾恺之的偏见思想只是只言片语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其偏见思想所折射出来的独特的美学价值。从读者的角度看,顾恺之的众多艺术作品大都经历了从不被理解到逐渐被理解的过程,这更加彰显了其偏见观念的理论意义。相比之下,顾恺之的偏见理论更具有合理性和普遍性:一是,偏见的确立必须基于明识。二是,偏见不离开一定的法则,否则,偏见就只能是谬误。显然,基于明识和法则的偏见思想对于人们来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解构主义虽然也有解构的规则,却声称其不具有方法论意义。德里达就如是说:“我想保持我所解构的一切的那种鲜活性。所以那不是一种方法。不过我们的确可以从中找到一定的规则,至少是临时性的规则。”[10]16为了防止人们对其规则作普遍化的理解,德里达强调说:“解构不是一种伟大的方法论,也不是一种伟大的思想技术。”[10]17因此,解构主义不是追寻本源,而是肯定自由游戏,使意义处于不确定性中,并满足游戏的要求。[12]700这种“打一枪就走”的游戏性解构策略最后留下的只是“断垣残壁、裂痕累累的荒原景象”[12]684。解构主义强调其重构系统的非普遍性,是由解构主义颠覆权威、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张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如果解构主义所重构的体系一旦具有了普遍性,那就意味着它也摆脱不掉语词中心主义的逻辑范式,进而又形成了新的权威和中心主义,这样就把自己置入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境地。从艺术实践的可行性看,顾恺之对偏见的看法显然不是解构主义式的有勇无谋,而是独具匠心的深思熟虑,对艺术创作极具现实指导意义。当然解构主义的结构思想单纯从文艺的创作看,确实在逻辑方面存在问题。但是,如果从其强烈的政治意图看,又是可以体谅的。如德里达在提到文学与民主、自由之间的关系时就认为“文学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意思的同盟关系”[10]20,“文学,即写作与说话的自由在全世界都是根本性的”[10]22。
四、结 语
在中国文艺史上,人们最熟悉的是顾恺之“以形写神”、“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等理论范畴,而对其如何建构艺术个性的偏见理论却未予以关注。人们也往往把他那种突破惯性思维的艺术实践行为视之为“怪异狡黠”,以至于《世说新语》、《京师寺记》这类稗官野史成为记载其具有个性的艺术行为的栖居之所。尤其令今人未曾料及的是,当许多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们挥舞着“解构主义”的大棒大革传统文艺之命时,顾恺之早在1500多年前已经在艺术领域践行他的偏见思想了。如果悬置其艺术偏见思想不论,单从他对艺术个性的肯定上看,也比注重个体审美鉴赏判断的康德早了近1400多年。康德在阐述鉴赏判断的特性时就曾如是说:“对于每个应当证明主体有鉴赏的判断,都要求主体应当独立地作出判断,而不需要通过经验在别人的判断中到处摸索,以及由别人对同一个对象的愉悦或者反感来事先教育自己”[13]108,因此他要求年轻诗人:“不要因为公众的,哪怕是他的朋友的判断而为他的诗是美的这种劝说所左右”。[13]108在鉴赏判断的第二特性中继续强调个体审美的价值作用:“他不可以受众口一词高度赞颂它所迫使而在内心中表示赞扬。”[13]109顾恺之这一中国古代艺术美学史上的经典案例再次表明:中国美学的现代性须在自身古文化的母体中寻得根基,借用佛法大师慧能的话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寻菩提,恰如觅兔角。”(《坛经》)如果我们离开文化的母体去寻求现代性,也大有“恰如觅兔角”的讽刺意味了。
[1]张法.秦汉到隋唐文化的五个方面[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3(3):27-35.
[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俞剑华,注释.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106.
[3]马采.顾恺之《论画》校释[J].中山大学学报,1984(2):32-41.
[4]陈传席.六朝画论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5]袁有根,苏涵,李晓安.顾恺之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6]郭静云.先秦易学的“神明”概念与荀子的“神明”观[J].周易研究,2008(3):52-61.
[7]陈望衡.中国美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83.
[8]王赠怡.论顾恺之的艺术美感思想[J].齐鲁艺苑,2011(1):39-41.
[9]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49.
[10]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1.
[11]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12]牛宏宝.现代西方美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3]康德.判断力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文格)
2016-01-22
王赠怡(1972-),男,四川省平昌县人,四川文理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及艺术美学研究。
B83-02;J120.9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6.04.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