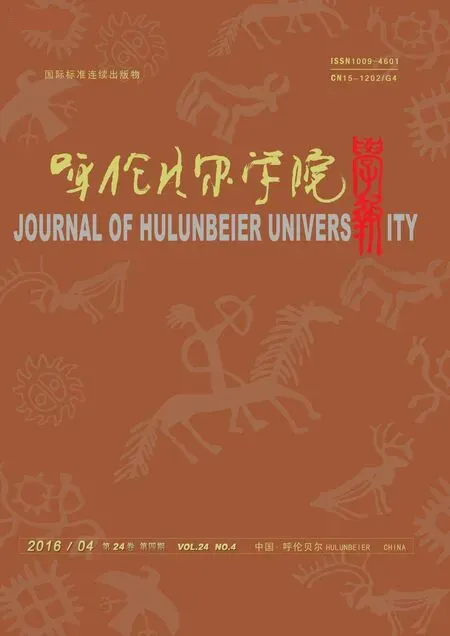苦难的沙漠 鲜活的葡萄
——试论《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形象的塑造
张碧涵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 徐州 221000)
从中国到美国,从东方到西方,横跨两个地域,体悟两种文化的严歌苓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的笔致塑造出了一个个饱满多汁的女性形象。其中,有流落异国委屈求生的多鹤、小渔;有出身卑贱内心圣洁的妓女扶桑、玉墨;有在求而不得中沉沦,在美好人性的感召中复归洁净的文秀、小点儿、巧巧;有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田苏菲、阿尕;还有模糊了女性特质的徐群姗、柯丹。但是作者在2006年所塑造的王葡萄,显然是她众多女性群像中的异类。
你好像在其他的女性的一举手一投足中看到了一个不完整的王葡萄,但是葡萄又并非像《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一样是一个组合堆砌众多女性特质的扁平人物,她有着活脱脱的生命和血肉,她是饱满而独特的,是一个一闭上眼睛就会清晰地映现在头脑中的真实的农村女子。她的泼、她的辣、她的柔、她的媚、她的至情至性、她的无知无畏、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膨胀着生命的张力。让你相信那些看似传奇和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只有这样一个葡萄会做,也只有这样的一个女子敢做。
一、行走在男权话语社会之外的寡妇
(一)正统思想规约的社会中女性被摧残的命运
自进入父系社会以来,随着女子经济地位的失落,女子便不可避免地沦为男性社会的附属物,即使是作为西方启蒙运动领袖的卢梭,在谈到女性问题时也秉承男子第一性的立场,称“妇女被创造出来就是听命于男子,妇女自幼年时起就应该学会容忍,甚至不公平也要容忍”。而中国正统儒家思想“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规约和钳制,使妇女的一言一行都被戴上了沉重的镣铐,而失去了强势一方庇护的寡妇在这样一个男性话语社会中更是处于一种极其卑微的地位。在封建的宗法制社会中,贞节牌坊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德行的最高表彰,也是对女性人性与自然欲望的残酷镇压,而寡妇不仅要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猜疑和审视,一旦德行有所偏差,那么诸如沉塘、火刑这些灭绝人性的惩罚依然被社会所集体接受而加之于女性,然而男性此时却多被当作是受寡妇诱引的受害者形象而被保护起来。
(二)男权话语主导下的残损寡妇群像
在古今中外作品中出现的寡妇形象,虽则身份各异,性格各异,但大多都逃不出悲剧的命运。有的是在命运的打击面前,形容枯槁,悲索地活着,却无论如何挣不开命运的牢网,例如《祝福》中的祥林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爸爸爸》中的丙仔的母亲。她们在世人虚伪的同情中像一个笑话一样活着,最终也在世人无情的厌弃和摧残中走向无法逆转的灭亡。有的作为家庭富足的牺牲品,她们在生命本能欲望的被压制之下熬煎着,最终被异化成了一群半人半鬼的怪物,她们像幽灵一样刻毒地报复着,最终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他人。例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怨女》中的银娣,她们健康活泼的生命力随着他们的丈夫一起化成了一堆“死肉”,她们明知挣扎无意便不再挣扎,她们用恨加固了自己的悲惨。还有一群是安然地享受着自己的寡妇身份的,例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富孀梁太太,她以自己的青春做筹码,换来了年老丈夫的早死,用他的钱搭住起一个声色犬马的王国,以求在男性世界中叱咤风云。而《兄弟》中的李兰、《活动变人形》中的静珍就是传统的中国式女人,一个在丈夫的逝去后永远走不出悲伤的苦海、一辈子活在过往的回忆中。而另一个硬把守寡视为至高无上的荣耀,结果只能以一次次地叫骂、一次次神经质的举动来疏遣心中年深日久的压抑与委屈。这些女性不论是病态的挣扎还是悲惨的接受,她们都无可否认地屈服于男性为主导的权力话语之下,在此过程中她们接受了女性弱势的现实,生命本体形态不可避免地模糊或发生了异变。
(三)男权社会中一次华丽的反叛,高贵的亵渎
与上述女性相比,葡萄显然是一个出格的,为封建卫道士所不容的寡妇形象。作为一个父母双亡,流落异乡,七岁就成为童养媳,十四岁就成为寡妇的女子,她在还不懂得爱的时候,就失去了爱的权利。况且在葡萄所生活的史屯,民风闭塞,妻子总是低眉顺眼地走在丈夫的背后,婆婆亦可以随意打骂儿媳,而通过革命寡妇之一蔡琥珀的话可以得出:女人在史屯不过是“两条腿的牲口”。由此可见史屯男尊女卑的封建正统思想依然顽固存在,而孙二大也明确跟葡萄说过“寡不好守”,但是寡妇的身份对于葡萄来说似乎只是多了一个名称而已,并不妨碍她浑然忘我地快乐着。在她的男人铁脑死后,她并没有觉得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天塌了,她反而从不提到他,也从来没想到过他,让人觉得铁脑是她生命中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在以后的岁月中,她经历过众多的男人,不管她爱或者不爱,她都尽情享受着性爱的快乐,尽情地释放着她青春热烈的生命中蓬勃的“力比多”,从来没有想过要为了哪个男人而守住贞洁,即使她明知对方已经有了家庭,她也不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罪恶。例如在铁脑死后,葡萄会爱上琴师朱梅,甚至动过和朱梅远走他乡的念头,在朱梅死后,她也没有悲伤多久,而是怀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和孙少勇走到了一起,而对于史冬喜和史春喜兄弟俩,葡萄虽然不爱他们,但是葡萄需要他们给予她肉体上的欢娱,同时依靠他们的力量来换取她和二大暂时的安宁。而在传统的男性话语之下“贞操被郑重其事的宣布为人类最崇高的美德,而且妇女发生性关系则是最大的罪过。”[1](P48)
但是这种金科玉律在葡萄那完全不起作用,然而葡萄又绝不是受五四新思潮感召而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的代表,她只是不愿意压抑自己性的渴望与快乐,就像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和她的几个女儿,她们从不受正统伦理的制约,总是投向不同的男人获得动物原始本能的快感,在莫言的眼中她们不仅是美的,就像叔本华所说“女人的美都与性冲动紧密相关。与其说女人是美丽的,还不如把她们描述为没有一点美感的性。”[2]而且她们代表了民间最旺盛的生命力。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贞节不是一条守则,也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种理想。”比起那些在性的泥潭中挣扎、异化的生命,王葡萄反而呈现出了一种健康圣洁的姿态。
此外,葡萄似乎从没有把传统的男尊女卑,中国社会惯有的等级制度放在心上,她虽然没有追求平等自由的觉悟,但是她的每一个言行都透露出不甘受人奴役的意志来。例如,当别的英雄媳妇都是低眉顺眼、跟在男人后面往回走时,只有葡萄大声地对铁脑呵斥“快起来!”,而且铁脑是跟在葡萄的背后往回走的,以至于让熟悉中国文化的日本军官都觉得葡萄的行为与别人的格格不入。而且,面对省城来的丁书记,她不但不像别人一样鞍前马后地奉承他,而且还在臭烘烘的猪圈里对他大谈特谈养猪经,并且当丁书记的脸脏了后,她直接用那块脏围裙给他擦脸。这一切未经打磨过的粗糙的行为,是没有被正统的强势文化所摧残过的最贴近生命本能欲求的,是健康的、是一个将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活的人,是对男权社会的一次华丽的反叛、高贵的亵渎。
二、在混沌自如的原始生命状态下的人性之美
(一)混沌自如的生命状态
1.葡萄的混沌之美在于与众不同
在作者的其他一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体会了生命一系列的得到与失去之后,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些变化,或者像《草鞋权贵》的霜降一样,在目睹了大家庭内部的勾心斗角与分崩离析后,失去了原有的纯真与快乐。或者像《白蛇》中的孙丽坤,在体会了文革对人性的摧残后,也渐渐偏离高贵优雅的本质,变成一个连自己都厌恶的粗俗、臃肿的妇人。即使《第九个寡妇》中的人物,譬如孙少勇、譬如史屯的百姓,人人为了自保,都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的极致拷问中丧失了原有的人性。而不管历史怎么变化,不变的只有王葡萄一个。严歌苓曾经说过“世事可以沧桑变幻,但那善良的人性永远不会改变,这也是这部作品给我最大的震撼。”[3]她始终以那一双混沌懵懂的七岁孩童的眼光来看周围的人和事。她在那个时代中是人人眼中的疯子,是“不觉悟”,“麻木”的“喜儿”,但是她却以自己那套简单纯粹的人生哲学活得比谁都清楚明白。“这就是女人为什么在其一生中始终保留着孩子般稚气的原因,她们所注意的只是她们眼前的事情,留恋的也只是这些,并把表面现象当作事物的本质看待,津津乐道于些微小事儿,重大事情却可不管不问”,葡萄从来不去想以后怎么样,只是心里认为是正确的她就去做。而这种混沌的哲学恰是葡萄身上燃烧的人性光辉。
2.葡萄的混沌之美在于朴素真实
如果葡萄也在时代的历练中变得耳聪目明了,那么她要么失去了自己,要么就无法在历史的沉浮中安然地活下去。在这部作品中不论是史屯的愚昧民众,还是像孙少勇、谢哲学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滚滚红尘中,都以自己最理性的姿态紧跟时代的步伐,结果均被时代狠狠地鞭笞,丢了自己、丢了尊严、丢了性命,这真的是对那个畸变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中畸形的民众的一个莫大的讽刺。正如《庄子·内篇·应帝王》中所寓言的“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4]而陈思和在分析沈从文《边城》中翠翠的形象时,说翠翠的美就在于她混顽不开,但是一旦她的心智中有了世俗的纷扰,她的悲剧也就来了。[5]但是翠翠生活的大环境是一个高度提纯化的蓬莱仙境,她眼睛触目所及的都是象征着美好纯粹的绿水青山,生的丑恶与黑暗永远地被隔绝在她的世界之外,所以翠翠的混顽懵懂是一种被保护了很好的少女心性,而一旦她的生活起了一丝波澜,那么她的懵懂快乐便打了折扣。然而人性的丑恶,历史的错乱与污浊都劈头盖脸地向葡萄砸来时,在种种艰难的存活中,她依然活得那么浑然天成,一副不知愁的模样。相比较纤尘不染的翠翠,葡萄反而给人一种真实的纯洁与美丽。例如在八个女人都选择牺牲自己的丈夫而救八路军的时候,只有葡萄坚持“铁脑是我男人,我不救他救谁!”[6]在正统的观念中,八个英雄寡妇是大义凛然的革命义士,她们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了一起,是值得青史留名的,王葡萄的行为是舍大家、保小家的所谓的愚昧落后行为,在当时是值得批判的。然而王葡萄所代表的却是最朴素的人伦观念。其实,严歌苓想要塑造的并不是一个林道静式的革命女英雄,她只是代表一种普通人的凡俗观念。葡萄连革命是什么都不太懂,她只知道铁脑是她的丈夫、是一起长大的亲人、是恩人的儿子,她不会去想老八为百姓谋福利,他们的命比家人的命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不瞒不欺地做出了一个人最真实的选择。而且这八个女人抛夫弃子,不顾自己年迈的公婆老年丧子的痛苦,深层原因并不在于她们有多高的觉悟,只是不愿意做“两条腿的牲口”,历史的光芒恰在此时掩盖了她们人性中最卑劣的部分,比较而言葡萄比她们要真实得多、高贵得多。
3.葡萄的混沌美还体现在她在时代中的停滞。
她不惧中央军的淫威,只知钱货两清,天经地义,反右、四清、饥荒、文革等历次的运动她都结结实实地参与了,但是这些对她而言不过是身边的人来了,走了,死了。让她开会就拿着鞋底去开会,在不毁坏她的利益的前提下,让她干嘛就干嘛。就像是一出戏,看过就罢了,她依旧自得其乐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她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腿的历史,葡萄从来都看不清历史的全貌,“但腿比脸诚实”,尽管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也让她抓住了最真实的那一部分。不管谁来了,还是谁走了对于她来说都没有什么影响,她只管关上门来过自己的日子。例如,当别人在议论哪一方的军队又驻扎在史屯时,她总是懵懂地来一句“哦,又打了”,似乎政治局势的变化还不如她手上纳的鞋底有实际价值。另外,当史春喜等人一味地对丁书记曲意逢迎的时候,只有葡萄不知道省上的官和他们史屯的官有什么区别,甚至当丁书记亲自来看她的时候,她还一心扑在她的猪娃上。这种在时代大潮中的怪异行为,并不是葡萄主动地去反抗这不公平的命运,葡萄读书不多,也不觉得自己的命运很悲惨,她没有这种觉悟,这一切都跟源于她的一颗赤子之心。如果不是她的那双未经世俗打磨的眼睛,就不会有一个传奇的葡萄。
(二)顽强不屈的生存追求
葡萄原始的生命状态还体现在她对生的强烈追求上,七岁父母双亡,流落到史屯的她便开始了融入这个异姓社会的艰难历程,葡萄在大是大非上让人觉得她是一个粗糙愚钝的乡野女子,但是在很多时候又让人觉得她实在是聪明得让人心疼。面对铁脑妈的百般挑剔,她只是默默地承受着,一次次地让自己做得更好。例如铁脑妈说她是全史屯手脚最笨的儿媳,她就夜以继日地练习剪纸,直到剪出让其他女子都称羡的窗花。挑衣服的时候,明明心里很委屈,但还是自觉地拿别人都不肯要的被印上大字的那件。此外,她不仅照顾好家里的杂活,还到柜台上帮忙收账、卖货,她只是为了证明她在这个家是有存在的价值的。而在严歌苓的另一部作品《小姨多鹤》中,多鹤作为战败国的子民,在张俭家只是作为一个生孩子的工具而存在,并且在自己亲生孩子面前却要以小姨的身份屈辱地活着,但是不管怎样她都愿意活着,像一头任劳任怨的母牛。在葡萄与多鹤身上都赋予了作者对于人性的终极理想,在肮脏的、一潭污水似的历史中,作者有意识地让这两个生活在时代的边缘中的女性,展现出了人性最动人的光辉。
葡萄在孙家遭逢大祸后,她将自己未死的公公背回地窖里藏了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不管多难,她都没有想过放弃,在她的心里“好赖都要活着”,“活着的都有理,死的都没理”。作为这个社会的弱者,为了能够生存下来,她练就了一副蛮横撒泼的本领,曾经为了和淘米儿抢夺一块肥皂,不计形象地在街上大打出手,为了不让中央军揭她家的锅,她拿着一根胳膊粗的木棍,像疯子一样和一群男人叫板“不搁下锅,我夯死他”,在大饥荒年代,她也学会了一套偷东西的生存之道,在她的概念中这一切与道德无关,只是人总要活下去的。就像鲁迅先生在评价萧红的《生死场》中说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7],葡萄不论经历了多少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与灾难,即使是像蝼蚁一样卑微地活着,她也从没想到过死,或者说她对死有着一种本能的畏惧。例如从没有害怕过的葡萄,第一次感到害怕的是在清算孙二大家的财物时,她被哄抢东西的人挤倒在地,她因为怕被踩死而发出一阵杀猪般的惨叫,而这一惨叫或惧怕本质上而言乃是出于对生存的追求和珍惜。葡萄虽然不像《生死场》中的人物渗透着一种野性、蛮荒、血腥的生命的强度,但是她对于生的热爱、死的恐惧恰也能体现这种不屈的生存意识。
(三)圣洁博大的生命关爱
她对生命有一种本能的敬重,不论是对人还是对动物。就是因为这样,当她们家那头老驴在公社化中,终于病得连路都走不了时,葡萄也不忍心将它变成一堆驴肉,而是一直守在它的身边,像保护亲人一样送它最后一程;在连孩子都欺负瘸老虎的时候,她主动跟他讲话,还帮他打水,以至于让瘸老虎觉得她精神不正常;在大饥荒年代,她饿得一脸菜色、脸庞浮肿的时候,她把好的食物省给自己的公公吃,而自己每天喝酸红薯叶汤,此外她还把省下来的吃食分给无依无靠的李秀梅;在文革时期,对于人人喊打的老朴,她像母亲一样疼爱着,在别人都不愿意给自己添负担时,只有她收养了女知青的孩子,也只有她会在劳模大会上说出“你们都不把人当人看,怎么会把猪当猪看”这样惊世骇俗的话,以及为了照顾自己的猪娃不愿意去省里开劳模大会。
葡萄从来不会认为自己哪里做得不对,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多么高尚,她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做自己该做的事,然而就是在这些游走于正常人之外、政治之外的行为,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懂世情的农村女人人性的美好与圣洁。看到了一个圣洁博大的地母般的胸怀,以及她对生命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列夫·托尔斯泰曾将一个好的作家定义为“不在于知道写什么,而在于知道不写什么。”在严歌苓的这个故事中,历史只是为了写人而存在,那种枪林弹雨的惨烈并没有强烈地摆在眼前,有人因此批评严歌苓作品的历史虚无主义,但是正如茹志鹃在谈到她创作《百合花》的动机时说的那样,她并不是为了在写战争的残酷,她只是为了表现在那样一个人与人只能短暂相交的年代,人性的美好。而严歌苓跨越历史的长河,并不为了写一部痛定思痛的宏大史诗,而是在表现历史中的各色人的表演,在表现人性的真善美。
三、弱势文化下的强势生命
(一)弱势文化锻造出的弱者
造人说由来已久。而西方基督教经典《圣经·创世纪》一篇中,则认为女人是上帝所取男人身体中的一根肋骨幻化而成,因为上帝耶和华觉得男人独居不好,需要为他找个配偶,于是取自他的“骨中骨,肉中肉”的一部分便被称之为女人。可见女人虽然是男性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她必须依附于男人才有其完整的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而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总体而言就是一部男人的历史,在封建君主制国家便明确标榜“女人不得参政议政”,“女子无才便是德”,而一个王朝的覆没,也往往被归结为“红颜祸水”,“牝鸡司晨”,因此女人在家国大事面前永远处于失语的位置。在男性话语里,女人被赋予软弱,顺从等特性,必须要躲在男性的羽翼之下,而男性家长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威随意决定女性的命运。直到西方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之风吹到东方,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二)弱势文化中被丑化了的强者
但是在不少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强势的女子一般都被丑化或妖魔化了,甚至消失了女性特征而男性化了。例如老舍《骆驼祥子》中的虎妞,精明能干,有胆有识,说爱就爱,能够在男性社会中活得风生水起,放在今天社会就是女强人,但是作者从一个男性的眼光来充分表达了对这种女子的不喜欢,将她描写得又老又丑,狡诈世故,像个妖精一样吸干了健康的、生命力旺盛的祥子身上的精血,将祥子的悲剧一大部分推到了虎妞身上。作者喜欢的是惹人怜爱、可以让男人在她身上看到自身强大力量的女性,例如凄凄切切的小福子。
(三)在弱势文化中盛开的强者
然而在严歌苓的这部作品中作品也极力将王葡萄塑造成这样一个强大的女人,但是她出于女性对美的追求,在王葡萄的身上不仅保留了种种苦难的印记,而且少妇身上所特有的柔媚使她对于男性而言就像熟透了的果实一样沉湎于她的诱惑之中,甘之如饴,所以她的蛮泼在男性视角中恰好是可爱的。在严歌苓的这部作品中,男人多数是软弱自私、残缺不全的。而作为男性文化中最弱小的寡妇却常以母亲般的姿态宽容和保护着他们,孙怀清那么全知全能型的一个人物,在浩浩荡荡的土改运动中也只能躲在葡萄为他搭住的那一方地窖中看着这个世界的沧海桑田;知名作家老朴经历了人事那么多的浮华与落魄,却只能在葡萄这里找到家的安全感;一心要求进步、一心秉承着自己错误的人生观的孙少勇,只有葡萄能够唤回他身上潜藏的人性,认清一个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面对无耻索取、忘恩负义的史五合,她也能以一种施舍者的悲悯眼光来看待他。在时代的鞭子抽到那些男人身上时,有的人选择泯灭良心,追寻时代的脚步,像孙少勇、史春喜一流;有的人在生与死的挣扎中,选择了更轻松的死去,像瘸老虎、谢哲学一流。然而只有葡萄这样一个女人,却在轻描淡写中躲过了生命一次又一次的暗礁。
在王葡萄身上并没有女人“第一性”的自觉性,也没有弗吉尼亚·伍尔夫所宣扬的超越性别的人道主义的关怀,[8]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还略微蒙昧的乡下女人,对男人的保护欲则主要是在逆境中锻造出来的强大力量,以及大多数女人天生都具有的母性使然[9],每一个男人在她的眼中都不是历史的统治者,都是需要她疼的孩子。在很多男性作家的作品中也都赞美过女人的这种母性,像张贤亮《绿化树》中的马缨花,川端康成《山音》中的菊子,但是男性视角下的这种母性中含有一种无原则的包容和忍让,甚至还有一种女性天生对男性的崇拜。那么有能耐,对马缨花那么好的海喜喜她不爱,却偏偏被孱弱无力的章炳麟吸引,只因为他是个读书人。而修一对菊子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却还是让她放弃自尊原谅他,只因为他是这个家的支柱。而在王葡萄的身上我们看到作者没有像塑造小渔、阿尕、田苏菲一样,让她们的喜乐都受一个男人支配着,为了讨得男人的一点垂怜而委曲求全,而是有意识地不让哪一个男人完全拥有葡萄,这就使葡萄不受谁的支配。即使在两性关系中葡萄也不是扮演被索取的对象,反而像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女王一样享受着男人带给她的快乐。
四、至情至性真葡萄
明代戏曲大家汤显祖认为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而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至情。按照传统道德观,至情应该和“至死不渝”,“忠贞不二”联系在一起,才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然而王葡萄的一生之中却历经多个男人,显然要被理学家斥为“淫妇”,这和古代男权社会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必须从一而终的思想正好不谋而合。但是王葡萄的至情至性恰好就在她与这几个男人的爱恨之中体现得最生动。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塑造了“霓喜”这一人物,她也是游走于各个男人之间,但是那些男人对霓喜来说只是乱世中的庇护伞,能够提供给她物质和肉体上的满足,爱这个字眼只是个与她无关的冷眼旁观。而王葡萄对于她生命中的每一个男人她都结结实实、真真切切地去爱,作者没有给葡萄大段的心理独白,或情感渲染来表达她的感情,但是读者从她的每一个动作里都能被她那种浓烈的感情所感染。
(一)最重的恩,最深的情
王葡萄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不是她的丈夫铁脑,也不是与她有感情纠葛的那几个男人,恰恰是她的公爹孙怀清(二大),葡萄与二大之间的关系简单而又复杂,首先二大是葡萄的人生导师,葡萄来到史屯后,她的生存之道以及做人的道理都是二大教给她的,因此葡萄可以看成是二大生命的另一种延续,例如二大无论做什么都做得漂亮,最怕闲着,这一点和葡萄很像,二大好赖都愿意活着,而葡萄更是这样。孙怀清从没有用封建社会那套对待女子的教条来规约葡萄,他只是在葡萄的成长过程中稍作提点,让她不致吃亏,同时也有意地不让葡萄被世俗的那一套毁坏了心灵。
二大是葡萄的恩人,王葡萄虽然从没表达过她对二大的感激,但是在孙怀清被抓走后,葡萄想着她要把二大的东西守住了,不能辜负了他,这里就存在了一种报恩的思想,如果当年二大没有买下葡萄,葡萄可能就变成了孙克贤豢养的一个发泄性欲的工具,可能早就被折磨死了,在葡萄十一岁发天花时,连医生都放弃了,只有二大没有放弃她。
二大还是葡萄的父亲,二大从来没有把葡萄当成过他家里的童养媳,他总是以最大的自由来释放葡萄的原始生命力,因此也养成了葡萄在苦难面前那种浑然自得的生存能力。很多人都说葡萄对二大是一种救赎,但是葡萄与二大之间更是一种相互支撑的关系,葡萄救赎的是二大的身体,而二大救赎的是葡萄那颗孤苦无依的心灵。没有葡萄二大可能就死在刑场上,按照当时孙少勇一味追求进步的六亲不认的行为,他可能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而葡萄如果没有二大,她可能就失去了支撑着她在艰难的时局中以一个寡妇的身份独立存活下来的精神力量,他们两人的心灵达到了最完美的契合,葡萄做的事,无需多言,他都理解。他知道葡萄在做她认为对的事情时有多么死心眼,他知道她有多不容易,就像别人只看到二大的“光洋”,而只有葡萄将二大两头的辛苦与光洋都看见了,他们也在互相心疼着。葡萄在她到了史屯之后,似乎就跟过去彻底断绝了关系,对于她死于黄水的父母,葡萄似乎已经忘记了,但是什么都不怕的葡萄,偏偏就怕没有爹,我们也可以看出葡萄虽然表面上看百毒不侵,其实她内心对于受过的伤害会有本能的防御。 所以她可以为了保护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公爹,放弃自己的儿子,放弃自己成为一个妻子的机会,不惜用利用史春喜这个当时的权力对象来帮孙怀清躲过可能遇到的危机,甚至可以忍受史五合无耻的威胁。
而她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就是她的儿子挺,葡萄当年那么难她都要生下挺,就说明她对这个与她生命息息相关的孩子是多么珍视,她狠心送走挺,一方面是因为她要保护二大,当初她千辛万苦不让人知道有这个孩子存在,葡萄不是怕别人的飞短流长,因为她曾说过“谁也逼不死王葡萄”,但是只要这个孩子存在一天,她这个小院的安宁就会被打破,二大就多一分危险。而且此前她听说过侏儒疼正常孩子,她想着这个世界上总能有一块地容得下一个婴儿,葡萄是相信他们是一定不会伤害挺的,而且还有一方面原因,按照葡萄那么烈的性子,她是万不会在这个时候与任何男人组成一个正常的家庭,至少她身边的男人都不行,而且她又是一个寡妇,在以后挺的成长过程中肯定会被当成野孩子而遭受到白眼、欺负,而且为了活下去她必须要依靠身边想占有她的男人,这种环境肯定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她可以不在乎,毕竟她已经吃过那么多的苦了,但是从葡萄对孙怀清的依恋程度可看出她深知一个孩子没有爹会多么痛苦,她不希望挺再延续她凄惨的命运,至少那群小人儿会给挺一个完整的家庭。而且她想到“那么些人将挺当心肝肉疼着”“比在咱这享福呢”,她就放心了,至少他们是不会让挺再孤苦无依。葡萄与挺从来都不需要说话,甚至都不需要相认,但是仅仅血脉的连系就足以让挺原谅他母亲当年的无情。而且挺这个形象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葡萄与那么多的男人在一起都没有孩子,只有跟孙少勇有了一个儿子。这和后面孙怀清讲的那个孙家祖奶奶的传奇故事正好契合,“孙二大在用一种很含蓄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一种关于轮回的希望,就是一种从很远古的史前时代最有力量的母系社会的力量,她不管一切,她只是在给你疗伤,只是在抚育你、生育你的一个母兽似的雌性动物。让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是她这样的一种非常有力量的人”[10],孙家的血脉在葡萄这里延续了下去,并且获得了新生。而葡萄的身上也被赋予了一种传奇性。
(二)爱恨交织下的救赎
葡萄对于孙少勇的情感夹杂着怨,也夹杂着爱,他们的爱是在亲人之爱、恩人之爱、肉体之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男女之爱。孙少勇是在葡萄再次孤苦无依的境地中出现的,让葡萄觉得自己终究不是一个人了,而葡萄对孙少勇感情的喷发,主要在于葡萄以为孙少勇可以救自己的父亲,那种感激之情让她觉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爱上了孙少勇。而初恋朱梅的死去,让她想要抓住在她身边的一份切实可感的幸福,如果孙少勇没有做出伤害孙怀清的事情,葡萄也是想嫁给他的,这说明在葡萄的内心深处是相信孙少勇是一个有担当的、值得托付的、可以给她一个家的男人。虽然孙少勇对葡萄是真心的,但是他的爱夹杂着太多世俗的元素,而且孙少勇毁了葡萄对于家的渴望,这种打击是致命的,所以他们无法走到一起。正如叔本华所言男人有时要通过女人来纠正自己的理性。葡萄还承担了拯救少勇岌岌可危的人性的作用。到了晚年的少勇,忽然变得和二大一样了。时过境迁,该有的恨、该有的怨,该散的都散了,经历了那么多,风光过,也被别人踩在脚底下过,还有什么看不开呢。可是这些道理,当年的他却不懂,他觉得自己是精明的,反而把自己陷在了历史的嘲弄里。
(三)最深的相知,最浓的不舍
而在众多男人中最可惜的就是葡萄与老朴的关系了,她与老朴之间有一种纯粹的美,他们并不需要肉体的接触,而是一种真正的心灵的契合,她带给老朴的是家的安心与温暖,而老朴对于她而言,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人,也是一个值得用心去疼的孩子。长时间的相处,她与老朴已经形成了一种最为默契的关系,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们都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些什么,这种关系将其他人都排除在外,任何人都插不进去。以至于孙怀清曾为葡萄遇到这样一个人而做过美梦,而老朴也应该是众多男人中最让葡萄觉出爱得苦楚的一个。
严歌苓在这部作品中没有写过葡萄失去其他男人后流露的感情,仿佛葡萄很无情。但唯独对老朴,葡萄总是想着“再过三年我兴许就能忘了他,那时心里就不会这么疼了”。老朴走后,她只跟二大说“爹,我手把绳子抓得老紧”。葡萄心里的不舍、难过都在这一句话里了,她知道老朴这一走,她就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葡萄这一生,拥有过那么多男人的爱,却一次又一次地看着她喜爱的男人离开。葡萄看上去没有心思,可是一旦动了心,那比谁都重。她不去送老朴,或许是她在最后都想留给老朴一个没心没肺、乐知天命的样子,她要让他安安心心地走,因为她明白老朴是注定不属于这里的,离开这里后他可以有大好的前途、大好的生活。
严歌苓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了一个行走在历史横截面之外的平凡女子的传奇人生,苦难的一生从来没有抹去她该有的美,她就像一株真正的葡萄,不管气候多么恶劣,它只管自在地结果,自在地分泌酸甜的汁液。历史的残酷与浑浊改变了身处其中的人,而她却无惧无畏地释放美好人性,普救众生。她活得任性潇洒,不受世俗的规约,敞开自己的心胸承接一个又一个男人的爱。严歌苓塑造了那么多的女人,只有她最特别,也最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