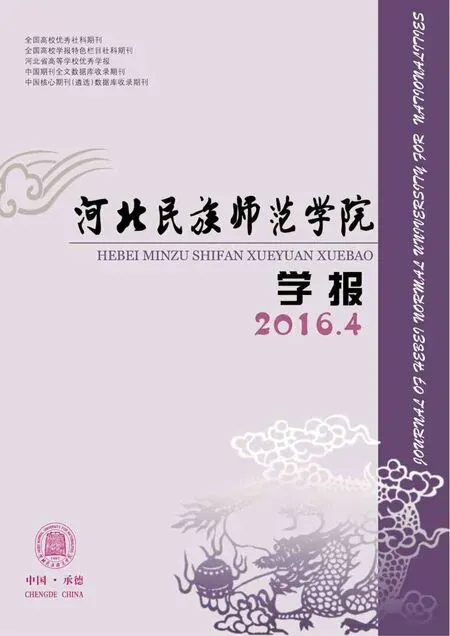把高海拔的雪花带回低海拔的生活——陈劲松散文诗文本简读
黄恩鹏
(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 100081)
把高海拔的雪花带回低海拔的生活——陈劲松散文诗文本简读
黄恩鹏
(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 100081)
陈劲松是一位纯净的散文诗人。他长年生活在青海格尔木,因此他的文本中有诸多明亮的高原意象:湖水、雪山、月光、鹰隼、青稞、冰雪、花香、麦子,这些自然元素,成为他喻指心灵和生命精神的重要代码,也为文本意境的扩展和意义的生成注进了活性。诗人对物象精神品质的把握和对人本价值观的开掘有敏锐的认知,作品呈显了他“劝诫”的美学对现实社会巧妙的批判。他的文本呈现出冰雪般的魅力:一是纯净的价值观与纯净的精神本质;二是“劝诫”的美学与批判现实主义;三是高原的精神征象成为文本的元素。陈劲松散文诗的魅力,还体现在他对语言精到的打磨和对人性的隐秘中心的打造上。
陈劲松;散文诗文本;高原;精神征象
两年前,我写了一篇研读陈劲松散文诗文本的论文:《对人本价值观或精神品质的坚守——读陈劲松的散文诗文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国家社科学报核心期刊)2014年第1期上发表。这篇近15000字的论文,已然道尽了陈劲松散文诗的文本特质。文章最后,我就陈劲松文本的价值,曾作如下结论:一是能在语言的铸炼中,贯注对现实的隐喻性批判。这种批判不张牙舞爪,而是以唯美“冷抒情”面对;二是在风景面前果断转身,赋予人性的思考。否决“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斫伤,让写作“离经叛道”;三是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个人标签”式的诗艺品格。
这三个判断,应该准确。在我看来,陈劲松是一位有着“纯净”和“孤独”两种境界的诗人。纯净境界——他的文本中有诸多明亮的高原意象:湖水、雪山、月光、鹰隼、青稞、冰雪、花香、麦子,这些自然元素,成为他喻指心灵和生命精神的重要代码,也为文本意境的扩展和意义的生成注进了活性。孤独境界——格尔木,或者说整个青海,写散文诗的似乎只有他一个(我说他代表青海的散文诗创作,这一点也不过分)。以上两种“境界”,决定了他对物象精神品质的把握和对人本价值观的开掘有敏锐的认知,作品呈显了他宗教般的“劝诫”美学和对现实社会巧妙的批判。陈劲松出生安徽砀山,大学毕业后即留在了青海高原格尔木。从秀美江南,到苍茫昆仑大地,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人生际遇的大改变。首先,他要战胜缺氧的高原反应,让自己平凡的肉身适应。其次,他要面对的是大地物象的不同,从砀山著名的遍地梨花,到青海大地疏散的红柳,这其间有多少生命的征象喻示着他的梦想变化。第三,他笔下的冰雪大地高原荒漠,要完全区别于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人家。这种“变化着的”漂泊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或多或少存在过。但是在陈劲松这里,却是如此的反差巨大,是他年轻时不曾想到的。为爱情?或生存?或许都是原因。陈劲松的散文诗作品,大概有三个层面的呈现:
一、纯净的价值观与纯净的精神本质
青海的月亮是照彻心灵的,做为一种精神喻象,有着超越性、丰富性和广延性。事实上,高原的月亮真的有别于内地的月亮。不用诠释,也不用理念去辨析月亮的清浊。高原之月,本就是一个现成的“纯洁的精神征象”,它的本质是精神性的,不带着有世俗的成份。它是一轮冰雪之水洗净了的月亮,借着灵魂的水光,能医治世俗之病痛。“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1],精妙概括了自然物象对人精神时空所起的作用。《3点45分的月光》揭橥诗人沉夜因病难眠的精神状态:寂寞、孤独、寒冷。“苦艾”是思念的脉息,也是纯净与孤独的味道。“轻移莲步”一词用的极妙,这是月光的动态,也是心灵的动态。让“神”作为一种抽象精神,存在主体之中,随时听见灵境的吁唤。神畅而病除。俗世的药不起作用。那么,没有审美心胸去看待月亮,也同样是“失效的药片”。这是“神机自运”获得的自我调适:“与我一起失眠的那一小片月光,在我枕边,心痛般,谁也无法拿走。”完全契合了苏轼所言的“自然本无常主,见者便是主人”[2]的人生观。其人生体验是一个“精神递进式”过程:身体之痛——精神之医——月光之感——时光之惜。因为月光,诗人孤独寂寞;因为月光,诗人富赡自适。文本中的诸多月光,浸透了他的“东方式”的哲学思考:
“由一小片的月光开始,我热爱天空中那枚孤独的月亮,它多像一个人被时光吹凉的背影啊。”(《今夜,我和幅员辽阔的爱》)
“回家的人,那枚月亮是他富足的盘缠。”(《月夜回家的人》)
“被无边的苍茫一遍遍锻打过的银币,它的光芒被斟入十万雪山的灯盏。”(《荒原上空的月亮》)
“只有干净的月光在它体内踱步。”(《青海湖边的小镇》)
自然之圣美,楔进了人的精神。一方面验证宗炳所言的“畅神”之“澄怀味象”,一方面又能将庄子的“物化”审美运用得机巧、灵动、曼妙。他的作品,有许多“神机自运”之精神征象:飘逸、峻峭、幽独、超拔。“仰望意识”进入文本,有效地拓展了文本的创作张力。用海德格尔的形象表述就是“此仰望穿越向上直抵天空,但是它仍然在下居于大地之上。此仰望跨于天空与大地之间”[3]。时间有了具体的形质,精神空间达天入地,生命本态虚极静笃。并能涤除玄鉴,融入灵魂。在《梨花,梨花》组章中,同样以物象“梨花”的纯粹来求证自身生命本态——《想象梨花在夜晚开放》之孤独、傲然、寂静;《梨花把故乡的夜色映浅》之人格操守、品德独立;《镜像:梨花·白马》之美好人生易逝、流变、叹惜等等,无不体现对人本价值的探求。《病中书》是自身的生命体验。一个生命的个体,带着病躯之身行走在这个世界,他所触到的不仅仅是肉体之痛,也有着精神和灵魂的疼痛。这种疼痛是不能殒灭的,它来自对生命本身和孤寂的震荡。“一个人紧绷的胸膛里,露出泄密的呻吟。”“心脏”是一个人的重要器官,它承载着躯身,更多的,是精神之形。而在这个精神之形,要保持完好,需要多少岁月的呵护,以及对于风雨的承担?“它从不曾褪色,依然鲜红,它跳动如昔,像上帝安置于我体内的时钟。”陈劲松让自己对于病痛的理喻,成为对于人生的理解。很平常,但无不透析我们难以触摸到的思考。这是人生的苦味,需要品咂。《六月,在甘南》组章,是陈劲松对美好事物的抒写,“六月,在甘南,一只蜜蜂,它轻易就打开了一个诗人诗歌中虚掩的门。”当一位诗人带着梦幻的脚步踏上甘南时,一种清澈了天、朗润了地、映彻透了心灵的大美风光立即吸引了他。与诗人居住的青海高原一样,在甘南,蓝天、阳光、草原、星辰、花香,也都是一尘不染的。恍若莅临天堂圣境:那被高原的溪流洗得发亮的绵邈苍茫的牧歌属于他;那被遍野草香和花魂萦绕的安详大地属于他;那被草原的阳光滋养得壮硕的牦牛和羊群属于他;那被自然美境陶醉了的几位诗人心灵沟通属于他……甘南山川的静美、无边的蔚蓝和大写意的辽阔,随纯净的文字静静漂泊,让俗世一切浑浊在这里全部退让。他让这些流诸笔端,一种大净之美。
二、“劝诫”的美学与批判现实主义
《草不知痛》是写圆明园诗意浓醇的一组。对历史的遗忘和集体价值观的失落,是后现代人的特征。因此这一代人的“心灵重建”是诗人思考的问题。《草不知痛》的“草”从废墟的缝隙里生出来,暗喻从苦难大地诞生的新生代人群,最不该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是相当可怕的,也是没有希望的。这章作品这不动声色批判,也是对一代人的提醒。陈劲松在写作时,是将废墟般的石头当作了墓碑来读解,而诗文本则是墓志铭。事实上,一个民族给一堆石头树碑是容易的,但是若是给整体的心灵树碑却又是很难。圆明园在都市的一个角落,周围是人车来往密集的现代化街道,那些硕大的广告牌和高耸云天的商厦,与这样的“历史废墟”,形成了明显的比照:一边是被遗忘了的历史,一边是有着快速增长点的现代社会。但,我们后现代的人们,却并没有将这样的历史遗存当作心灵教材来看,这真的很悲哀。《养雀笼》写一个王朝因腐朽而垮塌:“那些养尊处优的鸟儿歌声柔软,啁啾鸣啭,回荡在一个王朝溃烂的咽喉部位。”昔日光彩闪闪的鸟鸣,不能阻止战烟的摧毁。历史的枪炮,不会因为阳光中的一两声清澈的鸟鸣停息,我们仍然会思考那些在鸟鸣中凋败的命运:“在石头上坐下,谁依稀听到滴落的冰凉的鸟鸣,谁就能抚摸到一个王朝还未消散的隐隐的痛。”“雀”本应是自由自在的,却被关在了笼子里。喻象明晰、准确。在《那只低飞的乌鸦》中,乌鸦之黑与废墟的灰烬之黑,是一个藏着噩梦的警示。“是废墟上飞起的一粒灰烬,还是一百多年前剪下的一小块黑夜?”以“黑”来代替不堪的历史记忆。“黑夜”“黑木炭”“黑衣”等,喻写民族记忆的苦难。这个苦难的颜色,是火焰之后的黑色。黑即是无,是一段断裂了的历史之思。《火,依然燃烧》是这个组章交响乐的再现部,“灰烬”是无法再燃烧的,它丧失掉了本质的精神态和燃烧的力量。但是,火可以燃烧心灵的薪柴。这堆薪柴是取之不尽的。只有“遗忘”的“灰烬”才是绝灭了燃烧之本态,也正是丧失了记忆的精神本态。这组作品,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感”,是另类的批判现实主义精品力作。
陈劲松有这样的“散文诗观”:“诗歌应该更注意引体向下,让文字能够抵达时代的疼痛。”[4]这种强调“意义”存在,胜于单纯的个人表层化的小花小草杂咏抒情。作品外在平静,内里波涛汹涌。一些作品虽短,却似闪电般快捷、有力,直抵事实本质。《一棵树》既有浪漫主义手法,又有批判现实主义立场,更有大的精神意蕴。诗的开始以浪漫的姿态和悲悯的情怀,呈现一棵树的存在是天地大美:“我写到的那棵树:它有鲜花的头饰,清风的披肩。它有露珠的项链,鸟鸣的耳环。”借古人的妙境说:“陡然一惊,正是词中妙境”[5],这美出其不凡。赋树之美,是为后面的苦难做出铺垫。这种美就在人的恶欲下被砍伐、被剥夺去生命。他在树身上寄予的是对人类启示性的力量。这种大美体现在将树比喻或拟化、类比高贵的女性,以此求证这棵树的非凡。接下来他写曾经无数遍关爱的“那棵树”,“它在春天跌倒”——春天本是遍布生机的时光,却是死亡的降临。“一把斧子”将树送到了死亡深渊。凸显时代的沧桑感、悲凉感和疼痛感。过去的时空是绝美的,现在的时空是被残害的。去除了图式化的鞭挞,进入一种巧妙对现实的质问。他看到的,不止是“一根肋骨”,是“更多的春天的肋骨正被抽走”的更多苦难。以个体的苦难喻示众生的苦难。“咬着牙关”面对快速的砍伐。树的伤口,有百年的沧桑和时间大河的涛声,有旋荡的清流和岁月的见证。“第一圈”与“第一百圈”,从历史到现实,树被一只只罪恶的手斧砍锯伐,是人之罪恶。那么,制造个体苦难者,也会为整个大地制造集体的苦难。诗人将树比作春天的“肋骨”,为了凸显人的苦难,所获得的,是迥异于众家的“审美惊奇”,是“从灰烬里取回那首诗歌中词语的白骨”(《纸灰之冷》)之写作殉道精神,虽小叩,却发大鸣。
三、高原的精神征象成为文本的元素
《高大陆》苍劲的鹰翅,总能让我有拔升大地、抬高长天的感受。文本中多处有鹰闪现。鹰是高原的喻象。在西方文学里,鹰的喻象是上帝的使者,是上天之灵。在中国文学文本里,鹰同样有着无可比拟的神圣力量。它与太阳一样,是天高地远的生命征象。但鹰又是孤独和寂寞的,一种超越自然伟力的孤独和寂寞,在诗人的内心深处,找到了共鸣:“鹰,用飞翔的翅膀,扩大着整个天空的面积。”“一座座雪山多么从容地收藏起大雪、风暴、雷霆。”“没有固定的逻辑能让一只鹰放弃飞翔。”“正如不能把一只鹰从天空删去。死亡也不能!”“天空是一本巨大的书,鹰在疾风暴雪的情节中穿行,像是书中的一个突兀的细节。”诗人对鹰的恭诚、谦卑和敬仰,让纯净的高原风雪施洗。那只鹰与一座座雪山,是诗人的理想主义大情怀的显露。只有这里,才能让他成为“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实现生命理想。文本中又有“盐”、“铜”、“雪”、“酥油”、“青稞”、“羊群”、“红衣喇嘛”等等这些高原意象,在意念的引领下,这些意象进行组合,让一个个神性的灵魂,在明澈的阳光下粼粼闪光。如此雄浑悲慨,只有长期在高原之上生活的诗人,才能写就。高原的物象,是真如的本体,而人在这里,则成了客体。“真如本体是空寂的,由此中国佛教又把照与寂连用,从而有寂照和照寂之说。寂,寂静,反映真如本体的空寂状态。寂照,即寂体(真如本体)的观照作用。”[6]高原的诸多物象,在文本中起到的是“照”的作用,是镜像对人本的照鉴。“而我们小小的吟哦,微笑以及藏得深深的泪水与哭声,究竟能在你的怀中保留多久?”“我已决意在风雪中凿室而居。在下一场风雪到来之前,我该如何打扫我世俗的内心,让那盏叫做灵魂的灯,一直亮到春天?!”诘问和自信的结尾,是意义的倡扬和彪炳,恍若攒地而起的圣乐。陈劲松以文本为载体,盛装起高原的诸多意象,将高原精神与生命品格融铸在了一起,将灵魂的灯盏与血液的火光映在了一处。打造大意境,让精神高扬起来、立体起来、纯净起来。这种人格化了的心灵场域,是活在低洼处的诗人不能映射到的。
《青海湖》的意象之美让大地的色泽清亮。可以说诗人以“青海湖”来言天地大灵魂之美。诗人运用了蓝白黄三色。以油画般的“高光”技巧,将高原的神圣之湖瞬间涂亮。这是诗人超乎常人的喻象手法。在文字的一连串完美组合里,创造着诗的绝美奇诡之镜像:“一滴雨落下。那只停下来很久的白马又开始走动。我猜测:它的体内,一定有一座,开始融化的雪山。”这个结尾出人意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我在读这个文本时,思考为什么陈劲松要用“一滴雨”、“一匹马”和“一座雪山”来作结句?将这三个意象联结一起,是一位诗人所要追求的精神品藻!在对意象的把握和意境的铸造上,可以说,陈劲松非常杰出。耿林莽先生在《以意为帅 意在象中——对散文诗意、象关系的思考》论文的“摘要”中这样辨思“意”与“象”的关系:“‘意’和‘象’,是散文诗创作中的两个基本元素。孰先孰后,难以作简单的定论。‘象’是客观世界共性的存在;‘意’是诗人主观世界思想的形成。在散文诗创作中,‘意’不仅仅是诗人的思想、哲理性思辨,还应是情绪、感情的载体。将‘意’渗入‘象’中,心附物上,物化于心。这种思想的化境与铸炼,是诗人创作思维的一个相当艰辛而又复杂的过程。以意营象,意在象中,讲的是诗人的‘在场感’,也使得散文诗的抒情功能、思想意义指向更为明显、立体,有着纯美的个性色彩。”[7]如此“意”与“象”之辨,再明朗不过。散文诗文本的魅力,在于语言打造。陈劲松散文诗语言镜象,已然有着完美“意象造境”之个性化的标志。“意”与“象”是诗文本的生命,也是妆扮语言的必须,它能让文字“精神性”得以腾跃、展放。
《做一株麦子》是一章耳熟能详的作品,被收入了全国的幼儿教材,被众诗家赞为充盈着“阳光之作”。诗人将“麦子”人格化了,为人生理想与价值取向。语言形象、生动:“做一株麦子,在阳光中,向天空亮出自己小小的绿色的誓言”“在积雪下,叫醒最早的春天”。麦子的品格也是人的品格,从麦子的精神征象里抽取其谦逊的品格也是对理想的探求。这章作品很适合朗诵,其唯美的语言,闪烁心灵的方向。特别是在当代“出了问题”的中国的教育面前,一位诗人用他平静的呼喊,道出了我们应坚守的生命品格。由此我想到当下的新诗或散文诗,太需要一种人格化的集体的人性向善、精神向美的思考,而非那些不切实际的“历史虚无主义”浸泡孩子美好心灵的作品。《做一株麦子》是陈劲松用“高原”纯净元素创作的精神征象文本的一个很好的体现。这个体现,与恶俗社会的教育方式不同。它的意义在于:诗人的责任,是为我们的这个社会输出了一个纯美于心灵理想的生命价值观。
文本中还有许多“高原物象”,对人本精神的照鉴:
“诸神依然沉睡。 白头的豹子土地般沉默不语,它藏好自己斑斓的花纹。一滴雨水,还未给天空松绑。那场风,一张嘴,就说出了漫天的沙尘。” (《格尔木的春天》)
“轻一些,再轻一些。美,如薄胎的瓷,如瓷质的月光,如月光的背影。远一些,再远一些。别去试图触摸,那大荒原的心跳。”(《藏羚羊》)
“吹笛人,十指间一截雪白的坚硬的骨头里,拒绝流出陈旧的阴影,腐烂的嘘叹。”(《鹰笛》)
“在贵德,每一滴水都是神的幼兽。”(《在贵德,问一滴水》)
“万物被神放下,谁用秋风独自打扫,身体内的暮色和落叶。”(《高原秋日》)
探骊得珠,精短取胜。陈劲松走的是唯美化、精品化路子。每一字,每一句,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精心磨砺,玲珑、圆润,像小琥珀、似小玉器。意与象的有效结合,有效相映,把句子打磨得精美,就连一个标点符号,也绝不敷衍。作品的话语矩阵不复杂,清晰如缕。也绝不啰嗦或有意拖长句子结构,又有点儿像古代中国画作中的大量“留白”,总是能留下一定的空间,给读者创造想象的天地。而这个想象的天地,又总是能够牵绊着他的句子产生的唯美体系之中。事实上,陈劲松的散文诗作品,也是在呈现散文诗的一种观念,是存在的文本里某种梦幻般的特质,并用这个特质去掌握他的人生中的壮阔风景和高原的地志学。他掌握了太多的意象,又浓缩得如此精妙。句子与句子之间,有时候钳进一个很小的词,却能起到很大的裨补作用。是一种记忆,中间放入了一个间奏。让读者联类思考,但又能起到命题的效用。比如《纳赤台》《海拔5000米的草》《红柳》等等。这种语言的炼金术,给了他独特的文本特质,在当下散文诗界中,并不多见。在新近创作的《格尔木的夜》,这章仅有45个字的作品,具有“小中见大”的散文诗的美学特征:
风磨砺着风的嚎叫_____
格尔木的夜,有金属的胸腔。一个心怀大海的人,他咳出瘦小的海水,
和它的蓝。
许多作品,也是精短。如:《三月》《格尔木的春天》《沙枣花开了》《雪山》《高原秋日》《思念》《红柳》等等,四两拨千斤。很符合耿林莽先生提倡的散文诗要“小中见大”之精品化创作理念。阅读陈劲松的作品,总有一种如同《音乐之声》那种陶醉的场景:“大地真美”——雪山耸立。草地围绕。山水畅流。天空旋转。生命与自然相遇,“通灵者”再现。我想,青海大地之美,是精神性质的。这个精神性质,需要的,正是陈劲松这样的诗人,来解读高原神圣或神秘。我认为,他是一位敢于突破题材、并有独立思考品格的诗人。他在文本中找到了与生命相联系的敏感触点,不断打磨出思想含量高、隐喻性强的精品力作。
耿林莽先生这样评价陈劲松的散文诗:“劲松的散文诗语言简洁莹透,散文诗作品或清丽柔婉,或浑厚奔放,或简洁凝练,既有着浓浓的抒情,又有着理性的叙述。挺拔,刚劲,内蓄激情,语言深处深蕴力度,他在语言上狠下功夫,锤炼经营,不遗余力。结构上飘逸、灵动、干净,形成硬朗骨质和刚健清新的力度美。他的散文诗有着很强的美文质地,受到读者广泛的喜爱与推崇,我想,其原因之一,或即在于他对美和意义性的处理较为恰当……他的捕捉诗意美的能力,主要来自细致入微的感觉,及由此派生的丰富的想象力,这可能是他创造美的两大法宝吧。”[8]耿老对陈劲松的评论切中肯綮。
我曾有到过格尔木的经历,深知高原生活的艰苦程度。特别是冬天,在可可西里高原,因为缺氧,就连麻雀都是贴着地皮飞而无法振翅高翔。但他,却把自己的一生给了这里,把自己的肉身“流放”到了青海格尔木,把自己的梦想像红柳一样栽种在了这里。从南到北,茫茫荒寒,踽踽独行。他在青海大地,享受着大美的自然神灵的眷顾和爱怜。感知“白头的豹子土地般沉默不语,它藏好自己斑斓的花纹”(《格尔木的春天》)的神圣;感受“一尾红鱼,在石头深处醒来”(《荒原》)的苍凉;感喟“惊雷深埋于天空”(《三月》)的湛蓝;感叹“一场雪在海拔4767米的天空出现,我却无法把任何一朵干净的雪花, 带回我低海拔的生活”(《昆仑山口》)的圣美。由此我读到了他的文本呈现冰雪般的唯美:虽然说严寒的高原艰苦,他却在时时寻找内心的“乌托邦”,将高原山川物象看作是他生命本质的一部分,从而建立起属于他个人标签式的“灵魂家园”。文本呈现出的是:人本纯净的精神操守、追求以及善美的价值观。更多的是对世俗的反抗和做人的坚持。一如诗人所认为的,要做一块“拒绝融化的冰”。陈劲松散文诗的魅力,还体现在他对语言精到的打磨和对人性的隐秘中心的打造上。细致、机巧,有如玉器在握,甫一触之,沁凉、冷肃,久握就会有生命的热量迅速传导其中——这是诗的品格,是青海的品格,是肉体之温与玉器之温达成一致的生命品格。是带有高原气象冰雪气质的抒写。而这种抒写,我似乎只有在青海诗人昌耀的文本中发现,那种宗教般的圣心所化育的品格,超越了明确的方向感而坚守的一份真实。这份真实,是他时时为摆脱被现实击伤的灵魂之痛之诊治的有效良药。
[1]宗炳.《明佛论》.
[2]苏轼.《临臬闲题》.
[3]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192.
[4]灵焚主编.散文诗选·大诗歌(第一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5]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6]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32.
[7]耿林莽.以意为帅 意在象中——对散文诗意、象关系的思考[J].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2,(3).
[8]《文学报》2015年12月31日《散文诗研究》第24期.
Bringing High Altitude Snow Back to the Life of Low Altitude:a Brief Reading of Chen Jinsong's Prose Poem Texts
HUANG En-peng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cademy of Art, Beijing,China)
Chen Jinsong is a pure prose poet. As he has lived for years in Golmud, Qinghai, there are many bright images of plateau in his texts: lake water, snow mountain, moonlight, hawk, highland barley, ice and snow, flower fragrance and wheat. These natural elements have become significant codes that are used to refer to mind and the spirit of life, having injected activity into the expansion of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the generation of meaning. The poet has acute perception of how to grasp the spiritual quality of images and how to explore the values of human, and his works show skillful criticism of social reality with his “exhortation” aesthetics. His texts present the charm as snow and ice: The first is pure value and spiritual essence; the second is “exhortation” aesthetics and critical realism; and the third is the spiritual signs of plateau becoming the elements of texts. The charm of Chen Jinsong's prose poetry is also reflected in his ability of polishing language and building the center of secret human nature.
Chen Jinsong; prose poem texts; plateau; spiritual phenomenon
I206
A
2095-3763(2016)04-0056-06
2016-09-01
黄恩鹏(1967- ),男,辽宁沈阳人,解放军艺术学院科研部文艺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艺术学、文艺学、现当代诗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