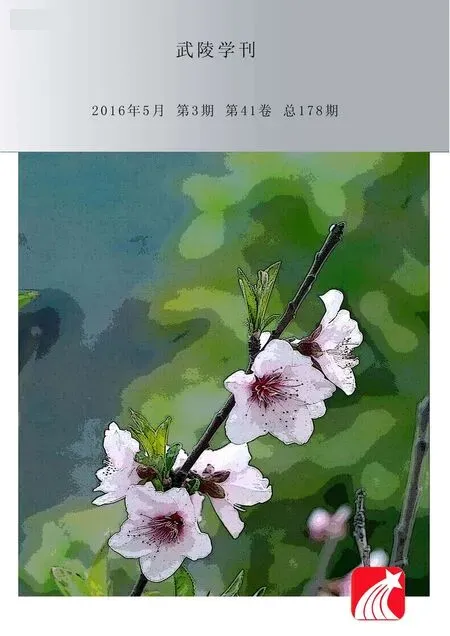论文学翻译之消极文化误读
岳曼曼
(湖南文理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论文学翻译之消极文化误读
岳曼曼
(湖南文理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文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文学翻译过程中存在积极文化误读和消极文化误读。不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及目标语的语言使用习惯,易导致消极文化误读。加强跨文化意识培养,塑造宽容、兼收的翻译文化观,能够有效地规避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消极文化误读。
文学翻译;文化差异;消极文化误读
文学翻译从本质上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语言活动。它作为语言以及文化传播的载体、一国与他国间跨文化沟通与交流的桥梁,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文学翻译的过程包含了对原文本信息、深层意义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传递,其中,译者扮演了信息以及思想文化的传递者这一重要角色。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提出:“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熟悉一国的文化甚至比掌握一国的语言更为重要,原因是构成语言的文字只有在其生存的文化语境中才获得意义。”[1]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作为一种手段,起着桥梁的作用,从深层意义上说,翻译是以文化移植为根本的跨文化活动。研究翻译必须正确处理语言与文化两者间的有机关系,并探析不同语言的文化特征及其根本差异。传统的翻译研究倾向于将翻译视为两种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极为注重语言成分的转换,忽略翻译中文化因素的作用以及跨文化的核心实质,易形成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漠视,频频产生文化误读,从而导致文化误译。爱德华·泰勒指出:“文化实则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具体涵盖知识、艺术、思想、信仰、道德、习俗、法律以及其他沿习下来的社会习惯与个体习得能力。”[2]
翻译是运用目的语语言把原语言的思想和内容重新表达的语言活动。表面上看来,翻译似乎只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实质上,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和手段,它是文化的基础,反映文化的方方面面。语言的不同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历史演变进程中,各种文化形态异彩纷呈,导致不同的语言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一方面体现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另一方面呈现在语言的内涵上。
一、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
杨武能先生曾将文学翻译的过程表述如下:作家→原著→翻译家→译本→译者[3]。作家创作作品的过程主要为以物化原著为核心。而翻译中,译者需要对原文本有一个从浅至深、全面充分的了解,实现自身与原文本创作者的沟通与对话[4]。这种对话不是基于一般意义的理解,而是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对原语实现创造性发挥与接受的过程。受不同“审美期待视野”和接受视域的影响,不同的译者对原著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这是理解阶段。译者获得对原文的理解之后,紧接着的任务就是用最自然、最贴切的语言把这一理解表达在目的语中,形成译文,这就是翻译的表达阶段。翻译好比绘画,原文蕴含的内容就如画家心中所感知体会到的客观世界,可形容为第一自然。译者也如画家,他的主要任务是用自己的文字把自身所见到的第一自然重新用语言表达出来,构成一幅图画,这又可以被称为第二自然。这样的一个翻译过程是译者从无到有、心领神会的再创作过程。换句话说,文学翻译过程中,作品的再构建必须通过创造来达到目的。
与文学作品的原创造性质相比较,文学翻译的创造性质不同,它属于二度创造,即再创造[5]。这种二度创造过程中,文化的解读效果也呈现译者主体性的特征。当今学术界,文化误读成为一种较受关注的文化现象。宏观上而言,作为一种阅读态度,误读在各方面体现和影响读者对于一种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体现在对原文的正读或误读里,这往往会导致不同译文的产生,揭示译者不同的文化态度和理解。作为一个术语,“误读”最早是比较文学界在对两种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在解读原文时,读者与作者不可避免会产生理解上的不一致,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关于“误读”,学界一般用“misreading”来进行阐释。国内著名比较文学研究学者乐黛云对“误读”也有过界定。她认为,误读就是在与他国文化接触时,一方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心理、思维模式,往往只能根据自身业已熟悉的文化传统、内容等来解读他者的阅读方式[6]。
根据文化误读的原由和特征,文化误读可分为消极文化误读与积极文化误读。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而出现的,读者无意识的误读为消极文化误读。这种误读是由于目的语言的读者知识、水平等方面的欠缺,对认知对象的理解不足,缺少对原文语言内涵或文化因素的了解所造成的。积极文化误读则为读者有意识的误读行为,这种误读往往基于某种特殊的文化、思想或政治目的,导致译文的变形,但同时又有益于译文的创新。下面,笔者想就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消极文化误读进行探讨,以期对文学翻译实践有所帮助。
二、文学翻译中的消极文化误读
前文谈到,文化误读可分为积极文化误读与消极文化误读。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消极文化误读往往导致消极文化误译。消极文化误读主要为以下两种:
1.词汇层面上的误读。词汇是一国语言中最生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成分。每个国家的物质状况、社会结构、文化信仰等都是由该民族所独具的词语表现出来。基于不同地缘、不同历史、宗教和民族文化差异,一国对外部世界独特的认识都灌注于其民族所创造的词汇中。正如著名文学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所述,他处理的不是单个的词,他面对的实则是两大片文化[7]。译者如果对于中西文化以及语言使用习惯不熟悉,就非常容易造成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误读。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著名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创作了一部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文学巨著——《围城》,在国内外文坛引起了轰动。但据笔者的研究,《围城》英译本由于译者对于原文的某些误解,在一些方面存在着消极文化误读。汉语的成语结构独特,寓义深刻,可谓中国语言文化的精髓。要将汉语成语转换成英文,对译者而言并非易事。例如,在《围城》中,方鸿渐的父亲为了节约,不愿意请乳母,向其媳妇解释时说道“上海不比家乡,是个藏污纳垢之区,下等女人少有干净的”。这句话译者译 为 “Shanghai wasn’t like their village but a disreputable place where very few of the lower-class girls were clean.[8]”disreputable这个词被用来表达藏污纳垢之意。这个成语是由两个动宾结构“藏污”“纳垢”组合而成。译文的disreputable为普通的形容词,译者这种采用一个形容词来简单替换寓义深刻的成语,极大地削弱了原词的语言力度和表现力。“藏”“纳”意义相近,“污”和“垢”喻指“坏人坏事”。这个成语一方面表达了方父态度的坚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身为文人的语言习惯。所以英译时译者须将原语的文化内涵以及这个成语所体现的痛恨之情充分传递出来。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认为“藏污纳垢”应当改译成“a sink of iniquity”较好,修改后的译文为:Shanghai wasn’t like their village but a sink of iniquity where very few of the lower-class girls were clean.又如“鸿渐鞠躬领教,兴辞而出,‘phew’了一口长气”。这句话中“鞠躬领教”被简化译成“bowed politely”,而实际上,鞠躬只是一种形式,领教才是真正目的。译者并没有领会这个词的结构和深层涵义,于是做了简化的处理,致使关键信息流失,造成了词汇层面的文化误读。对照原文,其实可以做出这样的修改:Hung-chien accepted his instruction,bowed politely,then saying goodbye,he left,letting out a long-drawn-out“phew”.
2.宗教、民俗、地域文化方面的误读。相对而言,宗教、民俗、地域文化方面的误读可归纳为宏观层面上的一种误读。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中起基础作用的人文基调。中华民族具有谦虚谨慎、韬光养晦的性格特点,尤其反映在谈到与自身相关的事物时,往往喜欢用谦逊的口吻和词汇去表达,而西方人的民族性格与中国人的谦卑不同,他们不论言语还是行为通常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宗教文化差异也是文学翻译中时常会导致文化误读的因素。中国人信奉的三大宗教为“儒”“道”“佛”。西方人主要的信仰为基督教,宗教信仰方面的意识差异对翻译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西游记》中的“阿弥陀佛”被译为“God bless soul”,就极大地削弱了原文的意义,这反映了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内涵的流失。而有些译文就基督化色彩较重,很多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天”都被翻译成“God”,译文的英语中心主义倾向较重。众所周知,英国为海上大国,英语中有大量与航海有关的表达方式。对于这类地域文化的翻译,译者须重现原语的文化特质,必要时加以说明。“东风”在中国人的心里,代表着“温暖和春意”,故有“东风报春”一词。而与此不同的是,英国的东风象征着寒冷,因而他们只喜欢给他们送来春意的“西风”。诗人雪莱就曾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西风颂》,其中的一句:Oh,wind,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这里的wind就体现了中西地域文化的差异。如果译者忽视了中西地域文化间的这种差异,将《西风颂》中的西风直译为west wind,会极大影响这首诗歌文化内涵的传递。
三、文学翻译中消极文化误读的规避
1.词汇层面消极文化误读的规避。词汇是一国语言的基本组成部分,文学翻译过程中,中西语言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语言上的差异,才使得翻译具有价值。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语读者由于缺乏原语作者与读者两者间共同拥有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在解读文学作品中容易产生文化空白。因此,作为跨文化沟通的中介,译者的跨文化意识至关重要,将直接影响译语读者对文学翻译作品的接受情况。一些译者从某种方面而言,虽然能够保证原语与译语在词汇传译上的准确性,但不能达到精妙的翻译效果。究其缘由,就是译者的跨文化意识不足。这种意识的不足致使译者在接触他者文化时,始终囿于自己所处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理解模式中,仅从单维度的方面对语言词汇中所蕴含的文化内容进行选择性的判断,导致消极文化误读。这种文化误读的例子很多,其中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为,国人馈赠他人礼物时,喜欢说:“一点心意,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些译者将这句话译为“It is just a little gift for you,which is not so good.”这句话的原文和译文在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心里产生的效果是截然相反的,心意和好东西都是中文里最普通平常不过的词语了,但正由于译者在理解中产生了消极的文化误读,尤其是面对一些深含文化意义的词语时,没有补充文化空白信息,从而导致的负面效果。因此,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加强语言层面上最基础的部分——词汇层面上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解读能力,尽量规避消极文化误读。
2.宗教、民俗、地域等层面消极文化误读的规避。宗教、民俗、地域等层面反映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一面。文学翻译过程中在处理宗教、民俗等一国特质文化内容时,一些译者往往不能译出优秀的作品,就如前文提到的那个例子,《西游记》中的“阿弥陀佛”被译为“God bless soul”,造成了文化误读和文化内涵的流失。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译者自身受到原有文化的严重束缚,很难发现异域他者文化语言中所隐含的独特文化信息,因而日益形成了一种封闭、保守的文化态度。为此,译者在面对别国文学作品时,必须要以宽容的文化观念去认知、接受他者文化的不同,抛开文化歧视和偏见,把自己定位在原作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中,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原文学作品的特质文化信息,尽量避免文化误读和翻译结果的偏离。《红楼梦》中有一句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将其译为“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原文的大致意思虽传递出来了,但深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天”的概念消失殆尽,仅以“weather”一词简单替代,原作的文化意义几乎都丧失了,译者的这种消极文化误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目的语读者去感受异国独特的文化魅力。中西文化差异是客观的存在,译者不能透过语言的表层形式,不去深入分析源文化的深层结构、文化意象和文化内涵,仅以自己比较熟悉的文化观念与主观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和阐释异域的“他者”文化,这必然难以减少文化误读和正确传递源文化内涵。文学翻译中的译者应当摈弃封闭、保守的文化态度,培养宽容、兼收的文化观,对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刻的把握,从而有效地规避消极文化误读。
结语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还包含了异质文化间的交流,文化因素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学译作的产生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学再创造,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有文化主导意识以及译者主体性意识,不能信笔挥毫、洋洋洒洒撇开原作,也不能完全臣服于原作,而是要将文学翻译置于跨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深刻体会中西文化差异,增强跨文化意识,并培养宽容、兼收的文化观,在两种异质语言和文化的空间内创造性地发挥,形成积极的文化误读,避免消极的文化误读与文化误译。
[1]Nida,E.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2]方梦之.译学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305.
[3]杨武能.尴尬与自如,傲慢与自卑——文学翻译家人格心理漫说[M]//许钧.翻译思考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43.
[4]袁莉.也谈文学翻译之主体意识[J].中国翻译,1996(3):4-8.
[5]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M].上海:译林出版社,2010:14.
[6]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
[7]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大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85.
[8]钱钟书.围城(汉英对照)[M].珍妮凯莉,茅国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刘英玲)
On Negative Cultural Misreading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YUE Manman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Changde 415000,China)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n intercultural activity.Positive cultural misreading and negative cultural misreading both exist in this process.Failing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language usag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will lead to negative cultural misreading.Strengthening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and fostering a tolerable and all-embracing cultural concept is efficient to avoid negative cultural misreading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cultural differences;negative cultural misreading
岳曼曼,女,湖南邵阳人,湖南文理学院教师,湖南师范大学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和比较文学。
H315.9
A
1674-9014(2016)03-0117-04
2016-03-09
国家留学基金委联合培养博士项目“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研究”(20140672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