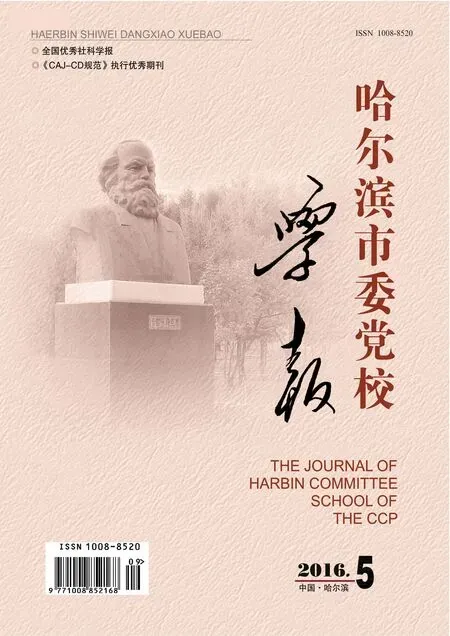东北解放区哈尔滨特别市法制研究
——以《哈尔滨市施政纲领》为视角
迟 政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东北解放区哈尔滨特别市法制研究
——以《哈尔滨市施政纲领》为视角
迟政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哈尔滨市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早接管和解放的大城市,其在政权和法制建设上表现出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1946年哈尔滨市临时参议会通过的《哈尔滨市施政纲领》作为宪法性文件,最具有代表性。它在政权主体、恢复和发展经济、外侨问题的规定上有很多特色内容,并且对哈尔滨市的政权建设和其他解放区的宪政实践产生了影响。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政权建设;法制建设;新民主主义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使得哈尔滨成为当时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中共领导的军事革命和政权建设也首次由农村根据地步入城市。这既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也是考验中共政权建设的一个新情况。因此,在哈尔滨特别市(哈尔滨市自1946年11月18日至1949年2月6日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的特别市。虽然《哈尔滨市施政纲领》通过时,哈尔滨仍为“市”,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其作为“特别市”的时间较长,且其后以《哈尔滨市施政纲领》为中心通过的其他法律文件均冠以“特别市”的名义,故本文采此说法)的法制建设上,也展现出了许多与苏区、边区时期法制不同的特点。
一、中国共产党对哈尔滨的解放与接管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在中共七大提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1]。因此,国共双方都很看重东北的战略价值,都意在在抗战结束后对东北地区展开争夺。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中共中央又做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派出了大量的干部和部队进驻东北。“此次我军十余万人进入东北和热河,新扩大者又达二十余万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加上党政工作人员,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2]解放和接管东北有了人员上的保障。
然而,苏联方面最初并未将哈尔滨市移交中共接收,而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移交给南京国民政府。对此,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在发给中央的电报中说道,“苏联除要我们军队退出大城市外,现在更要我们交还已接收的政权,禁止我们在三大城市中一切足以妨碍他们公开执行中苏协定的措施。为了执行中苏协定,苏联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必须的,是应该被我们谅解的”[3]。于是,中共军队和组织主动退出了哈尔滨市,建立北满根据地,北满分局和松江省党、军机关撤至宾县,哈尔滨市市委转入地下。1945年12月25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指示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哈尔滨市区在接收期间暂准按照伪满省市旧有管辖分别接收[4]17。国民党哈尔滨市政府制订了接收委员会委员名单和具体日程安排。1946年1月1日,哈尔滨市前市长张廷阁将政权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代表杨绰庵。
1946年4月25日,驻哈苏军开始奉命撤回国内,哈尔滨市内有国民党军队约6 000人[4]80,而中共集结于哈市市郊的部队约一万两千人,认为夺取哈尔滨市有把握[4]82。1946年4月28日,中共军队以东北民主联军的名义进驻并接管哈尔滨,全程没有受到抵抗。杨绰庵等国民党接收人员随苏军撤至海参崴后返回沈阳。当日,哈尔滨市民走上街头,欢迎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并于5月4日在兆麟公园举行了欢迎民主联军市民大会[5]。
至此,哈尔滨正式解放,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掌控的第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城市政权。
二、解放后哈尔滨的政权与法制建设
哈尔滨解放后,除了进行剿匪和在市郊进行土改外,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建立城市政权。在政权建设上,1946年7月1日,中共哈尔滨市委确立了“市政府是哈市之最高政权机关,无论任何机关部队应服从市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令”[6],并且,提出了召开参议会,制定施政纲领的决议。
1946年7月16日,在市政府礼堂召开了哈尔滨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大会,会议两度延长会期于21日闭幕。六天会议的过程中,参议员们听取哈尔滨市政府的工作,并通过了《哈尔滨市施政纲领》以及《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哈尔滨市敌伪财产处理纲要》等单行法规。作为政权构建的核心法律性文件,《哈尔滨市施政纲领》表现出了很多与边区施政纲领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体现出城市政权的特性。
(一)《哈尔滨市施政纲领》的内容与特色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共17条,内容涉及哈尔滨市的民主政治、人民权利、经济文化、公益事业、外侨事务等方面。其特色内容包括:
1. 政权的主体突出是“市民”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与苏区、边区宪法大纲或施政纲领最为不同的表述,就是在主体上不再称为“工农劳苦民众”(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或“抗日人民”(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而是将政权的权利主体因地制宜地改称为“市民”。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除了第5条“人民有申诉清算十四年所受敌伪、大汉奸恶霸政治经济压迫之权利”外,其余的表述主体均为“市民”,如第2条“保障市民集会结社出版信仰居住之自由”,第3条“任何机关或团体不得向市民征集金钱及物资”,第8条“平抑物价、改善市民生活”等。
以“市民”作为政权的权利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民主主义城市政权上的首创。由于哈尔滨市城区内农业人口比例较少、土地改革亦不是主要任务,因此这样的规定无疑是合理和切合实际的。
2. 规定了大量的经济和公共事业内容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在17条中规定的内容,涉及经济发展的有6条(分别是第4、6、7、8、9、10条),涉及公共事业的有3条(分别是第11、12、13条),上述9条内容构成了《哈尔滨市施政纲领》内容的大部。这与之前宪法大纲或施政纲领侧重政权建设、土地分配和人民权利有所不同。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从当时经济发展不佳和市政出现问题的角度加以考量的。在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前夕,即国民党接管末期,国民党长春市市长董彦平就市政问题给时任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发去电报,指出市内存在着卫生不良、电力不足、商业无秩序等诸多市政问题[4]23。并且,物价飞涨,“工厂不怎么开工、商店开门的也很少”[6]。
因此,《哈尔滨市施政纲领》规定了“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以繁荣市面”(第4条)、“提高农民之生产积极性,以繁荣国民经济”(第6条)、“采取有效办法,促进与协助未开工之公司工厂复业,以减轻失业,繁荣经济”(第7条)、“平抑物价,改善市民生活”(第8条)、“整理与统一税收,废除苛杂部分,以减轻市民负担”(第9条)、“在劳资双方自愿原则下实行分红制度,以促进劳资合作、发展生产”(第10条)等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以促进商业形势的好转。
同时,针对市政问题,《哈尔滨市施政纲领》规定了“发展国民教育,扩充中小学校,收容失业青年儿童”(第11条)、“改善公共事业设备,以保证市民水电之供给及交通便利”(第12条)、“保护及修补松花江大堤,以防水患”(第13条)等公共事业内容。
发展经济和公共事业既是从本市经济情况出发的考虑,也是出于支援前线的需要。在“钟子云关于支援前线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的钟子云指出:“支前是党的主要工作,全党的工作,每个同志的工作……我们如何支援呢?一是组织生产,二是节衣缩食”[4]473。作为当时全国最早解放的城市,进行工业生产和发展商业贸易,不仅对本市的市民生活、经济物价等有所裨益,对于东北解放战争前线亦有支援作用。因此,《哈尔滨市施政纲领》用了较多的笔墨规定了这两方面的内容。
3. 关于外侨问题的特色规定
哈尔滨是随着中东铁路的兴建而兴起,许多苏俄、日本、朝鲜外侨都在哈尔滨居住生活。在1912年,市区人口为68 549人,外侨人口为43 091人,所占比重高达62.86%。到1917年,哈尔滨的人口超过了10万,其中只有11.5%出生在本地,其余皆为移民[7]。至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进驻时,市区人口为531 070人,外侨人口为136 616人,比例仍占25.72%[8]63。人数众多的外侨使哈尔滨变为了一个文化多元的国际化都市,也使得城市管理面临与其他根据地不同的新情况。因此,在《哈尔滨市施政纲领》作出了相应的特殊规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对于外国人的规定较为笼统,并强调须从事劳动方享有权利,“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居住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有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对于外国人的规定进一步细化,规定了外国人的游历权和庇护权,“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针对当时抗战刚刚结束,日本作为战败国并有大量日侨留置哈尔滨的情形[4]100,《哈尔滨市施政纲领》作出了因时制宜的规定,“保护各友邦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严格管理日德侨民,任何国籍之侨民均应遵守政府之一切法令和负担市民应负之义务”。这样的区别规定是符合时宜且有必要的。其中,友邦侨民主要是指苏俄侨民,对日德侨民进行“严格管理”中严格的程度及管理的方式则没有细致化的规定也没有配套实施条例,在实践中,对待敌侨的主要方式就是遣返回国。从1946年4月开始的遣返日侨工作,共在东北地区遣返日侨约150万人,约10万日侨自愿留在东北生活[9]。其中,至1947年留在哈尔滨市的日侨为3 433人[8]64。留在哈尔滨市的3 000多名日侨,哈尔滨市政府采取了管理加保护的措施,在保障他们生活基本权利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区别对待和管束。
(二)《哈尔滨市施政纲领》的内外影响
1. 《哈尔滨市施政纲领》对哈尔滨市政权建设、经济恢复、法律适用方面的影响
首先,在政权建设上,《哈尔滨市施政纲领》第1条规定,“建立民主政治,实行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制度,自下而上的改造各级政权机关,选举市参议员与市长”。这一条规定体现了新生政权的民主性。在此之前,于1946年7月8日开始选举的临时参议会就是经过这样类似的民主选举进行的。在此之后,根据《哈尔滨市施政纲领》的精神所制订的《哈尔滨特别市人民政府组织条例》(草案)中,其第2条规定,“哈尔滨特别市政府由哈尔滨特别市参议会选举行政委员九人组织市政府委员会,并由市参议会在行政委员中选出一人为市长,市长及委员均于选出后呈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备案”。这条规定与《哈尔滨市施政纲领》一脉相承,在政府组织上体现了政权民主性。
其次,在经济恢复上,《哈尔滨市施政纲领》用了大量笔墨来规定经济内容,亦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效果。经过一年多的稳定发展,哈尔滨市在经济状况好转的基础上,还逐步实现了经济的国有化和公私合作化。至1948年,“从经济力量上来看,哈市国营经济是已占据很重要的地位”[4]274,并且,建立了三种类型的合作社,分别是消费合作社、加工性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独立手工业劳动者的产销合作社[4]281,把私营经济纳入了国家的管理范畴。在物价上,市政府于1946年9月23日发布了《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严禁抬高物价的布告》,禁止了囤积居奇和故意抬高物价的行为。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尚不能完全满足供给且需支援前线的情况,物价在之后还是出现了上涨,“本年(即1948年,笔者注)12月与1946年12月作比,涨率最大者,为主食品,高达98倍以上;次如副食品,亦高达95.5倍,涨率最小者,则为燃料品,将近37.8倍”[4]320。因此,笔者认为,要想解决物价这类经济问题,单靠法律规制和政策改革是不行的,从根本上发展生产才是解决问题之道。此时的国统区经济也为笔者的观点提供了例证——历次的货币改革非但没能降低物价,反而使物价上涨到整个民国时期的最高点。
再次,在法律制定和适用上,一是哈尔滨市参议会(后改为人民代表会议)、市政府根据《哈尔滨市施政纲领》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制定了一系列法令、通令、条例、决定和布告等,涉及城市管理和建设的方方面面。例如,《哈尔滨特别市战时工商业保护和管理暂行条例》、《哈尔滨特别市营业税暂行条例》、《哈尔滨特别市人民政府移民暂行条例》,等等。二是当时解放区并未废除六法全书,因此许多法律领域仍然按照旧有法律调整,比如在刑事领域,哈尔滨解放区 1949年2月以前审理普通刑事犯罪主要依据六法全书中的刑法典[10]。因此,在适用法律上就需要《哈尔滨市施政纲领》这样的宪法性文件给予指导,去除六法全书中与新民主主义政权不相符的部分,仅保留尚有存在适用意义的法律条文。
2. 《施政纲领》对其他解放区宪政实践的影响
作为解放区的第一个新民主主义城市施政纲领,《哈尔滨市施政纲领》对其后的解放区宪法性文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46年8月11日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东北各省市(特别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组织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这个施政纲领与《哈尔滨市施政纲领》一样,都着眼于东北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经济恢复以及人民权利等方面,其第2条建立各级参议会、第4条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第7条保障人民基本权利与《哈尔滨市施政纲领》的第1条、第4条、第2条相类似,尤其是在经济建设方面都着眼于减少失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平抑物价等东北解放区亟须解决的问题。当然,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东北各省市(特别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也增加了巩固东北民主联军武装、拥军优属等军事方面的内容。
此外,《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中的部分条文也与《哈尔滨市施政纲领》有相通之处。例如,《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第6、7条与《哈尔滨市施政纲领》第2条相类似。
但是,我们不能草率地认为《哈尔滨市施政纲领》就此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影响到了日后其他所有解放区的法制建设。一是因为哈尔滨仅是东北解放区的一座城市,不足以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二是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于1946年4月23日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更具有推广和指导意义。在内容上,《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的也比前者更为充分、全面。
因此,笔者认为,《哈尔滨市施政纲领》对同为东北地区的《东北各省市(特别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者制定通过的时间相距较近且在时局、地缘上都有类似之处。而其他解放区的宪法性文件可能会参考《哈尔滨市施政纲领》,但更重要的是参考《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在体现各解放区地方特色的同时,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
三、哈尔滨特别市法制建设的成就与不足
在《哈尔滨市施政纲领》的引领下,哈尔滨市参议会(后改为人民代表会议)、市政府根据《哈尔滨市施政纲领》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决定和布告等,其内容涉及城市接管的组织工作、民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与城市管理、土地改革与支援前线等。这些带有法律意义的规定,共同构成了哈尔滨市的法律体系。
在这些法规中,《哈尔滨市施政纲领》起到了纲领性的主导作用,并且也为其他解放区宪政实践提供了可借鉴之处。虽然其作为一个东北北部城市的施政纲领,在革命根据地宪政史上意义远没有其他纲领重要,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哈尔滨市作为中共第一个解放并接管的大城市,其法制领域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虽然夺取过南昌等大城市的政权,但都未长期驻守,而是转向农村根据地建设。因此,在解放战争时期,建设和管理城市的经验则更多地来自于哈尔滨市等东北城市。
对于哈尔滨市法制建设中的不足,则是这一时期法律制度上的通病。比如,军事、行政化色彩浓厚,许多民主权利未能落到实处,在土改和工商业改造的贯彻中出现了操之过急等问题。基于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这样的缺陷也是难以避免的。
综合正反两方面,解放战争时期的哈尔滨市法制建设是有所建树的,既有两个“第一部”[11]的宪法性文件《哈尔滨市施政纲领》,也有其他具体部门法规上的初创尝试,如《哈尔滨市处理继承办法草案》等。虽不及全国性、大区性立法成果影响广泛深远,但也有可圈点之处。
[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10-411.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1179-1183.
[3]陈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9-300.
[4]哈尔滨市档案馆.解放哈尔滨[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
[5]哈尔滨十五万人民举行盛会热烈欢迎民主联军[N].东北日报,1946-05-13.
[6]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政权[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195.
[7]国民党“接收”后的哈尔滨[N].东北日报,1946-03-22.
[8]Bakich, Olga Mikhailovna, “Emigre Identity: The Case of Harbin,”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99, No.1 (2000): 51-73.
[9]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总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63.
[10]曲晓范.战后中国对东北地区日本侨民的安置和遣返——近现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妥善处理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J].日本学论坛,2002,(1).
[11]孔令秋.论苏联法对哈尔滨解放区法制建设的影响[D].黑龙江大学,2007:36.
[12]孙光妍.新民主主义宪政立法的有益尝试——1946年《哈尔滨市施政纲领》考察[J].法学研究,2006,(5).
[责任编辑:梁桂芝]
2016-07-22
迟政(1991-),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研究生。
D929
A
1008-8520(2016)05-005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