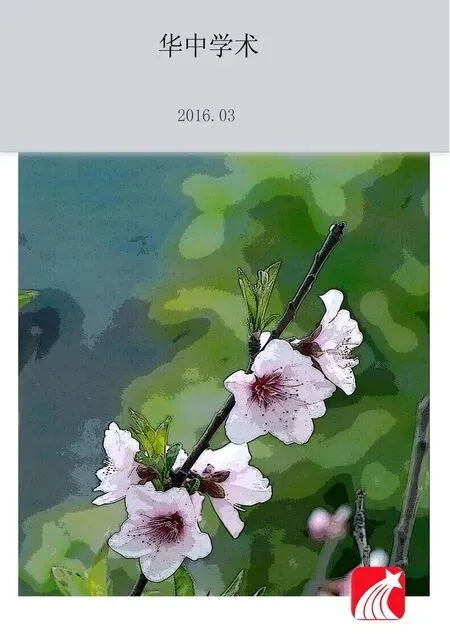文学伦理学视域下的《父亲的法律》
胡朝霞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衡阳,421001)
文学伦理学视域下的《父亲的法律》
胡朝霞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衡阳,421001)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出发,我们发现《父亲的法律》中存在父子和警匪两条伦理线,并呈现了混乱的父子关系、警匪关系以及各自的伦理选择。本文探讨了子辈的“弑父”及父辈的“护犊”等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指出了作者身上所存在的矛盾。小说既肯定了当时社会语境下的“弑父”意愿,又否定了子辈的非道德行为,因此成为一部具有复杂伦理内涵的作品。
《父亲的法律》;伦理身份;伦理选择
《父亲的法律》(AFather’sLaw,1960)叙述的主题相当广泛,如“犯罪与无辜、代与代之间恶化的关系、黑人警察和父亲的窘境、父亲警察和儿子嫌疑犯的关系。在一部小说中涉及了所有的现代主题”(Preface 1)[1]。小说叙述了黑人父亲鲁迪·特勒(Ruddy Turner)与儿子汤米(Tommy)持有不同的法律立场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念,因而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说明了心理学、哲学和犯罪学等诸多问题。小说探讨的是当今社会的法律和家庭观念等问题,呈现了儿子反叛父权的文化事实,父权成为应该被破除的“假象”(idol)[2]。然而汤米的“叛父抗法”是当时美国兴起反文化运动的典型案例,特勒在面对汤米弑父行为时的表现,体现了一种对子辈的复杂、矛盾与两难的态度。这正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伦理行为。
一、 父子伦理线与伦理身份
在《父亲的法律》中,父亲特勒作为一名警察,象征法律体系、社会体制和主流价值观,儿子汤米则代表着反主流价值观、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是当下社会体制的批判者。小说呈现了建立在感性的家庭伦理基础之上的父子伦理线以及建立在理性的法罪伦理基础之上的警匪伦理线,同时独特地描述了在两条伦理线上错位的父子、警匪伦理身份及其伦理关系。“在文学作品中,伦理混乱表现为理性的缺乏以及对禁忌的漠视或破坏。”[3]而在这部小说中,两条伦理线分别呈现出两种伦理禁忌:“弑父弃母”的家庭伦理禁忌、“法不容情”的职业伦理禁忌和“虎毒食子”的家庭伦理禁忌。正是这种伦理禁忌的触犯,使特勒处于一种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伦理两难之中。
小说预设了父子间的对立关系,导致伦理身份颠倒。从父亲的角度来看,汤米的伦理身份发生多次转变,从人子变成朋友再变为可怕的上司,最后成为挑衅者和背叛者。儿子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都向父亲的伦理身份进行挑战。父亲在儿子面前躲闪、退让,即使是抗议也是无力的,“我不愿意让纳税人听到你这么跟我说话”。从儿子的角度来看,特勒是一个没有思想、缺乏主见之人,难以担当起父亲的重责。在父子交锋中汤米多次嘲笑说,“我知道你理解不了我”、“我知道你被难住了”。汤米认为特勒没有能力以父亲的名义来约束和控制自己。除在智力方面嘲笑父亲的无能和怯弱外,汤米更在父性方面否定了特勒的价值。父性是父亲“作为生殖者不仅要提供给后人存活下去的食物,更重要的是将知识和文化传递给后代,使得种族的历史能够像血脉一样传递下去”[4],因而父性不仅具有生物学上的意义,更具有文化上的意义。提供食物只是父性的第一要素。特勒属于黑人中产阶级,在富人区拥有自己的住宅和小院,在物质上完全能保证汤米的生活富足,但他的这一父性并不被后者承认和接受。当汤米承认犯罪的时候,特勒完全出乎意料,反问汤米:“我对你不好吗?我没有给你任何你想要的和需要的东西吗?”在小说的末尾,汤米向环球杂志社“兜售”其罪证,暗示着他从此彻底与父亲割裂,否定父亲的物质付出。文化意义上的父亲是父性的第二性,较之第一性更为重要。“父性在黑人父亲身上表现出来的就是黑人性,黑人性的缺失必然导致父性的缺失。”[5]汤米认为特勒丧失了民族文化意义上的父亲内涵。从警之前的特勒保持着黑人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心理,诚实地对待自己的黑人身份和社会地位。从警后他居住到了富人区,竭力接近上层白人社会,自视为白人社会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环境的改变让他失去了自己的黑人身份和民族文化意识,自我感觉与贫穷的黑人不同,文化传承意义上的父性在他身上开始消失。“‘美国性’(主流文化)与‘黑人性’(黑人文化)造成了美国黑人思想的双重意识,两者关系的失衡导致白色文明对黑色灵魂的浸染漂白,黑人父亲人格分裂成为作品中的白奴。从文化角度说,黑人性的缺失也意味着父性的丧失。”[6]特勒最终成为一个被白人文化异化的工具,被汤米鄙视的“陌生的警察”。
二、 警匪伦理线与伦理身份
“反文化”运动是指美国20世纪60年代在青年人当中流行起来的,以反战和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抗议主流文化及其制度。在年轻人看来,警察是社会制度和文化的代表,“警察是压迫政权的代理人,已经丧失人性,变成了‘猪猡’,而警察则在许多众所周知的场合用警棍对学生的肉体进行报复”[7],双方有着深刻的矛盾和仇恨。
这部小说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在对法的本质和正义性认识之上所产生的严重的分歧。以特勒为代表的警察,包括韦德(Wade)、乔克(Jock)等对法律的认识模糊而盲目。他们思想僵化保守,狭隘地认为法律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并使世界永远处于理性状态。犯罪是非理性的结果,必须要受到惩罚,甚至应被处以极刑。当年轻的犹太警察艾德提出“犯罪是一种疾病,罪犯不应被惩罚,而应该加以治疗”的观点时,几乎招致所有父亲的反对。其中特勒的反对尤为强烈,他反对汤米接触各种异端思想和观点,并因儿子被视为“天才”而感到不安。在他看来,天才就意味着反叛体制,意味着犯罪。特勒对法的信念模糊、动摇,容易受到伦理、道德因素的干扰。故事开始,特勒视其职业是“工作、生命和法律”,坚定地维护现行价值观念、法律制度和理性秩序。随后,汤米抛弃女友玛丽(Mary)事件,却让他对法律产生了怀疑,认为世俗法律之上有某种神秘的、无法控制的“法”,犯罪不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在法律、道德和亲情的关系中,亲情高于道德,道德高于法律,法律最苍白无力。当汤米表现出符合嫌犯的种种特征时,他想方设法隐匿儿子的罪行,将法律当作父亲身份失败、儿子堕落的替罪羊。当汤米承认犯罪行为后,他又表示“不愿意打败法律”。在他的眼中,法律已经成为他的个人意志。我们认为特勒的做法模糊了法律的本质,从而偏离了执法者的伦理身份。
相对于父亲,汤米对法律的本质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更加坚定的信念。他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专门研究芝加哥南部贫困家庭问题,如阶级分化、贫穷、肤色意识、家庭破裂等。同时,他也对青少年犯罪问题有兴趣,曾多次到受害者家庭中去走访、调查。通过一系列的研究,他对社会和法律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20世纪60年代,犯罪高潮袭击了美国,对此种社会现象,梅勒和保罗·古德曼曾具有预见性地指出:“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现象以及犯罪和青年反常行为的瘟疫是整个制度中的裂缝。”[8]汤米和伊德代表了边缘化的批判者,他们质疑现行法律制度和社会价值体系,清醒地认识到父亲们所代表的法律是偏激而虚伪的,这样的法律并不能保护社会弱者、伸张正义。虽然上层阶级鼓吹法律保护社会各个阶层,然而富人们通过钱权等特殊手段,迫使警察消除了他们犯下的斑斑劣迹。于是法律成为富人们的保护伞。在小说里,前任警长Bill在特勒接任警察局长时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法律的本质是有钱人权力的体现。贫穷的匈牙利青年海杰克(Hyjicks)、卡兰(Calan)等就是富人法律的牺牲品。在否定法律的正义性、公平性之后,汤米更直接否定了警察的法律身份,认为父亲的枪只是被允许用来杀人的工具,警察就是“外出逮捕他人的一支武装力量”。父子两人对法律的不同认识造成了警匪伦理身份的混乱。同时,他们质疑世界和法律的理性,认为法律并不是一切,在法律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即“力比多”。法律缺乏灵活性,它只是部分信仰者的法律,法律对于不信仰者毫无意义,因此不能保护社会,人们应该遵循更高的“法”。
60年代美国青年一代“学生们是彻底的存在主义革命者,边干边学习全套的政治策略和可能性”[9]。相较于老一辈而言,汤米等青年人更善于接受新的法律知识,他们多次利用新的心理学知识来分析案情。在汤普森案件发生的时候,汤米认为“当他面对死亡而没有希望开脱死刑的时候,他确实想坦白一些罪行以便开脱死刑”,而特勒却始终不能相信这一点,这招致了汤米的嘲笑——“我不知道,我不能理解你的观点”。这就说明在这部小说里,“警”与“匪”具有不同的伦理意识与伦理思想,作为警察的特勒和作为犯罪者的汤米对于许多问题的认识是并不相同的,而他们之所以具有不同的认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具有不同的伦理身份,并不只是父亲与儿子的身份那么简单,而是与一定的阶层与阶级发生了关联,并且涉及了许多重要的社会伦理问题。
三、 “弑父”时的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方法论,强调文学及其批评的社会责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10]同时,“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历史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于文学的理解应让文学回归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11]。莫里斯·迪克斯坦认为,黑人作家“赖特成为一名作家和激进分子,把自己的反叛精神从一种无法避免的命运转变成一种战斗的美德”[12]。因此,特勒坚决反对白人的、父辈的传统价值观念,肯定青年一代的“弑父”行为。60年代的美国,青年人的成长环境是畸形的,他们“在一个道貌岸然的、压迫性的、假正经的、虚伪的和狭隘的世界里长大成人,似乎学不到什么美德,而只能染上大量的精神疾病,备受折磨”[13]。因此,汤米对美国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有着深刻理解,同情边缘人群和少数族裔,抗议、批判以特勒为代表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他秘密实施了“谋杀者攻击法律”的行为,射杀了多名宗教人士及警察康·合德(Karnn Heard)的儿子。这样的行为对于警察特勒来说,就是一种伦理、法律、文化上的“弑父”。在伦理上,汤米实施犯罪意味着死亡,意味着拒绝为父亲延续血脉;在文化上,向环球杂志社“兜售”罪行,意味着他鄙视和嘲弄资产阶级的金钱观;在法律上,面向媒体而不是面向法律坦陈罪行,则反映出其主观意识上否认自己的罪行。由此,他切断了与特勒之间的父子伦理关系,从人子伦理身份转向了罪犯伦理身份,并给父亲的职业生涯送上致命一刀。汤米的弑父行为并不是个案,特勒的同事杰姆斯·黑尔也遭遇儿子“弑父”,其子因盗车被判了监禁。对父辈的仇恨本质上“是一种抽象的、精神上的憎恨”[14]。
人性因子是理性因子,体现的是人类的伦理意识;兽性因子是向恶因子,体现的是人类的动物本能[15]。“力比多”就是一种人类的本能和动物性的体现。“60年代文化是解放文化——许多人说是太解放——是一次开放,它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途径,即是布莱克所谓的‘改进感官的享受’。”[16]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对父辈、警察进行污化描写,同时批判了那种无视法律和道德约束的行为,把汤米等一代人描述为受时代语境影响的富家子,容易在“力比多”的支配下从事违背法律的行为。汤米逐渐否定父亲和法律的过程,是人性因子走向兽性因子的过程。小说里的他一直认为在法律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即“力比多”。而人生活在由“力比多”统治的监狱里,个体可以任凭内心的强大力量自由行事。受“力比多”的驱使,汤米接受60年代反文化青年们的性革命观念,缺乏理性和道德的制约,与玛丽发生关系,之后由于梅毒又毫不犹豫、坚定地抛弃女友,对她不闻不问。这正是Brentwood Park富人区子弟先诱惑穷人女子上床然后无情抛弃的一贯做法。但是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男孩因为内心最强大的力量促使他所做的事情”,即他认可的“道德”。
所谓的“罪感”,也就是受到道德折磨所产生的个体感受,是个体伦理意识的表现,也是人兽区别的最为关键因素之一。汤米强调了个人意志的自由,在精神上免受任何由道德引发的罪感约束,在行为上免受法律的惩罚,因为他认为法律只是信仰者的法律,罪者因不信法律而免除罪感。个人因此可不受任何伦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无所顾忌、不受约束地表达自由意志和欲望。汤米抛弃玛丽事件正是60年代青少年身上“兽性因子”压制“人性因子”,追求欲望解放的结果。相比汤米,父亲特勒具有更多的道德责任感,对玛丽被抛弃事件心怀愧疚,多次去看望她,向她提供经济帮助和未来的承诺。对待玛丽事件两人截然相反的行为,正反映出两代人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念。同时,罪感的缺乏,导致60年代青年人任意射杀所厌恶的法律人士与宗教人士。布鲁诺(Bruno)在犯下谋杀罪被判15年牢狱后,出狱4个月就又一次因抢劫50美元而杀死了一个老人,对此汤米认为,频繁发生的犯罪是生活的常态,“Life,Dad,Life’s happening there”。而作家本人对于这种犯罪现象,则极为担忧甚至是痛心,可见作家本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小说里的特勒是不一样的,与汤米则更为不同。小说里人物的伦理道德观念与作家本人所持的并不相同,然而作家的伦理观念会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进行体现,特勒与汤米之间的否定与被否定的伦理关系,正是说明了作家对那个时代父子伦理关系的观察与思考,维护法律的正当性与人类的正义性,正常的伦理身份不可颠倒与混乱,不然的话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悲剧。
四、 伦理混乱的产生及其根源
“伦理混乱即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改变所导致的伦理困境。”[17]汤米在伦理选择上的主动性,导致特勒伦理身份的暧昧、模糊甚至悲剧。前任警察局长布莱登(Branden)就是由伦理混乱招致悲剧的典型。当时美国社会种族主义流行,白人享有种族特权,黑人备受歧视和压迫,但是为保持权力平衡,富人区大部分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都来自社会底层或少数族裔。在小说的开始,特勒坚守自己的警察伦理身份,忠实地维护现行的法律,惩罚罪犯,力图实现“为每个人所制定的,为黑人、白人、穷人、富人、土著和外来人等等遵守的法律”。后来,他身上的“理性因子”受到“非理性因子”的严重影响,开始相信非理性世界,伦理身份在警察和父亲之间游走,“不得不戴上两幅面具,往返于儿子和女友建构的非理性世界和法律建构的理性世界”。由于他认可法律受更高“力比多”的操纵,放任源自非理性情感的“父亲身份”冲击理性的“警察身份”。在对待社会底层卡兰和儿子汤米之间的事件上,他就表现出一种混乱的伦理身份。卡兰处于社会底层,没有固定职业,因偷窃入狱,期间又失去了在妻子死前临别的机会,于是对社会产生仇恨。于是特勒怀疑卡兰是凶杀犯,而有意忽视和回避儿子汤米与谋杀案之间的联系,因为“汤米,儿子,他的骨肉”。在此他陷入了一种伦理两难:或者选择警察身份,将儿子绳之以法,断送血脉亲情;或者选择父亲的身份,又违背了“法不容情”的禁忌,断送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随着故事的推移,他选择警察伦理身份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多次表现出对警察身份的悔恨,“我不应该将这该死的工作放在第一位”。
除了特勒对法律认识的动摇导致特勒伦理身份模糊、暧昧和混乱,犯罪心理学的相关意识也悬置了汤米的凶手身份,导致特勒伦理身份的模糊。汤米在家庭中对父亲和法律的反叛强化了他的犯罪嫌疑。同时,犹太警察Id认为,在犯罪心理学中存在一种情感冲动型犯罪,会导致个人因为外界现实不能如愿而产生情感冲动犯罪。玛丽事件让他在精神和情感上受到折磨,可能形成情感犯罪的动机。除理论上的推测外,汤米鞋上沾有与嫌犯掩埋38枪支现场相同的水泥,更进一步构成了犯罪的罪证。同时,在当时青少年犯罪相当普遍的社会环境,也让汤米具有重大的嫌疑。社会环境让警察们也认为,即使是警察的儿子也会像其他人的儿子一样,也会犯错甚至犯罪。人往往会因为承受不了内心埋藏已久的罪感,而借助他人曾犯下的罪行,来袒露自己内心的愧疚和罪感。但是,这种坦白绝不会是对犯罪行为的真实披露,因为他们有时甚至区分不开现实与想象,或者随便找机会坦白罪行来以投射出内心的罪感,获得内心的平和。在小说里有这样的情形,汤米因玛丽事件而精神崩溃,于是心生幻象,他也正是在幻觉中,才向媒体坦白自己的罪行。当然,“借罪”也可能是为掩盖更深层的谋杀罪行,而假装参与了一宗抢劫案,并有意将父亲的短波收音机安置于车中,以此强化自身“借罪”的事实,试图以小罪掩盖真实的大罪。可见一系列的犯罪心理学知识,在模糊汤米身份的同时,也模糊了特勒的警察身份。
古德曼认为艾森豪威尔时代的青年们会“以实际行动对一个有组织的体制进行批判,而这种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得到所有人的支持”[18]。作为黑人抗议文学的先锋,赖特在《父亲的法律》这部小说中,一定程度上承继了那个时代的创作精神,将特勒和汤米想象为父亲和儿子、警察和罪犯,具象化了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守旧与反叛之间的关系,影射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大量“弑父”现象,又表现了对非道德“弑父”的严重担忧。这正是一位父亲在面对儿子“弑父”时,所暴露出来的一种复杂的、病态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心态。这部小说之所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不只是因为作家关注了当时美国社会里大量存在的伦理混乱现象,还在于作家把这种现象表现得相当复杂,特别注重对父子伦理关系的刻画,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出现严重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伦理身份发生了变化,引起了伦理困境和混乱,所以造成了重大的人生悲剧与社会悲剧,体现了作家的人道情怀与悲悯精神,表现了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的转型及文化裂变,而这种不得不发生的社会转型与文化裂变,又造成了人物之间关系的混乱与困境。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实践研究”【13&ZD128】、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医学想象与帝国政治”【13BWW044】前期成果之一。
注释:
[1] Wright,Richard,AFather’sLaw,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8.
[2] Ward,Jerry Jr.,“The Weight and Substance ofAFather’sLaw”,Book Review.[2012年4月4日]http://www.nathanielturner.com/weightandsubstanceofafatherslaw.htm.
[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21页。
[4] 蒋天平:《上帝还是恶魔?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中的父性》,《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第155页。
[5] 蒋天平:《上帝还是恶魔?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中的父性》,《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第155页。
[6] 蒋天平:《上帝还是恶魔?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中的父性》,《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第155页。
[7]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方曙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57~258页。
[8]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方曙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9]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方曙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57~258页。
[10]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1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12]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方曙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13]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方曙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65页。
[14]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9页。
[1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16]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方曙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1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7页。
[18]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方曙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推荐人语】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重新解读当代美国作家赖特的长篇小说《父亲的法律》,提出了父子伦理线与警匪伦理线是构成这部小说的两条主线,而人物之间所发生的重大悲剧,其根源在于人物伦理身份变化而引起的伦理混乱。而之所以发生伦理身份改变,则在于当时美国所发生的“反文化”运动及人身上本有的“力比多”能量,以及其所导致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相互转化。本文选题新颖,问题突出,材料丰富,论述集中,是一篇有材料、有见解、有价值的学术论文。(邹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