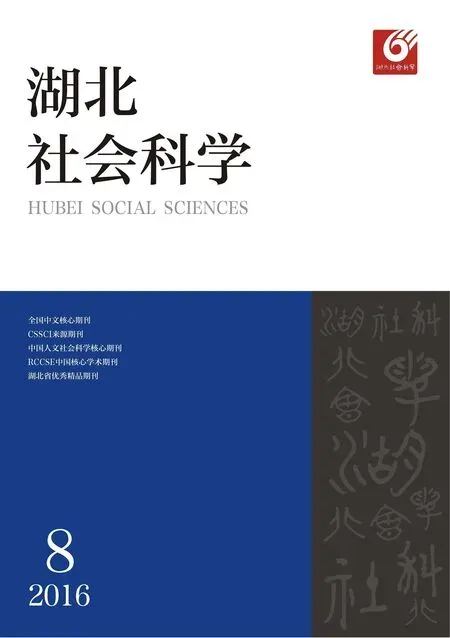宋型文化背景下宋代道统论之发展
——以孟子道统地位的确立历程为中心
武勇(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宋型文化背景下宋代道统论之发展
——以孟子道统地位的确立历程为中心
武勇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唐宋之际中国经历了一场大变革,宋型文化逐步形成。在宋型文化背景下,道统体系逐步确立,其中又以孟子道统地位的确立历程最为典型。有宋一朝,孟子在道统体系中的地位有了极大提升,被尊为宋以前道统的最后传承者。随着孟子道统地位的日益稳固,又推动了宋型文化的衍生、发展及其道德精神与内敛、理性特征的形成。
宋型文化;道统论;道统谱系;孟子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变革时期,传统社会文化结构渐趋解体,新的文化范型——“宋型文化”逐步形成。宋代经学也因此发生了明显转变,以孟子其人、其学的升格最为显著,尤其孟子道统地位的逐步确立又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一般而言,道统指儒家文化的传承统绪。[1](p187)孟子在宋代道统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清儒费密所说:“独言孟子之传,开于唐儒韩愈,至宋蔡京遂以王安石上下孟轲,程颐又以程颢为孟轲后一人,而尚无道统接传至论也。南渡后朱熹……乃倡立道统,自以为曾氏独得其宗,而子思,而孟轲”,[2](p16)可知孟子在宋代道统论发展过程中受到广泛推崇。目前国内讨论宋代孟子道统地位变迁的论文已有数十篇之多,如李峻岫《唐宋古文运动及道统说与孟子地位的变迁》、周炽成《唐宋道统新探》、彭耀光《二程的“道学”与道统观——以二程对孟子性论的诠释为中心》等,对孟子道统地位确立的过程及其思想理论等均有涉及,而以宋型文化为背景展开探讨的文章则不多见,因此从这一角度进行论述就很有必要了。
一、孟子思想与宋型文化背景下“道统”思想的契合
最早对唐宋之际变革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他首次提出了“唐宋变革论”。此后,国内外学者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对唐宋时期的复杂历史图景展开种种重构,“宋型文化”这一理论则是近三十年来探讨唐宋变革的又一重要成果。目前所知最早提出宋型文化概念的学者是傅乐成,他指出中唐以后儒学的逐步复兴使“民族本位文化益渐强固”,“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3](p380)王水照、[4](p2)刘方等则将宋型文化视作一种具备“新的文化特质的、与此前的文化范型有着深刻差异”的新文化范型。[5](p30)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将儒学复兴与理学形成视为宋型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核心问题,道统论又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道统体系包含“道”与“统”两方面内容,“道”即道统所传承的内容,在这一时期则主要表现为理学;“统”即道统传承谱系。孟子在宋儒所构建道统体系中地位的迅速提升,是由于其思想在道统传承的内容和谱系——即“道”与“统”两方面顺应了宋型文化的发展趋势。
其一,孟子思想中的学术传承谱系理论成为宋儒道统传承谱系形成的理论基础,顺应了宋型文化强调民族正统意识的特征。就外部政治环境而言,当时赵宋与少数民族政权冲突不断;内部文化环境而言,则有外来佛教不断挤压儒学,促使民族本位观念和正统观念逐渐兴起。正如向世陵所说:“理学道统论创立的前提或必要,在儒家外部,是要排挤佛老入异端而确立儒家自身作为中国学术的正统性和权威性。”[6](p17)因而建立一个完善、有据的道统体系,就成为排辟佛教及树立儒学正统性、权威性的迫切要求,故宋儒“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明确提出了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授系统”。[7](p245)在这一过程中,孟子思想发挥了关键作用。孟子提出的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的学术传承谱系,“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8](p376)对宋代道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孟子被列入儒家道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孟子心性论思想成为宋儒道统之道——即理学形成的思想资源,顺应了宋型文化趋向精深的精神特征。宋型文化是一种内省的文化,思想上表现为理学的兴起,正如张载所说:“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今日复有知者……志于道者,能自出义理,则是成器”,[9](p274)体现出当时道统之道趋于精深义理的倾向。陈寅恪先生指出,宋儒建立道统意在“证明其渊源之所从来,以压倒同时之旧学派”。[10](p319)宋儒崇尚义理之学,打破了汉唐以来以“天人感应”为思想特征的章句之学“旧学派”,建立起一套符合自身状况的儒学本体论、心性论思想体系,孟子则成为其重要思想来源。正如南宋施德操所说,孟子“道性善”、“明浩然之气”、“发孔氏之所未谈,述六经之所不载,遏邪说于横流,启人心于方惑”,[11](p134-135)孟子的这些理论成为理学兴起的重要资源,也成为孟子被宋儒纳入道统而荀子、扬雄等被排斥出道统体系的重要原因。
二、宋型文化背景下宋代孟子道统地位的发展脉络
道统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陈寅恪指出:“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盖非此不足以征信于人。”[10](p319)道统谱系滥觞于孟子,到中唐出于抗衡佛教法统的需要,韩愈发挥孟子的儒学传承理论提出“道统说”。从道统之道来看,韩愈认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12](p293)从道统之统来看,韩愈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谱系。[12](p20)足见孟子在韩愈道统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但韩愈的道统论也有不足,尤其是道统传承的具体内容并不明确。同时,韩愈的道统说在当时并不受重视,直到宋初才受到学人推崇。总体而言,孟子在宋代逐渐受到关注,道统地位也逐渐得以确立。孟子道统地位发展包含两方面内容,即理论上的深入与政治上的认可,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理论准备阶段,大致为宋初至北宋中期,成就主要在道统传承谱系的构建方面。这一时期,群儒受韩愈道统论启发,纷纷提出各具特色的道统谱系,其中以孙复、石介师徒最为著名。孙复指出:“吾之所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13](p174)石介则明确提出“道始于伏羲而成终于孔子……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孔子之道……天授之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孔子之道复矣”。[14](p141)即在韩愈基础上,加上了六位传说中的圣人以及荀子、扬雄、王通、韩愈四位贤人,肯定了包括韩愈在内的汉唐群儒在儒学传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一步巩固了孟子在道统谱系中的地位。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道统理论在道统传承谱系方面,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孟子在其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当时学者的认可。但仍有诸多不足,首先在儒学传承谱系中,孟子地位并不突出,而与其他几人一样仅被视为儒家道统的传承者之一;其次,道统之道还不具有鲜明的指向,汉唐章句旧学仍受到推崇。
第二阶段为道统基本确立阶段,时间为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初,成就主要体现在理论与政治两方面。首先,政治上孟子的道统地位得到了官方一定程度的肯定。尤其是在王安石主政时期,孟子首次得到官方封诰,允许配享孔庙,“自今春秋释奠,以孟子配食”,[15](p2549)表明朝廷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孟子在道统中的地位。同时宋儒将孟子在道统体系中的地位落实到经典认同方面,力图通过《孟子》一书为孟子道统地位的提升提供学理依据,故《孟子》一书地位的升格成为必然。如熙宁四年(1071)二月,《孟子》与《论语》并列为“兼经”,成为科举科目。[15](p3618)宣和年间,《孟子》首次被刻成石经。[16](p417)到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孔道辅所建邹县孟庙正式得到朝廷承认。[15](p2551)官方的这些措施,初步确立了孟子的道统地位。其次,在理论上,道统传承谱系与内容两方面的理论均有发展,学者中以张载、二程贡献最大。张载提出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武王到伊尹、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谱系,并强调“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9](p327)认为道统在孔孟之后中绝,强调了孟子在道统传承谱系中的重要地位,将之视为道统的最后传承者。此说实则是对第一阶段以孙复、石介等为代表的道统谱系中汉唐群儒的廓清,标志着儒家道统的传承内容与评判标准开始转向理学。二程的重要理论贡献则是论证了孔孟之间的师承授受关系,使孟子继承道统有了合理依据。二程认为:“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17](p327)同时论证了孟子接续道统的合理性,认为“‘五世’依约。君子小人在上为政,其流泽……五世而后斩”,“孔子流泽至此未五世,其泽尚在于人”。[17](p93)二程以此论证了孔孟之间的师承授受关系,使孟子传承道统有了较合理的依据。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学者对前一阶段的道统传承谱系进行反思,大体确立了孟子在宋代以前道统中的最后传承者地位,孟子道统地位空前提高。而荀子、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等则被清除出道统谱系,其原因在于宋儒认为其学说与圣人之道相去甚远,体现出道统之道开始转向心性、义理之学的趋势。
第三阶段是孟子道统地位与政治地位的最终确定与巩固阶段,大致为南宋中后期。当时理学迅速发展,其中以朱熹为主要代表。朱熹将道统谱系上溯至“上古圣神”,认为:“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之下,朱熹指出:“成汤、文、武之为君……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8](p14-15)在孟子之后道统中断,朱熹则接续以濂洛群儒,“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8](p2)“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18](p566)通观朱熹的道统理论,集张载与二程之长,不仅表现在道统传承谱系方面,也表现在道统传承内容方面。朱熹集前人之大成,构建了“精致的道的哲学”,以世间之道对接宇宙之道,“发展了道统思想的内涵,使作为道统传承内容的道,在哲学理论上达到了中国哲学道范畴发展的高峰”。[7](p357)朱熹的道统体系受到后儒推崇,如黄榦即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19](p388)到南宋末年,朱熹的道统思想在政治上得到了官方认可。宋宁宗年间,李道传、刘爚等先后奏请将包含《孟子集注》在内的《四书章句集注》列入官学,终获朝廷准许,[15](p12171)标志着《孟子》一书的经书地位得以巩固。宋理宗时,朝廷正式承认以程朱“道统”上承孔孟,[15](p821)此举不仅是官方对程朱道统体系的认可,也是对孟子道统地位的最终确立与巩固。
三、宋代孟子道统地位的确立与宋型文化的精神
孟子之所以能够在宋代确立道统地位,与当时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而随着孟子道统地位的逐步确立,学者对其学说、思想不断深入挖掘,又为宋型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1.孟子道统地位的确立与宋型文化的理性、内敛风格。宋型文化理性、内敛风格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过程。唐代对少数民族采取宽容态度,兼收并蓄成为唐型文化的显著特征。但唐中期以后到宋代,少数民族政权和外来文化的政治、文化压制,促使宋代民族意识高涨,士人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逐渐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转而走向对本民族传统儒学思想的挖掘,理学即是其重要成果。为达到文化上排击佛教、重树儒学权威的目的,儒家学者吸收佛教重传承之长,转而重视道统,进一步推动了宋型文化趋向理性、内敛特点的形成。
宋儒道统论总体表现为注重对经典义理的阐发与传承,而孟子即因其重视理性、心性的理论特点而被列入道统,这种崇理之风使宋型文化日趋理性。在诠释方法上,宋代孟学经历了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的转变。宋初三朝孟学沿袭汉唐章句之学,但当时学者已意识到章句之学难以挽救儒学发展的内在危机,如孙复指出:“汉魏而下,诸儒纷然四出,争为注解,俾我六经之旨益乱。”[13](p171)随着王安石新政,孟子地位迅速提升,学术著作显著增加,且日益转向义理阐发,其中以朱熹《孟子集注》最为著名。理论高度上,与章句之学相比,宋代重义理的孟学研究是形而上的。如《孟子·梁惠王上》首章“孟子见梁惠王”,赵岐指出其旨意曰:“此章指言治国之道,明当以仁义为名,然后上下和亲,君臣集穆,天经地义,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20](p3-4)赵注的着眼点在于“治国”与“仁义”。而朱熹《孟子集注》则认为:“此章言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8](p202)朱熹着眼于“天理”与“人欲”,将“仁义”与“利”的讨论引入理学体系,以申明其“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观念。足见,宋儒对道统之道的阐发已步入更为哲理化的新领域,形成一种更理性、更精深、更具形而上特质的义理学新范式。随着孟子道统地位的逐步确立,这种以阐发义理为特征的研究范式成为孟学主流,并被广泛用于诠释其他经典,通过“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10](p321)打破了汉唐章句之学的弊端,使得道统之道日益转向以道德本体论、心性论为特征的理学,促进了宋型文化内敛、理性风格的最终形成。
2.孟子道统地位的确立与宋型文化的道德精神。两宋以右文抑武为国策,文化教育趋向普及化、平民化,诸多寒门士人得以进入仕途,他们关心百姓疾苦,热衷于对道德人格的磨炼和对道德精神的探讨,其对孟子思想的重视,在宋型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随着孟子道统地位的逐步确立,宋人将孔孟等道统人物的高尚人格视为最高理想,如程颐所说:“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17](p189)将立志成圣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推动了宋型文化道德精神的逐步形成。其次,宋儒发挥孟子“心性论”,将道德准则本体化,尤其是随着孟子道统地位的逐步稳固,理学心性论逐渐形成,到朱熹大体定型。朱熹认为“理在人心是之谓性”,[21](p2514)“性即理,理即天”。[21](p1424)并将“性”与“气”结合,把人性分为禀理而生、纯粹至善的“天命之性”和禀气而生、有清浊善恶的“气质之性”,又以“天命之性”等同于“理”,实质是将道德中“善”的标准本体化,建立起以先验的、绝对的道德准则为人性基本特质的道德本体论,即理学。同时,朱熹指出:“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21](p133)认为普通人通过复其本性之善也能达到圣人境界,以此将道统体系中圣人人格社会化,乃至要求上至帝王、下至学者和平民都以圣人为榜样,通过修齐治平,将道统所传承的圣人之道贯彻到社会中,促进了宋型文化尚德行、重修养的道德精神的形成,“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15](p13149)足见,宋代道统说的形成,特别是孟子道统地位的逐步确立,催生了宋型文化的道德精神。
综上所述,宋型文化与宋代道统论的形成与发展相伴相生。孟子作为宋儒道统体系中的重要成员,正是宋型文化崇尚精深、正统的精神意识和整体文化环境选择了孟子,促成了其道统地位的确立。同时,孟子及其思想在道统之道以及道统之统方面,对宋型文化的核心——理学的形成,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孟子道统地位的逐步确立,更推动了宋型文化理性、内敛风格的确立及其崇德尚理精神的形成。
[1]潘志锋.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综述[J].广西社会科学,2008,(11).
[2]费密.弘道书[A].续修四库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傅乐成.汉唐史论集[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
[4]王水照.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王水照卷[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
[5]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M].成都:巴蜀书社,2004.
[6]向世陵.理学道统论的两类文献根据与实质[J].齐鲁学刊,2008,(6).
[7]蔡方鹿.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9]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1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1]施德操.施先生孟子发题[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C].济南:齐鲁书社,1997.
[12]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3]孙复.孙明复小集[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4]石介.徂徕石先生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7]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黄榦.勉斋集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9]黄榦.徽州朱文公祠堂记.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0]赵岐,孙奭.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1]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高思新
·历史·文化
B244.99
A
1003-8477(2016)08-0091-04
武勇(1986—),男,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