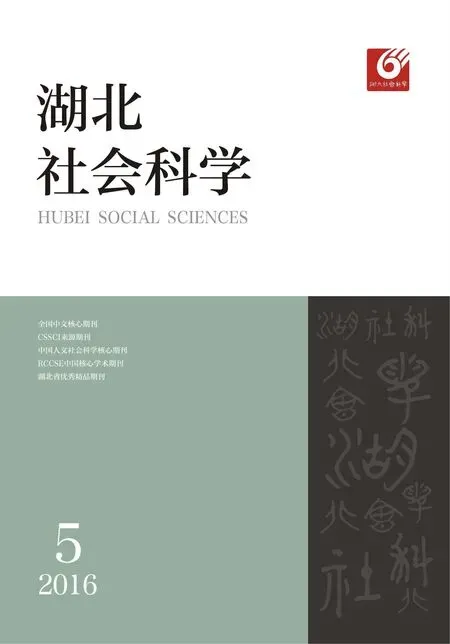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层次结构与功能阈限
胡心红,王习胜
(1.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安徽芜湖241000;2.合肥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安徽巢湖238000)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层次结构与功能阈限
胡心红1,2,王习胜1
(1.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安徽芜湖241000;
2.合肥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安徽巢湖238000)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体系结构是人主动建构的动态存在,与学者、专家的“书写”方式密不可分。它的层次性也有内外之分:其外部层次性,如常见的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划分,一般是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平面式的静态直观得出的结论;其内部层次性,是动态把捉方法论本身内在逻辑运动的结果,若循实践—理论的路线,可将之分为方法-方法观-方法论;若按方法论自身的发展逻辑,则又可分为论方法—方法论—方法学。不能简单化地理解方法论的指导功能,它的功能发挥是有条件、有代价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阈限表现在它的指导性和可教性两个方面。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层次;功能阈限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即理论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体系和结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性凝聚”和“本质直观”,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抽象化、普遍化、逻辑化表达。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书写”与体系建构
若把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简单理解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写法”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体系建构方法(尤见于学术专著之中)。郑永廷按照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线索,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它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方向、准则和基本要求,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工作相结合的方法等。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是指适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各环节的主导性方法,又可进一步按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之事前、事中、事后细分如下:事前的方法分为思想信息收集方法、思想分析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决策方法;事中的方法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方法、一般方法、综合方法和特殊方法;事后的方法有思想政治教育反馈、调节、总结评估等方法。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操作方法。即具体方法的实际运用,使得具体方法更加程序化、规范化,更具应用性和可操作性。第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运用的艺术和技巧。[1]
也可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结构体系或时空构成把它分为时间的方法和平面的方法,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最常见的两种“写法”,前者主要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书写”,后者主要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书写”。如有学者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过程为逻辑线索,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分为思想信息获取的方法、思想信息的分析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决策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综合教育的方法及思想政治教育检查、调节和总结的方法等。[2]还有学者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论为研究对象,以平面的方式构成逻辑主线,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分为实验法、问卷法、观察法、访谈法、个案研究法、质性研究法等。[3]
我们也可以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的)来划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或曰书写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政治观教育方法(如阶级分析方法、灌输法、忆苦思甜法等)、人生观教育方法(如榜样示范法)、道德观教育方法(如移情、慎独、体验等)。还可以根据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成效来划分,如提高知晓度的方法有传播方法,提高认同度的方法有说服方法,提高内化度的方法有感染方法,增强意向性的方法有意志训练法等。上述方法主要作用于人的品格形成的某一个要素,可以称之为单一效能的方法,除此,则称综合效能的方法,如理论教育法、实践教育法、自我教育法等。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一般分两个层次,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即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方法),前者如说理法、故事法等,后者如实验法、观察法等。若从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一种特殊教育门类的角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又可分为三大类: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进一步,作为教育方法,又可大致分为两类:动之以情(如故事法、感染法等)和晓之以理(如说服法、说理法等)。作为教学方法,大致分为两类:单向灌输法(如演讲式教学法、宣讲式教学法等)和互动生成法(如讨论式教学法、对话式教学法等)。作为研究方法,也可大致分为两类:思辨方法和实证方法,前者主要指概念推演或逻辑分析一类方法,后者如个案法、访谈法等。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内部层次性
以上皆可视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外部层次性,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本身还有它的内部层次性。
1.方法—方法观—方法论。作为经验性的存在或过程,方法是一种“物化的意识”或“意识的物化”,或者说是意识的对象化过程。它同时又是意识反思的对象。在从方法到方法论的发展过程中,思维的抽象度、系统性和理论的纯粹化都会得到提升。方法是方法论思想聚焦(认识、思考)的对象,在从方法到方法论的螺旋运动、理性提升的过程中,方法观处于中间层次。方法观存在于人的意识或观念之中,系于个人对方法的敏感性,往往是一种零散的、原始的、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观念性存在。方法论则常常以文本形式呈现,是一种抽象的、成体系的、有专业知识为背景的理性存在(理论存在)。在这里,文本(包括语言、符号、文字、图像、书籍、电磁材料等)是方法论的客观化产物。
马克思在谈到人的活动或劳动与动物的活动之间的本质区别时曾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4](p208)“没有思想的劳动”或“没有劳动的思想”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即便是“最蹩脚的建筑师”,可能还谈不上方法论,但却不能没有方法观。
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并非始于我们给思想政治教育“立名”、“正名”之日,也并非全然属于“官方话语体系”。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讲求一个“理”,崇尚“以理服人”。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有理还要讲出来,所谓“鼓不打不响,理不讲不明”;理有分歧,还要辩理(论理、评理),所谓“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理有不通,则说:“感觉不是那个理”。因为他们坚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孟子·告子上》)这些俗谚成语,皆蕴含着素朴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观。陈少明说:“中国人因为儒家发明的‘理’而使生活变得有秩序。”[5]“服人心者,莫先乎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要坚持:“说理教育法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并把它上升到方法论高度予以重视。[6](p1)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曾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对革命军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在农村和农民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党的宣传教育的重点难点。他们在农村“广泛张贴标语和图画、编唱歌谣、戏剧演唱、讲演、办农民学校以及出版专供农民阅读的书刊等”,[2](p31)毛泽东高兴地评论道:“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速。”(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延安整风时期,提出“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等原则方法,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了公式。
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任务和对象,创造性地推出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此过程中,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总结,如著名的“古田十法”、毛泽东的“七条经验”、“谭政报告”、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等。[7](p61-174)这些方法总结一般散见于党的文件资料、会议报告或领导人的讲话中,多属于经验总结性质,还没有达到方法论的理论高度,性质上属于方法观或论方法。专门的比较系统的方法论研究,则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建制以后的事。它与学科(学术)自觉紧密相连。在这里,经验思维、经验理性必然会上升为系统思维、科学理性。因为“形上学出自人的天性,是人的思维的自然倾向的发展”。[8](p129)
从思想或理论的成熟度来说,方法观还不能算作方法论,因此,方法—方法观—方法论的层次划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之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外部层次性。
2.论方法—方法论—方法学。这是就方法论的内部层次性来说的,因为已有“论”的因素涉入其中,但是由于理性、理论的介入和干预程度的不同,三者在理论的系统性、抽象度和纯粹化方面表现出由低到高的层次性。
自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正式创立以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就成为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初期的研究侧重具体方法的经验研究,以介绍各种方法为主要形式,特点是:方法命名(正名)+方法介绍+事例集锦+经验总结。例如:张洪华、杨亚平的《思想工作方法纵横谈》;范印华等的《艺术·快感·磁力:思想工作方法谈》;刘国彬、张运德的《古今思想工作方法例析》;姚毅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方法集锦》等。[9](p3-7)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玄武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首次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为逻辑主线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为之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堪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后,陆续出版了十几部此类专著或教材,代表性的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郑永廷,1999)、《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黄蓉生,2000)、《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祖嘉合,2004)、《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陈华洲,2010)、《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黄志斌,2012)、《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发展研究》(邹绍清,2013)等。还有一些关于专门方法的专项研究的著作,如《思想政治教育统计研究方法论》(戴钢书,2005)、《说理教育法研究》(潘莉,2013)等。它们或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为逻辑主线,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王玄武等,1985、1992)、《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郑永廷,1999);或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为线索,如《思想政治工作学比较研究》(戴耀荣,1992);或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作用为标准,如《思想政治教育学》(邹学荣,1992)等,旨在按一定的逻辑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系统,其研究视角已脱离单纯的具体方法的阐述,进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中的方法结构层次研究。其研究进路表现为:基于“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整合方法的体系、特点等。不可否认方法的结构层次研究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乃是以方法为对象,对方法进行结构层次的研究,所以难免带有论方法的特征。
论方法侧重具体方法的介绍、说明,围绕方法的实际使用,努力发挥理论的直接指导作用,研究方法是对经验方法的概括、总结和提炼,从而为实际使用者支“招”,其实质是一种“技术性思维”(“方法术”),解决的是“如何?”、“怎样?”的“路线图”问题。而方法论则具有“本质主义情怀”,执着于方法背后的最一般过程及其规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不仅要具有系统性,还应具有高度概括性和高度抽象性。“科学方法论提供给我们的是一般性的方法论原则,而不是具体的方法本身。就拿完成任务需要的‘桥’或‘船’的比喻来说,科学方法论并不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桥’或‘船’,但是教给我们认识造‘桥’和‘船’的一般原则。”[10](p18)人们研究方法论,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举出更多的方法、用系列方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也不在于为人们提供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而是要通过方法论获得更多启示和启发,从而发现新的规律。这才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价值——指导作用所在。如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倾向于具体方法的阐释,致力于搜集所有方法,这样非但不能罗列出所有方法,反而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作为一门科学应有的理论深度。”[11](p180-182)
理论要想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必须首先“脱离实践”。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理解方法论的简单定义——关于方法的理论体系。方法论是以方法为研究对象,但方法论的研究重点不仅仅在于分析具体方法,“它在研究、探讨和阐释各种方法时,侧重于找出方法的理论基础,分析方法的性质、特点、作用、范围和局限,研究方法的发生、发展规律,探讨各种方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探究发现新的方法和运用方法所遵循的原则等等。”[11](p180-182)这就由论方法逐步进入到方法论层次,最后必然进入到方法学层次(侧重概念考察、观念批判和经验反省,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元问题关于研究范畴、概念厘定、理论基础、基本体系和价值功能等的研究)。就目前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还略显不足,特别是方法学的研究偏少。
从论方法到方法论直至方法学,是理论研究深化拓展的客观过程,是理性或理论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理性冲力”的体现,也是理论的魅力所在。理论“脱离实践”,才能获得抽象性和高度概括性特点,才能更好发挥它的普适性和指导性价值。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功能阈限
1.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指导性。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把“思维着的精神”誉为“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12](p462)作为思维的成果——理论,更是与学术、学科、学问、学者等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传承和进步。尤其是科学理论,因其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系统性,而具有普适性、预见性、可迁移性和创造性等功能。概而言之,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我们常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但是,如果过分抬高理论的“指导”作用,则会陷入理论的幻觉。理论因脱离实践而获得了它的纯粹性,并赢得它的独立地位。毋庸讳言,理论与实践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处于对立的两极。若分别言之,则两种矛盾的性质及各自处理矛盾的方式又有所不同。理论本身的矛盾是一种思维中的矛盾,它处理矛盾的方式就是遵循形式逻辑的三大定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三大定律可以归结为一个定律:不矛盾律。也可以说,理论就是通过不断地发现和弥合自身的矛盾,来达到“自圆其说”的。而客观世界本身不存在矛盾,或者说无所谓矛盾不矛盾,矛盾恰恰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自我改造自我的过程中,就产生了矛盾。矛盾产生于人把捉世界的过程中,从这一点来说,矛盾具有属人的特性,其性质是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处理这个矛盾要精微和复杂得多,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人们常常以“知识”的标准来衡量理论和实践,并把实践排除在知识之外。殊不知,“实践有它自己的知”,恰如理论也有它自己的实践一样(如实验试验方法、调查统计方法、推理论证方法以及书写方法等)。“理论之知”,是一种“明述的系统的知”,它是在把认知对象“专题化”、“客体化”后得到的理论化的知识,是为“理解”而认知。这种眼光总是“把世界淡化到纯粹现成事物的齐一性之中。”[13](p161)“对世界的抽象理解,同时也意味着对存在的分裂或分离。”[14](p137)这也许是理论诞生的必要成本和代价。“实践之知”,则是一种“整体上的知”,涉及工具、材料、对象、环境、主体、客体、目的、手段等,需要权衡、博弈和算计。“实践是多多少少自主自治的活动”,是为“操劳”、“上手”而认知,追求“明慧和练达”。[15](p15-23)
说到理论的“指导”作用,方法论最有可能担当这一角色,因为它与实践的联系最紧密,同时还隐含着“巧”和“妙”的价值追求。方法论作为理论,具有抽象性的表象,但它同时追求具体性——“思维中的具体”,并由此而获得更大的普遍性和直接性。与此同时,它的一种“限制”或“阈限”——使自己或对方获得一种特殊的极限情况,也一道产生了。理论研究本身自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在,人们从事理论研究,倒不一定是为了指导实践,而是为了“理解”世界,它往往通过这些东西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方法论实质就是关于方法的一套解释系统,它使得千变万化的方法变成可理解的、确定的,最终达到普遍自觉。人们研究方法论,不仅仅在于举出更多的方法、用系列方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而是要通过方法论获得更多启示,发现新的规律。方法论研究也不仅在于直接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思想观念,从而间接影响决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并不一定能指导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更不是去实施或应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理论。即使作为方法论层次中的论方法,也不能把它视为“说明书”和“施工图”,如果将方法直接套用,也会有较大的风险,更遑论与实践渐行渐远的方法论和方法学。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特殊性还在于:它是我们自己的活动,是与人—社会打交道的活动,这些活动无法像物理学那样,使对象客体化,或充分客体化。它的实践活动的目的始终与它所涉及的对象交织在一起,无法完全独立于实践活动本身加以界定,并且活动主体也常常卷入其中。
2.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可教性。方法论的指导对象是方法,真正的方法具有个人性、情境性和无形性。方法总是与方法的使用者密不可分,它是一种内化的、嵌入式的内存知识,并且总是与特殊问题和任务情境相联系,是对特殊问题和任务情境的自觉综合和把握。人们虽然常常称羡它的“巧”和“妙”,但却难以用有形的物质实体作为载体表现出来(文字、语言也许只是它的外壳),同样也难以通过读书、听讲等传播手段获得。方法论总是带有“好为人师”的价值偏好,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方法是可教的,而方法的运用——更不用说方法艺术,则是不可教的,或者说是难教的。因为方法的真正载体是人,它来自个体的体验、洞察和感悟,而它的最终获得则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只能依靠个人实践,包括艰难的试错学习。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它的主体是人,对象也是人,这就有可能出现即使学会了方法,遇到不同的对象,遭遇不同的情境,效果很难逆料,甚至事与愿违。如果我们勉强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称之为“间接”的指导作用,这个“间接”则包含一个巨大的空间或“黑洞”,而这恰恰是“实践智慧”的作用范围。在一般原则和具体情境的结合中,我们需要的是实践智慧,而不是程序化的推理。“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易传·系辞上》)“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功于化。”(石涛《画语录·变化章第三》)这是一个“转识成智”的过程。
理论的产生是有代价和成本的,以之直接指导实践,是有一定风险的。方法论上的科学不能保证实践上的有效,但方法论的价值却并不因此而遭贬损。即使理论不能直接指导实践,却必然对实践活动产生影响,理论会“启发”、“启示”实践者,促进实践活动中的“明理”和“自觉”(马克斯·韦伯所谓“头脑清明”),从而有助于提升实践的品质。理论的风险意识告诉我们:理论既有创造性又有制限性。这一方面希望可以堵住教条主义的路,另一方面又给创新预留了后门。也许,我们在理论研究中需要努力做到的就是始终保持与实践智慧的联系,保持对实践活动的真切体会。
参考文献:
[1]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王玄武,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3]佘双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陈少明.经典注疏对现代人更有价值——专访中山大学教授陈少明[EB/OL].新华网,2014-09-27,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7/c_11 12652232.htm.
[6]潘莉.说理教育法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7]王茂胜.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简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8]郁振华.“具体的形上学”管窥[A].何锡蓉.具体形上学的思与辩[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9]祖嘉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研究回眸与展望[J].思想教育研究,2008,(12).
[10]孙小礼.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11]徐金超.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科学化[J].理论月刊,2009,(1).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
[14]何锡蓉.具体形上学的思与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5]陈嘉映.实践/操劳与理论[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责任编辑张豫
·传媒研究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6)05-0187-05
作者简介:胡心红(1969—),男,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合肥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副教授,硕士。王习胜(1965—),男,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人文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理论与方法研究”(13AKS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