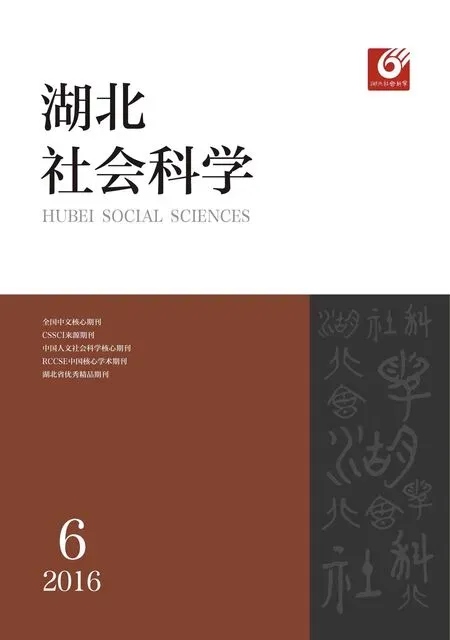秦汉时期基层官吏职务连坐新探
——基于秦汉简牍的考察
靳腾飞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秦汉时期基层官吏职务连坐新探
——基于秦汉简牍的考察
靳腾飞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以往对秦汉时期官吏连坐的研究多从历史学的角度展开,且分类标准模糊不清。从任用和管理的角度来看,秦汉官吏连坐现象可分为保举连坐和行政连带责任两大类,其中后者在基层手工业、军事事务以及官府财物的校验管理等不同职务领域规定不同。保举连坐和行政连带责任是秦汉时期重要的官吏管理制度,并且不断地成熟和完善,主要表现为整体刑罚的减轻和具体规则的细化。
秦汉;保举;连坐;连带责任;简牍;吏治制度
秦汉出土简牍中有不少关于基层官吏连坐的记载,以往的研究多称这类现象为官吏职务连坐,并根据连坐的对象分为举主(保举)连坐、公罪连坐,或根据连坐的具体原因和领域分为上计制度中的连坐、公务责任连带、考核竞赛中的连坐等类型。统观已有的研究,多单一地从历史学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考察,而且分类的标准不统一,界限模糊不清。本文将结合行政法的相关知识,对基层官吏连坐现象进行重新定义和梳理,探寻现象背后的行政法原理,并结合出土简牍中的相关记载,进一步研究秦汉时期这种吏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和历史作用。
一、行政法视域中职务连坐的重新定义
早在商周时就有了连坐的思想,如《尚书·泰誓》中记载:“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1](P402)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秦时的三族连坐之刑应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商鞅变法后,连坐作为法律制度正式颁布:“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牧司”谓相纠发,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商鞅把治理百姓与军功爵制结合起来,告奸者与斩敌首的奖励一样,可得爵一级。降敌者诛其身,因而“不告奸者”和“匿奸者”按军法进行连坐,都要处以极刑,惩罚严厉。这种制度最初用于对普通民众的治理,是法家重刑主义思想的体现,后来随着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官吏人数激增,如何有效治理庞大的官僚体系成为一个难题。连坐法强调组织成员间的相互监督和相互负责,能有效减轻统治者的治理负担,因而被应用到官吏的治理上。
秦汉时期的官吏连坐现象并没有明确统一的称呼,有的只称“坐”,如《效律》:“司马令史掾苑计,计有劾,司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计劾然。”[2](释文部分P76)有的列举了连坐的惩罚结果,如《秦律杂抄》:“戍者城及补城,令姑(嫴)堵一岁,所城有坏者,县司空署君子将者,赀各一甲;县司空佐主将者,赀一盾。”[2](释文部分P90)为了研究的方便,以往的学者多把这种因职务关系受到连坐的现象称统为“职务连坐”。
但是官吏连坐现象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领域,背后有其行政法学的原理以及相对应的指称,“职务连坐”这种称呼并不确切。首先这种现象发生在吏治领域,而连坐本是治理普通民众的一种制度,二者适用范围不同。其次,连坐法是本人无罪或没有直接责任,只是因为与其有关系的人犯罪而受到牵连获罪。而连坐现象中获罪的官吏虽然主观上没有直接违法或有过错,但由于地位或职权,其对上级、下级或同级的违法行为客观上具有一种连带责任,这种责任可能缘于监管或职务上的共担。因此,对于官吏的连坐现象,职务连坐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行政连带责任可能是对这种现象更为确切的称呼。“行政连带责任的成立,要求责任主体之间具有职权上的连带性。行政连带责任的哲理基础应当是行政职权越来越精细的分工。”[3](P17)秦汉时期政府职能不断扩大,官吏的职权也出现分割化的特征,为了有效治理这个复杂庞大的官僚队伍,秦汉统治者在吏治上借鉴了“连坐”的思想和方法,创立了那个时候的行政连带责任制度,将官吏的权责关系对等起来,使其权利义务统一起来。
保举连坐是官吏连坐现象中的一大类别,过去的研究中往往把它和公罪连坐现象统归为官吏的职务连坐,这也是不恰当的。职务连坐往往发生在在官吏履行职务的过程中,秦律规定:“同官而各有主殹(也),各坐其所主。”[2](释文部分P72)在同一官府任职而掌管的方面不同,官员要分别承担自己所管方面的责任。保举又称荐举,我国古代的荐举形式有私人荐举、制度荐举、官府举荐和自荐等等。因此保举有可能出于私人的行为,前者的概念范围并不能完全覆盖后者。公罪连坐类似于行政连带责任,“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4](P44)指因职务上的公事而受到连坐,并非出于个人主观故意,是一种事后的追责,而保举连坐现象本质上是对之前的保举行为负责,是一种事前保证,二者的发生机制不同,属于不同范畴的行政行为。因此,对于秦汉简牍中的官吏连坐现象,应具体分为保举连坐现象和行政连带责任两大类,以下对这两类现象分别进行研究。
二、秦汉时期基层官吏保举连坐的立法流变
秦汉时期的官吏选举有许多途径,如军功制、赀选制、察举征辟制、功劳升迁制等,而察举或荐举是选官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央及地方的长吏由朝廷直接选任,而公府、州府、郡府及县廷的属吏由各级主官辟除。为了保证官吏在保举时客观公正,防止各级官员结党营私,形成宗派党争,自秦国时开始推行“保举制”,当时的法律对于保举行为有严格的规定,引入连坐的思想和方法。如对于基层官吏的保举和任命,秦时有具体的法律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记载:“除士吏、发弩啬夫不如律,及发弩射不中,尉赀二甲。”[2](释文部分P79)秦时对于军队中士吏和发弩啬夫这类基层军事官吏的任命严格按照律令来执行,如果所任命的官吏不符合律令程序或射弩技能不合格,任命者也要受到惩罚。对此汉代也有类似的规定,居延汉简中就有相关的记载:“十一月邮书留迟不中程各如牒晏等知邮书数留迟,为府职不身拘校而委任小吏,忘为中程,甚毋状,方议罚,檄到各相与邸校,定吏当坐者言须行法。”[5](P40)程,法度、程式。《商君书·修权》:“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6](P107)秦汉时期专指邮书传递是否规范与及时,邮书按时送达即为“中程”,失期称为“不中程”,对于不能身体力行而委任小吏,谎报邮书“中程”的府吏晏,要“议罚”并追究“吏当坐者”。
除了保举和任命要遵守相关法律,对于被保举对象的资格和范围,秦汉时期也有具体的规定。在《秦律杂抄》中记载:“任法(废)官者为吏,赀二甲。”[2](释文部分P79)“废官”,曾被废置不用的官员,如果保举有此经历的人为官,在秦时是要被罚“二甲”的,官比吏的职位更高,一旦被废,即使降其身份担任小吏亦不可得,可见“不曾为废官”是当时被保举对象的资格条件之一。汉代的边塞简中,有很多关于边塞官吏任职评价的记载,如《居延汉简甲乙编》云:“肩水候官并山长公乘司马成,中劳二岁八月十四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年卅二岁长七尺五寸觻得成汉里家去官六百里。”[5](P9)从这条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是对该官员工作能力的具体评价,居延汉简中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可以肯定这三点是当时评价边关基层官吏的重要标准,也很可能是当时官吏被保举、升迁所需的必备条件。由这两条材料可以推测,当时的被保举对象应该还有其他具体的限制和要求。
保举连坐的主要目的在于防范保举人滥用权力,使其对被保举人在任职期间的不当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但在被保举人不担任行政职务时所发生的违法行为,保举人则不对其负责,这一点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有明确记载:“任人为丞,丞已免,后为令,今初任者有罪,令当免不当?不当免。”[2](释文部分P127)对于所任命的丞,在免职后有犯罪行为,初任者不承担责任。从这点可以看出保举连坐的法律效力范围是被保举官员在履政期内的行为,超出这一范围,保举人则不负连带责任。
汉承秦制,虽然秦汉均有保举连坐的现象,但保举连坐现象在这一时期内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战国中后期,连坐法被应用到官吏的保举制度上,具有直接套用的明显痕迹,惩罚较重,且现有文献的记载中没有太多详细的规定,如:“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各以其罪罪之”即要求保举人承担与被保举人相同的罪责,可见惩罚之重,且连坐的缘由仅为“所任不善”,并没有对引起保举连坐的不当行为作出具体的分类和规定。
随着吏治实践的发展以及制度上的完善,秦时官吏的保举连坐现象主要发生了两方面变化:一方面是惩罚力度的减轻;另一方面是制度规则的细化。如《睡虎地秦墓竹简·除弟子律》载:“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候)。使其弟子赢律,及治(笞)之,赀一甲;决革,二甲。除弟子律。”[2](释文部分P80)对于保举任用时的“不审”行为,采用“耐为侯”的惩罚,相比于“以其罪罪之”,“耐为侯”在量刑上已减轻了不少。而且这条材料是对“除弟子籍”这种具体行政行为的保举连带规定,可以推测对于其他类型的保举任命行为,也应该有具体的规定。
与秦时相比,汉初对于保举人的惩罚较轻而且规定更为详备。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记载:“有任人以为吏,其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罚金四两,戍边二岁。”[7](P172)《二年律令》应是从汉高祖五年到吕后二年施行的律令,可以看出当时导致保举连坐的原因至少有不廉和不胜任两种,对应的惩罚仅为免职。相比于秦朝因“不审”而“耐为侯”的标准要轻很多,而且当时对于不同身份的保举人或荐举人,惩罚标准也有所不同。保举人分为“吏”和“非吏及宦”两种情况,“宦,是宦皇帝者的省称,律文说对任人不廉不胜任者,其人若‘非吏’、或者是‘宦皇帝者’的话,惩罚是罚金和戍边;相应可以推知,这人若是‘吏’的话,惩罚就是‘免任’。”[8](P83)
到了西汉中后期,法家重刑思想在吏治实践中的影响进一步减弱,统治者关注的重点从国家系统的稳定转向有能之士的任用,如放宽了被保举人的资格限制。秦时“任法(废)官者为吏”是要受到惩罚的,但在西汉中后期更看重官吏的治理能力,如宣帝时,黄霸曾“阿从不举劾,皆下廷尉,系狱当死”,(《汉书·循吏传》)但在三年后出狱又被举荐,而成帝时红阳侯王立也曾举荐过因罪被罢官的陈嘉。
总的来看,秦汉时期对于官吏保举连坐的惩罚力度是逐步减轻的,有关的规定和相应的惩罚措施也在不断细化。发生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法家重刑思想在秦汉不同时期受统治者重视的程度不同,这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吏治思想的进步和吏治制度的不断完善。
三、秦汉时期基层官吏行政连带责任的分类
秦汉基层吏治中连坐思想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官吏履行职务时所承担的行政连带责任上,如在基层手工业、军事事务以及官府财物的效验与管理等方面都实行连带责任制度,出土简牍中对此多有记载。
——基层手工业
秦汉时期的统治者把连坐思想广泛地运用到基层官吏的治理上,实行了严格的上下级负责制,这突出表现在手工业的管理上,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中记载:
工匠到别的县领漆,运抵官府后要用“饮水”的方法对漆的质量加以测试,如果漆的质量不足,则根据所缺的数量进行不同程度的处罚,有赀二甲、一甲和一盾三种尺度。①关于甲、盾换算与值数的讨论,学界观点不一,于振波认为一盾为384钱,一甲为1344钱,参见于振波:《秦律中的甲盾比价及相关问题》,《史学集刊》2010年第5期。由于上下级之间职权上的连带性,材料中除了工匠要受罚,吏将者也承担同样的处罚。上位机构对下位机构具有职权上的包容性和连带性,这也是上级对下级负有行政连带责任的法理来源。在手工业的考核中,上级官吏的连带责任要轻一些。《秦律杂抄》中记载:“省殿,赀工师一甲,丞及曹长一盾,徒络组廿给。省三岁比殿,赀工师二甲,丞、曹长一甲,徒络组五十给。”[2](释文部分P83)“丞”应为负责工师管理的官员,曹长可能为工师中的小组长。对于工师的产品在考核评比中殿后的,负责管理的丞及小组长都要受到惩罚,但力度比工师轻,这是由于相比于工师,丞和曹长虽是上级,但并不是“省殿”的直接责任人。又如《秦律杂抄》中记载:“戍者城及补城,令姑(嫴)堵一岁,所城有坏者,县司空署君子将者,赀各一甲;县司空佐主将者,赀一盾。”[2](释文部分P90)“县司空署君子将者”应该是直接主管筑城和修城的底层官吏,他们对“城坏”负有的责任就大于“县司空佐主将者”,这是因为后者并不主管筑城和修城,只负有连带责任。
——军事事务
秦汉时军队的管理非常严格,军事事务中也实行严格的连带责任,如兵器的制造与管理,《秦律杂抄》中记载:“·稟卒兵,不完善(缮),丞、库啬夫、吏赀二甲,法(废)。”[2](释文部分P82)发给士兵的兵器如果质量不好,那么具体负责此事的丞、库啬夫、吏都要被罚,且永不续用,可见当时对于军队事务违纪的惩罚很重。又如汉初《二年律令·捕律》中规定:“盗贼发,士吏、求盗部者,及令、丞、尉弗觉智(知),士吏、求盗皆以卒戍边二岁,令、丞、尉罚金各四两。”[7]150该事例中,士吏、求盗是关于盗贼事务的直接责任人,所以惩罚较重,“戍边二岁”。作为士吏、求盗上级的“令、丞、尉”只因职权上的包容性而承担“罚金四两”的连带责任,相对于直接责任人,上级所承担的连带责任要轻一些。
对于边关基层官吏的管理,上级对下级的行政不当行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如《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记载:“第十四卒氾宽不在署,谨验问第十守候长士吏候史辤曰十二月五日遣宽〼”[9](P158)对于燧卒不在署的问题,主管的候长要受到验问。对于属下的过错,直接上级同样要承担连带责任,如《居延新简:甲渠候官》:“鉼庭候长玉护,坐隊长薛隆误和受一苣火,适载转一两到□〼”[9](P191)掌管边关烽火的燧长如果误传烽火,那么主管的候长也要受罚。
——官府财物的校验管理
秦时对于官府财物的校验管理非常严格,如果财物的管理与校验出现问题,则对相关责任人实行连带惩罚,如《秦律十八种》中记载:
此条中对于共同出仓人员明确规定“杂者勿更”,如果中途更换造成粮食不足数时,则令、丞都要受到惩罚,这是对出仓这个共同行政行为的惩罚,参与其中的个体均要承担连带责任。行政行为往往是以行政组织的名义实施的,但具体的行政行为却是由组织中的个体做出的。因而对于以行政组织为单位发生的不当行为,组织中的个体要承担行政连带责任。如果官府财物出现损失,而又无法明确具体责任的,官府里的个体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如《效律》:“官啬夫、冗长皆共赏(偿)不备之货而入赢。”[2](释文部分P69)这里是指以整个官府作为核验单位,当公共财物出现不足而又无法明确个体责任时,则作为这个官府机构中的官员个体都要承担连带责任,共同赔偿官府财物。组织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构成,组织行为也是通过具体的个人实施的。个人对组织的行政连带责任强调了官吏在履行职责时的合作意识和责任共担,有利于防范以组织为单位发生的行政不当行为。又如在《法律答问》中一条关于司法不直的事例记载:“赎罪不直,史不与啬夫和,问史可(何)论?当赀一盾。”[2](释文部分P115)判处犯人“赎罪”不公正,虽然“史”并没有赞同“啬夫”的判决意见,但由于“赎罪不直”是司法机关作为一个整体作出的判决结果,因此作为其中一员的“史”还是要承担连带责任,被罚一盾。
对于官府财物的校验审计也实行连带责任制度,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中规定:“县、都官坐效,计以负赏(偿)者,已论,啬夫即以其直(值)钱分负其官长及冗吏,而人与参辨券,以效少内,少内以收责之。”[2](释文部分P39)县、都官因为审计中出现问题而被问罪的,要计算应偿付的损失,由官府内的官长和其下级冗吏一起赔偿,这种规定有利于督促下级对上级进行监督,避免唯命是从。下级官吏要对上级官吏的过错承担连带责任,这主要是因为上下级均处在同一行政行为的链条上,相对于上级的决策或命令,下级是主要执行者,尤其是上级的违法犯罪行为也大多通过下级实施。校验审计中对于下级官吏的犯罪,上级同样要受到惩罚,如《效律》中的两条记载:
尉计及尉官吏节(即)有劾,其令、丞坐之,如它官然。
司马令史掾苑计,计有劾,司马令史坐之,如令史坐官计劾然。[2](释文部分P75-76)
对于主管会计的下属官吏,如有犯罪行为,其上级官吏令、丞或司马令史是要负连带责任的。“如它官然”、“如令史坐官计劾然”的记载,说明当时对于其他职能部门的官吏如有类似情况,也要承担连带责任。但相比于直接责任人,连带官吏所受的惩罚较轻,如《效律》:
官啬夫赀二甲,令、丞赀一甲;官啬夫赀一甲,令、丞赀一盾。其吏主者坐以赀、谇如官啬夫。其它冗吏、令史掾计者,及都仓、库、田、亭啬夫坐其离官属于乡者,如令、丞。[2](释文部分P75)
这条材料是关于会计核验不实的惩罚规定,其中主管会计的官啬夫与其上级官吏令、丞都要受到惩罚,但后者比前者轻。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秦汉时期行政连带责任制度已被应用到基层官吏治理的大部分领域中,而且秦朝的刑罚力度要比汉代严重得多,连带责任者所受的惩罚一般比直接责任人要轻,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连带责任的规定日益细化,制度逐渐成熟。
结语
综上所述,职务连坐作为一种吏治制度自秦时就已确立,并被广泛地应用到官吏的治理中,为后世所沿袭,至今仍是治理官员的重要手段。从官吏任用和管理的角度来看,秦汉时期官吏连坐现象主要分为保举连坐现象和行政连带责任两大类型,保举连坐有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行政连带责任有利于遏制行政体系中的权责不对等。虽然职务连坐有其残酷的一面,但其对官员的权力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强化了官吏行政过程中的责任与合作意识,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3]关保英.论行政连带责任[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3).
[4](唐)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战国)商鞅.商君书[M].石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7]彭浩,陈伟,[日]工藤元男.二年律令与奏谳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8]阎步克.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J].中国史研究,2003,(3).
[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4.
责任编辑 唐 伟
K232
A
1003-8477(2016)06-0113-05
靳腾飞(1988—),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2012级博士生。
——秦汉时期“伏日”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