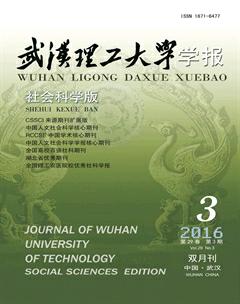郑振铎与战后“文学批评”
——以《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为考察对象*
晏 亮
(1.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郑振铎与战后“文学批评”
——以《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为考察对象*
晏亮1,2
(1.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战后,郑振铎延续了对于文学研究的一贯热情,适时推出《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专号通过反思早期学者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过程中的得与失,搜集众多当时一流学者在各自研究领域的厚重之作和大量俗文学批评理论,以及将中西比较研究提升到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中的方法论的高度,为战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与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郑振铎;《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中国文学批评史
作为20世纪的一门显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在上世纪前半期即经历了早期崛起、之后的突飞猛进、1930—1940年代独立成科的过程。为梳理这段历史,不少学者均在这一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以陈钟凡、朱东润、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等五位学者的成就最为显著。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独立成科的正式起步。1931年,朱东润在武汉大学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1943年其课程讲稿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之名正式出版。期间,方孝岳于1934年出版《中国文学批评》,郭绍虞分别于1934年和1947年出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和下册,罗根泽于1943年出版完《中国文学批评史》。与陈中凡相比,后四者明显在材料选择、体例编排、研究目的和论述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至此,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建立。
与上述五位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来完成学科创立使命的奠基者不同,几乎在同一时间从事文学批评的郑振铎,因为既无专著,且其与此相关的成果基本上也是散见于《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等其它文学史著作中,所以,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常常被忽视。其实不仅如此,与一般从事文学批评的专业学者不同,郑振铎还特别注意利用自己作为一名文学编辑的身份和特长,先后通过主编《小说月报》、《文学》和《文艺复兴》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号”,与上述学者一道,共同参与、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因此,本文试图以郑振铎在战后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为考察对象,来全面梳理、总结、评价其对战后中国文学批评的贡献。
一
从文学创作和创办社团开始其文学活动的郑振铎,早在起步阶段就表现出了对于文学研究的浓厚兴趣。1920年底,他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言及社团成立的动机时,他就曾明确指出:“一九二○年十二月间,有本会的几个发起人,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述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1]显然,包括“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等方面在内的文学研究工作,在此时的郑振铎心目中,即摆在了创作之前。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从创办文学研究会那时起,郑振铎就开始了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立的有关工作。但是,从他接手后来成为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的《小说月报》后刊物上出现的变化,就可以发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郑振铎利用自己创办多种刊物的便利条件,为建设新文学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客观上也为后面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不仅进行了可行性道路的摸索,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的材料储备。
作为战后“文艺复兴”系统工程中的一部分,3卷《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的缓慢刊出,与郑振铎策划的前两次“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相比,在当时经济形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未尝不是应付时局的无奈之举。但是正如郑振铎以《编余》形式发布的征稿启事中所言,“在第四卷里,我们想出版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这许多年来,有许多专家们,对于中国文学作了不少很深湛的研究,而没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文章。我们想给一期乃至两期的篇幅,专门的载这些文章。来稿盼望能够不迟于九月底以前交到。”[2]其创办3卷专号的初衷,更多的还是出于总结当时近十几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成果的目的。自1930年代的《文学》之后,在全民抗战的氛围中,为了配合时代的主旋律,除了从事与之相关教学工作的高校教师,大部分学者都不可能静下心来进行专门的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文学创作才是当时文坛的主流。因此,《文学》之后的1930、1940年代“纯文学”刊物里,基本上都是文学创作占主导。即使是《文艺复兴》的前20期常规杂志,从前文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与在文学创作上开创的精彩纷呈、大家迭出的局面相比,刊物在理论建构这个环节上则显得黯淡得多。无论在数量或者质量上,都与文学创作有相当的距离。这一点从刊物仅有的、由郑振铎亲自撰写的理论文章《发刊词》和《迎文艺节》即可看出。显然,这样的外在环境对于作为新兴事物的中国文学批评来说是极为不利的。那么,随着抗战的胜利,各项文学事业百废待兴,刚刚取得独立地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同样需要抓住这一契机,求得新的发展出路。所以,郑振铎于此时推出的《中国文学研究号》,无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在战后的壮大、发展做了一定的铺路工作。
自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叩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之后,各种以理性见长的西方文论纷至沓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许多学者直接参照西方文论,并以之全面质疑否定以诗性见长的中国古代文论,甚至有以西代中的趋势。20世纪前期由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奠基者掀起的古代文论研究高潮,虽然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独立成科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们研究的重点是中国文学批评发展演进的历史,主要侧重于史的宏观把握。其既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进行全面反思,又没有对处于各种西方文论包围中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到底该何去何从进行深入的思考或者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系统整理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孕育到独立成科近四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因此,在战后文化复员工作迅速展开的热潮中,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再次成为其中热门话题时,去总结处于风云变幻的20世纪前期的学者们在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过程中的得与失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此,郑振铎虽无专文进行论述,但是,从他专为《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撰写的《题辞》中就可以看出,他已经有意识地开始着手此项工作。
二
在《题辞》中,郑振铎在回顾完《小说月报》和《文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的成绩之后,随即分地区地对近十余年的文学研究的经验与不足进行了总体评述。首先,他对抗战期间沦陷区在文学研究工作上的漠然态度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伟大的抗战,占据了十之八的这个时间。中国分成了两个部分,自由区和沦陷区。在沦陷区里,除了极少部分的学者们在杜门不出,默默地从事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工作之外,其他公开的在敌伪所主持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只是留恋过去,谈谈不关痛痒的古典东西。可以说是一点创见、一点成绩也没有。没有灵魂的人如何能够写得出有灵魂的文章来呢?这里可以不必费辞地去述及他们。只有开明书店出版的《学林》和《文学集林》,比较有几篇结实的文章。”[3]接着,又对自由区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在自由区里,情形便不同了。虽然书籍的缺乏,成了普遍的现状,而在物质条件万分困难之下,却有了很好的成绩。郭沫若先生的关于屈原的研究和闻一多先生的《诗经新义》,《离骚解诂》,《天问释天》等篇,都有很大的影响。闻一多先生的关于唐代诗人的研究,像《杜少陵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等尤有新的研究的方法,开辟了一条从前没有人走过的道路。陈寅恪先生的关于《东城老父传》等几篇考证文字,也极有力量。还有很多的学者,也都在流亡与轰炸中成就了不少研究的业绩。”[3]那么,郑振铎进行上述近十年来文学研究得与失的总结的意义何在呢?
其一,虽然郑振铎并没有彻底摆脱时代局限性和较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对国统区文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热衷于中国传统文论和不与时局密切结合的倾向,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而对与之相对应的自由区文学的研究情况却予以绝对的肯定。这种“一边倒”的评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丧失了学者应有的客观冷静的基本素养。但是,他还是基本上切中了当时文学研究中的弊病和成绩。如,他严厉批评了一些学者在民族危难之际,仍然不问世事,彻底放弃“发声”的权利的做法,与此相反,他热情地赞扬了闻一多在艰难的物质条件下,仍然勇于探索,在唐代诗人研究上终于取得突破的事迹。而在194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刚刚独立出来亟待夯实基础的关键时刻,只有正视其过去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才能更好地利用战后可能出现的文学“空场”,进一步完善,从而迅速地发展、壮大。
其二,郑振铎上述分地区的总结性评述,虽然从表面上看言辞犀利,特别是对国统区的文学研究弊病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对于自由区的评价,其似乎更有舍之而就他之感。然而事实上,这些评价从客观上来说就是对1930—19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的梳理和总结,是对本民族文论何去何从的另一种思索,从有助于学科成长的角度来说,这本身就是一大贡献。无论是批评或是肯定,在此后的学科建设过程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来说,郑振铎在《题辞》中的上述评价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20世纪前期以陈、朱、郭、罗、方为代表的学科奠基者,由于更注重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种专门学科的独立意识,所以早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侧重于史的宏观把握和面上的广度,而对于具体每个点上的深度通常挖掘不够。以开创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先河的陈钟凡为例,1927年由他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在独立成科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该著作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对“文学”和“文学批评”予以概念上的界定;第三章讲述了我国文学批评的源起,指出其始于《典论》、《文赋》、《文章流别论》和《翰林论》;第四章至第十二章,以时间为顺序,将我国的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大致分为九大时期。这部著作自成体系,既有总体发展规模的概述,又有各个阶段的分述,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雏形由此开始显现。但是,这部著作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在后面九章的分段叙述中,只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关于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概况的初步轮廓,并没有在任何一点上展开深入研究,而且其在选材上也没有坚持科学客观的尺度,唐代之前的内容占三分之二,宋代以后的仅占三分之一,显得较为主观随意。从学科自身的健康发展的意义来讲,早期奠基者们在专著中体现出来的错误倾向亟待修正。
反观郑振铎主编的3卷《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从其所收集的文章内容及其所及的时间来看,既有上溯到神话传说中伏羲女娲时代的闻一多的《伏羲与葫芦》,也有对22位已故新文学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的唐弢的《新文艺的脚印》;从文章所涉内容来看,既有以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的朱自清的《“好”与“妙”》、高名凯的《音质与诗词》,又有纯粹的文学现象研究,如王瑶的《魏晋时代的拟古与作伪》、余冠英的《谈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即使在文学研究内部,也有比较具体的文体区分。如戏剧类的有严敦易的《元剧斟疑》、徐调孚的《现存元人杂剧目录》等;诗词类的有李嘉言的《词之起源与唐代政治》、黄贤俊的《二隐及其词》等;散文类的有《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等;小说类的有汪浚的《吴承恩与西游记》等。另外还有一些对于通俗文学、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有关中外文学比较与交流的文章。
上述文章不仅所涉及的范围广且丰,而且其作者大多都是当时一流的学者,而且从大部分文章的内容来看,其研究结论一般都建立在具体的事实材料基础之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专号文章精湛厚重的保证。因此可以说,当大部分文学资料在连年战火中损失殆尽时,郑振铎费尽心思搜集的这些“这许多年来,有许多专家们,对于中国文学作了不少很深湛的研究”[2]的批评理论文章,无疑为当时亟待加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不仅如此,这些评论文章由于本身所及的时间跨度大,内容涵盖面丰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缺陷的修正和弥补。
三
中国是诗与文的国度,小说、戏曲向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技”。与小说、戏曲的文学史地位相对应,小说、戏曲的批评同样不为人所重。而小说、戏曲的批评理论大多散见于序、跋、引、题词、评点等零散的文体形式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其研究的难度。因此,早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者大多以诗论、文论的研究为主。比如在陈钟凡、罗根泽的研究体系中,小说、戏曲批评是被彻底摈弃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考察范围之外的。朱东润、郭绍虞、方孝岳虽然偶尔涉及,但也仅限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和李渔的戏曲批评理论,且因为是出于叙述的需要不得不提,所以常常是一笔带过。与上述学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郑振铎自始至终对于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怀有由衷的激情与热爱。
早在1938年,经过多年的积累钻研,郑振铎撰写的《中国俗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著作延续了五四新文学对于民间俗文学和贵族正统文学的基本认知,在高度肯定前者的基础上对后者予以严厉贬斥,并将两者对立起来。同时,在写法上也体现了鲜明的郑氏特色,主要以对中国古代民间俗文学重要资料作大规模分门别类的铺陈展示为主,学术性的分析和论断则相对较少。尽管如此,这部不以理论思辨见长的著作,它的历史贡献仍不容低估。它在文学史的著述中将小说、戏曲等文体与正统诗、文比肩而立,从而将前者纳入了高贵的文学殿堂。而且经过郑振铎的整理,大量散乱无序的宝贵资料形成了一个体系和框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面学者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战后,郑振铎依然延续了对于俗文学研究的热情。在为《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撰写的《题辞》中,他特别提到战后成立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会”,虽然寥寥数语,丝毫不吝赞美之词。“胜利以后俗文学的研究也有了一个组织——中国俗文学研究会——并且在报纸上刊印了两三种的‘俗文学’副刊,那努力是很可佩服的。”[3]而在3卷专号中,同样包括了大量不为人知的俗文学批评理论。比如小说批评理论类的阎德栋的《〈降魔变文〉与〈目连缘起〉》、汪浚的《吴承恩与西游记》等,戏曲批评理论类的严敦易的《元剧斟疑》和《续元剧斟疑》、董每戡的《说傀儡》、李效厂的《论〈妓女告状〉》等。不仅如此,在小说批评理论领域,专号中的文章也打破了单纯的以小说文本作为评论对象的模式,在评论内容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比如在专号里我们看到了考证有关材料真伪的季羡林的《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严敦易的《元剧斟疑》和《续元剧斟疑》、董每戡的《傀儡戏考原》等文章。上述学者对于各自研究领域内的文献资料的考辨是否符合事实,我们暂且不作评述,但是作为文学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文献资料的真伪考辨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种考辨也为进一步的考证提供了一种思路,因此是值得肯定的。总之,专号中大量俗文学批评理论的收录,既体现了郑振铎在战后依旧极力为俗文学张目的努力,客观上也为刚刚独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注入了新的内容,为其赢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
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学思潮的大量涌入,不少学者开始尝试援引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解读中国文学批评。如陈钟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就大胆采用了“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4]的方法。他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指正”、“赞美”、“判断”、“比较”、“分类”、“鉴赏”等五种理论为蓝本,据此将我国的文学批评细分为十二类。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初期,这种以西释中的做法对于开阔学者的理论视野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些学者大多只是在研究实践中偶尔为之,在比较的过程中通常也是点到即止。
作为国内较早采用中西比较法进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学者,郑振铎无疑在这条中西比较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不仅借用“为人生的艺术”、“为艺术的艺术”等西方文学批评话语来分别解释白居易和温庭筠、李商隐的文学主张。而且为了突出中西文学批评的异同,郑振铎还直接将两者进行比较。如他曾经对比中国与希腊、印度在文学批评发端时间上的早晚,指出中国文学批评自觉期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略晚的特点。“文艺批评在希腊很早便已有了,阿里士多德的《诗学》已是集大成的一部著作,在印度也很早便已有了,当古典时代的开端便已有了很周密的文学论。但在中国,则文艺批评的自觉,似乎发生得最晚。”[5]更重要的是,郑振铎将中西文学批评比较研究提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他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一文中,将“文学统一的观察”视为文学研究的第一种方法,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这种方法的重视。对于这种方法,他是这么定义的:“以文学为一个整体,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的对象,同时与地与人与种类一以贯之,而作彻底的全部的研究。”[6]简言之,这个方法就是强调将各民族文论置于世界民族文论之林中,互相比较,互相学习,打破民族文论的界限。郑振铎提出的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主张将中西文论进行比较研究。所以,郑振铎在《题辞》中特别提到的北京大学和几位学者在梵文研究上的成绩,“关于梵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血脉相同之处,新近的研究呈现了空前的辉煌。北京大学成立了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几位都是对梵文学有深刻的研究的。”[3]以及一些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业绩,和中国文学被介绍到外国去的情况,“于外国的学者们研究中国文学的业绩,我们也想着做些介绍和批评的工作。外国的学者们的研究,有时很粗率、浮夸,但也是有深湛而独到的意见,可以给我们做参考。又我国文学作品曾被介绍到世界文坛里去的很不少;对于世界文学也相当的发生了影响。”[3]实际上就是总结1930—194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实践“文学统一的观察”的方法所取得的成绩。
不仅如此,在专号编辑过程中,郑振铎也有意识地选入了季羡林的《中国文学在德国》和王统照的《清中叶中鲜文艺的交流》这两篇与中外文学比较和交流有关的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再现了作者希望在战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过程中延续这种“文学统一的观察”的方法的努力。平心而论,上述两篇文章在当时和对后世均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季文以较大篇幅回顾了从18世纪末叶至194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作品在德国的译介和流传情况。认为“事实上中国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也不太大。”[7]但是文末,作者的一席话颇值得回味:“……有些人发现,他们自己的文化里或者真正有什么缺点,不然为什么总是在苦难里辗转呢?他们于是又把眼光转向东方,想从那里获得点什么去补救自己的文化,我并不赞成这办法;但他们的心情我却非常能了解……。”[7]如果仅从字面上来理解,这段话似乎暗含中国文化也应该从异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意思。后者通过对清代诗人吴兰雪与朝鲜诗人金山泉一家的函札往复、唱酬投赠,来证明当时中朝文化交流的密切。但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两篇文章无论是立意或是论述,均无太多可圈可点之处。在具体的写作上,主要通过大量史实的堆砌来证明观点,并无先进的理论支撑和独到深入的分析。但是,在战后文艺复兴的系统工程中,作为其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郑振铎继续倡导中西比较研究,不仅开启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而且扩大了其研究视野,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文学批评由封闭性的解读向开放性的中西比较的转变,而这一点对于刚刚走出异族侵略阴影的中国文学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中国现代最好的文学编辑之一,同时又是一个颇具开拓性的文学研究家,上述两种身份在郑振铎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从1920年代开始,郑振铎先后通过创办《小说月报》、《文学》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延续了其对于文学研究的兴趣和一贯的文学关怀的同时,也和陈钟凡、朱东润、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等学者一道,共同参与并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抗战胜利后,郑振铎抓住各项文学事业百废待兴的时机,适时推出《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专号通过反思早期学者们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过程中的得与失,不仅有利于我们在正视过去发展过程中不足的同时使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同时也体现了主编者对本民族文论何去何从的另一种思索。专号搜集了众多一流学者在各自研究领域的厚重之作,不仅为当时的文学批评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早期中国文学批评的缺陷的修正和弥补。专号上大量俗文学批评理论的收录,既体现了郑振铎在战后依旧为俗文学张目的努力,客观上也为刚刚独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注入了新的内容,为其赢得了更为广大的发展空间。郑振铎在专号中将中西文学批评比较研究提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新思路与新视角,客观上也有利于其由封闭性向开放性的转变。因此,郑振铎对战后“文学批评”的贡献不容忽视。
[1]郑振铎.本会发起之经过[J].小说月报,1921,12(2):87.
[2]谛.编余[J].文艺复兴,1946,3(6):762.
[3]郑振铎.题辞[J].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1948-09-10:8-9.
[4]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1927:6.
[5]郑振铎.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67.
[6]郑振铎.郑振铎全集:第15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139.
[7]季羡林.中国文学在德国[J].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中),1948-12-20:147.
(责任编辑文格)
Zheng Zhenduo and Postwar Literary Criticism:Taking “Renaissance-Research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Case Study
YAN Liang
(1.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Hubei,China;2.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HubeiNormalUniversity,Huangshi435002,Hubei,China)
In postwar period in China, Zheng Zhenduo still continued to be enthusiastic about literary studies, timely launching the periodical “Renaissance-Research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eriodical introspected and reflected the gains and shortcomings occurred in constructing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y by scholars in early phase. In addition, it gathered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theories and the majo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mong the leading scholars at that time, and enhanced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to the height of methodology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thus ultimately making tremendous contribution to making it an independent subje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Zheng Zhenduo; “Renaissance”; periodical on literary researches;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y
2016-01-19
晏亮(1982-),女,湖北省罗田县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新诗研究。
2015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5Q187)
I206.6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6.03.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