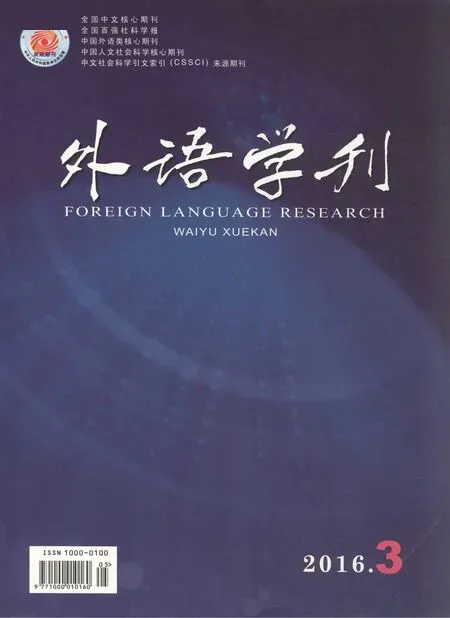“译”与“传”:辜鸿铭儒经翻译论
黄碧蓉
(上海海洋大学,上海 201306)
“译”与“传”:辜鸿铭儒经翻译论
黄碧蓉
(上海海洋大学,上海 201306)
辜鸿铭英译儒经文本是典籍翻译“走出去”的成功典范,是一种经典化儒经译本。但由于学界长期缠绵于翻译标准的“忠”、“信”之争,辜鸿铭开拓性的儒经翻译在得到极大肯定的同时也遭到部分学者的全盘否定。翻译传播本质的认识为我们研究翻译提供新视角,利用传播学理论能对辜译现象做出较好解释。因此,若能立足于翻译学自身的“译”理,吸收传播学之“传”艺,建构翻译传播理论体系,用于指导翻译实践,将会帮助翻译突破“译”的瓶颈,提高当前典籍翻译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引导译作的经典化,促进翻译学跃上新台阶。
辜鸿铭;儒经英译;典籍翻译;翻译本质;传播
儒家经典翻译是儒家思想域外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经典以更广阔的视域获得继续存在的基础。中国学者自觉向西方英译儒家经典的活动发端于100多年前,晚清名士辜鸿铭开启中国译者独立从事儒经英译的先河,打破此前一直以来由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垄断的局面。辜鸿铭英译儒经使中华文化的外传出现新局面,取得超越以往的成绩,揭开中国人自己向世界介绍祖国文化的新一页,意义非同寻常。可是,由于学界长期缠绵于翻译标准的“忠”、“信”,辜鸿铭开拓性的儒经翻译在得到极大肯定的同时也遭到部分学者的全盘否定。我们不禁要问,翻译到底是什么?怎样正确评价一部翻译作品,从而保证优秀的典籍翻译作品不至于因误判而明珠暗投?这项工作在中华文化亟需走出去的当下显得尤为紧迫,意义特别重要。
1 辜鸿铭译经之成就述要
从16世纪至今,《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不断被译为外文,然而众多的翻译文本中真正“走出去”的却屈指可数,大多淹没其中。辜鸿铭1898年推出的儒经华人“第一译本”——《论语》英译本和1906年推出的《中庸》英译本则产生巨大影响,轰动欧洲,“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泰西购者近百万部”,“销路极佳,罕有其匹”,竟一时洛阳纸贵。《中庸》英译本被收入英国《东方智慧丛书》,并重版4次,获瑞典皇家文学院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黄兴涛 1996:346)。辜鸿铭成为西方人眼中“中国最大的儒学权威”(Liu 1999:161),“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严光辉 1996:1)。译本还成为近代西方汉学家和学者有关中国儒家文化与东方文明著述的重要参考书和征引对象,如卫礼贤《孔子与儒教》(1928)和庄士敦《儒教与近代中国》(1934)。译本对近现代译经者也产生深远影响,传教士莱奥等的《中庸》英译本(1927)在阐释风格和阐释要点上都与辜鸿铭相似,这在译本前言中有正式说明;21世纪初美国浦安迪教授的《中庸》英译本,在对《中庸》的道德阐释方法以及核心术语译名选择上也仿效辜鸿铭的做法。
2 辜鸿铭译经之学界评论
学界对于辜鸿铭译经的评论,基本趋于两极:一是推崇达于极致,二是批评不遗余力(黄兴涛 2002:85)。
推崇者以林语堂为代表。20世纪50年代林语堂在美国得到辜氏《论语》英译本,甚为惊喜。1956年为辜鸿铭译本重印作序中,他不掩赞誉:“辜鸿铭先生向以英文译《中庸》,已为众所崇仰,而有《论语》译英文一书,业已绝版。我留意搜求数年,始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借得传抄,知其为精心结撰之作,不禁狂喜”。并评价说,“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总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异人之文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怪杰”(宋炳辉 1997:149)。此前,林语堂对辜氏《中庸》译文推崇备至,在其编译的两部中国古代经典书籍《孔子的智慧》和《中国和印度的智慧》(均被列入“世界名著文库”)中,完全采用辜氏《中庸》译文,这是他唯一采用他人的译文。林语堂说,“他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两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林语堂 1999:550)。他的儒经翻译“来自对两种文字的精通,以及对于它们较深奥意义的了解,是意义与表达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林语堂 1999:551)。
胡适早年的老师姚康候对辜氏的儒经翻译同样也是推崇有加。他评价辜译《论语》是“翻译的模范”(胡适 1933:141)。台湾学者瞿立恒认为,“近百年来,以中国六亿人口之众,国内治学与国外留学,士子之多,其能皓首译经,将中国学术要籍有系统译为英文者,唯辜鸿铭一人而已!吾不禁由衷赞叹曰:‘伟哉汤生先生!’”(瞿立恒1971:211-216)。
辜氏儒经译作受到王国维的几近全盘否定。辜氏《中庸》英译本1906年由上海英文《文汇报》社出版单行本。同年,王国维在上海《教育世界》发表“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痛陈辜氏《中庸》译本“大病”有二,“小误”若干。其之大病者,一是为求经义贯穿统一,用空虚、语意甚广的名词来阐释儒家基本概念,导致“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肤廓耳”;二是“用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解释过度,流于附会。“前病失之于减古书之意义,而后者失之于增古书之意义。吾人之译古书,如其量而止则可矣,或失之减,或失之增,虽为病不同,同一不忠于古人而已矣。”(王国维 1997:46-55)
后世学者一般从翻译策略、行文风格等方面给予辜氏译本全部或部分否定评价。全部否定的学者包括杨平、钟明国等,他们认为辜氏译本陷入误区,没有达到翻译目的。杨平指出辜氏译本在翻译策略方面的误区:(1)为了减除译文读者可能感到的陌生感,删掉或替换掉许多专名,因此丢弃中国特色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象;(2)借用西方宗教和哲学术语来翻译儒家词汇,抹杀儒学和中国文化的特征;(3)引用西方作家注释孔子思想,实际上中西方思想似是而实非,混淆不同见解(杨平 2008:158-159)。钟明国从辜氏语言策略和文化策略考察,发现辜氏译本采用完全贴近英语语言规范和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极端归化倾向,消解其翻译目的,失去完成文化使命的可能性(钟明国 2009:135-139)。部分否定的学者包括樊培绪、黄兴涛等,他们认为辜氏译本存在各种或大或小的缺陷。樊培绪说,辜氏译本“曲意迎合西方读者,不伦不类”,“任意添加”,“超过原文”,“好像在向读者讲解,而不是翻译”(樊培绪1999:50-52)。孔庆茂认为辜氏译本为求易解,失于冗长,丢掉原作风味(孔庆茂 1996:145-146)。黄兴涛指出,辜氏译本过于释意化,“一些重要概念的翻译不够直接和精确,有扩大概念意义范围和弄巧成拙之嫌”(黄兴涛 1995:90)。
总体来说,后世学者对辜氏英译本的批评基本没有超出王国维的“大病”和“小误”。
3 翻译本质之再思考
辜氏儒经译本空前成功,却遭学界的不同评价,特别是王国维的全盘否定,在很大程度上撬动人们对翻译本质的再思考。“辜氏翻译《论语》《中庸》的过程,与其说是在‘译’,不如说是在‘释’。他直接将儒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做出具有现代色彩的解释,而且这种‘释’甚至已经突破人们对解释性翻译的认识底线,让人发出‘这样还是翻译吗’的追问。”(王俊棋 2014:26-32)那么,什么是翻译,它具备什么本质特征?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话语),在保持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巴尔胡达罗夫 1985:1)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费道罗夫 1955:3)
“翻译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讯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奈达转引自沈苏儒 1998:131)
“翻译是转换承载信息的语言,把一种语言承载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通过两种语言的转换达到社会交际的目的。”(王德春 1997:321)
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翻译的本质是以译语表达原语意义的活动,即两种语言间的转换。但是,倘若止于此,对翻译的本质不做进一步探究的话,我们将无法走出传统的翻译标准论争,无法对辜译现象做出合理解释。因为学界对辜氏译作引发的争鸣,实际上是回归亘古绵延的翻译标准论争:我国古代佛经翻译时期的“文质”之辩,近现代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不顺”,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许渊冲的“三似、三化、三美”等。国外译界Tytler的翻译3原则、Nida的“功能对等”和“动态对等”理论、Newmark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等。这些翻译标准本质上都是以原作为中心来探讨译文与之形式和内容的对应,没有任何一方超出上述翻译本质的概念范畴。
因此,我们得回过头去仔细研究翻译定义。王德春的定义与其他3个定义的不同在于,不仅强调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还强调这种转换要达到社会交际目的。“交际”是其中的关键词。王德春从社会功能角度进一步阐发翻译的本质,把翻译视作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突出其交际的一面,这跟语篇翻译研究者的观点不谋而合:“翻译不仅仅转移原文意义,还要转移原文的交际价值”(Munday 2001)。从社会功能视角考察翻译,能突破以往仅仅从语言转换层面研究翻译的狭隘,突出翻译的“原作(作者)-译作(译者)-读者”的基本传递图式(张思洁 余斌 2007:130-133)。根据信息理论,交际的所有内容都可概称为信息,从原作到译文读者的联系纽带是信息,因此翻译本质上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这种本质特点的认识为翻译学研究提供新支点,自然联系和对接上传播学,为传播学向翻译学的渗透提供途径,也为翻译学研究借鉴传播学理论提供理论基础。于传播学视角下研究翻译理论,把翻译行为视作一个动态、开放的信息传递过程,而非两种语言机械的转换,搁置翻译标准“忠”、“信”与否之争,重视翻译过程中“传”的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将能得到新的发展,前述辜译现象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4 辜鸿铭译经之传播学审视
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首次提出传播过程的“5W”模式(Lasswell 1948)——传播过程由5个基本要素构成:谁(who)、说了什么(what)、向谁说(to whom)、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有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具体说,“谁”就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负责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递任务;“说什么”是传播内容;“渠道”是信息传递过程中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对谁”指传播受传者或受众,它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目的地;“效果”指信息到达受众后在其认知情感、行为各层面引起的反应,它是检验传播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郭建斌 吴飞 2005:116-125)。
从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可以看出,传播由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共同构建。传播受众是接受主体、反馈主体。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组成传播环流。没有传播主体就没有受众,没有受众,传播主体的存在毫无意义,最终也会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对受众进行研究,是考察传播效果、预测和评估传播的价值和意义的核心课题(赵水福 2000:25)。受众接受信息时都会有自己的定势和选择,在翻译传播过程中,作为传播主体的译者必须对译文的受众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考察他们与原作读者欣赏习惯的区别,了解“他者”的需求,根据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喜好等来决定翻译策略。
辜译的成功传播主要基于他对译作受众的了解。晚清时期,绝大部分西方普通读者对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缺少对源语文化的了解,难于接受充满太多异国情调和异质性的译文。(陆晓芳 2014:39)辜氏早年在西方游学,深谙欧洲思想意识、文化和读者的接受程度。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关照他们故有的文化背景、动机、情绪和态度等,对译文进行恰当引导和操控,减少译文给读者带来的误读,保证读者付出最小的努力而获得最佳的理解效果。至此,我们发现,王国维眼中辜译的“大病”、“小误”,恰是辜氏翻译策略的具体体现。
王国维对辜译的指责主要集中于两条“大病”:“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和“求统一”。先说前者——“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即以西释中,广引西方作家名言,中西概念对等置换。首先来看辜译的博采西言。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独具匠心为其添加副标题:“ASpecialTranslation,IllustratedwithQuotationsfromGoetheandOtherWriters”. 在《论语》译本序言中他特别强调,“书中引用了一些西方著名作家的话,包括歌德、卡莱尔、爱默生、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等,通过征集这些西方读者业已熟悉的名人思想,从而吸引西方读者,引起共鸣”(Ku 1898:1)。辜氏在翻译《中庸》时,也频繁引用《圣经》、歌德、莎士比亚、爱默生,以及卡莱尔、康德、托尔斯泰、弥尔顿等西方重要文化符号。以至于奈尔逊教授谈到辜鸿铭时说,“这个人他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个最好的基督徒”(黄兴涛 1995: 26)。其次,他使用文化概念类比法,把西方读者不易读懂的中文概念置换成对等西方概念。对于经文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以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地位和某些其它特点的人物进行类比。例如,将“舜、禹”译作The Isaac and Jacob of Chinese history,周武王译作the Moses or Solon of Chinese history,将孔子器重的两个弟子“颜回”、“子路”分别译作St. 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和St. Peter of the Confucian gospel等。对于经文中的儒家概念,以西人熟悉的概念进行类比。例如,将“天”译作God,孔子的“弟子”译作disciple,“教”译作religion,“圣人”译作holy men,“天命”译作the Commandments of God,“太庙”译作Great Cathedral. 对于时间概念的朝代,辜氏对“殷”朝和“夏”分别与the Greek history和the Roman history相联系进行比拟,告诉读者:“殷朝与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犹如希腊历史、罗马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
辜鸿铭通过广征博引西方名言哲理、大量类比使用西方文化符号,“一方面让西人在自己的符号体系中了解儒经思想的博大精深与经世价值,另一方面在不失儒经精要前提下不惜损失传统的精准翻译原则,主动逢迎西方民众,力求易于西人对东方文明形成可感知的认知”(姚刚 冯婕 2011:72-74)。这样的翻译让中西方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一次互动。本来在西方文化视角下如同天书一样不知所云的儒家经典经过辜鸿铭的翻译变得感同身受、亲切明晰。这种“归化”翻译/传播策略也得到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的认可和倡导,他在《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明确提出,译者应帮助目的语读者塑造作品意象,在翻译过程中可协调使用比拟与适度的异域化策略。这是由于读者在接受他文化作品过程中,很难靠自己的想象力接受异域主题或作者,最好的方式就是译者告诉读者这些实际上近似于读者文化中已有的意象(Lefevere 2004)。
第二条大病——“求统一”主要指责辜鸿铭翻译儒学核心概念上的求统一译法。对此,我们须要结合辜鸿铭儒经翻译的目的和对儒经的整体认识进行分析。辜鸿铭翻译儒经的首要目的是要让西方人认识“真正的”中国文明,改变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进而转变对华政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欧洲汉学的失望,他认为当时的汉学研究支离零碎,毫无整体观念。对儒经翻译集大成者理雅各博士的儒经翻译,他颇有微词:术语翻译生硬粗糙,不足达意,甚至还不地道;更糟糕的是,“无论注释还是绪论中,理雅各博士均无片语只言显示他对孔子学说有整体的、哲学的理解”(Ku 1898:116)
辜氏认为“道德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之于西方文明的优势所在。《论语》作为儒家文化中首部鸿篇巨制是为中国人提供“理智和道德的文化装备”,“半章《论语》可以振兴中国”(王静 周平 2010:124-127),而《中庸》则体现中国道德文化体系的精髓。他对《中庸》宣扬的“道德责任感”或“道”寄予厚望。因此,《中庸》是他重点翻译的一部作品,他说,“就我有限的知识来看,在所有欧洲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没有见过像在这本小书(指《中庸》)中所发现的那样简单明了到极点,同时有如此完整而丰富的关于道德责任感或道的阐说”(黄兴涛 1996:512),强调“只有通过理解全部文学——整个的人类精神史,或者把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领悟时,文学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黄兴涛 1996:513)。
为了让身处异域文化中的西方读者更容易读懂、接受《中庸》的道德内核,辜鸿铭在翻译《中庸》时特别注意显化它的有机整体性,以及它与前几部儒家经典译作的衔接,行文风格上也力求一致,以便给西方读者一种整体统一的认识。这种统一主要体现在一些儒学核心概念的翻译上。《中庸》的第一章至结尾的正文翻译中,均在核心术语前加上moral,并注意各译名自身的统一,以彰显中华道德文明之优势。例如,他将“道”译为the moral law,“仁”译为moral sense,“礼”译为moral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君子”译为moral man,“性”译为the law of our being,moral nature或our moral being,“中”译为our true self或moral being,“和”译为moral order,“中庸”译为the universal moral order等。通过添加并反复强调moral建构出《中庸》译本连贯的道德哲学主题,实现其向西方读者宣扬作为“普天之道德秩序”的“中庸”思想。相比较观之,理雅各博士在翻译《中庸》时,将“道”译作path,“仁”译作benevolence,“礼”译作propriety,“君子”译作the superior man,“性”译作nature,“中”译作the state of equilibrium,“和”译作the state of harmony,“中庸”译作the mean或the state of equilibrium and harmony,各核心术语间没有使用关键词串接,也不统一各译名。《中庸》的道德诉求散落于译文中,主要靠读者自己领悟,身处他文化中的读者难免因迷失而放弃,达不成其传播《中庸》道德文化的目的。
儒学概念于儒家思想实有提纲挈领、一以贯之的作用。译名统一而得体,则纲举目张,儒学的堂奥不难窥见。如随文释义,一词多译,听凭概念迷失于译文之中,则古书失却穿珠之线,弥显杂乱无章,读者也难以理清头绪。从传播学看,受众是交际传播的核心,是传播的最终对象和归宿,如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不为受众所理解和接受,那就失去其传播意义。
5 结束语
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信息的传递,这是翻译的两重本质属性。因而,翻译既要重“译”,也要重“传”。若单从语言转换层面一味追求原语与译语的形式对应,并以此评判译作的对错优劣,会不自觉纠缠于翻译标准的“忠”、“信”之争,而对优秀的翻译作品失于误判。“反观以往的翻译批评,我们恰恰是以实然判断的方式去检验形式是否对应的问题,甚至是把形式当成本体,使形式批评变成翻译批评的唯一内容。”(吕俊 2007:125-130)这对中华文化外传是有大碍的。翻译传播本质的认识给我们研究翻译及翻译批评提供新视角,利用传播学理论能对辜译现象做出较好解释。因此,若能在传播学理论指导下建构起翻译传播理论体系,科学有效指导翻译实践活动,将会帮助翻译突破“译”的瓶颈,提高当前典籍翻译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引导译作的经典化,促进翻译学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国内已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吕俊 1997:39-44),之后一些学者纷纷加入(廖七一 1997,岳启业2010等),为翻译传播理论体系的建构打下基础。但是,距离真正构建翻译传播理论体系尚有一定距离。特别是目前的翻译传播理论研究视翻译学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将翻译学置于传播学二级学科的位置,这有碍于翻译传播理论的独立及发展。立足于翻译学科自身的“译”理,吸收传播学相关理论的“传”艺,二者有机结合,方能建立起真正独立的翻译传播理论体系。
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樊培绪. 理雅各、辜鸿铭英译儒经的不及与过[J]. 中国科技翻译, 1999(3).
费道罗夫.翻译理论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 1955.
郭建斌 吴 飞. 中外传播学名著导读[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胡 适. 四十自述[M].上海:上海东亚图书馆, 1933.
黄兴涛. 文化怪杰辜鸿铭[M].北京:中华书局, 1995.
黄兴涛. 辜鸿铭文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6.
黄兴涛. 辜鸿铭——一个文化怪人的心灵世界[M].台北:知书房出版社, 2002.
孔庆茂. 辜鸿铭评传[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6.
廖七一. 翻译与信息理论[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7(3).
林语堂. 林语堂作品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陆晓芳. 晚清翻译的实学性[J]. 东岳论丛, 2014(12).
吕 俊. 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外国语, 1997(2).
吕 俊. 翻译批评的危机与翻译批评学的孕育[J].外语学刊, 2007(1).
瞿立恒. 辜鸿铭[A].中国文化综合研究[C].台北:华冈出版部, 1971.
沈苏儒. 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
宋炳辉. 辜鸿铭印象[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7.
王德春. 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王国维. 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A]. 王国维文集(第3卷)[C].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王 静 周 平.意识形态对辜鸿铭翻译的操控[J].外语学刊, 2010(2).
王俊棋.能动翻译的背后[J].华西语文学刊, 2014(1).
严光辉.辜鸿铭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6.
杨 平. 中西文化交流视域下的《论语》英译研究[D].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姚 刚 冯 婕. 文化传播视角下辜鸿铭英译儒经的翻译策略[J]. 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1(2).
岳启业.信息论翻译的多维度探索[J]. 外语学刊, 2010(4).
张思洁 余 斌.翻译的哲学过程论[J]. 外语学刊, 2007(3).
赵水福. 试论大众传播体系中的主体[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1).
钟明国. 辜鸿铭《论语》翻译的自我东方化倾向及其对翻译目的的消解[J]. 外国语文, 2009(2).
Ku, H.-M.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M].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td., 1898.
Lefevere, A.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Liu, L. The Desire for the Sovereign and the Logic of Reciprocity in the Family of Nation[J].Diacritics, 1999(4).
Munday, J.IntroducingTranslationStudies:TheoriesandApplications[M].London: Loutledge, 2001.
“Translating”and“Communicating”:KuHong-ming’sTranslationofConfucianClassics
Huang Bi-rong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Ku Hong-ming’s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re successful models for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s “going abroad”. However, due to Ku’s pioneer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his works have encountered a downright negative from some scholars, though they are warmly welcome by many others. The source for the divergence is around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criterion, whether the target text should be faithful to the source text or not. This has been a long-term argument among scholars. The communicative nature of the translation offers us a new approach to the translation study, and it enables us to resolve the divergence above on Ku. Hence, if we can integrate effectively both the theories in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o construct a communicative theory system on translation, and use it as a guideline for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we will help the translation study to get a breakthrough from its “translation” constraint,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ity and creativity of Classics translation, to facilitate the canonization of translation works, and finally to promote the translation study to step on a new stage.
Ku Hong-ming;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nature of the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H059
A
1000-0100(2016)03-0102-5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3.020
定稿日期:2015-10-21
【责任编辑孙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