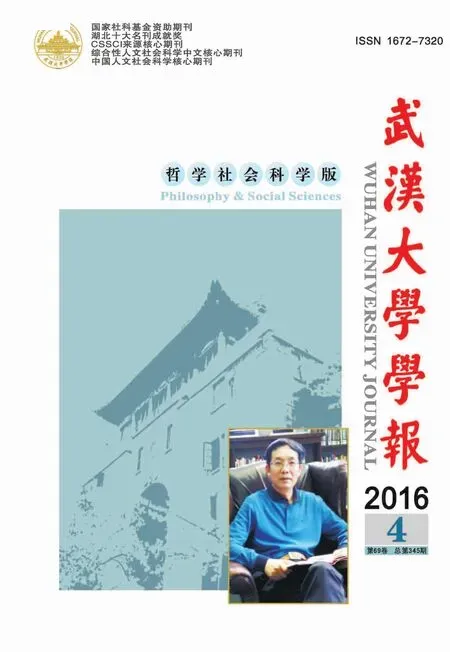滥用诉讼之侵权责任
张 红
滥用诉讼之侵权责任
张红
摘要:滥用诉讼是实务上的多发案件,对公正司法荼毒日甚,且囿于实体法律规制阙如,其已成理论与实务两界之难题。滥用诉讼之侵权责任证成难点主系于主观过错洞察与客观损害厘定。主观层面需至恶意之衔,从合法性与合理性两条主线予以结合考察。客观损害主系纯粹经济损失,根据现行《侵权责任法》关于一般侵权责任之规定,通过对“权益保护”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在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可以对滥诉行为课以侵权责任。对于有错误裁决之滥诉类型,亦不可违既判力制度之矩矱,应当结合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之相关规定,通过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或执行异议之诉先行撤销错误裁决之前提下,再另行提起侵权之诉。
关键词:滥用诉讼; 民事诉讼法; 侵权责任; 恶意诉讼; 纯粹经济损失; 既判力
“法院不能让自己被利用作为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工具。”(德沃金,1998:42)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进一步就净化司法环境达成共识。显然,规制虚假诉讼等不当诉讼行为已成国家顶层治理之重大关切,是司法体制改革力图剔除之劣性顽疾。近年来,对于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行为,立法上的正面回应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第13条第1款,第56条第3款及第112条*《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款所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也被视为包含禁止滥用诉讼权利的内涵。但原则的适应仍然依赖于具体制度的回应,《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第三人撤销制度的设立被视为是应对虚假诉讼而生之制度,但对第三人撤销制度应对虚假诉讼情势的适用,也有不少忧虑。第112条对虚假诉讼等有所规制,此系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后之新增条款,但该条对于当事人实施虚假诉讼等的法律责任的措施为驳回请求,拘留、罚款与追究刑事责任。。反观司法实践,有最高人民法院虚假诉讼第一案之称的“上海某公司、辽宁某公司与谢某借贷纠纷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中字324号民事判决书。亦昭示着司法机关对于识别虚假诉讼,大力惩治虚假诉讼之决心。
需说明的是,在我国,不论司法实务抑或学界贤达之探讨,都存有对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概念之争*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争议:(1)虚假诉讼是恶意诉讼的一种形式。(2)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是并列关系。此外,与“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相关的概念表述诸如“不当诉讼”,“诉讼欺诈”,“诉讼诈骗”,“滥用诉权”等。。虚假诉讼概念之定义在民事诉讼实践中难有统一,作为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学概念,是司法实务部门对相关案件类型的感触与总结(任重,2014:6)。综而观之,张卫平教授对二者概念之厘定可资借鉴*张卫平教授认为,虚假诉讼系“系形式上的诉讼双方当事人共谋通过虚构实际不存在的实体纠纷(包括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实体法律关系以及虽存在实体法律关系,但并不存在争议两种情形),意图借助法院诉讼的判决达到损害诉讼外第三人权利或权益的诉讼。”恶意诉讼则为“一方当事人通过捏造事实或理由,滥用诉权提起民事诉讼,以达到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恶意诉讼损害的是对方当事人的权利,只要受害方当事人正确行使抗辩权,恶意诉讼的违法行为便不能得逞。。笔者所意欲探讨之情势,涵盖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讼等行为,为顾概念之周延,故而统采“滥用诉讼”之概念,就文义而言,“滥用”一词,含“无节制、不加选择”之意,既含主观状态之倾贬,又达客观形态之抽象,二者兼顾,且于学理和比较法皆有迹可循,较为妥适。
在实体法方面,虽然关于滥用诉讼之侵权责任的学理探讨如火如荼,但从笔者选取的30个典型民事判决观之*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则:“赵俊诉项会敏、何雪琴民间借贷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12期(总第218期),第28~30页;“勋怡公司诉瑞申公司财产权属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3期,第30~36页。《人民法院案例选》4则:“广州东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广州市成均水电管道安装有限公司虚假诉讼案”,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1年第1辑),第206页;“吴荣平诉洪善祥民间借贷再审纠纷案”,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年第1辑),第157页;“上海迅通物流有限公司诉上海凌运庆铃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载《人民法院案例选》(2013年第4辑),第167页;“杨敏诉姚正祥不实诉讼损害赔偿纠纷案”,载《人民法院案例选》(1999年第4辑),第92页。《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则:“南京金盟房地产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诉江苏国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恶意诉讼保全侵权案”,载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1年民事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65页;“北京儒鼎时代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诉程爱华法律服务合同案”,载《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0年民事审判案例卷)2011年,第451页。《人民法院报》2则:“河南高院判决老黄记公司与黄家老店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6月6日,第6版;“李某某诉杨某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11月20日,第7版。北大法意数据库2012年至今的随机抽取的20则:参见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2014)鄂秭归民再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书;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4)杭西商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二终字第777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2013)绍越商再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衢民再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徐民再终字第0032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法院(2013)叙永民初字第2364号民事判决书;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黑监民再字第139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3)武民再字第00006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3)温乐商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3)温瑞商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法院(2013)宿中民再终字第0011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2012)芝民简初字第1036号民事判决书;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2012)宛龙七民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2)新民再初字第0011号民事判决书等等。,实务处理中俨然形成以《民事诉讼法》第112条为中心之程序法主导模式,课以侵权责任者仅有5例*“李某某诉杨某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11月20日,第7版;“甲公司诉乙公司滥用民事财产保全权侵权案”,参见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宜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杨敏诉姚正祥不实诉讼损害赔偿纠纷案”,选自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第92页;“陈某等与甲厂财产保全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徐某诉甲公司财产保全损害赔偿纠纷案”,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12869号民事判决书。。从实务案例采集状况观之(如表1):
显然,对于滥用诉讼之侵权责任的请求与成立,类型偏向性大,虚假诉讼竟无一例,裁判上持肯定态度者亦不为多,且依据各有所异;在虚假诉讼中,鲜有主观过错之考量;而在恶意诉讼中,何为“恶意”不甚明了,缺乏统一判定标准;至于损害方面,赔偿力度各不相同,亦无法定明确范围,填补损害之机理未得充分发挥。然,滥用诉讼肆起之根本原因,在于行为人心怀歹心之贪欲,程序法上进行打击和预防,确有助益,但始终无法实现损害填补的救济核心。因此,增进侵权法与程序法对滥诉行为之协力共制,方为解决之道。
当然,在此需加说明的是,该30例系笔者从众多案例群中筛选而得,并未将所选案例尽数堆砌,以顾代表性与充实性之协调。具言之,从案例时间来看,所选案例大多来源于近两年的司法实践,以求尽可能地把握新近司法审判动向;从案例代表性来看,公报、案例选、审判要览等代表性案例皆有采纳,其余则以类型化为导向,以同质异素为标准,主在说明当前集中于民事诉讼领域的典型性焦点问题,毕竟文题与各项部门法皆有涉猎,相关案例选库选确系浩如烟海,仅以拙文难以穷尽。因此,在后文将要展开的类型化论述中,各项类型之划分系分别以主观要素判定和客观要素考察为基准,以实务频发性问题为类聚,各项类型之集合固然无法涵盖一切滥诉行为模式,但每案皆与文题所述要旨息息相关,具体将予下文详述。
依通说,一般侵权行为之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之违法性、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张新宝,2010:29),滥用诉讼之侵权责任亦非例外。关于行为之违法性,《民事诉讼法》第13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第13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112条之首要法律依据可谓足格。至于“因果关系”,实务裁判与学界观点未有显著争议,遵循一般因果关系理论即可。而主观过错与客观损害之认定,则是侵权责任构成之难点,亦为下文所需考究之重点。不可忽略的是,在滥用诉讼之特殊语境中,侵权之诉之成立,非仅赖于构成要件之完璧,亦与民事程序配置制度休戚相关,故不得不理顺二者之关系,方谓圆满。
二、 滥用诉讼之主观判定
(一) 多次撤诉型
案例一:原告某法律服务公司因法律服务合同纠纷前后共计五次将被告程某诉至法院,又均撤回起诉,且未说明正当理由,一审和二审皆为败诉。后本案主审法官明确指出:原告三番五次在无充足理由的前提下对被告提起诉讼,有违诉讼之本质,据此可推断原告之起诉与撤诉行为存有一定的恶意。虽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对恶意诉讼的处罚措施,但本院裁定其败诉,以示惩戒*相关内容可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季版)·2010年第2辑(总第72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106~112页。。
案例二:杨某曾先后五次对李某提起诉讼,后三起均以杨某撤诉结案。在五起诉讼中,法院均依据杨某申请裁定冻结了李某银行存款或法院代管款。法院认为,被告杨某应知其证据为假,仍三次连续重复诉讼给李某造成无端诉讼负担,遂认定其起诉行为及申请保全行为均有“恶意”,并判决赔偿李某相关损失(徐俊、俞硒,2014:A07)。
由上可知,认定“恶意”之标准,因法条规定相对浅显模糊,法院判词并未集中于此。而是将恶意之论证立足于合理性的论述之上。案例一中法官以情理作为推理基础,面对原告多次无端起诉后撤诉之滥诉行为,囿于当时法制阙如未予严惩,遂裁定其相反行为。案例二中因被告杨某应知其证据为假,仍三次连续重复诉讼给李某造成无端诉讼负担,遂认定其有“恶意”,并判决赔偿相关损失。而在“甲公司诉乙铁路局滥用民事诉权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仅起诉一次,且原告声称被告滥用诉权证据不足,无法证明被告存有“恶意”。要言之,在该类型中,起诉次数、撤诉事由、前后诉衔接是否合理、证据是否真实等因素系法官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恶意”之核心要点。
(二) 恶意财产保全型
恶意财产保全亦属典型滥诉行为之一,其规制条款主系《民事诉讼法》第10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第105条:“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对于该条中申请财产保全行为是否“错误”之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2011]41号)明确指出,将“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和“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列于“侵权责任纠纷”项下,实务处理中均结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采过错责任原则处理。综据数案,其又可具分为“前提错误”、“对象错误”与“数额错误”三类,下文将各取典型予以详述。
案例三:原告甲公司起诉某铁路局,以“该铁路局与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而起诉,使其耗费人物财力甚巨”为由起诉某铁路局要求赔偿因其滥诉导致的损失。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该铁路局主观上并无过错,遂判决驳回原告诉请。二审则对“滥诉行为”下有定义,成为二审判决之关键*二审法院认为,滥用诉权的行为是指,当事人故意或相当于故意的重大过失,缺乏合理根据,违反诉讼目的而行使法律所赋予的诉权,纠缠法院或对方当事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财力浪费的行为。滥用诉权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应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参见左昆:《滥用民事诉权的司法界定》,载陕西法院网,http://sx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3667,2015年5月24日最后访问。。
案例三系“前提错误”类之典型代表。所谓“前提错误”,系指申请人之诉讼请求未获至法院之准许。在此需澄清一个误区,并非凡申请财产保全尔后败诉者即为错误,毕竟官司输赢系诉讼常事,其中因果千千万万,而保全制度仅系应急之策,只凭败诉后果便认定保全有误实乃荒谬。从案例三观之,某公司因无法适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责任规则使其财产保全行为丧失了适用前提,其主观恶意可谓昭然。另,在“陈某等与甲厂财产保全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民一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中,申请人之诉讼请求已遭高院两次驳回,且与之相关的民事判决已生法律效力,足可认定其财产保全行为缺乏合法理由,应认定为保全错误。概言之,法院对于“前提错误”之认定系以实然层面申请人之诉讼请求之正当性与可能性为考察基准。不得不提的是,财产保全制度之初衷,本为更好地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法院裁决顺利进行。倘法院发现申请人诚无诉之必要或极具恶诉倾向,此显与财产保全之制度目的相悖,其适当前提亦荡然无存。
案例四:被告甲公司在另案中因买卖合同纠纷申请保全原告徐某、胡某之房产。而法院于另案判决中明确认定徐某在代为清偿合同中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之所有收益已向甲公司清偿债务。甲公司对此应当明知,其对于申请保全的财产应尽审慎之注意义务,不应涉及原告之其他财产,故甲公司之行为具有主观过错*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12869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四系“对象错误”类之范例。在该案中,法官基于合同明确约定与法院判决确认之双重铁证,足以证明徐某之房产显非涉案财物,进而断定甲公司系明知不当为而为之,盖有恶意之嫌。查《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财产保全仅限于请求的范围或与本案有关的财物,此系法律层面对保全对象之规定。然,合法性验证仅系判定行为人主观状态之首要步骤,毕竟仅因保全对象有误尚难得证系申请人蓄意所为,疏忽大意亦有可能。透过案例四法官之论证逻辑,在全面事实认定与整合证据链条之基础上,行为人注意义务之缺失实有跃然纸上之感。依传统理论,注意义务可分为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的注意义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本案主审法官在后文评析中主张应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12869号民事判决书。,另有法官则主张普通人之注意义务即可*参见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衢民终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笔者认为,宜采普通人之注意义务。一方面,财产诉讼中保全手段之运用已属司空见惯,滥用之事亦时有发生,对申请人课以善良管理人将其视为己务之标准过于严苛,反易加剧保全制度之滥用;另一方面,普通人标准及于常人,易于把握;且要求程度愈低仍有违反者,足见其不负责任之歹心。要言之,于此情形下,法定要件之考察与注意义务之洞悉系法官进行主观认定之两大基点。
案例五:甲公司以恶意超额保全造成融资成本损失为由将乙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关于主观过错方面,法院认为:乙公司申请保全400余万元,根据生效判决,实际款项为267万元,此中数额差系当事人对工程款之确定方式存在分歧所致,乙公司对此并无恶意;且乙公司有权选择保全财产的种类,甲公司以不方便变现、不利于执行之房产作为担保请求解除其账户冻结,乙公司有权拒绝,不存在滥诉行为*“甲公司诉乙公司恶意诉讼保全侵权案”,参见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11年民事审判案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65页。。
“数额错误”类在实务中时有发生,其主观认定有其特殊性。除案例五外,在“A公司等诉B公司等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632号民事判决书。、“C公司与D公司因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上诉案”*参见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镇民终字第0034号民事判决书。中,法官皆指出,财产保全金额一般应与诉请金额或判决后金额相当,然保全制度仅系诉讼之中间程序,非属权利义务之终局确认,况且其中不少在紧急情势下为之,数额偏差实乃常理,仅依此点难断过错。因此,对于《民事诉讼法》第102条中“限于请求的范围”应采扩张解释。亦即申请人之申请保全金额与诉请金额在合理误差范围即可,苛以精准实无必要亦无可能。约言之,在该种小类型下,实务通行做法为:若无其他事实依据予以辅证或足以认定申请人存有恶意之嫌,仅依保全金额与诉请金额之数额差尚不足以苛之过错。
综上,“前提错误”与“对象错误”系实务中法官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滥用财产保全之多发地带,“数额错误”虽时见争议,却常属情理之中,法官尚难凭此独断。在三种小类型化中,个案法官皆秉承合法性与合理性双重考察原则,尤其在现有事实证据之基础上对主观状态之条分缕析,实现与法律层面上过错要件之对接,可谓精到。
(三) 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型
该类型系《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制之主要类型,因其多采伪造证据、虚构债务之手段行事,实务亦多谓“虚假诉讼”。下文将结合典型案例,具而述之。
案例六:上海某公司为原审原告,辽宁某公司为原审被告,谢某为再审一审申诉人,原审中第三人。原一审中,法院查明原告与被告共签订九份《借款合同》,原告在合同签订后如约将款项付给了被告后,被告公司在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内,均未予以偿还。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借款实际发生之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一审裁判生效后,第三人谢某提出申诉,认为原告与被告无真实借贷关系,原告与被告恶意串通,通过虚构债务的方式,恶意侵害其合法权益。其后,案件再审。再审中,辽宁高院结合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借款过程及诉讼中发生的情形,以及原告公司借款进账后将大部分款项转出的情形,认定原被告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法律关系。原审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此案争议焦点之一,系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真实借款关系。
申言之,对于本案中诸多矛盾和违反常理之处,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均未作出合理解释,原审原告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明其就案涉争议款项与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而对本案是否存在恶意诉讼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原告与被告对原审被告与申诉人及其他第三人债权债务应系明知,而在当庭询问时,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之债务偿还状况表述不清,表明其提起本诉之目的并非系实现债权,而是通过司法程序进行保护性查封以阻止其他债权人对特莱维公司财产之受偿。以虚构债权而兴讼不止,恶意昭然若揭。综上,最高人民法院据以《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的虚假诉讼行为予以认定并进行处罚*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中字324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七:原告孔某与被告郑某系母子,郑某与陈某系夫妻,原告以郑某、陈某购置婚房向其借贷为由起诉两被告,一审判决已生效。被告陈某遂提起再审。后再审法院查明,本案中两被告的婚姻关系、司法送达程序以及所提交的证据皆存在不同程度的可疑性。综上,再审认为原审原告孔某之诉求、证据以及郑某之答辩意见前后不合逻辑,有虚假诉讼之嫌,遂撤销原判,驳回原审原告之诉讼请求*参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3)杭西商初字第268号民事判决书;杭州市西湖区(2014)杭西商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
不可忽略的是,诸如以上通过伪造欠条、虚构法律关系等手段来参与他案执行分配、规避债务等滥诉行为已经成为司法实务中的老大难问题*除开上述三例外,下列裁决文书可予佐证: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2013)温乐商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3)东二法民四初字第48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3)武民再字第00006号民事判决书;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2013)黑监民再字第139号民事判决书;海口海事人民法院(2013)琼海法商初字第133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2013)邳民再初字第0011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崇民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等等。。实务处理中几乎皆系通过《民事诉讼法》第112条将其诉讼请求予以驳回。在主观要件考察方面,行为人之间“恶意串通”系《民事诉讼法》第112条得以适用之前提。而对虚假诉讼下恶意之洞悉,并未以明示主观状态为标准。以案例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某公司、辽宁某公司与谢某借贷纠纷案”为例,对于虚假诉讼的识别,法官从当事人“其自述及提交的证据和其他在案证据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矛盾,在诉讼前后的诸多行为违背常理”等七个方面予以综合性判定*本案再审中,最高人民法院从7个方面的矛盾进行考察:(1)从借款合意形成过程来看,借款合同存在虚假的可能;第二,从借款的时间上看,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前后矛盾。第三,从借款的数额上看,当事人的主张前后矛盾;第四,从资金往来情况看,欧宝公司存在单向统计账户流出资金而不统计流入资金的问题;第五,从所有关联公司之间的转款情况看,存在双方或者多方账户循环转款问题;第六,从借款的用途看,与合同约定相悖;第七,从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诉讼和执行中的行为来看,与日常经验相悖;参见最高人民法(2015)民二终字324号民事判决书。。
进而言之,法官对“真实义务”之考查可见一斑。参酌比较立法,1933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必须在诉讼中履行真实义务。此处的“真实”,是指行为人主观状态的真实,当事人若是违反该义务,极有可能导致法官对其作出不利评价(肖建华,2012:4)。正如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所言:“诚实信用原则已经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在其他领域里也被采用为指导原理等事实存有重大意义。”(谷口安平,2002:147)反观我国最近的民事诉讼法之修法趋势,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明列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第13条第1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91条第(一)项、第92条第3款新增条款出台,充分反映出当前背景下立法者对诉讼程序中的“真实义务”日趋重视,任何诉讼行为亦不可违背诚实信用的基本法则。约言之,常理性之诊断依据随之法制健全进步逐步转化为法律规定要件,证据法之渐精愈详使滥诉行为之违法性更加突出。一旦行为人如此斑斑劣迹被法官所确认,那么其主观恶意自属不证自明之事。
(四) “恶意”之概念界定与判定路径
由上观之,在三大类型化中,几乎任一案件中的滥诉行为人皆存“恶意”之嫌。自罗马法以来,“恶意”与“善意”相伴而生,究采何意,纵览比较立法,暂无范例*大陆法上,德国民法有多处涉及“恶意”这一概念,从德国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来看(如第826条关于故意违反善良风俗),未使用“恶意”这一概念而系“故意”。《奥地利民法典》第1295条第2款规定:“一个人以违反公共道德的方式恶意侵害他人,应当为此承担责任。”英美法中,恶意有两层含义:(1)明知自己的行为违法,或会对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但是由于法律或他人合法权利的漠视,仍实施该行为的心理状态;(2)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无合法或正当理由故意违法,或者法律在特定情况下推定行为人具有恶意的心理状态。。相对于“故意”,“恶意”这一概念因其高度流动性而被称之为不确定概念,其可在不同领域以不同称谓出现。有学者将各领域的“恶意”分为如下三类:第一,“明知”;即“知”某种影响决定行为人所希望发生的法效果是否能发生的情状;第二,涉及行为人动机、目的等主观心理状态,类型上比较复杂;第三,“恶意”被用来作为将道德接入法律的口径,如有关公序良俗的规定(于飞,2012:4)。
甚值辨析的是,“重大过失”得否纳入其中?在我国,主观过错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基于过失程度考量,又可具分为重大过失、抽象过失、具体过失*学者分类的依据为违反的注意义务的程度上的差异,具体以言,第一,最低限度的注意义务为普通的注意,违反此种注意义务是为重大过失;第二,以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义务为中,不能尽此种义务的,是为具体过失;第三,最高层次的注意义务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其未尽注意义务的过失则为抽象过失。。在英美侵权法上,对于重大过失与过失之间是否具有同一关系尚无定论,并渐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之分歧*客观说认为轻率与一般过失一样,均为客观过错,只不过对注意义务违反的程度更加严重;主观说认为轻率是一种主观过错,与一般过失的客观属性有别。。国内亦有学者认为,重大过失非属“过失”一类,理由在于重大过失与故意同属于主观过错,不同于采取客观化判断方法之一般过失;况且,据其定义,行为人对一项极有可能发生之损害后果已有预见,但此又非其所欲,应系介于故意与普通过失中间之独立过错形态(叶名怡,2009:6)。申言之,法律和道德对这一过错形态显异于一般过失,后者仅可表明侵权行为未能符合法律规定之行为标准,对评判行为人之心理因素难谓充分。基于此,重大过失更接近于故意。此外,不论是罗马法上“重大过失等于故意”(Gross Negligence Equated with Intention to Harm)之法谚,还是近现代国家将重大过失与故意连用,并在法律条款中表述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之通行做法,皆倾向于将重大过失从“过失”中萃取出来,将其视为与“故意”极其相近之单独过错类型。职是之故,有学者认为在特定情形下,重大过失亦可构成恶意(汪泽,1996:1)。
笔者认为,“恶意”不能包括重大过失。重大过失与故意之同源性不能成为混淆二者的理由。依重大过失之义,唯行为人确信损害后果很可能发生,但终非其所愿。依常理,一般情形下,任一诉讼及其中间程序之提起皆系任一行为人自主积极地提起(不可能存在过失起诉之行为),若不幸造成另一方受有损失,当否赔偿,尚难定论。而“恶意”所含之意,应系对“故意”之加重修饰,应释为“致人损害之故意”。只有在此限定下,方可将滥诉行为与正常诉讼行为区分开来,针对性地对滥诉行为课以侵权责任。职是之故,滥诉行为之主观条件,谓之“故意”尚难谓足格,遑论“重大过失”之适用余地。
再者,损害填补与行为自由系现代侵权法之核心任务。倘将重大过失纳入其中,行为自由将大大受限。换言之,诉讼本为化解民事纠纷、保障实体权益之公共制度,凡普通大众皆可用之,若滥诉行为之主观要件门槛放低,一般人本为讨回公道而来,却或招致得咎之祸,诚非所盼;长此以往,易使欲诉之人畏首畏脚,在行使诉权时瞻前顾后,错过最佳追诉时机。
基于前文对实务案例之类型化论述,特别是徐俊、俞硒法官之审判经验总结*徐俊,俞硒二位法官认为,“恶意”之判定可从如下方面进行考量:(1)是否存在伪造证据、恶意串通、歪曲法律、诱使证人作伪证等情节;(2)利用生活经验法则、逻辑推断、地方风俗等“思维工具”;(3)对同类型行为多发区域加强关注,包括程序性请求,如起诉、保全申请、延期申请、程序异议等环节,以及实体性问题,如证据属性、基础法律关系真实性等方面;(4)法庭调查与庭外调查相结合;(5)不能仅凭相关案件判决的胜败结果作为认定依据。,“恶意”之判定,实系主客观相结合考察之经验性活动。从判定原理来看,《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款中诚实信用原则系法官自由裁量之根基,在不同案件中又分别具化为注意义务、真实义务之考察。进而言之,滥诉行为之主观认定系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之程序法、证据法日趋完善,法律漏洞日益缩小,滥诉行为发生之可能性愈小,认定其主观恶性亦愈加全面准确。
三、 滥用诉讼之损害厘定
(一) 损害之类型化与纯粹经济损失
“无损害则无救济”,“损害”之认定系侵权行为法之核心(冯·巴尔,2001:53)。奥地利民法典第1293条规定,“损害是给某人财产、权利或人身造成的不利益”(U·马格努斯,2009:59)。据笔者所查,依受损客体之不同,滥用诉讼之损害类型化有四:
其一,侵害一般财产权型;常发生于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以物权纠纷为多,如在“祝某甲、江某某、祝某乙、祝某丙与被上诉人祝某丁恢复原状纠纷案”*参见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衢民再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中,上诉人一行借恶意诉讼侵害祝某丁之相邻关系等。
其二,侵害知识产权型;为了获得荣誉称号、广告资源、物质奖励,政策优惠等目的,企图通过制造虚假诉讼,快速达到认定驰名商标之目的。“甲公司与乙公司、丙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案”是为例证*参加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云高民三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
其三,侵害人格权型;侵权人通常利用社会对于“耻讼”、“厌讼”之念,以损害相对人名誉为目的,提起恶意诉讼,一般情形多见于名誉权之损害*“法学教师为何状告校长”,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法院网站,http://www.gzhsfy.gov.cn/shownews.php?id=1566,2015年5月20日最后访问。。
其四,纯粹经济损失型;主要包含两大方面:一方面,依正常诉讼程序可得之财产利益。以上文中“侵害第三人利益型”为典型,如案例七中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方式抽离在另案夫妻离婚诉讼中的夫妻共有财产。另一方面,被侵权人因被迫参与滥用诉讼所直接产生之相关诉讼费用。显然,在滥用诉讼之语境下,诉讼本身已遭利用,故该损失可谓普遍存在,如在“甲公司诉乙公司滥用民事财产保全权侵权案”*参见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宜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中律师费赔偿、“杨某诉姚某不实诉讼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交通费、误工费赔偿等。
依据现行法律规范,第一、第二种类型之受损客体皆明确规定于《侵权责任法》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之“列举式”权利群中,法律适用实无争议,暂不予详述;至于第三种类型,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2条之规定,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必须满足“侵害他人人身权益之严重后果”之前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处理即可,亦非本文重点。而纯粹经济损失方系滥用诉讼最易招致、且最为普遍之损害后果,得否赔偿,关乎若干受损人之财产流失得否弥补。
(二) 纯粹经济损失之请求权基础
纯粹经济损失(Pure Economic Loss,reins Vermögensschaden)是比较法上热门话题,其系司法实践为确立损害赔偿之界限而构造的理论工具(张新宝、张小义,2007:4)。《瑞典赔偿法》第2条尝试对纯粹经济损失作出了定义,该定义是:“依据本法的纯粹金钱上的损失是一种在任何方面都与对人身伤害或财产伤害没有关联的损失”(冯·巴尔,2001:49)。
不论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损害之内容均涉及纯粹经济上之损失,于滥用法律诉讼之情势中得否受保护?这也是此种情形下侵权责任构成之关键。比较法上,关于纯粹经济损失是否应予保护,规定不一*《法国民法》第1382条规定,因过错侵害他人的,应负损害赔偿责任,未对保护法益进行区分,纯粹经济损失在实务中主要通过因果关系进行限制,法国判例认为纯粹经济损失与侵权行为需具有直接性的因果关系,始得请求赔偿。与之相对应的德国采“权益区分保护”的保护模式,《德国民法》第823条、第826条通过“权利侵害型”、“违反保护性法律”及“故意违背善良风俗”三个小概括条款对权利和利益进行区分保护。而纯粹经济损失仅限于“违反保护性法律”或“故意违背善良风俗”致损时,始得请求赔偿。。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第2款虽含多项列举式规定,以“等人身、财产权益”所兜底,纯粹经济损失是否然包含于“等财产权益”的范围之内,是否得以保护,采何种保护模式,国内学者莫衷一是*张新宝教授认为,可类采英美法上之“水闸”理论,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或是公布指导性案例之权威形式,来掌握闸之开放大小。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理解与适用》,《法律适用》2012年第10期,第28~32页。王利明教授则认为该条主在保护绝对权,纯粹经济损失若得获致赔偿,一需限于法律明确规定,二则借以相当因果关系予以把控。参见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第62、75、76页。葛云松教授在其文中将关于纯粹经济损失之零散法律规定与实务典型案例予以系统翔实之类型化总结,并进一步通过目的性限缩解释,主张将“民事权益”分解为德国民法中三个小概括条款,以供利益之筛选与救济。参见葛云松:《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条款》,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第689~786页。。概言之,建立相对合理的利益遴选和排除机制已成学界共识,只是方案各有出入。实务上,尽管法院对于纯粹经济损失之概念较为陌生,但我国已有法院也据此概念进行侵权责任构成之审视,影响颇为广泛的判例诸如“重庆电缆案”*参见“黔江区永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与黔江区民族医院、黔江区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此外,我国实务中,在判决中明确提及纯粹经济损失概念的有如下判例:(1)“宋正辉诉华帆公司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12)沙法民初字第06218号民事判决书;(2)“洪德记诉厦门洪氏企业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海民初字第2544号民事判决书;(3)“向勤与刘大顺等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衡中法民一终字第288号民事判决书;(4)“上海蓝奇电讯设备有限公司诉上海杨浦赛博数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侵害企业经营权纠纷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06)杨民二(商)初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书;(5)“张小峰与贾永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城关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天民一终字第104号民事判决书。在此几则判例中,多数以侵权一般条款加以规范。。葛云松教授曾对我国实务态度有所总结,认为我国法院的基本立场在于纯粹经济损失属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之保护范围,因过错导致纯粹经济损失时应予赔偿一般适用侵权一般条款,而有特别法规定时,通常援引特别法规定,其他情形下是否侵权需要满足严格的构成要件,但对于要件缺乏全面的探讨(葛云松,2009:5)。
特别立法中对纯粹经济损失有所回应,回归到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情势之下纯粹经济损失的保护,立法上没有予以明确回应,正如所有纯粹经济损失的裁判难题,依据法释[2008]14号第39条第2款之规定*法释[2008]14号第39条第2款:“申请再审人或者申请抗诉的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致使再审改判,被申请人等当事人因申请再审人或者申请抗诉的当事人的过错未能在原审程序中及时举证,请求补偿其增加的差旅、误工等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请求赔偿其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解决。”,因提起再审方之过错造成另一方差旅、误工等诉讼费用应予赔偿;由此扩大至直接损失具有可诉性。此系针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规定。我国实务中,也有对故意导致纯粹经济损失之侵权赔偿,对于虚假诉讼、恶意诉讼下的纯粹经济损失,采保护之态度是应有之义。
四、 侵权之诉的提起与诉讼制度的配置
我们将滥用诉讼侵权责任简单表述为以下:(1)以故意致人损害为目的,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而提起民事诉讼致使对方在诉讼中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当事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致使第三人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滥用诉讼侵权之诉如何提起,与具体的民事诉讼制度如第三人撤销之诉、再审制度、执行异议等如何配置密切相关,此亦实现侵权救济的重要问题。滥用诉讼常见情形为骗取生效法律文书,利用生效法律文书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然,错误的生效法律文书对当事人,以及对案外第三人的利益影响为何,这是侵权之诉之提起所需解决之前提。简言之,即错误判决之效力于当事人及第三人之影响。
关于判决之效力,从程序法原理而言,从判决成立之时起,便对具有特定效力,随着时间或程序的推移,判决一旦确定,还会发生其他效力包括既判力(张卫平,2015:1)。一般而言,既判力的作用有积极与消极作用之分,消极作用是指禁止双方当事人再就具有既判力的判断内容进行争执;积极作用表现为要求后诉法院在审判时应以有既判力的判断内容为前提(李龙,1999:4)。具体到滥用诉讼致人损害之情势,最为关键在于对既判力主观范围的理解,确定判决并非对任何人皆有既判力,原则上既判力只作用于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对于案外第三人不产生约束效力(肖建华,2002:1)。侵权之诉的提起,不能一概而论,应当依据不同情形探讨:第一,恶意诉讼情形下,未涉及第三人利益,侵权之诉的提起应当如何进行?第二,虚假诉讼情形下,涉及第三人利益,前诉与案外第三人的相互关系何如,如何提起侵权之诉?
(一) 恶意诉讼下侵权之诉的提起
恶意诉讼为一方当事人通过捏造事实或理由,滥用诉权提起民事诉讼,以达到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恶意诉讼致相对方(被告)损害,相对方(被告)提起侵权之诉怎样进行也视情况而定:(1)诉讼过程中,法院识破恶意诉讼,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此种情形下,法院判决主文一般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其后,若前诉中的被告提起侵权之诉,不受既判力约束,不论是从既判力的积极作用,抑或是消极作用均不受影响。因为此系全新诉讼,从既判力的消极作用来看,尚未构成重复诉讼,从诉的要素角度,诉讼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皆与前诉不同,法院应当受理*法释〔2015〕5号第247条第1款规定了重复起诉的标准:“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从既判力的积极作用考量,法院也不受前诉约束。(2)法院未识破恶意诉讼,据此出具错误生效法律文书。在此情形下,以如下案例为例,A捏造对于B实际所有的名画的事实,对B提起恶意诉讼,致使法院错误将B的名画判决给A,并且法院判决已经生效。此种情形下,法院未查明A为恶意,法院关于名画所有权属于A的判断已经产生形式上的拘束效力,此后如果B提起因A恶意诉讼导致所有权被侵害之侵权之诉,当事人与法院皆会受到前诉约束,因为关于A与B之间名画所有权的争议,法院已作裁判,尽管B可以提起新的诉讼,因为前诉A与B为关于画的确权之诉,而B提起的是关于A滥用诉讼侵害所有权之给付之诉,但由于法院对画的所有权所属关系已经确认,后诉不得作出相左裁判,画的权属受生效判决作用。因此,在我国,通常情形下,B只能先申请再审,通过再审更改确权,尔后提起因滥用法律诉讼侵害财产权之诉,实现民事权利救济。案情如下图所示:
(二) 虚假诉讼下侵权之诉的提起
生效裁判原则上只对当事人之间产生拘束力,案外第三人仍可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即便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前诉存在出入,亦不构成前后裁判之冲突,此亦民事裁判既判力客观范围和主观范围的基本要求(段文波,2012:5)。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法律允许和承认判决的既判力突破相对性原则限制,对案外第三人发生作用*我国学理界对既判力扩张范围总结为以下类型:诉讼的承继人、诉讼担当的利益归属人、诉讼请求标的物的占有人,退出诉讼的人,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之判决效力及于未参加诉讼之人等。。然而,仅就我国现状而言,我国仅有既判力理论,而无既判力制度,对于既判力的相对性不予考量,大陆法系国家常常允许当事人提出前诉判决作为证据,从而使既判力相对性原则逐步弱化。例如我国关于免证事实的规定,依法释〔2015〕5号第93条第5款之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效力的裁判文书所确认的事实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既判力相对性原则,不利于第三人利益之保护。对案外第三人而言,最优厚之程序保障方式,乃为贯彻判决效力相对性之原则(胡军辉、廖永安,2007:5)。简言之,从民事程序一般理论与现有的第三人撤销制度出发,虚假诉讼并不会损害案外第三人的民事程序权利造成损害。
解决侵权之诉的提起,必须回应的是虚假诉讼下,前诉中骗取的生效裁判是否会直接损害案外第三人的民事权益?其次,若第三人民事权益因此受有影响,该如何在现有的民事程序配置下,提起侵权之诉?
1.虚假诉讼之生效裁判与第三人利益之关系
虚假诉讼能否侵害案外第三人民事实体权益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应当从民事生效裁判的作用方式来思考,依据民事生效裁判的“诉讼法说”,前诉当事人通过虚假诉讼获得的错误裁判并不会发生实体法律关系的后果*对于民事生效裁判的作用方式有“实体法说”与“程序法说”,根据实体法说,民事生效裁判具有直接变动或间接变动实体法律关系的效果,根据诉讼法说,民事生效裁判只是对实体法律关系的确认,原则上并不具有变动实体法律关系的效果。。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民事生效裁判的作用方式,依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及第112款规定,错误的生效裁判似乎与民事权益受损的结果直接相连。但有学者总结认为,结合我国《物权法》第28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8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们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们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并非所有的判决都产生直接变动物权的效力,能够导致物权变动的法院判决仅指形成判决,不包括给付判决和确认判决(程啸,2013:1)。因而,由此推导而得,虚假诉讼骗取生效裁判损害案外第三人民事实体权益的可能存在于一下两种类别:一类系当事人协商未果,法院对共有财产分配所作出的形成判决;另一类是在认可合同被撤销情况下存在物权变动时,法院作出撤销合同的形成判决(任重,2014:1)。
2.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执行异议之诉与侵权之诉提起
(1)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及执行异议之诉适用关系。
在侵权之诉与三者如何配置的问题解答之前,三者内部如何自洽,亦属不可回避之难题。第三人撤销之诉设立后,关于上述三者适用关系,学理上争议不断,法释[2015]5号对此下有定论。首先,关于第三人撤销制度与再审程序的衔接,依法释[2015]5号第301条规定*法释[2015]5号第301条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审理期间,人民法院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裁定再审的,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将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并入再审程序。但有证据证明原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先行审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裁定中止再审诉讼。”,案外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审理期间,法院对生效裁判裁定再审的,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院应当裁定将第三人诉讼请求并入再审。易言之,一般情形下,当第三人撤销之诉和再审并存时,优先适用再审程序,将第三人请求并入再审程序。深言之,第三人撤销之诉虽与再审制度虽在适用前提上有相似之处,但再审制度启动更为严格,其解决范围亦比第三人撤销之诉更为宽泛,第三人撤销之诉毋宁系一项中间性的特殊程序,其虽与再审相类,但并不可取代再审之效能(郑金玉,2015:6)。例外在于,虚假诉讼情形下,优先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止再审诉讼。而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执行异议的衔接,依法释[2015]5号第303条规定*法释[2015]5号第303条规定:“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后,未中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执行的,执行法院对第三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的执行异议,应予审查。第三人不服驳回执行异议裁定,申请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案外人对人民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申请再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二者只能择一进行。
(2)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执行异议之诉与侵权之诉提起。
在理清上述三者内部自洽性后,最后一关在于,侵权之诉是单独另行提起,还是与三者诉讼结合合并提起,若采后者,关键在于是否有合并提起的法律依据。
关于再审与侵权之诉的关系,比较法上各有所异。德国曾有判例认为,通过诈骗法院或当事人而取得的判决根本不发生既判力,被侵权人无须提起再审,可径直通过《德国民法典》第826条“背俗故意致损”条款提出侵权之诉(奥特马,2003:339)。后德国联邦法院予以修正,认为既判力本质为诉讼法确定的效果,不能简单认定为无效,损害赔偿之诉在数项情形下相当于发挥了再审制度的功能(蔡章麟,1984:14)。日本亦有判例与此类似,日本最高法院判例认为,诈骗取得的法院判决具有既判力,但被侵权人仍可避开再审制度,直接提起侵权之诉(高桥宏志,2003:585-586)。在我国,第三人申请再审的,应当另行提起侵权之诉。依法释[2015]5号第40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法院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再审的范围仅限于原审的请求,一般案外人对于因虚假诉讼而申请再审,有侵权损害赔偿的诉求属于新的诉讼请求,应另行起诉。其次,第三人申请执行异议之诉,是针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请求,因滥用诉讼侵权属于新的诉讼请求,也应当另行起诉。最后,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与侵权之诉的配置,第三人撤销之诉仿似一个局部的再审,其审查仅限于对案外人不利的部分(吴泽勇,2014:3)。从实务反映观之,大多数法院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仅判决撤销错误裁决,对于撤销后具体的权利义务部分,几乎有赖于当事人另行提起诉讼(王亚新,2014:6)。综而言之,第三人撤销之诉在于救济利益受侵害第三人的程序权利,仅解决错误裁判、调解中的错误部分,对于新的诉讼请求也应当依据再审制度的思路,另行提起。侵权之诉的提起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再审程序及执行异议流程如图2。
五、 小结
法为公器,法治应择其善者而用之,然滥用诉讼系钻营法律漏洞而图不义之利,有碍法之正义实现,理应规制。鉴于现行法及实务多依靠《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第207条为核心来规制滥诉行为,效果甚微。笔者另辟蹊径,参酌中外学说法例,基于我国实务见解,尝试通过对滥用诉讼课以侵权责任,以促程序法与实体法之协力共制。
第一,滥诉行为之主观状态需为恶意,即“致人损害之故意”程度,方可契合其侵权责任之评价标准。实务处理中,合法性与合理性系认定恶意之两大基点。以法定要件为前提,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根基,辅以注意义务、真实义务之考究,透过行为之异常性、虚假性来推断主观状态系实务处理的通行之法。
第二,基于目的性限缩解释,《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6条第1款、法释[2008]14号第39条第2款、法释[2015]5号第315条系滥诉行为侵权责任之请求权基础。具体赔偿范围应当包括因滥诉行为所损失之直接财产利益和被侵权人被迫参与滥诉过程所直接产生的诉讼费用。
第三,为促既判力与权益保护之协调、顾实体法与程序法之效能,保障诉讼阶段各项制度之融通自洽,实务处理步骤应作如下细分:在滥诉行为于法庭即遭识别时,法官可径直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2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此时错误裁决尚未形成,侵权之诉自可另提无碍。倘错误裁判业已形成,在恶意诉讼情形下,被侵权人需先通过再审申请将错误裁判予以撤销,其后再提起侵权之诉。在虚假诉讼情形下,受害第三人亦需基于法释[2015]5号第301条、303条、405条之指引,借助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或执行异议之诉撤销前诉错误裁决,再另行提起侵权之诉。
参考文献:
[1]冯·巴尔(2001).欧洲共同侵权法(下册).焦美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蔡章麟(1984).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上).台北: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3]程啸(2013).因法律文书导致的物权变动.法学,1.
[4]德沃金(1998).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5]段文波(2012).民事程序视角下的同案不同判.当代法学,5.
[6]葛云松(2009).纯粹经济损失的赔偿与一般侵权行为条款.中外法学,5.
[7]高桥宏志(2003).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8]谷口安平(2002).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9]胡军辉、廖永安(2007).论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政治与法律,5.
[10] 李浩(2014).虚假诉讼与调解书的检察监督.法学家,6.
[11] 李龙(1999).论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法律科学,4.
[12] 任重(2014).论虚假诉讼:兼评我国第三人撤销诉讼实践.中国法学,6.
[13] 任重(2014).形成判决的效力——兼论物权法第28条.政法论坛,1.
[14] U·马格努斯(2009).侵权法的统一——损害与损害赔偿.谢鸿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15] 汪泽(1996).民法上的善意、恶意及其运用.河北法学,1.
[16] 王福华(2014).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逻辑.环球法律评论,4.
[17] 王亚新(2014).第三人撤销之诉原告适格的再考察,法学研究,6.
[18] 吴泽勇(2014).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适格.法学研究,3.
[19] 肖建华(2002).论判决效力主观范围的扩张.比较法研究,1.
[20] 肖建华(2012).论恶意诉讼及其法律规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4.
[21] 徐俊、俞硒(2014).恶意诉讼之“恶意”的判断标准及损害赔偿范围认定.人民法院报,2014-11-20.
[22] 于飞(2012).违背善良风俗故意致人损害与纯粹经济损失保护.法学研究,4.
[23] 杨立新(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北京:法律出版社.
[24] 奥特马·尧厄尼希(2003).民事诉讼法(第27版).周翠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5] 叶名怡(2009).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法学研究,6.
[26] 张卫平(2012).第三人撤销判决制度的分析与评估.比较法研究,5.
[27] 张卫平(2013).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构成与适用.中外法学,1.
[28] 张卫平(2015).既判力相对性原则:根据、例外与制度化.法学研究,1.
[29] 张新宝(2010).侵权责任法(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0] 郑金玉(2015).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践运行研究.中国法学,6.
■作者地址:张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Email:18600014012@163.com。
Tort Liability of Action Abuse
ZhangHong(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Action abuse occurs frequently in practice. This causes heavy damage to justice, and has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ecause of lacking substantive law. The main difficulty of tort liability hinges on inspecting the subjective fault and objective damage. Subjective level requires malignity, which is combined with two main lines of legality and rationality. Main objective damages is pure economic loss. By adopting a teleological limited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protection of interests and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xisting “Tort Liability Act” and drawing on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it is possible to impose the tort on action abuse. In terms of wrongful judgments in action abuse, it is supposed to obey res judicata. A separate appeal for tort action should be lodged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n Civil Procedure Law Judicial Explanation, on the premise that wrongful judgments are revoked with retrial, third party discharging the judgment or execution disagreement.
Key words:action abuse; civil procedural law; tort liability; malign action; pure economic loss; res judicata
DOI:10.14086/j.cnki.wujss.2016.04.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4ZDC027)
■责任编辑: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