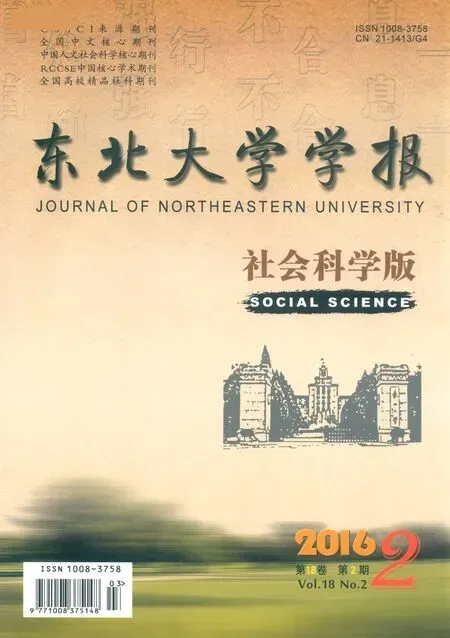论防治土地荒漠化国际环境立法的伦理基础
刘 继 勇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 北京 100088)
论防治土地荒漠化国际环境立法的伦理基础
刘 继 勇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 北京 100088)
在一系列环境危机中,土地荒漠化已经被明确地认定为最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土地荒漠化问题的实质是人的问题,防治土地荒漠化的国际环境立法作为规范人类对土地行为的一种途径,具有显著的公益性,其目的不仅在于保护人类的基本生活环境,更在于维护和改善全球的自然生态环境。为此,必须检讨人类内在的环境思维和伦理观,尊重自然的生存权,最终实现人类整体的长远的生存利益。这既构成了立法的伦理基础,更是立法的价值及其完善的根源所在。
土地荒漠化; 土地价值; 土地伦理; 国际环境法
土地荒漠化的防治并非一个新议题,应该说人类社会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然而,21世纪的今天荒漠化现象仍在不断加剧,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深刻反省。回顾历史,国际社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讨论防治土地荒漠化的问题,1977年《阻止荒漠化行动计划》的制定标志着防治荒漠化国际立法的开始。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防治荒漠化被列为国际社会优先行动的领域之一,其中《21世纪议程》为防治荒漠化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技术基础,这是防治荒漠化国际行动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1994年《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公约》(以下简称《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签署,标志着解决土地荒漠化问题的全球性环境条约的出现,这是关于解决荒漠化问题首部真正的、正式的法律文件。
可见,从行动计划到行动指南再到正式法律,应该说人类对防治荒漠化的认识和觉悟是逐渐提高的,但面对荒漠化这一顽疾,目前的一切努力仍显力不从心。究其原因发现,计划也好、指南也罢大多仍停留在文字上,即便是作为真正法律工具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其条款也多以鼓励性为主,且尚存诸多不足和模糊之处,难免流于形式。挖其根源,不能不说,人类对土地价值的认知、土地伦理的理解、人与土地的关系等问题之领悟还是远远不够的。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终极意义上对防治土地荒漠化国际环境立法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思考和研究,旨在以新的范式为该领域国际环境法的建立与健全尽绵薄之力。
一、 土地伦理的提出
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发表了被誉为“开创伦理学新纪元”的《自然保护伦理》一文。他提出,应把伦理学研究对象扩大到大地系统(自然界),主张不仅生命的自然,而且包括生态系、自然景观、土地和岩石等无生命的自然都有其“固有的价值”与“权利”。这种“自然的生存权”揭示了“环境”的伦理基础[1]41,而人类尊重她,实际上就是尊重自身的存在,关注自身存在的利益、幸福和命运。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立足于自然生态思维,承认生态系统、环境或大地的权利,开创了以“大地”的健康和完善为尺度的整体论的伦理思维方式,是对环境伦理学的划时代贡献。
伦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是对生存竞争中行动自由的限制;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则是对社会和反社会行为的鉴别[2]192。正如利奥波德所言:哲学家们所研究的伦理关系的扩展,实际上是一个生态演变的过程。从最初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再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观念的这种进化源自于人类对自身的再定位及对生态价值的深层理解。土地荒漠化是最为典型且严重的环境问题,该问题的解决追根溯源要有赖于个人的生态学头脑。相比较政府的管理而言,使个人负有伦理上的责任,将更适合解决这种巨大的、复杂的甚至是分散的环境灾难。所以说,一种土地伦理反映着一种生态学意识的存在,而这一点反过来又反映了一种对土地健康负有个人责任的确认[2]209。可见,在土地资源的保护上,人类的伦理意识举足轻重。荒漠化的防治需要科学,更需要对土地的人文关怀。人类只有认识到生态规律的真理性和不可抗拒性,才能发现生态平衡对人类生存利益的价值性,进而作出保护自然的道德选择。人与非人类存在物的一个真正具有意义的区别是,动物和植物只关心(维护)自己的生命、后代及其同类(在自然界存在一些为维护下一代的生存而牺牲自己的动物,如北美阿拉斯加的鼠与狐),而人却能以更宽广的胸怀关注(维护)所有的生命和非人类存在物。不仅认可他人的权利,还认可他物——动物、植物、物种、生态系统、大地——的权益[3]48。人的这种能力应该得到实现,当然这有赖于那些源远流长的文化态度的改变。必须承认,当人类能以反映人与自然的正确的伦理关系来指导其道德生活时,人类将会获得更大的自由。
二、 土地荒漠化问题的实质
土地荒漠化已经被明确地认定为严重的环境问题[1]313。荒漠化是指由于受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在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所产生的土地退化。它意味着有生产能力的土地的消失,进而制造出成百上千的“环境难民”;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造成沙尘暴肆虐;天然水域缩小使得水资源锐减……,直接威胁着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基础。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估计,全球目前有约1/4的土地受到荒漠化威胁,超过2.05亿人遭受着荒漠化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耕地和牧场变得贫瘠,使得100多个国家的超过10亿人的生计问题处于危险境地。
土地荒漠化是人类面临的最为典型且严重的环境灾难。追溯该问题的产生,有自然因素亦有人为因素,比较千百年来缓慢形成的自然荒漠化,今日的荒漠化的特征是人为加害力远大于自然加害力[4]。也就是说,如今最大的威胁不是源于自然界的敌对力量,而是源于人类自身对自然界极其扭曲的认识,即坚守自然永恒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一度引发了人类对土地资源的任性行为:肆意挥霍、为所欲为。更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定胜天”的豪言依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就在我们身边依然存有“让高山低头,让河水改道”的“欲望”和“壮举”。不可否认,对于荒漠化而言,人类对土地的漠视、不屑及巧取豪夺无疑是雪上加霜,无情地加剧了这一过程。人类由此而付出的代价更是惨痛的,它对粮食及食品安全、生物多样性、地球生物群和生物生产力,以及全球的气候变化都是一种重大的威胁。总之,土地荒漠化是遭受磨难的土地反馈给人类的一颗苦涩之果,它的出现与蔓延要求人类反躬自省。一面在为荒漠化的防治绞尽脑汁,一面仍以发展为名向大地发动讨伐,如此矛盾之举再次暴露了人类的肤浅与狭隘,揭示了环境教育的欠缺与公众意识的淡薄。诚然,人类已认识到:规则与法治是约束行为的有效方式,但依然存在的利己私念致使立法每每陷于私己泥淖而裹足难行。可见,防治土地荒漠化国际环境立法的前提必须要准确定位人的观念和意识,因为环境破坏源于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又取决于人对环境的态度,环境问题必须要通过人心的变革得以化解。
因此,笔者认为:荒漠化问题不单是土地本身的问题,更多的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如果人的生态意识不确立,再多的资金投入,再先进的技术设备也于事无补,甚至会造成更大的生态破坏。这种生态意识,其实质就是要求人类应当对土地(地球)负有责任,即确立土地伦理观。它要求人们承认土地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不只是被利用的客体,人与土地是一个统一的联系着的内在的生态系统。人应当爱护土地,认识和尊重土地在环境变迁中表现出的自然规律。唯有认识到人应当对土地负有某种责任,并由这种责任出发,才会从根本上引导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三、 防治荒漠化国际环境立法的目的和性质
土地荒漠化的防治行动开启于20世纪70年代的非洲,一直以来,国际社会为防治荒漠化进一步扩大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但事实上,全球荒漠化现象依然严峻,这十足令人担忧,不能不让人屏息反思,问题都出在哪里?笔者认为,防治荒漠化必须冲破仅靠技术手段的末端治理模式,要深刻反省人类对土地的伦理观和价值观,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因此,防治土地荒漠化国际环境立法必须植根于人类的内在修为,必须明确法律规范的立足点不是维护私利,而是要提倡公益。进言之,公益不仅要关注全人类,更要放眼于全球生态。只有理性地认识到立法的目的和性质,才能制定出以全人类的利益和追求为指向的良善之法,才能使人们深谙其所担负义务的真正意义,作为天下之公器的法律才会因人类意识的内在援助而顺利实施。
必须看到,土地荒漠化已成为人们生活和生存的严重灾难并导致贫困和阻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5]。《春秋繁露·观德》指出,“天、地、人,三才一体”,“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也就是说,有天、地而后有万物(包括人在内),人的繁衍离不开自然的哺育。而今全球约1/4的陆地处于荒漠化状态,又何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解决土地荒漠化的问题上,需要把人的正当行为概念延伸到土地,调整、规范人类对土地的不当态度和失范行为。既不能脱离土地资源、生物群落来追求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也要顾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说到底,燃眉的危机要求我们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以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而这套行为规则的出发点必须着眼于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防治土地荒漠化的国际环境立法作为规范人类对土地行为的一种途径,不仅在于保护人类的基本生活环境,更在于维护和改善全球的自然生态环境,最终建立一个人类可持续生存的国际社会。土地荒漠化的问题虽开启于以非洲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但其立法规制必须以“环境无国界”为理念实现国际社会的统一行动,换言之,必须立足于全球层面关注防治土地荒漠化的国际环境法律规范的建立与健全。土地恶化是危及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保护土地资源是为了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和共同福利,通过国际合作制定的法律规章,其显著的公益性就不言而喻了。
《防治荒漠化公约》作为目前国际社会为解决该问题而制定的正式的、真正的法律文件,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终归势单力薄,且自身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模糊不清。实际上在其制定实施20多年来,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土地荒漠化仍在不断发展、扩大。可见,公约尚未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和效力,其完善与健全势在必行。为此,我们不仅要认清防治荒漠化国际环境立法的目的和性质,更要追根溯源,检讨人类内在的环境思维和伦理观,尊重自然的生存权,进而实现人类整体的长远的生存利益。也就是说,土地荒漠化问题的深层折射是土地价值观念的危机、环境伦理文化的危机、生态文明理念的危机,只有消解这些危机或困境,立法才有根基,才有意义。
四、 土地伦理对防治荒漠化国际环境立法的要求
伦理,即事物的条理,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法是一个工具,属于主观范畴。如果说土地伦理表明了为何要保护土地,那么防治土地荒漠化国际环境立法的作用便是要解决如何保护土地。进言之,要想推动立法(主观)的发展,须使其符合伦理(客观)的要求,唯有这样才能构筑良善之法。因此,为使防治荒漠化国际环境立法与土地伦理相契合,笔者认为,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其一,要全面认知土地的价值。与空气、阳光、水一样,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之一,而且,不唯独人类,土地也是自然界中其他生物(包括动植物、土壤生物等)生存和发展的载体,是它们在地球上生长繁衍的条件。近年来随着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关注,土地在生物圈的作用也愈发凸显。同时需要明确,土地不是仅指土壤,而是一条由土壤-植物-动物-人所组成的相互依赖且复杂的线路。土地是所有生物的生命线,她演绎了人类文明。然而“文明人跨越过地球表面却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这说明“人类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虽然已经发展了多种技能,但是却没有学会保护土壤这个食物的主要源泉”[6]。人口膨胀导致土地压力过大;毁坏森林使地表层流失;过度放牧使土地荒漠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人类缺乏对土地价值的认知和对土地特性的了解。2015年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关于落实《防治荒漠化公约》面临的主要挑战,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莫妮克·巴尔比认为,相比技术、资金、人力等方面的问题,缺乏对土地的了解是当前的一大挑战。利奥波德也曾言:“我不能想象,在没有对土地的热爱、尊敬和赞美,以及高度认识它的价值的情况下,能有一种对土地的伦理关系。”[2]212可见,全面认知土地价值,不仅是土地伦理观形成的前提,亦是推进荒漠化防治立法进程的源动力。
其二,土地伦理决定了防治荒漠化国际环境立法的责任导向。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土地上生长的动植物是相互影响的共同体。作为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人类需要去竞争,这是本能的表现。同时,更需要尊重与合作,这便是伦理的要求,即土地伦理就是要改变人类在共同体中征服者的面目,使其成为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这就是说,人类对土地不仅具有使用上的权利,更要对土地负有伦理上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为了全体人类的公共利益,而不是某种私人利益;这种责任的实质在于公正合理地重新分配不同人类群体在土地利用中的利益,既要符合代内公平,还要符合代际公平;这种责任在效果上应当是最有利于土地和环境整体发展的,不得给土地和环境造成长远的伤害,这实际上要求人必须将自己与土地看做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不能为了人的某种好处而以损害土地为代价。总之,只有土地的利益得到了保护,人的长远利益才能真正得以持续。《防治荒漠化公约》已然体现了责任论的立法导向。公约在总则部分明确规定了缔约国各自应承担的义务,这符合土地伦理要求人承担对土地的责任的内在要求,确立了立法的根本价值取向。当然,对于土地荒漠化的责任的承担,不是不加区别的。对于荒漠化,一方面,对于那些因采取错误政策(如滥伐森林、耗竭水资源等)促成荒漠化的发展中国家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即便是未受直接影响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同样为此负有责任。实际上,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除了受土地荒漠化的间接影响外(如生态难民的非法迁移),同样也遭受着荒漠化的直接影响,以欧洲为例,每10年其土地退化的面积就相当于一个塞浦路斯岛。也就是说,所有国家在环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均应承担责任,这与出现荒漠化的土地是否属于本国管辖范围内无关。从国际环境法的角度看,发达国家要对土地荒漠化承担更多更重的责任。唯有如此,才算是落实了土地伦理责任对于公正的要求。
其三,土地伦理要求荒漠化防治国际环境立法采纳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模式。伦理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因此,要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以代内、代际公平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推动人类发展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变。唯有如此,荒漠化防治的国际环境立法才会因人类生态伦理观的确立而得以稳固与完善。正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所言,若认为自然除具有为人类服务的工具性价值外没有价值,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价值观,必然使得人类对于自然采取贪得无厌、疯狂掠夺的态度。根据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土地是一个共同体,不仅包括被人类利用的工具价值、自身的内在价值,还包括生态系统本身的价值,人类必须从整个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完美出发,采取符合生态规律的行动。对于土地而言,其质量是可变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脆弱的、不可再生的,为了保证土地生产力的持续不断,人类必须要尊重和保护土地,其实践行为不能违背土地的自然规律。换言之,土地伦理要求必须从人与土地的有机联系中处理如何对待土地的问题,那这客观上必然要求人不但要考虑自己的需求,还要考虑所有有利于土地保育的因素。这导致立法鼓励的治理手段必须是综合性的,这种综合性手段兼顾了所有与土地有关的主体的利益和诉求,并将其与土地自身的利益结合起来,不断地通过互动和调适,最终实现整体环境公益的和谐,这种和谐既能够实现土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能够实现不同主体利益的均衡,因而为立法所采纳。
五、 结 论
人与土地在本质上是共存共荣的关系,土地荒漠化问题关键是人的问题。因此,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对人类自身进行约束,其中包括作为自律规范的伦理与作为他律规范的法律两大手段。二者看似两种力量,但却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即伦理是法律的根基和前提,法律则是伦理的载体和升华。由此,防治土地荒漠化的国际环境立法必须着眼于环境伦理在法律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功用,明确并维护国际环境法的公益性,进而保证法律作为一种行为导向能够得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为此,人类要在高度认识土地价值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生态伦理观,将道德关怀付诸于土地,依靠道德的力量,对人类的思想观念进行内在自律。当然,作为一种文化态度的改变,生态伦理观在全民意识中的形成自然不会一蹴而就,因而需要发挥环境教育的作用以促进环境理念的育养。一旦土地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概念真正被深刻地融汇在我们的理智中时,人类的行为便有了生态伦理的内在要求。
从法律角度而言,国际环境法是属于为全人类共同利益而制定的规则[1]45。它对环境的保护是通过法律规则而不是道德规范来实现的。然而,环境伦理的价值认知为环境立法提供了内在支持和道德基础,对法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必须认识到,“决定人类存亡的不是外在的极限,而是内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者脆弱的物质极限,而是人和社会的内在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的极限”[7]。由此,荒漠化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对土地环境意识的危机,必须要把人类从自我中心主义、物质主义意识中解放出来。全面认识土地的价值并树立土地生态伦理观,这是化解土地荒漠化问题的一把金钥匙,更是完善土地荒漠化国际环境法规制的根源和基础。为此,笔者认为,防治土地荒漠化的国际环境立法要以生态伦理观为依托,尊重自然的生存权,约束人类的行为保护土地资源,最终实现人类整体的长远的生存利益。这不仅构成了立法的伦理基础,更是立法的价值及其完善的根源所在。
[1] 林灿铃. 国际环境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2] 奥尔多·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M]. 侯文蕙,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3] 裴广川,林灿铃,陆显禄. 环境伦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4] 林灿铃. 国际环境法理论与实践[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5] 林灿铃. 荆斋论法——全球法治之我见[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1.
[6] 弗·卡特,汤姆·戴尔. 表土与人类文明[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87.
[7] 欧文·拉兹洛. 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异端反思[M]. 黄觉,闵家胤,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王 薇)
Ethical Ba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on Land Desertific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IUJi-y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Land desertification has been clearly identified as the most serious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 amongst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crises. The essence of the problem is a human issue, and as a means to regulating human behaviors towards l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of land desertification has significant public benefits. The purpose is not only to protect the basic living environment of human beings, but also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 global natur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ultimately realize the mankind’s long-term survival benefits, we must review our inherent environmental thinking and ethical views and be fully aware of the nature’s right to survival. This not only constitutes the ethical basis of 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but also explains its value and the source for its perfection.
land desertification; land value; land ethic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10.15936/j.cnki.10083758.2016.02.012
2015-10-23
刘继勇(1975- ),女,辽宁阜新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环境法研究。
D 99
A
1008-3758(2016)02-018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