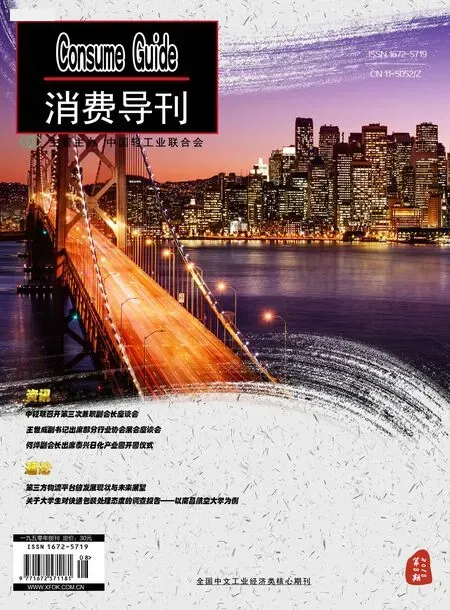论一般人格权
——对德国民法的拿来主义
苏宁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论一般人格权
——对德国民法的拿来主义
苏宁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技术是我国法制建设伊始对西方法律制度进行移植的过程的宗义。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法典式国家,其大陆法系国家的标杆式法典——《德国民法典》,为我国法律制度的移植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素材。这种法律移植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称为“拿来主义”。本文就是以一般人格权为例来看对德国民法典的拿来主义。
一般人格权 德国民法 拿来主义
一般人格权是针对具体人格权来说的,指以人的人格尊严、人格平等、人身自由为内容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权力集合性特点的权利。它是一条概括性的条款,具有具体人格权的目的和指导价值。
一、一般人格权概念的拿来主义
我国《民法通则》中并无对于一般人格权的相关规定,只是在《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具体人格权的权利的保护范围做出了规定,一共列举了18项权利: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和继承权。但是,近来人格权利发已经成为讨论的热点,尤其是一般人格权理论。一般人格权是德国民法的一个概念,一般人格权在德国民法中并不是一项成文法律制度,而是由学说和司法实践共同发展起来的一项判例法。学者对德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持肯定态度,认为一般人格权是人之存在的价值和尊严的权利,是对人格权的概括性规定,概括了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和人格平等为一般内容的人格权益,是一种兜底性条款。
(一)战前的一般人格权状况
实际上,在19世纪20年代德国的立法者是从根本上否定一般人格权这一概念的运用的。“做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这是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核心。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即秉承这一理念。虽然民法典中有姓名权(第12条)等具体人格权的规定,但立法者却出于法律安全性的考虑拒绝在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中制定一条普遍适用的侵权法上的一般性条款,以保护“神人格”。其理由有三:第一,不可能承认一项“对自身的原始权利”,否则会得出一项“自杀权”的结论;第二,债的产生以财产价值受到侵害为前提;第三,人格权的内容和范围无法予以充分明确的确定。[1]
(二)二战后的一般人格权状况
由于纳粹专政时期滥用国家权利,侵害个人人身自由、随意践踏人身权利。引起了个人对人格权利的自觉保护和社会对个人人格权力的重视。因此,二战后德国基本法开宗明义对一般人格权作出了保护性的规定。而德国法院对一般人格权的发展正是基于德国基本法而来的。
《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故意或过失而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财产所有权或者其它权利的人,有义务向他人赔偿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在这一款的规定中将侵权行为固定在具体的客观方面上,为公民全力保护提供了依据。随着司法判例的发展,一般人格权已经成为了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其他权利”。[2]
二、一般人格权性质归属的拿来主义
一般人格权是一种框架性的权利,在它受到保护的范围内究竟承载了什么样的内容,有着什么样的边界都是值得探讨的。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这种所谓的“框架是权利”应当作为一种权利还是权益进行保护呢?权利是民法的中的中心概念,民法以权力为本位。依据通说的观点,民事权利本质上是法律为保障民事主体的特定利益而提供法律之力的保护,是法律之力和特定利益的结合,是类型化的利益;权利的功能在与保障个人的自由范围,使得其自主决定、组织或形成其社会生活,尤其是实践司法的自治原则。权利是主观的化的法律,法律则为客观化的权利。[3]
在我国一般人格权是作为一种权力进行保护的而不是一种利益进行维护。之所以这样划分是考虑到对权利与权益的保护力度的差别:对于权利侵害一般司法解释中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对于利益的侵害只有在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道德时才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的考虑的基础也是源自《德国民法典》对相关问题的规定。在德国是严格区分权利和利益的,如果权利遇到侵害采用一般的侵权构成要件,对于利益的侵害则采用更加严格的责任构成要件,一般通过采用违反善良风俗或者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这样一些限制来进行更加严格的规范。
《德国民法典》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其他国家进行法律移植的范本。在一般人格权的概念的使用和对一般人格权权利性质的定位上,我国对德国民法的“拿来主义”可见一斑。
[1]霍尔斯特·埃曼:《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邵建东等译),载《民商法论丛》总第23卷,第413页
[2]冉克平 《一般人格权理论的反思与我国人格权立法》《法学》2009年第8期
[3]王泽鉴,《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85页
苏宁,女,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
——评《其精甚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