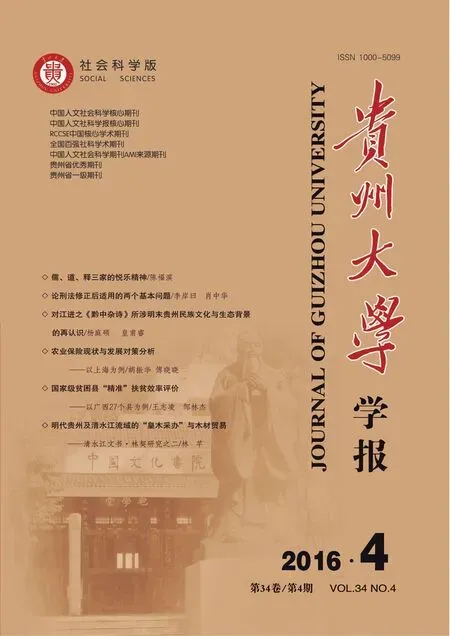论戈迪默《新生》中的三重伦理关系
胡忠青 蔡圣勤
(1.长江大学 工程技术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论戈迪默《新生》中的三重伦理关系
胡忠青1蔡圣勤2
(1.长江大学 工程技术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最后作品《新生》没有沿袭她以往作品的反种族隔离主题,而是讲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在后种族隔离时代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故事。该故事向我们展现了当下南非人的生活,尤其是白人家庭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本文以文学伦理学为批评视角,分析《新生》在特殊的伦理环境中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相互联系而又相互依存的三重伦理关系。
戈迪默;《新生》;伦理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我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4.027
2014年7月13日,南非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与世长辞,享年91岁。她的离世让读者们惋惜不已。戈迪默生前著作颇丰,仅长篇小说就有14部,另外还有许多短篇集和文论集。她的虚构作品多聚焦于反映南非的社会现实,体现出了一个作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被曼德拉赞誉为“南非的良心”。
她人生中最后的一部作品是出版于2005年的《新生》。这部作品并没有沿袭她以往作品的反种族隔离主题,而是聚焦于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生活变迁。男主人公保罗因为罹患甲状腺癌症做了手术,术后的治疗使得他的身体成为了一个放射源。为了儿子的顺利康复和其家人的安全,保罗的父母阿德里安和琳赛将他接回自己家照顾。最终,保罗顺利康复,和妻子的关系也得以修复。他们的小儿子也顺利降生。琳赛因为年轻时的一次婚外恋一直对丈夫心怀愧疚并努力弥补。儿子病愈后夫妻二人出国旅行。阿德里安却在旅行中爱上了自己的导游,并最终客死他乡。小说没有宏大的历史背景,也没有荡气回肠的情节发展,作者平静地描述了一个白人家庭的情感变化过程。简单平实的故事却让我们窥见了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人民的生活,尤其是白人种族的伦理困境。本文以文学伦理学为批评视角,分析在特殊的伦理环境中故事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三重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
一、《新生》中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
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作为人之存在的本源性关系始终是各种伦理关系的核心内容,因此,“从道德意义上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当代伦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1]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人类终于实现了和自然的分离,随之而来的是人类自然属性的丧失。自此,人类开始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探索。人究竟是应该害怕自然,利用自然还是和自然和谐相处?在南非,这样一个急需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自然很尖锐:一方面,南非有良好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利用;另一方面,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南非经济的发展并不能满足普通民众想要改善生活的愿望。但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被利用和自然环境的被破坏。这个时候,探索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新生》讲述的家庭故事源于保罗罹患甲状腺癌,之后所有故事的展开都围绕着他的疾病。“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92疾病标志着自然环境受到了某种伤害后对人类身体的惩罚,是大自然对人类无序利用自然的报复。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情就像是上帝的愤怒”,[3]9只是,这个“上帝”是大自然。保罗为了治疗甲状腺癌症,不得不在术后服用放射性碘液杀死残留的癌细胞。他的身体也随之变成了一个辐射源,凡与他接触者都会受到辐射的威胁。但他的亲人并没有因此遗弃他。为了不给他的妻儿造成危害,他的父母把他接回自己家精心照顾。他的妈妈琳赛为他专门布置了“隔离区”,而且尽量“……使他,也使阿德里安以及她本人尽量不感到尴尬,并尽可能少地意识到它的存在。”[3]14父母每天探望他时只能“鬼鬼祟祟”地挤在门口跟他说话。他的妻儿来看他时也只能隔着栏杆远远地和他说话。尽管家人对他的隔离让保罗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在送往国外前需要隔离豢养几个月的“可怜狗狗”,[3]16但他对此却无能为力。家人本能的自我保护和“隔离”措施是人类面对自然伤害时的本能反应,显示出了人类在面对自然伤害时表现出的脆弱。
“过分地掠夺自然界,实质是切断了人同自然相统一的纽带。”[4]239所以,保护大自然成为了生态学家保罗的职业追求。政府要让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到“非洲伊甸园”奥卡万戈和蓬多兰地区开发修建高速公路、大坝、核电站和沙丘采矿的项目。保罗的环保组织配合国际环保组织成功地阻止了该项目的实施。环保主义者们胜利了,但项目的搁浅使得当地人民想要获得工作机会、改善生活困境的梦想破灭了。不仅如此,因为没能修建“十个大坝”,当地人民不得不饱受洪水之苦:一方面,人类在保护自然的同时需要舍弃自己的利益追求,但另一方面,“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自然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一定条件下自然也以积极的方式反作用于人。”[5]洪水在毁坏人们的家园的同时帮助受淹地区的土地进入一个新的轮回,帮助“这个名叫奥卡万戈的整个的有机体进行着自我更新。”[3]198
保护自然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存活,那么“实现工业化”“不正是利用我们丰富的资源,来发展我们的经济,提高穷人的收入吗。如果贫穷不结束,那么还有什么能存活下来。”[3]183戈迪默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解决方案。但通过公园中鹰的故事,我们依稀可以读懂作者的意图。一般来讲,鹰一窝只孵两个蛋。雏鹰出壳后会互相竞争。为了更好地存活,其中的一只雏鹰“亚伯”会把另外一只雏鹰“该隐”杀死,扔出巢外。活下来的那只鹰会得到父母的喂养直到成年。因此,作者提问自己:“如果亚伯必须被该隐扔出巢外;那不也是为了一种更大意义的存活吗?”[3]183如果连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都不能满足,生命无法延续,那么保护自然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所以,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存活,仅有保护是不够的。而作者对鹰巢的描写有着更深层次的隐喻意义。崖缝间的鹰巢空间局促,似乎根本不可能容纳下鹰硕大威武的身体,为了降落在巢穴里,它需要收拢折叠自己的身体,“主动使自己适合家居”,“把自己安置在了它那树枝铺成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3]177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源于希腊神话。强盗普洛克路斯忒斯把人放在一张铁床上,如果身体比床长,他就砍去长出的部分,如果身体比床短,他就用力把身体拉长,使之与床齐。作者把鹰巢比作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其用意不言而喻。鹰,生命的象征,尚且知道如何收拢自己的身体去适应有限的自然环境,那么人类更应该规范自身的行为去适应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从而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二、《新生》中人与他者的伦理关系
人,总是以群体的形式存在的。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是通过一定角色和身份与他人进行交往而发生各种关系。“从伦理学的角度看,社会对人的每一角色和身份都会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由此构成人的伦理权利和义务。”[6]每一个伦理主体在享受一定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一定的义务。在特定伦理关系中,只有伦理主体相互共同行驶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伦理关系,伦理双方才能和谐相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在物质生活获得满足的同时,精神世界开始荒芜。对物质的过分追求、基本道德感的丧失,无可避免地导致伦理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失衡,最终导致伦理关系的严重疏离。
《新生》有两个故事主线:第一条线索是保罗夫妇。在这个故事中,保罗的身份是生态学家,受聘于一家基金会,从事自然资源保育和环境控制方面的工作。他妻子蓓蕾妮丝却是国际广告公司的高管,专门为那些砍伐森林、破坏生态的客户们做广告宣传:“工作性质风马牛不相及”。即便是在一起生活了5年,两个人之间仍然有陌生感,“虽然不乏一些事情要谈论,……,但是却总有陌生者的成分,双方都在用第三只眼睛,用别人的眼睛,来看待事情。”[3]6夫妻两个工作目标的背道而驰导致了夫妻二人的心理距离渐行渐远。夫妻二人在生活中本应互相支持,但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导致了双方关系的异化。在这里,我们无法用伦理权利与义务来考量二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二人工作性质的巨大差别实际源于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的保护永远是一对难解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二人关系的疏离也是一个难解的题。琳赛和保罗在谈话中提到关于阿德里安放弃考古赚钱养家的时候提到过:“像你这样心中只怀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使命,这个使命是第一位的,……几乎没谁有你这样的运气。”[3]133其中的潜台词不言而喻。保罗之所以能全身心投入环保事业,关键的保障是妻子的丰厚收入让他没有养家糊口的顾虑。夫妻二人关系的疏离使得他不止一次有过离婚的念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事业方向的相悖确实是二人关系的一个诱因,但保罗内心深处的个人主义却是他们二人婚姻危机的根本原因。保罗生病期间的隔离给了两个人一个反思的机会,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缓和。而新生儿的降生给了他们的夫妻关系一个新的开始。
第二条线索是琳赛和阿德里安夫妇。阿德里安年轻时酷爱考古,但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为了挣钱养家糊口,不得不放弃自己所热爱的追求,进入公司经商。琳赛是一名民权律师,天生丽质。作为丈夫,阿德里安为了妻子,为了家庭履行了作为丈夫的伦理义务。那么如此同时,他应该享有相应的伦理权利,也就是享受妻子应该为他履行的伦理义务。但因为受西蒙·波伏娃的“偶然之爱”观点的影响,琳赛有过一段长达4年的婚外恋经历。这给“直接而诚实”的阿德里安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作为妻子,琳赛享受了丈夫对自己的扶持义务,却没有履行自己对丈夫应有的伦理义务,即忠诚。伦理双方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导致夫妻关系出现裂痕。即便是阿德里安在发现妻子的婚外情时采取了隐忍的态度,没有提出离婚,也仍然为今后夫妻关系的破裂埋下了隐患。幡然悔悟的琳赛终止了这一段不伦的婚外恋,回归家庭,并尽可能地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错,但她对丈夫的伤害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他们的儿子保罗病愈后,为了圆丈夫的考古梦,夫妻两个踏上了去墨西哥的路程,琳赛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先行离开,丈夫却在她走后爱上了比自己小30岁的年轻女导游。但“如果有谁能够理解的话,那么这个人应该是她。”[3]136她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因为只有她明白丈夫为了这个家,为了曾经的婚姻牺牲隐忍了多少,他应该追求本真的自己,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享受自由选择的快乐。因为自己曾经的背叛,她把丈夫的移情当成是自己救赎的苦药。作者对该故事的情感结构安排似乎也是为了告诫读者,任何事物有因必有果。在生命旅程中,人需要不断做出自己的伦理选择,但要为自己的伦理选择承担相应的后果。
在两对白人夫妇之间伦理关系异化和疏离的同时,我们却看到了黑人和白人关系的亲近。在这个故事中,琳赛家里有一个黑人保姆普里姆罗斯,琳赛夫妇俩为保姆的孩子支付学费,还帮助她支付建房子的定金,在保罗到琳赛家修养之前,夫妇俩还计划着如何在保护保姆的自尊的情况下说服她暂时离开,为的是不让她“暴露在辐射之下”。一个雇主如此贴心地对待一个家庭保姆,而作为保姆,她本可以在拿着工资的同时短暂休假,还可以远离辐射的危害,但她却选择了留下来,和琳赛夫妇一起尽心尽力地照顾保罗。在这对主仆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如今的南非社会中黑人和白人关系的“亲密无间”。故事中另外一个黑人是保罗的同事塔佩洛,作为他的同事,他深知辐射的危害性,但他却经常来看望保罗,毫无顾忌地和保罗在花园里聊天喝茶。来看保罗时,他竟然“张开双臂,要来一个非洲人的碰肩式拥抱,保罗却向后退开,这种拥抱是黑人对为争取自由而并肩战斗过的战友的一种表达。”[3]65两位黑人对待保罗的态度和白人对待保罗的态度截然不同。白人们在采取各种专业的措施隔离保罗的同时,黑人们却无视保罗的病情和他正常交往,甚至是身体接触。为什么呢?“这两个人怎么竟然都不害怕呢;若是归于情感,那就未免太简单了,保罗是个白人,是有历史沿袭性的,这个历史相信黑人更坏,然而显而易见的则是,这两个人都是黑人,却更好。”[3]66曾经的种族隔离政策让南非的黑人们的身心都遭受重创,如今的黑人们却没有因此活在仇恨里,而是与白人们相互支持和关怀。经历过太多伤痛的黑人们似乎无惧任何威胁,包括辐射。 正如Wagner所说:“黑人世界被压迫地越无情,他们的最终回归将越坚定。”[7]两位黑人展现出的勇敢无畏也象征着如今的黑人在南非的主人翁姿态,“在宣告,这里是他的土地,而不是一个暂住居民的家。”[8]而黑人主体身份的回归也为白人和黑人关系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基础。
三、《新生》中人与自我的伦理关系
人与自我的关系是各种伦理关系中最内在的,也是最难究明的。“文学之所以会有揭示人性、人生的无限深广度,即在于人与自我关系的复杂性。”[9]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领域划分为三大领域或层次,即“本我”“自我”“超我”。 “本我”即本真的我,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生存的基本需要。“超我”即理想的我,体现出人的社会属性,是人发展的最高境界,以人的道德至善为核心。“自我”即现实的我,处于“本我”和“超我”两者之间,能有效地把两者协调在一起,是理性和机智的代表。[10]李定清教授认为:“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以求圣为切入点,内在地传达着终有一死的人由凡入圣的道德伦理欲求。”[9]所以,人的一生当中,人的自我反思、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由现实的我向着理想的我不断靠近的求圣之旅。但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不乏本真的我的放纵,从而导致人在三种我之间徘徊。戈迪默在《新生》中塑造的保罗、琳赛和阿德里安就是这样不断求索的典型代表。
作为一名生态学家,保罗的职业目标是保护大自然,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努力。即便是在病痛中,他也仍然坚持工作。他的职业目标体现了他的崇高道德追求,是向超我的不断靠近。为了更好地体现自身价值,他和同事们一起成功地阻止了一个又一个项目的实施。最终,他们胜利了,“爆发出有几分凯旋意味的大笑”。[3]204而人所追求的超我应该是我的思想和行为对自身有着积极向上的意义、作用和影响,并“有利于他人、集体、社会、自然和全球,并非鼓吹个人主义、自我中心、自我膨胀”。[11]正如马克思所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达到完美。”[12]保罗为了人类更长久的幸福生活而努力是对自身的完美,即超我的不断追求。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保罗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和稳定工作,夫妻俩的收入可以让这个家庭过着体面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白人。在阻止项目进驻的同时,他也让很多贫困的家庭失去了得到工作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维护自由政策的抱负实际上是把南非的底层人民排除在外的。”[13]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推断,作为白人的保罗,他并没有体会到底层人民,尤其是贫困黑人的艰难处境。他对超我的追求里是否有霸权意识存在呢?
保罗对超我的追求存在着明显的悖论,而琳赛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改造之旅则展现了人与自我关系的复杂性。年轻时候的琳赛漂亮能干,为了实现本真的我,追求自己的快乐,她和自己的一个同行有过一段长达4年的婚外恋。本以为掩盖得很好,却不知丈夫知晓了此事并忍受着巨大的心理痛苦。婚外恋是琳赛的自由选择。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在强调自由的同时,却不能逃避道德责任和社会道义,人终将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因为 “自由是人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情的权利,或者像1791年《人权宣言》所说的‘自由就是做一切对他们没有害处的事情的权利’。”[2]438琳赛的自由选择给他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也使自己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折磨。人是伦理性的存在,生活在社会中的任何人在享受本我的自由时都不能凌驾于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之上。因为“自由不是个人的为所欲为,或是横行霸道、作恶多端,而是标示这社会关系中公民的权利和行为的量度”。[4]100可以说,因为对本我的过分追求,她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所以,悔悟后的琳赛开始努力平衡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在之后的生活中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努力弥补。她的“求圣之旅”也自此展开。先行离开旅游地的她在家里给丈夫攒了一大摞丈夫爱看的杂志和报纸,满心希望地等着丈夫的归来却等来了丈夫告知自己他已移情别恋的信。她震惊,但她“不气愤,无权气愤”[3]144。因为她知道:一方面,如同她自己曾经有过的自由选择一样,尽管这种自由选择不符合伦理道德规范。阿德里安也有权选择做本真的自己:另外一方面,她知道,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挽回和弥补的。丈夫曾经给予她的原谅并不代表她对夫妻感情的伤害已经消失不见了。琳赛要为自己曾经的错误选择承担后果。因为“过去的一切不是消失了,沉寂了,而是令人尴尬地顽固存在着,它将不断回过头来纠缠我们,除非我们彻底解决一切。”[14]
琳赛接受了丈夫移情别恋的事实,没有对此做出离婚的选择,而是继续与丈夫保持着通信交流。现实的琳赛开始了自己全新的生活,她领养了一个被人强奸,患有艾滋病的被人遗弃的3岁黑人小女孩。一个身心遭受巨大创伤的黑人女孩进入了琳赛的生活。琳赛没有告知大家小女孩应该如何称呼她。不管是奶奶还是母亲,她成了小姑娘的合法监护人。她需要给予这个小姑娘所需要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遭到丈夫背叛的琳赛在这个时候做出这种选择,其实是在原谅丈夫的同时想要全身心地为一个急需关怀的人给予她能给的一切。与一个身心俱伤的社会边缘人建立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并且担负起相应的伦理责任,她的这种伦理选择彰显的是她对超我的至高追求。此外,琳赛在同事家的宴会上认识了一个退休了的同行。她没有排斥这个同行对她的追求。开放式的故事结局并没有告诉我们琳赛最终是否接受了这份感情。但至少说明,琳赛并没有因为丈夫的移情而自怨自艾,而是愿意开始新的一段感情,坚强地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最终,丈夫在挪威的斯塔万格离世,他没有运回他的尸体,因为“家,从斯塔万格,重新开始,从坟墓中”,“找到了归宿”。[3]192她替丈夫做了最后的选择,帮助他实现最终的本我。从容淡定地面对丈夫的背叛,勇敢地担当一个监护人的职责,并且开始追求自己崭新的个人幸福,现实的琳赛用行为证明了自己的勇敢无畏和独立自强。从在本我的迷失中走出来,坚定地走向超我,这个发展历程让我们看到了琳赛的自我在本我与超我的博弈中的重要调和作用。所以,要造就和谐自我,就要培养强有力的自我。
故事的另外一个主人公阿德里安的情感历程展现了一个男人在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过程中的担当和无畏。婚姻生活开始的时候,为了支持妻子对事业的追求,为了养家,他毅然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考古,转而从商。而妻子琳赛的婚外恋给他们的家庭生活蒙上了一层永远也去不掉的阴影。阿德里安发现了妻子的婚外恋,在妻子坦白后说了一句话:“我以为你要告诉我你要走呢。”[3]79他让妻子自由选择。作为丈夫,作为父亲,阿德里安扮演着不同的家庭角色。对于他来说,“角色之下的真实的自我的表达开始变得如此艰难,自我内心的真实世界与社会赋予的角色之间充满着矛盾和冲突。”[15]为了家庭,愤怒痛苦的他选择了隐忍和宽容。他给予妻子的无私支持、选择自由和原谅体现了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道德追求,也即超我的追求。
退休之后的阿德里安为了实现年轻时候的考古梦想决定和妻子一起去西班牙旅行。他的决定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觉得阿德里安有权利进行他那机缘到来的考古冒险”,因为“人有自己的爱好完全是应该的”。这个“可怜的顾家男人”[3]133开始了对本我的追求之旅。他在旅行途中爱上了自己的导游。这一次,他放弃了自己的家庭角色,选择积极应对本我的诉求。所以,琳赛认为:“对他,对我,……这件事有一种乐意的成分,愿意进入它,进入这一状态,即使它一方面是疏远,而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实现。”[3]138疏远”的是自己过去压抑本我的家庭生活,而“实现”的则是阿德里安现在的本我诉求。在一个远离家人的地方爱上了另外一个人,阿德里安没有选择隐瞒,而是完全坦白给了妻子,因为“他想要像他自己一向的那样,对她直接而诚实”。[3]136一直以来,阿德里安对妻子都是真诚的。真诚,对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能够变成真诚的:这是我的责任和我对真诚的努力所意味着的东西。”[16]所以,真诚对于阿德里安来说是一种责任,一种努力的方向。他在坚持自己的个体自由的同时,也在捍卫着琳赛的自由,因为“人只有通过捍卫他人的自由才能拓展个体的自由,才能本真地实现自身。”[15]和妻子的婚外恋一样,阿德里安的移情超越了道德规范所允许的范围,但这却是他实现本真的我的最佳体现。在给妻子的信中,阿德里安称自己的移情别恋为“老年人的最后放纵”。[3]137“最后的放纵”意味着他知道生命即将终结,也体现出他对死亡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中,人们还是可以进行各种各自生存的选择,逃避此种害怕的东西或通过努力重新获得失去的东西,甚至可以改变心态,不再害怕此种东西,或移情别恋,不再喜欢这一东西。”[17]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决定在生命的最后做回本真的自己,这实际上体现出了他“向死而生”的生存观。既然死亡一开始就已存在于生命的终点,那就勇敢面对死亡,积极地生活。而他最终的平静辞世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曾经有人质疑:“在失去了反种族隔离制度这一基本文学主题后,南非白人作家是否还能生存,还能保持强劲的创造力?”[18]通过对戈迪默的《新生》中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以及人与自我这三重伦理关系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告诉我们:当人们不再沉湎于种族隔离这一沉重历史伤痛,开始全新的黑白种族融合的生活的时候,人们面临的是更为难解的题: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做到可持续发展;如何与他人坦诚互爱,共同创造和谐社会;如何坚定自我,平衡本我的本真诉求和超我的至高召唤。蕴含着丰富人文关怀的《新生》不仅有力还击了他人的质疑,而且向读者“展示一个‘后’殖民的世界,意味着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并以一种与过去大不同的方式再现这个世界”[19]。
[1]马永庆.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伦理关系[J].齐鲁学报,2004(1):17-2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纳丁·戈迪默.新生[M].赵苏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4]张之沧.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马永庆.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伦理关系[M].齐鲁学报,2004(2):17-21.
[6]朱海林.论伦理关系的特殊本质[J].道德与文明,2008(4):32-36.
[7]Wagner,Kathryn.Rereading Nadine Gordimer[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83.
[8]Heywood, Christopher. Nadine Gordimer[M]. Windsor: Profile Books, 1983:158.
[9]李定清.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文精神建构[J].外国文学研究,2006(1):44-52.
[10]马克·柯克.人格的层次[M].李维,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38-154.
[11]陈文化.关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思考[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16(2):1-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
[13]David Tenenbaum. “Survival Systems” in Nadine Gordimer’s Get a Life[J].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2011(2): 43-54.
[14]德斯蒙德·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M].江红,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1.
[15]刘晓春.个人本真性的建构[J].文化研究,2011(4):52-57.
[16]萨特.存在与虚无[M].修订译本.陈宣良,等,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7:92.
[17]刘瑞享.生的沉思及死的默想[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23(2):79-82.
[18]Witalec, Janet.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M].Detroit: Gale Research Company, 2003:362.
[19]艾勒克·博埃默.殖民和后殖民文学[M].盛宁,韩敏,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13.
(责任编辑钟昭会)
2016-04-2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20世纪南非英语小说研究”(14BWW075)。
胡忠青(1980—),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蔡圣勤(1966—),博士,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西方文论。
I3/7
1000-5099(2016)04-016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