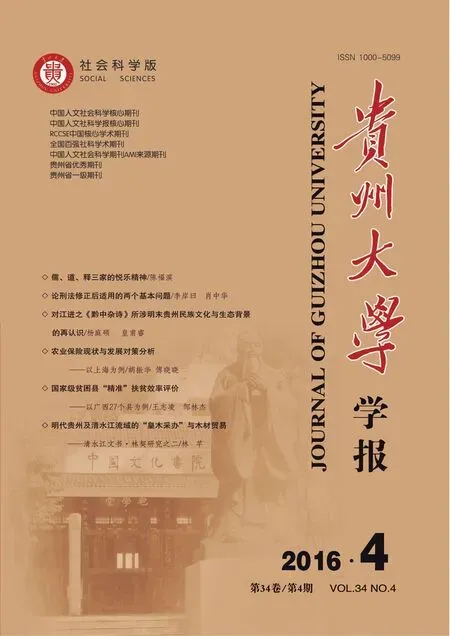儒、道、释三家的悦乐精神
陈福滨
(辅仁大学 哲学系,台湾 新北 24205)
儒、道、释三家的悦乐精神
陈福滨
(辅仁大学 哲学系,台湾新北24205)
儒家、道家、释家是中国哲学的三大主流,全都洋溢着悦乐的精神。儒家的悦乐源自于好学、行仁和人群的和谐;道家的悦乐在于逍遥自在、无拘无碍、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乃至于由忘我而找到真我;禅宗的悦乐则寄托在明心见性,求得本来面目而达到入世、出世的和谐。真正的悦乐,不是用任何方法可以直接追求的,只有当立己达人的工夫到达某一境界,这时悦乐才会自然而然地从心灵深处涌现出来。
儒家;道家;释家;悦乐;行仁;逍遥;明心见性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4.001
悦乐的精神,不属于解析知性的范畴,也没有形式上逻辑的必然性。正因为它超越了“必然”,由精神的幸福所带来的生活快乐,就出自他智性慧悟、启示信仰所导发的和谐与悦乐,其间充满活泼底生机与丰盈的生命。
儒家、道家、释家是中国哲学的三大主流,吴经熊先生认为:“这三大主流,全都洋溢着悦乐的精神。……儒家的悦乐源自于好学、行仁和人群的和谐;道家的悦乐在于逍遥自在、无拘无碍、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乃至于由忘我而找到真我;禅宗的悦乐则寄托在明心见性,求得本来面目而达到入世、出世的和谐。”[1]1真正的悦乐,不是用任何方法可以直接追求的,只有当我们立己达人的工夫到达某一境界,这时悦乐才会自然而然地从心灵深处涌现出来。
一、儒家的悦乐精神
《论语》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说,悦也;朱熹认为:“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又引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乐由说而后得,非乐不足以语君子。”[2]47人若通过学习不断地求取知识,当有得于心时,自然衷心喜悦。远方有人来问学求道,心有所感,则慧命相续,故自然悦乐。杨祖汉认为:“这是理性的,仁心道心呈现时之怡悦喜乐,并非因感性欲望得到满足而乐。且人来问学求道,则在践仁成圣的路途中,便有许多真实生命在相感照,不断有师弟朋友先后相承,而使慧命相续。”[3]96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虽疏食饮水,而不改其乐,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一般,说明了孔子注重精神上的悦乐。虽然孔子亦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富而可求也。”(《颜渊》)但是,显然不是纯粹从物质上来说的。所以,《学而》有:“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之言。因此,夏长朴认为:“孔子所乐的对象应该就是道。”[4]又<雍也>云:“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寠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2]87颜回虽然面对现实生活的困顿,但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如曾昭旭所谓:“用一般人之不能忍来对比出颜回已超越了现实与气质生命的限制,而掌握到精神上的自由之乐。这自由本质上是永恒的、可以自主的、不受外物影响的,所以用‘不改其乐’来表示。”[3]185同时,孔子也认为自己的为人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此正孔子真实生命的呈现,内心悦乐的真情流露,也显示出孔子内得于心的悦乐境界。
《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由根植于人性的善端,走向“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人格完成。“善”之于“心、性”言, 孟子于《公孙丑上》云:“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乍见是本心、仁心的真情流露,人皆有“仁、义、礼、智”四端之心,此四端是“根于心”的,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之性分所当尽者,而此性分之所当尽者是吾人内在本有的道德心、性所自发,孟子指出了性善乃源之于心善的“即心言性”的理论。又《告子上》云:“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朱熹言 :“乃若,发语辞。情者,性之动也。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2]328在这段话里,孟子所谓的“善”性是就人性之实所具有“为善”之能力来说的,袁保新认为:“‘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这段文字是孟子对于自己为什么将‘善’系于‘人性’概念之下,……第一个‘可以为善矣’的‘善’,是指具体的善行而言;第二个‘乃所谓善也’的‘善’则是指人的可以为善的能力,亦即就人性自身而言。前者是即‘事’而言的‘事善’,后者是即“性”而称的‘体善’……”[5]53-54。因此,第一个“善”字指具体行事上的善,第二个“善”字则是就人性自身来说的,表示每个人都具有足以“为善”的能力,因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而此“我固有之”的“仁、义、礼、智”都是一价值观念,我们的善性也就能作价值判断的主体,良知本心也就是知是知非之价值判断的主体。
在《孟子》一书中孟子将“善”与“诚”作了结合,孟子所谓“反身而诚”的“诚”是经由“反身”而来,“明善”亦是在“反身”的过程中而彰显,“善”是人性的根源、自我的根源;此说明了人能有意识地自觉,“反身而诚”正所以“明善”。然而,孟子所欲“明”之“善”为何?“善”是否具有“自明性”、“可欲性”?在孟子看来,“民可得治、获上有道、信友有道、悦亲有道、诚身有道、明善”须立基于经由“明善”的“反身而诚”上;“善”是一切价值所从出,其本身就具自明性;“善”是“反思”所要彰显者,正《告子上》所谓:“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人之“善端”乃天之所与我者,人心无不悦理义,程子言:“但圣人则先知先觉乎此耳,非有以异于人也。……须实体察得理义之悦心,真犹刍豢之悦口,始得。”[2]330“善”虽然经具“反思”的“诚”而彰显,但“反身而诚”是以“善”之“明”作为其必然条件;换言之,没有不以“善”之“明”而为的“反身而诚”;所以,此“善”应是自明的。
然而,“善”除了自明性外,又具可欲性;《尽心下》言:“可欲之谓善。”朱熹注言:“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2]370此段话是浩生不害问“乐正子,何人也?”孟子回答认为乐正子是“善人也,信人也。”的话语;然而,就广义言之,所谓的“可欲之谓善”,亦可以诠释为“善是可欲的”。但是,人当“为善”却“为不善”,除了“由于人心之陷溺于外物之环境中”外,更重要的是因其“不能尽其才”,“不能尽其才”乃由于“弗思”所致;然而人何以会“弗思”?《告子上》言:“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此处所说的“思”是道德本心对其自身的明觉,所以“思”与“不思”正是“大人”与“小人”的区别。同时,孟子“善”的可欲性不是为了“小体”的满足,而是为了“大体”的成全,心之大体可以统摄耳目之官的小体;因此,唐君毅认为:“一切不善,只是人之感觉性活动与仁义礼智之性分离;身体耳目之官与心之官分离,小体与大体分离,以致人只求由身体耳目之官之发出之感觉性的活动之满足,为外在之欲所蔽,及使心之功能仁义礼智之性无由显发。……人只去尽其部分之性,也就根本不是尽性,不能尽性。”[6]又说:“耳目食色之欲,并非即不善者。不善,缘于耳目之官蔽于物,或人之只纵食色之欲。而耳目之官蔽于物,与人之只纵食色之欲,则缘心之不思而梏亡。故人不得以人有食色之欲等,疑心之性自身之善。”[7]所以,须经由“思”,这“善”的“自明性”才会完全朗现;经由“善”决定何为我的“可欲”,因着“善”决定我人之“可欲”,所以才会“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公孙丑上》)“善”决定了我作为一个“大体”、一个“思诚者”,所以“善”的“可欲”是对此一“大体”、“思诚者”的“可欲”,而非小体的可欲;若“反身而诚”经由“思”得到落实,它也就是“天之所与我者”在我反身过程的实践;由此,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除此而外,孟子更在《尽心上》扩充悦乐的意涵,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朱熹注云:“此人所深愿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乐可知。”又引程子曰:“人能克己,则仰不愧,俯不怍,心广体胖,其乐可知,有息则馁矣。”又朱熹云:“尽得一世明睿知才,而以所乐乎己者教而养之,则斯道之传得之者众,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矣。圣人之心所愿欲者,莫大于此,今既得之,其乐为何如哉﹖”[2]354可见,君子三乐,分别是从伦理、心灵与教育等三个面向来说的;享受天伦之乐是第一乐,俯仰无愧怍于天、人是第二乐,作育英才以贡献社会是第三乐;这三种快乐,都是由人的道德理性和生命信念所共创。
要知, 孔、孟思想都以知天命、顺天命,行天所赋予的使命为己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为人生的至乐,面对此一生命态度,孔子尝“弦歌不辍”(《庄子·秋水》),但是也“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同时也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而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都在在突显其悦乐之精神,并将进至“天人合德”的境地。
二、道家的悦乐精神
道家形上超越思想的氛围,给了中国文化中无为恬淡、逍遥自在的气象。《老子》言:“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第四十九章》)王弼注云:“各因其用,则善不失也;无弃人也。各用聪明。皆使和而无欲,如婴儿也。”[8]129圣人治理天下,不以自我之意欲作判准,却能以善心诚心对待任何人,因此就无弃人;百姓皆注其耳目,则各用聪明,以致产生纷争;圣人抱一守朴,使百姓皆回返到婴儿般浑朴真纯的状态。傅佩荣认为:“圣人是启明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他还乐于告诉人他是‘如何’知道的;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既很容易了解也很容易实行,但是‘天下莫之能知,莫之能行’。因此他只好‘抱一’以做为天下的楷模。……圣人不仅为天下式,而且为天下立官长。……圣人所要做的只是要帮助百姓回复他们的本性而已。”[9]因此,此一“和而无欲”的和谐,正体会了人生的面向。另则,《老子》亦要吾人当“知足常乐”,故言:“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王弼注云:“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贪货无厌,其身必少。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为病也﹖甚爱,不与物通;多藏,不与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众,为物所病,故大费、厚亡也。”[8]121-122楼宇烈言:“‘甚爱,不与物通’,意为私爱名过多,则不能与万物沟通一气。‘多藏,不与物散’,意为私藏利过多,则不能与万物分享所有。”[8]122过于爱名者,必损其精气;且名高谤至,伤性失神,正所谓:“久受尊名,不祥;长享尊名,必有不祥。”如欲歛天下之财货,则必失之也多,岂可不慎!要知,“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因此,唯有知足,方能常乐;才是“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才是恬淡自然、无拘无碍的人生。
《庄子》内篇《逍遥游》开宗明义,发挥生命哲学之义理;其主旨在说明人如何才能适性解脱,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逍”是消解的意思,消解我们形躯所受到的限制,以及因着形躯的限制所带来的约束、制约性;“遥”是心灵的放旷自达;“游”是人生的自在自得,心灵上无拘无束、自如自得的境地;叶海烟认为:“‘逍遥’有其高超的象征意义,而唯落实于生命之历程与生命之内涵,逍遥的种种象征才可能获致实际的意义。……道在生命的具体呈显及‘无’在‘有’中的具体作用,吾人可以发现生命之超越属性乃是生命所以能逍遥的根本。生命在绝对性及无限性中不断进行的创化,则不断提供可由吾人理性加以鉴定的生命信息。……生命之逍遥展现了生命全面之属性,生命之象征性因此富有高度的形上意义。……”[10]而“逍遥”之生命所体现的就是精神自由,逍遥之乐就是自由自在之乐,此为庄子人生的最高典范与幸福;故林希逸言:“逍遥游,即《诗》与《论语》所谓乐也。”“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乐之地也。”[11]无何有之乡,“乃无为精神所开拓出来的广大的生活空间,它已不是一般客观意义之自然界。无为而自由,无为而逍遥,……是吾人心灵世界中无所依傍无可企求的自足状态。”[12]《逍遥游》从“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所点出的大鹏鸟,以为神秘的象征,透过转化来超越自身,以自由超脱而向上提升;此正所以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终至绝对自由,与道体合而为一。
又《庄子》外篇《秋水》言:“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何以庄子在濠梁上游得快乐,便以为鱼儿在濠梁下也游得快乐呢﹖盖庄子以游鱼之乐为己乐,是为一感受力、感知力之美的欣赏,以天地之大美为人生至乐的泉源;所以吴怡认为:“庄子已入物我一体的境界,他在濠梁上所感觉的快乐,正是得之于鱼儿在濠下的悠游自在。鱼和庄子的各得其乐,这是自化;庄子因鱼之乐而乐,因己之乐而推知鱼之乐,这是物化;濠上濠下不分,一片逍遥之乐,这是神化。所以庄子的‘我知之濠上也’,完全是一种化境的体悟。”[13]将人与自然合为一体,,此乃心之悦乐的呈现。
《庄子》:“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让王》)展现了顺乎自然、无入而不自得的乐趣;庄子精神上的逍遥,超越了人世间的小大之别、是非之辨、有用无用之差;庄子的逍遥之悟,即在消除自我执着之迷,认定一切世俗的是非、价值判断多为一己之成见,《齐物论》的“吾丧我”就是要破除偏见,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和谐,更说出了道家境界的精蕴。
三、释家的悦乐精神
印度佛教之基本观念中有“三法印”的思想,“三法印”指的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其中“诸行无常”的“行”指一般意欲活动,意欲本身变异不定,时时落在新需求上,使自身陷“苦”,此变异即“无常”。生活中所以有“苦”,乃因生命永有所需求,每一需求构成一压力,即成为生命中之“苦”,“乐”是须通过“苦”而界定;故生命之真象乃一串需求一串苦是也。“苦”“乐”如影随形,“烦恼身心名苦,适悦身心名乐”,佛家言苦有:二苦、三苦、四苦、五苦、八苦、十苦等;其中最常说的是四苦,八苦;四苦指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再加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盛苦,就是八苦。惟有身心解脱才能离苦得乐,而此乐是与生命自觉之状态并存;因此,佛家有五乐之说,五乐指:出家乐、远离乐、寂静乐、菩提乐、涅槃乐,“救世多慈悲,即心无行作;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乐”在于逐步脱离烦恼,澄心静虑,发慈悲心,以澈悟生命真相而得到生命的大自在,如此自家悦乐自然涌现。
释家空灵虚妙意境的氛围,给了中国文化中见性开悟、普渡世人的气象。太虚大师言:“中国佛学,并非与发源之印度及弘扬于世界各国的截然孤立,不过从中国佛教历史研究,就有中国佛学的特殊面目与系统,把中国佛学的特殊面目与系统讲出来,就成为‘中国佛学’—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14]而吴经熊也认为:“释家尤以禅宗为最重要”“禅宗是在大乘的冲击下形成的,并且因而承袭了它宽宏大度的气象;不过,就其教训的内容与思维的模式而言,则纯粹是中国的,因为它融冶了道家的空灵与儒家的人道于一炉。”[1]1-14是以本节言及之悦乐精神系依禅宗为论;禅宗的代表惠能付法后,弘传禅法四十余年,对顿教之开展,给出了决定性的影响。六祖以下,宗风大畅,其学说为:(1)见性成佛:惠能曰:“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着。不起诳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六祖坛经·般若品》)佛就在心中,佛是不须要远求于外的,佛是不须要经过经典的阐述才能认识佛是什么,能够明心见性,就能够见性成佛。(2)定慧不二:惠能曰:“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六祖坛经·定慧品》)因为一般修习佛教之时,比较注重工夫,而不重视真谛。重视工夫就有二层,一种是修养的观,如:数息观、瑜珈行等;那在禅宗而言称为禅定。然而定中要有慧,不能定慧分离,故定慧乃是要双修的。(3)无相、无住、无念:无相、无住、无念是般若法门修行的三大要领。在性空,无所得理念的指导下,契入诸法实相。实相,是无相的。如《金刚经》说:“实相者,即是非相”。又曰:“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由认识到实相之无相,生起无住行。《金刚经》说:“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又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由无住达到无念的境界。《坛经》也以无相、无住、无念,作为禅者的修证要领。经中说:“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何为无相?《坛经》说:“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则法体清净,此以无相为体”。无相是离相,不住于虚妄差别之相。何为无住?《坛经》说:“念念中不思前念,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若念念不住即无缚,此是以无住为本。”无住,是-个念头上保有智慧的观照,不住着于六尘境上。何为无念?《坛经》说:“于诸境上心不染着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尽即绝,一念绝即死”(《坛经·定慧品》)。因此,无念并非什么都不接触,或者什么都不想,而是在接触外境时,心不染着境界,如同明镜,物来则现,物去则无。所以,无相、无住、无念是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正念,我们不能在念中有所迷,而有所失。“无念”是在“无相”的基础上不动任何念头,停止思维活动,“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无相”即“于相而离相”。“无住”即绝不容许意念住某一点上,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此,故言之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4)不依经论: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六祖坛经·机缘品》说,六祖得法后,至曹溪弘化,无尽藏比丘尼问他既不识字,怎么能够理会《涅槃经》要义,惠能大师自信地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大师认为一切经书,大小二乘,十二部经,其目的是为了让迷人开悟,愚者心解。万法本在自心,应从自心中证悟真如本性。所以,语言文字只是方便开启法门的工具,可见六祖是彻底落实禅宗“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宗旨。,不依着任何的经典做为论述的依据,这不代表他不要经典,而是可以豁然畅法的去论述一切,不是只根据着某一经典,局限于经典之内。
佛教中的禅宗主“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现存的《六祖坛经》有多种版本,以敦煌本为最古,敦煌本《六祖坛经》中,提到“佛性”一词有下列四段:(1)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2)善知识!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3)惠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4)和尚言:造寺、布施、供养只是修福,不可将福以为功德。功德在法身,非在于福田。自法性有功德,平直是德。佛性外行恭敬,若轻一切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德。至于“心性”一词,敦煌本未用这一术语,曹溪本《六祖坛经》则出现一次:“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见性开悟”以普渡世人,生活中应抱持着“平常心是道”的精神面对人生,唤起生生不息,时空交融的觉悟;平是平等无别,常是常住不迁,而所谓的“平常心是道”,乃来自于惠能“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谓道”(《坛经·护法品》)的思想,即后来道一所谓:“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贤圣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道一的平常心,即自然心,也就是“常道”。崇慧禅师通过诗偈开示提问僧侣,应体会“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永恒意涵;“万古长空”,象征着天地的悠悠与万化的寂静;“一朝风月”,则显示出宇宙契机的生动流行;长空,万古永存,浩瀚而无法穷其边涯;风月,一朝涌动,华丽而无法究其幻化。长空,恒定;风月,易替。静寂和流动,永恒和短暂,都在这短短八个字中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在动与静之间,在永恒与短暂交关的当头,智慧的可贵、悦乐的心境方得以显现出来。长空的静寂,因此更让我们感到渺小、孤独。然而,天地永恒的静定,来自万物暂幻的搏动,月映万川,夜间蛙鸣,都融入于天地,而化为“万古长空”的永恒。南宋禅师善能就如此注解“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义理云:“不可以一朝风月,昧却万古长空;不可以万古长空,不明一朝风月。且道如何是一朝风月?人皆畏炎热,我爱夏日长;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可以说道尽了人世的总总,写尽了宇宙自然的奥秘与玄奇。又《坛经·付嘱品》言:“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然而当人们一见到了“自性”*“自性”是什么?在《六祖坛经·付嘱品》言:“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所谓“含藏识”依字义来看,是指人的如来藏识,或称为阿赖耶识,意即第八识。在《坛经.机缘品》言:“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意指人的自性具有三身即“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清净法身”是指人的本性是清净的,“圆满报身”是指智慧,能念念圆明、念念自见;“千百亿化身”是指人的行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念恶化为地狱,念善化为天堂,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不思万法,性本如空。成就菩提道果不能离开转识成智的过程,即《坛经·机缘品》偈言:“大圆镜智性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镜。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三身元我体,四智本心明,身智融无碍,应悟任随形。”依六祖的见解,即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八识为大圆镜智;迷为识,悟则为智,修行不外从“意识”来转。《坛经·般若品》言:“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因为“如来藏”含藏有成佛的种性,六祖虽言:“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但得待清净后才能成佛,烦恼也得透过“转识”方能见菩提。六祖所言的“自性”虽含藏万法,若没有透过去芜存菁的过程,佛性便无法显现;所以,“自性”不能当作“佛性”来解释,亦即顿悟还须渐修,才有得菩提、证清净法身、成佛道的机会。人人本具佛性,不待修便有,若没有机缘显现,等同于无。,便会超脱无知的小我,在行住坐卧间充满了悦乐,完成生命中的大醒或大归以超越生死,到达此一境界,正是云门禅师所说的“日日是好日”。是以,禅宗的悦乐是寄托在明心见性,求得本来面目,在生命中完成大醒或大归,对体认真我、超越生死有所觉悟,终至达到入世、出世的和谐。
四、结语
悦乐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儒家之于贤者乐道安贫,箪食瓢饮不改其乐,期使人们坚守高洁,启发乐道无欲有志的心灵;发扬人性的仁心善念,以至情及物,以至性待人,以至善履行,“诚”之自我悠然呈现。道家形上超越思想的氛围,给了吾人无为恬淡、逍遥自在的气象;逍遥之悦乐,在于全属自我主体的修持与涵有,于入世的谨严中培养出自由自在、无拘无碍的飘逸,“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是谓坐忘。”(《大宗师》)摒除了幻识假知的我,而达至忘知真知的我,以唤起心灵的直觉与自然相融。禅宗三祖僧璨所书之信心铭尝言:“大道体宽,无易无难,……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绝恼。……一如体玄,兀尔忘缘;万物齐观,归复自然。”此“任性合道,逍遥绝恼”,“万物齐观,归复自然”之境界,正闪烁着道家的智慧;而释家的“明心见性”,于实存的生活中,心无束缚,意无障碍,恬静平和的无名、无相之乐油然于心,在明净悦乐的心境中见性,终至达到入世、出世的和谐。吴经熊认为:“‘和谐’是儒家、道家、禅宗三家悦乐精神的核心,有和谐就有悦乐。”儒家、道家与释家,虽然其所乐容或各有不同,“可是他们一贯的精神,却不外‘悦乐’两字。”[1]1因此,可以说他们全都洋溢着悦乐的精神。
[1]吴经熊.内心悦乐之源泉[M].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台北:鹅湖出版社,1998.
[3]王邦雄,曾昭旭,杨祖汉.论语义理疏解[M].台北:鹅湖出版社,1997.
[4]夏长朴.寻孔颜乐处[J].哲学杂志(第六期),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22-36.
[5]袁保新.孟子三辨之学的历史省察与现代诠释[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6]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十八[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135-136.
[7]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卷十二[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102.
[8]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4.
[9]傅佩荣.从比较的角度反省老子“道”概念的形上性格[J].哲学杂志(第七期),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24-37.
[10]叶海烟.庄子生命哲学研究[D].台湾:辅仁大学,1989:236-237.
[11]林希逸.庄子口义[M].台北:弘道文化公司,1971:16.
[12]叶海烟.思惟的自由、平等与解放——〈庄子〉齐物哲学新探[J].哲学杂志(第七期),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84-96.
[13]吴怡.禅与老庄[M].台北:三民书局,1971:164.
[14]太虚大师.中国佛学的特质[C]//张曼涛.禅学论文集.台北:大乘文化,1976:1.
(责任编辑方英敏)
2015-08-25
陈福滨(1951—),男,台湾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汉哲学、宋明理学。
B234
A
1000-5099(2016)04-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