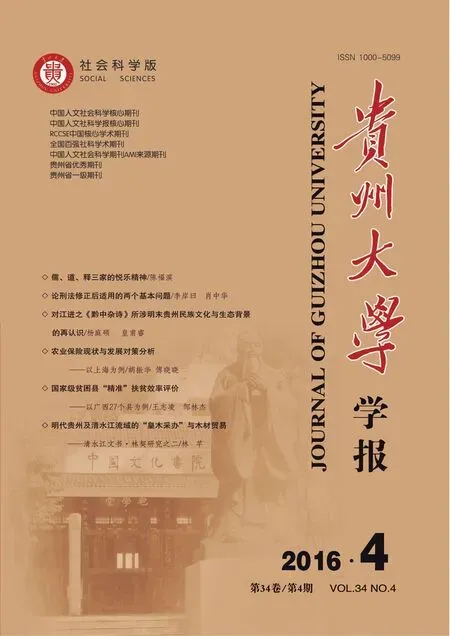论刑法修正后适用的两个基本问题
李岸曰 肖中华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72 )
论刑法修正后适用的两个基本问题
李岸曰肖中华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1000872 )
对于刑法修正前后的规范意义是否发生实质变化,需要加以甄别后作出判断,因为条文的删改增设有时只具有形式意义而不带来规范的实质变化。甄别对行为评价带来的是形式变化还是实质变更,主要把握两点:一是保护的法益,二是增加要素的含义。面对刑事立法不断扩大刑罚处罚范围的趋势,刑事司法只需忠实于合理的刑法解释规则,在语言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内合理解释刑法,就正确地实现了刑法的目的。
刑法修正;刑法解释;处罚范围;刑法目的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4.014
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典进行修改补充,已经成为刑事立法的常态现象。面对刑法修正活动的常态化,刑事司法活动仅仅停留在对法条进行纯粹的、“线性”解读的层面,显然是不够的。为了正确适用刑法,必须合理把握刑法修正前后的变化特征,领会立法目的与司法职能的关系。
一、刑法修正后规范意义有无实质变化
刑法修正在形式上表现为对刑法条文的增设、删除和更改,但刑法修正后规范的意义是否发生实质变化,需要加以甄别后作出判断。
以嫖宿幼女罪的删除为例,《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修九》”)直接把刑法第360条第2款嫖宿幼女罪之条款和罪名都删除了,这是否意味着对嫖宿幼女的行为进行了非犯罪化?或者说,刑法修正把嫖宿幼女罪这个罪名直接取消了,《刑修九》施行后,嫖宿幼女行为是否就合法化了呢?当然不是!应当强调,对于嫖宿幼女的,今后都应依照刑法第236条以强奸罪定罪从重处罚。道理很简单,嫖宿是男子与女性发生性关系的一种,无非是支付了嫖资的发生性关系,而无论是哪一种,只要是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就是“奸淫幼女”,而奸淫幼女就是强奸罪。这是法律明文规定,应当定罪处刑的。
对此,有人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嫖宿幼女在《刑修九》出台前就是一个独立的罪名、一个单独的类型,而《刑修九》施行前后的刑法第236条第2款并无任何变化,其规定的“奸淫幼女以强奸论处、从重处罚”内容始终如一,而《刑修九》施行前嫖宿幼女就不按强奸罪处理,这说明现在废除嫖宿幼女罪后,嫖宿幼女的既要像以前一样不能按强奸罪处理,嫖宿幼女罪现在没了,也不能按嫖宿幼女罪处理,所以就是无罪!我们应当注意,过去有嫖宿幼女罪,并不是说嫖宿幼女的行为就不符合强奸罪的构成,只不过在当时的立法背景下强奸罪和嫖宿幼女罪两个法条之间存在竞合关系。《刑修九》废除嫖宿幼女罪条款后,就只有强奸罪这个条文来评价嫖宿幼女行为了,所以,《刑修九》废除的实际上是嫖宿幼女这个条款、这个罪名,而不是说隐含在后面的禁止规范。
再以《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修八》”)对刑法第226条强迫交易罪构成要件的修正为例。这个罪原来规定得很简单:“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处……”《刑修八》在保留原来两种行为类型的基础上,增加了3项,其中第3项就是“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的”。《刑修八》于2011年2月28日通过,5月1日起施行。某一案件发生在2011年4月,裁判时已经是2011年5月。案情大致情况是:行为人以竞拍人身份进入某商品房的拍卖会现场,手持砍刀对现场其他竞拍人和拍卖师进行暴力威胁,不准其他竞拍人举牌,当场强行以起拍价拍得商品房数套,并当场转让获利数十万元。公安机关移送后,审查起诉的检察机关以“强迫他人退出拍卖属于修正案新增加的行为类型”为由,认为“行为时法无明文”不为罪,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这个案件中的行为,在形式上看的确属于《刑修八》增加的“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类型,而且条文的描述还具有明确的针对性。然而,这个案件能够简单地说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认为无罪吗?我们认为不能!为什么?我们审视一下行为实施时的刑法,也就是修正之前的条文,当时的条文就有“强买强卖商品” 这样的规定,而案件涉及的商品房无疑属于“商品”,拍卖不过是买卖的一种程序或形式,行为人以对竞拍人或拍卖师实施暴力、威胁的方法强买商品房,当然就是“强买强卖商品”。也就是说,即使行为时法(即修正之前的刑法第256条)规定的“强买强卖商品”也同样具有针对性(尽管不是那么明确)。因此,该行为无论根据行为时法还是裁判时法都是有罪的,且法定刑一致,对其适用修正之前的刑法第256条定罪处罚就是正确的。而不是说行为时法认为无罪,裁判时法认为有罪。
当然,这里涉及刑法用语含义的相对性问题:修正之前刑法第226条的“强买强卖商品”包括“强迫他人退出拍卖”在内,但修正后刑法第226条的“强买强卖商品”则不包括“强迫他人退出拍卖”,因为后者已经为独立类型了。2014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强迫借贷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迫他人借贷,属于刑法第226条第2项规定的“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以强迫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将来如果刑法修正案“强迫他人借贷”作为一个新的类型独立出来了,其意义也是形式上的。
所以,有关修正案的内容,特别是构成要件、量刑情节的修正,一定要善于甄别,对于我们所要处理的案件、所要评价的行为来说,带来的到底是发生了从无罪到有罪、或者从有罪到无罪这样的实质上的变化,还是只是变换了罪名(如嫖宿幼女行为被评价为强奸罪),甚至罪名都没有发生变动(如上述强迫交易罪行为类型的增加)这样的形式上的变化!不应从文字的形式上就轻易得出发生了根本性评价差异的结论。
事实上,采取修正案修改刑法之前的刑法修改活动中,对构成要件的设置,本身也具有相对性、动态性,一些行为在修改前后都是有罪的,不过变换了罪名或者构成要件类型发生了变化。比如,绑架犯罪设立前后的抢劫罪之构成要件:绑架犯罪设立之前,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涵盖绑架他人当场索取其相关人员财物的行为,因而,司法实践中,将许多绑架勒索行为认定为抢劫罪是恰当的。但绑架犯罪设立后,这部分行为改由绑架犯罪的构成要件来解释,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只解释以暴力(包括绑架)等方法当场取得被害人(包括被绑架人)财物的行为,由此也产生了抢劫罪与绑架犯罪的区别。*在此使用“绑架犯罪”一词而非“绑架罪”,主要是因为现行刑法规定的绑架罪,并非完全由1997年刑法新设,其渊源于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该《决定》设立了绑架妇女、儿童罪和绑架勒索罪,前者是指以出卖为目的的绑架妇女、儿童行为,后者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行为(对象不限于妇女、儿童)。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绑架妇女、儿童罪纳入拐卖妇女、儿童罪之中作为严重情节,对绑架勒索罪扩大外延,增加了“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类型。因此,实际上《决定》增设绑架勒索罪后,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就发生了变化。然而,我们并不能在绑架罪设立后,认为以往在没有绑架罪的立法框架下将绑架勒索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存在不当。因此,实践中,一些实施绑架勒索行为被认定成立抢劫罪的犯罪人,在绑架犯罪设立后以自己的行为当时无罪为由提出申诉,是不应得到支持的。
怎样去甄别对行为评价带来的是形式变化还是实质变更呢?基本的把握有两点:一是分析这个条文原本是要保护什么法益,为什么要作出规定,作出这样修正的目的是什么,探究刑法规范的目的;[1]二是考虑修正案增加的要素,它的语言文字含义在修正前的条文中是否本身就解释得出来、可以包含。就删除的文字而言,删除文字所包含的评价要素在现有的(包括修正前原有的和新增的)其他规范中是否可以得到解释?
刑法规范都是为了保护法益而设立的,具体的某个规范都有其具体或特定的目的,刑法修正某个条文,必然有它特定的目的,我们应该结合立法背景(历史)、规范结构体系等因素探寻修正的目的。比如,强迫交易罪明确强迫他人参加或退出投标、拍卖的类型,还有强迫转让公司企业股份等,是为了更广泛地保护公平交易秩序;《刑修八》对盗窃罪增加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3种行为类型,也是要扩大盗窃行为成立犯罪的范围。所以,这些条文的修正有共同点——都是加强法益保护,扩大处罚范围。[2]但是,对于刑法修正增加要素的文字含义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强迫交易罪的修正只是在形式上将过去包含的东西分立出来、明确化。而盗窃罪就不同。《刑修八》施行之前刑法规定了两种盗窃类型:一是盗窃的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二是多次盗窃。前者注重的主要是客观的财物价值大小,财物价值是立法时衡量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程度的重要因素,后者强调的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即使盗窃的财物价值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但行为人多次盗窃,立法者认为也应当予以刑罚处罚。《刑修八》增加的3种行为类型各有意义:入户盗窃,强调的是行为人带着非法的目的进入他人的“户”盗窃,危及他人的居住安全,数额是否较大或是不是多次偷盗,都已经不重要;携带凶器盗窃,对财物及其所处环境具有破坏性,有的对人身安全也具有潜在的危险,所以也是一种可以单独评价为盗窃罪的类型;扒窃,有它的手段特点,往往还结伙作案,人们深恶痛绝,所以也单独规定为一种类型。这3种类型,不像商品房可以解释为商品、拍卖可以解释为买卖的形式,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无论怎么解释,都解释不到可以包含上面3种类型的任何一种的地步,所以,构成要素实质性地增加了。因此,《刑修八》施行前实施的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或扒窃,只有符合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这样的条件时才成立犯罪,如果这样的行为在《刑修八》施行前实施、《刑修八》施行后裁判,就要从旧,作无罪处理。
《刑修九》的修正内容,有形式上、也有实质性的修正。当然这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就具体的视角而言来下结论。比如,就单纯的虚假诉讼而言,如果以前这种行为也不符合妨害司法的一些罪名,如帮助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等罪,从有罪无罪角度说,《刑修九》的修正带来的就是实质上的变化,因为无罪变有罪了。但如果以前按照当时的刑法也成立某种犯罪,现在不过新增了虚假诉讼罪,那么在“有没有罪”这一点上是没有实质变化的。诉讼诈骗行为呢?可以十分肯定的是,修正前后的评价没有变化,事实上《刑修九》完全可以对诉讼诈骗问题不作规定。不能认为以前诉讼诈骗不是诈骗。诈骗罪的构成是: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他人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处分了财产,从而导致有人财产遭受损失。这里受骗的人和财产受害人既可以是同一个人,也可以不是同一个人。诉讼诈骗中,行为人欺骗了法官,法官是受骗人,法官基于错误的认识处分了被告的财产,财产被害人是被告。再如,以非物质形式帮助恐怖活动的,修正前符合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罪,或者因具体实施恐怖活动而成立的杀人、绑架、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帮助犯的,以这些犯罪的共犯论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行为,以前相当一部分是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罪或者杀人、绑架、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罪的预备行为,视情况判断是否具有可罚性。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为他人组织考试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以及非法出售、提供考试试题或答案的行为,在《刑修九》生效之前可能成立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或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在《刑修九》生效之后成立组织考试作弊罪或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此时,如果裁判时法处罚轻于行为时法,须适用裁判时法。*201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第6条对为他人组织考试作弊提供作弊器材等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是,仅就《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而言,类似的法律适用问题也很多,司法解释并未一一予以规定。总之,就一项有待评价的行为而言,相应的刑法条文或规范修正前后的评价有无变化,是怎样的变化,不能简单地从文字形式的变动去判断。涉及从旧兼从轻原则适用时,讨论到底是适用行为时法(旧法)还是裁判时法(新法因轻而从之),其前提是评价它的新旧法律规范在处断行为的结果上(包括是否成立犯罪、罪轻罪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更;反之,规范没有实质性变更,而仅有形式的变化,则无讨论适用旧法还是新法的余地。
二、面对刑事立法不断扩大处罚范围的趋势,刑事司法怎样正确实现立法目的
综观至今为止的9个刑法修正案,从罪名的增加这一点就可以轻易得出结论,刑罚处罚范围在不断扩大。另外,从原有的规范和新增加的规范在“可罚的违法类型”设置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们还通过几个途径扩大处罚范围:
一是在违法类型上突出行为本身的可罚性,强调行为无价值的立场。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行为应该被规定为犯罪,不像以往立法那样特别强调行为造成什么实际危害结果,而是关注行为(相对脱离结果、与结果相对分离的行为)本身就值得刑罚处罚,将其规定为犯罪的类型。这无疑会扩大刑罚处罚的范围。比如,对于盗窃、诈骗、抢夺这些行为,我们刑法过去都规定要数额较大才成立犯罪,后来逐渐把“多次盗窃” “入户盗窃”等并非强调结果的类型增设到构成要件中。《刑修九》增加的帮助恐怖活动罪,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强制猥亵、侮辱罪,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组织考试作弊罪、代替考试罪等考试犯罪,都没有要求特定的实际损害结果发生或“情节严重”才成立犯罪。结果,无价值走向行为无价值的趋势比较明显。
二是将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把刑法防线前移。如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这些犯罪的成立不仅不需要特定的危害结果,实际上本身原来是一些预备行为。预备行为实行化了之后,这些新的实行行为的预备行为就相应地可能成立预备犯或预备阶段的中止犯了。
三是将共犯行为正犯化。如帮助恐怖活动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过去,这些行为理论上值得处罚,实践中有的考虑情节较轻并没有处理。
四是不作为犯罪的增加。如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要求严重后果或者情节严重),拒绝提供间谍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要求情节严重)。这些是纯正的不作为犯罪,增加这种犯罪,无疑加大公民的社会责任,扩大了刑罚处罚范围。
面对上述立法不断扩大刑罚处罚范围的趋势,刑事司法如何正确领会立法精神、合理实现刑法目的?理论上和实务界有人认为,刑法的目的就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刑法第2条),既然立法在不断扩大刑罚处罚范围,那么我们司法必须顺应立法的趋势,尽可能地扩大处罚范围。[3]
我们主张,刑事立法已经在扩大处罚范围的观念指引下确立了相应的规范,那么这个规范本身就是已经扩大了处罚范围的,刑事司法只需要忠实于合理的刑法解释规则,在语言文字可能具有的含义内合理解释刑法,就正确地实现了刑法的目的。因此,对于那些存在扩大处罚范围初衷的规范,司法实践不能人为地再次扩大处罚范围,否则就超出立法的目的了。
以《刑修八》增加的危险驾驶罪为例。刑法把原本只实行行政处罚的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规定为犯罪,司法是不是也要尽可能地打击的范围大些、入罪的标准要松动些?实践中的情况是,一些地方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且基本判处实刑。一般都是按酒精含量作为量刑依据:115 mg/mL左右判1个月,140 mg/mL左右判2个月,185 mg/mL左右判3个月,210 mg/mL左右判4个月,300 mg/mL左右判5个月,几乎没有判缓刑的,更没有在检察院相对不起诉的。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主张一律入刑、判处实刑的主要理由,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第一,此罪法定最高刑只有6个月拘役,即使顶格判处实刑也不至于量刑畸重;第二,刑法没有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要“情节严重”,因此,不存在考虑情节而免刑的问题;第三,在司法实践中考虑情节轻重区分哪些不判、哪些判缓,不好区分,既然区分不好,就不要区分。
我们认为,上述3点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首先,法定最高刑较轻不能成为不得判处缓刑的理由,因为适用缓刑的犯罪恰恰就是轻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者尚且可以宣告缓刑,法定最高刑只有6个月拘役的为何就不得判处缓刑?没有道理;其次,刑法没有规定“情节严重”,在衡量醉驾行为是否成立犯罪或需要判实刑时也有必要考虑情节,因为刑法第13条对分则条文都有指导或约束意义,抢劫的行为尚且还有“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更不能排除;最后,以所谓情节轻重不好区分为理由否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免刑或适用缓刑,逻辑上更不能成立。刑法中有许多“不好区分”的疑难问题,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认真研究如何区分。事实上,在实践中,许多醉驾行为存在一些从宽处罚的特殊情节,比如血液酒精含量刚刚达到醉酒标准,没有造成他人任何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的后果,或者造成的后果特别轻微,认罪态度也很好;有的行为人酒后找代驾人员将车开进自家住宅小区后,因为自己车位被别人车辆所占,在代驾人员离开后自己仅仅实施了驾驶车辆停入车位的行为,等等,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考虑适用缓刑。
扒窃作为成立盗窃罪的行为类型后,理论上和实践中也发生了这样的争论:是不是扒窃成立犯罪不再需要考虑盗窃数额大小了?从实践的情况看,有的地方犯罪嫌疑人扒窃了十几元就被起诉了。我们认为,这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扒窃作为与数额较大、多次盗窃等并列的行为类型,虽然强调不需要考虑数额较大和盗窃次数的问题,但不考虑“数额较大”,并不是说对于扒窃的就完全不考虑其中的数额问题,没有其他一些特别的情节,扒了一块眼镜布、一张餐巾纸、一毛钱、一分钱也要予以刑罚处罚吗?即使站在行为无价值的立场,我们对于扒窃行为能否成立犯罪,也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不能因为刑法不要求情节,就完全不考虑案件的情节。从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看,对于非法制造、买卖枪支行为成立犯罪,司法解释还规定了一定的数量标准;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虽然刑法没有“数额较大”标准的限制,但司法解释还设置了数额的限制。
[1]肖中华.构成要件形式与实质的变更及其合理解释[J].政治与法律,2011(8):26-31.
[2]张明楷.盗窃罪的新课题[J].政治与法律,2011(8):2-13.
[3]王永茜.论现代刑法扩张的新手段——法益保护的提前化和刑事处罚的前置化[J].法学杂志,2013(6):123-131.
(责任编辑钟昭会)
2016-04-12
李岸曰(1961—),女,山东聊城人,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刑事法。肖中华(1970—),男,江西丰城人, 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刑法等。
DF01
A
1000-5099(2016)04-008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