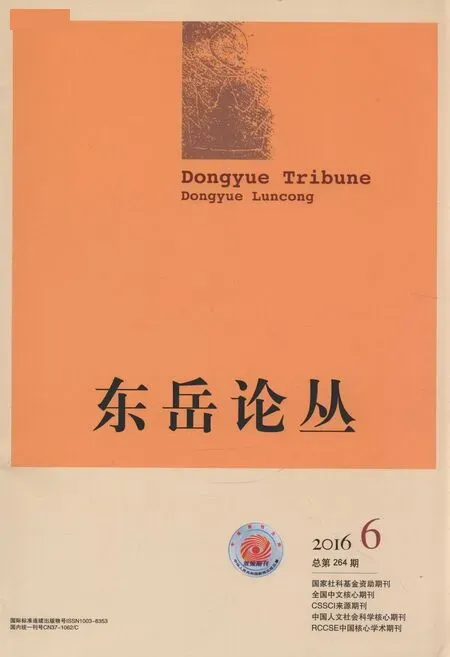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及其史料价值
李如冰
(1.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2.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文学研究
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及其史料价值
李如冰1,2
(1.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2.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南唐刘崇远的《金华子杂编》,保存了较为丰富的晚唐五代史料,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文学风尚等都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主要体现在:一是记载了帝王、藩镇、官宦的言行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客观反映了晚唐五代社会现实,有政治资料价值。二是记载了晚唐五代文人轶事及文学活动,有助于研究作家作品及创作情况,有文学资料价值。三是记载了唐代科场轶事、士族风尚、民间娱乐等内容,有社会风俗和文化资料价值。
刘崇远;《金华子杂编》;晚唐五代史料
《金华子杂编》为五代时期一部重要的笔记著作,作者为南唐刘崇远。刘崇远“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释羇鞅于放牧间,读其书,想其人,恍若游于金华之境”①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序》,见《全唐五代笔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8页,第3128页,第3129页。,于是自号金华子,并因以名书。刘崇远生平事迹史无明载,根据陶敏先生的考证②详见陶敏:《刘崇远及其著作考略》,《云梦学刊》2006年第6期。,刘崇远系出河南刘氏,为唐昭宗宰相刘崇望从弟。黄巢之乱,刘崇远一家避乱江南。迁居江南数年之后,大约在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前后,刘崇远在江南出生。童年受到良好教育,但其仕途却并不如意。大约在吴睿帝顺义四年(924)或稍后,已经三十多岁的刘崇远才步入仕途,“莅官于畿甸”③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序》,见《全唐五代笔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8页,第3128页,第3129页。,“承乏丹阳”④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崇远犹忆往岁赴恩门请,承乏丹阳。”见《全唐五代笔记》,第3143页。。后仕南唐,为上饶、晋陵二县令⑤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有“予宰上饶日”“予往岁宰于晋陵”之语,分別見《全唐五代笔记》,第3148页、第3150页。,在外二十余年。南唐中主保大(943-957)年间,罢秩归京,任大理司直⑥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序》署名作“文林郎大理司直刘崇远撰”,见《全唐五代笔记》,第3129页。。在此期间,刘崇远“以坐遇明盛时而抱名称不闻于世”,“因念为童时,侍立长者左右,或于冬宵漏永,秋阶月莹,尊年省睡,率皆话旧时经由,多至深夜不寐。始则承平事实,爰及乱离,于故基迹,或叹或泣,凄咽仆隶。自念髫龀之后,甚能记听。今虽稚齿变老,耄忘失忆,十可一二,犹存乎心耳。并成人游宦之后,其间耳目谙详,公私变易,知闻传载,可系铅椠者,渐恐年代浸远,知者已疏,更积新沈故,遗绝堪惜,宜编序者,即随而释之云尔。”⑦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序》,见《全唐五代笔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8页,第3128页,第3129页。因此,《金华子杂编》为刘崇远晚年追忆童年时听闻故老谈话及成人游宦后所见所闻之作。其资料来源可靠,因此保存了晚唐五代时期一些珍贵的史料。
《金华子杂编》原书已佚。《崇文总目》卷二传记类下著录《金华子杂编》三卷,《宋史·艺文志五》小说家类、郑樵《通志·艺文略三》杂史类均有相同著录,《宋史·艺文志》标明作者为刘崇远,《通志》则云:“伪唐刘荣(崇)远记大中、咸通后事。”⑧郑樵:《通志》卷六五《艺文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衢本《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金华子》三卷,提要云:“右唐刘崇远撰。金华子,崇远自号也。录唐大中后事,一本题曰《刘氏杂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金华子新编》三卷,云:“大理司直刘崇远撰。五代时人,记大中以后杂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明《文渊阁书目》《秘阁书目》子杂类有刘崇远《金华新编》三册。以上各书著录虽书名不同,实为一书则无疑。胡应麟(1551-1602)《九流绪论》尚提到此书,但此后即不见于各家书目著录或相关文献记载。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其佚文六十余则编成二卷,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读画斋丛书》本、《函海》本、《反约编丛书》本、《榕园丛书》本等,均源于《四库全书》本。《读画斋丛书》本因刻入了周广业校注,补充了部分佚文,尤为世所重。陶敏先生主编《全唐五代笔记》,其中《金华子杂编》的校注即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校以《读画斋丛书》本。
对《金华子杂编》一书的性质,历来认识不一。从以上各目录学对此书的归类即可看出。有的其归入杂史类,有的将其归入小说类,有的则将其归入子杂类。这与该书内容较为驳杂有关,如宋濂即认为其“驳乎不足议”*宋濂:《文宪集》卷二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胡应麟则斥其“猥浅不足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八《九流绪论》中,上海书店,2001年版。,而四库馆臣则认为其“其中于将相之贤否,藩镇之强弱,以及文章吟咏、神奇鬼怪之事,靡所不载,多足与正史相参证。”*清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中华书局,1997年整理本。并指出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亦从中取材。笔者则认为,《金华子杂编》不仅可补正史之缺,而且有着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一、政治资料价值
《金华子杂编》内容丰富,举凡君主功过、朝廷掌故、将相贤愚、官宦治迹、民间舆论都有所反映,是我们了解晚唐五代社会政治的一面镜子。
如李昪为南唐先主,正史视其为“僭伪”,对其功绩往往一笔带过。而《金华子杂编》卷上第一条却为我们生动描述了李昪重视文教的举措,“悬金为购坟典,职吏而写史籍”,以及南唐文化复兴的盛况:“由是六经臻备,诸史条集。古书名画,辐凑绛帷。俊杰通儒,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咸慕置书。”*⑦⑧⑨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第3129页,第3133页,第3134页,第3145页。这些记载无疑为我们了解南唐文化发展的社会政治因素提供了重要信息。
《金华子杂编》记唐宣宗政治情况颇多,如卷上十一条记宣宗批评令狐绹擅自移授:“朕以比来二千石多因循官业,莫念治民,故令其到京,亲问所施设理道优劣。国家将在明行升黜,以苏我赤子耳。德音即行,岂又逾越?宰相可谓有权!”⑦令狐绹闻言流汗浃洽,重裘皆透。书中对宣宗的评价甚高:“宣宗临御逾于一纪,而忧勤之道始终一致。但天下虽宁,水旱间有。大中之间,越、洪、潭、青、广等道数梗,以上之恭俭明德,始无异心。方隅诸将,虽失统驭,而恩诏慰抚,不日安辑。舆论谓上为‘小太宗’。”⑧唐代自宣宗之后即一蹶不振,唐代遗民眷念故朝每钟情宣宗,故津津乐道于宣宗治迹。
《金华子杂编》对晚唐五代时期国家重大历史事件亦有反映。如卷下十二条记黄巢之乱,且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于君也,善则归服,恶则离贰。始盗贼聚于曹濮,皆承平之蒸民也。官吏刻剥于赋敛,水旱不恤其病馁,父母妻子,求养无计。初则窥夺谷粟,以救死命。党与既成,则连衡同恶,跨山压海,东愈梁宋,南穷高广。蟒喙嘘天,翠华狼狈而西幸;豺牙烁日,齐民肝脑以涂地。酆镐陵夷,往而不返矣。世之清平也,搢绅之士,率多矜恃儒雅。高心世禄,靡念文武之本,群尚轻薄之风。莅官行法,何尝及治?由是大纲不维,小漏忘补,失民有素,上下相蒙。百六之运既遭,翻飞之变是作。”⑨比较客观地揭示出黄巢之乱发生的社会原因,有益于对这一深刻影响唐王朝历史走向的重大事实的理解。
晚唐时期,藩镇林立,但相关文献不多。正史多着眼于藩镇的“跋扈”,而《金华子杂编》却记载了藩镇的另一面。如记载青州藩镇王师范对新到县令“必备仪注,躬往投刺”,能用礼正身;而且“性甚孝友,而执法不渝”,在舅父杀人事件中秉公裁断,竟令舅氏伏法。这一行为颇得地方民众的赞赏,“至今青州犹印卖王公判事”*②④ 《全唐五代笔记》,第3130页,第3130页,第3132页。。类似这样的记载有利于全面了解藩镇这一历史形象及藩镇在势力范围之内的统治情况。
二、文学史料价值
《金华子杂编》记载了很多晚唐五代文人轶事,有助于研究作家生平、交游和创作情况。如:
段郎中成式,博学精敏,文章冠于一时。著书甚众,《酉阳杂俎》最传于世。牧庐陵日,常游山寺,读一碑文,不识其间两字,谓宾客曰:“此碑无用于世矣,成式读之不过,更何用乎!”客有以此两字遍谘字学之众,实无有识者,方验郎中之奥古绝伦焉。连牧江南数郡, 皆有名山,九江匡庐、缙云烂柯、庐陵麻姑,皆有吟咏。前进士许棠寄诗云:“十年三领郡, 郡郡管仙山。”为庐陵顽民妄诉,逾年方明其清白,退隐于岘山。时温博士庭筠方谪尉随县,廉帅徐太师商留为从事,与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学相遇。常送墨一铤与飞卿。往复致谢,递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为其子安节娶飞卿女,安节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乐府新录》行于世。②
这段文字是研究段成式、温庭筠生平、创作及相互交游的重要资料。《旧唐书》记载段成式“咸通初,出为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阳,以闲放自适。”*《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七,中华书局整理本。但并没有说明解印原因。《金华子杂编》则说明“为庐陵顽民妄诉,逾年方明其清白。”故解职闲居。《新唐书》《旧唐书》对温庭筠的生平记载有分歧,对于其何时赴襄阳徐商幕府语焉不详。学界对此也争执颇多。《金华子杂编》的这段记载则明言温庭筠赴徐商幕府在谪尉随县之后。并且记载了温庭筠与段成式的密切交往情况,不但互赠礼物,来往唱和,还结为儿女姻亲。其唱和文字达九函之多,均收入《汉上题襟集》。这对研究温庭筠、段成式等人的襄阳唱和及业已失传的《汉上题襟集》亦很有价值。文中还提到段成式《酉阳杂俎》及其子段安节《乐府新录》在当时的流传情况。
杜牧是晚唐著名诗人,研究者众多。但对其卒年认定一直有分歧。《金华子杂编》卷上三十三条记杜牧临终事,透露了杜牧卒年信息,是研究杜牧生平的重要资料。书中还多处记载杜牧事。如其与韦楚老同年生,情好相得。其子杜晦辞大有父风等。
更可贵的是,《金华子杂编》在记载文人轶事时还照录了一些作家的作品,可供辑佚和校订。如卷上第三载陆翱事,录其《闲居即事》《宴赵氏北楼》二诗,这两首诗是陆翱目前仅存的两首诗,正是赖《金华子杂编》保存至今。书中还提到陆翱擅长咏物诗,有《鹦鹉》《早莺》《柳絮》《燕子》等诗,當時甚播於人口。惜今已不存。卷下第二十一条引顾况集中文字,为今传顾况集中所无,可供辑佚。卷上第九条,杜悰镇淮海,耽于燕乐,有“狱市”之谓,宣宗闻之,即以崔铉代杜悰。该条载宣宗李忱赐崔铉诗落句云:“今遣股肱亲养治,一方狱市获来苏。”④与《全唐诗》所录残句“七载秉钧调四序,一方狱市获来蘓。”不同。“七载秉钧调四序”亦见于《旧唐书·崔铉传》和《唐诗纪事》所载,但并无下句。“今遣股肱亲养治”句则仅见于本书。因此可供辑校。又如卷下第三记李郢事,不但照录了《寄内》《宿虚白堂》二诗原作,而且详细说明了这两首诗的创作由来及背景。可供辑校和研究。
《金华子杂编》还保留了一些仙话传说。刘崇远信奉道教,书中多记一些神仙鬼怪之事,也许正因如此,明代胡应麟斥其“猥浅不足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这部分内容如果从史学角度来说,当然是荒诞不经。但从文学角度来说,书中保留的这些仙话和民间传说却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如卷下之二十三:
沂、密间有一僧,常行井廛间。举止无定,如狂如风。邸店之家,或有爱惜宝货,若来就觅,即与之。虽是贵物,亦不敢拒。旦若舍之,暮必获十倍之利。由是人多爱敬,无不迎之。往往直入人家,云:“贫道爱吃脂葱杂面饦,速便煮来。”人家见之,莫不延接。及方就食将半,忽舍,起而四顾,忽见粪土或干驴粪,即手捧投于碗内,自掴其口,言曰:“更敢贪嗜美食否?”则食尽而去。然所历之处,必寻有异事。其后河水暴溢,州城沈者数版。州人恐惧,皆登陴危坐,立于城上。水益涨,顷刻,去女墙头数寸。城人号哭,数十万众,命在须臾。此僧忽大呼而来,曰:“可惜了一城人命,须与救取!”于是自城上投身洪波中,躯质以沈,巨浪随陷五尺。及日晚,城壁皆露。明旦,大水益涸。州人感僧之力,共追痛,相率出城,沿流涕泣而寻其尸。忽于城西河水中小洲之上,见其端然而坐,方袍俨然。大众欢呼云:“和尚在。”就问,则已溺死矣。乃以辇舆舁起赴近岸,数百之众,莫可举动。又其洲上淤泥,不可起塔庙,相顾计议未决。经宿,其涂泥涌,高数尺,地变黄土,坚若山阜,就建巨塔,至今在焉。*②③ 《全唐五代笔记》,第3149页,第3134页,第3136页。
文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举止无定,如狂如风”,关键时刻却能以死济人的神僧形象。类似的神僧形象无论是《高僧传》等佛教典籍中,还是在文人笔记、民间传说中都有。但具体情节却又各不相同。刘崇远所记应是当时流传甚广的一个民间传说版本。
又如卷下第二条的胡人识龟宝故事、卷下第二十六条的凤雏传说、卷下第二十八条的海眼传说,都是民间传说中的常见题材,这些记载既启发了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为我们深入研究仙话传说提供了可贵的文献资料。
三、社会风俗和文化资料价值
《金华子杂编》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典章制度和社会风俗习惯,是研究当时社会风尚的珍贵资料。
唐代的科举制度本为拔擢寒门才俊所设置,但中晚唐之后,这一情况起了变化。一方面进士地位提高,更多宰辅出身于进士。另一方面由于宣宗取消了科举制度对士族子弟的限制,导致宣宗大中以后,权豪子弟鹜趋进士科。《金华子杂编》对这一科举风尚变化有具体生动的记载。如卷上第十四条记“崔郑世界”:“崔起居雍,甲族之子。少高令闻,举进士。擢第之后,蔼然清名喧于时,与郑颢同为流品所重。举子公车得游历其门馆者,则登第必然矣。时人相语为‘崔郑世界’,虽古之龙门,莫之加也。”②卷上第二十条“点头崔家”:“崔雍为起居郎,出守和州。遇庞勋悖乱,贼兵攻和。雍弃城奔浙右,为路岩所构,竟坐此见害。雍与兄朗、序、福昆仲八人,皆升籍进士,列甲乙科,尝号为‘点头崔家’。”③这些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中晚期世家大族势力渗进科场而使家族更为煊赫的现实。是研究唐代士族与科举制度的重要资料。
对唐代世家大族的人情冷暖,《金华子杂编》也有记载。如卷下第一条记琅邪及太原王氏、博陵及清河崔氏等世家大族:
琅邪王氏与太原同出于周。琅邪之族世贵,尝有“锥头”之名。今太原王氏子弟,多事争炫,称是己族,其实非也。太原贵盛之中,自有“钑镂”之号。而崔氏博陵与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大房、第二房虽长,今其子孙即皆拜三房子弟为伯叔者,盖第三房婚嫁多达官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倨受大房二房之礼。清河崔氏亦小房最专清美之称。崔程即清河小房。世居楚州宝应县,号八宝崔家。宝应本安宜县,崔氏曾取八宝以献,敕改名焉。程之姊,北门李相国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盐铁,程为扬州院官,举吴尧卿,巧于图利一时之便,蔚以为得人,竟乱筦搉之政。程累牧数郡,皆无政声。小杜相公闻程诸女有容德,致书为其子让能取焉。程初辞之,私谓人曰:“崔氏之门着一杜郎,其何堪矣?”而相国坚请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宝应诸院间取一弟侄,以应命而适之。其后让能显达,封国夫人,而程之女竟无闻焉。*②③④《全唐五代笔记》,第3141-3142页,第3138页,第3137页,第3144页。
像王、崔、李等世代贵盛的显赫家族,至唐代中晚期,其处境已今非昔比。崔、李二家族只因三房多达官,便可倨受大、二房之礼。“累牧数郡皆无政声”却仍抱着门第观念不放的崔程因看不起新贵而葬送了女儿的幸福。可见唐代门阀世家已不能仅靠家世立足于世俗社会,想要维持门第尊严,还需要官位显达。这些记载对研究唐代门阀世家及新兴士族风尚有重要参考价值。
《金华子杂编》中还保存了有关唐代社会文化娱乐的资料。这些民间的娱乐方式在正史之中往往很少记载,因此《金华子杂编》的这类记载就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卷上第五条记载端午节习俗:“每先数日,即于湖沜排列舟舸,结络彩槛,东西延袤,皆高数丈,为湖亭之轩饰。”反映了杭州端午节竞渡的盛况。卷上第二十五条,记载“长安坊巷中有拦街铺设,中夜乐神,迟明未已”②。则是反映长安城的夜生活。
唐代有一种进行滑稽表演的伶人,其特点是以语言表演见长,以戏谑娱人为事。《金华子杂编》卷上第二十三条,记载伶人赵万金察言观色,即兴口号表演“相公经文复经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闻阿舞婆,如今亲见阿婆舞。”令赵国公李绅“冁然久之”③。卷下第七条,记载伶人孙子多的即兴表演“风貌闲雅,举止可笑。参拜引辟,献辞敏悟”④。这些记载不但使赵万金、孙子多流芳后世,也让我们一窥唐代伶人滑稽表演的风貌。
唐代重视马政,尤重个人马术的训练。唐玄宗曾发布诏书将马球运动推广至军中。这既有利于将士身体素质、反应能力的提高,又能提高策马作战的能力,有助于作战水平的提高。而马球技艺高超的将士,还可以得到破格提拔。因此,马球运动很快在军中流行起来。《金华子杂编》就记载了周宝的马球技艺。
周侍中宝与高中令骈,起家神策打球军将,而击拂之妙,天下知名。李相国都领盐铁,在江南,驻泊润州万花楼观春。时酒乐方作,乃使人传语曰:“在京国久闻相公盛名,如何得一见?”宝乃辍乐命马,不换公服,驰骤于彩场中。都凭城楼下瞰,见其怀挟星弹,挥击应手,称叹者久之,曰:“若今日之所睹,即从来之闻犹未尽此之善也。”
这些记载反映了马球这项体育运动在唐代的勃兴,而且对于研究马球运动与唐代军政的关系也是珍贵的资料。
另外,《金华子杂编》记载了一些当时的社会习语,并做出了解释,对我们理解相关文献并理解其背后的史实大有禆益。如卷上第十二条记二十条关于“辱台”:“旧俗,除亚相者,百日内,若别有人登庸,谓之‘辱台’。”卷下第十八条“恩府”:“以恩地为恩府,始于唐马戴。戴大中初为掌书记于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贬朗州龙阳尉。戴著书,自痛不得尽忠于恩府,而动天下之浮议。”即说明了恩府即恩地,也涉及到唐代官场习俗。
除以上所述之外,《金华子杂编》还有一些其它方面的资料,如卷下第二十二条记新安仙源及信州灵山令居人长寿,说明自然环境与人寿命的关系。卷下三十一条记生附子之药性,可供中医借鉴等等。相信随着研究的进展,《金华子杂编》的价值会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
[责任编辑:曹振华]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委托项目(项目号:10@ZH011)、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2013335,依托单位:运城学院)成果。
李如冰(1974-),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I206.2
A
1003-8353(2016)06-008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