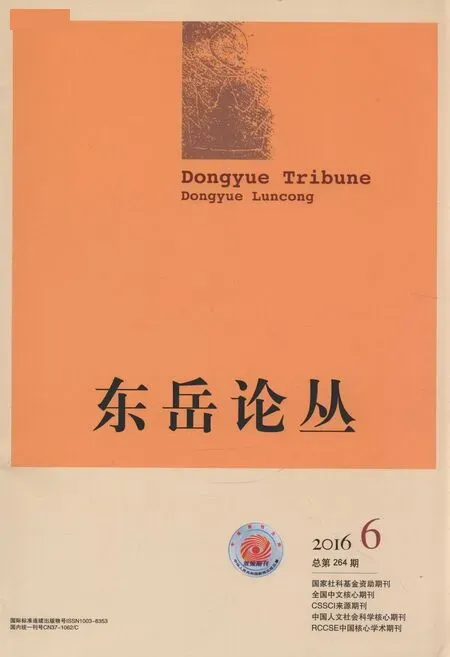试论“颜回之乐”的本质及其“归仁”的途径
——兼谈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证道追求
秦大忠
(山东大学出版社,山东 济南 250014)
哲学研究
试论“颜回之乐”的本质及其“归仁”的途径
——兼谈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证道追求
秦大忠
(山东大学出版社,山东 济南 250014)
自宋代学者周敦颐提出“孔颜之乐,所乐何事”的命题以来,历来研究者甚众,诸研究者从儒学、玄学、理学、心学以至于近当代的心理学、美学等各个角度切入并立论,给人以诸多有益的启示。但是,关于颜乐的本质、实现这种乐的根本途径以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的研究仍显暧昧或不足。实际上,“颜回之乐”本质上是一种离开了二元对立的、不依于任何外在因缘的至乐,而“克己复礼以归仁”就是实现这种至乐的基本途径。同时,只有从悟道和证道的角度来理解“颜回之乐”,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孔颜之道作为圣贤之道的本来面目。
儒家思想;颜回之乐;本质;实现途径;传统文化;证道追求
颜回(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1年),字子渊,又称颜渊,春秋时期鲁国人,历来被认为是孔子七十二位最贤良的弟子之首,又往往被作为孔门“德行”科的代表性人物。的确,颜回令当时以至后世的学人士子以至普通百姓尊敬和爱戴,固然主要靠其自身的高尚德行,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师孔子的不吝赞美密不可分。孔子肯定颜回的安贫乐道,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称赞他为人谦逊好学,与人为善,精进不辍,所谓“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赞赏他异常尊重老师,对老师之教无不悦服,却并非唯唯诺诺,而是在实践中力行老师的教诲,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等等。孔子更总赞颜回“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一、颜回之乐,所乐何事
孔子为什么会这样高调地称赞颜回,而且又在各种场合不断地称赞颜回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颜回是一个能够体认大道并能够“乐道”的人!这一点,只要考察一下孔子所称赞的具体是什么,就十分清楚了。孔子十分看重颜回,主要是由衷地赞叹其“不改其乐”,是称赞他不因时因地因处境不同而有任何改变地“乐”着,这个乐,颜回时时有、处处有,正如孔子所赞叹的那样——“其心三月不违仁”①长久地契合于仁之道。孔子对于自己的弟子,以“仁”相赞的似乎只有颜回一位。比如《论语·公冶长》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路、冉求、公孙西三人,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孔子对这三个人的才能,了如指掌:子路善治军,冉求善理政,公孙西善于交际,而孔子却不能确认这三位学生是否达到了仁这一境界,可见孔子心目中仁的标准是很高的。,即是言其能时时处处安住于“仁”这一至道,时时处处乐道而不动摇,不因穷通利害而有任何改变*关于“乐为仁中自有之乐”,明代的曹端即持此种观点,认为颜回在仁的道德实践中体会到了无忧的乐处。参见汤一介等:《中国儒学文化大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而这种不依因缘(外在的条件)而常在的乐也只能来自于“悟道”,正如孔子自言“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孔颜乐处”这一形而上的课题并进行探讨的,是北宋时候的理学家周敦颐,他说“颜子箪瓢,非乐也,忘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大学·中庸·孝经》,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9页。,也就是说,颜回并不是以相对的苦乐为苦乐,而是安住于忘我悟道之乐中,这种“乐”完全与一般的苦、乐无关,既不依一般的乐缘而乐,又不以一般的苦受为苦,而是一以贯之的契道之乐,即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大学·中庸·孝经》,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9页;杜豫,刘振佳:《“颜乐”新探》,载《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第24-27页。,换句话说,能享受到这种乐的人,无论处在何种境况下都能与道契合、自得其乐。应该说,“孔颜之乐,所乐何事”这一命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内在精神进行深刻反思和探究的结果。
当代许多学者也对“孔颜之乐”多有探讨。有学者从孔子和颜回的好学切入,透过其好学解读出其所好的是对绝对化的知识及知识乐境的追求,认为相对于个体生命和社会现实而言,知识的本体为道体,真正的君子都是在真理性的知识、智慧追求过程中实现内圣,并同时尽享所感知的纯粹快乐的。孔子和颜回都是纯粹追求学“乐”和“乐学”的人,而结果他们也确实实现了自己的“内圣”理想,都成了乐道的人*杜豫,刘振佳:《“颜乐”新探》,载《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第24-27页。。应该说这一看法是相当有道理的,问题只在于其忽略了在知识体系以外道体也同样普遍存在并可以被体证这一事实,逻辑上显得不够严密。又有学者在对“礼”和“仁”进行详细阐释的基础之上,指出颜回由礼而入仁,终其一生实践了其师孔子所推崇的“性与天道”,找到了自得其乐的精神家园,实现了自身的高度和谐,与此同时,这种完全“向内”的实践也同时成就了“外王”与“内圣”的统一,即独善其身已足可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境地,而这就为“文化中国”的形成奠定了深刻的文化底蕴*孔德立:《从“孔颜乐处”诠释儒家的和谐思想》,载《齐鲁学刊》,2007年第2期,第18-22页。。应该说这一认识是相当独到而深刻的,而把“孔颜乐处”作为儒家和谐思想的重要范畴也是比较精准的,特别是这位学者对子思、孟子的思孟学派以至颜氏之儒有可能转入庄周学派的问题进行了考证,并依此认为儒家的精神家园就在以实现自身和谐为指归的“孔颜乐处”,亦给人以较大启发。但令人稍觉不足的是,虽然该研究也明确指出了“仁”是道体,但对如何“因礼而入仁”、“契道方得至乐”等问题的阐述显得不够充分,因而有进一步进行阐述的必要。此外,还有学者将颜回之乐与颜回之勇进行对比分析,认为颜回知、行合一,其乐是在个体不断进行自我超越后获得的情感享受,是由于体悟了道而契入的一种“内圣”之乐,而其乐和勇则统一于以内圣为终极目标的人生践行中*万春香:《管窥“圣徒”颜回之乐与勇》,载《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该研究者初步接触到了颜回之乐的实质,特别是明确提出了“颜子之乐是乐在其内在的精神境界超越了外在环境”的观点,而其之所以实现了超越,则正是因为坚信“夫子之道”是普遍的大道并终其一生努力体证的结果,这些都是比较新颖和深刻的认识。
事实上,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颜回的乐道及孔子对他的激赏并不是一个孤例,而是可以说,在至少已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化发展和传承过程中,世世代代的求学者都似乎本然地存在一种求道和证道的内在诉求,即根本上不以获得外在的知识和技能为能,而是以悟实相、开本智、得至乐为根本目的。甚至可以说,追求个体的证道并乐在其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道统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道统。春秋时的颜回是这样,东晋时的陶渊明也是这样。但是对于这一点,后来者的体悟逐渐变得没有那么深刻,因此,对于这一道统的认识也渐渐流于肤浅,对于以颜回、陶潜为代表的向道、乐道者的内在精髓了解不够,世俗社会中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矮化甚至贬低的倾向。这是很令人惋惜的。
本文拟主要以《论语》的若干记载以及部分有关“颜回之乐”的先行研究为基础资料和相关佐证,对颜回之乐的本质进行较为深入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实现“乐道”的手段——“归仁”进行分析,最后就颜回的乐道及归仁对后世的积极影响及其现实意义进行相关的探讨。
二、颜回之乐的本质:不依于外在因缘的至乐
儒家思想一般被认为是入世的,但实际上儒家的最高追求是离开出世和入世两边而契入圣道,而且儒家认为,只要契入了圣道,就会获得人生的至乐,也只有契入圣道,才能真正做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这一点,孔子曾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这就是说,无论是行(入世),还是藏(出世),都不妨碍契证圣道,并安住于悟道行道的至乐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孔颜之乐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作为苦的对立面而存在的相对的乐,而是一种离开了苦、乐两边的至乐或极乐。这种乐的获得,不依赖于外在的贫富、穷通、顺逆等因缘或条件,比如说贫穷困顿时可以怨天尤人(苦而不乐),也可以乐天安命(不改其乐);富贵通达时可以为富不仁(不知正道,不晓真乐),也可以富而好礼(能行圣道,能得真乐)。换句话说,这种乐的获得与否,与一切外在的条件都没有关系,而实际上只需要一个根本条件,那就是:自在的、内发的、智慧的觉醒!换句话说,一定要悟圣道,行圣道!而要想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先对孔子一生所学、所行有个比较深入的了解才行。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孔子的一生,那就是“力行教化”,无论是游历各个诸侯国,还是后来的杏坛讲学,都不出“教化”的范畴:或教化诸侯,或教化百姓,或教化学生!但这里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是:孔子所教化的到底是什么?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承认的事实是,孔子在教化方面是主张有教无类的,即所有的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同时他又主张因材施教,即结合受教育者不同的根基、程度而展开差异化教学活动。因此,从《论语》中我们看到,孔子对不同求教者的不同提问,在回答时也确实千差万别,但似乎各种回答都能令相应的提问者有所获益。我们不禁要问,孔子何以能无所不知一般地进行教化活动呢?这在根本上又离不开一个大前提,即孔子本人对于大道之极深的领悟!他所行的教化,也不过是不离“大道”而针对不同程度的求教者进行相应的启发和教诲。如果不悟道,那么孔子的所谓教化就都不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论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若对上下文的文义进行综合考察,就会发现这里的“学”显然并不是指一般的学问,而是“觉悟之学”的意思,是悟道、行道的意思。只有这样解才能真正讲得通,才能避免出现矮化圣人境界的情况。基于这一认识,这一段的本义似可解释为:我十五岁就有志于觉悟大道的希圣之学,三十岁就树立起正知正见,到了四十岁就断除了一切疑惑,五十岁时就明白了自己人生的天命,六十岁时就于一切顺逆境界都能平等对待,七十岁后心就完全与道相契合而达到一种既自由自在又完全不与世俗相违的境界。而且孔子也曾自己道出一种“无知而无所不知的”的“得道”境界:“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唯其因为无知,心中“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或成见,所以当有人向其问道时,孔子才能“叩其两端而竭焉”,非常圆满地回答不同程度求教者的提问。
在真正了解了孔子之道以后,对于颜回之道也就不难理解了。毋庸置疑,颜回之道与孔子之道是一个,否则孔子便不会把颜回引为知己,并且从来不吝于赞叹颜回。那么在颜回的眼中,孔子之道又是什么样子的呢?颜回也自己说出来了。颜回曾喟然叹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仰之弥高”,说明先生之道不能见顶;“钻之弥坚”,说明先生之道不可动摇;“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说明先生之道不可把捉,不可思议。“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不知道该如何行先生之道。但这种道又不是什么也没有,因为它竟令人“欲罢不能”!这样一种玄妙的境界,实在令人心向往之。
综合考察孔颜之道,会发现这种道以及得道之后的那种乐是一种超越了外在的一切相和内心一切执著的悟境,是一种不依于任何外在条件的个体性体验,得道或得乐完全是一回事,也是同时发生的,是对一切内外境界进行形而上超越的结果。正如孔子评价颜回时曾说过的一句话:“吾见其进(超越)也,未见其止也。”这种“进”实际也超越了任何宗教的门户之见或者是任何学派的学术界限,而与所谓正法眼藏的禅宗非常接近。比如,《六祖坛经》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是不动……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六祖坛经》,王月清注评,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这里,六祖大师先是为“坐禅”正了名:不是执着于心,也不是执着于一个净相,也不是以常坐不卧等为能事,而是对着外面一切看起来或善或恶的境界都不起心动念,同时向内又能见到自己的本性是本来不动的。那么,如何修呢?本性人人具足、本来清净,因此从实际理体上来讲是本来无修也无证的,但为方便教化而说修说证,且这种修证的结果也不过是一种内在的发现而已:外应离相,因种种相本性空故;内应不乱,因本性本自清净寂定故。这种禅定的境界无所谓“在”或“不在”,也无所谓“有”或“无”,而只取决于一个人能不能悟到它(发现它),只在于能否获得真心本性上的超越性的大觉醒。看了这一段,再回头来看孔子与颜回之道,其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等特点便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也并非那么不可理解了。换句话说,孔颜之乐所赖以产生的道并不是具体的某一种学说或思想,而是那个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的纯粹的、超越性的觉悟之道。
三、颜回之乐的获得方法或途径:归仁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可见,孔子认为只有对于中等资质以上的人,才可以与其讲说最高层次的道。那么孔子与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之间,又是如何论道、特别是如何讨论悟道之根本途径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论语》的字里行间,也能窥得若干端倪。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在这一段中,最重要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仁是什么”,另一个是“归仁(发现和安住于仁)的途径是什么”。在儒家的语境中,“仁”可被看作“道”体,这一点基本已成公论。透过《论语》我们看到,孔子最为推崇的就是仁,仁可以说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也是孔子的最高理想。比如孔子曾非常明确地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这就是说,无论是礼还是乐,都要寄寓着、体现着仁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否则就难免流于空洞的形式,甚至对社会产生若干负面影响也未可知。由此可见,这个仁,正是孔子的道之所存、学之所本,明显具有形而上的性质。但是,围绕这个“仁”字,即使是孔子本人也有诸多解释,比如在答复学生樊迟时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这里的“爱人”可以理解为一种博爱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首先要自重己灵”,因为只有重视自己的性灵而悟得人我平等才可能真正达到博爱的境界。而孔子自己也曾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更可佐证孔子治学首重自觉、自悟的特点。孔子在另一场合论“仁”时则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这里则主要是讲“仁”的起用问题,只有体悟了仁之境界的觉悟者才能做到好恶有则、好恶有度。而到了颜渊问仁时,孔子的回答更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成了完全从“悟道、证道”的角度来解释仁的境界,并同时给出了达到这一境界的根本手段——克己复礼,就是说“仁”的起点和根本是“重己”,看重以至珍视自己的清净本性(仁),并通过克己复礼来回归那个不受染污的本性(归仁)。
对于此处的“礼”,按照一般的解释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是偏重于形式的一种东西,但在颜回问仁而孔子作答时,这个“礼”却更多地具有了实质性的意义,结合上下文来看,此处之“礼”显然并不是指一般的伦理道德规范,甚至也不是“秩序”的意思,而是“合于道之轨则”的意思。王阳明就曾提出“礼”通“理”的看法:“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而其在于人也,谓之性;其粲然而条理者,谓之礼;其纯然而粹善者,谓之仁……礼,无一而非仁,无一而非性也。”*《礼记纂言序》,《王阳明全书》(一),第12页;转引自秦家懿:《王阳明》,2011年版,第87页。也就是说,在王阳明看来,这个礼已经完全成为天道、天理的一种外化。这个解释是很令人信服的。而孔子与颜回接下来的问答,也足可证明这一点。颜回在已经大体了解了老师的真意之后,又问具体的下手方法是什么(“请问其目”)。对此,孔子的回答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分别对应着人的眼、耳、口、身,表面看起来是人感官边的事情,但实际上却是要做心地上的功夫,即从眼见、耳闻、言说、行动等各个方面加上一定的作意,这里的作意就是“克己复礼”。基于以上所作的分析,“克己复礼为仁”一句的根本义似为“克除自心虚妄的染污,使一切视、听、言、动都合于道的轨则”。所克之“己”,非道也;所复归之“礼”,真道也。换句话说,一方面,性德是人人皆具的本性,是人的本来面目;而另一方面,性德虽人人本有,却是须修方显的。注重并加强克己复礼的“修”德,就可助人证悟实际理体上的性德。在论语的语境中,这就是“归仁”。
由此可见,孔子与颜回论仁,实际上是在论道,仁的起点和根本是“重己”,而与人毫无干系,正如孔子当时即教导颜回的那样,“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其他场合,孔子又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教诲。这说明,达到仁的境界是一个完全个体的自由的过程,是不需要任何外在条件的,正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旦在克己复礼上做到了,即作为个体证悟且安住于大道了,就实现了“天下归仁”,即再也没有了对立,物与心、人与我,一切都圆融无碍了。这一点亦似可与佛教大乘经典《楞严经》的如来藏思想相印证——“汝等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皆悉消殒”*南怀瑾著述:《楞严大义今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92页。,物与我的界限完全消泯不见了。综合来看,只有从个体的悟道和证道的角度来理解“克己复礼为仁”,才能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孔子以“非礼勿视”等四个纲目来回答颜回的提问,同时,整个孔颜之道作为追求悟道、证道的圣贤之道的本来面目也才就此显露无疑。
实际上,中国儒家传统的求道和证道的手段就是“克己复礼以归仁”。只有人人都珍爱并看重、了解并体悟那个清净无染的本性,才是真正的归仁,也只有在真正归仁之后,才能真正推己及人。也正因此,以悟道、修道为终极追求的儒家人士才郑重宣示:“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四、颜回之求道与乐道对后世的影响
颜回所乐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唯一可谓一脉相承的东西,那就是求道、悟道、证道,乐道是儒家“内圣”思想的最具体、最根本的体现。而以颜回为代表的悟道、乐道的传统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影响至巨。
颜回以降,最能够体得颜回之乐的代表性人物似乎当数东晋时代的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⑤陶渊明:《饮酒》,《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1页,第151页。世人往往只留意到陶氏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认为他不与权贵同流合污,品质高洁。这固然也是不错的,却不是陶氏能归隐田园、永不再仕的最深层和最根本的原因。至于那个根本原因,其实是陶氏悟道了,能够在艰苦备尝的田园生活中乐而忘忧!“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陶渊明:《归园田居》,《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页。,可见生计不可谓不困难,劳作不可谓不艰辛;但是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⑤,显而易见,他所乐的是道,是只可身体、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大道。正是因为乐道,才能安贫,才能矢志不移,度过了诗酒田园的一生,自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渊明:《形影神·神释》,《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页。。诗可言志,亦可直接以志入诗。作为一位稍显与众不同(不仕而隐)的传统文化人,陶渊明就在自己的诗中明确地道出了心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页。可见,正是因为证悟了先师之道,得到了如孔颜一般的至乐之受,陶渊明才能在清苦的隐居生活中乐而不疲。
此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儒、释、道三教合流经常为人津津乐道。很显然,在这里儒、释、道并非作为三种类宗教的存在而是作为三种教化而被认知和接受的。而三教的最终指归都是悟道证道,而且在各家的著述中也有对于所证之道不二的重要论述。作为中国佛教文化之重要代表的禅宗的例子此前已经举出,在此再以道教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作为道教文化重要一支的全真教的代表性人物王重阳,就在自己的诗作中明确提出儒释道三教原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观点:“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悟彻便令自出入,晓明应许觉宽洪。精神气候谁能比,日月星辰自可同。达理识文清净得,晴空上面观虚空。”*《重阳全真集》卷一之《孙公问三教》,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03/09/1917612_36588948.shtml。作为道教重要一支的全真教的教主,心中却全无门户之见,这正是悟得一切学问之共同指归的那个“大道”的表征。也正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大道值得去悟解、去体证,中国传统文化才体现出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独有的特质,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之处。
再回到颜回之乐的起点,我们看到,只要求道、悟道、证道、乐道,在儒家“内圣”的一面就已经做到圆满了,作为个体的人生,也已经达到无怨无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了。而即便是就“外王”的一面来说,实现了证道、乐道之后则主要是看有没有机缘“传道、授道”了,所谓君子因时而动、顺天应人而已。而就行道的本义来说,个体的证道和乐道已经足够了,这和孔子的最高人生理想也是一致的,即“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证道与乐道的指归,就是人心与天下俱太平无事、熙熙而乐,如此而已!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要建设和谐社会,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首先搞清中华传统文化的真正的、最重要的道统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才能避免文化发展中的物质化和庸俗化倾向,而回复追求至道、至乐的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而颜回之乐以及孔子与颜回所主张的“克己复礼以归仁”的实现契道、安住至乐的根本途径,恰好可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和良好的借鉴。
[责任编辑:杨晓伟]
秦大忠(1971-),男,山东大学出版社编辑,日本东北大学博士。
B222
A
1003-8353(2016)06-003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