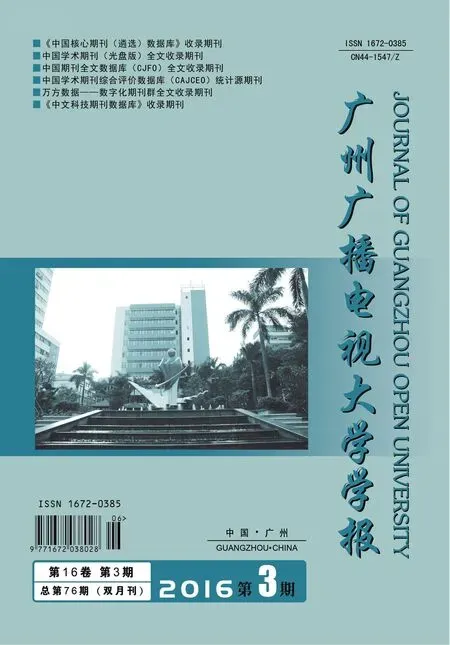“革命+恋爱”题材的现代诠释
——以格非的《人面桃花》为例
曹 琳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革命+恋爱”题材的现代诠释
——以格非的《人面桃花》为例
曹琳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人面桃花》是格非最接近传统的小说文本,作品沿用了流行于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恋爱”的小说创作模式,描述了一幅古代革命先贤追寻乌托邦生活的美好愿景,表达了作者对于乌托邦世界近乎痴迷的追求者的敬佩和同情。作品采用的叙述方式标志着作者从“先锋”到传统的回归,不管是对于由恋爱引起的革命的描写,还是对于世外桃源和大同世界的叙述,都使我们感受到了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执著追求,也使我们看到了在这看似美好的愿望的背后,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古至今难逃孤独的宿命。作者以新的眼光重新看待那一段历史,采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缔造出一种文本时代与五四时代和现代的精神联系。本文试图从作品的“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入手,分析文本背后体现的作者的深意,感受作者表达的“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空虚与孤独。
关键词:人面桃花;革命;恋爱;孤独
浪漫主义思潮起源于西方,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其中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为代表的创造社成员,倡导“为艺术而艺术”,最早在中国提倡浪漫主义文学。五四时期是中国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赵诗园曾说:“每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都容易产浪漫的情绪。”[1]五四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思想和社会大变革时期,浪漫主义至此找到了其扎根的土壤。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内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展开,一时间,革命至上的时代情绪取代了五四时期追求个性解放的极端自由思想,浪漫主义文学随之发生改变。因此,以表达个人情绪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一次从个人浪漫主义到集体浪漫主义的转变,即从浪漫到革命的转变。面对这一转变,文学形式也相应发生变化,表现在小说领域即为由五四时期的“身边小说”“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到“革命+恋爱”题材小说的转变。
“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产生于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受当时国民大革命的影响,革命情绪成为当时时代的主要情绪,“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便是当时中国社会情绪的直接反映。“革命+恋爱”是一种小说的创作模式,它通常指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在陷入革命和恋爱的挣扎之后,甘于放弃爱情投身革命的故事内容。即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的革命意识都是由于恋爱而产生的。如“革命+恋爱”题材小说的代表作——丁玲的《韦护》中所描写的那样,革命者韦护和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陷入了恋爱和革命的冲突之中,韦护一方面站在不可动摇的革命工作上,另一方面站在生命的自然需要上,经过思想斗争,终于革命战胜了爱情,离开了丽嘉。韦护走后,丽嘉虽然感到幻灭的痛苦和悲哀,但还是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决心要做出点事情来。这种题材的小说后人多有诟病,当时左翼作家认为小说过于呆板,内容受限于形式,人物脸谱化,观念在小说中大行其道,因而此类小说缺乏其深刻的内涵。但是到了2004年,格非《人面桃花》问世,我们似乎在作品中看到了这种“革命+恋爱”题材的全新运用,同时也看到了其新的生命活力和作者所赋予的更深层次的含义。
《人面桃花》讲述了几代人追求世外桃源乌托邦的故事。故事发生于辛亥革命之前,通过少女秀米的成长经历和爱情经历,为我们讲述了中国的仁人志士追求革命乌托邦,到革命梦碎之后陷入空虚与孤独的人生悲剧。秀米在走向革命,并为之奋斗一生的过程中,爱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革命以恋爱为前提
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虽然内容各异,但无一例外,书中的男女主人公走向革命的原因都是因为恋爱。对于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来说,革命首先是搭筑其恋爱的桥梁,其次才成为了他们的人生追求。正是因为同革命者恋爱,他们接受了革命思想,最后陷入了革命与爱情的两难抉择之中,导致最终爱情的失去,陷入了一种人生的孤独。《人面桃花》亦是如此,秀米一生遇到过三个珍爱她的男人,一个是引领秀米走向革命的人生导师——革命党人张季元;一个是为了得到秀米而协助革命党人夷平花家舍的马弁,一个是因爱慕秀米而离家出走最后死于清廷武装之下的谭四。秀米所经历的三段爱情都掺杂了革命的因素。当秀米在经历了生理期的痛苦和父亲出走事件之后,年幼的秀米由懵懂走向了自知,一方面是对自己作为女性的重新认识,一方面是对于普济之外世界的好奇与感知。这说明女性意识自觉和革命乌托邦意识开始在秀米的内心苏醒。乌托邦意识与意识形态本身都属于集体无意识,这说明女性意识自觉和革命乌托邦意识开始在秀米的内心苏醒。这时,张季元闯入了秀米的生活,他那一副仿佛不是世间男子的容貌打开了秀米情窦初开的心,“他皮肤白皙,颧骨很高,眼眶黑黑的,眼睛又深又细,透出女人一般的秀媚。虽然外表有点自命不凡,可细一看,却是神情阴冷,满脸的抑郁之气,似乎不像是活在这个世上的人。”[2]张季元自带的神秘之感,将本来对他有好感的秀米引向了更加好奇的地步。在秀米一步步揭开他神秘面纱的过程中,难以言说的情愫在两人心中蔓延,而这一点一点的情愫慢慢发酵,最终在张季元的那本日记中转化为浓烈而深沉的爱。这本日记不仅解开了张季元的身份之谜,也使秀米渐渐懂得了父亲发疯的原因。张季元是清末革命党蜩蛄会的一员,他胸怀雄心壮志,企图通过革命的力量,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可是由于清廷的绞杀量悬殊,最终死于非命。只给秀米留下了一本日记和象征着革命信仰的金蝉。张季元在日记中毫不避讳地写下了他对秀米的挚爱和对革命事业的忠心,虽然只是一些冷冰冰的文字,但却如一股暖流奔涌于秀米的心中。正是由于张季元在日记中给予了秀米强大而坚实的力量,才促使她耗尽一生心血来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走上了同他一样的革命道路。这不仅是秀米对于张季元的思念,更是秀米对于自己年少爱情的怀念。如果说张季元是秀米人生的导师,是她爱情和革命信仰的启蒙,那么对于马弁和谭四来说,秀米则是他们人生存在的意义。由于喜欢她和爱她,马弁由一个受人欺侮的马仔,在革命党人小驴子的诱导下,协助他杀害了花家舍的几位当家。他根本都不理解“革命”的真正含义,只是因为小驴子对他说杀了几位当家,他便可得到秀米,于是他便无所畏惧地投入到了“革命”计划之中。对于秀米人生中最后一个男人谭四来说,革命更是他追求秀米的唯一途径。从花家舍土匪窝回到普济的秀米,兴办学校,创立普济自治委员会,联合乡里乡亲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使得普济村民都将她当做小疯子看待。可是在谭四的眼里,秀米似乎仍然是那个同他一块去夏庄送信的青葱少女。为了她,他不顾父母反对,终日陪伴在秀米身边,成为秀米追寻乌托邦道路上最大的精神慰藉。深爱着秀米的三个男人无一例外都死了,留下秀米一人孤独终老,他们三个分别担任了秀米成长道路上的不同角色,完成使命后,共荣隐去,只剩秀米一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孤独前进。这种典型的“革命+恋爱”题材的叙事方式,使得我们在感叹秀米爱情的同时,也会对秀米所一直追求的革命理想产生一丝丝怀疑,内心会疑问秀米追求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同时也会对由于恋爱而引发的革命观产生疑惑,甚至会质疑以爱情为前提的革命追求是否存在意义。但是纵观本文对于不同派别的革命党人的描述,我们感觉到了作者是在进行批判,是在从侧面向我们展示由恋爱引发的革命本身就是不成熟的。
二、不成熟的革命者
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年代,似乎每一个经历了五四退潮时期的年轻人都走上了一条坚定的革命道路。在他们看来,自我价值的实现,或许只有通过牺牲小我,奉献集体才能实现。在这样的时代情绪下产生的文学作品 必然深深地打上了属于那个时代独有的记忆。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一经发表并迅速风靡文坛,但是却遭到当时进步作家的强烈谴责。1935年,茅盾曾指出,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为了革命牺牲恋爱”、“革命决定了恋爱”、“革命产生了恋爱”[3]。瞿秋白认为这些小说在描写由恋爱向革命转变的过程时,常常写得“莫名其妙”。因此批评其“不能够深刻的写到这些人物的真正的转变过程,不能够揭穿这些人物的“假面具”[4]。因而,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展现出来的革命者都体现着一些共同特征,即经常陷入革命与爱情的挣扎之中,对于革命有着过分的执着,以及难以克服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性。
格非在《人面桃花》中塑造了一批革命者的形象,不管是蜩蛄会成员张季元、薛祖彦、小驴子周怡春,还是花家舍总揽把王观澄,亦或是秀米的父亲陆侃,他们都对于革命,对于乌托邦的理想世界有着很深的执念,甚至到了一种发狂的状态。但是无一例外,他们所追寻的革命或者是大同世界都以失败告终,他们本人也陷入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之中,进入一种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状态。他们都在秀米追寻革命道路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格非在书中既表达了对于他们注定失败的惋惜,但也一以贯之地表现出他所持有的批判的态度。格非虽然采取了同30年代相呼应的“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但是却比30年代的“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更接近于现实主义创作传统。30年代“革命+恋爱”题材的小说流于了“革命的罗曼蒂克”的怪圈,离本身要所追求的现实主义却越走越远,格非的《人面桃花》无疑是向现实主义的一次回归,因而作者在这种创作模式背后表达了对于革命者深深地思考。不管处于哪个时代,由于爱情、社会情绪而引发的革命理想都是稚嫩的,而持有革命理想的革命党人也是不成熟的。
(一)革命与爱情的冲突
《人面桃花》中的张季元就如同《韦护》中韦护一样,陷入了革命理想与情爱需求的挣扎之中,因而总是表现出一种神秘感和不安全感。一方面是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方面是自己忠爱的事业,两难选择的背后必然是革命者的爱情失去,自己以一种孤独者的姿态走入自己所追求的革命事业当中,虽然路途艰险,却也无所畏惧。清朝末年的中国就如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府腐败,各地革命团体涌现,他们都受着激进的革命思想影响,希望协有志之士,改变中国之面貌。中国同张季元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不在少数,以张季元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似乎就像是之后韦护那样,陷入一种“灵与肉”,“革命与爱情”的挣扎之中,因而他们的思想是不成熟的,他们所进行的革命事业也是不成熟的,他们革命的动机更多的是出于心中的那一腔热血,缺乏周密的考量,完整的计划,最终只能导致革命失败,客死他乡。
(二)人生的执念
《人面桃花》中塑造了两位士大夫形象,一位是秀米的父亲陆侃,一位是花家舍的总揽把王观澄,虽然书中并未提到他二人之间有任何联系,但我们却能从他二人的追求中感受出他们的相似。他们都属于封建王朝的士大夫阶级,本应在清廷制度体制内安稳过完一生,可是他们却对陶潜所描述的桃花源,孔子所向往的大同社会过分痴迷,由于心中那份强烈的执念,陆侃罢官回乡,在普济开始了他长久的思考,王观澄则落户花家舍实践他心中所想。正如尼姑韩六所说的那样,人这一辈子不能过分执着,伤人伤己。虽然这是从佛家阐释出他二人的悲剧,但是在我们现在看来,他们二人的悲剧则是因为他们的梦想都不切实际,只是存在于幻想阶段。陶潜所描述的桃花源就是一处幻境,真实世界是不会有这样一片天地的,孔子所提出的大同社会更是孔子对于统治者给予的深深厚望,国家要想实现大同,只能说这还是属于我们对于国家的未来所抱有的美好梦想。想要凭借一己之力提前实现这一梦想,似乎有点痴人说梦的嫌疑。正是因为二人心中有着深深的执念才造就了二人一死一疯的悲惨结局。
(三)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中国的革命历来都有其自己的表述,不管是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还是近现代的社会革命,我们始终看到的都是革命的波澜壮阔,可是当革命卸下他光鲜的外表,会发现原来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需要,中国的革命历来都与金钱脱不了干系。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钱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同样,钱也是腐朽革命党人,压垮革命的最后一根稻草。蜩蛄会的革命党人薛彦祖富甲一方,对于革命有着深深地信仰,也给予了革命团体巨大的财富支持,可是当灾祸降临,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财主的仓皇害怕,还伴随着视财如命的不堪。表面的他侃侃而谈,谈理想,谈革命,私下的他招妓,对蜩蛄会所明令禁止的条例置若罔闻,临死前还想着自己的金银财宝。我们真真的看到了革命党内部的胆小懦弱之徒,最后落得个惨死的下场,令人唏嘘。随着革命党人被清廷逮捕,蜩蛄会的元老级成员张连甲坐不住了,誓要解甲归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平安过完下半生。之后的蜩蛄会树倒猢狲散,犹如一盘散沙,再也没有与清廷相抗衡的力量,逐渐销声匿迹。可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虽然书中对于蜩蛄会的描写只是只言片语,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团体内部的不堪,我想格非也有自己的思考,中国革命的失败不仅是外因的影响,内因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梦醒之后的孤独
当轰轰烈烈的五四革命由高潮走向退潮,中国的时代情绪也由自由的呐喊走向了苦闷的彷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浪漫主义在中国完成了第一次华丽的转身,浪漫主义文学由直击内心的创作走向了为革命奔走呼号,但是文学作品中的有志青年却一直走入了更加孤独的境地。不管是鲁迅笔下的涓生还是丁玲笔下的韦护,他们全都抛弃了爱情,走向了一条自以为更为合适的的“康庄大道”,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孤独者的迷茫与彷徨。《人面桃花》中秀米的结局似乎也是同那个时代相呼应。秀米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结束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在痛失了亲人之后的秀米,开始了对自我的惩罚,她将自己封闭起来,拒绝与人交流,完全陷入一种与人世隔绝的状态。正如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强调的那样:“乌托邦的消失将产生一种静止的事态,在这事态中人本身成了物。”[5]没有了精神寄托的秀米真正的进入到了一种归隐的状态,达到了陆侃和王观澄一生所追求的状态,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其实,王观澄陆侃所追求的世外桃源同张季元和秀米最追寻的革命理想,看似都是乌托邦,但却是两种形态的乌托邦世界。前者是希望世界大同,属于幻想阶段,后者是希望借助革命的力量,改变中国之形态,走入更加文明开化的状态,虽然形态不同,但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缺乏真实的土壤。所以不管是王观澄和陆侃追求一生,还是秀米和张季元奋斗一生,终究是在别人看不懂的世界里自娱其乐,一旦梦醒,生活还是原来的样子,留给自己的却是更加孤独和难以释怀。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走。”[6]在这里,精神孤独的宿命似乎进行了一个轮回,五四时期的鲁迅曾在小说《孤独者》中阐释了孤独的概念,为我们描述了三代人的孤独,向我们说明,孤独一直是我们每一个人挥之不去的时代印记,今天的我们同样也在《人面桃花》看到了相似的主题的表达,不管是追求革命失败的革命党人,还是普通百姓,都难逃孤独的命运。因而作品在精神上是同五四的时代精神相呼应的,作品也在内容上因此更加接近于现实主义。
四、结语
《人面桃花》虽然通过“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为我们展示了乌托邦的美好和现实的残酷,但是在其叙事模式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作者对于革命者以及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孤独感的深深思考。因而整部作品有着好的憧憬,也有着痛的批判,我们通过书中人物追求理想而不得感受到了人生无力的悲痛感,同时引发了我们对于孤独的宿命感的关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究。
参考文献:
[1]陶晶孙.记创造社[M].北京:太平书局,1944.
[2]格非.人面桃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3]瞿秋白.革命的浪漫蒂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J].文学第四卷第一号,1935.
[5]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6]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385(2016)03-0088-04
收稿日期:2016-04-02
作者简介:曹琳,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