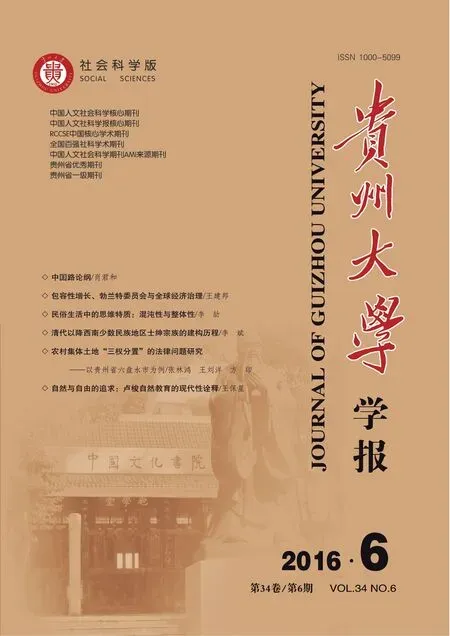村上春树作品中的“审父”叙事
——再论短篇小说《第七个男人》
沈丽芳,沈媛媛
(1.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2.贵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村上春树作品中的“审父”叙事
——再论短篇小说《第七个男人》
沈丽芳1,沈媛媛2
(1.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2.贵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第七个男人》在其作品贯有的“丧失与恢复”的表层叙事下,隐藏了父子关系这一“审父”叙事。本文通过对《第七个男人》暗藏的“从父——反父——离父——寻父”这一叙事结构的分析,探讨了小说主人公自我成长的心路历程。这一解读方法对进一步理解村上春树后期作品中“审父”叙事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村上春树; 《第七个男人》;“审父叙事”;自我成长
村上春树的作品中很少涉及“父亲”形象,特别是在其前期作品中,家人、父亲几乎从未出现。加藤典洋将村上春树的作品分为初期(1979—1982,《且听风吟》等)、前期(1982—1987,《寻羊冒险记》、《世界末日与冷酷仙境》等)、中期(1987—1999,《挪威的森林》等)后期(1999—2010,《斯普特尼克恋人》、《海边的卡夫卡》等)、现在(2011—,《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等)五个阶段[1]108。加藤指出“后期对于村上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后期的变化正是在村上对自己的创作方式进行反思,毫无成见地投身于故事世界,潜行于自己的潜意识深处这样一种对新创作形式的极致追求中诞生的。……同样,在潜意识中,他慢慢触及了与‘父性存在’的对峙·对立这一主题。该主题在《神的孩子全跳舞》中初显,在《海边的卡夫卡》中发展成为‘杀父’主题”[1]206。
诚如加藤所言,后期之前村上很少在作品中触及“父性存在”这一主题,甚至可以说对“父性存在”不太关心,对父子关系这一主题也甚少涉及。但是发表于《神的孩子全跳舞》之前的短篇小说《第七个男人》(发表于《文艺春秋》1996年2月号,后收录于同年11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列克星敦的幽灵》)中已经隐现了父子关系这一“审父”叙事。在《第七个男人》中,主人公“我”作为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人讲述了自己十岁在海边遭遇巨浪时抛弃了好友K致使其被巨浪卷走的可怕经历。少年时“我”与好友K亲如兄弟,在一次台风风眼的短暂平静中,K跟着“我”一起去附近的海边探险。“我”在自以为安全的地方探险,却发现波浪已无声地靠近,“我”感到莫名的恐慌,一个人逃往了防波堤。当“我”在防波堤再次向K呼喊时为时已晚,眼看着K被巨浪卷走。在第二次巨浪中“我”看到K狰狞地笑着,仿佛要将“我”带入另一个世界。此后,“我”被梦中K的狰狞面孔和溺水而亡的恐惧纠缠,最终逃离故乡,却始终不能摆脱噩梦的纠缠。直到40年后,“我”再次与K的画作相遇并重返海边,终于从噩梦中解脱,重新开始人生。
申寅燮、尹锡珉认为“内心饱尝的丧失感和痛苦感是村上春树作品的基调,其作品大多都在传达一个信息,即活着就是治愈过往所受心灵创伤的过程”[2]。从作品的表层结构来看,《第七个男人》讲述了少年时的心理创伤及其后的恢复过程,具有明显的“丧失与恢复”的主题特征,是一篇非常村上式的短篇小说。从“我”的讲述来看,只有真正面对“恐怖的本源=自己中的他者”,才能摆脱恐怖[3]。但是,无论是作为故事起源的心理创伤源头事件——K之死,还是作为故事转机的心理创伤恢复契机——再遇K的画作,无不与父亲相关。《第七个男人》中父亲的出场次数屈指可数,却仿佛一种暗流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在“我与K”的表层叙事之下,掩藏着“父与子”的深层叙事主题。重新解读《第七个男人》中“审父”叙事下的父子关系,对于深入剖析村上春树后期作品中与“父性存在”的对峙·对立这一主题具有重要意义。
父子关系是复杂的、动态变化的关系,其中有传承有对抗,父亲是曾经的儿子,儿子是未来的父亲。“审父叙事中的‘审’不是审判而是审度、审视、审察”[4],“审父”不仅是对过去的、现在的父亲的审视,更是对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自己的一种全方位观照。本文将以《第七个男人》中的父子关系为主线,从“我”对父亲的“从—反—离—寻”的认知变化入手,探讨其中的“审父”叙事。
一、从父——父性存在的绝对权威
对于孩童时期的“我”来说父亲是绝对的权威性存在,“我”在精神上处于父亲的绝对控制之下。在日本影响深远的“家父长制”家庭体制虽然在二战后的新民法中被废除,但是这种“家父长制”长期以来的影响在日本依然根深蒂固。在这种家庭观念之下,父亲作为一家之长对于家庭成员具有绝对的控制权[5]。作品中“我”家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式家庭结构。父亲是开业医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赚钱养家。台风到来之前,“父亲与哥哥一大早就带着装有锤子、钉子的工具箱将家中所有的雨篷钉好,母亲则在厨房准备饭团”*作品引用参照《七番目の男》(《レキシントンの幽霊》.文藝春秋.1999)。引用部分均为笔者自译。。父亲带领长子维护家庭的安全,保护家人不受侵害,是家庭的精神支柱。而且,作为医生的父亲从事治病救人的职业,在当地那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父亲在家中占有统治性地位,拥有绝对的权威。
“我”在作品中叙述“父亲是开业医生,我的童年过得没有丝毫的不自由”,在父亲的绝对性权威的统治之下,“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不自由,这种感受佐证了“我”在精神上受到父亲绝对统治的事实。如果对父亲的言语心存质疑,对父亲的命令抱有反感,是不可能感到“没有丝毫的不自由”的。孩童时期的“我”精神方面受到父亲的绝对控制,只是按照父亲的指示行动,完全没有自我,父亲与“我”之间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强—弱”关系。
二、反父——自我的萌芽与萎顿
随着“我”的成长,“我”在肉体和精神方面日渐成熟,自我意识逐渐萌发,孩童时期完全受到父亲精神统治的“我”慢慢从无条件的“从父”状态脱离出来,呈现出与父亲对峙的“反父”的倾向。这种“反父”倾向主要体现在与K胜似亲兄弟的亲密关系中。
“我”与K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截然不同。“我”“相对体格健壮,擅长运动”,而K“消瘦、白皙”,“身体羸弱”;“我”“受到大家的一致肯定”,而K“有语言障碍”,初次见面的人甚至“可能觉得他智商有问题”。“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回家玩耍时,我都以K的保护者自居”,“我”与K之间这种胜似亲兄弟的亲密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强—弱”关系体现。“父—子”关系中处于被保护者、被控制者地位的“我”在“我—K”关系中逆转成为保护者、控制者,这种姿态的转变暗示了“我”潜意识中主动要求成为保护者、控制者这种权威性存在的心理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姿态与心理的转变是与父亲这种权威性存在对峙的开始。
而且,“K”擅长绘画,“总是能瞬间挥洒出栩栩如生的线条与色彩,对此我相当佩服,并为之惊讶。现在想来,那应该就是纯粹的才能吧。”人总是在潜意识中追寻自己所缺失的,K在绘画中所体现的对线条、色彩的绝对控制和无限自由,也正是吸引“我”的重要原因。对这种自由的向往也是“我”对孩童时代的父亲控制下的所谓自由的反思。由此可见,虽然“我”并没有在语言与行动上明确表现出对父亲的不满、反叛,但无论是“我”面对K时的保护者姿态,还是对自由的重新认识,都是成长之后的“我”潜意识中试图摆脱父亲的精神统治,与权威性父性存在对峙的开端,是自我意识萌芽的体现。
这种潜意识中与权威性父性存在对峙终于在台风到来这一非常环境下爆发,显现为违抗父亲的有意识行为。台风风眼的间歇,“我”征得了父亲的同意外出散步,并和K一起去附近的海边探险。“我们在防波堤上坐着看了好久”,终于“走下防波堤,留意着周围的情形在海浪退去的海滩上走着,翻看着留在海滩上的东西”。防波堤是“我”从过去的“从父”转为未来的“反父”的分水岭。出门前父亲叮嘱“只要起风了就必须马上回来”,这是父亲对“我”远离一切危险的要求,危险的情况、危险的地方、危险的行为都包含在内。“我”在防波堤上看到异于平常的大海,“海浪平静得可怕”,对于从小长在海边熟知这片海岸的“我”来说已经预感到危险,但是少年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急切地探索非同一般的海岸。是遵从父命放弃探险,还是遵从自我违抗父命?一直受到父亲精神控制的“我”和现在的要彰显自我意识的“我”无声地交锋,终于自我意识占据了优势,“我”违背了父亲的命令开始海边的探险。
但是,在父亲长期的精神控制之下,自我意识虽然萌芽并逐渐壮大,但依然势力微弱。虽然“我”开始在海边探险,但是在探险之初“我”就一直被违抗父亲所带来的恐惧纠缠着。我们虽然注意远离海浪,但是海浪悄然靠近。“一种强烈的不祥像爬虫类的触感一样瞬间使我身体僵硬”,“那海浪的确是有生命的。海浪清晰地捕捉到我的身影,要把我握在掌中。就像巨大的食肉动物潜伏在草原某处锁定我,幻想着用锋利的牙齿撕碎我”。“我”的恐惧不仅是对于自然界的海浪中所隐藏危险的恐惧,更多的是对于自己违背父亲命令的探险行为有可能带来的惩罚的恐惧。在这里,海浪象征着父性权威,是父亲的隐喻[7]。对于“我”而言,父性存在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违背父命的惩罚即将到来。在这样的巨大的精神恐惧之下,“我”抛弃了K独自逃生,致使K被巨浪卷走。
K之死隐喻着反抗父亲的“自我”的彻底覆灭。首先,与K的交好,成为K的保护者的姿态中隐含着“我”潜意识中与父性权威的对峙和成长为父性权威的欲望,K的死亡是对无法保护K的弱小自我的嘲笑,是对“我”成长为父性权威资格的否定。被保护者K的死亡即是“我”的保护者身份的丧失。其次,在“我”的认知里,K的死亡是来自父性权威对“我”违抗父命到海边探险中越境行为的惩罚。面对K的死亡,第二次巨浪到来时,“我”已经做好了接受惩罚被巨浪卷走的心理准备,这时“我”看到了浮现在浪头的K,他狰狞地笑着,“向我伸出右手,就像要抓着我的手带往另一个世界”,K的狰狞形象是“我”对自己的暗示——应该接受来自巨浪这一父性存在的惩罚,走向死亡。“但是只差一点点,他的手没有抓住我”,“然后我失去了意识”,这一结果暗示着“我”最终还是没有勇气直面巨浪这一父性存在的威压,没有勇气接受惩罚。在抛弃K致其死亡的心理折磨之下,在父性存在的威压之下,在对怯懦的自己的失望之下,“我”的精神濒临崩溃,还未壮大的自我意识全面崩溃。
人总是通过意识层面来认识现实,通观“我”对海浪事件的讲述,除了K被巨浪卷走是确定的事实之外,“我”的述说更多是因为心理作用、因为对父性权威的个人认知而产生的想象,第二次巨浪中的K更是一种非现实的幻觉。事发四十多年之后,“我”对当时的情景、感受依然记忆犹新,足见事件对“我”影响之深,而且这种心理作用、个人认知四十年没有被打破,顽固地统治着“我”的意识与行为。
三、离父——异化与分裂
海边事件发生当年年底,“我”终于决定离开故乡。“我无法继续在眼睁睁看着K被巨浪卷走的这片海边生活,而且正如大家所知我夜夜被噩梦侵扰。只要能离开这里去哪儿都行。不然我会发疯的。”正如前文提到,巨浪是父亲的隐喻,“我”想离开故乡并不只是想离开事发现场,更是想要离开父亲这一权威性存在。但是“我”“离父”的愿望虽然强烈,但态度并不坚决,行动也并不彻底。
首先,“我”的“离父”依然借助了父亲的力量。“我”没有离家出走,也没有自己决定目的地,而是“将自己想尽早离开这里搬到别的地方去的想法告诉父母”,“父亲听了我离家的理由,开始给我办理转学的手续”。当然,在生理上“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少年,没有独立行为能力,但这也表明“我”并不能真正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离父”。借助父亲的力量达到远离父亲的目标,让人不由地对“我”的“离父”感到唏嘘。
其次,“我”虽然离开了故乡,但并没有在实质上实现“离父”。“我一月搬到了长野县,开始在当地的小学上学。因为小诸附近有爸爸的老家,家里人让我借住在家里。我在那里上了初中、高中。假期我也不曾回过家。只是父母有时来看我。”“我”虽然离开了K遇难的海滩,在空间上远离了父亲,但是并没有真正切断与父亲的联系。“我”住在父亲的老家,依然在父亲的庇护之下,“我”与父亲之间的间接联系依然紧密。而且父母有时会来看“我”,“我”与父亲之间的直接联系也依然保留。所以即使“我”搬到了别的县,也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离父”。
这种不完全的“离父”并没有给“我”带来预期的救赎,反而使“我”陷入一种异化的状态。“离父”并没有帮“我”消除噩梦。虽然“离开那个城市后不久,我就不再像之前那样频繁地做噩梦了”,看似“离父”对于摆脱恶梦有一定的效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噩梦并没有从我的生活中离去。噩梦有时就像讨债人来敲门一样,又来到我身边。就在我即将忘却的时候。和以前一模一样的梦。连细节都完全一样。每次我都惊叫着醒来。汗水濡湿了被褥。
在K离去四十年后,“我”依然会做噩梦,不仅噩梦“和以前一模一样”,“连细节都完全一样”,说明“离父”对于解救被噩梦困扰的“我”没有丝毫作用。而且,虽然看起来噩梦的频率有些许降低,但是噩梦的威力对“我”来说不降反增。噩梦已经变成“讨债人”,“在我即将忘却的时候”悄然而至,一遍遍地刷新“我”对过去的记忆,一遍遍地拷问“我”的情感与理智。因此,“离父”并没有给“我”带来救赎。
“离父”后的“我”长期处于一种分裂和异化的状态。“我”认为自己和普通人一样工作,生活。就像大家看到的,和大家没什么区别。在人际交往方面虽然说不上多好,但是因为喜欢登山,所以也有那么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在短短的描述中“我”反复强调自己和普通人别无二致,但正是这种强调暴露出“我”对自己“不普通”的认知。当我们都是普通人时,并不会观察所谓的普通人是什么样子,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不同是必然存在的,也是正常的。只有自己觉得自己“不普通”时,才会反复观察自己和别人是否有不同,是否被人特别对待,才会反复的强调自己和普通人别无二致,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四十年来,“我”一直处在白天若无其事的生活着的“普通状态”和夜晚被噩梦纠缠惊叫着醒来的“异常状态”的分裂之中。
而且,“噩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精神层面,对“我”的生活也产生了实质的影响。
不只是那个海边,只要是海我都决不靠近。我害怕如果去了海边,噩梦中的情景就会变成现实。而且本来我很喜欢游泳的,但是自那以来我连在游泳池游泳都戒掉了。河、湖我也决不靠近。船也不坐。我从未乘飞机到过国外。
“我”所恐惧的对象从事发的海边扩展到所有的海边,扩展到所有的水域。行为的禁忌从噩梦中的在海里游泳扩展到游泳池里游泳,扩展到与水域有关的坐船,甚至是和水域没有太大关联的乘飞机出国,只因为飞机在海域上空飞过。噩梦对“我”的影响从抽象变为具象,从精神性蔓延为行为性。因为“我不想半夜两三点大声惊叫着惊醒身旁的某个人”,而且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也“不可能向谁诉说”,所以“我”虽然有喜欢的女性,但是没有结婚。在这样状态下,未来的“我”也不可能结婚、生子。噩梦不仅影响“我”的过去,也将继续影响“我”的未来。四十年间,“我”一直处于这样的一种扭曲的异化状态。
杨经建指出“父辈与子辈的复杂关系已构成了人类生存最深刻的部分, 它往往体现出生命密码的递转和文化基因的重编, 这种递转和重编并不就等于后来者和先在者的断裂和决绝, 相反, 倒有可能为后来者寻获新的生长点和支撑点。……无父的儿子在失去文化记忆的同时也会因此在根本上失去与历史、传统和秩序的内在关联, 人因此失去证明自身存在意义的价值参照, 使‘自我’处于一种‘无根’的漂流状态。所以放逐‘父亲’的同时‘自我’也被放逐。”[4]“我”逃离父亲后四十年间的分裂与异化状态也正体现了这一点,“我”主动离家、离父,妄图重建自我,却失去了“生长点和支撑点”。四十年中除了肉体在自然的力量下走向成熟、衰落,在精神上处于一种完全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四十年前随着孩童到少年的成长,“自我”还有过成为保护者(强者)、成为权威的成长欲望,“离父”后的四十年里“自我”却处于完全萎缩的状态,沉沦于过去造成的精神创伤之中无法自拔、无以自救。“离父”不仅放逐了父亲,也放逐了“自我”,无“自我”的四十年像一段真空,割裂了过去与未来,没有现在。
后来父亲去世了,“我”物质性地实现了真正的“离父”,但是依然没有从噩梦中得到救赎。后来因为与K的画作重逢,以此为契机重返海边,“我”才真正的摆脱恶梦,走向恢复。而这种恢复的过程正是“我”的寻父之路。
四、寻父——恢复之路
父亲去世后,哥哥为了分割财产卖掉了祖宅,给“我”寄来了留在家里的物品。其中就有少年时的K送给“我”的画作,在画里“我”重新认识少年时“我”与K认识世界的目光:
在那画里我深刻地体会到少年K的心情,我感同身受的深切理解了他是用何种目光看待周围的世界。……那也是少年时我自己的目光。那时的我与K两人肩并着肩,用同样生动、无霾的眼睛看着世界。
“目光”是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的象征,不同的“目光”导致了对世界不同的认知方式。K的画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唤醒了“我”少年时期认知世界的目光。这种目光的复苏使“我”察觉了四十年来对K的误解,“横卧在浪头的K并没有憎我、恨我,也并没有要将我带我某处,……他最后向我温柔的笑着,告诉我他永远的离去”。同时,这种目光的复苏也促使“我”在内心深处对父亲进行重新认知,这种认知的变化给“我”带来了恢复的希望。“终于黎明到来。新生的太阳将天空染成淡淡的绯色,鸟儿苏醒啼叫”。这“黎明”是四十年黑暗的黎明,“新生”是四十年停滞后的新生,预示着“我”的恢复之始。“那时候我觉得我必须重返故乡,马上”。
父亲已经离世,“我”要寻访的并不是存在于现实中的物质性父亲,而是存在于思想与记忆中的精神性父亲。这种精神性父亲存在于故乡、海边、海浪之中。
防波堤的对面和以前毫无二致,大海一望无际,不受任何人的遮挡。……风景安详而优雅。从这风景中无法相像曾经猛烈台风袭来,巨浪吞噬了我唯一的好友。而且记得四十年前那场事故的人,现在也寥寥无几了吧。让我觉得所有的一切是不是都是我自己在脑子里制造出的精密幻觉。
当我突然发觉的时候,我心中的黑暗已经消失了。和它出现的时候一样毫无预兆的,消失在了某处。
巨浪是父亲的一种隐喻表现,浪是大海与陆地的接触形式,也是父亲与“我”的接触形式。“我”对大海的风景的重新认识,正是对父亲的重新认识。正像重访海边之前,“我”发觉了对K的误解一样,看着大海的风景,“我”也发觉了对父亲的误解。“我”的噩梦源自于对父性权威的恐惧,源自于对因为违背父命而产生的惩罚的恐惧。不能消除对于父亲的误解,无论如何远离父亲,都不能从噩梦中获得解脱。当对父亲的误解消失了的时候,由此而生的噩梦,以及心中的黑暗,自然消失无踪。
我走到海浪边,连裤脚也没卷就静静地踏入浪里。而且就穿着鞋子,让涌来的海浪拍打着。海浪和小时候涌来的海浪别无二致,像和解般地久违地拍打着我的脚,濡湿了我的衣服、鞋子。……是的,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我终于到达了这里。
“我”没做任何措施径直走进浪里,像受到了父亲的召唤一般。“我”无法顾及现实中的种种,遵从自己的意志与海浪(父亲)进行最直接的对话。海浪“像和解般地久违地拍打着我的脚”,与其说是海浪与“我”和解,不如说是“我”与海浪和解。海浪一如既往地存在,不同的只是“我”的认知,认知的改变带来了态度的改变。“我”对父亲的态度从少年时的反抗、逃离转变为对话、和解。“我终于到达了这里”,“这里”是物质的故乡、海边、波浪,更是精神的解脱与自由。
在四十年的煎熬之后,“我”终于摆脱了对父性权威的恐惧与逃离,重新走上了“自我”的重塑与发展之路:
我身体里的时间之轴嘎吱作响。四十年的岁月在我的身体里像腐朽的房屋一般崩塌,旧的时间与新的时间混入一个漩涡之中。周围的声音消失了,光线摇摆不定。然后我失去了身体的平衡,倒在涌来的浪里。……但是我不害怕。是的,我已经没有什么害怕的了。那已经过去。
在父子之间,父亲象征过去的积累,儿子象征未来的命运[4]。父亲是过去的儿子,儿子是未来的父亲,进入父系社会以来,这种“父—子”角色的转变与轮回正是人类社会文明传承与不断发展的轨迹。无法认同过去的父亲即是无法认同未来的自己,对父性权威的恐惧与逃离,必将阻碍“自我”成长与发展。正如前文论述,“离父”所带来的无的“自我”的四十年像一段真空,割裂了过去与未来,没有现在。在自我发展的路上,“我”裹足不前,甚至倒退,饱受四十年心灵黑暗的折磨。当“我”摆脱了对父性权威的恐惧与逃离,与父亲对话、和解,建立了新的联系之后,四十年的真空“像腐朽的房屋一般崩塌”,阻隔了“自我”的过去与未来的巨大心理障碍消失了。“旧的时间”是因海边事件而自我崩溃与发展停滞的“我”的过去,也是父亲代表的过去的积累,“新的时间”是自我发展的“我”的未来,也是儿子代表的未来的命运。“过去带着时间的索引,把过去指向救赎”[7],“旧的时间与新的时间混入一个漩涡之中”是过去的积累与未来的发展之间联系的重新建立,也是“我”的自我发展之路中断后的重新开启。在“我”对父亲,对自己的未来有了全新的认识与坚定的信念之后,面对未来的人生之路也不再害怕。
五、结语
“审父”叙事在文学作品中多有涉及,无论是渎父、杀父还是寻夫,父子关系这一主题在文学领域、社会领域都受到重视。孩子,特别是男孩,反抗父亲、超越父亲是自我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父子关系及其辐射出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对个人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千百年来父子之战反反复复,从不停息,在现实中面对父亲不能合理应对,不能完成自我成长的个案不再少数。
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第七个男人》贯穿着反抗父亲、逃离父亲、寻找父亲的“审父”叙事,其中的艰辛令人唏嘘,几乎耗尽了毕生的岁月。这一痛苦的过程唤起了埋藏在很多人心中的灰暗过往,激起无限共鸣。而且在村上春树的叙事中,经历了从父、反父,最后寻父、认父的结局之下,暗藏着父亲病故这一形同杀父的事实。这些叙述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村上春树对“审父”叙事的独特思考,揭开了村上春树作品中对父性存在书写的序曲,直至后期作品《海边的卡夫卡》、《1Q84》中与父性存在的剧烈交锋。《第七个男人》中“审父”叙事的解读对于深入探讨村上春树后期作品中对父性存在的叙述,捕捉其作品创作的演变过程,透视其思想动态具有启示意义。
[1] 〔日〕加藤典洋.村上春樹は難しい[M].東京:岩波書店.2015.
[2] 申寅燮,尹锡珉.共同体伦理的失范与心灵创伤的治疗——评<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J].外国文学研究,2013(6):55.
[3] 〔日〕角谷有一.作品の深みへ誘う「読み」の授業を求めて――村上春樹『七番目の男』を取り上げて[J].日本文学,2004(3):8.
[4] 杨经建.以“父亲”的名义:论西方文学中的审父母题[J].外国文学研究,2006(1):159-165.
[5] 申蓮花.日本の家父長的家制度について-農村における「家」の諸関係を中心に.地域政策研究[C].高崎経済大学地域政策学会,2006(4):99-104.
[6] 沈麗芳.村上春樹における〈父なるもの〉の浮上―短編「七番目の男」論.アジア·歴史·文化,2016(2):64.
[7] 〔德〕瓦特尔?厲本雅明著,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04.
(责任编辑 杨 飞)
2016-07-12
跨文化语用视域下的陕西日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构建与应用研究(2015K017)。
沈丽芳(1979—),女,河北邢台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近代文学。 沈媛媛(1980—),女,贵州贵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文学与教育。
I106.4
A
1000-5099(2016)06-0163-06
10.15958/j.cnki.gdxbshb.2016.06.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