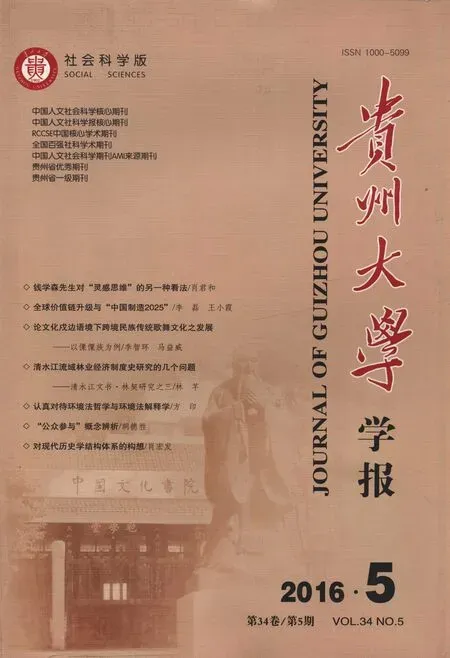自相矛盾人物形象的产生与化解
——以文艺复兴改革家萨伏纳罗拉为例
杜佳峰
(北京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1)
自相矛盾人物形象的产生与化解
——以文艺复兴改革家萨伏纳罗拉为例
杜佳峰
(北京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1)
萨伏纳罗拉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重要的历史人物,但无论是西方学界还是中国学界,都对他的历史定位长期存在偏差。本文归纳出诸多史学界主流的萨伏纳罗拉历史形象:西方对他的认识有意大利共和政治的捍卫者、固执中世纪思想的人等,中国则将他理解为人民起义领袖、宗教改革先驱、神权政治家和反人文主义者等。这些历史形象不仅导致了现代人对萨伏纳罗拉的误解,还阻碍了人们对文艺复兴运动中世俗与宗教关系的正确认识。唯有通过研究同时代人对萨伏纳罗拉的评价,才能消除偏见,还原萨伏纳罗拉的历史形象,重新审视文艺复兴时期世俗与宗教的关系。
文艺复兴;萨伏纳罗拉;人物形象;历史语境
吉罗拉摩·萨伏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是15世纪末期佛罗伦萨家喻户晓的政治家,他结合共和政治与基督教信仰理论,使之为复兴佛罗伦萨共和政治服务,并在1494—1498年的佛罗伦萨政治改革中实践了这一设想。萨伏纳罗拉不仅影响了马基雅维里和圭恰迪尼等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还对后世的德国农民战争中的百姓共和国理论和英国托马斯·莫尔等人的乌托邦思想产生了影响。
萨伏纳罗拉不仅有复兴佛罗伦萨的共和政治,他还是多明我会修士和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的院长,曾全力推进“基督徒正当生活”改革*基督徒正当生活运动,参见杜佳峰:《论萨伏纳罗拉的基督徒正当生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2016年第2期,第35-43页。,这使得他成为了争议人物,现代文艺复兴学界认为萨伏纳罗拉是一个需要一分为二看待的问题人物,有的认为他是宗教改革先驱、意大利共和政治的卫士;也有的认为他是中世纪思想的卫道士、神权政治家和反人文主义者。这些功过并存的历史形象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对萨伏纳罗拉言行中宗教因素的非议,对于宗教的偏见源于后世默认为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由宗教向世俗过度的历史运动,忽视15世纪意大利社会和文化也都完全处于基督教氛围的包围之中的历史语境。因此,唯有研究同时代人对萨伏纳罗拉的历史定位,才能消除“宗教偏见”,客观地还原萨伏纳罗拉的历史形象,重新审视文艺复兴时期世俗与宗教的关系。
一、历史发展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
萨伏纳罗拉在西方学界最主流的历史形象有两个:第一,意大利近代共和政治的奠基者;第二,人文主义文化的破坏者。第一种历史形象是在意大利形成民族国家的“复兴运动”(Risorgimento)中产生,由意大利历史学家帕斯夸莱·维拉利(Pasquale Villari)提出,他把萨伏纳罗拉塑造成了一个意大利近代政治思想的奠基者、一个为政治自由献身的共和战士。后一种形象是人文主义文化史的开创者布克哈特,他将萨伏纳罗拉塑造为一个人文主义新文化反对者和中世纪思想的卫道士。
19世纪后半叶,意大利“复兴运动”完成了民族国家构建和国家统一。萨氏被视为民族英雄,为了纪念他的牺牲,佛罗伦萨在1882年6月25日修建了萨伏纳罗拉广场,广场中央矗立起他的雕像。雕像右手向着天空高举十字架,左手抚摸着象征佛罗伦萨的雄狮,象征着萨氏结合基督教与共和传统,为维护佛罗伦萨自由而奋斗。雕像下有铭文:“384年后,被解放了的意大利献给萨伏纳罗拉。”*参见萨伏纳罗拉广场雕像的铭文:“A Girolamo Savonarola dopo trecentottantaquattro anni L’italia redenta”。萨氏逝世于1498年,意大利在1882年完成统一,这段铭文表明,萨氏已经与民族国家的构建相联系,他结合基督教传统与意大利共和自由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近代意大利的新思想,从而维护了意大利政治的共和与自由。萨氏被塑造成创造新文化的伟大思想家和维护佛罗伦萨政治民主自由的民族英雄。
这种历史形象提出者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帕斯夸莱·维拉利(Pasquale Villari),他在名著《萨伏纳罗拉生平与时代》一书中提出:萨氏是一个意大利现代文明的伟大思想家、一个保卫佛罗伦萨共和自由的民族英雄。[1]
维拉利认为萨氏是意大利现代文明的伟大思想家,具体是指他在努力调和基督教文明与现代文明。“意大利人(维拉利)看到的是一个先知,他对自己的时代有着令人称道的洞察力……维拉利认为萨氏深奥的思想是他把文艺复兴的新观念与基督教相结合的重塑……”因此,“维拉利的萨伏纳罗拉是一个双面的形象,既回顾中世纪,又展望新时代”,所以维拉利描述的萨伏纳罗拉是一个新旧时代的混血儿。“不过维拉利回顾的中世纪是一个公社自由,公共道德建立于私人道德,建立信仰的时代。”[2]4-5维拉利笔下的萨伏纳罗拉还是一个预言意大利自由的先知,他要唤醒人民,促使意大利人回归真我。萨伏纳罗拉要反对文艺复兴人性的解放唤醒的阴暗一面——肆无忌惮的自我中心主义。对维拉利来说,“萨伏纳罗拉就像哥伦布一样是文艺复兴的真正表率,他们都是对未知世界不知疲倦的探索者,都是破除了黑暗,开辟了新航道,在他们身上意志和信仰的动力大于理性的动力,他们都有先知的头脑,英雄的心灵和殉道者的命运。”[2]5所以,萨伏纳罗拉是意大利新文明的探索者,他的特殊使命是调和理性与信仰、宗教和自由。萨伏纳罗拉的事业有着继往开来的效用,他继承了天主教改革的传统,融合了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但丁等人的思想,所以他是意大利文明的伟大思想家。
维拉利把萨伏纳罗拉塑造成维护佛罗伦萨共和自由的民族英雄意图集中体现在《萨伏纳罗拉的生平与时代》中大洛伦佐·德·美第奇临终时与萨伏纳罗拉的一段故事里。大洛伦佐意识到他的大限将至,派遣他的儿子皮耶罗前往圣·马可修道院请萨伏纳罗拉为他做临终忏悔。萨伏纳罗拉在其的病床前提出为他做临终忏悔的三个条件:“第一,对上帝的仁慈要坚信不移。第二,你必须归还你所有的不义之财,或者至少令你的儿子们以你的名义归还它。”对于这两条大洛伦佐都点头以示同意。接着,萨伏纳罗拉提出第三条:“最后,你必须把自由归还给佛罗伦萨人民。”而大洛伦佐的表现却是“用他最后的气力,愤怒地转过身去,没有说任何话”[1]148-9。这段家喻户晓的故事中,萨伏纳罗拉象征佛罗伦萨的民主自由,大洛伦佐代表着大家族对佛罗伦萨的暴君专制。暴君愿意口头称颂和臣服上帝,也愿意散尽不义之财,但是他宁愿不被上帝宽恕也不愿意把自由归还给人民。而萨伏纳罗拉是与美第奇家族相对的共和自由的象征,同时,精英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也被维拉利认为是寡头统治。至此,萨伏纳罗拉与美第奇家族之间的政治斗争被描述成了共和民主与暴君专制之间的斗争,这个区分被现代许多研究者毫不怀疑的接受了。但萨伏纳罗拉是否提倡民主,大议会的扩张统治基础的初衷是否与现代西方民主是同一概念却是值得商榷的,萨伏纳罗拉政治改革的目的是推进佛罗伦萨的宗教改革,拯救佛罗伦萨人,并使得佛罗伦萨成为正基督教世界改革的引领者,这与西方现代提倡的民主政治也相差甚远。维拉利是一个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中的历史学家,要从历史中找寻为意大利争取自由的依据,因此,在他的笔下,萨伏纳罗拉成为一个意大利共和政治的守护者。
与之相对的是布克哈特笔下阻碍历史进步的萨伏纳罗拉。布克哈特的否定主要是针对萨氏的政治理想和文化措施。在政治上,“他的理想是一个神权国,在那里边所有的人都以神圣的谦卑服从不可见的上帝”,除此以外,“他的整个精神都写在‘市政厅大厦’上边的那个铭刻里边,铭文的实质就是他早在1495年所提出和他的党徒在1527年所庄严地再次倡导的那个箴言:‘耶稣基督按照元老院和人民的决定被选为佛罗伦萨人民的君主’。”[3]518-9可见,布克哈特把萨氏的政治理想理解为恢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政体,是和政教分离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在文化方面,布克哈特认为萨氏是反人文主义的,“我们不能想象有比这个更幼稚的推理方式”[3]520,萨氏和文艺复兴新兴的艺术科学是对立的,他禁止和对抗新文化,“新生的古典文化和由它带来的人类思想和知识的无限扩大,对于一种能够适合于这种情况的宗教可能给予很好的确认;这一种简单的想法,似乎甚至于从来没有在这个好人的头脑里发生过。他要禁止他不能用任何其他方法来应对的东西。事实上,他就是不开明的。”[3]520他还把萨伏纳罗拉和哭泣者派进行的宗教游行和“大焚烧”等守规运动认为是对世俗精神的一种倒退和徒劳地抵制,“他实际上是最不合适于做这种工作的人”[3]518。可见,布克哈特从政治和文化两方面认为萨伏纳罗拉是阻碍文艺复兴历史进步的,他是中世纪思想的产物,其思想与文艺复兴精神格格不入。
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几乎是与维拉利的《萨伏纳罗拉的生平和时代》同时出版,*维拉利的《生平》第一卷出版于1859年,第二卷出版于1861年;而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出版于1860年。但为什么布克哈特与维拉利的定位却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布克哈特的断代文化史研究秉持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和历史进步这两个观念。中世纪是黑暗的,文艺复兴是近代的前夜,是一个弘扬以人为中心的、强调世俗生活人文主义的时代。与之相对,布克哈特把萨伏纳罗拉与宗教相关的思想归结到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之中。因此,在布克哈特眼中的萨伏纳罗拉是与他所描述的以人文主义世俗生活为主流的意大利格格不入,是一个来自中世纪的人,阻碍了历史的进步。这又源于布克哈特的“现代性危机”史学观念,他恐慌过分强大的国家对人自由和个性的压迫,他的“国家、宗教和文化”三元推动历史动力中,只有文化是促进人的发展的,而国家和宗教是束缚人的自由创造的。文化、国家、宗教三中力量相互制约,共同影响历史的发展。布克哈特把文化与另外两个力量作为对照加以论述。文化是一种精神自觉的产物,它不要求普遍的和强迫的认可,因而文化相对国家和宗教这两个权威的力量是自由的。同时,国家和宗教是我们生活中两个相对稳定的机制,而文化则是代表这成千上万不同形式的变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潜能。因此,文化能起到对国家和宗教批判的作用。对此,布克哈特说:“文化对国家和宗教总是起催化剂式的或者瓦解性的作用。”[4]5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布克哈特对自由的向往,文化代表的是自由精神的产物,它受到的世俗的限制相对国家因素和宗教因素来说较小;而国家和宗教这两个力量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有强迫别人接受的特性,这也正是权力让布克哈特感到不安和窒息的地方。所以貌似三元的力量后面隐藏这文化针对国家宗教的对立,这种对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潜能和两个稳定的潜能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自由和秩序之间的矛盾。而萨伏纳罗拉思想核心是“国家和宗教”,这些正是布克哈特不喜欢的因素,因此,萨氏被称为了中世纪精神的维护者,成为人文主义文化史观所批评的对象。
总之,从萨伏纳罗拉两种对立的形象中,我们看到后世历史学家在构建萨伏纳罗拉人物形象带有主观性,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受到史学观念、政治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西方学界主流的萨伏纳罗拉形象未必就是符合历史原貌的形象。
二、中文语境下的萨伏纳罗拉
从中国眼光看萨伏纳罗拉的人物形象主要有以下四个:第一,人民起义领袖;第二,宗教改革家;第三,神权政治家;第四,反人文主义者。人民起义领袖的形象来自于中国古代史,宗教改革家的形象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研究有关,而神权政治家和反人文主义者则受到布克哈特文化史的影响。前两者是正面评价,后两者是负面的评价,因此,中国学界对萨伏纳罗拉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认为他既有进步性又有落后性,这实为一个模棱两可的评价。
第一,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人民起义领袖,这是萨氏最主要的中国形象,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萨服那洛拉起义”词条[5]632-3:“1494-149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城市平民反对美第奇家族专制统治的起义”,萨伏纳罗拉被认为是起义的领导人;“1494年,领导佛罗伦萨人民群众举行起义,推翻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回复了共和国”[6]600;“1494年9月在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之际,领导佛罗伦萨人民举行公开起义,把美第奇家族驱逐出境,恢复共和国”。[7]759这里“市民起义”是与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工人和无产者起义类比的结果,起义的原因是,“由于平民不满美第奇家族的暴政”,初期“建立了城市共和国”,之后,起义成果被窃取,“政权仍操在城市贵族之手”,革命的果实落到了由大商人、大银行家等大资本家等构成的“城市贵族”手中,最终,“当权的贵族”将萨氏杀害,起义失败,共和国灭亡,美第奇复辟。事实上,这是一场由城市显贵发动的推翻美第奇家族统治的政变,在政变的过程中萨伏纳罗拉并没参与,萨伏纳罗拉也不是因为未改善平民处境而失去支持,而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开除其教籍的绝法令。重要的是,他的被杀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覆灭没有直接关系,他被杀害于1498年,而佛罗伦萨共和国一直持续到了1512年,中间相隔着14年的时间。
第二,萨伏纳罗拉作为“宗教改革家”的形象。[5]632; [6]600; [7]759这源于人们认为萨伏纳罗拉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存在某种联系,其实,萨伏纳罗拉与路德的宗教和神学没有直接关系,两人的共同点只是因为反对教皇而被开除了教籍:1520年,马丁·路德当众焚烧教皇令,之后受到教皇开除教籍、停止圣事的处罚,当时他的处境与萨伏纳罗拉在1497年相似。1523年,路德出版了萨伏纳罗拉的一本小册子,这只是路德一生上千本书中的一本,但它却被后人用于证明萨伏纳罗拉是宗教改革前驱的证据,萨伏纳罗拉就“理所当然”变成了宗教改革的先驱。
第三个形象是神权政治家。他的产生与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有着密切关系,其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在1979年首次译成中文,他对文艺复兴人物的评价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中国反对僧侣干预世俗政治,认为这会导致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但对于宗教改革家却持肯定的态度,因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被认为是促进政教分离的和反对天主教的,而神权政治是封建制度的帮凶,它是控制人民的思想意识的工具。因此,萨伏纳罗拉转变为“一分为二”的历史人物。
第四个形象是反人文主义者。主要是针对萨伏纳罗拉的“虚荣之火”(Bonfire of vanities),他“在佛罗伦萨焚烧香料、面纱等奢侈品以及珠宝、华丽衣衫等珍贵品,连薄伽丘的《十日谈》和其它一些古典的和人文主义的作品也被付之一炬”,[7]759他“将许多华丽服饰、珠宝、奢侈品、艺术品和书籍付之一炬,禁止演奏世俗音乐,代之以圣歌”[6]600。萨氏在四旬斋焚烧奢侈和下流的物品,这只是一个仪式性的活动,象征性大于实际效果,是为了配合萨伏纳罗拉关闭妓院、禁止同性恋、打击奢靡淫秽、整肃社会风俗的改革,他向佛罗伦萨人提倡简朴生活,希望市民能过一种“基督徒的正当生活”。而后世将萨氏的“虚荣之火”夸大为成破坏艺术品、反对世俗文学的运动,并将其诟病为反对人文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萨伏纳罗拉的评价与当时中国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理解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中国学界认为,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反映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展开反对教会的精神统治和封建神学的斗争”,“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以神为中心考察一切。提倡‘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标榜‘人权’来反对教会的‘神权’,用‘人道’来反对‘神道’。他们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歌颂俗世,蔑视天堂,反对宗教束缚,主张个性解放,在历史上曾起过很大进步作用。”[8]226
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关于同一人物形象的异同,可以得出中国对萨伏纳罗拉形象既有接纳西方的部分,也有按照自己观念重新塑造的成分。“中国制造”是把西方萨伏纳罗拉形象纳入中文历史语境中,使用中国人熟悉的人物形象和概念去诠释外来人物,为的是使不为中国人熟知的、生硬的萨伏纳罗拉易于消化,但这种代入也使得萨伏纳罗拉却失去历史的精确性。人物的真实一面出现了变形,历史的真实性有所下降,例如:萨伏纳罗拉领导人民进行推翻美第奇专制、萨伏纳罗拉的死标志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覆灭等等,这些已经与真实的历史产生了错位。同时,人物原本的整体性与和谐感也被破坏,呈现在中国历史书中的是一个“矛盾的人”,一边是正面进步的反封建人民起义领袖,一边是禁欲主义、狂热宗教的神权政治家。这种对立分裂的人绝不是文艺复兴意大利环境中的人物所应有的,重塑破坏了萨伏纳罗拉自身的整体与和谐,在重塑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保留“原汁原味”,不去破坏本来的面目。
在中西方重塑人物形象过程中,都设想建立理想角色模型或者使用现成的角色模型,把历史人物纳入这个角色模型中;如果一个角色模型不能完全收容人物,那就用几个角色去容纳历史人物,试图用复数的理想角色模型去收容,结果却撕裂了人物的统一性。如何保留萨伏纳罗拉形象的真实性,是文艺复兴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难题。
三、解决萨伏纳罗拉形象失真的方法
上文各种有偏差的萨伏纳罗拉历史形象都是由于历史语境变化而产生的。脱离萨氏自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后世评价者在各自的语境去看待古人,这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历史人物形象。文艺复兴时代人与萨伏纳罗拉身处相同的历史语境中,他们对萨氏评价较后世更加贴近历史真实。文艺复兴重要的史学家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里亲身经历了整个萨伏纳罗拉的改革,我们通过他们的评价能够消除后世的偏见,了解一个更贴近原貌的萨伏纳罗拉。
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在1494年的美第奇政权倒台中幸存,经历了萨伏纳罗拉共和国时期,在美第奇家族复辟后,又在两位美第奇教皇*利奥十世和克莱门七世。的治下担任官职,他将萨伏纳罗拉视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圭恰迪尼钦佩萨伏纳罗拉的能力:“花费笔墨讲述他的品质并不为过,因为在我们、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所处的时代,从未有一个修士拥有如此多的美德,或者说从未有一个人获得如此高的名望和权威。甚至他的敌人们都承认他在许多方面的博学……在我看来,他的布道清晰地说明了他谙熟统治这个世界的原理。”“因为他践行的结果是如此的好,又因为许多他的预言实现了,尽管有绝罚令,有审判和处死,但许多人继续相信他真的是上帝派遣的,是真的先知……我确实相信:如果他是好的,那么我们见证了一个自己时代的伟大先知;如果他是坏的,我们见证了一个伟大的人。”[9]148圭恰迪尼还褒奖了萨伏纳罗拉政治改革的两大成果:建立大议会和促成反美第奇的新政府与前美第奇政权的支持者达成大和解,这缓解佛罗伦萨内部的党争,促进内部的团结,“是萨伏纳罗拉修士独自使避免所有的混乱
成为可能。他引入了大议会,它给那些想成为城市统治者的人套上了缰绳。他向执政团提议,这扮演了保护市民的守卫。他带来了大和解阻碍了那些在重建古代秩序旗帜下想要惩处美第奇支持者的人。无疑这些措施拯救了城市……”[9]147-148而作为美第奇支持者圭恰迪尼本人也受益于萨伏纳罗拉“大和解”的政治大赦。
虽然圭恰迪尼任职于美第奇家族,但他内心的理想政体是萨伏纳罗拉所宣扬的民众政府。在《洛格罗尼奥论集》中他接受了萨伏纳罗拉把共和作为佛罗伦萨天性的观点。萨伏纳罗拉认为并且共和制已经成为佛罗伦萨的第二天性,“佛罗伦萨的人民从古代就选择了市民政体,并形成了许多与之相应的习惯,市民政体比别的形式的政体更加自然更得到赞同,因为习俗已经深深地烙在市民们的心中,要他们抛弃这种政府是困难和不可能的。”“我们意识到不仅个人统治的政府不适合于佛罗伦萨人民,而且精英市民统治也不适合,因为风俗是第二个天性。”[10]182-183圭恰迪尼沿着这条思路又说:“佛罗伦萨人此时已十分习惯于他们的自由,觉得自由‘对他们说来是与生俱来的’,而且认为自由乃是‘该城固有的和天赋的’”。[11]167在《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中,圭恰迪尼也说:既然“该城一向是自由的”而且“天生是自由的”,那么佛罗伦萨人由于他们的政治传统和“既定条件”就有义务要捍卫这种已经被接受的价值。[11]167可见,在15世纪的历史语境中,圭恰迪尼并没有感受到萨伏纳罗拉宗教与政治结合的不妥,而是更加关心萨伏纳罗拉的政治能力和思想。
与圭恰迪尼的大加赞扬相比,马基雅维里对于萨伏纳罗拉的评价更加冷静,他更多地看到了萨氏的政治野心和手段。马基雅维里是在萨伏纳罗拉倒台,其追随者“哭泣者派”*1494—1498年,佛罗伦萨内部的主要派别:哭泣者派(Piagnoni),支持萨伏纳罗拉,政敌嘲笑他们在听修士布道时哭泣而得此名;疯狗派(Arrabbiatti),由反对萨伏纳罗拉的城市显贵组成,他们既反对萨氏,也反对美第奇家族复辟,政敌嘲讽这派激烈的反对声如疯狗狂吠,因此得名;灰党(Bigi),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在新政府治下,无法光明正大的行事,只能在阴影中活动。逃亡,政府职位出现空缺的情况下担任官职的*马基雅维里1498年6月被“大议会”任命为第二国务秘书。。作为一个他认为萨伏纳罗拉是狡猾的,萨氏通过宗教宣传的话语巧妙地把的自己的政治动机伪装起来。
在萨伏纳罗拉去世多年后,马基雅维里在书信中,马基雅维里在和圭恰迪尼书信讨论要为羊
毛业行会物色一个布道者,说要找一个“比吉罗拉摩修士更奸诈”的人,[12]635这流露出马基雅维里对修士的看法。马基雅维里认为萨伏纳罗拉“狡诈”的原因是:萨氏巧妙地把政治动机伪装起来,假借上帝名义宣扬改革。在《论李维》第1卷第11章《论罗马人的宗教》谈及宗教信仰对国家昌盛的作用时,把信仰作为国家幸福是主要原因,“它(信仰)促成了良好的秩序,良好的秩序有为国家带来好运,好运使得国家事业多有成就”,同时又提出敬畏神明比敬畏君主对国家更有利,“敬奉神明是共和国成就大业的原因……失去对神明的敬畏,王国要么覆灭,要么援以对君主的敬畏,而这种敬畏,无异于取信仰之短。”[13]79-80之后,马基雅维里又说:“共和国或王国的安全,不系于生前治理精明的君主,而系于一人妥善谋划的制度,使其死后仍能存续。化外之民固然更易于服膺新的制度或见识,不过,那些自诩不属于化外之民的文明人,并非完全不可说服。佛罗伦萨人看上去既不蒙昧,亦非蛮人,教士吉罗拉莫·萨伏纳罗拉却能让他们相信,他是代上帝立言。我不想深究此事的真伪,因为在谈到这位大人时,我们应当心存敬畏。不过我确实要说,虽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使人们必须相信他,相信他的人仍然无以计数。因为他的生平、他的学术、他所延揽的臣僚,足以让人们对他深信不移。然世人不必因为未能做到别人成就的事而气馁。”[13]79-80最后一句流露出对萨伏纳罗拉治国能力的认可,赞扬萨伏纳罗拉运用信仰凝聚人心化解了政府危机的能力。
他认为萨伏纳罗拉奸诈主要是因为萨氏在具体政务处理中不守法律、党同伐异。在《李维史论》第1卷第45章中,马基雅维里批评萨氏:“不遵守法律,尤其是立法者本人所为,便树立了恶劣的先例”[13]161-162,这个不守法的批评是针对1497年8月萨氏不遵守自己设立的上诉法,借着“五人叛国阴谋”审判,处决自己的政敌。
从马基雅维里和圭恰迪尼对萨氏的评价中,我们能够看到,虽然在他们眼中的萨伏纳罗拉形象是不同的,但是对萨氏的政治能力都予以肯定。我们能够感悟到那个时代的佛罗伦萨政治家,他们更多思考的是现实问题,关心的是政府统治如何复兴佛罗伦萨,怎样实现国家的“富裕、强大和荣耀”。同时,在当时人眼中,用“神意”为政府提供了政体理论合法性,符合当时佛罗伦萨安定发展的需要,萨氏的基督教并不是要退回中世纪,而是在创造一种新的模式,这与后人认为宗教是阻碍文艺复兴运动的观点截然不同。
历史人物形象的构建是每一个历史研究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萨伏纳罗拉的个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后世研究者的分析固然重要,但有时候却是遮蔽了历史人物的原貌,使人物呈现出荒诞和矛盾。这时只要结合历史事件,回到同时代人评价,才能逐步理解人物和历史的原貌。
[1] 〔意〕 Pasquale Villari.Life and Times of Girolamo Savonarola [M]. Linda Villari, trans.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09.
[2] 〔美〕 Donald Weinstein.Savonarola and Florence: Prophecy and Patriotism in Renaissanc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3] 〔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 〔瑞士〕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M].金寿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 简明历史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6] 世界历史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7] 大学历史词典[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8] 中外文化知识词典[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9] 〔意〕 Francesco Guicciardini.The History of Florence[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10] 〔意〕Girolamo Savonarola.Selected Writings of Girolamo Savonarola[M]. trans. Anne Borelli and Maria Pastore Passaro.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英〕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文艺复兴[M].奚瑞森,亚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12]〔意〕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利全集:书信集(上)[M].段保良,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3.
[13]〔意〕马基雅维里.论李维[M].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方英敏)
2016-07-12
杜佳峰(1985—),男,上海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意大利文艺复兴史。
D091
A
1000-5099(2016)05-0018-06
10.15958/j.cnki.gdxbshb.2016.05.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