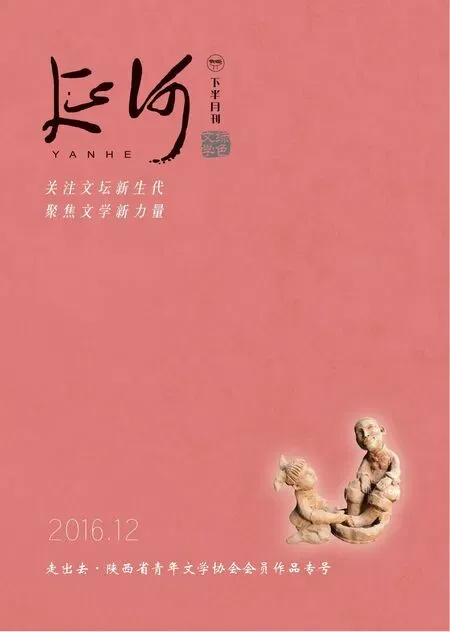秘 密
□ 李尔莉
秘 密
□ 李尔莉
一
有的秘密,就像枯萎的日历,顺手一扔便可,即使在风里飘扬,也没有人愿意过问;有的秘密,要年年清洗晾晒,防止岁月的尘埃涂抹演变,使它露出一点点儿端倪。
梅走了好多年了,就连她的名字也被好多人从记忆里驱赶出来,偶尔有人提起梅,也没有人详细打听。可是,梅却在我的记忆里结晶成体,无论走在哪里,都会提醒我——梅有一个秘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秘密。
梅常给我讲述自己的感情经历,梅说希望我能替她写点文字,当初我并没有感觉到梅有死亡的趋向,因为梅才三十一岁,况且像梅一样的女人见得多了,自然就少了灵敏度,甚至感觉她提供的素材也平淡无奇,于是,没有写下一段与梅有关的文字。
直到那个深夜,梅的QQ突然亮了起来,并且给我发过来一条短信息:“还记得我对你说的话吗?你一定要替我写点文字。”然后又变成灰色的离线状态,梅的QQ已经有五年处于离线状态,按理来说,我应该删去她的QQ,毕竟阴阳两隔。可我并没有感觉到恐惧,我怀疑这是梅生前写的一句话,可能设置了发送时间,慢条斯理到五年以后才发送过来,她要提醒我,她一定要做我的小说的主人公。我将梅的QQ空间打开,里面的日志早已清除,只有梅的一张照片,肤如凝脂的脖颈围着薄如蝉翼的粉红色纱巾,头发打理得似瀑布般流畅,眉眼清秀如深潭秋水。她双眼凝视着我,含情脉脉爱意浓浓,好像有许多话要倾诉一样。
夜深了,窗外漆黑一团,只有汽车的鸣笛声断断续续地传进来,好像要扰乱我的写作空间。可是,我看着梅的照片,浮想联翩,就连妻子什么时间端进来一杯菊花茶,我都全然不知。我抽完烟盒里的最后一根烟,吐了几个好看的烟圈,在烟雾弥漫的空间,我仿佛看到了心事重重的梅,眉宇间蹙成一个疙瘩,坐在我的对面,像林黛玉一样: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突然我有许多话想说,或者说是替梅说说。
二
“梅,你也老大不小了,有了工作,找个好婆家,不要再让家里人操心,咳——”母亲拍打着胸口,好不容易把话说完,然后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脸黑紫黑紫的。就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随时等待病情的惩罚或者纠缠。
“妈,我知道,你放心,婚姻大事我一定慎重考虑!”梅赶快把母亲扶在床边,并且递过来一杯水,嘱咐母亲吃药。
母亲常年有病,脸色时常是黑紫色的,虽然不干重活,可家里乱七八糟的事也够她担了,所以,病情一天天的恶化,有时还呕血,她的身体每况愈下,这让梅不由地产生了压力,肩负着重任。懂事的梅不断地安慰母亲。她知道母亲成天为她担忧,怕她吃不饱穿不暖,怕她没钱花没人照顾没有立足之地。母亲是个病人,按理来说没有多少精力替她操心,可是,母亲又如何能轻易放下这些忧虑呢?这是一个母亲的责任或者说是墨守成规的约定。
梅,天性儒雅,外貌清纯,话语柔和。她的工作是当“孩子王”。孩子王,一个诱人的头衔,整天面对一双双充满求知欲望的眼睛,不断地进行传道授业解惑,那是何等的幸福和骄傲。这正是她所渴求的职业,她知足了,满意了,脸上时刻写满了笑容。
有了一个铁饭碗,就告别了伸手问父母要钱的日子,再不要羡慕别人的漂亮衣服,再不要因为没有钱而放弃她所需要的东西,一件美丽的衣服,一套昂贵的化妆品或者一部爱读的名著。总而言之,她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可以支配自己的钱财,可以挺直腰板走路,可以出入各个超市。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为母亲选几件像样的衣服,为弟弟选几本课外书,过年过节也可以大包小包地出入家门。
“梅娃,你不是说有个男孩对你不错吗?你感觉和他合适吗?”母亲忽然追问起这件事,让梅也不由地想起这位俊逸的男孩来。
他是一个潇洒的男孩,一米八五的个头,国字脸,浓眉,目光犀利,唇角柔和,看上去刚柔相济,一表人才。尤其是他的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他的眼睛会让人浮想联翩,如果说世界上真有一见钟情,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
男孩是来学校接弟弟时认识她的,当他看到腼腆的她,娴静文雅的她,温柔似水的她,他就产生了一种冲动,有一种想和她搭讪的冲动:“我弟经常提起你,说你是个好老师。”他望着她,含情脉脉的,像一个熟悉的友人,他的脸上当然还有笑容,他的脸上总有法国人所谓“意气相投”的和善的感觉,加上高高的额头和粗粗的黑发,他的脸更给人有一种自我的精神美。
“你弟乖巧聪明,我很喜欢他。”她说的是真话,他弟弟品学兼优,尤其是那双大大的眼睛,这或许就是遗传因子,给他们本来就好看的脸面更是增添了几分姿色。
从此,他借故接送弟弟经常来学校,他们很快就熟悉了,也就开始了如火如荼地恋爱。她也逐渐地了解了他,他叫王浩,家在城里,有楼房有宝马,父亲是工头,家境很好。可遗憾的是他没有正式工作,他上学不爱学习,拿到书就打瞌睡,好不容易凑合到高中毕业,就跟着父亲学包工。他真实地对她表白,表面上看他并没有欺骗她,可他已经欺骗了她,因为他并没有告诉她,他正在恋爱当中,他们已经恋爱八年之久。这是一个秘密,他并不能泄露天机。
随着情感加速的升温,他们已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可是她害怕,因为在农村,铁饭碗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她对自己的婚事开始担心。结果正是如此,当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都坚决反对。他们不允许一个大学毕业生嫁给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不管他家境有多好,钱财有多少。
可梅并没有听从父母的摆布,她是新社会的人,她相信爱情,相信爱情这种别样的感觉,这种真实的情感。她爱他,她无法放弃这段感情,她决定与父母抗衡,她要嫁给他。她与他如胶似漆,甚至周末也不回家,因为她不想听父母的唠叨,因为她的爱情她做主,因为她知道:真正的爱情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
不久以后,母亲病倒了,母亲危在旦夕,母亲接受不了女儿的果断做法,母亲为自己的呕心沥血而悲痛。母亲终于抵抗不住病魔的快速蔓延,不到一个月,母亲就走了。
母亲走的时候,梅不在家,她还在城里工作,在城里恋爱,爱得热火朝天。当她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她愕然了,她想不到母亲能走得这么匆忙。母亲的病虽说很难治愈,但也不至于这么快就离她而去。她哭天喊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她抚摸着母亲黑瘦的脸颊,紧握住母亲冷若冰霜的目光,她哭得哀怨凄迷揪人心肺,哭得抽抽噎噎气绝声衰。她的哭声响遍了整个村庄,感天地,泣鬼神,村里的街坊四邻也饱含热泪劝她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并且说人死是不能复活的!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有好长时间,梅都生活在一个极度内疚的世界。母亲的离去,让她变得悲观起来,她不能原谅自己的轻率举动。可是她又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因为她生活在一个自由恋爱的年代,难道她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爱情吗?她不断地扪心自问。
三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人常说:孩子就活个妈,没有妈,温暖就少了;没有妈,家里也冰锅冷灶的,没有妈,家里的笑声也少了,家庭成员也都变得沉默寡言,气氛一天天紧张起来。
从此,梅成了一个没妈的孩子。本来患病的母亲却因为她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对于她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她茶饭不思,不久也病倒了,这时王浩寸步不离,他给她提饭打水,给她削苹果扫地洗衣服,她被他感动,尽管她失去了母亲,但她还是不能失去他。
父亲拿她没办法,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看到摆在他面前的四十个响洋坨子,他也动心了。钱似乎能买通一切,父亲的脸上终于绽开了笑容。不过一年时间,父亲就用这些钱给她找回一个后妈,还连带着一个憨儿子,头摇得像拨浪鼓,一问三不知,问他多大了,半天掰着指头,说八岁,今年八岁,明年还八岁,后年还是八岁。尤其是他的饭量大得吓人,三碗不饱五碗不放,好像上辈子就是个破纪录的“一级乞丐”。
有了后妈的家,梅回家的次数少了,可是每到逢年过节,她还没忘记给母亲上坟,在母亲的坟头诉诉苦衷,拉拉家常。死了的人上了极乐世界,而活着的人又将要承担多少痛苦?
这个后妈,人还不错,精明能干。当她回来的时候,后妈总是热情地招待,不是炖肉就是包饺子,父亲兴致勃勃地品尝着锅里还没有炖好的羊肉,嘴角呈现出享乐主义的弧线。可见,父亲并没有因为母亲的离去而痛苦不堪,反而因为新婚的甜蜜而年轻了好多,精神了好多,说话做事利索了好多,这让梅的内心有一种无法表白的酸楚。人啊人,死了的苦了自己,活着的人照样春风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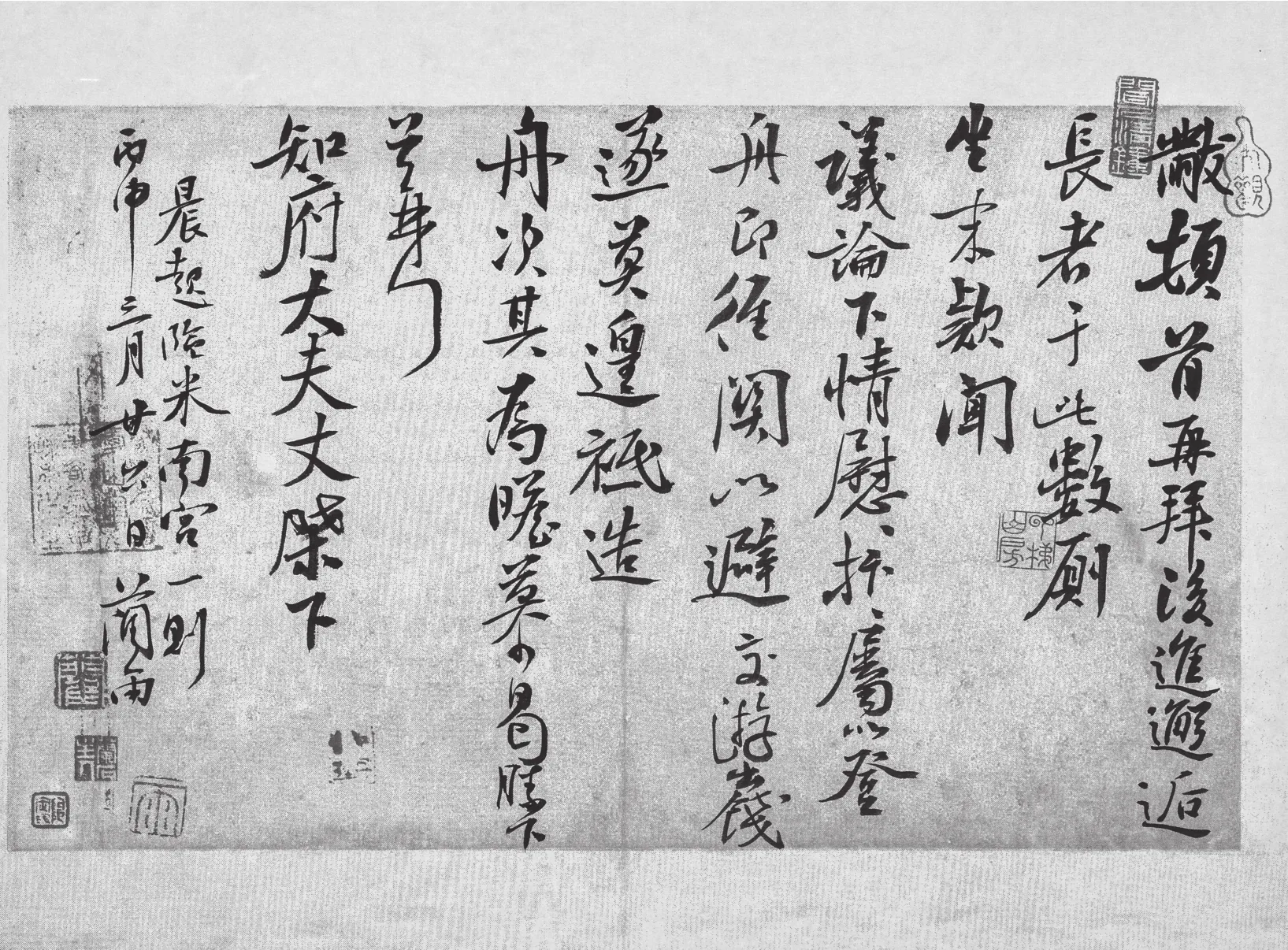
蔺雨 书法
“大姐,你真好,来了给我带这么多好吃的。”后妈的憨儿子小宝不知何时把她的包打开,他慢条斯理地品尝着这些从未见过的东西,什么的瓜果梨枣面包饼干,西红柿黄瓜茄子,就连生虾生鸡生鱼他也不放过,他的脸糊得五花八门,还一个劲地叫嚷着:“大姐,没味道,嚼不烂。”
“小宝,你又胡闹了,看我打死你。”后妈拿起笤帚照他的屁股扔过去,他却跪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好像一个木桩,脸色红不红白不白的,呈现出一副不羞不臊厚颜无耻,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父亲的脸憋得通红通红的,直朝小宝翻白眼。在他的心里早就引发了一场战争,主角就是他和小宝,他正在殴打小宝,把他压在地上,使劲地打,狠狠地打,用笤帚打,用鞋帮打,用拳头打,但现实呢?他只能翻翻白眼解解恨,他知道如何把握一个度,如何经营这段还算幸福的婚姻,毕竟她还是爱她的,给他做饭洗衣,给他铺床暖被窝。在他需要她的时候,她会紧密地配合,让他恢复了男人的阳刚之气,再不要藏在被窝里想入非非彻夜难眠,受那种孤苦伶仃的个人主义罪。其实他对这个傻儿子早就不耐烦了,不仅能吃能喝能说,还常常惹得鸡犬不宁,母鸡不下蛋,他非要抓住揣摩看有没有怀蛋;狗不咬人,他非要拍打着狗脑袋问:为什么见了生人不“汪汪”?直打得狗一见他就耷拉着脑袋,连眼睛也不想睁,好像遇见了仇人一样。甚至对母亲半夜跑在父亲的被窝里,都要把灯打开探个究竟,质问母亲为什么夜里乱跑,问他们呼哧呼哧直喘气,是不是晚上做梦还在赛跑?搞得人哭笑不得,拿他没办法。
有一天,小宝神秘地失踪了,家人找了一天一夜,最后还在他的呼噜声的提示下找到的。那呼噜声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就像一台将要断电的录音机。当大家找到他时,他躺在一堆谷草上呼呼大睡,怀里抱着二十个热乎乎的鸡蛋。在你推我搡的过程中,他终于醒了,还理直气壮地说他在孵小鸡呢!
对于家,梅总有一份牵挂,因为家里还有生她养她的父亲,父亲的幸福也就是她的幸福。她衷心地希望父亲能平安幸福,她虔诚地希望父亲能学会宽容。对傻儿子小宝,也应该像亲生儿子一样,毕竟他是维系他们第二次婚姻的纽带。
四
蓝天铺着一层撕开的云絮,风在沙地上奔跑,扯起团团尘雾,像手舞足蹈的精怪。
王浩一家人对梅的体贴和照顾,让梅感动了,让梅走火入魔了,梅与王浩未婚就同居了,梅非得嫁给王浩。
“我今晚不回去了,就住在你这儿。”王浩死皮赖脸的一再恳求她。
这不是一次两次了,王浩以前提出要与她同居的要求,她都婉言谢绝了。她是农村长大的女孩,受传统思想的约束,她不能在婚前失去女人的贞操。她把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可是,他的咄咄逼人,他的情真意切,让她时刻有乱了分寸的可能,终于乱了,那天,她也动了真情。在他的一阵又一阵的狂吻之后,她情不自禁地解开了自己的衣服。她在那个寂静的夜晚里,恐慌而又沉默地经历了由女孩到女人的转变过程。她的身体开始飘升,像一朵失去了家园的云。又一次的,她听到了自己的尖叫,那尖叫充盈在宇宙之间,来回反射。那一夜,整个城市的房子都好像晃动不安起来。那一夜,寒冷的严冬溪流淙淙,花朵吐蕊,树摇春风。
他看着那块血红的床单,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得到了她,她也得到了他,他们也该结婚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他们很快就结婚了。王浩家里给梅的父亲拿了四十个响洋坨子,还送给了四万元钱,说是彩礼也不是,哪有这么多的彩礼;说是抚养费也不是,哪有公婆给媳妇还抚养费的。反正这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进了梅的父亲的腰包,梅的父亲很高兴。不管怎样,梅找了个有钱人,城里人,家底厚实的人,他安心了,满意了,见人话也多了。没说几句就非要扯起他家梅,说她婆家有车有房有钱,说她家钱多得没处花,钱像复制的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农村人都睁大好奇的眼睛听梅的父亲夸夸其谈。他们早听说过有钱人,但具体没见过有钱人的模样,所以,每当梅与王浩回来,农村人都要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要探个究竟,看城里的有钱人究竟什么派头,模样和农村人一样不一样,说话和农村人一样不一样,走路和农村人一样不一样,打哈欠和农村人一样不一样,谈恋爱和农村人一样不一样……
王浩对农村人的虎视眈眈有些不解,但他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面对这么多双鬼鬼祟祟的眼睛,他依然镇定自若,该笑的时候笑,该说的时候说,该抽烟的时候抽,该打哈欠的时候也打,该与梅打情骂俏也照样进行。你打他一下,她打你一下,然后就是手拉手,肩并肩……农村人通过仔细地观察,认真地研究,终于总结出了一些道理:城市人里比农村人穿得干净利索些,说话比农村人用的修辞多了一些,走路比农村人脚抬得高了一些,打哈欠比农村人多了一个动作,就是用手遮住偷偷地打。城里人敢爱敢恨,打情骂俏也无拘无束,旁若无人一样。他们似乎明白了好多关于城里人的事情,于是,他们知足了。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梅家的老院子,好像把好多的心事已经看穿,他们的心情特别好,三个一群,两个一伙说说笑笑,各抒己见。路旁的白杨树也冲他们不断地点头哈腰,好像突然很崇拜他们,认为他们是心中的偶像。
后妈系着围裙忙得不可开交,打鸡蛋烙饼子,鸡肉摊馍馍羊肉饸饹,好吃的办了个遍。土特产洋芋绿豆荞面装得大包小包的,也把车装得满满的。
不结亲两家人,结亲就是一家人。王浩临走的时候,还不忘记给岳父岳母每人怀里塞一千元钱,让他们买两件好衣服穿,把傻小子小宝半面着急得直叫唤,说姐夫怎么小看他,不往他怀里塞几分钱,让他也买几个糖蛋蛋,把大家逗得前俯后仰,说这个傻小子脑子还清楚着呢!
五
一年以后,梅就生了个千金,孩子的出生,并没有影响他们夫妻的感情,他们依然感情深厚,从没有吵过一次嘴,而且脸也没有红过一次。
随着孩子的出生,王浩的事业也蒸蒸日上,而且每年赚不少钱,本来家底不错的他,更是更上一层楼,他们的小日子过得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没钱的盼钱,有钱的又盼孩子多情人多,有了孩子又盼孩子的性别比例平衡,有了情人又盼后院不要起火。
于是,没有儿子的生儿子,没有女儿的生女儿。偷偷摸摸地生明目张胆地生,想方设法地生绞尽脑汁地生,有的办假离婚,有的四处逃匿,有的干脆出钱买准生证。总而言之,大家都冥思苦想地生,生一胎,再生一胎,直到男女平衡为止。
当然,有了钱的王浩也不例外,他终于与梅达成了协议,要梅再生个儿子。梅是贤妻良母,梅也喜欢儿子,梅自然配合默契。经过处心积虑地酝酿,梅终于怀孕了。结果,生的还是千金,谁知王浩很豁达,并且说不管男女,都是一种福气,他们的两个女儿,更是给家里增添了几分温馨和热闹。
就在生完第二个女儿四个月以后,梅病了,梅和母亲患的病一样,医生说是遗传病,本来患这种病的女人不能生养,梅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医生说如果她不要生第二个孩子,或许病不会发作。
梅的脸色像她的母亲一样,也开始变暗变黑变紫,药瓶子也开始围着她团团转,不能伤心也不能激动。俗话说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脾,她像一个活着的死人一样,躺在哪儿,就是哪儿,没有一点表情色彩,像谁丢下的一口袋粮食。她渐渐地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人也憔悴不堪,家里的气氛立刻变得浓重起来,孩子也仿佛有了心事一样,心情跟着大人的脸色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人要是倒霉起来,盐生蛆,背生疮,背个手电不聚光。就在梅患上重病的同时,王浩回家的次数也少了,偶尔回来一次,不是半夜就是三更,梅问起他,他总是用忙搪塞而过。
忽然梅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王浩回家总是唉声叹气心事重重,难道王浩遇到麻烦不成,终于有一天,在梅的一再追问下,王浩说出了心里话:“梅,我做生意赔了,我们俩办个假离婚,把家产全部抵押给你。”王浩的头低着,好像一个罪犯一样。
“真的吗?为什么,这几年我们总是不如意?”梅哭了,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王浩抱紧了梅,他们大哭了一场,第二天,梅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梅相信王浩,这是假离婚,梅没有半点疑问。
六
离婚以后,王浩回家的次数更少了。每当梅打电话问起他,他总是支支吾吾吞吞吐吐,有时说忙,有时说有应酬,有时又说在外地采购材料。
梅相信王浩,作为男人,就要以事业为重,所以他的忙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是生意赔本的王浩。
“梅,你上当了,王浩在外面早有了女人。”
“梅,不要再妄想了,王浩有了新家。”
“梅,我见你家王浩领着一个女人。”梅的同学纷纷打来电话。
“哪有的事?王浩对我很好,我们从来也没有吵过架,我相信他。”梅对别人的说法置之不理,梅根本不相信王浩会背叛他。
“梅,你上当了,王浩在外面有了女人,而且那个女人已经生下了儿子。”姐姐也这么对她说。
“无中生有。”梅上前给姐姐一个耳光,这是生气的、愤怒的耳光,这一个耳光也意味着梅开始确认这个事实,她隐隐约约感觉到事情不妙。
她终于拨通了王浩的电话,她要问个究竟。
可是电话那一头,是长久的沉默,紧接着听到一个女人的骂骂咧咧摔盆子掼碗声,最后电话还是断了,好像被谁摁断了。
梅终于清醒了,可是她是个病人,医生嘱咐她不能生气不能劳累,要好好休息,可是她能不生气吗?她也患了失眠症,她的眼泪尽情地流,这是一个女人唯一的办法,她无法保护好自己,这多年以来,是她自己欺骗了自己,是她主张的自由恋爱,把她推向了悬崖峭壁。
梅一病不起,躺在病床上的梅,后悔当初听信王浩的甜言蜜语,让她失去了母亲,也让她生不如死。可是这一切都晚了,这是人生的一团谜,今生她也无法解开。
王浩终于来了,他流着泪,怀中抱着刚满两周岁的小女儿。她紧紧地抱着爸爸,生怕他走了,大女儿含着泪默默地望着父亲,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走过去,握紧父亲的手,这时父亲的手机响了:“你他妈的,又哪去了,买的奶粉在哪里?你听见了吗?”电话里是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声音,她的声音很高很高,高过城市,高过医院,高过梅的耳畔,高过纷乱的浮躁的世界。
听来她是一个泼辣的女人,没有梅的温柔体贴,没有梅的知书达礼,没有梅的豁达开朗,然而,她却胜利了。
“梅,好好养病,我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他站起来,低声嗫嚅着。他才刚刚坐下有几分钟的时间,是电话怂恿他站起来的。他的脸色苍白无力,他瘦了好多,眼窝也深陷,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
梅没有说一句话。她枯瘦的双臂慢慢地抬起来挡住自己多余的视线,她的眼前一片模糊,黑咕隆咚一片。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从房顶上落下的雨滴,笃、笃、笃,一下又一下,似是落在人心里,溅起一圈圈的涟漪来。
七
那是一个阳光充足的下午,天空澄澈,树阴碧绿,风像绿薄荷一样清亮。梅打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那是三年前读《婚姻与家庭》时抄过来的三段话:
“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一书中提出,社会冲突最深层的原因在于生存空间的窄逼,对立、敌意、暴力皆由此而生。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家庭的冲突若援引莫里斯的看法,也可以认为是家庭中的主要成员——夫妻双方生存空间的逼迫引发的。要使家庭能‘长治久安’,根本的方法就是解决空间的紧逼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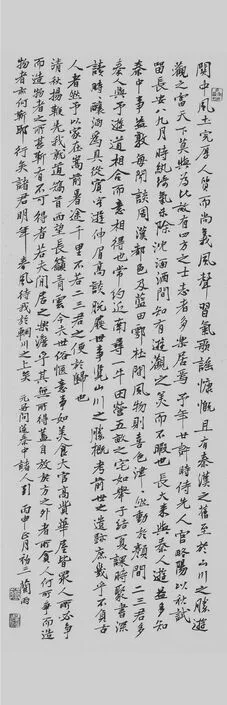
蔺雨 书法
“婚姻为相爱的人营造了共同生活的合法空间,婚姻要求两个个体尽量发挥彼此的共性,允许保留自己的个性。但是,在现今人人要求体现个性的社会,个性却在婚姻中慢慢磨灭,个人的空间成了一种奢望,她生活在他的呼吸中,他总在她的眼皮下。他们开始拥有的越来越多,房子、车子……但是,个人空间却在渐渐丧失,甚至成了稀缺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不防试着把你们的婚姻空间做一下‘格式化’处理,就像把电脑的硬盘空间重新分配一样,分为C、D、E盘,甚至再多几个也可以。可以分配一个区间给你们婚姻中共同承担的部分,假设就是C盘,并把它设为共享盘,这个空间由你们俩人共有。然后在剩下的空间里,为自己找一个空间,假设它是D盘,再允许另一半使用E盘。一般情况下你们不用踏入对方的区域,如果需要也可以进去窥探一下。如此,你们就可以做到既在一个家庭的氛围中,有共同承担的责任部分,也能享有个人空间了。如果想保留个人‘绝对隐私’,还可以在自己的盘里建个文件夹,然后加密处理。这看起来是e时代处理婚姻关系很不错的办法。”
梅仔细读了这三段话,她的脑海里立即涌现中一串串疑问:婚姻空间能做格式化处理吗?网络和现实真能结合起来吗?记得曾有一个叫“神秘使者”的网友要和她交朋友,并且要求和她视频,她婉言谢绝了,而对方却发过来一段文字:“这是一个网恋年代,人们的心思再也不会停留在现实中孤注一掷,而是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网恋不会拆散家庭,甚至终生不需要见面,只通过一张虚拟的网,结婚生子,甚至过日子,这样可以弥补现实给人带来的空虚和百无聊赖。”而她却因为这段话,将他拉入了黑名单,因为她不需要网恋,那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她感觉他有点神经质,她只喜欢现实,现实里有可以触摸到的爱,家庭,婚姻,安全的港湾,温馨的呼唤。
八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手机响了,梅的脸上立即浮起一丝笑意。
“你还好吗?我很想你。”梅听出来这是王浩的声音。正当她打算倾诉,倾诉她对他的爱,她对他的恨,可是对方只说一句话然后就挂断了。好像他们的通话有约定的期限,如果超出期限,就会发生什么意外。
从此,病床上的梅,每天都会接到一个祝福她的电话,每当接完这个电话,梅的脸上就会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梅还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她要好好地活着,她相信王浩能回心转意。
山上的打碗碗花开了,苦菜花也开了,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季。梅坐在阳台上,手里拿着一张发黄的照片,那是她与王浩的结婚照:他们幸福地相拥着,她在笑,他也在笑,那是人生最灿烂的笑容,也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她看着微笑的王浩,忽然感觉到他就在面前,正讲述着这几年的不易。先是那个女人的诱惑,继而她又以怀孕威胁他,如果不结婚,她就要起诉他。
于是,他们结婚了。可是他一点也不幸福,他想的是梅,他想天天回来看梅,可是那个女人太厉害了。她不让他离开半步,也不让他打电话给她,还命令他换了电话号码。
那个女人叫芸,是他的初恋,也是他上学时的同学。他们从初中就开始恋爱了,长达八年之久,最后还是他提出了分手,因为他的生活中有了梅,于是他对芸说:我们分手吧,以前毕竟我们太小,不能承担爱情这个永恒的责任。
当听了王浩的绝情之言,芸傻眼了,想不到她一心一意地爱他八年,最后换来的却是他的一句话。那天,她撕碎了他的所有信件,偷偷地离开了这座城市,去远方独自谋生。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她终于成功了,有了自己的公司,可是她还是没有寻找到如意郎君。她把他们与王浩对比,没有王浩的潇洒漂亮,没有王浩的能言善辩,没有王浩的成熟稳健。于是,过分挑剔的她依然一个人生存。
谁知十年以后,在生意场合,他们又一次相遇,而且成了合作伙伴,她依然爱着他,她要想方设法得到他。
于是,她不断地引诱他,人说: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终于他也动摇了,就当逢场作戏罢了,可是他并没有想到离婚。
他要像一些成功的男人一样,家里的红旗不倒,外面的彩旗飘飘。
可是,事在于人而不在流的问题,这外面的彩旗飘久了,就累了,就需要一个温馨的港湾,需要一个安全地带,需要战争,需要武器,需要裁判,需要优胜劣汰。
在那个女人的威逼利诱下,他投降了,他屈服了。可是离婚的他,并不幸福,他想两个女儿,想一病不起的梅,可是他经受着另一场婚姻的约束,他背叛了梅,也背叛了自己。他陷入一个内疚的世界,不断地折磨着闹腾着这场盲目的婚姻。
王浩并没有来。王浩被爱的绳索捆绑着,梅终于失望了,她紧紧地抱着这张结婚照,幸福地闭上了眼睛。这时窗前的梅花开放了,颤颤地立在枝头,婉约而清丽,在如血的夕阳里,摇曳出令人垂泪的风姿,有一滩鲜红的血瞬间弥漫了朦胧的往昔,城市的步伐越走越快,窗外鞭炮声阵阵,唢呐声阵阵……
又有一对新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走进了婚姻这座坟墓,经受着幸与不幸,体会着吵吵闹闹爱爱恨恨离离合合的婚姻经历。突然一个豁牙老汉高声说:又有一个女孩要变成女人了,又有一个男孩要变成男人了,紧接着是一阵哄堂大笑,从偌大的玻璃窗外面争先恐后地钻了进来,遗憾的是,她再也听不到了。
可是,有谁知道,就在前一小时,梅突然有过一个惊人的决定,让一切从头开始。她重新启动电脑,准备对硬盘进行格式化,她知道这样多年的心血就此将化为乌有。没什么,一切从头开始,梅这样安慰自己。
突然屏幕跳出一个小窗口,像一个妩媚的眼睛:你确定要进行格式化操作?这样会丢失所有的资料,那里面包括你们结婚十年的明细账簿,有苦,有笑,有苦笑不得;有爱,有恨,有爱恨情仇;尤其是还有你们离婚的原因:谁是第三者,至今是一个谜……梅平静地点击了“YES”按钮,然后就伏在键盘上呜呜地哭了,肩膀一抽一抽的。因为她知道一个更加残酷的事实,婚姻并不能格式化。
这时一个女人走进了她的视线,她穿着一件雪白的夹克衫,配着黑色打底裤和黑色短裙,黄色的套花长筒靴镀着零零星星的水钻。她与一个男人勾肩搭背,他们同时沉浸在MP3的音乐里,音乐声很大,从劣质的耳机里漏出那首歌:baby,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回去谈何容易,确定你就是我的唯一,独自对着电话说我爱你,我真的爱你。这时他望着她,含情脉脉的,他的脸上当然还有笑容,他的脸上总有法国人所谓“意气相投”的和善的感觉,加上高高的额头和粗粗的黑发,他的脸更予人有一种自我的精神美。
这时,另一个女人也走进了她的视线,她烫了一头羊毛卷发,脸上拍着厚厚的脂粉,嘴唇涂得像火焰山,给人以烧灼感;眉毛黑漆漆的,如两道深渊;耳朵、脖颈、手腕和手指上戴着形形色色的饰品,胖得汹涌澎湃,她满脸杀气腾腾,骂骂咧咧,像要和谁进行一场大战一样,但他们对于她的辱骂置若罔闻,他们认为她神志不清。因为这是十年后的自己,他们根本认不出她,他们只知道她早已化作了尘埃。
西边山头上的日头,“哐当”一声滚落到山下去了。梅的身躯也跟着倒下了,紧接着半山坡上多了一座坟茔,坟茔上长满了野草野花,有绿的,红的,粉红的,五颜六色争奇斗艳。蝴蝶在花丛里翩翩起舞,将最美丽的夏天封存起来。
九
夜深了,窗外依然人声鼎沸,城市的夜并不孤独,因为,每到深夜,妖魔鬼怪就会混在人群里声嘶力竭。在这个噪声污染的世界,我终于完成了这篇小说。
我又一次打开梅的QQ空间,用黑体字写下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我一直记得你,其实,婚姻并不能格式化,可是以前我并不知道,毕竟我认识你时才二十二岁,那时我还没有结婚,并不知道婚姻是什么,能不能格式化也很难说清。”
突然梅的QQ亮了起来,而且很快做出回答:“如果我还活着,如果我们现在才认识,那该有多好!”
我迅速关闭了电脑,我再也不敢与她网上聊天,毕竟我们阴阳两隔,我为她做的只有写这篇小说,其余的只能用沉默的叙述方式来表达,因为梅根本不知道,我就是她的网友——“神秘使者”,虽然她把我拉入黑名单,但是我用另一个网名“重新再来”加了她,我原打算和她进行一段网恋,因为后来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爱上了她,并不是乘虚而入,相反,感觉她是一个值得爱的女人,就连她在病床上每天接的一个电话,也是我假装王浩打的。为了给她生活的勇气和力量,我费尽了心血,但是最终她还是化作了尘埃,我才发现:网络,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网络,是泡沫上的舞步,薄冰上的行走。
有些东西,可以时时刻刻与之相对。但其实,你只是在消磨——消磨时间和孤独。像浮在水面的肥皂泡沫,太浅,瞬间即逝,所以无法触及灵魂。我说的,仅仅是网恋。
□李尔莉,吴起县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会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出版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