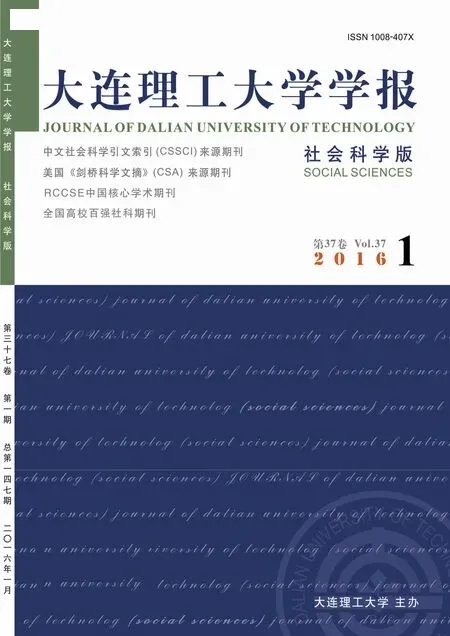元代“歌诗”的繁荣与历史定位
韩 伟
(1.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2.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元代“歌诗”的繁荣与历史定位
韩 伟1,2
(1.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2.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歌诗”是对中国古代尤其是汉代以后入乐之诗、可歌之诗的泛称,元代是古代歌诗发展的重要时期。元代歌诗在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同时,亦与辽、金“歌诗”传统有所联系。此种背景下,“歌诗”概念在元代被普遍接受并使用,很多文人陆续创作了大量的歌诗作品,其热情不亚于杂剧和戏曲的创作。同时,元代“歌诗”理论也表现出了崇尚情性、崇尚自然声律的特征,这与时代主流的理学思想形成了对话关系,表现出二元性特征。整体而言,元代“歌诗”在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史上是十分必要的一环。
元代;歌诗;二元性
元代仍坚持以“歌诗”概念对可歌之诗、入乐之诗进行称呼,且尽管有些元代诗歌甚至唐宋作品是否入乐现在已不可考,但透过元人的一些记述,可以发现实际上以前我们熟悉的很多诗人的诗作是可以歌唱的,起码在元人眼中是这样的。元的歌诗创作较之辽金要繁盛得多,且歌诗观念在元代文人中十分普遍,在他们眼中入乐可歌是诗歌的应有之义。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将着重对元人的歌诗观念进行考察,并试图钩沉元代重要的歌诗作品。
一、辽、金“歌诗”的中介作用
辩证地看,辽人文化乃至文学水平的落后,对于可以歌唱的歌诗而言恰是好事,使得许多诗作仍保留着相对原始的诗、乐不分的特点,这与汉族文学自汉代以后便出现的诗乐分途局面不尽相同。现存最早的契丹族诗歌是《焚骨咒》,全诗仅仅四句:“夏时向阳食,冬时向阴食。使我射猎,猪鹿多得。”[1](p3)它是契丹人焚化父母尸骨时所吟唱的祷祝之歌,并希望得到祖先的庇佑,较为质朴自然,体现了契丹原始文化中相对朴拙的一面。从全诗的外在形式上看,前两句对仗相对整齐,同用“食”字结尾,后两句虽为叙述,但仍押韵,加之该诗属于祭祀所用之“咒语”,所以总体上应是唱诵的乐歌。另如刘海蟾的《还丹破迷歌》,全诗较长,现仅列前四句便可窥其大略:“传闻世人有金丹,学者如麻达者难。不在水,不在山,原来只是在人间。”[1](p11)可见全诗带有极强的口语性和民间性,非常适宜歌唱。
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创作尚处于原生态的状态,而从原生态到文人态的转向发生在圣宗朝之后。在辽中后期,其文学水平大幅度提高,此时辽人的音乐实践开始逐渐丰富,并较重视音乐人才。据辽人王鼎《焚椒录》记载,道宗时耶律乙辛曾上《奏懿德皇后私伶官疏》[2](p182),载皇后与伶官赵唯一私通事,而赵唯一被选入宫中则“以弹筝琵琶,得招入内”。对此,王鼎在《懿德皇后论》[2](p207)中认为“私通”一事是“史册所书未有之祸也”,为懿德皇后(即萧观音)鸣不平,称懿德招祸原因为“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能诗善画耳”。对这段公案之是非姑且不论,从另一个侧面则可反映辽宫廷对音乐的重视程度。辽最成熟的歌诗作品当是寺公大师所作的《醉义歌》,全诗120句,是最能体现契丹文化发展水平的作品,也是契丹文学艺术领域所达到的最高峰,该诗原用契丹文字书写,元著名文士耶律楚材将其译为汉文,其在译序中称寺公大师“贤而能文,尤长于歌诗”、“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这些评价虽有过誉之嫌,但不难看出其对寺公大师的敬服。
由此可以看出,契丹民族的歌诗是有一个日渐成熟的过程的,早期歌诗带有较大程度的天然性和封闭性,突出表现为采取相对自由的形式表达主观情感,这在圣宗朝之前的作品中体现尤为明显,圣宗朝之后逐渐开始体现出汉文化影响的特征,比如已经存在唱和体(如《玉石观音像唱和诗和诗二十四首》)、歌行体(如《醉义歌》)、骚赋体(如《绝命词》)等。
金朝无论在音乐、歌诗创作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表现出与辽朝明显不同的样态。辽的文化起点较低,而金从建国之初便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就歌诗而言,其在数量上明显多于辽代,在质量上由于金初文坛基本以“借才异代”的方式为主,所以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高士谈、马定国等一批亡宋文人承担了金初文化建设的主要责任。总观金朝歌诗,以世宗朝为界可以分作前后两期,前期带有较强的自发性和朴素特征,后期歌诗则主要以道教歌诗为主,全真道人成为创作主体。
首先考察世宗以前的歌诗情况。现存较早的金朝歌诗与其他民族一样带有较强的巫文化色彩,《金史·谢里忽传》载:“国俗,有被杀者,必使巫觋以诅祝杀之者,乃系刃于杖端,与众至其家,歌而诅之曰:‘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白尾,横视之则有左右翼者。’其声哀切凄婉,若《蒿里》之音。既而以刃画地,劫取畜产财物而还。其家一经诅祝,家道辄败。”[3]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金初文化仍较为原始,被杀之家要接受巫觋的祈祷,其祷词实为一种带有程序化的祭祀套语,音声悲凉。需要指出的是,金朝处于这种艺术相对粗疏的阶段较短,建国之后很短的时间内便发生了从原始歌诗到文人歌诗的跨越。宇文虚中、高士谈等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歌行、词曲、吟颂等形式相继出现在金源文学领域,较典型者如高士谈的《春愁曲》,“芙蓉帐暖春眠重,窗外啼莺唤新梦。……游丝飞絮俱悠扬,慵倚绣床春昼长。郎马不嘶芳草暗,半筛急雨飞横塘。”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女子慵惰闲适的外在形态,美景与美人相得益彰。而且宇文虚中、高士谈等文人最大贡献不仅体现在其自身创作的文学作品上,更主要的是他们营造了一种较好的歌诗氛围,金末文人刘祁在《归潜志》中有如下一段话:“先翰林尝谈国初宇文太学叔通主文盟时,吴深州彦高视宇文为后进,宇文止呼为小吴。因会饮,酒间有一妇人,宋宗室子,流落,诸公感叹,皆作乐章一阕。宇文作《念奴娇》……次及彦高,作《人月圆》……宇文览之,大惊,自是,人乞词,辄曰:‘当诣彦高也’。”[4]这则记载虽为文坛轶事,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宗朝以前歌诗唱和的繁荣局面,文人歌诗的出现是对世宗朝之前的原始歌诗的超越。
世宗朝以后,除了文人歌诗向更为华丽的方向发展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道人歌诗的大量出现,甚至其质量和数量可以与文人歌诗相比肩。其实道人歌诗的开创性人物当是被奉为全真祖师的重阳子王喆。王重阳富于文采,他的作品大多带有较强的宗教说理色彩,但语言形式并不晦涩,读来通俗易懂,很多作品适于歌唱,以《了了歌》为例:
汉正阳兮为的祖,唐纯阳兮做师父。燕国海蟾兮是叔主,终南重阳兮弟子聚。
为弟子便皈依,侍奉三师合圣机。动则四灵神彩结,静来万道玉光辉。
得逍遥,真自在,清虚消息常交泰。元初此处有因缘,无始劫来无挂碍。
将这个,唤神仙,窈窈冥冥默默前。不把此般为妙妙,却凭什么做玄玄。
禀精通,成了彻,非修非炼非谈说。惺惺何用论幽科,达达宁须搜秘诀。
也无灭也无增,不生不灭没升腾。长作风邻并月伴,永随霞友与云朋。
整首诗以宣扬道教逍遥、自在的精神追求为主,口语色彩较浓,与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跛足道人所唱《好了歌》颇为相似,在王喆文集中这样的宗教歌诗尚有许多。世宗朝以后,道人歌诗仍然在自己的系统中发展,题材内容上较为一致,文体上仍然以倡道之“歌”为主,且带有仪式性。全真道人如王处一、刘处玄、丘处机、白道玄、侯善渊、李道玄等都有大量此类诗作,限于篇幅不赘列。
综上,金代的文人歌诗与道士歌诗虽然沿着各自的脉络分别向前推进着,但其总体趋势是相似的,文人歌诗水平远远超于辽代,而接近两宋水准,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元代文人歌诗乃至音乐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中介性的作用。与此同时,道人歌诗主要以全真道人的作品为主,这些作品在宣扬道旨的同时,在形式及艺术性方面有所拓展,体现出了文人歌诗对道士歌诗的影响和渗透,这也为元代道教文学地位的确立,以及道士歌诗的大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元人对“歌诗”之体认及创作
“声诗”概念与“歌诗”概念在元人文集中都曾出现,对于中国古代音乐文学中的这两个概念在宋代以后的使用情况,笔者曾在拙著《宋代乐论研究》中用一节的篇幅加以考订[5](p192-197),兹不赘述。相较于“歌诗”,“声诗”概念在元代出现的次数则十分有限,袁桷在《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书余国辅诗后》中有这样一段话:“余尝以为声诗述作之盛,四方语谚若不相似,考其音节,则未有不同焉者,何也?诗盛于周,稍变于建安、黄初,下于唐,其声犹同也。豫章黄太史出,感比物联事之冗,于是谓声由心生,因声以求,几逐于外,清浊高下,语必先之,于声何病焉?法立则弊生,骤相模仿,豪宕怪奇而诗益浸滛矣。”[6](p1231)可以说袁桷的认识在元代是一种共性认识,在当时文人看来“声诗”特指“有声之诗”,运用这一概念时主要的目的是想表明诗歌的音乐性,“若声诗者,古之乐章也”[7],先有声音然后才有文字形态的诗歌,且这种声音也必须是人内心的真情实感,也就要求文学创作不能先设立外在的框架然后才“为文造情”,因此这也是对诗歌创作尤其是宋代以来诗歌创作弊端的反思。由此可见,在元人文集中“声诗”概念的偶尔提及,其目的并非进行定义,而是为了说理。相形之下,元代文人反而更愿意使用“歌诗”概念,宋元时期“歌诗”除了可以涵盖新旧题乐府、唐教坊体(如《阳关曲》、《柳枝》、《杨柳枝》等)之外,尚有乐语、口号、乐章、上梁文、青词,以及一些杂记文和墓志铭后面的赞语等,对此笔者将另作专文具体介绍。
元诗中乐府体和歌行体大量出现,占相当大的比重,几乎每个诗人的诗集中都有这类作品。这是与宋代明显不同的[8],且较金代歌诗也前进了一大步,究其原因是元代文人歌诗创作有意回避宋人诗歌的枯瘠,而追慕汉唐文风,有意恢复诗歌与音乐之间的天然关系。所以,歌诗或者更大范围来讲,音乐文学到了元代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很多元代文人眼中,宋代之前的诗歌多是入乐的,所以多以“歌诗”称之,对音乐文学异常繁荣的唐代更是如此,这一点在元代辛文房所编的《唐才子传》中有充分的体现,兹罗列数例:
有冠冕佩玉之气,宫商金石之音,为一代文宗,使颓纲复振,岂易言也哉?固无辞足以赞述云。至若歌诗累百篇,而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卷三《韩愈传》)
自李杜之后,风雅道丧,至元和中,暨元白歌诗为海内宗匠。(卷三《张籍传》)
能博览为歌诗,议论多出于正义刚直。(卷三《刘义杰传》)
乐府诸诗云韶众工皆谐之律吕,尝叹曰:“我年二十,不意一生愁心,如欲谢梧桐叶矣。”李藩缀集其歌诗,因托贺表兄访所遗失,并加点窜付以成本。(卷三《李贺传》)
乐府歌诗,高雅殊绝,拟蔡琰胡笳曲,脍炙当时。(卷四《刘商传》)
由是为汉南幕宾,日与谈宴,歌诗唱答,大播清才。……有歌诗六卷,今传。(卷四《刘言史传》)
效李长吉为歌诗,颇涉狂怪,耸动当时。(卷六《赵牧传》)
峤,字延峰,陇西人。宰相僧孺之后,博学有文,以歌诗著名……自序云:“窃慕李长吉所为歌诗,辄效之。”(卷六《牛峤传》)
王毂,字虚中,宜春人。自号临沂子,以歌诗擅名,长于乐府,未第时尝为《玉树曲》……(卷七《王毂传》)
自称桑苎翁,又号东冈子,工古调歌诗,兴极闲雅,着书甚多。(卷八《陆羽传》)
善为歌诗,性诙谑,不修检操,工画山水。(卷八《顾况传》)
韬玉歌诗,每作,人必传诵。(卷九《秦韬玉传》)
鼎,字台业……工诗,集一卷,今行。同时赵抟,有爽迈之度,工歌诗。(卷十《张鼎传》)
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时与王执谦、杨载齐名,《唐才子传》成书于元大德八年(1304),书中保留了大量唐代诗人(也包括部分五代诗人)的生平传记。由所列文字可以看出,元文人仍然通用歌诗概念,辛文房对唐“才子”多存服膺之情,对他们的歌诗才能十分推崇,该书虽属辑录性质,但通过对术语的运用亦可看出辛文房的基本思想倾向。辛文房的具体生卒年虽不可考,但大略可以确定其属于元代前期人物,《唐才子传》是宋元之际诗风转变的产物,可以说该书的基本倾向也是元代整体歌诗观的缩影。
基于对前代歌诗风习的推崇,元代本朝歌诗唱和之风亦十分盛行。元人不仅在创作层面有意追崇汉唐,大量创作乐府、歌行,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进行唱诗活动,文人间的相互唱和始终有音乐相伴,这一点也体现出了对汉唐音乐文学传统的继承。在他们看来,前代尤其是与之较为接近的唐代诗歌多是可以歌唱的,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评价杜甫《题省中院壁》便说“此篇八句俱拗,而律吕铿锵。试以微吟,或以长歌,其实文从字顺也。”[9](p1114)在方回看来即使有的诗歌为拗体难合格律,但只要能符合演唱之音律也属于上乘之作,方回实际上属于由宋入元文人,在文学史上通常将其归入江西诗派后学一脉,其同黄庭坚后期的诗学旨趣一样[5](p237-251),较重视从实际律吕和歌唱的角度看待诗歌是否优美,配乐能歌是其衡量诗歌优劣的重要标准。为了实现唱诗的目的,他有时甚至将一些诗歌与已有的歌诗唱腔进行嫁接,在谈到宋人胡宿《过桐庐》(原诗:两岸山花中有溪,山花红白徧高低。灵源忽若乘槎到,仙洞还同采药迷。二月辛夷犹未落,五更鸦臼最先啼。茶烟渔火遥堪画,一片人家在水西。)一诗时,称:“武平此诗妙甚,八句五十六字无一字不佳,形容桐庐尽矣。起句十四字并尾句,可作《竹枝歌》讴也。”[9](p1405)即是主张用唐教坊曲《竹枝词》的格调对之进行歌唱,这是宋代以后一种典型的“着腔子唱好诗”的方式。可以说,方回的观念在元代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
元代许多著名诗人都擅长歌诗创作且有作品存世,比如戴表元、杨载、范梈擅长创作歌行。杨维桢和萨都剌的乐府诗独具特色,甚至元末很多文人竞相模仿唐刘禹锡《竹枝词》,以“西湖竹枝词”、“海乡竹枝歌”等为名进行大量创作。以杨维桢为例,在他看来律诗的出现是对音乐文学传统的戕害,“诗至律,诗家之一厄也”,因此他极力倡导古乐府,其门人吴复在至正六年将其作品编辑为《铁崖先生古乐府》十卷,其中多数作品沿用古调,也有在仿古基础上有所创新的,比如在该书卷十列有《西湖竹枝歌》9首、《吴下竹枝歌》7首、《海乡竹枝歌》4首,这些作品便是在保留原有格律、曲调的基础上反映“西湖”、“海乡”、“吴下”具体地点的所见所闻,极富写实性。
从元代《竹枝词》的流行可以想见元代歌诗创作风气之盛。除《竹枝词》之外,其他乐府旧题也在元诗中大量出现,而且元代文人所作、所唱的歌诗并不仅限于乐府、歌行等传统体裁。他们对音乐文学传统的接续是全方位的,这集中表现为他们不仅以“歌诗”称呼汉唐乃至宋朝的入乐之诗,甚至对本朝诗歌亦以“歌诗”加以泛称:
今年春,房山高公彦敬归休于旧隐,夏五月,延陵吴君成季,首为歌诗以致其怀贤 之思,于是次于其后者,凡十余人矣。(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四《仰高倡酬诗卷序》)
(萧景能)尤喜为歌诗,以汉、魏、晋为宗,下此惟陈子昂、李太白、韦应物以为稍近于古。长短句则曰:“周美成、秦少游、姜尧章吾师也。”(揭傒斯《揭傒斯文集》卷八《萧景能墓志铭》)
赤城黄岩之境,有山曰委羽;有士曰刘德玄;隐居自放,不求闻于人,独喜为歌诗。情有所感,辄形于言。(贡师泰《玩斋集》卷六《羽庭诗集序》)
《鹊华集》者,集贤直学士、陇西侯李公所著歌诗也。(贡师泰《玩斋集》卷六《鹊华集序》)
闽海佥宪郑君彦昭,间集其歌诗为二卷,题曰《行役藁》、《揽辔藁》,携以示予。予读之,而有以知其心之所存、作之不苟也。(贡师泰《玩斋集》卷六《郑彦昭诗集序》)
庐山陈君惟允好为歌诗,凡得若干首,读之悠然深远,有舒平和畅之气。虽触事感怀,不为迫切愤激之语,……自成天籁之音,为可尚矣。(倪瓒《清閟阁集》卷十《秋水轩诗序》)
延陵谢君仲,野居乱世而有怡愉之色,隐居教授以乐其志,家无瓶粟,歌诗不为愁苦无聊之言,染翰吐词,必以陶韦为准则。(倪瓒《清閟阁集》卷十《谢仲野诗序》)
于是进士临川葛元哲闻而叹美之,题其所居曰“孝友之堂”,亲为制文以记之。四方之士得诸传诵者,作为歌诗,以反复咏叹其事。(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陶氏孝友堂诗序》)
往年客钱塘,与金仁翁、刘养源、处静辈,商略乐府,往往花朝月夕,皆能自为而自歌之。(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九《王德玉乐府倡答小序》)
通过上列文字,反映了当时的著名文人如袁桷、揭傒斯、倪瓒、戴表元等都不约而同地以“歌诗”称呼时人作品,其中戴表元是元初力主文坛革新主将,其“尊唐弃宋”的主张对元中后期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袁桷曾受学于王应麟和戴表元,其诗学观点与戴表元相近,推崇唐音而反对江西诗派。揭傒斯为“元诗四家”之一,主张诗法正宗,诗文要以六经为楷模。倪瓒诗风清雅,不事雕琢,其诗学主张亦是如此,杨维桢称其“风致特为近古”。同时,上列的各种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还原当时社会的文学状况,从而能够为我们构筑一个更为圆融的元代音乐文学景观。由于史料有限,所以很多元代文人及其文集在文学史中都无法出现,对他们的创作亦不得而知,在这些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元人的歌诗创作热情是十分高涨的。总之,虽然元代的歌诗创作不如杂剧和戏曲为人们所熟知,但其在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史上却是十分必要的一环,没有元代的承传,就不会有明清的延续。
三、元人“歌诗”观的二元性
下面主要从理论层面梳理一下元人的歌诗理论和歌诗倾向。诚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比较而言,在这时的诗文领域中,却显得比较沉寂,杰出的大诗人寥寥无几,卓有识见的诗论专著更是凤毛麟角。”[6](前言p10)确实,与杂剧、散曲、南戏的创作及理论相比,诗歌领域显得不够繁盛。元代总体上是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其虽产生于宋代,但真正被官方认可且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时期则是在元代。因此,元代的文艺理论基本是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展开的,很多文人如许衡、刘因、吴澄等都首先是理学家然后才是文学家,即使是以文学见长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柳贯、黄溍等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理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对元代的整体文艺思想亦需要辩证地看待,就与文学相关的音乐思想来说,因为元人仍主要坚持传统的礼乐观,加之理学的现实影响,所以乐论表现出与理学的密切联系。就文学思想而言,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文论与诗论有所交叉但又不完全相同,文论主要以雅正淳厚为基本指导,体现出对汉魏文风的皈依,诗论尤其是歌诗理论则更多地表现出崇尚性情的特点,理学的影响较淡,体现出对歌诗精神的因袭。
以理学家吴澄为例,其基本的理学倾向是以调和朱、陆为主,推崇朱熹格物、诚意之学,也倡导陆氏学必以德性为本之说,创立“草庐学派”,《宋元学案》有《草庐学案》,其对理学在南方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与同一时期的北方的许衡并称“南吴北许”。与此同时,他也颇富文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六《吴文正集》提要称其“词华典雅,往往斐然可观”。吴澄与宋代以来其他的理学家相比,其诗学思想表现出与理学倾向若即若离的倾向,具体而言其诗学思想虽然有理学的影子,受邵雍影响较大,《元诗选》中称“先生雅好邵子书,故其诗多近之”[10],而其更多地表现出对唐诗尤其是晚唐诗风的追慕,从而形成了一种“风格雅淡,情意深浓,笔法也颇老苍”[11]的诗风,故明人徐渤说其“专志理学,而诗亦多巧思”,往往能够“超脱理学蹊径”[12]。
与这种倾向相一致,吴澄的歌诗思想亦表现出崇尚情性、崇尚自然声律的一面,所以他在积极主张恢复音乐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也承认“人声”的重要性,在《四经叙录》中他说:“《诗》风雅颂,凡三百十一篇,皆古之乐章。六篇无辞者,笙诗也。旧盖有谱以记其音节,而今亡,其三百五篇,则歌辞也。乐有八物,人声为贵,故乐有歌,歌有辞。”[13]对人声的承认表明其歌诗思想并不是完全如宋代理学家一样受“天理”所左右的,这也是其诗论思想中较为透脱的一面。受其影响,他的学生虞集对人之“情性”的重视要更进一步。虞集是元代中期著名学者、诗人,与揭傒斯、柳贯、黄溍并称“儒林四杰”,在诗歌领域与杨载、范梈、揭傒斯并称“元四家”,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等。虽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理学思想,但在文学领域颇有建树,清四库馆臣称“大德、延祐以还……要必以集为大宗”[14]。虽然文学史上通常将其归入元中期师古之风的代表人物,但需要指出的是其所崇尚的“雅正”观,实际上便是对清新自然诗风的追求。他一方面认为歌诗当与社会、政治相连,“世道有升降,风气有盛衰,而文采随之。其辞平和而意深长者,大地皆盛世之音。”(《李仲渊诗稿序》)承认自先秦以来“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儒家正统诗乐观,与此同时,亦承认人之情性在歌诗创作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诗人应具备六个条件:“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学其资也,才其能也,气其充也,识其决也。”(《易南甫诗序》)很显然他是将性、情看作诗歌创作的最主要因素,惟其如此方能体现出与世道伦常的真切联系。就其歌诗思想而言,也与上述总体倾向保持一致,他所崇尚的古代歌诗传统实际上是一种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的传统,“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顺之积而发于咏歌,故其声气明畅而温柔,渊静而光泽”(《李景山诗集序》)。其自然、质朴的歌诗美学在其文集《道园遗稿》中有最为集中的体现,具体而言该文集卷二为七言古诗,基本上以歌行为主,卷六为乐府。一些优秀的歌诗作品如《吴中女子画鸟歌》、《墨竹歌》、《射虎歌》、《烛影摇红》、《蝶恋花》、《贺新郎》等都收在上述两卷之中,另外在其《道园学古录》的《归田稿》部分也收录了一些歌诗作品,不赘述。
如果说吴澄的歌诗观是理学家阵营歌诗观的缩影的话,那么虞集则代表了文学家阵营的歌诗思想的主要方面,与吴澄有类似观点的还包括揭傒斯,其主张“诗者,人之情性,途歌里吟皆有可采”(《文章正宗》),承认真情实感对歌诗的重要性。刘敏中在《江湖长短句引》中主张“声本于言,言本于性情。吟咏性情莫若诗,是以诗三百皆被之弦歌,沿袭历久而乐府之制出焉,则又诗之遗音余韵也”[15],认为以乐府为代表的歌诗与人之真性情密不可分。元代文人中有上述观点的人还有很多。总之“吟咏情性”这一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在元代的出现频次是非常高的,有学者曾指出元代文学的“吟咏性情”有“感性”和“理性”之分[16],笔者认为用之区别元代文人歌诗观与理学家歌诗观也是适用的,前者对性情的认同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以及“四灵”、江湖诗派诗风进行纠正基础上的,从而回归到自然真性情的正确轨道上来。后者对性情的重视,主要是在理学框架下完成的,其所谓的“性”、“情”是在“理”的背景下展开的,带有形而上的色彩和道德纯粹性,这就与文人眼中的自变性情不同了。
[1] 阎凤梧,康金声. 全辽金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2] 陈述. 全辽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元)脱脱等. 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540.
[4] (金)刘祁.归潜志:卷八[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83-84.
[5] 韩伟. 宋代乐论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6] 吴文治. 辽金元诗话全编[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7] (元)胡翰. 古乐府诗类编序[A]. 李修生.全元文(第51册)[C].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186-187.
[8] 韩伟. 声诗还是歌诗:宋代音乐文学概念辨析[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4(4):121-124.
[9] (元)方回. 瀛奎律髓汇评[M]. 李庆申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 (清)顾嗣立. 元诗选:初集卷十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32.
[11] 邓绍基. 元代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438.
[12] (明)徐渤. 徐氏笔精[M].(清)纪昀,永瑢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6册[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02.
[13] (元)吴澄. 吴文正集[M]. (清)纪昀,永瑢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
[14] (清)纪昀.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97.2228.
[15] (元)刘敏中. 中庵集[M].(清)纪昀,永瑢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6册[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79.
[16] 查洪德. 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M]. 北京:中华书局,2005.149.
Prosperity and Historical Position of Geshi in Yuan Dynasty
HAN Wei1,2
( 1.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2.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
Geshi is the name of a kind of special poetry, which can be sang in ancient China. And Geshi of Yuan not only is influenced seriously by Han nationality culture, but also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eshi of Liao and Jin. In Yuan Dynasty, it is widely accepted and used, and a lot of scholars gradually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them as well as drama and opera. Moreover, the Geshi theory of Yuan respects feeling and natural rhythm, which forms the dialogue relation with the thought of Neo Confucianism, showing the feature of duality. Overall, Geshi of Yuan is an essential part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China music literature.
Yuan dynasty; Geshi; duality
2015-05-23;
2015-07-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乐论与文论的关系谱系研究”(14CZW001);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中国古代乐论与文论的关系谱系研究”(2014T70180);黑龙江省普通高校青年学术骨干项目:“中国古代乐统重建与文统分化的关系谱系”(1254G031);黑龙江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辽金元音乐文学及其理论形态研究”(UNPYSCT-2015055)
韩伟(1981-),男,黑龙江海伦人,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美学研究,E-mail:hanweihekelina@163.com。
I 207.209
A
1008-407X(2016)01-01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