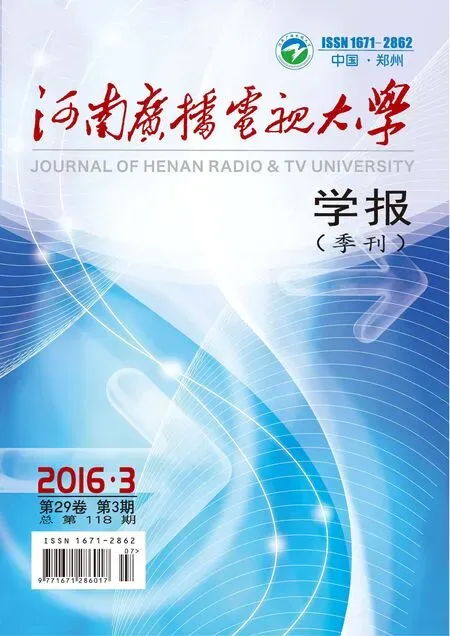从容跨越先锋浪潮——余华创作转型研究
张晓敏
(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6)
从容跨越先锋浪潮——余华创作转型研究
张晓敏
(辽宁大学,辽宁沈阳110036)
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很有影响力和个性的一位作家,他始终秉承着自我真实、不断思考、勇于改变的创作实践。在他将近30年的创作中,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型,1990年左右的第二次转型因直接和先锋文学的走向以及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关系密切,因而格外引人瞩目,这次转型也让余华从容地跨越了先锋浪潮,为自己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疆土。以此次转型为出发点,通过解读余华小说文本,重点探讨余华小说在主题内涵和艺术运筹上转型的具体呈现,并且以此为基础,分析余华转型的精神驱动力。
余华;小说创作;转型;先锋浪潮
一、在冷酷中回归——余华小说主题内涵的转型
(一)从“暴力血腥”走向“温情宽厚”
1987年,余华发表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其风格诡谲怪诞,惊悚怪异,引起文坛关注,之后的《一九八六》中历史老师的疯狂行径以及妻女的冷漠可怕,《现实一种》中家庭内部的相互残杀等将余华贴上先锋作家的标签。此时余华手中的笔像一把犀利的刀,用夸张变形的手段彻底地抖出丑恶、阴暗、残酷的一面,同时他那绝对冷漠、旁观、残忍的叙事态度也使人不禁发出“他的血管里,流动的一定是冰碴子[1]”的呼喊。但是余华是一个不断思考的作家,他明确表示过“一成不变的作家智慧快速奔向坟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和喜新厌旧的时代”。[2]因而20世纪90年代,他迅速抛出 《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力作,这些作品中,原本那种冷酷的情绪逐渐消解了,代之一种脉脉的温情。比如《细》中孙光林与父亲和哥哥孙光平之间的关系,在仇恨不屑中带有一丝的温暖。文中有这样的描写:“我”考高中时哥哥孙光平帮我还考试费,并送我去学校,父亲在母亲死后深更半夜去母亲坟地哭泣。《活着》中福贵面对着七位亲人一个个地离去,以及命运对家人的捉弄,没有怒骂、凶残、报复,而是选择了忍耐和接受。透过他的笔触可以看出,余华20世纪80年代的“愤怒和血腥”在岁月长流中逐渐化为一种脉脉温情与舒缓包容。
(二)从“人性恶”走向“人性善”
支撑余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人性恶”。他在前期作品中强力表达了“人性恶”以及由这种恶衍生的暴力和死亡。无论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人们对“我”前行不能提供任何帮助还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想搭车却被吆喝滚开,以及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却不被司机认可的传统观念的破坏和模糊,都使我们看到人性恶的一面。《现实一种》则赤裸裸地表现出人性的恶,皮皮将堂弟摔倒地上,却有一种快感,显然暗示着“恶”从孩童年代便衍生出来。进入90年代,余华开始怀疑并改变“人性恶“的观念,走向民间,发现了“人性善”的光芒。1991年创作的《在细雨中呼喊》,在展现人性恶的同时,也赋予作品强烈的悲悯意识,祖父的死让父亲流泪忏悔,哥哥对我考上大学倾力相助,哥哥背病重母亲进城求医,以及临别时交代妻子“照顾好儿子和娘”等一些细节,在之前作品里是不曾看到的,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复杂,在恶之外还是有善良的一面。人性善的一面在此后不断得到强化。《兄弟》中,宋凡平和李兰半路夫妻结合,不动声色的深情之爱,李光头和宋刚“有饭一起吃,有衣服一起穿”的朴素亲情,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三)从“支离破碎”走向“家庭重建”
对于中国人来言,“家”是中心,是维系人生而为之的原始动力,也是维系感情的最重要的场域。作家创作的转型,必然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发生微妙变化,而这些变化直接作用于家庭结构的重新构建。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作品,余华作品中的“家”是支离破碎的,家仅仅是个空壳。《现实一种》中山岗和山峰两兄弟关系冷漠,彼此是幸灾乐祸的;与妻子间的关系是暴力的,残忍的;与母亲之间是隔绝的,互不关心。到了90年代,余华笔下的家庭重建了。福贵对妻儿的疼爱,儿子的死让他痛不欲生,但为了妻子家珍的身体,而不告诉她实情,独自默默承受着丧子之痛;为了哑巴女儿凤霞的尊严,福贵举起了手中的石头,女婿死于工伤之后,年迈的福贵默默承担起抚养下一代的重任,以及福贵与妻子之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感情,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家,一个有着深厚爱和呵护的家真实地存在着。许三观一生十二次卖血,除了第一次将钱用来娶妻之用,其余几乎都是为了家庭和他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正的家庭,它不是单纯的框架,而是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爱和牵挂,是人心灵的真正栖息地。至此,余华笔下的家庭得到重建,成为他转型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四)从“启蒙立场”走向“民间立场”
早期余华的写作,基本上可以归属于启蒙立场,对社会始终保持着一种警惕,并对现实的一切现象持批判态度。《此女献给少女杨柳》看似讲述国民党军队撤离时在小城埋下的十颗炸弹的故事,实则是对现实生存环境危机四伏的隐喻。《河边的错误》中通过讲述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子杀人的案件,表达了知识分子阶层对社会秩序的忧虑。余华以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启蒙意识审视这个社会,直至竭尽全力地用暴力和凶残使人们感到震惊和惊醒,从而试图唤醒麻木的大众。90年代的余华,创作突然转型,他带着寻找生机的企图走向民间。他开始与笔下人物从心灵上进行沟通,开始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以平民的意识反映他们的生活。《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历经了人世间最惨烈的悲痛,但他依然固执而顽强地活着,这是一种卑微、沉默、痛苦、执著的生命存在,却折射出生命的光彩,这是一种民间的智慧,是余华积极探索的结果。余华以转型后作品表达了他民间立场的坚决性,也表达了对大部分平凡的中国人的生命态度的一种体察,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他在民间化的文学形式下传达最现代的生命观念,并在传统与先锋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
二、从诡谲中走向平实——余华小说艺术运筹的转型
(一)叙述姿态:从冷漠屏蔽走向温情关怀
余华之所以能够成功转型,首先归功于他的叙述态度,由冷漠屏蔽到温情关怀。90年代以前,余华作品中作者充当着绝对冷漠的叙述者,他像一个刽子手任意安排着笔下人物的命运,暴力、血腥、死亡笼罩着他们,同时“零度叙事”姿态,使得90年代之前创作的作品,无论是《世事如烟》中一连串阿拉伯数字代替的人物,《十八岁出门远行》中面对世界的荒诞和诡异,《鲜血梅花》中对武侠庄严的颠覆,《现实一种》中亲人间相互残杀,等等,都能够看出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是完全受控于作者的,没有个人情感。但到了1990年以后,他开始从残忍和诅咒里急流勇退,在叙述的虚构中,让自己的声音逐渐消失,更多考虑笔下人物的声音。在《活着》中,我们则已清楚看到闪耀着美丽光环的人物形象:福贵毅然地承担起了赡养父母和照顾妻儿的重担;家珍善良勤劳,对福贵不离不弃;凤霞美丽善良;二喜憨直勤劳;有庆天真可爱;老母亲对日子会一比一天好起来的向往……这里人物的形象是丰满的、立体的,正是因为作家写作态度的转变,给予了笔下人物“发声”的机会,因此作家从过去“想象中的现实”走到了“现实本身”,实现了创作转型。
(二)叙述语言:从暴力消解走向简单幽默
余华80年的创作,基本上打破了完整的故事性和情节的连贯性,在语言上总是试图以晦涩、暴力、血腥来引起社会的警醒。《一九八六》中疯子的自残过程被表现得酣畅淋漓,而血肉模糊的自残场面又是那么令所有人心惊肉跳,再嫁的妻子精神崩溃,女儿的生活也变得沉闷枯燥。叙述语言在幻觉与现实、过去与现在之间不停地转换和跳跃,小说叙事被引向疑难重重的“实验性”领域。后期余华的创作语言便明显地走向了简单幽默,《活着》中写道:“凤霞是个好孩子,到了那时候也没哭,只是睁大眼睛看我,我伸手去摸她的脸,她也伸过手来摸我的脸。她的手在我脸上一摸,我再也不愿意送她回那户人家去了。”[3]没有骨肉分离的渲染,没有跌宕起伏的心理描写,只是寥寥几笔就将父女亲情的温馨和浓郁呈现在我们面前,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许三观卖血记》中,困难年代,许三观用嘴给孩子炒菜吃,“你们就用耳朵听着吃了,你们别用嘴,用嘴连个屁都吃不到,都把耳朵竖起来,我马上就要炒菜了”[4]。这些幽默性的话语,把许三观那种幽默、乐观而豁达的性格表现得一览无余,生活的沉重和悲凉变成了一幕活生生的幽默剧,生活的悲剧被喜剧的场面所冲淡,沉重感被缓解了。
(三)叙述视角:从多重繁复走向单纯有限
余华先锋时期的小说叙述视角是多重的、复杂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运用少年视角,以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来看待社会的纷繁复杂,同时在少年的背后还隐藏着叙述人作者。《一九八六》则提供给我们一个偏执狂、精神病的视角,叙述视角不断地在疯子、观众、妻子、女儿身上跳跃,多重而繁复。90年代后余华的创作,在叙述视角上开始走向单纯有限。《活着》虚设了一个民间采风的文化馆馆员,整个故事都是通过小说主人公福贵第一人称的有限叙述视角讲述,这个时候作品中叙述视角已经转换为单一的。《许三观卖血记》叙述视角是第三人称,到了《兄弟》,叙事视角又变成了“我们刘镇”,小说通过“我们刘镇”见证李光头这个顽童如何成长为一个名人大亨。至此,余华小说叙述视角进行了彻底的改变。余华认为,一位艺术家最大的美德是两种,一种是单纯,一种是丰富。假如有人同时具备了这两种,他肯定是大师了。余华做到了,在他小说中重复是一种单纯的美,而这种单纯又是和丰富联系在一起的。
三、困境与突围:余华小说转型的驱动力
(一)中国先锋派的集体退潮
“当先锋文学确立了他在社会文学中的合法地位,渡过了苦难历程,并被社会普遍接受之后,先锋文学的使命即告终结。”[5]中国的先锋文学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宿命。“文革”之后,中国新文学开始蓬勃发展,先锋文学继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之后,迅速出现在文坛上并掀起浪潮。实际上,中国的先锋是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的夹缝中生存,当被逐渐承认时,先锋派也已经接近偃旗息鼓了。照搬西方先锋文学技巧,极度地应用在文学创作中,一度只重视抽象的形式主义试验,使得他们不再能够表现直接的现实生活,现实隐退到了叙述结构、感觉和语言的背后,很容易让先锋文学只是短暂地引起文坛兴趣,而其本身创作生命力的衰弱,最终将自己逼上了形式主义的绝路。正如余华自己说:“几乎所有的大家,我们发现,无一例外,刚开始都是先锋,慢慢地都变得朴素,都走着这样的一条道路。”[6]所以先锋文学的创作路线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有长远的生命力,因而寻求改变是必要的。
(二)作家创作观念的自我转变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捉摸不定与喜新厌旧的时代,事实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理论写作的作家是多么可怕,而作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在于经常的朝三暮四。为什么几年前我们热衷的话题,现在已经无人顾及。是时代在变?还是我们在变?这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却说明了固定与封闭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作家的不稳定性取决于他的智慧与敏锐的程度。作家是否能够使自己始终置于发现之中,这是最重要的。”[7]余华在给自己前期作品做总结的同时,也预言了他以后的创作走向,表明了他是个不断求变的人。即使是在前期先锋创作,他也没有脱离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因而当一直秉持一种创作模式并且出现写作困境时,必然“穷则思变”。余华曾谈及自己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感,而这紧张感在创作《活着》时得到改善,所以不论是出于对先锋退潮的忧虑,还是余华自身在处理与社会、与作品中人物之间紧张关系的调整,都表明作家创作观念不断求变,因而余华转型也是必然的。
(三)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催产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社会大背景是不相同的,不同环境给予文学不同的生存土壤。80年代之前的十来年时间,文坛死气沉沉,而新时期的到来,让文学开始有了自由开放的机会,仅几年时间,国外几十年的文学思想如大浪般一涌而来,文坛一下子活跃起来,各种思想被争先恐后表达出来。同时80年代人们急于表达个人思想,对“文革”岁月进行控诉,对人生价值进行怀疑,对人生虚无进行肯定。但到了90年代,社会文化背景发生巨大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让文学创作环境出现了新的特点,这时人们的激情慢慢退却,开始拒绝激进的反叛和狂妄,平和地与当下现实进行友好握手。另外,90年代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大众文化消费群体的读者,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他们更希望读到一些与现实紧密联系的作品,而一旦他们对叙事技巧开始“厌烦”,不再产生兴奋之后,便将目光转向了通俗文学。不可否认,90年代给文学创作带来挑战,作家必须考虑市场和读者的接受情况,而这也是余华转型不可忽视的外界因素。
[1]朱玮.余华史铁生格非林斤澜几篇新作印象[J].中外文学,1988,(3):29.
[2]余华.余华作品集(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3):289.
[3]余华.活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10):56.
[4]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11):71.
[5]余华,潘文凯.新年第一次文学对话[J].作家,1996,(3):22.
[6]孟繁华.九十年代:先锋文艺的终结[J].文艺研究,2000,(6):12.
[7]余华.河边的错误[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12):39.
I206.7
A
1671-2862(2016)03-0067-03
2015-12-24
张晓敏,女,山西运城人,辽宁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