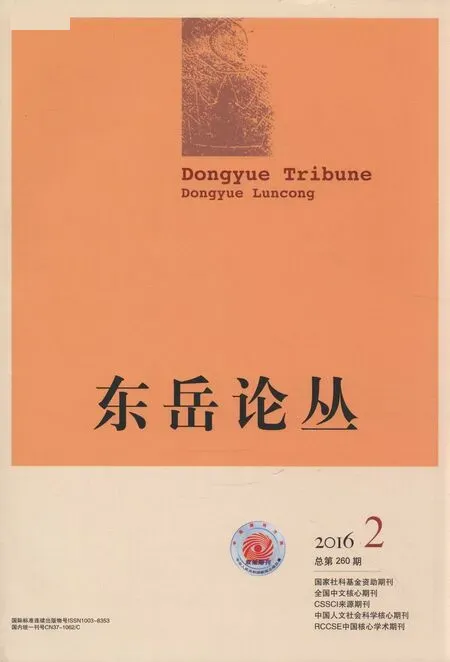《狂人日记》的哲学寓言形态及其意义
郭 帅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鲁迅研究
《狂人日记》的哲学寓言形态及其意义
郭帅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显示了他对文学“形式”的选择与创造。狂人发现“吃人”真相,是一种哲人的反思过程。反思性的内容与“日记体”的层级形式,共同形成《狂人日记》的哲学言说形态。《狂人日记》借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具有哲学寓言的形态特征。理性往往淹没个性,假如没有哲学寓言形态,《狂人日记》的内涵则无法明显区别于当时的启蒙言论而达到震撼人心的程度。《狂人日记》的“格式”是“表现”得以“深切”的凭借。这种哲学寓言形态使《狂人日记》成为鲁迅小说启蒙母题的一个发源。
《狂人日记》;鲁迅;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鲁迅自述的“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①《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是对其小说较为经典的价值判断。这则判语,在我们的接受中,常被视为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形态,即“表现的深切”单指向内容方面,“格式的特别”单指向形式方面。也就是说,鲁迅小说,既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又具有特别的形式感,在“内容/形式”两方面,鲁迅的小说均达到了现代小说的高峰。因而,当具体分析鲁迅小说的价值时,“内容如何,形式如何”的二分法,成为较为常见的思路。然而,把小说分为“内容/形式”的二元格局,会损害其整体性价值。部分对于整体才有意义,正是这两方面乃至多方面的有机整合,才形成了鲁迅小说的整体特色,才最终显示了鲁迅小说的力量。《狂人日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一、“狂人”的哲人身份与言说方式
鲁迅对新文学的思考,从日本时期就已经开始。所以,他为《新青年》做的第一篇创作,包含着他深思熟虑的内容。据周作人所说,鲁迅关于《狂人日记》的“吃人”思想,早年便已形成,只是缺乏一种合理的文学形式将它呈现出来②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可以说,《狂人日记》特别的格式,是鲁迅为他早年的思考所精心选择的表现形式。
独特的《狂人日记》,既与当时所出现的论文和诗歌小说相异,又与鲁迅之前创作的杂文和论文相异,这一点在《狂人日记》发表后便为批评家注意,茅盾认为它有“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③雁冰:《读〈呐喊〉》,《文学》,1923年第91期。,偏重于《狂人日记》的形式;成仿吾认为是“自然派所极主张的记录”,“假的写实主义”④成仿吾:《〈呐喊〉的评论》,《创造》季刊,1924年2卷2期。,则看到了《狂人日记》中类似政论的理念言说;后来,也有人认为是意识流。总之,已超出了写实主义的范畴。的确如此,在《狂人日记》中,没有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和空间,人物大多没有名字,“赵贵翁”“陈老五”这样高度隐喻性的称谓其实是泛指。情节上,则更是非现实主义的怪诞:“吃人”与反“吃人”。即使狂人发现“吃人”真相的方式,也是非现实主义的: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25页。
狂人是第一个发现“吃人”真相的人,但他的发现方式实在是匪夷所思,不是被告知的,也不是他看史书得来的——真实的字缝中怎么可能有“吃人”二字。狂人的这种发现,不是历史研究上的“文本细读”,而是他对于史书的经验论归纳,是一种顿悟,是长久的思考和突然的看破。小说中写狂人“睡不着”“想个明白”“翻开历史”“看了半夜”等,为这种顿悟提供了一种哲思的环境和氛围。
小说正文虽然是狂人的十三则日记,但是其中第四、八、十、十一则,其描写的生动和现场感,已经不像是私语性的日记,更像是充满叙事动作的小说。而其他的日记,才更像是日记,因为这些日记用高度私人化的语言,记述了私人化的思想流动,并同时在反思第四、八、十、十一则日记所记载的事情,这种情况,可参考如下的对比: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了我点头,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第八则——笔者注)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第九则——笔者注)
从动作转向心理,从现场转为叙述,《狂人日记》的这种文本内部的层次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反思”结构,也就是说,狂人是通过在夜深人静的夜晚,不断地进行反思,最终发现了“吃人”的真相。而且,狂人对于“吃人有罪”的认识是完全自觉的。可以说,狂人具备了哲学发现的条件,他的思考方式,类似于哲人。
狂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近于现象学的方式,属于一种哲人式的“反思”。无论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以胡塞尔现象学为基础的存在主义,还是黑格尔的现象学,都以“我思故我在”的“反思”行为作为其学说的立论基础。在现象学看来,客观的“物自体”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存在,正如狂人所看到的“亲情”“史书”并非“存在”。真正的存在是“我思”,是“自我意识”,即主体对物自体的思考与反思,也正如狂人对“亲情”“仁义道德”的反思一样。正是这种“我思”的形式,确立了“我在”的事实,也就是说,现代哲学家们,是在“反思”的行为中,不断发现与描述着现代“人”的存在境遇,其中并不乏“吃人”似的颖悟。
学术界之所以指认《狂人日记》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源头,主要因为它代表着中国现代小说所谓“现代性”的确切的发生。狂人的发现,在现象学的视野中,正是一种“现代性”的发现,是超越性和创造性的发现。他的表述,也是创造性的。我们很清晰地看到,小说中的狂人与他的大哥等人完全无法实现“对话”,比如:第八则中,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的青年,对狂人的“吃人的事,对么?”“从来如此,便对么?”的问询,基本不做回答也无法回答;第十则,狂人力劝大哥改过,大哥起初是莫名其妙,其后便认定狂人疯了,“疯子有什么好看!”狂人与周围人的对话出现“断裂”。这种“断裂”,凸显出异质的一端。
狂人在“断裂”之下的不断言说,正带有着哲学家的悲悯情怀。然而,这种具有英雄气质的个人,通常是孤独的,因此命运也通常带有悲剧性,正如鲁迅认为狂人“是个人对庸众的宣战”,“要独立,要与众不同,藐视当时的社会,逐步变得悲观”*《随感录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第311页。。这种悲剧性的烈度往往会突破文本的叙事框架,在文本之外参与形成一种说服机制。卢卡奇就认为史诗中的个人与小说的英雄具有互文性,“严格地说,史诗中的英雄绝不是一个个人。这一点自古以来就被看作史诗的本质标志,以致史诗的对象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共同体的命运。”假如说史诗中的个人所象征的是一个共同体的本质核心,那么小说中的英雄则代表着一个“心灵近似者”群体的理想诉求,显然,《狂人日记》具备了这种品质。卢卡奇就发现几乎所有伟大史诗与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孤独的:“社会首脑人物是唯一的,其内心的冲突,在保持象征性生存的感性假相时,仅仅从悲剧性的难题中产生出来;因为,只有这种首脑人物才能在其外部的表现形态中具有孤独意义的必要气氛。”*卢卡奇:《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燕宏远,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9-60页。卢卡奇所说的“悲剧性难题”,在《狂人日记》中可被指认为“救救孩子”的悖论。不过,《狂人日记》的言说方式与一般小说(史诗)描绘与哲学论述不同,它以糅合小说叙事与哲学言说的形式,描述并隐喻了这种“悲剧性难题”所造成的“孤独意义”,因而,狂人作为小说主人公,总能够非常轻易地突破小说文本的框架而获得某种独立性。
狂人身份的独特性,在与果戈理《狂人日记》的比较中更加突出。在“日记体”的形式方面,鲁迅对果戈理同名小说《狂人日记》的借鉴是非常明显的,但又是极为有限的。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狂人”和波普里希金在精神气质上大相径庭。狂人的言说含蓄蕴藉,内中充满了反思精神与创造活力;波普里希金的言说更像日记体故事,叙事成分得到强化,充满了现实生活内容。所以我们会认为狂人是“佯狂”,而波普里希金是“真疯”。进一步而言,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佯狂”后的启示与反思,而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是一个疯癫者的生活实录。鲁迅的《狂人日记》,其张力结构正是狂人的“身份”和狂人的“发现”共同形成的,这种结构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鲜见,在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狂人一般的一些人,而诗人和哲学家中,往往更容易找到这样的人,鲁迅也认为狂人“大抵有几分天才”,又有“几分狂气”。从一定意义上说,狂人就是诗人和哲学家的雏形。
二、取法《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哲学寓言结构
《狂人日记》在形态上与西方现代哲学的相通,不是偶然。鲁迅深昧中国小说传统,但在《狂人日记》中,存在主义式的思想与特别的反思结构所共同形成的文本形态,显然已经远超中国古代小说思想与形式的边界。周作人认为鲁迅的“礼教吃人”思想早已形成多年,却迟迟不发。而一出手就是形态奇特的《狂人日记》,是否就是因为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
学者张钊贻曾这样回忆:“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在香港,刚对现代文学产生兴趣,开始读鲁迅的书。有一天下午,在旧书摊看到一本《苏鲁支语录》,随手翻翻,不禁惊愕不已,何其相似!简直以为自己是在读鲁迅。于是毫不犹豫掏出午饭钱把书买下。”*张钊贻:《沉迷鲁迅、尼采二十年 著译者言》,《读书》,2002年第7期。有很多读者曾有过类似的感受和表达,那就是,鲁迅和尼采的许多言说方式十分相像。
张钊贻认为,鲁迅在日本时期,至少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传》(即“登张竹风收有《弗里德里西·尼采论》的《尼采与二诗人》”)、勃兰兑斯的《尼采导论》接触到了尼采的相关学说*张钊贻:《早期鲁迅的尼采考——兼论鲁迅有没有读过勃兰兑斯的〈尼采导论〉》,《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6期。。这些书目以及日本当时的“尼采热”,让鲁迅对尼采学说的深刻理解成为可能,而且,也为他从更新的角度考察中国问题提供了方法和时间。鲁迅归国前夕的诸论文中,尼采的影响已随处可见。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表达了对尼采学说的部分认同。《摩罗诗力说》“题记”就是尼采的话:“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深渊,其非远矣。”*《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3页。鲁迅前期的创作受到尼采及其代表性哲学文本的影响,是确切无疑的。
《狂人日记》最为明显的是受了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影响。关于“超人哲学”的基本观念,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行为与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尼采的“权力意志”,是“超人”得以实现所凭借的最终事实与有机世界的本质。人要克服自己,需要“重估一切价值”,也就是对西方的道德、文化、宗教以及生命状况进行彻底的反思,尤其拒绝一个普遍、统一、绝对的道德体系。在《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意识,正在于对东方文化的价值基础进行强有力的反思。可以说,“反思”,正是狂人和超人通往真理的共同途径。
而小说《狂人日记》所使用的这种“日记体”形式,很好地为狂人的“反思”提供了必要的结构。日记的形式与主人公“迫害狂”的身份,为狂人高度主观化地用第一人称表达曲高和寡的理念,提供了文本便利。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能发现文本中鲜明的层次感和隐约的撕裂感,尤其是小说后半部分的理念叙说部分显得有些浮露。事实上,鲁迅采用日记体的方式来写小说,而且这些日记在日期上并不具有连续性,便先在地内含着叙事弱化的危险,换句话说,在鲁迅对小说的预设中,“故事”并不被凸显,动作性被弱化,“故事”的讲述者独大,对话和理念增多,这些做法,明显对小说的叙事功能有所偏离,因而在当时会使人感到不适应,感到“特别”。所以,《狂人日记》是鲁迅的一次策略性的写作,它的“表现的深切”主要借助于“格式的特别”——“日记体”——来实现。
这种日记体,也多从尼采处得到了灵感。在鲁迅的笔下,“狂人”的诸多思想主要来自于尼采的超人哲学,然而这种思想较为突兀,一般的文本装置很难容下。对于尼采本人而言,也是如此。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同样“格式特别”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这部书中,尼采用“非直写主义”探索着“超人”的精神世界。鲁迅曾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中反复引用它的内容。毫无疑问,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之前已经受到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哈罗德·布鲁姆将后代诗人从前辈诗人那里所受的影响分为六种类型,《狂人日记》所受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在形式方面基本上可以归入“苔瑟拉”(Tessera),即“续完和对偶”,“这是一种以对偶方式对前驱的续完,诗人以这种方式阅读前驱的诗从而保留原诗的词语,但使它们别具他义”*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页。。布鲁姆认为,修辞学意义上的对偶,使后代诗人保持了与前辈诗人的“核心关系”。鲁迅的整个文学生涯受到尼采的极其大的影响,至少在前期,他与尼采保持了一种较为紧密的“核心关系”。而这种“核心关系”的维持,依靠的正是鲁迅对于尼采的“续完和对偶”。尤其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种尼采式的“非直写主义”形式对鲁迅的影响特别大。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对这部著作的借鉴是非常明显的,关于进化论的很多论述就是横移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形式上,《狂人日记》的“日记体”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相似性也更显而易见。
在形态方面,《狂人日记》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以及《关于更高之人》《关于新旧牌匾》《关于背叛者》等众多篇什存在四点相似:一是两者都无具体时间与空间,忽略环境与背景交代,然而通过文本的隐喻功能,我们可以掌握其时空所指;二是两者都以“则”的形式组成,并且则与则之间的字数乃至语气并不相同;三是二者都是以主人公的反思和对话来构成全篇;四是在人物序列上,二者都建构了主人公与他者(即群众)的紧张关系。在人物选取方面,查拉图斯特拉是古代波斯火神教的教主,是一个上帝式的人物,天生具有神觉,这种神觉却是逆反的,他对于美德、死亡、身体、激情、偶像、贞操、邻人等等的表述,都有悖于时,而狂人虽不是传奇人物,但他的“迫害狂”使他同样具有“神觉”,这种“神觉”同样是逆反的,他对于亲情、道德、死亡等的感受和表述,更是石破天惊。在语言方面,两人的表述都是高度隐喻性和抽象性的,都形成了与周围民众的言语的断裂。甚至在题目的选取方面,《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狂人日记》也具有相似性,都直白明晰地强调了主人公对言说动作和内容的主体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鲁迅亲自翻译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部分,他的翻译工作可能更有助于他具体体会并借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艺术特征,尤其是言说方式方面*特别注意的是,《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最初发表于1920年9月,据《鲁迅日记》记载,他对该序言的翻译工作截止时间为1920年8月10日夜:“夜写《苏鲁支语录》迄,计二十枚”, (《鲁迅全集》第14卷,第393页)但开始时间并无交代。笔者结合其他资料,也无法确定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与翻译《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时间的先后,因此只能视作平行关系。。仅以序言而论,《狂人日记》与其有几点相似:两者则数相近,《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分为十则,《狂人日记》分为十三则;两者都由主人公的自述与对他人的谈论组成;两位主人公的语言非常晦涩,多用譬喻;两位主人公都试图说服群众却终于失败*唐俟:《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新潮》,1920年2卷5号。。在翻译时,鲁迅就对该序言的言说方式特别注意:“尼采的文章既太好;本书又用箴言(Sprueche)集成,外观上常见矛盾,所以不容易了解。”显然,鲁迅早已经意识到该序言“极好”的内容与“箴言”的形式所形成的“外观上的矛盾”,造成了“不容易了解”,因而在《译者附记》中专门介绍“含有意思的名词和隐晦的句子”*鲁迅:《〈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者附记》,第439页。原载唐俟:《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新潮》1920年2卷5号。——鲁迅翻译《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所使用的语言方式显示了他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在《狂人日记》中也有明显的表现。所以,假如有人把《狂人日记》翻译成外文的话,大概也需要像鲁迅翻译《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一样,对《狂人日记》中“不容易了解”的“含有意思的名词和隐晦的句子”专门作一个《译者附记》来说明吧。
三、母题发源:《狂人日记》形态学的意义
《狂人日记》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相似性,综合起来看,形成了《狂人日记》的形态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类似于尼采哲学的“非直写主义”表述形态。换句话说,《狂人日记》的形态,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般通过诗学的方式,具有了高度抽象的哲学功能。同时,尼采之于鲁迅的“影响的焦虑”很好地被鲁迅加以解决:如果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表述指向哲学,那么,《狂人日记》的表述更内蕴了民族国家意识。
《狂人日记》的哲学寓言的形态学,以内敛性的私人话语涵括外倾性的理念意图,使鲁迅较为容易、抽象、概括地表达他对于当时民族国家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就像查拉图斯特拉通过寥寥数语就对人类、上帝、未来和时间等命题进行概括一样。然而,类似于《狂人日记》的这种表述形态,在《呐喊》《彷徨》中再无复现。也许,这样的文本本来就不需要太多,一个就足矣。《狂人日记》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乃至整个文学生涯中的独特地位,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开端,更是一个伟大的思想策源地,它以哲学形态统摄着其他的小说主题,尤其在“启蒙”主题方面,更是如此。
鲁迅的几乎所有小说仿佛都在呼唤着“真的人”的出现,“人”的“非圆满”状态,成为他的小说的内在焦虑。这种焦虑及其解决,以启蒙主题为外观,不断被重复,最终形成了鲁迅小说的一个母题。这一母题,发源于《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演绎了这个母题的哲学形态。鲁迅的很多其他小说,几乎都能在《狂人日记》找到源头。
然而,《狂人日记》乃至《呐喊》所体现的民族国家意识内涵,并不十分特别。杰姆逊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普遍具有这种焦虑。李泽厚认为鲁迅对于启蒙的观点与瞿秋白陈独秀等人相比并没有特异之处。《狂人日记》等所标志的启蒙思想并不具有原创性,至少可以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早期论文中找到源头。也就是说,《狂人日记》以独特的形式,包含的是对鲁迅个人和新文化运动诸君而言并不独特的思想内容。
当理性成为一种即使流行在小范围内的“共识”时,理性也常常反而会淹没个体的个性。《狂人日记》的脱颖而出,可能主要因为在形式方面显示了鲁迅的创造性,以及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贡献。
与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新文化者以论文“正面攻击”相比,《狂人日记》显然更能对青年人的心灵造成冲击,身临其境地看,这才是《狂人日记》的“深切”之表现。余英时认为,从谭嗣同的《仁学》到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实践,主要表现为一种理念的叙说型的“正面攻击”,“鲁迅用新文学的笔触揭露纲常名教的残酷性的一面”,其“吃人”的概括远远超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而笼罩了全部中国文化的传统”,但与谭嗣同、陈独秀等人的论说宣讲不同,鲁迅的《狂人日记》传达出一种“感人的力量”*余英时:《中国近百年价值观的变迁》,《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一直关注并参加《新青年》反对礼教的主攻手吴虞,在读过《狂人日记》之后写了《吃人与礼教》一文,毫无讳言地表达了《狂人日记》对他的震撼:“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1919年六卷六号。鲁迅在谈到《狂人日记》等小说的成功时,也认为这些小说“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因此可以说,《狂人日记》以文学的形式将反传统的内容更为有效地表达了出来,诗学与哲学凝为一“体”。这种有效,在于小说对一种“度”的把握:既不削减批判传统的深度与烈度,又拒绝流于理念的申诉,既要使文本具有直指人心的效果,又不能过于含蓄深沉。《狂人日记》以高度浓缩的哲学寓言形态,恰恰满足了这种历史性的要求,文学虚构与理念言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在文本内部保持了难得的平衡。如此一来,在陈胡等人的论说启蒙之外,《狂人日记》让人们看到了以小说(文学)进行启蒙的可行性——属于鲁迅的时代到来了。
鲁迅的启蒙思想,也正是借助《狂人日记》式的虚构性文学,才具有了一种深度模式,才真正具有了“深切”的性质。李泽厚曾认为鲁迅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启蒙,他独有的“孤独和悲怆”具有两方面的内涵,一个方面是“形而上的人生意义的感受和寻求”,另一方面则“具有非常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 正是这两者结合交融才构成了鲁迅的个性特色。“因为有后一方面,鲁迅才不会走向纯粹个人主义的超人幻想,才不是那种纯粹个人的失落感、荒谬感、无聊厌倦和脱离现实。因为有前一方面,鲁迅才没有陷入肤浅的‘人道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中,而忘却对个体‘此在’的深沉把握。”*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但是,具体地考察鲁迅的《呐喊》《彷徨》,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方面在鲁迅的小说中并没有完美地实现平衡,鲁迅有时会着意突出其中一个方面,这种文本创造的可能,在《狂人日记》中已有显现。它以高度抽象的哲学寓言形式涵括的启蒙主题,成为之后的启蒙小说的源头,而它的这种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种文本只能是独一无二的,否则便会相互消解。后出的启蒙小说基本都是从这个源头裂变而来,所以我们谈论鲁迅的小说,总能从《狂人日记》出发,又总回到《狂人日记》,就像我们谈论新文学,从鲁迅出发之后,又总是回到鲁迅一样。
鲁迅早年曾十分确信尼采式的“超人”的实现:“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随感录四十一》,《鲁迅全集》(第1卷),第325页。所以,鲁迅并没有让狂人绝望,也没有让狂人死亡,而是让狂人“赴某地候补”。值得玩味的是,“赴某地候补”的狂人,在《狂人日记》单个文本的叙述中,我们会认为他被“治愈”后异化为“吃人者”。然而,若是把“赴某地候补”的狂人放在整个《呐喊》《彷徨》中来看,他可能有别的际遇:他可能变成了魏连殳和吕纬甫,也可能正在回“故乡”的船上,也可能与一个叫子君的女子谈了一场恋爱,也可能做官不利,流落咸亨酒店去做了一个识字先生,没有名字,被人叫做“孔乙己”——也就是欧阳凡海等人所认为的《狂人日记》中人物的“毛坯”性质。总之,《狂人日记》为“后起的‘狂人日记’”提供了多种开放性的主题可能。
[责任编辑:曹振华]
郭帅,男,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
I210.96
A
1003-8353(2016)02-0121-06